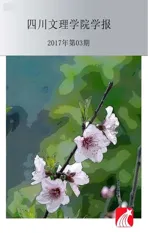“何事长向别时圆”的喟叹
——苏轼诗意人生的生命美学价值
2017-04-14范藻
范 藻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四川达州635000)
“何事长向别时圆”的喟叹
——苏轼诗意人生的生命美学价值
范 藻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四川达州635000)
有宋一代著名的文艺大师苏轼,置身变革的时代,面对苍茫的天地,在诗意人生的千古谓叹中,思考着生命意义的永恒追问。从得意与失意的人生经历、全才与天才的文艺成就、出世与入世的哲学思想、生命意义的永恒追问四个方面,探讨苏轼诗意人生的生命美学价值所在。
苏轼;诗意人生;生命美学
一、引言:诗意人生的千古喟叹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每一个时代都会耸立起一座以某一伟大诗人为代表的文学高峰,战国有屈原、魏晋有陶潜、唐代有杜甫,那么宋代呢,毫无疑问就是苏轼了。正如王国维所谓的:“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1]当代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以“苏轼的意义”为题,说他不仅是那一时代“文艺思潮和美学趋向的典型代表”,而且对他以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2]几乎是空前绝后,更是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段历史的苏轼,中国文化史上的旷世奇才,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代天骄,中国思想史上的三教合一,他神奇的文笔、多样的才艺、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思想、高尚的人格,还有他那对生活的深挚热爱、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对生命的深切体悟,这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苏轼”。
这一切在他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得到了典型的体现: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这丙辰中秋之夜,万家团聚之时,他在一一追问“明月几时有”“今夕是何年”“何似在人家”而不得解后,终于向着这“阴晴圆缺”的月亮和“悲欢离合”的人生发出了质疑:“何事长向别时圆”,你这郎朗的明月,为何总是亲人分别时,才如此的皎洁圆满?与其说这是巨大而深重、悲切而沉重,甚至是宏丽而隆重的质询,不如说是深切而忧伤、无奈而忧愁、甚至就是悲悯而忧郁的喟叹,其中包含的是渺渺的“天问”与悠悠的“人事”之间强烈的反差和不协调而碰撞出的电光石火般的悲剧意识,由此构成了苏轼执着与旷达、忠诚而反叛、浪漫又现实、敏捷还愚鲁的悲喜交加的“诗意人生”。的确,诗酒相伴、情感丰富、才华横溢的“诗意人生”所闪耀绽放出来的生命之美的成因和底蕴、特征和风采、意义和价值、启迪与昭示,必须上升到生命美学的高度,方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下”,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迷失于他所指陈的观察误区和思维死角:“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那就让我们从“何事长向别时圆”的喟叹中,开始苏轼诗意人生的生命美学解析吧!
二、兹游奇绝冠平生:得意与失意的人生经历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写于元符三年,即1100年,这年5月新登基的皇帝宋徽宗赦免了他,6月20日他横渡琼州海峡,离开了他生活三年零八天的海南岛儋州,其时,他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打击和变故后,已经垂垂老矣,生命的烛火即将熄灭。这首诗就是写渡海北上那个晚上的情景。同样是这轮明月,“云散月明”而色泽朗朗清清,“天容海色”而人生清清白白,尽管遭逢人生的这次最后厄运,反而是他生命最美好的一次游历,全诗充满着屈原九死不悔的倨傲性格和渊明旷达豪放的乐观情怀。1101年,他溘然长逝,可谓功德圆满。
这位诞生于1037年的大文豪,生长在物华天宝,地灵人杰的四川眉山的一个书香之家。少时天资聪颖,曾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幅对联:“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被传为佳谈。在母亲言传身教的启蒙下,饱读诗书;在父亲耳提面命的教诲下,正直勤勉。应试及第,名满京城。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不及二十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把他判为第二;殿试时,他又献上二十五篇进策,深得仁宗皇帝的欢心,被评为翰林学士。以后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初步展示了他理政抚民的才能,期间初尝官场争斗的苦,又历经了父亲和妻子的的去世,一度身心疲惫。熙宁元年(1067年)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由于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皆以诗文名世,然而两人的政治观点和改革思路相左,王安石施行新法,大刀阔斧,而苏轼主张“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只好调任杭州通判,公务之余,结交知己,游山玩水。三年后,调任密州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创作出了诸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名篇。不久他遭受了人生最大的挫折,元丰二年(1079年),因被人告发“文字毁谤君相”,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几次濒临死刑,后判流放黄州。次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开荒种地,乐观豁达,身处仕途的低谷,却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圣地。四年后,他恢复名誉,召回朝中,先后出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要职,因不容于新派和旧党,他调转任杭州知事,元祐七年(1092年)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旋即升为礼部尚书。由于抨击了旧党的腐败,又遭到了诬告陷害,绍圣元年(1094年),被贬岭南惠州,后放逐到了海南岛的儋州直到1100年才赦免。
就是在这种得意与失意交织的人生历程中,他宦海沉浮,历经沧桑。在65载岁月里,或少年得意,或仕途坎坷,或金榜题名,或生活窘困,但他始终未曾颓唐丧志,一直坚强的活下去,并活出了精彩和风采。如果说得意是生命的正能量,那么失意则为生命的负能量,正是因为二者的交替出现,此消彼长,才呈现出一个真实而鲜活的生命个体。如果说这样的经历本身就具备了传奇般的人生美,那么最后能够融合二者,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即生命的能量正负抵消后,充满风轻云淡般的恬静和自然,这才是真实而超迈、稳健而洒脱的生命之美。正如他在《定风波》最后表白的那样:“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的,苏轼“归去”了,去了一个没有世事纷扰,只有诗意氤氲的伊甸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三、浓妆淡抹总相宜:全才与天才的文艺成就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于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1071年—1074年)在杭州任通判,曾写下大量有关西湖风光的诗作,这首无疑是最脍炙人口而流传千年的名篇佳句。诚然,它不是写西湖一时或一处之景,而是用美学家的眼光对西湖美景的高度概括和提炼。诗中既生动地描写西湖“水光潋滟”的晴天之明丽,也传神地描摹了西湖“山色空濛”的雨天之迷蒙;既勾画出了近处水光之动态美,也勾勒出了远处山色之静态美。这里,透过苏轼对西湖之美的“言不尽意”的艺术技巧的赞叹,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地发现了苏轼文艺成就的奥秘。即苏轼的文艺创作,既有“水光潋滟”一样的晴天之明丽,也有“山色空濛”一般的雨天之迷蒙;既有潋滟水光一样的生动活泼,也有空濛山色一般的空灵迷幻,以至于让我们无法用简明的语言来解说他的文艺创作。这种既是全才又是天才的艺术家,是千载难逢的,古有苏东坡,今有郭沫若,非常凑巧的是他们同出生在西蜀之嘉州。
中国的文学艺术,门类繁多,数不胜数,名家迭出,灿若星汉,从屈原到鲁迅,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时代,都有杰出的大师,而苏轼则不然,他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全才和横空出世的天才。首先,在文学领域,他共创作了2700多首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情真意切、朴实无华,自不待言;而且他的写景诗和理趣诗,非常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饮湖上初晴后雨》《题西林壁》《琴诗》;他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苏轼结合自己的诗文诵读、应制考试和政治生涯,写了不少的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谈史议政的文章,如《进策》《思治论》等,笔势纵横,思想敏锐,见解独到,针砭时弊,直陈己见;还有像《喜雨亭记》《石钟山记》等游记体散文,写景如在目前,抒情直吐胸臆,叙事跌宕起伏,议论精辟深刻,并且将四种表达手法熔于一炉,尤其是他的前后《赤壁赋》,一写清风朗月的秋光,一写水落石出的冬景,描绘逼真,情景如画,哲思盎然,境界高妙;此外,他还有很多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日喻》等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和笔记文《东坡志林》也做到了信手拈来,深入浅出。他还有像《易传》和《书专》一类的学术著作。其次,在艺术领域,他是著名的书法家,正如他自己说的“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擅长行书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其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等数十篇。黄庭坚,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显示出丰腴跌宕、天真浩瀚的风格,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苏轼在绘画上以画墨竹见长,他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苏轼的文艺天才,不但表现在所涉足的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贡献,而且表现在对作为“诗之余”或“长短句”的词脱胎换骨的创造性的改造升华。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三)中指出:“苏轼的词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他进一步冲破的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大到词的领域里去。”[3]他创作的三百五十多首词,豪放与婉约并存,写景与抒怀同在,典型的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等等。这些经典词章,有效地打破了“诗尊词卑”的传统观念,开启了宋词典雅化的风气,他当之无愧的以“词的革新家”“别开生面的大家”,指明宋词的前进方向而铭记史册。
就像西湖的美与西子一样,“淡妆浓抹总相宜”,那么,苏轼在文艺创作上所具有的全才也罢,天才也罢,总是让我们心向往之而钦佩之至。作为一代大家的苏轼,用多方面的才艺和超常人的才智,将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力量和创造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他旺盛而火热的生命激情、无穷而多样的生命空间、澎湃而细腻的生命情调。全才与天才,如此相得益彰而交相辉映,从广度和深度上,展现出浩瀚而深厚的生命之美。
四、只缘身在此山中:出世与入世的哲学思想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写于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途经九江,游览庐山的所思所感。从庐山之峰峦起伏的景象到游人移步换景的感慨,与其说写尽了庐山的千姿百态,不如说写出了人生的迷离倘恍,更准确地说,这首诗应该是苏轼对世界和存在、对他人和自己、对社会和环境的感性体验与理性反思交织一体的顿悟。诗的前两句揭示的是世界的境况,即我们因为自己位置的不断变换和视点的不停游移,世界只能呈现出支离破粹的景象;诗的后两句指陈的主体的状况,即如果要认识世界的真相,只能离开这个世界,否则的话,只能如盲人摸象似地看见局部的世界。令人困惑的是,我们究竟应该走出这个世界,还是深入这个世界呢?
由于苏轼遭遇了复杂的经历、遭受了多变的人生、遭逢了大起大落的悲欢离合,生活历练出他超常的哲学智慧、超俗的人生境界、超迈的艺术风格,从而形成了他丰富而多样,甚至是矛盾的哲学思想,这就人们常说的儒释道三种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圆融无碍的辩证统一。著名美学家王世德教授说道:“苏轼从儒家吸取的主要是经世致用、舍生取义的人格精神;从到家吸取的主要是崇尚自然、不计得失的精神境界;从佛禅吸取的主要是对空明心境的感悟。他扬弃了儒佛道三家的缺陷,取三家相通或一致之处,交相为用,认为三家有不谋而同之处。”[4]他一生遭受两次大的政治迫害,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密州,依然“老夫聊发少年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总是积极用世,勤于政事,为地方百姓多做实事,如徐州防汛、杭州筑堤、儋州授馆、兴修水利、架桥凿井,甚至晚年在贬到惠州后,他还在为民造福,说明他身上有着儒家浓厚的经世济民的思想。苏轼一生崇尚自然超脱,清静无为,尤其是人生遇挫后,老庄思想成了他人生的“后花园”,佛禅思想成了他精神的“净土寺”。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一文里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这也典型地体现在《前赤壁赋》里,作者由曹操“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入世境况中,进入“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道家境界,最后是遁入“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的人生空门。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在几次大起大落的仕宦经历中,苏轼却最终以“出世入世”既矛盾又统一的方式,完成了他生命特殊形态的哲学思想。
这深入庐山与跳出庐山的鉴赏过程,也正是苏轼入世人生与出世人生的文学隐喻,与其说是苏轼艺术领域哲理诗的创作成就,不如说是他人生境界超越性的哲学思想。“达者兼善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儒家的人生态度早已为苏轼这样的人准备了游刃有余的人生选择,这也几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和人生状态的准确诠释,而苏轼比他们高妙之处在于用佛家思想丰富和延伸了“出世”的含义和意义,化为“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景”的空明澄澈,由此而形式了他由儒至道再达于佛,或儒道佛三位一体的生命之美,那就是“何妨啸吟且徐行”的悠然、“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坦然、“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然。
五、结语:生命意义的永恒追问
正是人生经历的得意与失意的交织、文艺成就的全才与天才的交结、哲学思想出世与入世的交集,使得苏轼的诗意人生的生命之美不仅有丰富的旅程、丰硕的成果和丰厚的底蕴,而且在这矛盾的构体和冲突的结构中,形成了巨大而无限和复杂而充盈的生命张力。著名文学家林语堂是这样评说他的:“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间存在驱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从而形成了他,“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见识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5]或许也正是因为兼容并包而多样统一的人生观,构成并彰显出了他独具魅力与意义的生命之美,那就是“大丈夫”处世的独立品格、“儒释道”一体的和谐状态,“逍遥游”存在的自由境界。这与其说是给传统文人的深刻启迪,不如说是给现代国人的深刻启迪,直言之,苏轼的价值和意义应该是以追求生命意义为鹄的生命美学的永恒追问。
追问之一:如何流连自然又超越自然的“宇宙情怀”
人的生命来源于自然形态,更要超越它而进入文明状态,尤其是进入文明社会后,我们又渴望回归自然,于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就成了疲敝心灵的伊甸园。苏轼一生从少年的西蜀峨嵋游到青年的江南西湖游,直至老年的岭南天涯游,可谓“身行万里半天下”。他在《超然台记》写到:“凡物皆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这也。”这实际上是物与意的关系,他在《宝绘堂记》中说道:“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如此才能达到如《赤壁赋》所企慕的境界,让我们听听苏轼的解说吧:“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最后达到流连自然又超越自然的“宇宙情怀”。苏轼以流连自然之美的斑斑足迹,留下了扣问自然之意的款款跫音,近千年过后,依然在我们心里发出沉重的回响。
追问之二:贴近时代又批判时代的“人文使命”
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使命激励下,中国文人陶养出了深深的“经世致用”社会责任、“知行合一”治学精神和“文以载道”的艺术担当。王国维之所以把他和屈原、渊明和杜甫相提并论,是因为他们都有忠君报国的情怀、愤世嫉俗的性情和优乐黎民的情感。苏轼在地方任职时,兴利除弊,在朝廷做官时,谏言纳策,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争斗中,他据理力争,绝无妥协,其“忧国忧民”的情义可见一斑。但由于他秉性正直,襟怀坦荡,如在《思堂记》的自评:“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这典型而生的地体现在创作的《荔枝叹》,苏轼托古讽今,借用“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贱血流千载”的历史事实,抒发“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的悲悯情怀,揭露官吏“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的巧取豪夺,批判皇帝“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休何陋耶”的寡廉鲜耻。这种人文使命,具有现代的知识分子的公共义务和理性精神。
追问之三:张扬艺术又反思艺术的“审美境界”
苏轼作为宋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的代表者,他在诗歌、辞赋、散文、书法、绘画,以及策论、古文等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尤其是在词作方面,给宋词带来了全新的面貌,提到了全新的高度,使之从音乐的附属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诗歌方面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在散文方面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在词作方面与辛弃疾同为豪放派的代表,并称“苏辛”。他游离了大半个中国,所到之处均留下了诗词歌赋。可以说,文学艺术在他笔下得到了尽情的张扬,文人性情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的释放。同时,他还对文学艺术进行的深刻的反思和理论的提炼。他总结了一系列具有辩证意义的文艺美学见解,如“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艺术理想,“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的艺术情调,“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艺术构思,“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艺术风格。由此可见,他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艺术家,而是具有理论自觉和审美思辨的艺术家;与其说这是他艺术造诣达到的境界,不如说是他审美人生达到的境界。
如此“宇宙情怀”“人文使命”“审美境界”,践行的正是以爱为宗旨、以美为追求、以善为伦理、以真为风骨和以超越为方式、以信仰为源泉、以梦想为动力、以自由为境界的生命美学的所思所愿和所感所悟。自从屈原开启了“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的文化苦旅后,陶渊明在“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的超脱中走向田园自然,杜甫在“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叹息中垂垂老矣,而唯有苏轼却在“大江东去”的豪迈中,在“把酒问青天”的潇洒中,在“聊发少年狂”的义气中,在“寂寞沙洲冷”的孤独中,走遍东南西北,尝尽酸甜苦辣,历经悲欢离合,体验喜怒哀乐,他把中国古代一个文化人有限的个体生命存在,开拓至无垠的界域、提升至无限的高度、获得了无比的成就。
“斯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此时是2016年的岁末,苏轼创作于1076年的那首《水调歌头》,过去940年了,创作于1082年的《赤壁赋》,过去934年了。芸芸众生的我们,“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然而,长江还是那条长江,“但见长江送流水”。月亮还是那轮月亮,“何事长向别时圆”?面对这浩茫的千古喟叹。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醍醐灌顶,大彻大悟。这才是苏轼给生命美学留下的精神财富!
[1] 王国维.文学小言[M]//王国维遗书:五.上海:古籍书店,1983:29.
[2]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05.
[3]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55.
[4] 王世德.儒道佛美学的融合——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4.
[5] 林语堂.苏东坡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4.
[责任编辑 范 藻]
Understanding of“Why Is Always Moon Full When Departure”: Aesthtic Value of Su Shi’s Poetic Life
FAN Zao
(Journal Edition Department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The thesis discusses the aesthtic value of Su Shi’s poetic life, including his life in luck and unluckiness, his literature achievements by versatility and talent, his phylosophy about socialized and unsocialize manners, and his ceaseless sake of life significance.
Su Shi; poetic life; Life Aesthtics
2017-01-12
范 藻(1958—),男,四川成都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与文艺批评研究。
B834
A
1674-5248(2017)03-004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