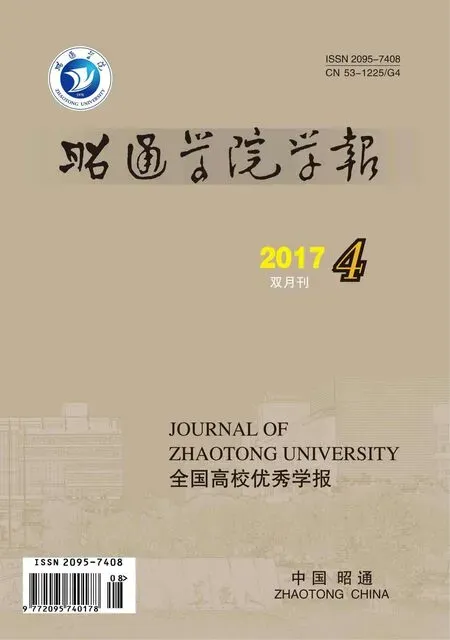论《中庸》“诚”的本体论思想
2017-04-14段博雅
段博雅
(西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
● 哲学研究
论《中庸》“诚”的本体论思想
段博雅
(西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
“诚”在《中庸》中被当作核心范畴加以论述,其内涵得以扩展和提升到了充分的哲学意义,发展成为儒家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与其他文本中“诚”的不同是,《中庸》以“诚”为本体,建构起了严密、丰富的“诚”本体体系。文本以“成”为切入点,依循“诚”成己、成人、成物的逻辑,探讨“诚”沟通天人关系,以释天下之“大本”——“诚”。
诚; 本体论; 成; 天人关系
“诚”最初起源于原始的宗教信仰,表示对鬼神的笃信与忠诚,反映了当时的诚德观念。在后世的发展中,“诚”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周易》中“孚”代表了“诚”,即诚信;《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徐复观先生认为孔子的“仁”则为“诚”承继与发展,“《中庸》下篇之所谓诚,也正是以仁为内容。下篇虽然只出现两个仁字,……但全篇所言之诚,实际皆说的是仁。”[1]而《中庸》的出现,“诚”由一般的道德意义上升到了哲学范畴,因为《中庸》内涵了一个层次丰富、逻辑较强的“诚”本体思想,即明确地将“诚”视为本体,既有宇宙本体的意蕴,又有道德本体的含义。
《中庸》的“诚”仍含有真实无妄的意义,确切地说是指万物本来真实的样子,即万物之本原。这个本原就正如“天命之为性”所描述的那样,是天所赋予的本性,也就是说天命下贯于万物则为“诚”。因为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身就是以事物本来的样子存在,本身不存在诚与不诚的说法,那么这个“诚”则是特定对人而言,因而“天命之谓性”我们展示的是人作为人在于人回应、接受和完成自己的天命,人在天命的召唤下,为完成天命必须尽其可能之性,这便是人之所以为人,即人之性。因此,我们将“率性”理解为“尽性”,去“尽”人在完成天命时的可能性,如是人之道才得以运行。为了完成天命,人必须尽己之性,为了尽己之性,人必须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诚可以说是人作为人首先需要完成的具体天命。由此,我们认为“诚”就是动态的,人需要不断地靠近“诚”,我们以“成”来述说,即“诚”不仅显示了万物(包含了人)之本性,并且不断以道德意义要求万物成“诚”。所以,我们从“诚”成万物出发,阐发《中庸》“诚”的本体思想,能够较为清晰地理解“诚”作为哲学范畴的意义。
一、诚者尽己之性
在《中庸》中,“诚”首先出现在讨论如何获取他人信任的问题中。“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信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2]420人的三种社会关系——亲、友、上,其亲密距离则是友近于上,亲近于友,因而在获取他人信任的顺序则是:在上者看我如何对待友者,友者看我如何对待亲者,如是间接的观察为获信之道。在这里便会有一个疑问:我与亲者关系的“我”,我与友人关系的“我”,我与上级关系的“我”,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当然,父母可以说是与我关系最亲近的人,因为我们的社会关系往往始于父母关系,父母关系是我们与他人发生的第一关系。因而,从这个层面来说,展现在父母面前的我是相对“我”本身。然而其他人则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认识“本我”,这就预设了“我”不是一个绝对透明的存在。如果从形态来认识,人们是可以看到“我”便了然于心,但是“我”并不仅仅是形态,个体意识和内在思想构成了“我”的不透明因素,所以他人无法直接看到“本我”,需要借助于一个与“我”距离更近的人的关系表现中来判断“我”是否值得信任。
上者、友者通过我与亲者的关系来认识我,那亲者该如何来认识“我”呢?因为展现在父母面前的“我”只就是一个相对“我”本身,“我”无法给出一个透明的“我”给以父母认识,那么按照亲密关系递进,父母则需要通过观察我与“自己”如何相处,这便需要“反诸身”[2]420。“反”理解为返回,“反诸身”则是返回到自身,预设了我与我本身存在差异,才给予我返回自身的可能性。那么如何才能返回到自身?《中庸》给出的答案——“诚”(诚于己)。 这样,我们可以完整地表述获信之道:对上级忠诚,须首先对朋友有信;对朋友有信,须得首先对父母有孝;对父母孝顺,首先必须对自己诚。因而,“诚”便成为了伦理关系原则中的起点,一切社会关系的有效性来源于“诚”,“诚”就具有了根源性质,由“诚”开始的社会伦理关系规定了“我”是谁。那么,“诚”在这儿便有了“成就”我的含义,即成己。
成己不仅仅停留在人在社会关系中来认识自我、面对自我,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尽己之性。《中庸》明确指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2]420。这个“性”则是“天命之谓性”[2]415,即天赋予己之性,“尽其性”是指完成自身的天命。而能尽其性的即是诚者,因为诚者乃是能够让自己面对自己的人,面对自己就意味着面对透明真实的自己,这一真实的自己也就是人接受天命并且能够回应、把握天命。所以《中庸》说道:“诚者,自成也。”这就是诚能成己的最终归宿,即完成天命,“诚”也因此有了形而上的内涵。
“我”在实现自身天命可能性的基础上,也能够让他人完成自身天命的可能性,也就是尽他人之性。“我”作为人,与他人有同样的天赋予的性,即是作为实现天命可能性的存在。只有真正能够面对自己的诚者,能够引导自身在开放的天道之中完成自身天命,也就是“诚”使得“我”作为真正的自己而存在,因而他人同样可以通过“诚”成为他们自己,由是同样能够完成他们的天命。如果一个人不能尽己之性,也就不能真正面对那个作为完成天命可能性而存在的自己,那么这样的自己不仅不能尽他人之性,甚至可能成为他人的负累,阻碍他人实现自身天命的可能性。因而“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2]420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在尽己之性就一定能够能尽他人之性,《中庸》强调的是人之能“诚”使得一切事物得以实现自身天命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人能诚则能面对真正的自己,将自己作为实现天命可能性的存在来对待,也就是让人有意识地趋向完成天命。那么与“我”相处的他人也包含其中,所以诚在我的尽己之性使他人的尽己之性成为可能,即让他人有可能尽己之性。
二、不诚无物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2]420诚者的“能尽其性”没有仅停留在尽己之性与尽他人之性上,而在横向上扩展到了尽物之性。所谓“诚者自成”[2]420就是指只有诚者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进而成就自己之为自己,即尽己自性,完成自身天命的可能性。那么,诚者尽物之性也同样应该是让物成为物自身。但是,物与人不同的是,物无法给出另一个物自身来让物回应,因为物本身就是作为物而存在,始终都是现成者,又何须等待人之诚来成就呢?“尽其性”不能与创造同意,而是在创造的基础上成就物之性。因而,我们将诚者尽物之性理解为诚者使得物各正其性,也就是说,让万物是其所是,就像一叶知秋,秋也隐身于这落叶中那样。这其中蕴涵着“顺”的意味,正如合四时之序,万物才能生焉。人之“诚”真实地认识自身,认识世界,只有在“诚”的情况,人所看到的物才是物本身,才是物的“所是”。反之,人不能诚,物于人便没有呈现出物自身。以人的视角看待物反映了《中庸》的人本主义色彩,在这里须得将“尽物之性”与“利物之用”区别开来。虽然我们以人之诚作为尽物之性的起点,但尽物之性的终点则是万物各得其是;而“利物之用”一以贯之的是人的需要和人的价值判断。对“尽物之性”作了细致的阐释之后,我们便能理解“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的深刻内涵了。
“尽物之性”则是成就物是其所是,即成物。《中庸》道:“成物,知也。”[2]420“知”既包含知识和认知,同时也意味着“智”,当然,这也以人的角度来言说的,因为这是人所独有的。人能知物其所是,能理解物之为,如是才能真正地“有”物,这也是人之智。“知”并不是只等待被认知为物所以为物,而其本身就已经参与到成物的过程,可以说“成物”本身也是“知”。这样,“成物”同样要求人之诚,依赖人之最根本性的诚。朱熹在《中庸章句》中以体用释之:“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皆吾性之固有,而无内外之殊。”诚者兼有体用,通过尽己之性的向内存养,通过尽物之性向外展现其用。朱熹的解释将人之诚与成物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化,“诚”对成物起绝对性作用的同时,成物也成为人之诚不可缺少的环节。那么,“诚”作为本体在成物这一层面上表现得更接地气。
三、至诚不息
成己、成人、成物都有待于人之诚,而人之诚有待于人去到达“诚”,即至诚。在《中庸》文本中“至诚不息”既是前一章的总结,又是后一章的开端。“至诚”并不是是已完成的最高境界的“诚”,我们认为“至诚”是“至于诚”,是一个运动着的“诚”状态,由是才能不停息。正是如此,人的“至诚”活动蕴涵着运动变化,而非静止不变。并且,这样的运动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的运动变化:在时间上,“至诚”具有久、远的特点;在空间上,“至诚”具有高、厚的特点。《中庸》给予了“至诚”至高赞颂:“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2]420-421朱熹认为博厚载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就意味着“圣人与天地同用”[3]35;“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意味着“圣人与天地同体”[3]35。在儒家哲学中,“圣人”对人的德行理想的规定,其本也是人,那么“圣人与天同体”便意味着人本身就可以与天地“同体”(同一)。如果仅一处言之或许有些暧昧,那么《中庸》的这段话则直接指出了至诚者可以与天地参。“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2]420天地育万物包含生与养,人之“诚”成就万物建立在生的基础之上,《中庸》说“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就说明了“诚”是万物之为万物的不可缺少因素,从这一点上来极大地肯定人之至诚。
人之至诚得到极大的肯定,并在这样的肯定下趋向着与天地合一。“合一”是一种双向性的运动:一方面,“人”合于“天地”,即人通过“诚”面对真实的自己,面对天命,从而接受、回应、完成天命,从而与天地成为一体;另一方面,“天地”合于“人”,即让天地等同于最高境界的至诚者,等同于成己、成人、成物的人。《中庸》作出的选择是:“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生物不测。”[2]421“不贰”则是“诚”,朱熹认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不过曰诚而已”[3]35。紧接其后《中庸》道:“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2]421“博、厚、高、明、悠、远”并不是天地本来具有的特征,也就是说,这里的天地形象隐含的是至诚者的形象。所以“合一”运动趋向便一目了然了。
我们说人能诚内涵着人之不诚的预设,但是,一旦人开始让自己诚,人就开始成,成己、成人、成物便就开启,进而“诚”成就一切,这一切便是世界,换句话说,人之诚便给出了一个让万物都成之为万物的世界,那么我们可以说“诚”为万物之“本体”。因而《中庸》也总结道:“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2]422通过对“至诚不息”的阐述,我们发现人之“至诚”并不仅仅只有本体的含义,还内涵工夫。换言之,《中庸》的“诚”是即本体即工夫的范畴,因此,“诚”在《中庸》中拔高到了核心哲学范畴的地位。
四、总结
《春秋繁露·立元神》说道:“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 在《中庸》中做到了人与天地合一,其条件是“诚”。人之至诚不断地追求面对自己作为完成天命可能性的存在,成己的基础上成就他人,成就万物。而万物本身是存在的,却依赖于人之诚使其是其所是,因而人之“诚”在成物的过程中参与天地化育万物,形成天、地、人三参的局面。但《中庸》中“天地”形象隐含着“至诚”者的形象,由是人与天地合为一体。那么,人之“至诚”也就是万物之本,天下之“大经”、“大本”。通过探寻“诚”成万物的基础上,“诚”追求的终极是使人与天地相参,实际上不仅突出了“诚”道德本体意蕴,还赋予了道德本体形上意义,这对宋明儒学的“诚学”体系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31.
[2]陈戌国 校注. 礼记[M]. 长沙:岳麓书社,2004.
[3](宋)朱熹. 四书章句[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4]钱 穆. 四书释义[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5]伍晓明. “天命:之谓性!”片读《中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陈 赟. 中庸的思想[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Research of “Cheng”-Ontology in Chung-yung
DUAN Bo-ya
(Institute of Marxism.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
“Cheng”(sincerity, truth, or reality) ,the core category in Chung-yung, has been extended and elevated into fully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which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Confucian philosophy. What the difference with others is that “Cheng” in Chungyung is with the meaning of ontology. It has build a rigorous and ample system of Cheng-ontolog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chooses “Cheng”(finish,make, or create) as the breakthrough-point,follows the logic of making self、making person、making things,probes how “Cheng”communicate Heaven and Man,and then explains the great foundation ——“Cheng”.
“Cheng”; ontology; make;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B222.1
A
2095-7408(2017)04-0033-04
段博雅(1993— ),女,四川康定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