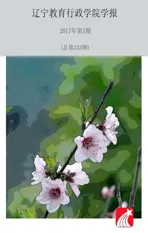池莉和王安忆小说生命力体现之比较
2017-04-14王曦筱
王曦筱
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110136
池莉和王安忆小说生命力体现之比较
王曦筱
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110136
池莉作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她的作品描写武汉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王安忆用写实的笔触展现上海这块神奇的土地以及上海市民的生活,从中折射出历史的变迁。同为女性作家,二者的作品既有相同的特质,又具有独特的对生命力的书写。通过比较二者之小说,阐述双方生命力体现的异同。
池莉;王安忆;小说;女性;生命力
作为当代两位著名的女作家,池莉和王安忆都以根植于某片土地的渊远文化为根基,书写着对人生的体悟。同为女性作家,二者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同质的因素:作为女性本身的柔情关怀以及视角向女性的投注。而毕竟由于秉性、成长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差异,二者书写的独一无二风格构成辨认她们的最明显的标识。无论在具体的书写、语言的遣用上,池莉与王安忆都显示出巨大的差异,而在根本上造就这种不同的关键因素,在于二者所追寻的生命感的偏离。前者凸显在日常的市井生活中的生命力的蓬勃生长;后者则注重于与城市历史变迁相回响的生命的坚韧。不同的生命情怀与相似的视角关注,建构出二者趋同又各自独立的书写风貌。
一、池莉与王安忆小说的相同点
池莉小说以平民化角度与写实手法,描写普通人生活中的困境与烦恼、生存与生命意义,以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对于现实人生的顺从、挣扎与抗争,其作品展示出当代普通人生活的生命本真状态。以平视的角度,通过繁琐而冗杂的生活表象,塑造出一系列个性鲜明又颇具时代特色的人物,揭示世俗生活变动中人们所遭遇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挖掘在世俗生活下隐藏着的坚强而厚重的生命力,给平庸的世俗生活添一分精气神儿,这便是池莉写作的魅力所在。正因如此,其作品也获得了独特的意义与价值。也正因为其小说拥有那么多精神特质,她的作品才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绵延至今并备受人们的关注和推崇。和池莉相似的是,王安忆在创作中对于笔下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生命体验和女性独立的个体意识一直保持高度的关注。在这些作品中,王安忆坚持不懈地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生存进行书写和建构,深入挖掘女性个体甚至整个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对待物质和精神世界特有的身心感触,从而显现出人物鲜活而持久饱满的生命状态,对笔下女性进行着持续的解放和救赎。由于王安忆对于女性旺盛生命力的强烈观照,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显示出生命的蓬勃与绚烂,在任何生活状态下都能坚韧执着地放射出生命的光彩。
二、池莉与王安忆小说的不同点
(一)城市生活的生命活力
池莉在散文中曾这样描写武汉三镇:“在武汉市,无论你居住在三镇的哪一个镇,无论天气多热多冷,无论你是在挤车还是挤船。忽然在某一个时刻,呜的一声船鸣缓缓滚过,这声音是那么巨大却又绝不高亢尖锐,它远远超越城市的嘈杂,清晰而从容地从你心头抚摸而去。那感觉真熨帖,仿佛那是你百岁祖父慈爱的手。”[1](P30)在池莉的小说中,武汉人的衣食住行和这座城市有些密切的关联。甚至可以说,武汉这座城市塑造了这样的武汉人,而池莉也同样在文本中把武汉的热、武汉的饮食文化、武汉人的语言特色以及武汉人的真性情都表现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武汉被称为“火炉”,其夏天之热在国内可谓登峰造极,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武汉人却照样散发着火辣辣的生命活力。池莉在《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里关于武汉的酷暑天气是用猫子所讲的“一支爆裂的温度计”这样的奇闻异事来表现的,而其女友燕华焦躁但不做作的直率性格也与这样的气候相协调。全篇都在围绕猫子店里的一只体温表炸裂,不同职业又形形色色的人物登场带一句诅咒天气的话语,然后又各自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在这样的登场又退场的过程中,武汉人没有被热天气所压抑,而是更加认真自豪又毫不矫情地投入到每天的生活中去。猫子的巧舌,燕华的热辣,都不动声色地表现出来。
武汉人的这种火辣辣的生命活力也可以从他们的语言中体现出来。在池莉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武汉人标志性的说话方式——“婊子养的”口头禅。另外,在《太阳出世》中,小兰的婆婆看到小兰生了女儿之后不屑一顾,四嫂安慰小兰道:“婆婆是筲箕圈、六点钟——半转;莲藕灌进了稀泥巴——糊了心眼”,[2](P140)这样通俗易懂的民间方言的歇后语,一下子就点明了婆婆的为人和心思。在这种粗俗的语言表达中,仍旧流露出武汉人的真性情。在地域文化和文学作品相融合这一点上,池莉的作品给出了极好的示范。武汉人的日常,在她的笔下活灵活现,武汉人的生命活力也在她笔下蓬勃热辣。
而王安忆是属于上海的。有关上海题材的作品在文坛上层出不穷,王安忆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常青树,对于上海的书写是透进骨子里的,是一种丰富且独特的存在。通过王安忆对上海日常生活的生动描摹,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社会的历史变迁,体会到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汇聚起来的一股似有似无但却绵延不绝的力量,如小说《长恨歌》,王琦瑶这个上海小女子由弄堂内的闺阁女子到成长于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最终命落黄泉的丰富多彩却又跌宕起伏的一生,折射出上海城市的辉煌、萧瑟和历史变迁。王安忆作品风格的一个转变是在《流逝》中,昔日生活优越的欧阳端丽在遭遇家庭变故之后,通过精明打算和坚强韧性来撑起一个家庭。其实,无论是一生具有奇幻色彩的王琦瑶,还是在遭遇家庭变故后的欧阳端丽变得坚强独立的经历,都体现出王安忆关注笔下人物在日常世俗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一股努力生活且不能低头认输的韧劲。不仅如此,作为上海城市中的一个独特文化风景——弄堂,《长恨歌》中开篇就对其大肆渲染笔墨:“上海的弄堂真是见不得的情景,没有半点偷懒和取巧,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掬一捧漏一半地掬满一地,一锅粥似的,枝枝杈杈数也数不清,有着曲折的内心,确是稠密。”[3](P3)在上海,弄堂就是中国市井社会或者世俗生活的一个微缩,王安忆小说中的弄堂书写,是其上海题材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王安忆看来,上海的核心就体现在弄堂生活中,她以弄堂女性的命运为载体,再加工市井居民的日常生活,以提取弄堂生活中的人类普遍的生存要义。因其独特的理性思考和人生体验,市井人生在弄堂中的琐碎与平庸被赋予诗意的审美形态,超越了作为居住地的弄堂本身。其小说以日常生活为基础来塑造女性,两性的和谐共生在弄堂这一文化空间内,使女性的生命形态呈现出一种温婉的状态。同样,在表现方式上,日常生活书写在王安忆的笔下也显现出独到之处。她善于体悟生活,特别注重对细节的刻画。同样的,她小说中的散文化叙述,也使得她笔下的城市日常生活变得诗意盎然,具备了非凡的情致。
池莉描绘武汉,王安忆书写上海,本质上都是地域文化的张扬,在现实意义上,只是地点的不同。但在这里,正是由于地域的不同,其根植于某一片土地的独特生存方式得以每天都外化于日常的生活习惯、方言俚语。武汉人在炎热天气中的振奋,上海人稠密的弄堂生活,无不带着土地给予的生命的烙印,各自地闪耀人性的光辉。
(二)艰难困境中的顽强意志
池莉说过:“我尊重、喜欢和敬畏在人们身上正发生的一切和正存在的一切,这一切皆是生命的挣扎与奋斗,它们看起来是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是生老病死,但是它们的本质惊心动魄,引人共鸣和令人感动。”[4](P365)显然,池莉正是想通过这种普通人在生老病死艰难困苦中的奋斗和挣扎来反映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丰富情感与不屈的意志。在《你是一条河》中,池莉塑造了辣辣这一不屈的女性形象。辣辣三十岁成为寡妇,到五十岁绝望离世的二十年中,历尽千辛万苦抚养起七个儿女,战胜生活中其他男人的骚扰,失去小叔子的感情等。尽管受尽屈辱,但她仍不懈地追求着微弱希望,坚韧顽强地生活下来。在辣辣身上,人们看到的是永怀希望的抗争精神。《烦恼人生》中,印家厚每日坐船来往于公司和家庭之间,他深刻体会到诗作《生活》中的寓意:网。但是当他劳累一天回家之后有热菜热饭等着,他就感到了无以名状的幸福。《太阳出世》中,作者形容“母爱是这世界上唯一兼具伟大和糊涂的激情。母爱来了,小事也是大事,大事也是小事。”小赵和小李在经历了快一年的为人父为人母的过程中,尽管生活如此平凡琐碎甚至不称心,“但是他们仍然能感觉到一种幸福,这幸福凌驾于一切困苦之上,那就是他们女儿朝阳的进步”。[5](P132)
王安忆对于人物的设定与池莉稍有不同,她将人物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中,让她们在坎坷的命运和艰难的处境下,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以柔弱之躯抵御艰辛、对抗磨难。她们身上跃动着的强悍的生命力,和有如神启般的睿智,使得这些女性在生活中不慌不躁,安然处理一切。如《桃之夭夭》中的郁晓秋,面对自己的身世,爱情和亲人的伤痛,她不逃避,处之泰然。如文中结尾总结的,她就像那种长在石缝里的小草,有时甚至能开出黄色的小花。《“文革”轶事》中的姆妈,面对一切冲击都是淡然模样,文中写到这些事“和那些浮华往事不同,它不会叫人心绪骚动,感时伤怀,它含有旷达和认知的平和宽度。”[5](P477)这种直面苦难的淡定体现了人物豁达的生命态度与坚韧的生命耐力。
(三)女性生命的灿烂绽放
同为女性作家,池莉和王安忆对女性人生有着各自独特的感受和经验。“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池莉以背离男权审美理想、还原当代妇女本真形象为创作准则,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有欲有情的妇女形象”。[6](P83)无论是耿直率性的燕华,还是特立独行的艾月,或是性情叛逆的豆芽菜以及最终幡然醒悟的戚润物,也无论是知识女性的代表梅莹,还是底层市民女性的精神象征来双扬……这些女性形象都真实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女性在社会角色、主体意识、生存方式、婚爱追求与人生理想等方面的观念演变。在人人都歌颂爱情的80年代,池莉写出了《不谈爱情》。在这部小说中,女性不再是攀援在男性身旁的一株木棉花,而是能够把握机会创造爱情的生命主体。小说中,中上层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庄建非和花楼街小市民家庭出身的吉玲从恋爱到结婚的过程,显现出这两个阶层之间的碰撞和吉玲底层市民的智慧。吉玲作为推动整个情节发展的轴心,她精明算计又不失尺度,主动创造机会周旋在各个团体之间,拥有小市民特有的圆滑世故和泼辣勇敢,自始至终贯穿着她独立又独特的女性意识。也就是说,在小说创作中,池莉不仅表面地观照和展现女性生存本相,而且也追根溯源,探寻根深蒂固的父权意识下的女性创造力和生命力,表现独立的女性人格和价值观。
女性人生也是王安忆关注的重心。“纵览王安忆几十年繁复多变的文学创作,无论是早期的雯雯系列,随后的‘流逝’系列,还是城市小说、乡村小说、性爱小说以及个人成长史小说等,女性始终是她关注的焦点。”[7]相较于池莉的创作,王安忆更多地是从性别层面刻画女性,从寻找男子汉起步到确认自然性别再到探索社会性别,构成了她女性创作的衍进路线。按照王安忆小说创作的发展脉络,以时间为序可以划分为特征明显的三个阶段:女性意识觉醒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作品,有《雨,沙沙沙》《幻影》《金灿灿的落叶》《流逝》等;女性欲望的浮现,对自然性别的确认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作品,还有“三恋”小说、《岗上的世纪》等;探索性别的社会构成,对性别的超越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如《我爱比尔》《米尼》《长恨歌》等。王安忆在文本中一直对女性生存的物质和精神空间给予殷切的关注,如在小说《妹头》中,妹头是标准的淮海路上生长的女孩,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历经了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妹头显现了独到的眼光和品味。与《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相似,妹头同样善于过自己的小日子,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相较于王琦瑶,她能更为主动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感情上,她主动抓住小白;事业上,她毅然把握住机遇与阿川合作做起服装生意,凭借自己的才能过上了新的生活;而最后当被丈夫得知她和阿川的婚外情后,她也能勇敢承担后果,最终离婚,把孩子带走。在上世纪80年代,王安忆的小说在展现女性的生命欲望,肯定女性自然生命力价值上可谓开风气之先。在她的“三恋”即《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中,女性对于身体和精神都同样有着自己的追求。王安忆不消解她们的母性,更不避讳她们对于肉体的渴望,在她们身上融入了女作家当时当刻的生命感悟和生命体验,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赋予了作品崭新的意义。
池莉和王安忆,是当代文学中极其重要的两位女性作家。总体来看,池莉和王安忆都注重对当代女性的观照,并赋予其解放独立的女性意识和面对困境的坚韧不拔。人物的生命力,就是在琐碎的城市生活的浮沉中体现出来。而具体看来,炎热天气中的市井气息,同稠密弄堂中的吴侬软语,折射出的是不同的生命形态。不同的生命情境,最终都指向不同的生命感的高扬。王安忆与池莉,二者的独特的生命力的书写,就在这些差异中。
[1] 池莉.池莉文集(第4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2] 池莉.池莉文集(第2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3] 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
[4] 池莉.池莉文集(第5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5] 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6] 吴惠敏.试论池莉小说的女性意识[J].文艺研究,2000.
[7] 李海燕.王安忆女性人物形象论[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责任编辑:彭琳琳)
王曦筱(1994-),女,陕西铜川人,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
2017-04-15
I247
中图分类号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