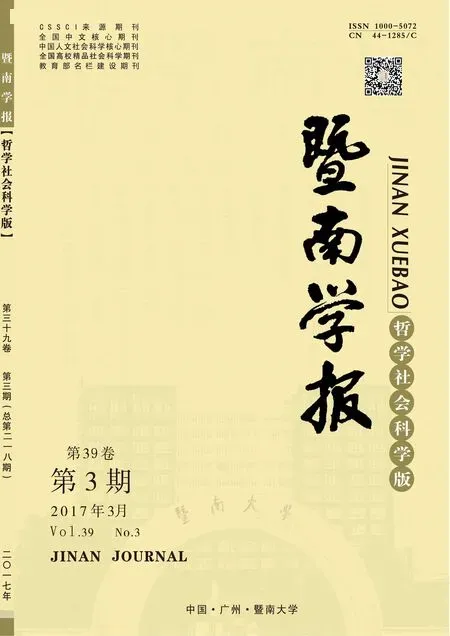舆论的动力中介:政治效能对青年政治表达的影响
——基于中国大陆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研究
2017-04-14卢家银
卢家银
(中山大学 传播与设计学院, 广州 510006)
【新闻与传播】
舆论的动力中介:政治效能对青年政治表达的影响——基于中国大陆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研究
卢家银
(中山大学 传播与设计学院, 广州 510006)
政治效能在舆论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回顾政治效能对公民政治表达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境内的大学生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N
=2188),系统分析了内部政治效能和外部政治效能对中国青年政治表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内部政治效能不仅对青年的线上、线下政治表达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中介了传媒与网络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线下政治表达的影响;外部政治效能既对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有直接促进作用,又中介了传统媒体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正面影响,还中介了网络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正向作用。同时,研究还发现,媒介新闻使用对青年的内部和外部政治效能感正负效应兼具。公共舆论; 政治效能; 政治表达; 青年网民
一、问题的提出
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从表达主体上讲,既有普通民众情绪与理性交织的利益表达,又有意见领袖专业活跃的监督与质疑,还有党政部门形式多样的舆论引导与抚慰。从表达形式上讲,既有人大、政协、信访、传媒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又有互联网、非政府组织等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不断拓展的非制度化表达渠道,甚至还有部分民众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的另类或极端类(乃至违法的)抗争性表达方式。从表达内容上讲,既有持续不断的对主流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又有对其他社会思潮和思想的探讨与争论;既有对娱乐圈明星的茶余八卦,又有对腐败官员的口诛笔伐,还有对垄断部门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批评,尤其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住房、医疗、环保和食品安全等问题。社会公众当前的这种意见表达,不仅受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结构调整和利益格局变动的冲击,而且受公民自身政治效能感、媒介使用和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政治效能是考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内在指标,它能反映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现有研究发现,公民政治效能感的高低会影响其政治行为。并且,随着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广大民众(特别是作为网民主体和政治参与主体的青年)通过网络获取、传播信息和表达的便捷与自由会提升民众的政治效能感,这可能影响他们线上与线下的政治表达行为,进而导致舆论波动。对于该问题,目前尚无专门研究,且缺乏对网络使用主体青年人群(亦是当前和未来政治参与的主体)政治表达影响的直接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将全面研究政治效能对青年政治表达的影响及其相关因素,以此探索舆论形成中的动力机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所谓政治效能(political efficacy)是指个人认为其政治行为确实或能够对政治过程产生影响力的心理感知。它既是衡量民众政治参与的一个预测指标,又是民众评价政府及其自身能力的重要依据。国内学者普遍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态度,认为政治效能感是民众在与其政治系统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自身政治影响力和政治系统回应力的内在的、比较稳定的评价系统,是主体以自身为参照对象形成的对自我政治能力的判断、评价和反思的结果。在政治态度的相关研究中,政治效能感仅次于政治认同,是研究最为广泛的一个话题。政治效能通常可分为内部效能感(internal efficacy)和外部效能感(external efficacy)两种。内部效能感是指个人相信自己拥有能力能够了解政治事务、认知政治过程的全貌,以及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外部效能感则指个人相信政府关于对民众需求反应与重视的程度。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形成早期是由个体学习和其自身需要直接催生,后期则多受教育程度、媒介使用、政治兴趣、社会经济地位等各类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多年来,对政治效能与政治行为之间关系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重要命题。学术界普遍认为,政治效能感在政治活动中最为直接的作用就是对政治表达和参与的影响。臧雷振等学者研究发现,政治效能感是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政治效能感越高,政治参与就越积极。“当政治效能感较高的时候,公民相信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民众考虑的,而且他们的行动会对政府产生积极的影响。”史蒂芬·克雷格(Stephen C. Craig)等人指出内部效能感与外部效能感对于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力有相当大的不同,内部效能感对个体的传统政治活动与社区活动的参与影响更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外部政治效能感能够明显提升政治信任,而内部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则很弱或不明确。在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背景变量的情况下,内部效能感较高的中国公民比内部效能感较低的公民更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而外部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行为的相关度则不显著。与此相近,黄信豪通过对台湾地区政党选举的全面研究,发现代表自我政治能力评估的内部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相当重要的心理基础;在投票选举中,感受政府回应程度较高者,将显著地选择执政党,而外部政治效能感则成为无特定政治立场或偏好的选民是否选择继续支持执政党的重要依据。另外,有研究还表明政治效能感作为个人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重要的中介变量,在促进个体政治交流与参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均能显著地影响民众的制度型参与和公共型参与,只是外部效能感对抗争型参与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内部效能感对抗争型参与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做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H1):内部政治效能对青年的线上政治表达(H1a)和线下政治表达(H1b)具有正面促进作用。
假设2(H2):外部政治效能对青年的线上政治表达(H2a)和线下政治表达(H2b)具有正面促进作用;
政治效能除了影响公民的政治行为,自身也受媒介使用的影响。“就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而言,电视的影响力最为重要,民众对电视的暴露程度或注意程度,与其政治效能感具有显著的关联性;至于民众人际沟通的社会网络的部分,以选民和他人政治的讨论程度,对其内在政治效能感有显著的影响,但对于外在政治效能感,社会网络的影响力则未显现。”国内学者周葆华通过实证调查与质化访谈的方法,分析了媒体接触、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传统媒体新闻使用(电视新闻)和政治参与对内部效能产生了显著影响,而传媒新闻接触、网上或是网下参与均对外部政治效能无显著影响。与之类似,另一位研究者发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对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感影响不同,新媒体相对而言显著性更高。就大众媒介对于城市居民政治效能感的培养而言,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影响力更具有显著性。对此,韩国学者李俊雄(June Woong Rhee)和金恩美(Eun-mee Kim)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匿名的网上政治讨论与互动有助于公民外部效能感的提升,且网络政治协商的数量与质量对于政治效能感具有非常重要且相互独立的影响。对于政治效能感的复杂影响,还有研究指出,网络政治新闻使用与内部效能感对竞选活动和投票意愿这两种政治参与行为具有交互影响,即内部政治效能感越高,互联网政治新闻的关注对参与竞选活动的负向影响会越大,而互联网政治新闻的关注度对投票意愿的负向影响反而会越小。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与问题:
假设3(H3):传统媒体的新闻使用对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H3a)和外部政治效能(H3b)具有正面促进作用。
假设4(H4):网络媒体的新闻使用对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H4a)和外部政治效能(H4b)具有正面促进作用。
研究问题(RQ1):政治效能是否中介了传统媒体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影响?
研究问题(RQ2):政治效能是否中介了网络媒体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状况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探索了政治效能对青年政治表达的影响。调查对象为中国境内的18-35岁的在校大学生。本次调查范围覆盖了东中西部的七座城市、15所大学,采用的是分层抽样的方法,按照地域、城市、学校、学院、专业、年级和班级的层级,在东部地区抽取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在中部抽取的是武汉和郑州,在西部抽取的是兰州和西安。在北京的59所本科院校中,本研究抽取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北京工商大学;在上海的35所本科院校中,则抽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在广州的27所本科院校中抽取了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含南方学院);在武汉的32所本科院校中,抽取了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含文华学院);在郑州的20所本科院校中则抽取了郑州大学;在兰州的12所本科院校中,抽取的则是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和兰州城市学院;在西安的32所院校中抽取了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在问卷发放过程中,我们委托被抽样班级的学生志愿者和访员通过电子邮件、QQ、微信和手机短信四种方式邀请所在班级的学生在网上填写问卷。从2015年7月20日开始发放问卷,共向9114人发出邀请。截至9月20日,共成功收回有效问卷2188份。其中,在北京收回507份,在上海收回153份,在广州收回351份,在武汉收回411份,在郑州收回154份(其中7份问卷城市值缺失),在兰州收回354份,在西安收回258份,调查问卷的成功回收率为24%。
在调查样本的2188份中(参阅表1),男性青年占37.4%,女性青年占62.6%;年龄分布范围在17~3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1.4岁;在读专科生(部分院校招收少量专科生)占3.0%,大学本科生占80.5%,在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16.5%;中共党员占32.3%,非党员占67.7%;家庭收入在当地平均水平的占62.3%,月收入平均在2000~5000、5000~10000之间的青年最多,分别占样本总体的28.6、30.0%。

表1 样本基本变量描述性分析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1)线上政治表达

(2)线下政治表达

2.自变量
(1)内部政治效能
对于内部政治效能,本研究使用理查德·尼米(Richard Niemi)和史蒂芬·克雷格(Stephen Craig)等人设计的量表进行测量。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完全同意,5=坚决反对)中报告其对于下述观点的赞成程度:①政府的工作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很难明白;②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参与政治事务。这两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大学生的内部政治效能感(M
=6.48,SD
=1.80,α
=0.76)。青年群体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变化情况可参看图2,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感水平高于外部效能感,且于30岁后出现大幅波动。
图1 青年群体的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状况
(2)外部政治效能
对于外部政治效能,本研究使用约翰·盖斯提尔(John Gastil)和迈克尔·谢诺斯(Michael Xenos)设计的量表进行测量。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完全同意,5=坚决反对)中报告其对于下述观点的赞成程度:①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会影响政府的做法;②政府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这两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学生的外部政治效能感(M
=5.74,SD
=2.03,α
=0.80)。青年群体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变化情况可参看图2,青年的外部效能感水平低于内部效能感,且于30岁后开始迅速下降(虽会回升,但在35岁后仍会下落)。(3)传统媒体的新闻使用
本研究使用日本学者山本正弘(Masahiro Yamamoto)等人设计的媒介使用量表测量青年群体的传统媒介使用,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从不,5=总是)中分别填写他们每月在线下从事下述活动的频率:①阅读报纸新闻;②阅读期刊新闻;③收看电视新闻节目;④收听广播新闻节目。四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大学生对传统媒体的新闻使用情况(M
=9.68,SD
=2.90,α
=0.85)。青年群体对传统媒体新闻使用的情况可参看图3,青年的传媒新闻使用频度低于网络新闻使用频度,且在33~34岁期间会明显增长。(4)网络媒体的新闻使用

图3 青年群体的媒介新闻使用情况
对网络新闻使用的测量,本研究亦采用山本正弘等人设计的媒介使用量表。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从不,5=总是)中分别填写他们每月在网上从事下述活动的频率:①阅读报刊新闻;②收看网络电视新闻节目;③访问大型新闻网站;④阅读知名人士的博客、论坛文章;⑤使用搜索引擎搜索时事新闻;⑥使用微信获取时事新闻。这六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大学生对网络媒体的新闻使用情况(M
=17.16,SD
=3.92,α
=0.75)。青年群体对网络新闻使用的情况可参看图3,青年的网络新闻使用频度明显高于其传媒新闻使用,且在33-34岁期间会明显升高。3.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政治社会化研究成果的变量设计,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政治面貌(M
=0.31,SD
=0.46)、政治兴趣和网络讨论规模八项。其中,教育程度通过受访者报告已就读年限测量(M
=3.01,SD
=1.60)。家庭经济收入通过询问受访者家庭月平均收入(1=1000元以下,2=1000~2000,3=2000-5000,4=5000~10000,5=1万~1.5万,6=1.5万~2万,7=2万元以上)和家庭总体经济状况(1=远低于平均水平,5=远高于平均水平)进行测量(M
=6.60,SD
=1.78)。政治兴趣通过询问受访者对时事政治感兴趣的程度和对选举活动感兴趣的程度进行测量(M
=6.17,SD
=1.50,α
=0.79)。对于网络讨论规模,本研究主要是通过受访者自我报告在过去一个月在线下面对面讨论时事政治和在线上讨论时事政治的人数而测定(M
=4.20,SD
=1.84,α
=0.81)。(三)数据分析
本文首先对所有研究变量进行零阶相关分析,然后进行层级回归分析。在回归模型中,依次将人口统计学变量、政治变量和媒介变量代入回归方程,以阐释政治效能对政治表达影响的因果关系。为了分析政治效能是否中介了媒介新闻使用对公民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影响,本研究最后进行Bootstrapping检验。本研究中,所有数据均是运用软件StataSE14.0进行分析和处理。
四、研究发现
H1假设内部政治效能对青年的线上政治表达(H1a)和线下政治表达(H1b)具有正面促进作用。相关分析显示(参看表2),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与线上政治表达(r
=0.20,p
<0.001)和线下政治表达(r
=0.09,p
<0.001)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回归方程显示(参看表3),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对内部政治效能的回归都不显著(p
>0.05),H1a、H1b遭到拒绝。H2假设外部政治效能对青年的线上政治表达(H2a)和线下政治表达(H2b)具有正面促进作用。相关分析显示,青年的外部政治效能与线上政治表达(r
=0.23,p
<0.001)和线下政治表达(r
=0.14,p
<0.001)之间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方程亦显示(参看表3),青年的线上政治表达对外部政治效能的回归显著(p
<0.01),作用方向为正向(β
=0.065),H2a得到支持。与之类似,青年的线下政治表达对外部政治效能的回归亦显著(p
<0.05),作用方向为正向(β
=0.059),H2b得到支持。这表明,青年人群的外部政治效能感越高,其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频度就越高。
表2 背景变量、自变量与因变量的零阶相关分析表
注:p
<0.05,p
<0.01,p
<0.001
表3 政治效能对青年政治表达影响的回归分析表
注:*p
<0.05, **p
<0.01, ***p
<0.001;表格中的β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H3假设传统媒体的新闻使用对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H3a)和外部政治效能(H3b)具有正面促进作用。相关分析显示(参看表2),传统媒体的新闻使用与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r
=0.12,p
<0.001)和外部政治效能(r
=0.21,p
<0.001)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方程显示(参看表4),青年的内部效能对传统媒体新闻使用的回归显著(p
<0.001),作用方向为负向(β
=-0.072),H3a遭到拒绝。这说明,青年对传统媒体中的新闻使用越多,他们的内部政治效能感就越低。与之不同,青年的外部效能对传统媒体新闻使用的回归显著(p
<0.001),作用方向为正向(β
=0.149),H3b得到支持。这意味着,青年对传统媒体中的新闻使用越多,他们的外部政治效能感就越高。H4假设网络媒体的新闻使用对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H4a)和外部政治效能(H4b)具有正面促进作用。相关分析显示,网络媒体的新闻使用与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r
=0.20,p
<0.001)和外部政治效能(r
=0.14,p
<0.001)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方程则显示(参看表4),青年的内部效能对网络媒体新闻使用的回归显著(p
<0.001),作用方向为正向(β
=0.090),H4a得到支持。这表明,青年对网络媒体中的新闻使用越多,他们的内部政治效能感就越高。与之相反,青年的外部效能对网络媒体新闻使用的回归显著(p
<0.001),但作用方向为负向(β
=-0.072),H4b未得到支持。这说明,青年对网络媒体中的新闻使用越多,他们的外部政治效能感就越低。
表4 媒介使用对政治效能感影响的回归分析表
注:*p
<0.05, **p
<0.01, ***p
<0.001;表格中的β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对于RQ1(政治效能是否中介了传统媒体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影响),回归方程显示(参看表3和表4),线上政治表达和线下政治表达对外部政治效能的回归、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对传统媒体新闻使用的回归、内部和外部政治效能对传统媒体新闻使用的回归均显著,只是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对内部政治效能的回归不显著。这意味着,外部政治效能中介了传统媒体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影响,内部政治效能可能中介了传统媒体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影响。
对于RQ2(政治效能是否中介了网络媒体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影响),回归方程显示(参看表3和表4),线上政治表达和线下政治表达对外部政治效能的回归、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对网络媒体新闻使用的回归、内部和外部政治效能对网络媒体新闻使用的回归均显著,只是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对内部政治效能的回归不显著。这意味着,外部政治效能中介了网络媒体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影响,内部政治效能可能中介了网络媒体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影响。
为了检验上述中介效应,本文使用Bootstrapping方法进行分析。经过检验(参看表5),本文发现,内部政治效能既中介了传统媒体的新闻使用对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影响,又中介了网络媒体的新闻使用对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影响;外部政治效能既中介了传统媒体的新闻使用对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正向影响,又中介了网络媒体的新闻使用对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正向作用(间接与直接效应值可参阅表5)。

表5 政治效能感的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检验表
注:表中的β
为非标准化系数。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将政治效能感放置在媒介新闻使用的背景中,全面分析了内部和外部政治效能感对青年政治表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治效能感在舆论的形成和演化中扮演了动力中介的重要角色:内部政治效能既有对青年线上政治表达的直接促进作用,又中介了传媒和网络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正向影响;外部政治效能既有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直接推动作用,又中介了传媒和网络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积极影响。
第一,内部政治效能是影响青年政治表达的重要因素。虽然它对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未产生显著影响,但是中介了传媒与网络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正面作用。已有研究发现,内部政治效能感中介了媒介新闻使用对政治行动的影响。李蓉蓉等人认为,政治效能感是一种政治态度,带有准备与行为意向的特征,具有对行为的预测和影响的功能。尤其是内部政治效能感会对公民的政治行动产生推动作用。由于互联网的相对匿名和使用的便捷,随着内部政治效能感的提升,青年在线表达的心理准备和动机基础就会越充足,这就越有可能引发和刺激线上的政治表达和参与等政治行为。
第二,外部政治效能是影响青年政治表达的关键变量。它既对青年的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有直接促进作用,又中介了传统媒体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正面影响,还中介了网络新闻使用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正向作用。这意味着,青年群体的外部政治效能感越高,他们在线上和线下的政治表达频度就越高。与内部效能感的影响力相比,外部政治效能感对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的影响力明显高于内部政治效能感(表3中外部政治效能感的β
值大于内部政治效能感,且后者不显著)。并且,内部政治效能与外部政治效能互为因果(参看表4),二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显著作用:青年人群的内部效能感愈高,其外部政治效能感就愈高;青年人群的外部效能感越高,他们的内部政治效能感也会越高。第三,媒介新闻使用是推动青年政治表达的重要变量。媒介新闻使用对政治表达的这种影响,除了直接效应,还有通过政治效能的间接影响。其中,传统媒体的新闻使用通过内部、外部政治效能均间接促进了青年的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网络新闻使用既通过内部政治效能促进了青年的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又通过外部政治效能间接推动了青年的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同时,媒介新闻使用还是影响青年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虽然传统媒体新闻使用对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感、网络新闻使用对外部政治效能感具有负向作用,但传统媒体新闻使用对青年的外部政治效能感具有正面促进作用,网络新闻使用对青年的内部政治效能感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第四,虽然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政治效能对青年政治表达的复杂影响,但是本研究可能仍然存在三方面的不足。其一,本文使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对全国在校大学生进行了抽样,但是仅从东中西部抽取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郑州、兰州和西安七个城市,相对于全国655个城市的总量,覆盖率并不高。并且,调查对象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对其他社会青年群体,特别是农村青年群体未能予以全面覆盖。其二,在分析政治效能感对政治表达的影响时,本文重点考察政治效能感可能发挥的中介作用,并未对其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其三,本研究虽然对公民的线上和线下政治表达进行了研究,但对线上政治表达的测量仅覆盖微信和微博平台,对线下政治表达的测量只涉及合法的抗议和游行,并未测量线上和线下非法、暴力和非理性的政治表达,测量并非特别严谨和准确。当然,这些不足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启发,未来的政治效能研究可以对这些不足进行修正与完善,并做进一步探索。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李晶晶]
2016-12-05
卢家银(1979—),男,甘肃永昌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媒介法与政治传播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交媒体对当代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与引导机制研究》的阶段成果(批准号:14CXW032)。
G206
A
1000-5072(2017)03-01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