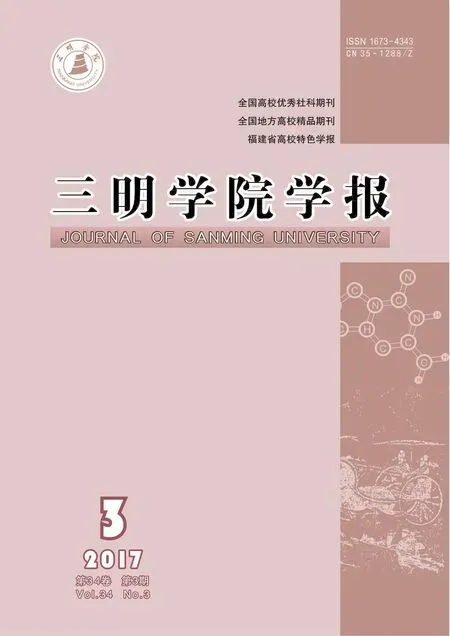“江南三部曲”的中国式虚构与抒情
2017-04-13冯跃华
冯跃华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江南三部曲”的中国式虚构与抒情
冯跃华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江南三部曲包含“虚构”与“抒情”,在“写实”与“载道”的传统之外,接续了中国文学“虚构”与“抒情”的文学能力,且迥异于西方。在虚构技巧方面,江南三部曲自“写实”中生发出幻灭与诗意;在抒情风格方面,江南三部曲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抒情传统,包括“红楼遗梦”“纸上江南”两大文学传统。江南三部曲的“虚构”与“抒情”体现了格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这一深刻思考被深深地嵌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创作的范式转换之中。
江南三部曲;虚构;抒情;格非
小说的发展实际上历经了一个从“虚构”到“写实”的过程。就近百年的文学史来说,谢冕曾用“辉煌而悲壮的历程”来概括,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1](P1-3)这样的评判当然有其道理,但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并未截断虚构与抒情的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的庐隐和废名,直至新时期以来的邓友梅、贾平凹、汪曾祺等人,虚构与抒情的传统一直作为文学创作的一股“潜流”存在。但可以明显看出,虚构与抒情的传统毕竟只限于少数作家以及少数作品,实际上,这一传统成为了强大的写实传统中被压抑的“他者”。中国当代文学中以虚构与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创作,多受西方荒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而并未接续中国文化内部生发出带有鲜明中国色彩的虚构与抒情。格非江南三部曲(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三部小说组成)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况,它是“来自东方的他者”,属于典型的中国式虚构与抒情。
一
一般而言,虚构特征明显的小说在时间上总是指向未来,空间则指向一个与世隔绝、遗世独立的地方。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写于20世纪初期,时间则指向60年之后;王小波写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时间指向了2015年、2020年;柯云路的《孤岛》设置了一个封闭性质的空间:被洪水围困的小岛;梁晓声的《浮城》则把故事的发生空间安排在一块和大陆架断裂的孤岛之上。这些小说都是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设置使文本具有强烈的虚构性。但江南三部曲完全指向了过去,江南三部曲的时间跨度从民国时期一直到当代社会,但完全没有涉及未来世界。江南三部曲的空间指向也很奇特,它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环境,而是呈现出一个扩大化的趋势(从普济岛梅城到鹤浦)。此外,江南三部曲虽表现出明显的虚构气质,但这种虚构的呈现并不根源于强劲的想象力,而是从个人的角度进入历史,用写实的手法来描摹历史,怪力乱神之事在江南三部曲中几乎不存在。江南三部曲的虚构气质并不呈现为鬼怪之事、荒诞之流亦或是十分夸张的想象,而是在幻灭与诗意两个层面呈现其独特的虚构气质。
幻灭感的产生首先体现在人物设定方面。无论是《人面桃花》中的陆秀米,还是《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作者将他们置于时代风暴的中心,却又给他们以局外人的身份,从而产生一种巨大的错位感。他们身上都具有一种泛哈姆雷特式的性格,有一种“骨子里的犹豫和忧郁,一种深渊或自毁的性格倾向,有局外人或走错了房间的错位感,有一种狂人或幻想症式的精神气质”[2](P6)。如此,便在历史的主人公与叙事的主人公之间产生了一种对立。一方面,叙事主人公沉浸于自我建构的内心世界之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外在世界逐步抛弃了这些“革命者”,革命的发起人最后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在二者的对立之中,格非消解了革命者作为“此在”对于世界这一实体的意义,一种巨大的错位感和幻灭感就此产生。在叙事方面,江南三部曲以三代知识分子对乌托邦的追求为主线,衍生出诸多根须式的叙述,使得文本呈现出一种“漂浮”的状态。三代知识分子对乌托邦的追求在文本中并未占据主要篇幅,主要情节被“淹没”在“旁枝末节”的叙述之中;江南三部曲整体上可以说是一种轮回式的结构,从《人面桃花》中的父亲下楼、秀米初潮直至《春尽江南》的家玉之死,格非写道:“端午已经开始写小说。因为家玉是在成都的普济医院去世的,他就让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普济的江南小村里。 ”[3](P372)如此巧妙地一笔,使得三部小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江南三部曲的叙事节奏逐步加快,在文本前一半,格非对故事中的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叙述,甚至会有很多细枝末节、旁逸斜出的东西。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叙事节奏逐步加快,故事的主人公都在一种莫名的力量的推动之下莫名地奔向死亡,如同飞蛾扑火、旅鼠迁徙。这种结构上的循环和叙事节奏的有效控制亦产生一种幻灭的感觉。
诗意的产生首先源于语言。格非的语言偏向于《红楼梦》的语言:优雅、精致、纯粹,富有古典气质。总体而言,江南三部曲的语言简洁而富有诗意。在平实直白的语言中,具有一种抒情写意的气质(受废名小说的影响,格非的小说创作甚至可以被称为抒情写意式的小说)。这种气质有时内含一种淡淡的悲哀,有时则表现为一种庄禅式的空灵。江南三部曲实际上是采用了两套叙述语言:一套描摹理想生活,温暖而富有诗意;另一套描摹现实生活,简单、直接,甚至稍显粗鄙。在两套语言的对比之中,诗意气质更为明显。
其次是景物描写。当格非想到了冰,想到了在瓦釜中迅速融化的冰花,格非就想到了秀米的过去和将来,想到了整部《人面桃花》;当格非想到了阳光下无边无际的紫云英花地,想到了花地中矗立的一棵孤零零的苦楝树,格非就想到了姚佩佩,想到了谭功达和《山河入梦》。如此一来,瓦釜中迅速消融的冰花、无边无际的紫云英和孤零零的苦楝树可谓是《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的创作“原点”。但这种“原点”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原点”,同样也是小说语言和格调的“原点”。从这三个简单的景物描写出发,江南三部曲的整个格调被限定在了一种诗意的表达之中。此外,江南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在江南,格非在文本中选取了大量的景物进行了描绘,淅淅沥沥的江南烟雨、隐于深山老林的招隐寺、大片的紫云英、荷塘中的紫色睡莲等景物,使人不自觉地沉浸于对江南的诗意幻想之中。
最后,从初始的《祭台上的月亮》到最后的《睡莲》,从彪德西到海顿、莫扎特,格非在叙述中穿插了对诗歌、音乐的叙述和描绘。虽然文本中对诗歌和音乐的穿插只占据很小的一部分,但这种插入使得文本的故事时间出现了停顿,这种停顿短暂却至关重要,起到了一种“芥子纳须弥”的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每一首诗歌、每一首音乐中都蕴含着现实时空之外的另一个时空,这另一个时空又是具有诗意的时空。随着另一个时空的出现,轻易地打破了第一个时空的滞重感,将文本笼罩在诗意之下。更重要的是,对诗歌和音乐的描绘不仅是作为叙述的道具来运用,而是为了契合了整部小说的基本格调,在诗歌与音乐大量的穿插下,文本逐步脱离写实,显现出一种虚构气质。
二
格非的幻想和其他人的幻想迥然不同,其根源在于,江南三部曲并非福柯式的“历史编撰学”那样五光十色的信息杂糅所产生的历史修辞,而是成功地将这种叙述“归入了‘中国经验’的根部和谱系之中”[4](P48)。
在张清华看来:“他(格非)为当代中国贡献了独特的叙事,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修复了几近中断的‘中国故事’——从观念、结构、写法、语言乃至美感神韵上,在很多微妙的方方面面。在他的手上,一种久远的气脉正在悄然恢复。”[5](P84)确实,在江南三部曲中出现了一种“魂兮归来”的迹象,但这种迹象的出现并非毫无缘由。总的来说,文学创作出现了一种认同的转向,这种认同就是当代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审美风格的继承和回归。随着文化认同的转向,一个迫切的问题便是:“当代文学创作如何继承和再生中国的文化意识与审美意识。”这种转向作用于格非身上,就是格非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界定。他将中国文学的传统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小传统便是五四以来在外国文学影响下的文学传统,而大传统则是以《红楼梦》《金瓶梅》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在格非看来,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一重写意,一重写实;一重模糊混沌,一重具体清晰;一重简洁含蓄,一重重复与完整”[6](P9)。 进一步,格非从抒情性的角度定义了中国小说传统。江南三部曲和 《红楼梦》虽然在叙事内容上差异巨大,但二者在文化意蕴和审美风格上却极其相似。从这一点来理解,江南三部曲可以称之为“红楼遗梦”。
在格非看来,中国文学有一个坚硬的内核:感时伤生。而感时伤生的核心只有一个字:悲。从《诗经》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屈原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杨慎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到《红楼梦》的“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些都是“悲”的体现。 这种“悲”,既是“悲壮”,亦是“悲惨”,更是“悲哀”,在这种“悲”的氛围之中,中国传统文学生发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观念和审美风格:一种神秘主义式的宿命与轮回,一种永续的重复和幻灭。《山河入梦》中的一首词可说是“拟古”之作:
见过你罗裳金簪,日月高华
见过你豆蔻二八俊模样
见过你白马高船走东洋
见过你宴宾客,见过你办学堂
到头来,风云暗淡人去楼空凄惨惨天地无光
早知道,闺阁高卧好春景
又何必,六出祁山枉断肠
如今我,负得盲翁琴和鼓
说不尽,空梁燕泥梦一场[7](P9)
这首词和《红楼梦》的诸多诗词具备相同的哲学观念和审美风格。这首词描绘的是《人面桃花》的主人公陆秀米的一生,其中东方的轮回、宿命观念显而易见,一种永恒的幻灭感透纸而出,让人产生“人生如梦”的感觉。从文本来看,陆秀米的一生真可谓是“大梦一场”,她的一生充满了宿命的色彩,从父亲出走的那一刻起,到与革命人士张季元的恩怨纠葛,出嫁的过程中被劫到花家舍,再到之后的走东洋、办学堂,直至结尾在瓦釜的凤凰冰花之中看到离家出走的父亲和未来的儿子谭功达。她的一生处于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之中。不仅她无法摆脱,当陆秀米在凤凰冰花中看到了谭功达之时,结局便已经注定了,他的儿子谭功达,甚至是他的孙子谭端午同样摆脱不了。三代主人公都无法摆脱这一奇怪的宿命,而在一种无法解释的力量的推动之下,进行着永续的重复与不断的轮回。因此,上面的这首词不仅是对陆秀米一生的注解,更是对整个江南三部曲的注解,他们三个人的命运奇妙地变成了一个人的命运。这种不可理解的宿命,不断的重复和轮回,使得文本具有一种强大的神秘感、幻灭感,也支撑起了江南三部曲的哲学观念和审美风格。这样的哲学观念和审美风格,投射到文本的形式上,便是人物与历史的错位、人物性格的犹豫和忧郁、叙事的逐步加快、草蛇灰线手法的运用、轮回式的文本结构、语言的古典化等等。
三
江南三部曲还塑造了一个“纸上江南”。所谓“纸上江南”,它不仅指作为地理空间的江南,也不仅是一种精神空间上的江南。“纸上江南”在更多意义上指向爱德华·索亚所谓的第三空间。“纸上江南”既包括地理学意义上的江南,也包括作为精神空间的江南。它既是真实也是虚构,既是精神又是物质,主体和客体同时存在于这一空间,“而这一空间将永远保持开放的姿态,永远面向新的可能性,面向去往新天地的种种旅程”[8](P35)。
最早的江南并非作为一种想象空间而存在,作为地理空间的江南本身便具有一种诗性审美。以汉乐府《江南》为例: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首诗本是采莲之时所唱之民歌,完全是一副现实图景,并非一种想象的江南,但其中自有诗意。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初步改变,《西洲曲》写一对男女恋人之间的相思之苦。但对江南的景色进行了大量的铺陈和想象,江南不再仅仅是一副现实生活图景。而对江南想象的最终定性应该是在唐朝,唐朝的诗人对江南进行了大量美好而富有诗意的想象,王勃在《采莲归》中写道:“官道城南把桑叶,何如江上采莲花。”王勃明确将桑叶和莲花进行了对比。这里不仅是一种南北方现实图景的对比,更是对江南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其后,数不尽的诗人共同参与了对江南的想象,杜甫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韦庄的“人人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苏轼的“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纸上江南”逐步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想象中固定下来。
当代文人继承了对“纸上江南”的想象。吴晓东写道:“我第一次去江南之前,关于江南的想象都来自于文学作品,我早已经建构了关于南方的形象。到了南方之后才发现,真正的南方和我想象中的并不一样。奇怪的是,以后我再想起南方,脑海里出现的仍然是文本中想象化的南方,而不是现实中我见过的南方。”[9](P58)“纸上江南”就这样在中国文人的记忆中一直流传,它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江南,更是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它不仅是山明水秀、风景如画的江南,更是象征着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一种远离红尘喧嚣、避开俗世繁华、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诗意生活。
江南三部曲所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纸上江南”。文本中有大段关于江南景色的描绘,以江南风景中最具典型性的莲花为例,格非就写了很多莲花,不仅有《春尽江南》中招隐寺院外池塘里紫色的睡莲,“荼靡花事”门前廊檐下的睡莲,呼啸山庄的一池莲花,还可以想到附录中那首名为《睡莲》的诗,甚至还有《人面桃花》中秀米和喜鹊种出的两缸莲花,《山河入梦》谭功达和小韶乘船谈心的芙蓉浦中如天幕一般的荷花。不仅是江南的风景,甚至格非在形容其他事物之时,也在用江南风景进行转喻,如:“那瓦釜竟发出当当的金石之声,有若峻谷古寺的钟磐之音,一圈一圈,像水面的涟漪,慢慢地漾开去,经久不息;又如山风入林,花树摇曳,青竹喧鸣,流水不息。 ……”[10](P68)
在风景如画的江南美景中,一种诗意化的生活方式悄然生发。在《春尽江南》中,主要表现为以谭端午为代表的人物群体同整个社会的对立。在现代化的滚滚浪潮之下,谭端午偏偏要寻找一个“纸上江南”。主人公谭端午远离时代中心,这既是时代的发展,也是一种自觉。在一个“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的年代,端午兢兢业业地写着一首叫作《牺牲》的诗,只是不再拿去发表;他热爱古典音乐,“每天听一点海顿或莫扎特,是谭端午为自己保留的最低限度的声色之娱”;更奇怪的是,他总是捧着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在读,直至文本的结尾,端午终于读完了它,给端午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呜呼”二字。谭端午身上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一种“落伍的超然”,由于年久失修,方志办的大楼古旧而残破,灰泥斑驳,苔藓疯长。方志办的工作亦百无聊赖,用家玉的话说,“他正在那个小楼里一点点地烂掉”,“而端午倒有点喜欢这个可有可无、既不重要又非完全不重要的单位,有点喜欢这种正在烂掉的感觉”。在百无聊赖的时光中,端午悠闲地读着他心爱的聂鲁达和里尔克,听听音乐,写写诗歌,和冯延鹤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庄子,谈论着“无用者无忧,泛若不系之舟”之类的话语。不仅谭端午的生活和世界相隔膜,就连端午的朋友都和他一样,徐吉士并非一个趋炎附势的文化官员,韩守仁也不是利欲熏心的奸诈商人,绿珠则“喜欢戈壁滩中悲凉的落日。她唯一的伴侣就是随身携带的悲哀”。呼啸山庄被设置成一个“被围困的孤岛”,是端午、吉士、守仁、绿珠四人的“私人会所”:“花园的东南角新建了一座八角凉亭。凉亭边有一座太湖石堆砌的假山……花园里原先有一个挖了一半的水坑,守仁曾想修一个露天游泳池,现在则在四周砌上了青石,养起了莲花。 ”[3](P30)四人之间的交往,也并不掺杂任何利益关系,他们都是不修边幅,散淡处世,厌倦生活的方外之人。它们终究是不属于这个资本统治一切的年代,而更像是生活在烟雨江南之中的中国传统文人。
自1840年起,中国便一直奔波于“追求现代性”的道路之上。于文学而言,则是一个不断抛弃传统、走向现代,抛弃本土、走向世界的过程,文学的发展陷入了“现代性”的困境——文化同质化。然而,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言,“现代性是一个复数。”在不断的“模仿”中,“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逐步在“西方”这一“镜像”中发现了“自我”这一“主体”的存在,逐步觉醒了其“东方特性”。表现于文学、文化上,这又造成了对传统文学、文化的难以割舍。这种“中心化”的心理情结,加之以民族主义、新儒学的复兴以及各种“后”学理论的全面开花,使得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了一次“范式转换”,以本土对抗世界、以传统对抗现代的呼声在对80年代“启蒙”的批判中日益高涨,这便是江南三部曲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为曾经的先锋作家,格非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发展脉搏。江南三部曲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格非对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深入剖析的结果。在一个人人尊崇现实的时代,格非讲述了一个有关幻想的故事;在一个人人追求现代的时代,格非讲述了一个有关传统的故事;在一个人人追求西方的时代,格非讲述了一个有关东方的故事。这或许就是江南三部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1]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2]张清华.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J].当代作家评论,2012(2).
[3]格非.春尽江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4]王小王.格非:《江南三部曲》:确有可能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格非《江南三部曲》学术研讨会发言纪要[J].作家,2012(10).
[5]张清华.知识,稀有知识,知识分子与中国故事——如何看格非[J].当代作家评论,2014(4).
[6]郭冰茹.回归古典与先锋派的转向——论格非回归古典的理论建构与文本实践[J].文艺争鸣,2016(2).
[7]格非.山河入梦[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2.
[8]陆扬.析索亚“第三空间”理论[J].天津社会科学,2005(2).
[9]刘永.江南文化的诗性精神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0.
[10]格非.人面桃花[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刘建朝)
On the Chinese Style Fiction and Lyricof the"Jiangnan Trilogy"
FENG Yuehua
(College ofLiterature,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Jiangnan Trilogy"is full of"fiction"and"Lyric"in the"realism"and"moral"tradition,following the literary competence of"fiction"and"Lyric"of Chinese literature,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literary competence.In the fictional techniques,Jiangnan Trilogy produces disillusion and poetic lyric stylefrom the"realism";in terms of lyric style, itinheritslyric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including the two major literary tradition of"Red Mansions"and "Jiangnan Paper".In addition,the"fiction"and"lyric"of Jiangnan Trilogy reflects Gefei's deep thinking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which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paradigm shift of the literary creation in 1990s.
Jiangnan Trilogy;fiction;lyric;Gefei
I207.42
A
1673-4343(2017)03-0057-05
10.14098/j.cn35-1288/z.2017.03.010
2017-03-06
冯跃华,男,河北邢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