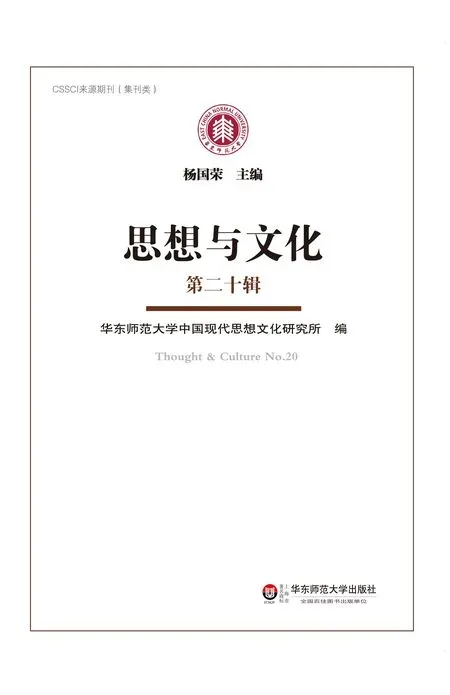冯友兰对宋儒“义理之性”概念的诠释*
2017-04-11
●
冯友兰新理学思想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基本形成,抗战期间是其哲学体系的完整建构时期,其间包含《新理学》在内的思想成果奠定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冯友兰《新理学》立足新实在论,以理性主义的视域,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传统理学予以梳理和改造,将传统理学概念灌注以新的思想内涵。冯契说:“‘新理学’的真正贡献在于他将逻辑分析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使得蕴藏于传统中国哲学中的理性精神得到了发扬。”*郑家栋、陈鹏主编: 《解析冯友兰》,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宋代儒学尤其是朱子学构成了冯友兰新理学的思想源头。理性精神的发扬与其说是注重对于历史上传统理学思想的分析与解释,不如说更注重在未来学意义上对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新导向。这一诠释工作的展开是具体的,解析冯友兰对宋儒“义理之性”概念的发展,对于透视冯友兰新理学思想以及由此理解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宋儒“义理之性”本义
明代学者尤其是心学派学者对于宋儒人性论一以拒斥,其中以谈及宋儒“义理之性”观念时尤甚。本文所用“宋儒”概念,均系沿用明代学者之意义。考索文献可见,明代学者此处所使用“宋儒”概念实际指称的是“朱子学”*“朱子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随着近年来相关研究系统化和成熟化的提升,特别是随着朱子门人后学思想研究与朱子讲侣思想研究的推进,已然成为中国当代学术的重要语汇。2013年10月18到21日,“张栻思想与现代社会国际论坛——纪念张栻诞辰880周年”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陈来教授于致辞中详细阐释了“朱子学”概念。他指出,“朱子学”虽冠名以“朱子”,但作为一个学者共同体,此概念包含朱子本人的思想、朱子门人后学思想与朱子讲侣学友思想。详见蔡方鹿主编: 《张栻与理学》,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页。,尤其是朱子本人及其门人后学相关思想。“义理之性”概念系朱熹永嘉弟子陈埴(1176—1232)提出和详细阐释。明代心学派学者以性二元论对“宋儒”的“义理之性”观念进行批判,一是由于张载、二程、朱熹的相关论述为陈埴“义理之性”概念的拈出提供了逻辑和思想条件,一是出于这一称谓显然有利于他们对“宋儒”心性论做整体性否定。
对于宋儒“义理之性”概念本义的澄清,可以一个关于“义理之性”的回顾开始探讨。明儒唐鹤征主张“天地之间只有一气”,认为:“心性之辨,今古纷然,不明其所自来,故有谓义理之性、气质之性,有谓义理之心、血气之心,皆非也。性不过是此气之极有条理处,舍气之外,安得有性?心不过五脏之心,舍五脏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处在方寸之虚,则性之所宅也。”*黄宗羲: 《明儒学案》上册,北京: 中华书局,2008年,第605页。在《木钟集》中,陈埴曾区分“血气之性”、“气禀之性”等。唐鹤征认为,就像不能说“义理之心”“血气之心”一样,不能承认有相对待的“义理之性”、“气质之性”。杨东明主张“盈天地间皆气质”,并认为“气质之性四字,宋儒此论适得吾性之真体”,但谈到“义理之性”时,他则说:“今谓义理之性出于气质则可,谓气质之性出于义理则不可,谓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合并而来,则不通之论也。”有问:“孟子道性善,是专言义理之性乎?”杨东明答曰:“世儒都是此见解。盖曰专言义理,则有善无恶,兼言气质,则有善有恶,是义理至善而气质有不善也……孟子道性善,就是道这个性。从古圣贤论性,就只此一个。……自宋儒分为气质义理两途,而性之义始晦。……故识得气质之性,不必言义理可也,盖气质即义理,不必更言义理也。识得气质之性,不必言气质可也,盖气质即义理,不可专目为气质也。学者悟此,则不惑于气质义理两说矣。”*黄宗羲: 《明儒学案》上册,第649页。陈埴在回答门人“孟子道性善,盖谓性无有不善也”时,有曰:“孟子专说义理之性。”从其“世儒都是此见解”可知,在杨东明看来,当时持“宋儒”见解的人之众。陈埴说:“才识气质之性即善恶方各有着落,不然则恶从何处生?以孟子说未备,故程门发此义。孟子专说义理之性,专说义理则恶无所归,是论性不论气。孟子之说为未备,专说气禀则善为无别,是论气不论性,诸子之论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质论性。”*陈埴: 《木钟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7页。可见,陈埴在程朱之后标立“义理之性”概念,在结论上本与杨东明一样是为了解决立足孟子传统性善论立场上如何解决现实人性恶的问题。不过,他们立论的角度明显不同。
刘宗周一样立论意欲横扫自张载、二程至朱熹陈埴的人性论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是性与气,分明两事矣。即程子之见,亦近笼统。凡言性者,皆指气质而言也。或曰:‘有气质之性,有义理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又,“或曰有‘气质之性’,有‘义理之性’,则性亦有二与?为之说者,本之人心道心而误焉者也。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若既有气质之性,又有义理之性,将使学者任气质而遗义理,则‘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之说信矣!又或遗气质而求义理,则‘无善无不善’之说信矣!又或衡气质义理而并重,则‘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说信矣!三者之说信,而性善之旨复晦,此孟氏之所忧也。须知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所以为性也。”又,“性只有气质之性,而义理之性者,气质之所以为性也。”又,“故宋儒气质之说,亦义理之说有以启之也。要而论之,气质之性即义理之性,义理之性即天命之性,善则俱善”。*黄宗羲: 《明儒学案》下册,北京: 中华书局,2008年,第1539页。
刘宗周细致分析了标举“义理之性”观念对于儒学人性论的理论弊端,并主张消解宋儒义理之性。黄宗羲评刘宗周“性命之辨,莫明于此”,并指出“宋儒”之论“岂不误哉?”*黄宗羲、全祖望: 《宋元学案》,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第612页。黄百家亦曾有以按语曰:“只为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分析后,便令性学不明,故说孔子言性是气质之性,孟子言性是义理之性。愚谓气质还他是气质,如何扯着性?性是气质中指点义理者,非气质即为性也。”*黄宗羲、全祖望: 《宋元学案》,第695页。
又,黄氏在按语中驳张载“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时说:“性既在此气质,性无二性,又安所分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乎?”*黄宗羲: 《明儒学案》下册,第983页。
冯从吾则认为“吾儒之所谓性,在知觉运动灵明中之恰好处,方是义理之性。”黄宗羲评曰:“其论似是而有病。”又冯氏认为:“圣贤学问,全在知性。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如以义理之性为主,源头一是,则无所不是。”黄宗羲以“皆末流之论也”评之。*黄宗羲: 《明儒学案》下册,第983页。
综上所述,明代学者尤其是心学派学者在心性论上以拒斥和批判“义理之性”而否定“宋儒”。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一种特定思潮在结构上具有三种要素: 范式、研究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如果我们将“宋儒”看作一个研究共同体的话,上述明代学者是在一个全新的心学研究范式中对传统所作的批判。
陈埴在回复学生问“程子说性与孟子不同”时答曰:
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禀赋之不齐,故先儒分别出来谓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仁义礼智者,义理之性也。知觉运动者,气质之性也。有义理之性而无气质之性则义理必无附着,有气质之性而无义理之性则无异于枯死之物,故有义理以行乎血气之中,有血气以受义理之体,合虚与气而性全。孟子之时,诸子之言性往往皆于气质上有见,而遂指气质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他义理上说,以攻他未晓处。气质之性,诸子方得于此,孟子所以不复言之;义理之性,诸子未通于此,孟子所以反复详说之。程子之说正恐后学死执孟子义理之说而遗失血气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 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程子之论举其全,孟子之论所以矫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达孟子之意,则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陈埴: 《木钟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第704页。
即性是具于人心的天理,由于禀赋有差异,所以先儒将性分别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其中,仁义礼智是人之义理之性。知觉运动指的是人的气质之性。若仅有义理之性而没有气质之性,则义理没有附着安顿处。若仅有气质之性而没有义理之性,则人之性无明无识就像枯死之物一样,所以人性中有义理运行在血气之中,而血气承载着义理,有虚灵不昧之体还有血气才组成人性的整全。孟子之时,诸子论性往往只是从气一面看,而认气质为性,这只是明了人性中的形而下者,因此孟子回应这些人时单就义理一面说,以回击其未明之处。因为诸子已然明了气质之性一面,所以孟子没有再从气质一面讨论;而诸子未明义理之性,所以孟子对此形而上者予以详细讨论。程子论人性在于唯恐后学者机械地秉持孟子从义理一面论性而遗失了血气之性的一面,因此将二者并重言之曰: 只论性而不论气是不完备的,只论气而不论性是不明通的。程子论人性是从性之全体来看,孟子论人性是出于矫正诸子论性的偏弊。后学者如能即程子的人性学说而通达孟子论性的真正意图,则二者论人性的不同之处就不待分别而自然明了。
陈埴论“义理之性”在《木钟集》中多处可见其细致分析和阐释,兹不多引赘述。正如陈来先生分析朱子心性论所言:“如果在同一层次上来,不能说在气质之性以外另有本然之性。”*陈来: 《朱子哲学研究》,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6页。而对于陈埴,如上“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待发明,则是在理学本体论进程中又推进一步。“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显然已是两个层次的概念。如果说朱子的人性论是一元而二层的,那么陈埴的人性论则是一层而二元的,即陈埴的“义理之性”不再停留于程朱只是在“继之者善”的先天层面讲,而是允诺作为性的性之本体的存在,即义理之性指谓的是作为现实人性所依照的本然标准的、形上的和全善的理,这与程朱无论在时间还是在逻辑上的不同阶段上论述有质的差异。而这种二元论学说不仅构成后来心学派学者攻击的目标,同时也是后来冯友兰立足新实在论利用“义理之性”加以阐发新意的原因和基础。
二、 冯友兰对“义理之性”概念的诠释
显然,如上所述,对于宋儒“义理之性”概念在明代适应过程的回顾与对于此概念本义的澄清是一个过程。陈埴“义理之性”概念所含蕴的一层而二元式的人性论,实际上是对程朱理学道德形而上学进程的又一推进。而如果说“义理之性”是陈埴人性论的结论,则冯友兰对于“义理之性”二元性一开始就是作为前提和基础而自觉运用的,其所立足的是西方哲学关涉事物存在“共相”理论的新实在论。如有的学者所描述的:“冯友兰一直认为,最哲学的哲学应该是形上学,它的实际内容是本体论。”*单纯: 《旧学新统——冯友兰哲学思想通论》,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又,“就新理学作为最哲学的哲学,它是形上学。”*高秀昌: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9页。而下面将揭示,与西方共相理论一样,冯友兰为“义理之性”这一“概念套子”灌注了新内涵,这一内涵溢出了儒家道德形而上学,是包含了物性论在内的哲学形而上学。
对于“真际”与“实际”两个世界的区分,可以说是冯友兰新理学思想的立言宗旨。正如张岱年先生在《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中说:“《新理学》的中心观点是两个世界的学说……所谓两个世界,一个是真际世界,一个是实际世界。真际世界又称‘理世界’。区别两个世界,这是新理学的基本观点。”*郑家栋、陈鹏: 《解析冯友兰》,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6页。对于新理学中具体观念和观念的理解和诠释需要以此为准衡。冯友兰说:“哲学底活动”在于“由知实际而知真际。”*冯友兰: 《贞元六书》,北京: 中华书局,2014年,第221页。又,“哲学是以真际为其研究之对象。”*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178页。在冯友兰新理学中,真际是洁净空阔的理世界,是实际之所“依照”者。他否认“真际即是实际;实际之外,别无真际”*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178页。的观点,主张真际即理世界的客观性。冯友兰讲:“我们的主张,可以说是一种纯客观论。”*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40页。又,“我们的纯客观论则主张不独一件一件底实际底事物是客观底,即言语中之普通名词或形容词所代表者,亦是客观底,可离一件一件底实际底事物而独有。不过此所谓有,只是就真际说,不是就实际说。”*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46页。按冯友兰的逻辑,真际与实际都可以说是客观存在的,只是需要注意真际的客观存在与实际的客观存在不同,是在“思与辩”中把握的。陈来先生认为:“理学的理是内在于气或事物之中的,而‘新理学’则不肯定这一点。”亦即,“照‘新理学’,形而上的基本意义之一即不可以在时空中,不可以在物之中,理只能被物所依照,而不能在物”。*陈来: 《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75页。冯友兰在阐释“何以名为新理学”时说:“理学即是讲我们所说之理之学,则理学可以说是最哲学底哲学。但这或非以前所谓理学之意义,所以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40页。所谓“最哲学底哲学”,一言其客观实存性,一言其纯形式性。冯友兰讲:“哲学或最哲学底哲学,所有之观念,命题,推论,多系形式底,逻辑底,其中并无,或甚少,实际底内容,故不能与科学中之命题,有同等之实用底效力。”*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20页。涂又光在《新理学: 理论与方法》中说:“逻辑分析方法,与西方现代其他哲学方法相比,有一个特点,就是使用这个方法,不会随之羼入内容。”*郑家栋、陈鹏: 《解析冯友兰》,第179页。总而言之,“义理之性”概念须在上述思想语境中才能得以准备理解和诠释。
正如贺麟先生在其《冯友兰的新理学》中所说:“冯先生认为任何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必依照理,必依据气。这是继承朱子认事物为理气之合的说法,而冯先生复特别对于朱子凡物莫不有理之说加以新的发挥。”*郑家栋、陈鹏: 《解析冯友兰》,第40页。“对于朱子凡物莫不有理之说加以新的发挥”,亦即冯友兰自述“理之学”。只是在冯友兰,理并非如朱子所认为是实际地与气为一体的,理是一种非时空性的实存。在此意义上,理亦可称为义理,理之实现于具体的人、物或事即为性。义理之性即超然和外在于事物的一类事物之理,此理是且仅是关涉真的实存,不具有道德善恶属性。陈战国阐释冯先生“义理之性”时说:“义理之性即一类事物之理,气质之性即以事物所实现的理;义理之性是外在于事物的,气质之性是一事物所具有的;义理之性是绝对完全的,气质之性是不完全的。”*陈战国: 《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义理之性一开始就是在超越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普遍层面展开阐述。冯友兰说:“性善性恶,是中国哲学史中一大问题。旧说讨论此问题者,皆是就人性说。但我们不妨将此问题扩大。我们所说义理之性及气质之性,既已不专就人说,所以我们于讨论人性之善恶之外,亦可讨论一切事物之性之善恶。”*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105页。这与宋儒以道德主义诠释社会和自然不同。冯友兰又讲:“在程朱及一般宋明道学家之哲学中,所谓善即是道德底善;而整个宇宙,亦是道德底。我们的说法,不是如此。我们以为道德之理,是本然底,亦可说是宇宙底。但宇宙中虽有道德之理,而宇宙却不是道德底。”*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112页。冯友兰谈论的“义理之性”概念不是在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中探讨的,即不能说义理之性是或不是道德的,毋宁说其问题域和着眼点非在于此。如此一来是否还有善恶问题呢?在冯友兰看来,善恶问题在于是否合乎实际事物实现自身所依照的标准及其程度。冯友兰说:“每一类事物,皆有其本然底标准,及其实现底标准。其本然的标准即是其理,其义理之性;其实际底标准即其类事物于一时普通所能达到之合乎其本然底标准之程度。”*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107页。又说:“所谓善者,即从一标准以说合乎此标准者之谓。从此标准说,合乎此标准者是善,则此标准即是至善。”*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107页。完全合乎某一标准者是善,亦即该事物之义理之性。同理,不善和恶就是不合乎和反乎事物之义理之性。冯友兰讲:“我们可以说,不合乎一标准者是不善;反乎一标准者是恶。”*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111页。即义理之性指的是超越于事物的本然标准。冯友兰详细阐释“义理之性”道:
一某类事物之义理之性,即某一类事物之所以为某一类事物者,亦即是某一类事物之理。程朱说,“性即理也”,正是就义理之性说。我们说某理时,我们是就其本身说。我们说义理之性时,我们是就依照某理之事物说。所以义理之性虽即是理,但因说法不同而可有二名。义理之性即是理,是形上底,某一类事物必依照某理,方可成为某一类之事物,即必依照某义理之性,方可成为某一类之事物。某一类之事物,于依照其理,即其义理之性,而成为某一类之事物时,在实际上必有某种结构,能实现某理者。能实现某理之某种结构,是实际底,形下底,即是此某种事物之气质或气禀。此某类之事物,虽均有某种气质或气禀,以实现其理,其义理之性,但其完全之程度,则可因各个事物而不同。因此此类之各个事物,实现其义理之性之程度,又可各个不同,有实现其八分者,有实现其七分者。此其所实现之八分或七分,即此事物之所实际地依照于其义理之性者,此即其气质之性。*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101页。
至此我们可以归结出冯友兰“义理之性”的三个特性: 一是,义理之性是事物超越的形上本体,虽不具有时空性,但却具有客观实存性;二是,义理之性虽实质上同于理,但义理之性的称谓本身指向事物本然的绝对标准,实际中一时一地的事物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其标准,与义理之性本身无涉;三是,义理之性不是伦理学和道德哲学论域中的概念,其所关涉的善恶问题在内涵上包括人类社会中的伦理善恶问题。
事物之本然标准的涵义对于冯友兰义理之性的理解如何推举都不为过。不惟一个“义理之性”的概念,“哲学”本身也被如此衡定,冯友兰讲:“我们的哲学是最哲学底哲学,意即是说,我们此派的哲学,是最依照‘哲学’者,最依照哲学之本然系统者。我们的新理学与程朱的旧理学,俱属于此所谓我们此派,但我们的新理学,较旧理学更依照此派哲学的本然系统。”*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178页。即如果为冯友兰增加第三个“何以名为新理学”的原因的话,无疑就是强调新理学对于哲学之所以成其为哲学的本然标准的自觉,亦即“哲学”的“义理之性”。此前有学者虽已认识到:“冯友兰在照着讲的同时,将旧理学的某些命题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展。”*柴文华: 《冯友兰思想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2页。但未及展开论证,而将论述的重点转移在“冯友兰则对朱熹哲学中未明加阐发的地方给予清晰化,并做了相应地修正”*柴文华: 《冯友兰思想研究》,第433页。,这就难免对冯友兰特定哲学思想造成忽略。
三、 冯友兰对“义理之性”概念诠释的意义
后五四时代的新儒家哲学,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哲学家处在古今中西问题的激烈洪流中,他们的哲学研究本身就承载着反思与重建中国学术和中华文化精神的使命。这一思想特征在冯友兰哲学思想体系中反映尤其显著。新理学体系所着力的是现代新儒学形而上学的重建。
冯友兰阐述中外重要哲学家的思想成就时认为:“独其形上学,即其哲学中之最哲学底部分,则永久有其存在之价值。其所以如此者,盖其形上学并不以当时之科学的理论为根据,故亦不受科学理论变动之影响也。”*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22页。结合如上分析可见,冯友兰此论也是对于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建构的自我要求。他对于“义理之性”的新阐发就集中反映了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旨趣。这里需要申明,冯友兰所谓形上形下的标准是逻辑分析。如其言:“我们此所说形上形下之分,纯是逻辑底,并不是价值底。”*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44页。程朱理学的形而上学性是冯友兰利用其特定概念予以发展性诠释的主要原因,如他在辨析程朱理学与孟子哲学的主要不同点时所说:“在孟子哲学中无形上形下之分,所以其所说之性,是形下底,而在程朱哲学中,有形上形下之分,其所说之性,是形上底。”*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101页。这形上的性冯友兰表达为“义理之性”。冯友兰讲:“义理之性即是理,是形上底,某一类事物必依照某理,方可成为某一类之事物,即必依照某义理之性,方可成为某一类之事物。”*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101页。形而上者即属于真际世界,即实际世界中的事物实现自身所必依照者。“就真际之本然言,形而上者之有,不待形而下者,惟形而上者之实现,则有待于形而下者。”*冯友兰: 《贞元六书》,第45页。可以说,义理之性作为事物自身的本然标准,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依照而实现,是不会随之改变的。这与西方哲学中的共相理论相通。陈荣捷在《冯友兰的新理学》中说:“理是自存的,绝对的,永恒的,是公孙龙和西方哲学所理解的共相。”*郑家栋、陈鹏: 《解析冯友兰》,第81页。在《新理学》中,冯友兰实际也以其逻辑性肯定先秦哲学中公孙龙名学的哲学性。当然,作为一个思想整体,宋代理学的本体论特征是冯友兰借以阐发新说的原由。冯友兰哲学作为儒学第三期之一例自觉利用程朱理学思想遗产,可以说是儒学内在逻辑与文化历史的必然。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借由澄清冯友兰诠释宋儒“义理之性”概念的意涵,揭示新理学哲学思想的精神特质与理论宗旨,阐明新理学重建儒家形而上学的具体运思理路,从而也以此彰显冯友兰新理学形上学体系对于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奠定的新的理论基础。蒙培元在阐释冯友兰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贡献时说:“‘新理学’完成了一个概念体系,使中国哲学走向近代化的分析之路。”*郑家栋、陈鹏: 《解析冯友兰》,第183页。冯友兰借由西方逻辑分析方法诠释和重建儒家哲学体系虽不必然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唯一道路,但毋庸置疑的是,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确是当代儒学研究所不可绕过的重要思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