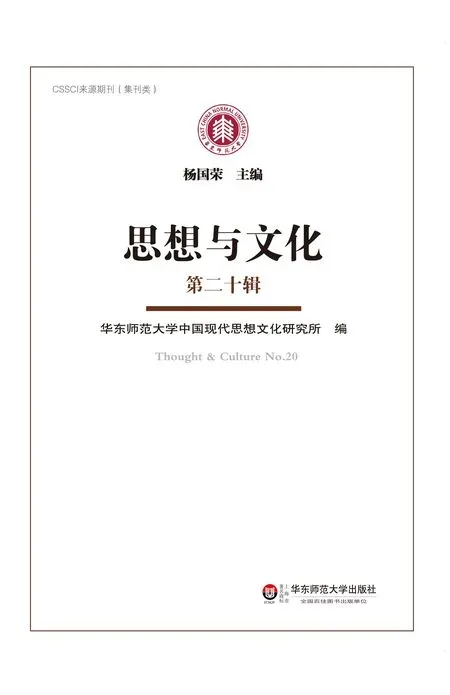日本“伦理学”概念构建中的儒学传统
——从早期“伦理学”教科书看日本国民道德之建构
2017-04-11
●
一 “伦理学”译介
若论近代伦理学(ethics)概念在东方的接受过程,首先要确认明六社引入伦理学概念时的情形。明六社因成立于明治六年(1873年)而得名,并创办有自己的杂志——《明六杂志》。中村正直以《西学一斑》为题,在《明六杂志》上介绍西洋学问的历史发展及其本质时两次提及ethics概念:
1. 上帝道革新の後〈天文年中〉、エチツク〈倫常の道、また修徳の道〉の学、おおいに明らかなることを得たり。*中村正直: 《西学一斑续译》,大久保利谦监修: 《明六杂志》(复刻版),东京: 立体社,1976年,第11号—3。
2. “エチツクス(人道の学、また修徳の学)”,*中村正直: 《西学一斑》,大久保利谦监修: 《明六杂志》(复刻版),第16号—3。
分别以“伦常之道”、“修德之道”、“人道之学”来解释西方ethics概念。这充分地表明,对当时的东方人来讲ethics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权且以儒教之“修德”相附会。同样地,在使用“伦理学”译介ethics之前,“伦理”一词的使用明显与西方意义上ethics的概念有所差异。我们在《明六杂志》可以找到几处“伦理”的用例。如,森有礼“正血统为欧美之通习,伦理之所在……如我国,轻血统之甚者,不行夫妇婚交之道,故至不知伦理为何”。*森有礼: 《妻妾论》,大久保利谦监修: 《明六杂志》(复刻版),第11号—2。西周:“人世之伦理纲常,恒定无变。”*西周: 《教门论》,大久保利谦监修: 《明六杂志》(复刻版),第9号—3。以“伦理”指代“人伦之道”、“共同体秩序”,与西方ethics概念无涉。西周之外,阪谷素在《转换蝶铰说》中提及,“徵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勇,一身之モラル”*阪谷素: 《交换蝶铰说》,大久保利谦监修: 《明六杂志》(复刻版),第35号。,用“モラル”表示moral;阪谷登载文章的38号刊上同时也刊登了西周的《人世三宝说》,于此刊号上,西周以“道德”翻译moral。另外,中村在《创造善良之母说》中提及:“我曾讲演改造人民性质说,以修身及敬神之教育(moral religious education,モ-ラル·レリチヲス‘エチュケーション)和艺术及学术之教育(art science,アートサイエンス)焕然人心,推进至一新的高度。”*中村正直: 《创造善良之母说》,大久保利谦监修: 《明六杂志》(复刻版),第38号。复将“モラル”译为“修身”。于是moral相对应的汉语因此便有两个:“道德”、“修身”。结合上文中村所举《西学一斑》中的译法,可知儒教中的“修身”一词可以同时用来翻译西方moral和ethics。
当然,仅从《明六杂志》的刊文,并不能全窥明治初期的思想状况,但却可以一窥ethics出现在日本后面临的种种翻译困难。也就是说,明治初期并未确定ethics的对应译词,译词中即便是“伦理”二字也并非用来指称西方世界语境中的ethics概念,“伦理”仍抱有东方语境中的“修身”性质。而且,日本人并未在moral和ethics的译词上做出区分。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的西方伦理学书籍,在输入日本明治政府前期,基本上都翻译为“修身”。根据《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明治期刊行图书目录》,直到明治二十年,发行的与伦理学相关的译书计有10册,其中7册以“修身”为标题,不涉及“伦理”用语。1875年平野久太郎将弗兰西斯·淮兰德(Francis Wayland)TheElementsofMoralScience译为《修身学》出版发行。此后,淮兰德的书复经多次转译,作为“修身”学科教科书被广泛使用。平野称“此书原名ElementsofMoralScience,即以修身,教说德行之道为学问之义”。*弗兰西斯·淮兰德: 《修身学》第1—4卷,《绪论》,平野久太郎译,东京,1875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将西欧的伦理学说逐渐导向对于儒教“修身”的理解,并以儒学解释西学,对“修身”在译介西方伦理学说时所发挥的作用充满期待。然而,明治二十年之后,伦理学相关译书达74册之多,内中以“修身”为题的仅3册,“修身”之用语几乎消失殆尽,以“伦理”为题的则多达54册。然而,无论是“伦理”还是“修身”,皆以儒教用语翻译西欧“伦理学”。直到19世纪末期,“‘ethics’即‘伦理学’”的译法才被固定下来。井上哲次郎开其先:“伦理学,之前将之译为修身学、道义学、德学,没有定着。我借用《礼记·乐记篇》中的伦理一词,将其翻译为伦理学。”以井上为中心编纂的《哲学字典》中已将ethics译为“伦理学”,而非如同之前那样译为“伦理”,开始区分“伦理”与“伦理学”。“伦理”取自《礼记》*《礼记·乐记篇》:“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但“伦理学”却是学科领域内的一个分支。自此,西方伦理学译作中,儒教意义上的“伦理”意味开始逐渐褪色。
1883年,井上哲次郎出版《伦理新说》,首次以专著的形式论述“伦理学”。井上在《伦理新说》中指出,“想要成为如我这般的哲学士,必要考究伦理之大本”,将“伦理之大本”作为“欲成哲学士”的目的。“昔首倡之伦理”,以新的实践规范为目的,而今之伦理学“以讲究伦理之大本为鹄的”。*井上哲次郎: 《伦理新说》,酒井清造等刊,1883年,第4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与平野在《修身学》绪论中对ethics的理解不同,井上已经脱离了儒教意义上解释伦理学的路径,开始在作为宇宙根源的“万有成立”上寻找伦理大本。
通过《哲学字典》、《伦理新说》阶段对于伦理学的翻译介绍,《明六杂志》中所见之“エチツク”、“伦理”、“人道学”、“修德之学”等用语已不复用来指代ethics所深具的含义,开始固定使用“‘ethics’即‘伦理学’”。
二 修身科: 日本儒学之教与西洋伦理学
“‘ethics’即‘伦理学’”的译介过程,不仅反映在学问领域,还在教育政策和修身教科书中有所体现。1871年明治政府设置文部省,选举精通欧美教育制度和行政事务的河津祐之和萁作麟详为起草委员,制定《学制》。《学制》的教育理念深受西欧个人主义影响,因而修身学科在《学制》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上等中学校的15个科目中,修身科排在了第13位;下等中学校16门科目中,则排在了第14位。因为修身学具有儒家伦理的意味,且时人尚未真正理解西方伦理学的真正概念,因此,学校虽允许外籍教师教授修身学科,但这些修身学科所传授的内容已经不是儒家道德意义上的修身学问,而是具有西方伦理学的某些实质性内容。为此,明治政府为修身科的传授限定了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大多从西方学者的著作翻译而来,被标记上了“修身学”的名称,实质上却与儒家道德不相干。其中包括淮兰德的日译本《修身学教授本》(moralscience)、哈本的《修身学》(moralphilosophy)。除平野的有关修身书的译本外,阿部泰藏译《修身论》(1874年)*弗兰西斯·淮兰德: 《修身论》后编第1—2卷,阿部泰藏译,东京: 文部省,1874年。以及河津祐之译《修身原理》(1884年)也由文部省编辑局陆续出版发行。*弗兰西斯·淮兰德: 《修身原理》,河津祐之译,东京: 文部省,1884年。
1879年,在元田永孚的主导下制定了《教学圣旨》,批判《学制》的教育理念,强调“教学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究智识才艺,以尽人道。我国祖训国典之大旨,在于教上下所有之人”。试图复活儒教道德。同年,《学制》废止,发布《教育令》。第二年,根据《改正教育令》,明治政府强化中央集权的儒教教育。1881年《中学教规则大纲》中,原本处于末位的“修身”学科被置于首要位置。在此政策的支持下,明治政府曾先后禁止在学校教育中使用翻译的教科书,并宣称这是对行之过度的欧化政策的反省,企图以此宣扬日本主义。但是,与“修身”相关的西洋伦理学教科书却未被彻底清除,依然在学校教育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使用。
如上文所言,1883年之后,日本人在学术领域已经厘清了西方ethics概念的含义,并使用“伦理学”一词与之相对译。也就是说,此时“修身”学与“伦理学”的定义界限已十分明确,“修身学”即是儒教道德学说,“伦理学”也仅指称西方伦理学之大本,早期翻译过程中“修身学”与“伦理学”之间的混乱状态已不复存在。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学制》中对于“修身科”与“伦理学”解释的西方主义倾向,使得具有东方伦理意味的“修身科”成为《学制》打击的对象的同时,试图在学校教育中引入西方伦理学意义上的“修身教科书”。因此,在《学制》行之有效期间,一些译介的西方伦理学教科书以“修身学”为题名得以在日本出版发行。然而,随着《教学圣旨》的颁布,日本民族主义氛围日渐浓烈,儒学中的伦理因素开始吸引统治者的目光,在教育政策上也有所倾斜,开始将末位的“修身”学科置于首要位置,成为竞相学习的对象。在此阶段,西方伦理学概念与东方儒学传统道德概念逐渐明晰,在《教学圣旨》的支持下,“修身”学科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宣称自己与西方伦理学之间概念上的差异,强调自身学科内容的优越性,以及蕴含于自身中的民族主义成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教育制度的制定才不惧学界对于西方伦理学概念的澄清,因为正是民族主义的兴起构成了西方伦理学与东方儒教传统概念区分的背景。由此,在贬低西方伦理学概念的同时,助长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日本特有的国民道德。
1886年,明治政府发布《中学校令》,在《寻常中学校之学科及其程度》(文部省令14号)中,将之前一直使用的“修身”学科名改为“伦理”(1901年又改回“修身”)。这不仅是名称上的改动,同时也意味着“‘ethics’即‘伦理学’”译词开始在教育制度内得到日本政府认可。《寻常中学校之学科及其程度》中,伦理科作为教授“人伦道德之要旨”的首位学科而受到重视(将修身和伦理作为首位学科是《改正教育令》之后明治政府一贯主张)。修身科向伦理科转换的过程中,开始了日本人自己编写伦理教科书的尝试。然而,“‘ethics’即‘伦理学’”概念的确立,伴随着教育制度上的儒教主义的情绪高涨。“‘ethics’即‘伦理学’”确立前,无论是平野的《修身学》,还是河津的《修身原论》,皆视西洋之“伦理学”与儒教“修身”之“本邦之教”相同一。而“‘ethics’即‘伦理学’”的确立,则意味着“修身”自“‘ethics’即‘伦理学’”中分离的开始。
由此,西洋伦理学说(ethics即“伦理学”)便与表示道德实践的“国民道德”区分开来了。不久,西欧伦理学翻译著作中,便不再使用“修身”一词,随之紧锣密鼓地重新构建国民道德与西洋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并且,日本人编写的修身教科书中,开始大力鼓吹日本优越论,日本传统文化以“国民道德”的姿态逐渐居于西洋伦理学之上。1900年井上哲次郎批判西方功利主义:“维新以来,世之学者,或倡导功利主义,或主张利己主义,致我国国民道德心之戕害。在国家经济主义层面犹可言功利主义,作为个人之唯一道德主义则不可。因于个人场合,一种他律的道德,对培养心德无所成效。”*井上哲次郎: 《日本阳明学之哲学》,东京: 富山房,1900年,第3—4页。并在1902年的《国民道德概论》中强烈要求进行有关国民道德的研究。
井上认为,明治以前,构成日本国民道德要素的是日本固有之精神、儒教和佛教。儒教和佛教传入日本之后,被日本的国民性同化,成为日本文明的要素。明治维新以来,西方文明进入日本,又丰富了日本国民道德的内容。但是,西方文明包含许多复杂的因素,甚至有一些具有破坏国民道德的不健全思想。为此,井上认为,应该以教育敕语要旨为中心,对其做出甄别。“道德,古今东西并无差别,但是,实施道德之手段、方法因境遇不同而有所差异”,此便为国民道德形成之原因。紧接着,井上讨论国体和国民道德之间的关系,即日本国民道德基于其日本国特有的国体,而日本国体则又以万世一系的皇统为基础,附带有七个特点: 国体与政体的分离,忠君爱国之一致,皇室先于国民存在,祖先崇拜,家族制度体系,君臣分明,国民统一体。对于国民道德而言,家族制度至关重要。家族制度,即谓由家长统率一家而组织形成的制度。在《敕语衍义》中描述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时,井上以父母与子孙的关系相比拟,“一国乃一家之扩充”,试图构建家族国家观。*井上哲次郎: 《国民道德概论》,东京: 三省堂,1912年,第277—278页。
在井上哲次郎的影响下,井上圆了(1858—1919)改变了原先对于伦理学的正确认知。《教育敕语》颁布之前,井上圆了在《伦理通论》中主张伦“理学”(ethics, moral philosophy,moral science)即理学(science)。伦理学即“论定善恶标准道德之规则,命令人之行为举动的学问”。“论定”是指从逻辑上考订究明。对此“古来世间所传之修身学”——孔孟之修身学,耶稣教之道德学,道义学——不过是假定臆想之物:
孔孟之修身学,以仁义礼让定人之道,唯不究明仁义礼让为人之道的理由,将其视作天然人人相守之既定事实,这只不过是假定而已。余窃以为,将此类修身学附以伦理学的名称恐有不当,而真正之伦理学即为理学(science),是为逻辑上考究种种事实,审定一定之规则,组成一派之体系的学问。*井上圆了: 《伦理通论》,东京: 普及社,1887年,第4页。
此时,井上的目标是在理学上建立伦理的新的基础。然而,《教育敕语》颁布后,井上认为,“人伦,道德之原理。不问世之古今,勿论国之内外,恒常为一而不为二”。但是,另一方面,又说,“依风俗、习惯、政治、国体之诸事差异,生一国一社会特有之道德”,承认道德的历史性和社会性。而且,“其特有之道德中,存一脉贯通之理法。讲究此理法,制定原理原则者,归之于伦理学之理论部分。考究应对其世其国之事情而生发之变化异同者,归之于伦理学中应用部分。在应用部分,亦有理论与实际之分。即追求因世因国不同而生不同道德之理由者,谓之理论。其理论已假定,仅修习其方法,谓之实际。今,余为便宜起见,讲授其学问中理论部分。名之为理论伦理学。涉及到应用的部分,名之为实际伦理学。与技术相关的,称之为修身法或修身术。而且,余所论者,为实际伦理学,即对一国一社会特有道德产生之原因过程进行论述”。*井上圆了: 《伦理通论》,第20页。
在承认伦理的普遍原理的前提下,井上提倡究明日本社会具体的特殊现象的实际伦理学,认为这种学问才是“日本伦理学”,将问题以普遍原理与特殊具现相结合的辩证法来把握。然而,井上却将教育敕语中“我邦教育,道德方针”作为前提,使理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显得迂阔,从而放弃了给予实际伦理基础的普遍伦理原则的逻辑究明。即放弃了早期作为science的伦理学的基本课题,失去将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根据所在。由此,伦理只不过是既存国家社会体制以及政治的手段而已。井上认为,日本、中国、西洋各具固有之国体,因而,各国皆异于其国体,教育、人伦的适用也应依据国体不同而有所差异。基于这样的认识,教育和道德,当然就要以此国体为基本进行组织了。他写《日本伦理学案》的目的,也不过是于“(日本)国体之上,适用教育道德,尊奉敕语圣意,”并由此“论定日本一种之固有伦理”。*井上圆了: 《日本伦理学案》,东京: 哲学馆,1893年,第59页。因此,井上新的伦理学说是以《教育敕语》为前提的,只承认敕语所云作为国体净化的忠孝为人伦之大本,并为其说编织各种说辞,早期以兼爱为善恶标准的说法则全然消失。
《教育敕语》发布后,1893年文部省令9号,特别重视小学校教育中的“修身教育”。*中学校有着从修身向伦理转换的过程,但小学校一直是修身科目。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更需统合国民,为此于1898年组织寻常中学校教科细目委员会,试图统一中学校学科教授内容。教科细目委员会制作而成的《寻常中学校教科细目调查报告》最终形成1901年文部省令3号《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如上所述,此时“伦理”科目再次改为“修身”科目,开始强化了以修身科为中心的政府教育指导。
三 “国民道德论”批判
藤井健次郎在《国民道德论》中言及新旧思想交替时人们在道德领域内的挣扎:“当此明治四十年之际,所谓新道德的精神与历史的国民思想之间,渐成中坚对中坚,根底对根底的犄角之势。一方是个人权威、人格尊严、主我、权利,一方是忠、孝、无我、义务。两者之间关乎胜负的争斗不可谓不甚,不得不对其进行认真的考察。”*藤井健次郎: 《新来思想和历史思想的冲突》,《太阳》第18卷第12号,1912年,第62—63页。藤井指出,新旧思想相斗产生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道德行为与内在信念之间的表里不一。即,一方面重视以自由平等为依据的人格思想,同时又难以摆脱历史上的国民思想。“建国以来,忠孝是我国国民未变之精神……只需守此唯一,无需他求。”*藤井健次郎: 《新来思想和历史思想的冲突》,第64页。然而,明治以后,国家设立的基于自由平等主义概念的各种制度,随着人类精神的发展,自然要由群众意识向个人意识迈进。可见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明治四十年是无法得以缓解的。即,不可能完全抛却历史的国民思想,专行自由平等之个人主义。但,藤井又说道:“我等明治儿,在这个难以评判的建设社会中被养育,受教育,渐渐地以此塑造了我等良心,慢慢地便舍弃旧道德,缓缓地向新道德移近。”*藤井健次郎: 《新来思想和历史思想的冲突》,第65页。
在《国民道德论》一书中,藤井对国民道德论进行了一般考察,指责那种“鼓吹国民道德,而舍弃伦理学”的错误想法。通过明晰个人主义思想的真正内涵,藤井反驳了那些认为“个人主义思想与日本国民道德相悖,从而仇视、并企图扑灭个人主义思想的人”。藤井认为,对于国民道德的态度有二: 一则以信仰为支撑的实践道德态度,一则是探讨、存疑的考察态度。两种态度需并重而行。但是,一直以来,国内人士对国民道德的态度倾向于前者,即盲信态度。大多流于枯燥的教训和说教,最终成为宗教式的教条。藤井认为,国民道德表现“在某国民中践行的道德事实”,因此,“国民道德是所与的事实,伦理学则是基于事实而成的理论”。*藤井健次郎: 《国民道德论》,东京: 北文馆,1920年,第201页。但是,国民道德论者常将国民道德与伦理学视作对立。又因伦理学以西洋思想为根底,所以对日本国民的实践并不能起任何作用,日本国内仅需国民道德便可,伦理学实为画蛇添足。
藤井还提出“国民道德与个人思想”问题。在藤井看来,日本思想史中个人思想开始于明治维新以后。维新以降,日本国家和社会文物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有个人主义色彩。第一,政治、法律层面个人色彩鲜明。维新前的政治完全是专制主义,维新以后变成舆论主义,国民可以凭借一定的资格而被赋予参政权。刑法以及民法的权利义务主体是个人。第二,现代产业组织以自由契约和自由竞争两个自由原则而得以成立。而自由的原则是个人或以个人为基准的法人。第三,文学、艺术也具个人主义特征,若无个人的个性则无文学与艺术。*藤井健次郎: 《国民道德论》,第219—221页。
个人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含四个要素。第一,我们属于人类,不同于其他一切事物。产生“我是人,他人也是人”的自觉。第二,由“我是人,他人也是人”,生出“人皆平等”的意识。第三,个人具无限发展自身之极大力量的自觉。这种力量是生物学上“自我保存之欲求”,哲学上“自己创造的秘力”。而“个人自由”是其产生的源泉。第四,个人是多数人中的一个人。个人的自由被大多数承认,此被承认的自由,名之曰“权利”。因此,个人思想包含个人、平等、自由、权利四个观念。从这四个要素中,藤井选取“自由”、“权利”两个观念考察最初时期国民道德和自由思想的关系。*藤井健次郎: 《国民道德论》,第233—235页。自觉的个人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领域出现。自由思想是对前代政治的反抗,其特点是抵抗上司,抗争吏僚,以消极多于积极,否定强于肯定,破坏多于建设为特征。这是因为当时导入的个人思想是18世纪欧洲的个人思想,此思想比较浅薄,包含危险激越的成分。因此,日本也不可避免受其影响。但是,19世纪欧洲的个人思想渐次深刻,提倡康德哲学的人格主义以及具有批判精神的理想的个人主义。随着欧洲个人思想的不断深入,理想的个人主义色彩也渐浓。个人主义在哲学、伦理、教育、政治、法律、经济领域的影响也随之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即此种个人主义是否可以容纳于日本国的国民道德之中。为了解决国民道德与个人思想的对立,藤井区分了三种自由观念: 政治自由,心理自由,伦理自由。由此考察政治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关系。
在藤井看来,国家的机能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消极的任务是维持国内安宁和秩序,国民安居乐业,进行日常活动。积极的任务是国家应为了自身发展,或者说为了国民的幸福积极行动。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国家应持有维持秩序,保有统一的权力。个人因为国家维持秩序的功能,才能享受自由乐趣。藤井说道:“因为国家的存在,个人的自由不是被限制了,而是得到实现了”。*藤井健次郎: 《国民道德论》,第253页。
紧接着藤井讨论“自由与服从”的关系。他认为,服从是所有国家道德的重要内容,在日本尤为重要。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明然有别。敬上、服从尊者为日本的道德。从动机来看,服从可分为半意识的服从、利己的服从、道德服从。其中道德服从指,反复检讨命令的内容,踏袭服从之真义,服从于此命令。换言之,深信被给予的命令含有极高的道德价值,不得不服从。然而,不能以强力助长服从。因为,“用强力迫使服从在无意间会打消伦理自由。伦理自由灭亡之后,将是一个伪善、虚伪的世间”。*藤井健次郎: 《国民道德论》,第279—280页。
最后,藤井考察了一般道德(人类道德)与国民道德的关系。他认为:“为了践履国民道德,为了使践行的道德附有价值,便不得不考察普遍道德、宗教教义以及历史事实。如此一来,实行国民道德,便是实行人类道德,不实行国民道德,人类道德也就不可能实现。同时,在没有实现人类道德的情况下,也断不可言说可以实现国民道德……但是人类有自负傲慢的弱点,我们有自己特有的道德,便以为此特有道德优于其他国民的道德的傲慢,即以自己特有的道德列于价值上第一等的道德地位的傲慢。由此必然卑他排外,此为人情之弱点,需深以为戒。”*藤井健次郎: 《国民道德论》,第344—345页。
结论
日本明治以降,国民道德论者为反对明治前半期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在日俄战争后的道德混乱中,强调以封建时代忠孝之道或对主君忠义的国体论,培养对天皇的忠乃至“忠孝一本”的道德意识。如此,欧美的个人主义在经济领域虽受到承认,但于教育和学术领域仍主张向国民传授“忠孝一本”的修身教育。因此,由以教育敕语为权威的家族国家观向国家至上主义迈进的道路,实则是国民道德论者们以及国民道德论的批判者(和辻哲郎由于过分强调整体而忽视了个体)著作中一种隐藏的脉络,包含以下错误认知: 首先,不了解宗教、道德、政治的区别。其次,不知家族制度与个人主义的区别,仅将两者折中后使用。第三,将修身教育从伦理学中切除,无视道德的普遍原理。第四,没有检讨社会全体的存在样态,仅关注自国的道德优点。最终由国民道德论走向天皇制国家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