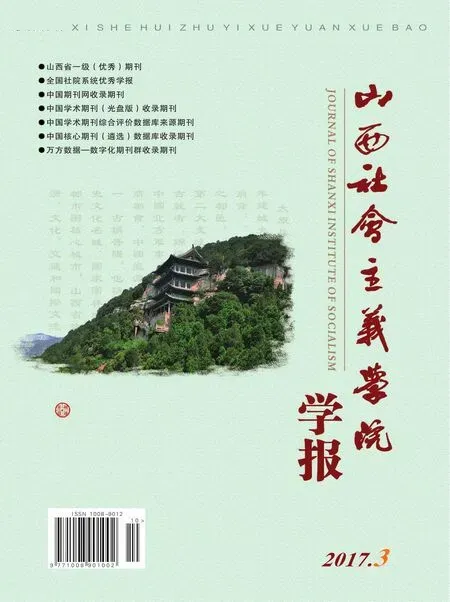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解析
2017-04-11刘晓潇
刘晓潇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山西太原030001)
国学茶座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解析
刘晓潇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山西太原030001)
对“人”之存在和发展的终极关怀,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呈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对“人性”的观照、剖析、圆满,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和根基。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其理论端口也要归结到关于人之本性的争论和论证。儒家的“人性论”、“心性学”虽然最终以“礼乐”为面世和变现的主要载体,但实质上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各种人文价值的集合体,并以一种穿越时空的影响力关涉着现当代人们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行为范式和生存模式。
“人性”论;“礼乐”文化;人文价值;文化熏染
在以“天、地、人”三者集成的宏大生命场景里,“人”的意义定位和价值走向始终是三者关系运行的主旋律,也是文化得以形成和演进的根本动力。从文化最本质的状态来说,它是天地万物在繁衍生息的动态过程中相互渗透、融会贯通而成的信息总和,而这一动态过程主要由“人”的主观能动性所推动。所以,一切关于文化的探讨,最终都要归结到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终极关怀上来。
文化的这一特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呈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对“人”和“人性”的观照、剖析、圆满,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和根基,儒、道、墨、法、禅、兵等各家思想无不涉及。赵士林先生“以儒做人、以道养生、以禅清心、以墨尽责、以法为基、以兵入市”①的概括亦是基于此理。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旨,是对人之本性的深挖细掘和再加工,这一工程由纯粹思想的力量和制度法则(制度法则亦是文化产物)的力量共同作用,为“人”对“自我”的意义追寻和价值追求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一、儒家思想:以“礼乐”为“变现”方式的人性之论
(一)儒家的“人性”之辩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和主体,而关于人之本性的争论和论证,一直是解读儒家思想实质的理论端口。儒家“人性”论经先秦时期、汉唐宋时期以及明清时期的流转传承,大致呈现出三种形态:
一是“性善论”。如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②并由此以“不忍”之心得出“仁义礼智”的“四端”说,以“良知”、“良能”得出“人之初,性本善”的基本判断,以“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得出“知天事天”、“修身立命”的处心之道。
二是“性恶论”。如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③虽然荀子的“性恶论”有着“察乎性伪之分”到“化性起伪”的思辨性过渡,但是相较于孟子之言“性善”,仍然有着善恶论上的明显区分。
三是“性无善恶”。如告子、王阳明,主张“心性不二”、“感而遂通”。告子其人其论,在《孟子》一书中可窥一斑,在与孟子的诸多辩论中,其“性无善恶”论最为世人熟知——“生之谓性”、“食色性也”、“性无善,无不善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水之无分于东西也”④。对于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之说,王阳明认为“亦无大差”:“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⑤顺口溜式的“四句教”,成为解读王阳明心学的入门法则。
实际上,回归到先儒孔子那里,“仁爱忠恕”之道、“性相近、习相远”之法,已然对“人性”有所预设,性善性恶也好、无善无恶也好、可善可恶也好,都是对这一预设的回应,而这一预设以及由此导出的儒家政治、伦理的全部论证,就在于对人性“为善”的一种朴实信任。所谓“为”善,正是要突出人的主体愿望和主观能动性,正如荀子和张载所言,“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⑦。
“人性”的育化、养护和流变是浑然一体的自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先天根据和后天功夫缺一不可。故笔者认为,基于“人”本身“身心”合一的极端复杂性,“性善”抑或“性恶”的简单划分并不足以构成对“人性”的全部理解。“我欲仁,斯仁至矣”⑧,善恶只在“欲”和“一念”之间,“欲”和“一念”而发所依凭的、由先天根据和后天功夫共同发力而成的那些特质,才真正关涉到“人性”。
(二)“人性论”是人文价值的集合体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得出关于“人性”的大概理解:所谓“人性”,意指根源于生死本能之间、使得“人之为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先天属性与后天属性冲撞调和、最终沉淀于心灵而发散于外形的那些特质,包括形体、行为、性格、情感、精神、人格、认知等多个层面。虽然先儒们没有对“人性”有过这种现代语境式的概括,但是儒家关于“人性”的解析却始终围绕着这些范畴展开,并渐进式地演绎为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人文价值体系。
从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定位,到他的继承者们开创的基于“人性”的意义世界,儒家集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价值理念体系,这些价值理念包括“仁、礼、义、智、圣、和、忠、恕、敬、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孝、悌、中庸”等诸多因子,并经历代儒者认真研习概述而成“五常”——仁、义、礼、智、信,由此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基本社会人伦关系进行调整和规囿,为后世开创了一方得以运筹帷幄的人文天地。虽然“五常”经常和“三纲”相提并论被进行多重意义上的理解和发挥,但其中蕴涵的对“人”和“人性”最原初的善意却不会流失在价值理念的长河里。
因此,儒家思想多从人文,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⑨等道德伦理所充实的价值体系,为我们构建起“修身、为人、治学、齐家、处世、理政”等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是非标准和行为规范,而这些标准和规范都有一个突出特质,就是“道德性”。
“道德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无论性善性恶,均可以道德的形式去感化和流转,由此衍生的道德自律和道德规范,成为源于人性并规定“人性”的基本要素。虽然目前为止儒家“德治”大多作治国理政层面的政治性解读,但笔者认为,所谓“德治”,必先“以德修身”、“以德治人”方可“以德治国”,故儒家“德治”首先应该从“正心诚意”的个体修身谈起,从人之本性的感化谈起,这是儒家“德治”的题中之义。或者说,正是由于儒家对“人性”的信任和超越,才造就了其道德学说的普适性和普世性,进而铸就了中国“伦理型”、“道德型”的社会传统。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一门以“德”为核心价值的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他者、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人学”或“价值学”。
(三)“礼乐”是人性的“变现”方式
“人学”或“价值学”视域对于“人性”的解析和诠释,很多时候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式的自我体证,用现代语境解读即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畴。对“人性”的体察成果要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有所呈现和运用,就必须寻求可观、可感、可触、可行的实现载体,这种载体对儒家而言就是“礼乐”。儒家学说之所以被认为是“入世的”,正是因为在儒家那里人与社会是不分离的,研究“人性”的视角最终要投放到社会中去。“人性”如何发散为社会性、社会性如何皈依于“人性”,对于儒家而言始终是同一个命题。所以,无论是学理化地解读“人性论”,还是制度化地解读“礼乐刑政”,都能导出同样的结论:“心性之学”与“礼乐之治”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一体两面”,“礼治”实际上是“德治”的另一种形式,故“礼乐”制度不过是抽象“人性”的变现方式而已,这种变现方式基于儒家对人性与制度、人性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刻洞悉。
“礼乐”文化以“礼”为主、“乐”为辅,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中均有论述,其中《礼记》正是对圣人之行、君子之德的专门性规定,由此“知书达礼”成为君子入世和处世的合理途径。儒家孔子对“礼”的推崇,有史为载:“民之所由生,礼为大。”⑩“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⑪故儒家礼制纷繁复杂,“冠、婚、丧、祭、射、朝、聘”等仪式众多,不可累述。其中贯穿的两大立法原则,一曰“尊尊”,二曰“亲亲”,蕴涵了“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级秩序的明确划分和“尊君敬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社会伦理的多维层面,构成了“礼治”之道的整体脉络。在孔子作为下,以对人世秩序合理安排为首要关怀,以“仁义忠恕”为主要铺陈,以“诗书礼乐”为重要形式,儒家构建起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礼乐”制度,并以“礼乐”文化的特定形态充实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中。
虽然“礼乐”文化因其等级制、宗法制、君主制等历史局限性而备受诟病,但以“人性”为根本依凭、以血缘关系为重要联结、以家庭与社会政治合一为基本取向,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剖离出“礼乐”之道的可取之处。“礼乐”文化是对儒家入世精神的现实印证,“入世”即意谓着对“人之为人”的关怀,“礼辨异,乐统同”⑫,虽然“礼”以“辨异”为准绳区分出人世间的高低贵贱,但这种区分又通过歌舞器乐的情感渲泄达致不分等级的内心和谐;又如“正名”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⑬。“为人”、“处世”、“为政”必先“正名”,“正名”在儒家那里即是确立并遵守以实现“仁”为目的、符合“礼”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是以“义”来“正名”而后获得“礼”。由此,“礼”的约束和“乐”的感化共同构成“人性”修为的路径,所谓“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⑭。
二、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现代调和路径
礼教乐化通行天下,纵贯古今。虽然随着历史变迁和时代更替,传统“礼乐”制度的诸多内容和形式已日渐式微,然而对“人性”施予浸润的基本定调却始终如常。“礼乐”文明所彰显的精神品质和价值内涵经现代方式的萃取、提炼,以一种更为醒目、更为直接的方式作用于“人之为人”的道德基因和人格架构。现代语境下,包括“礼乐”文化在内的古典文明之所以还有价值,正是基于其一以贯之的文化质地,即以“人”为中心,以“道德”和“制度”为原则,构建人间生活的各种秩序,并在调和“人性”的基础上解放“人性”,最终把“人”代入到“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和谐生命场景中。这种“代入”,主要经由两种方式来实现。
(一)“礼以修身、乐以养德”的道德修行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⑮正如前文所言,儒家“礼乐”之治是“德治”、“仁政”的另一种实现途径,“德”与“仁”的具体化、制度化、实质化则为“礼乐”。《礼记·曲礼》中说:“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制“礼”作“乐”是为了以文以德来教化天下、育化众生,通过润物无声的内在道德力量,使得人们能够经“修身养性”达致“体悟天道”的修行境界,经“谦和有礼”成就“威仪有序”的社会秩序,这是中华文明显著区别于西方文明的论点之一。西方更重理性认知,东方更具人文情怀,源于心、发于情、止于仁德的“礼乐”教化,才是道德修为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在现当代社会的人文情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当现代商业和科技文明大行其道,当物质和市场成为世俗生活的主要谈资,以“礼乐”文化为载体的道德教化和人文育化便岌岌可危,由此思想蜕变、道德滑坡、信仰缺失便成为常态,被世俗化、市场化的古典文明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成为商业社会的装饰品,失去了深刻的人文内涵和精神本质。所以,重新挖掘传统“礼乐”文化中道德修养的文化因子,对于改善社会风气、和谐人伦秩序大有裨益。
“礼之用,和为贵。”⑯“礼乐”之“和”,奠始于人和、彰显于家和、归结于社会和谐,这既是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更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寓意。其中,“人和”是基石,用现代观念来诠释,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对“人”之个性、人格、能力、素养、权利、地位最大限度的发挥,简言之是对“人性”最大限度的解放,这种解放只有在充盈着人文精神的道德社会才能真正达成。
在此基石上,“人”和于自身,则是身心通泰;和于亲朋,则是安居乐业;和于他人,则是睦邻友爱;和于社会,则是国泰邦安。世俗社会中“为人处世”的各项原则,只有经过“德治”传统的内在性浸润、调整和凝结,才不致于在科技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辐射下扭曲、变异和迷失,才能使得大中华儒化而成“文质彬彬”的民族风貌,并以这样的风貌站立于世界舞台之上,这是古典文明对现代文明的馈赠。
(二)“以礼入法、礼法合一”的制度承接
“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⑰人世间合理而稳定的秩序维续必然基于一定的法则,这些法则生发于自然则为规律,生发于人为则为法律,而“则天垂法”、“因俗制礼”、“承天道而治人情”的儒家“礼乐”制度,兼备自然之法与人为之法的双重质地,正所谓“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犹政事之必因风俗也”⑱。从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宗教祭祀仪式,到周公制礼后运行于社会生活中的律令制度,再到儒家“礼乐”之治在文化形态上的升华,“礼”作为一种修行路径和制度规范,已经渗透到“礼仪之邦”的每一寸肌肤和血液中,映射着当代社会的人文思想和社会制度。
“礼”对于社会制度的映射,与“乐”同行则为“德治”,与“法”同行则为“法治”,故“礼法”是儒家对“礼治”的另一种界定。对儒家而言,“礼”即“法”、“法”即“礼”,道德化的“礼”和法律化的“礼”实际上是同质的,正如《礼记·曲礼上》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从“礼”所确立的严格社会规范和对社会行为秩序的直接约束力来看,“礼”不仅承担着道德驯化的责任,更具有明显的法律性质。从荀子的“隆礼重法”,到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再到《唐律》和《宋刑统》,我们都可以找到“以礼入法、礼法合一”的影子,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由以“礼”为介质对法律的儒化上可见一斑。
儒家“礼法”对社会秩序的全面规定和直接约束力,为“以礼入法、礼法合一”的现代转换,为礼法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现代整合提供了可能性。现代法治社会对传统“礼法”制度的开显和推演,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作为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为完善人格、确立价值、追寻意义提供依据;二是作为强制施行的法律条文,为调整关系、规整行为、规范秩序提供保障。
实际上,现代道德规范和法律条文也并非绝对泾渭分明,判定法律“正当性”的因素之一正是道德的“普世性”。道德理念铸化则为法律,道德是法律的价值基础;法律内化则为道德,法律是道德的发扬路径。二者内在统一于对“人性”的调试,这与传统“礼法”思想异形而同质,也是传统“礼法”思想在现代社会进行合理演绎的可行路径。■
注释
①赵士林,《国学六法》[M],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出版。
②《孟子·告子上》。
③《荀子·性恶》。
④《孟子·告子上》。
⑤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⑥《荀子·非相》。
⑦张载《正蒙·乾称篇》。
⑧《论语·述而》。
⑨《论语》。
⑩《礼记·哀公问》。
⑪《论语·泰伯》。
⑫《礼记·乐记》。
⑬《论语·子路》。
⑭《礼记·乐记》。
⑮《礼记·乐记》。
⑯《论语·学而》。
⑰孔颖达《礼记正义》。
⑱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1] 李德嘉.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法哲学意义新探[J].《求索》,2016(12).
[2] 吴光.论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普世性与当代儒学的新形态[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4).
[3] 王永利,王银英.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优劣性及其现实意义[J].传承,2011(28).
[4] 任强.知识、信仰与超越:儒家礼法思想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G122
A
1008-9012(2017)03-0058-05
2017-08-15
刘晓潇(1985-),女,山西社会主义学院统战教研室讲师,中山大学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与中华文化。
(责任编辑 王怡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