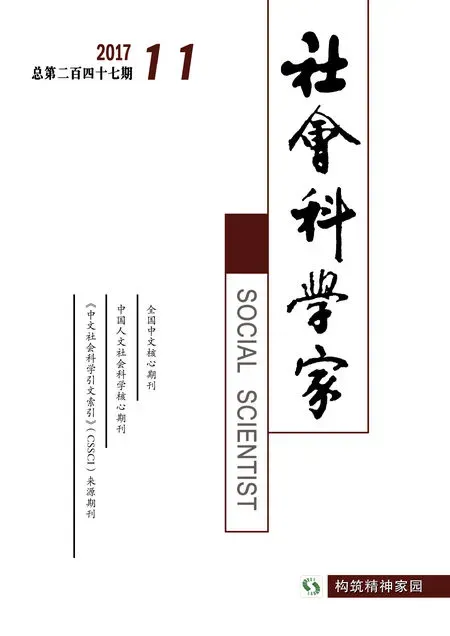从新文学的范本到新国学的建构
——论歌谣运动的转折轨迹(1918-1926)
2017-04-11张敏
张 敏
(1.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2.河南科技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一百年前,蔡元培在1918年2月1日的《北大日刊》头版上发布特殊而醒目的《校长启事》,[1]以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向全体师生乃至内地各处的报馆、学会及杂志社征集全国的近世歌谣。这般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把歌谣视为珍宝广泛征集是前所未有的现象,由此拉开了歌谣运动的序幕,并以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为中心向四处蔓延开来。新知识分子搜集研究歌谣、借鉴利用歌谣、挖掘歌谣价值……在“到民间去”的思潮下,歌谣运动持续多年,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大将——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等站在歌谣运动的最前沿,成为新文化运动中非常重要的风气现象。
以往学界通常把歌谣运动看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整体,但是在仔细考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运动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之后,发现它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不断连续地向前推进,而是历经了高调兴起——波折低潮——路径转化——再度兴起的过程。我们归纳出一条主线:1918到1926年的歌谣运动经历了从新文学的范本到新国学的建构的内在转折。透过这一发展轨迹,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知识分子的“民”的立场与文化人固有的“精英意识”的碰撞交流,民众与精英这对矛盾的张力交叠从新文学伊始就挥之不去,在语言文字、审美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犬牙交错。从这个意义上说,歌谣运动是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极富包孕性的鲜活而复杂的文化缩影,它呈现出中国新文学在现代转型中错综复杂的语言文字观念、审美判断和文化身份定位。
一、高调兴起:“民”的价值立场下新文学的范本
蔡元培之所以发布征集歌谣的《校长启事》,是接受了文学革命的先锋——刘半农的建议。1917年,刘半农和胡适、刘文典等一起被陈独秀聘入北京大学,以壮大新文学的声势。刘半农来北京大学之前,就已经对以歌谣、通俗小说为代表的民众文艺形式相当关注了。他出身贫寒,有着浓厚的底层情结,而早年与“鸳鸯蝴蝶派”的结缘也使得他成为五四新文学家中最早重视通俗文学的作家。在上海写文的时期,他注意到《新青年》对新文学的提倡,写作《我之文学改良观》,主张韵文的改良须借鉴自然之天籁,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和增多诗体。之后,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认为诗歌应该注重内容精神上的革新,提倡要向民间的真诗学习、借鉴。到了北大之后,他仍然延续着此前对歌谣等民间文学的关注和“眼光向下”的民众立场。1918年1月,刘半农在发表《应用文之教授》时,将署名“半侬”改为“半农”,意味着他彻底抛弃了身上残余的“鸳蝴派”式“你侬我侬”的才子心态,而是“体农向农”,决心在民间展开自己的文学革命事业。随之他为了创作新诗而自觉地寻求本土的民间资源,遂向蔡元培建议征集全国的近世歌谣,成为最先发起歌谣运动的重要人物。刘半农转向民间并非个体事件,而是蕴含着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转变这一重大社会和思想课题。
美国学者洪长泰谈及五四运动兴起之初,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定位的变化:“他们对精英文化极度失望,对民间文化抱有更高的期待,逐渐以一种十分理想和浪漫的情怀,对‘民众’发生了亲切的认同”。[2]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读书人、知识分子的身份不是普通的乡野村民,而是高于“民”、走向“官”的“士”,是介于“官”、“民”之间面目模糊、立场游移的群体。“学而优则仕”是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然而随着科举废除,新式文化教育得以发展,成就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正如陈思和所言:“严复、张元济、蔡元培等人从千年宦海梦中惊醒过来,他们开始远离庙堂,或从事思想传播,或从事商业出版,或从事办学教育,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开辟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逐渐确立起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价值取向。”[3]新型知识分子远离庙堂,走向广场,舍“官”向“士”,由“士”倾“民”。这种偏移于“民”的身份定位是他们征集民间歌谣、推崇平民文学、到民间去的内在原因。由此刘半农等“发现了民间文学,颠覆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往的正统文学观;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基本态度”。[2]
由于“民”的身份定位和价值立场,新文学在语言文字方面倡导白话,“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4];反对文言及与此相联系的贵族文学,“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5];在审美风格方面强调“自然”和“真实”,“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6];“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4],推崇真实的平民文学;在意识形态上处处为“平民”的言说权力张目:“中国的‘黄钟’实在是太多了……我现在要试验一下,能不能尽我的力,把数千年来受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斧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7]强调将创作题材着眼于广阔的底层社会中“引车卖浆之流”的下层百姓,“工厂的工人,街上的洋车夫,老妈子,优伶,舟子,庄稼汉,以及于监中的囚犯,贫民窟里的叫花子……的生活,都有很好的材料供作家的采择”。[8]
在新型知识分子“民”的价值立场下,歌谣这一古老的本土资源被发现并被塑造,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要载体和重要表征。歌谣心口如一、口语化的表达风格与胡适提倡的“不避俗字俗语”、“不无病呻吟”等标准相当吻合,被新文学的建构者看成是白话文写作的鲜活的范本材料,成为了特定历史时期对“小传统”的文化选择。歌谣中自然、真实的审美风格成为刘半农等新诗人孜孜以求的美学特征,歌谣长短不限,不拘格律,遣词造句无比灵活,抒情表意明白清楚,有助于新诗摒弃古典诗词的格律,打破旧诗对诗歌形式的束缚,用浅白质朴的语言自由地表达情感。对朴实自然、不尚雕琢的歌谣的推崇正是新诗人的艺术吁求和审美期待。歌谣作为一种长久存在于民间的文学与文化资源,与民众百姓的日常生活、世俗情感、习俗仪式等紧密相连,契合了新文学要表现“最大多数人”[9]的观念,成为解构传统的文化文学秩序,建构现代性的“人”的文学的绝佳资源。正因为歌谣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民”的价值和作用,所以歌谣运动一开始就得到了众多新知识分子的拥护和支持,呈现出高调兴起的局面。
二、波折低潮:“民”的立场与精英意识的碰撞
歌谣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路高歌,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呈现出“高开低走”的局面,从1918年2月到5月间,头三个月征集了1100余首,而从1918年5月到1920年12月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才征集了600余首,[10]没有完成编写《中国近世歌谣选粹》和《中国近世歌谣汇编》的计划[11],以歌谣为范本的新文学创作的探索也遇到了瓶颈问题。原因何在?
歌谣运动伊始是出于新诗革命和白话文创作的诉求,在刘半农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对入选歌谣有一定的资格要求,征求的是反映“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同时“寓意深远有类格言者”、“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韵者”[12]……这些定语清楚地表明了刘半农歌谣征集的文艺标准。然而这一资格限制本身即存在着悖论。歌谣本是民众表达日常生活、情感、风俗的自然手段,对于民众而言是简单而直接的,难免存在着大量粗鄙、低俗的内容。刘半农筛检、挑选新文学的“范本”,意味着必然会带有源于传统写作经验和文本形式的眼光和标准,亦或是说,是新知识分子用“新文学”的标准对民众的原生态文学进行了精英性的提纯,这对民间反而有着某种程度的遮蔽。正如有评论所言:“这种对歌谣的有条件的筛选,过滤到了平直浅白或粗鄙淫亵的歌谣,而实际上这类歌谣在民间世界占了大多数。所以这样的征集要求其结果并不是接近民间,而是在新文学标准的尺度下重新对民间实现筛选和区隔”。[13]
出于“民”的价值立场对白话文学和平民文学进行大力推崇,而绝对质朴、不乏粗俗的原生态歌谣又时时和“文”的精英本质冲突。这里面搅杂着一些容易混淆的理论命题,首先是语言文字方面的“白话”与“白话文”。歌谣中的白话被认为是白话文创作的最佳资源。其实,“白话”与“白话文”是两个概念,“白话”是民众的日常口头语言,“白话文”是以“白话”为基础的书面语言。口头和书面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与之相关的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新文学理论建设之初,两者常常被混为一谈,一味推崇“白话”,但是歌谣中真正的大白话,如大量堆垛式的歌谣又无法被从事“白话文”创作者的新文学者所接受,认为其只对民俗学、心理学有价值而对文学创作无益。而新文学创作者所实践出的“白话文”对于唱着歌谣的底层百姓而言,却是同“文言文”一样的隔膜。其次是审美风格方面“真”、“自然”,“雅”、“俗”的混淆。以“真”为“美”,以“俗”为“雅”是歌谣运动中对传统审美的反拨。刘半农在《征集简章》中提到记录歌谣时,“无论如何,不可润色”;要求“真实记录”,这里面隐含着“真”即是“美”,即是“自然”的价值判断。殊不知在民间,“真”的歌谣往往是“写实”,类似“放屁”、“粪桶”、“屁眼子”、“屁股蛋”、“驴粪蛋”的字眼在歌谣中比比皆是,而这在文学家看来就不是通俗,而是低俗了。这种真实的“俗”和刘半农所预设的“不涉淫亵,自然成趣”、“似解非解,天然神韵”这些精英的文学审美必然有所冲突。再者在文学观念方面,歌谣是百姓日常化、世俗化的表现,内容往往是爹娘兄嫂、家长里短、婚丧嫁娶、爱恨情仇、童言稚语……也就是说,歌谣始于日常,也止于日常,它没有超越世俗日常的动力与可能。正如林庚所言,好歌谣只在于把日常生活表现得更热闹[14]。而对于新文学的创作者而言,好的作品不仅要表现平民的人生,而且还要“为人生”,具有表现日常且超越日常的能力,去揭示日常之外灵魂的生活,而歌谣远不能满足新文学这种精英观念的要求。
歌谣运动者对“白话”、“真实”、“平民”等概念进行想象,将其“建构”成“白话文”、“美”、“为人生”等精英文学意识。这些本有着不同内涵的词义被新文学的建构者拿来混用,他们没有意识更无法解决其中存在的差异,形式困惑和价值焦虑自然难免。这些内在的矛盾从歌谣运动开始就伴随其中,因此歌谣“文艺的”现代诗学路径并未蓬勃发展。五四诗坛将歌谣作为新诗范本进行创作的有刘半农、刘大白、胡适等,主要形式是模仿民间歌谣的语言和体式,如刘半农的《瓦釜集》及《扬鞭集》中的部分诗作,《开场的歌》:“一双雄鸡飞上天,我肚里四句头山歌无万千。你里若要我把山歌来唱,先借个煤头火来吃筒烟”;《第三歌·情歌》:“郎想姐来姐想郎,同勒浪一片厂上乘风凉。姐肚里勿晓得郎来郎肚里也勿晓得姐,同看仔一个油火虫虫飘飘漾漾过池塘。”这些都是诗人模仿家乡人的口吻,直接用江阴的方言土语来进行创造。类似的还有刘大白《卖布谣》《田主来》、胡适的《人力车夫》等。这既是诗人们努力对“民”的原生态生活的呈现,也是对“言文一致”的新文学运动主张用自然真实的口语代替硬化僵死的文言的有力支持。然而,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却不同于语言本身,仿拟歌谣崇尚原生态,语言不经提炼,必然和诗歌本身的文体特点相违背。苏雪林评价刘半农的《扬鞭集》,“粗俗幼稚,简单浅陋,达不出细腻曲折的思想,表不出高尚优美的感情,不能叫做文学”[15]。曾对歌谣寄予厚望的朱自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歌谣的文艺价值在作为一种诗,供人作文学史的研究,供人欣赏,也供人摹仿——止于偶然摹仿,当作玩艺儿,却不能发展为新体,所以与创作新诗是无关的”[16]。出于民众立场推崇歌谣,但在现代诗学建构中却无法摆脱“诗文”的精英特质,以歌谣为文学范本的创作实践很快被淹没在新诗发展的历史轨迹之中。歌谣运动文艺的路径遭遇发展瓶颈,必然面临着路径的转化。
三、路径转化:“民”的立场与精英意识的调和
《北京大学日报》从1918年5月20日开始开辟歌谣选栏目,“日刊一则”,持续了一年时间,至1919年5月22日发表歌谣148首后难以为继。1919年底,刘半农赴欧留学,歌谣征集工作也陷入停顿,加之以歌谣为文学范本的路径中有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歌谣运动出现低潮波折。在北大学生常惠的呼吁下,1920年12月,在原来歌谣征集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更加规范的学术机构——歌谣研究会,请来曾经从事过歌谣征集并具西方人类学知识结构的周作人“主任其事”,歌谣运动才出现转机。
在周作人的力主下,歌谣研究会将刘半农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进行了修改,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将征集歌谣的“不涉淫亵”的限制去掉,改为“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17]当初刘半农之所以加上资格限制,是由于文学创作的诉求,为新文学寻求写作的范本,而周作人将简章修改,并特别强调“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蕴含着从“文艺诉求”向“学术研究”思路的转化。换言之,如果说刘半农认为只有“好”的歌谣才有借鉴的价值,周作人则认为只要是歌谣就是“好”的,它的“好”表现在可以对“民间”进行客观呈现和深入研究,被认为是歌谣的最大价值。如果说文艺的诉求时时处处要面临“民”的立场和精英文学观念冲突的话,那么学术研究的方法则能很好地调和了两者之间的矛盾、碰撞:把歌谣作为学术对象进行研究,既和平民文学的倾向紧密相关,同时研究者的身份能从研究对象中剥离出来,是具有学术眼光的文化精英对广大民众的研究。这样就化解了以前“文艺的”单一路径,而是以“学术的”视野和眼光将心怀民众的知识精英聚集在歌谣运动的大旗下。
周作人将“学术的”研究视角引入到歌谣运动,一方面是他同样经历了“平民”和“精英”的矛盾冲突后而做出的路径选择,另一方面和其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历有关。作为文学革命的先锋,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一样是平民文学立场的表现,相比胡适强调文学语言形式,周作人更侧重对平民文学内容的建构。他关注歌谣,推动歌谣运动都和此有关。但周作人很快就对歌谣的文艺价值产生了反思质疑,作为一个对文字、语言、文学有着高度认知和持续敏感的新文学作家,他有着更加自觉的“白话文”的文体意识,在胡适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基础上对新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怎么说”、“怎么表达”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此他不止一次对歌谣言语粗鄙、形式单调表示不满,对歌谣等民间文艺形式的价值判断颇为复杂。出于“民”的立场对民间文学、艺术中蕴含着的真挚自然力量充分认同,而出于“精英”的文学情结又无法容忍其语言、审美中确实存在的弱点,对歌谣的文艺价值判断始终处于相当矛盾的游移状态。他很警惕由于“民”的倾向而夸大民间语言价值的浪漫主义趋势,“以为提倡国语乃是专在普及而不在提高,是准了现在大多数的民众智识的程度去定国语的形式的内容”[18],这是对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均有着高要求的周作人不愿意看到的。而且,他对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之间的决然对立也表示怀疑。周作人曾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学的讨论》《贵族的与平民的》,认为并非平民的最好,贵族的全坏。只要是能表达真挚普遍的感情就是好文学,而且“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19]。这种观点显示出周作人身份认同和文化心态的复杂性。既“在”十字街头,又躲进“塔”里,[19]“在”而不“属于”的身份使得周作人对民众既有同情与体察,更有理性的审视批判态度。
在语言文字、审美和身份定位的摇摆中,周作人自身的知识结构、学术经历为他提供了歌谣研究的另一种思路。周作人在日本求学期间,深受西方和日本人类学、民俗学理论的影响。安特路郎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弗莱则(J.G.Frazer)的《金枝》、霭理斯(Havelock Ellis)的《性心理研究》等等都为周作人打开了一扇全面认识人类的知识大门。而他对歌谣,特别是儿歌的兴趣和重视,与其新文化运动期间要重新认识人、以人为本的思想武器密切相关。“他对童话、儿歌、民谣、神话、笑话、民间故事的见解,那是高度自觉地借鉴民间文化艺术。目的是为了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以求了解幼年时期的人类”。[20]周作人选择从人类学、民俗学出发,将尽可能保持原貌的原生态歌谣材料从民众文化心理的角度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歌谣来了解深藏民间的国民心态、民众生活境况和情感逻辑,把“民”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来建构“人”的文学的思想体系,并从中获得文学语言的鲜活资源。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言:“历史的研究一方面,大抵是属于民俗学的,便是从民歌里去考见国民的思想,风俗与迷信等,语言学上也可以得到多少参考的材料。”[19]
民俗学、人类学的学术研究路径使得周作人可以暂时搁置歌谣作为新文学范本时所无法解决的矛盾困境。以猥亵歌谣的研究为例,周作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十八拍”等唱本之所以猥亵完全是因为文字的原因,词句粗拙令人蹙眉。[21]然而他为了“从这里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看他们(也就是咱们)对于两性关系有怎样的研究与兴味”[22]而去积极热心的征集猥亵歌谣,不仅和钱玄同、常惠共同发表《征求猥亵的歌谣启》,还打算编写《猥亵语汇》和《猥亵歌谣集》。周作人的这种研究思路是将歌谣作为“他者”进行客观冷静地观照,如果说对歌谣文艺价值的反思和质疑流露出周作人坚守精英文学观的话,那么热心于底层民众口中“不登大雅之堂”的歌谣研究,又是其深入民间的最好贯彻,由“文艺”向“学术”的路径转化很好地调和了“民”的立场和精英意识的矛盾冲突。
这一时期报刊登载的歌谣研究也体现了这一趋势,《晨报》副刊从1920年10月26日起设置专门栏目连载民间歌谣。比起《北大日刊》,它的研究更加学术化,既有详细的注释、民俗学的考证,同时还有对方言词汇的注音、解释等,顾颉刚等人是供稿的主力。这些研究都为歌谣研究会并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将歌谣纳入“新国学”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思路。
四、再度兴起:新国学的建构
1922年,歌谣运动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即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建立。“国学门”的成立和1919年前后“整理国故”的思潮密不可分。新文化运动热潮过后,在近代欧美学术反倒关注“中国学”(Sinologist)的刺激下,中国学者认为研究“吾国固有之学术”同样重要,提出要整理“国学”。不过,“此国学”非“彼国学”。新知识分子在“民”的思潮下,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建构了新的“国学”,否定了传统的国学(经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摆脱了“儒书一尊”的观念,把属于民众的文学,特别是歌谣、小说等提升至和传统国学同样的高度。“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23]这种平等的眼光在北大国学门同人那里,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他们认为“一概须平等看待。高文典册,与夫歌谣小说,一样的重要。”[24]
于是,歌谣研究会在国学门成立之初就被并入其中,成为了“国学门的老大哥”,[25]而歌谣也成为了“新国学”。如果说周作人的民俗研究路径更多的源于个人的学术经历和知识结构的话,那么,歌谣运动在“国学门”平台上被纳入到“新国学”的建构,则成为知识界、学术机构、众多文化精英的共同的努力。“歌谣”被发掘为全身都是宝贝的学术研究热点:流传在各地民众口中的歌谣一定绕不开方言、方音、文字、词汇;歌谣中的民俗、地理非常值得深究;歌谣中蕴含的传说、故事能揭示出历史的秘密……在这种趋势下,歌谣运动终于出现了专业的研究刊物。1922年12月17日,在北大成立25周年纪念之日,《歌谣》周刊诞生,这一刊物汇集了大批知识精英,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胡适、林玉堂、黎锦熙、常惠、顾颉刚、董作宾、魏建功、钟敬文、鲁迅、台静农、朱自清……等等,影响力可见一斑,他们从文艺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历史学等多种不同学科对歌谣及其相关的民间文学进行研究,逐渐发展成一门重要的“歌谣学”,多方面地推动了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建设,达到了歌谣运动的高潮和顶点,提升到系统的学术研究的层次。正像顾颉刚所建构的那样:
研究歌谣不但在歌谣的本身,歌谣以上有戏剧,乐歌,故事,歌谣以下有方音,方言,谚语,谜语,造成歌谣的背景的有风俗,地文,生计,交通诸项。我们所有的材料,仅仅歌谣尚是极不完全,何况这许多项目?所以我们单单空想研究歌谣,原是甚易的,而其实做研究的功夫确实难之又难。[26]
这般“歌谣学”就不再仅仅是“引车卖浆之流”和“京津之稗贩”们的口头艺术,也不属于个人性的偏好行为,而是众多新兴的知识分子拓展的新的学术范畴,发现新的语言文字资源以及构建的新的研究思路、方法和范式,既不失研究者的文化精英身份,又契合了时代背景下新知识分子的“民”的价值立场,达到了两者的促进融合。
歌谣等民间文学研究此时能获得大批知识精英内心的认同主要缘于两个方面:“新国学”中对“民”的阐释规避了一味强调“平民”和“贵族”的对立,而是在“民众”、“平民”的基础上加入了“民族”、“国家”的维度,与重建中国本土文化、表达民族性诉求有了同构的关系。“以民歌充实国学”、“用国学整合民歌”,[27]“源于民众和民间的歌谣说唱等‘俗不堪言’的东西,在一批‘国学大师’的不断努力下,被纳入到了国家正史之中,变成可以用来同西方匹敌的‘中国文化之重要部件了。”[27]歌谣运动将民众口头艺术视为“新国学”,通过创造性阐释来达到对民族文化的批判和继承,契合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内在诉求。此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是吸引众多文化精英来研究歌谣、传说等“新国学”的另一原因。五四是一个高举科学的时代,任何研究如果具有“科学的价值”则能获得学者的青睐和认可。而顾颉刚等歌谣运动中的大将彰显的恰恰是“新国学”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的价值。
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国学是科学的一部分(如其是用了科学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可与科学对立的东西。倘使科学不是腐败的,国学也决不会腐败。倘使科学不是葬送青年生命的,国学也决不会葬送青年生命。[28]
歌谣是新国学,新国学是科学,那么研究歌谣就是研究科学,自然被赋予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科学至上的新文化运动高潮中,以研究国学(国故)的学者多少都会有压力感,而通过国学是科学的逻辑阐释,研究歌谣等新国学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研究会获得一种时代感的肯定和认同。
《歌谣》周刊从1922年12月17日到1925年6月28日,持续了97期。前49期以登载和研究各地征集的歌谣为主,在这期间,歌谣研究会之外酝酿出了风俗研究会和方言调查会,《歌谣》随之成为三会共同的会刊,之后大量的版面用于方音方言、孟姜女专号、婚姻专号等民间传说及民俗的理论探讨,越来越偏重于学术研究。《歌谣》周刊后来并入到《国学门周刊》,意味着歌谣等民间资源完全汇入到新国学的建构中去。《国学门周刊》1925年10月14日创刊,至1926年8月18日停刊,前后出版了两卷二十四期。内容包括歌谣、唱曲、风俗、传说、语言文字及训诂、学术思想、考古学、金石学、目录及校勘等。可以看出,歌谣只是占据了其中少量的部分,而其他的文章大多属于学院派的专业化研究。专深的研究不但排斥了民众,就连普通的知识分子也难以介入其中。始于“民”的价值立场,矛盾于“民”和“精英”的冲突,并试图以新国学来调适平衡,却最终以“精英”性而再度兴起,与“民”乃至歌谣都渐趋渐远,歌谣运动呈现出新文学发展中意味深长的现象。
[1]蔡元培.校长启事[N].北京大学日刊,1918-02-01(1).
[2]洪长泰,董晓萍.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1.
[3]陈思和,张涛甫.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转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
[4]胡适.文学改良刍议[A].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C].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43;36.
[5]陈独秀.文学革命论[A].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C].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44.
[6]胡适.什么是文学[A].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C].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214.
[7]刘半农.瓦斧集代自序[M].上海:北新书局,1926.7.
[8]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M].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14.
[9]胡适.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5.
[10]曹成竹.从“民族的诗”到“民族志诗学”——从歌谣运动的两处细节谈起[J].文艺理论研究,2011(8):137.
[11]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73.
[12]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N].北京大学日刊,1918-02-01(1).
[13]曹成竹.在文化革新与文学审美之间——20世纪早期中国歌谣运动的回顾反思[D].山东大学博士后报告,2013.85.
[14]林庚.歌谣不是乐府亦不是诗[J].歌谣,1936,2(11):4.
[15]鲍晶.刘半农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301.
[16]朱自清.歌谣与诗[J].歌谣,1937,(3):5.
[17]北大歌谣研究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N].北京大学日刊,1922-12-06:(1).
[18]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国语改造的意见[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61.
[19]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贵族的与平民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6;272;35.
[20]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70.
[21]周作人.猥亵的歌谣[J].歌谣纪念增刊,1923.22-24.
[22]周作人.征求猥亵的歌谣启[J].语丝,1925(48):3.
[23]胡适.发刊宣言[J].国学季刊,第一卷,第 1 号:4.
[24]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A].蒋大椿.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C].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681.
[25]常惠.一年的回顾[J].歌谣周年纪念增刊,1923.42.
[26]顾颉刚.舒大桢通信[J].歌谣,1923,1(38).
[27]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M].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15;69.
[28]顾颉刚.论风俗歌谣是国学[J].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