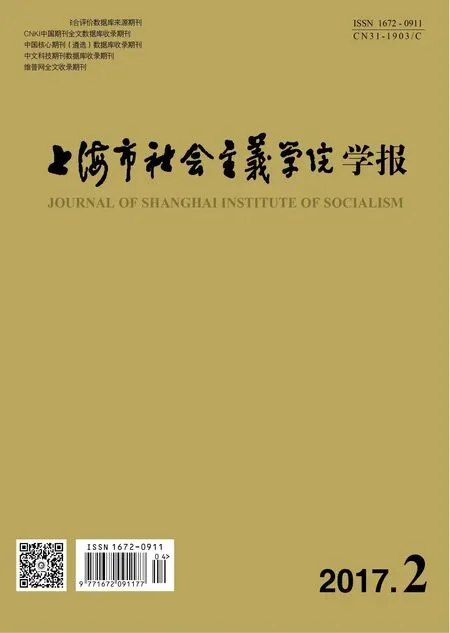协商民主视阈下九三学社先贤政治主张的历史定位
——以褚辅成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为中心
2017-04-11张涛
张涛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200235)
协商民主视阈下九三学社先贤政治主张的历史定位
——以褚辅成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为中心
张涛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200235)
九三学社先贤褚辅成在1924年提出的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具有协商民主的色彩。这一文件的提出,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协商民主的迫切期待,反映了民主人士对协商民主的积极尝试;而其失败,则提醒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才是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必然归宿。
协商民主;九三学社先贤;政治主张;历史定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统一战线的制度化体现,而协商民主则是这一制度的工作方式和方法[1]。2015年初,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印发,这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将对协商民主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断尝试、进取才逐渐获得的智慧结晶。这段探索历程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在此历程之中,我们能看到不少九三学社先贤的身影,其中一位就是褚辅成先生。
早在九三学社成立以前,褚辅成先生就参加了革命。他受戊戌变法思潮影响,主张民权,锐意改革。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同盟会,1912年任浙江民政司长,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因弹劾袁世凯而遭迫害,系狱三年,出狱后追随孙中山到广州政府,1921年保释陈独秀,1922年在上海发起组织全浙公会,1923年领衔弹劾曹锟。在此期间,他发表了许多著名的进步言论。到了1924年,褚辅成先生撰就了一份与近代中国协商民主颇有关联的文件,这就是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
褚辅成先生认为,当时民国分裂已久,失去重心,“非将各派领袖冶于一炉,融为一体,断不能收拾时局”,因此,就要 “集合各省有力者于一堂,各式公开讨论,……舍短取长,主席总其大成,如有意见可陈述”,“共谋国家统一”[2]。为此,他在1925年 4月4日善后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以求 “罗致各派要人、各省主帅,集中首都,使之躬自为政,共济时艰”。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分为 “总说明”与 “正文”两部分,“正文”部分共计16条,部分条目还附有相关说明。其核心思想是改组国务院,由临时执政、地方最高长官及推举议员和善后会议选举出的 “元勋、名流、自负有解决时局之能力者”共三十三人组成,不得委派代表,接受法律限制与人民监督,共商国是,如各省自治、军队由中央政府裁撤,等等。这份草案中的内容体现出了若干协商民主的色彩,如以往的政治决策,都操纵于几个军事强人之手,而褚辅成先生虽然同样没有突破政治、军事强人的范围,但是他主张三十三人合议,这样就扩大了政治讨论的包容性。他强调 “以执政三十三人组织国务院,骤思之似嫌过多,或有运用不灵之虑。然英国战时内阁阁员亦近三十人,未闻发生议事迟滞、行政掣肘诸弊。盖行政会议席上,凡议一事,赞否片言立决,即有争执,亦可取决于多数,决不致稽延政务也”。协商民主强调积极主动的参与,强调理性沟通以达成共识,形成决策,褚辅成先生针对有人以此前广州军政府七总裁不能合作为由反对协商,特别指出 “广州军政府之所以破裂者,在总裁多数不到,各派一不负责任之代表列席会议,于是诸总裁间,情意隔阂,主席总裁得以操纵其间。名为合议,实仍独裁。群情不服,卒至解体。今当引为殷鉴”,故制订了三十三人需亲自出席,非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不得开议、非出席者过半数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的规定。这也与协商民主强调程序正义的精神相符合。
可是,由于段祺瑞临时政府将之视为 “捣乱”,褚辅成先生精心准备的这份提案最初甚至未列入议事日程[3],后来又被搁置不议,最终也与善后会议本身一样,不了了之。
褚辅成先生之所以做出这一提案,以及这一提案无疾而终的原因,都是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之后,各军阀派系形成了暂时 “均势”的局面。善后会议就是在此背景下,由段祺瑞临时政府举行的一次 “政治协商”会议。当时北洋军阀 “武力统一全国”的主张已经破产,因此,善后会议旨在通过会议协商的方式来谋求国家统一。愿意参加善后会议的学界名流胡适也说:“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4]可见以协商的方式来谋求国家的统一与发展,成为当时很多人的共识。
毋庸讳言的是,1920年代前期,中国还处于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自然也没有出现较为成熟的民主力量。当时国民党正在酝酿改组,未几即成立广州国民政府,筹备北伐。成立未久的中国共产党,还在不断摸索中逐步成长。各系军阀及其操控的党派拥兵自重,各怀鬼胎,彼此利益纷争,僵持不下。据说当时在北京,“实无正式之政党可言”,但若不以严格的政党定义来区分,则约可分为四派:
1.政府党。“此党人数无定,亦无宗旨可言,不过受政府之指挥,为政治上捧场之角色而已。”
2.联治党。“此党以联省自治为标帜,与执政府完全立于反对地位,……其在京冲锋陷阵者,则为褚辅成、杨永泰、钟才宏诸人。”
3.曹吴党。即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党羽。
4.国民党。与段祺瑞执政府为难。联治党与国民党部分人物,“已有相互援助之形势”[5]。
据此分析,褚辅成先生的提案与进步的国民党较为接近,而为主导善后会议的段祺瑞临时政府所不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提出的废督裁兵的主张,无异于与虎谋皮。
由于各方力量僵持不下,更由于当时的中国距离现代社会真正的协商民主尚非常遥远,这次会议毫无悬念地失败了,并没有能够达成共识。尽管如此,善后会议仍被称为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次“艰难政治尝试”[6],而褚辅成先生提出的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也自有其历史地位。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要放在近代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演变序列中,才能予以准确的历史定位。结合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认真分析褚辅成先生提出的这份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三点认识:
首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提出三十三人组成国务院,接受法律限制与人民监督,协商国是,共谋国家统一,针对的是此前军阀混战的乱局,代表了许多期盼统一、发展、建立共和的人士的呼声,在当时是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的。褚辅成先生对时局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在参加善后会议之前,他曾对上海报界发表演说,指出:“盖处此纷扰之局,能得各方实力。相晤一堂,亦为解决国是之万一机会,……余意我国各党各派,俱已在政治上为一度之试验,无不失败。今后已应有相忍为国之觉悟。况中国之事,最坏在不见面,一见面纠纷转可稍解。……此案纯系个人意见,并不代表何方。”[7]虽然有人认为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符合西南军阀的利益,但是褚辅成先生个人则是出于公心,是他眼见着民国初年政治、军事纷乱之后所作出的抉择。褚辅成先生认为,“本草案所拟各条,绝非移植欧制,亦非妄参理想。不过察全国之情势,应国人之要求,就现在种种事实,略加厘订匡正而已”。事实上,这种想法并非褚辅成先生一人之私见,在善后会议上,他的提案还获得12人联署,分别是:费行简、周钟岳、林知渊、徐之深、刘燧昌、李华英、彭养光、蒙民伟、马君武、陈强、常恒芳、马聪。可见主张各种力量协商以定国是的褚辅成先生确乎是 “吾道不孤”。
其次,褚辅成先生1920年代的这一主张,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历史的局限,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仅仅试图依靠上层力量的相互妥协来达成政治统一,而没有认识到开发民众力量的必要性。在善后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7月、1924年11月接连发表 《第二次对时局主张》《第四次对时局主张》,呼吁召开由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指出,“只有国民议会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8]。与此相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所关注的仅仅是少数军阀、官僚,虽然也提出了要各省由民众选举的意见,但无法付诸实行,尚未能充分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如果不能深入民间,充分唤起民众,即便是进步革命的力量也很难做到平等协商,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到1920年代末,另一位九三学社先贤许德珩曾对革命力量之间难以协调的现象加以猛烈抨击:“革命的力量之分歧,在全部的革命势力中,各有各的一党,在一个党中各有各的一派,在一派中又各有各的一系,所以从斗争的事实上讲起来,他宁可使反动的势力得点便宜,不可以使同势力的异党,同党中的异派,同派中的异系讨了好处;他宁可使反动的势力一天天的高涨,不可以使同势力的异党,同党中的异派,同派中的异系抬起头来!”[9]就当时的褚辅成先生而言,他虽然也对此种现象有所认识,可是却无法找到解决方案,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意识到民众力量的重要意义。
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回顾褚辅成先生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的历史遭遇,将会更加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法性。协商民主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不断思索国家发展、民族命运的必然选择。以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国内实际问题,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内在机理的基本需求之一,这一点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表现了出来。“武夫当国”的北洋军阀最初妄想以欧美选举民主的外衣掩饰其拥兵自重、割据称雄的本质,终至破产。国民党早期提倡国民会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响应,而后来国民会议却沦为其一党包办的专制独裁工具,失去了民心。历史的重任不得不落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商民主之上。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先后创造了 “三三制”、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大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前后一脉相承[10]。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国共产党九十余年、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奋斗历程,就是不断进行协商民主探索和实践的历程。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核心工作有二:其一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协商对话;其二是在基层政治中政府与民众的协商[11]。以此来衡量褚辅成先生1920年代的提案,可见其虽有协商以定国是的美好愿望,但既无力给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平等对话提供有效保障,更缺乏对基层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足够重视。褚辅成先生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的提出,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协商民主的迫切期待,反映了民主人士对协商民主的积极尝试;而其失败,则提醒人们既要注重在制度层面确保党际协商民主得以实现,又要注重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协商、沟通渠道畅通。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必然归宿。而在此之前,包括褚辅成先生这样的九三先贤在内的先进中国人进行的协商民主的努力,其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珍视。
[1]李君如.协商民主在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5.
[2]褚辅成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善后会议.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371-377.
[3]善后会议议案总目(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善后会议.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93-95.
[4]胡适致许世英(1月,稿)[G]//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13.
[5]谢彬.民国政党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119-120.
[6]杨天宏.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9(05):74-89.
[7]征求新闻界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意见时的致词(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九日)[G]//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褚辅成文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315.
[8]张予一.中国共产党大事典[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1.
[9]许德珩.新时代的酝酿与中国革命的新趋向[J].民众先锋,1919(01):1-6.
[10]林尚立,赵宇峰.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修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7-20.
[11]俞可平.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几个问题[N].学习时报,2013-12-23(03).
(责任编辑:刘 颖)
统战宣传报道中涉及民族方面应注意把握的有关问题 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对容易引发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反感的问题,要慎重把握。我国有10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对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要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对少数民族多样的婚姻习俗和家庭关系也不要探秘、猎奇,不能主观臆断,以偏概全,肆意渲染,更不能加以丑化、侮辱、胡编乱造。
——摘自 《统一战线知识手册》
10.3969/J.ISSN.1672-0911.2017.02.023
D613
A
1672-0911(2017)02-0023-04
2016-11-25
张 涛 (1982-),男,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