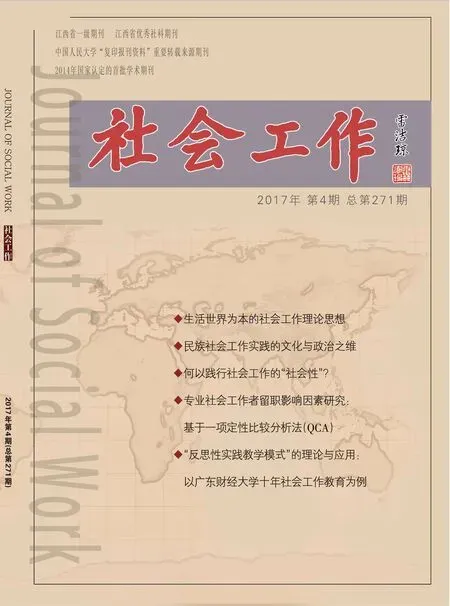遭父性侵女性成年后的家庭困局
——一项基于系统视角和依恋理论的临床案例分析
2017-04-11夏丽丽
夏丽丽
遭父性侵女性成年后的家庭困局
——一项基于系统视角和依恋理论的临床案例分析
夏丽丽
儿时遭受父亲性侵犯会对被侵犯者身体、心理和社交各方面都造成深切伤害和创伤,未疗愈的创伤往往会一直延续至成年。本文尝试以临床个案为例,以系统视角和依恋理论来探讨受父亲性侵犯的女童在成年后如何依然受困于此创伤,并在个人发展、婚姻关系和教养子女方面遇到重重困难,进而影响其家庭整体互动和氛围。本文亦以发展的视角探讨子女的发展迟缓和青春期如何加重童年曾遭受性侵犯的母亲的“侵犯代际重演”的焦虑以及在父女关系上的矛盾心理。最后,作者以优势视角为指引,探讨此类个案和家庭的抗逆力和所蕴含的资源,建议社会工作者或家庭治疗师在协助此类个案/家庭时以探索和肯定个案能力、疗愈伤痛和促进家庭内部相互支持为原则和方向。
遭父性侵女性 人际创伤 性侵犯的长远后果 家庭关系(family relations) 优势视角
夏丽丽,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博士后研究员,香港注册社工(香港 999077)。
儿童性侵犯作为一个高发且危害极大的社会问题,在国外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Sanderson, 2006),也引起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关注(Chen,Dunne&Han,2004,2006;Ji,Finkelhor&Dunne,2013;龙迪,2007)。如近期台湾年轻女作家在书写儿时性侵经历后,无法走出事件所带来的深刻痛苦而自杀的事件,引起社会大众、社会工作服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短期而言,儿童性侵犯的受害者在生理上会出现不同部位的身体疼痛、妇科疾病等;(心理上往往出现焦虑、抑郁、恐惧、紧张,发展负面情绪与认知、经历睡眠困扰(失眠、做噩梦)等甚至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Courtois,1996;Ma&Li,2014;Putman,2009);行为方面,他们可能在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调适上出现困难(陈辉女、廖凤池,2006),表现为逃学、离家出走、攻击行为,或发生自残自伤、自暴自弃、暴饮暴食、遗尿等行为(陆士桢、李玲,2009)。
长远而言,被性侵犯的经验将负面地影响个人成长发展的方方面面。Sanderson(2006)将这些长远后果总结为以下几种:情绪困扰(例如抑郁、焦虑、低自尊、内疚、愤怒、恐惧)、认知失调(例如否定、认知扭曲、解离、多重人格障碍)、人际困难(例如不信任、社会退缩或封闭、亲密关系恐惧、亲职困难)、负向身体反应(例如睡眠困扰与心身症状)、性别角色认知及行为问题(例如自我伤害、自杀、进食障碍、酗酒、非法药物滥用)。
一般大众大多认为儿童性侵犯的侵犯者陌生人居多,殊不知由成年亲属或其他相熟成人(例如学校老师、家庭的朋友)施加的比例最高(Celbis,Ozcan&Özdemir,2006;Courtois,1996;徐铭绣,2009)。在孙言平、段亚平(2004)等对606名成年男性儿童期性侵犯发生情况调查显示,侵犯者中亲戚占4.5%、师生占14.6%、邻居占21.3%、同乡占46.1%。李长山、段亚平、孙言平(2004)等对701名成年女性儿童期性侵犯发生情况的调查显示,侵犯者中熟人占47%,其中亲戚占21.3%。而父亲对女儿的性侵犯在已知所有亲属施加的儿童性侵犯案件中发生比例最高(Ansermet,Lespinasse,Gimelli,Béna &Paoloni-Giacobino,2010),侵犯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独特关系也令这份伤害比其他类型性侵犯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更加复杂、严重(Cyr,Wright,McDuff&Perron,2002;Tang,2002;陈慧女、廖凤池,2006)。
一、系统视角(依恋视角)和依恋理论对受父性侵对受害者的影响分析
家庭系统理论涵盖Bronfenbrenner(1979)的将个人置于不同层级的社会环境中的一般生态系统理论和Bowen(in Kerr&Bowen,1988)的强调家庭内部互动和心理动力代际传递的家庭系统理论。家庭系统理论视角下,父性侵犯子女(多数为女儿)的发生及其后当事人、受害者和家庭其他成员的回应都彼此相关,且受整体社会对性侵犯的认知和观念影响。
依恋理论由Bowlby(in Kerr&Bowen,1988)提出,并指出依恋是儿童和其照顾者之间通过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感情关系。它是生命系统的一部分,与个体的生存与适应息息相关,构建个体终生适应的基本特点,并帮助生命个体终生向更好适应生存的方向发展。一般而言,儿童从与照顾者的互动中形成一种特定的“内在运作模式”,即认为自己是否值得他人关爱、他人是否值得信任(Bowlby, in Alexander,Anderson,Brand,Schaeffer,Grelling&Kretz,1998)。内在运作模式既是人际关系的认知模型,也是情感调节的方法。生命早期充满压力的生活经验可能会损害个体的内在运作模式,影响个人定义、调节、整合自己的不同方面;在人际层面则影响其经验和培育对他人的信任与信心(Liem& Boudewyn,1999)。
本文采用家庭系统理论(Courtois,1996;Croll,2008)和依恋理论来理解父性侵子女事件本身及其对受害者的多方影响。
首先,侵犯者与受害者之间特殊的父女关系令受害者对侵犯者的感情变得矛盾而复杂(Courtois, 1996)。她们或因无法确定父亲行为的是非对错而茫然无措,或被这种行为吓倒而抑郁、愤怒、无所适从(Rhind,Leung&Choi,1999)。当逐渐意识到父亲行为是对社会道德与法律的违反时,她们可能又会为自己的遭遇感到自责、内疚(Croll,2008;Coutrois,1996),尤其是当侵犯者指出“性交也给你带来身体欢愉”时,这种内疚更是折磨至极(Wang&Ho,2007)。父亲,一个本应是儿童最重要的保护者之一,竟以性侵犯者的身份出现,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背叛,打破了父女之间的天然信任与联结(Rudd& Herzberger,1999)。另外,受害者甚至产生和内化“身体被糟践”“破损的自我”等认知(Stroebel, O'keefe,Beard,Kuo,Swindell&Kommor,2012;2013),造成深刻且持续的伤害。
第二,多重身心压力令受害者不敢披露性侵事实,侵犯也经常因此持续多年。一方面受害者往往会被侵犯者以暴力或羞辱威胁而不敢公开,另一方面受害者也担心披露给家庭带来震荡(Courtois, 1996;Stroebel et al.,2013)。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更不愿意披露受性侵事实(Finkelhor,Mikton& Dunne,2013;Tang,2002),尤其是家内性侵犯(Rhind,Leung&Choi,1999)。其原因有四:一是中国文化里对“性”话题的禁忌,二是孝道文化所暗含对长辈的服从和尊从,三是“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四为中国社会关于面子与羞耻的道德谴责,连同对女性的歧视和“贞操”观念,让所有道德压力都落在受害者身上(Tang,2002;Tsun,1999;王小红、桂莲,2014)。在这种文化和社会氛围里,非侵犯的其他家人即使发现性侵事实也往往不愿披露,或不支持受害者(Tang,2002)。
第三,父对女性侵所涉及的复杂家庭关系令其他家人(尤其是非侵犯的母亲)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他们往往难以积极正面地回应事件的披露并保护受害者。母亲们通常受限于父亲是经济来源,抑或屈服于维系家庭完整或家庭颜面的压力,而选择否认性侵事件或不将父亲逐出家门(简美华、管贵贞,2006)。但是,对于儿童期曾遭父性侵的女性而言,非侵犯母亲的应对是影响受害儿童长期适应的关键之一(简美华、管贵贞,2006)。家人的负面回应,或否认或谴责受害者或强迫保密,都会给受害者带来二度伤害(Courtois,1996)。
受父亲性侵犯的儿童容易发展出多种身心问题,但这并不是必然。那些日后恢复和发展良好的受害者,其母亲的支持与保护起了关键的作用。当然,母亲能否支持和保护受害者也与诸多因素相关,包括她个人的成长经历(例如,她自己是否曾被性侵犯,是否有边缘性人格障碍)、婚姻状态与质量(例如,她与侵犯者正处于婚姻关系中让她更难在事发后支持和保护受性侵犯的孩子)、个人与社会支持的多寡、与受害者的关系质量以及受害者的年龄等(例如,许多母亲会倾向相信年幼而非青少年女儿的投诉与披露)(Cyr,McDuff&Hébert,2013;Stroebel et al.,2012)。Rhind,Leung和Choi(1999)在香港的一项研究显示,很大比例的母亲们会否认女儿披露的受父性侵事件。她们或责备女儿撒谎,或逃避再提起此话题。有些受害儿童甚至会通过否认自己的经历来调节承受不了的情绪,这是一种在内心深处对自我的背叛(Courtois,1996)。许多家内性侵犯的受害者在有独立生活能力后,多与原生家庭断绝关系或维持非常糟糕的联系(Fitzgerald,Shipman,Jackson,McMahon&Hanley,2005;Rudd& Herzberger,1999)。
第四,与原生家庭的恶劣关系不单意味着其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缺失,更意味着父亲性侵对受害者生活的深远影响,尤其影响她们成人后建立亲密关系,和为人父母后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受父性侵事件让她们难以信任他人,或难以形成恰当的性行为和角色定位。此创伤记忆可能会嵌入脑中,遇到特定的人、事、物时会不断回放,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与伴侣的关系。Stroebel等人(2013)研究发现,受父性侵的受害者在性满足、夫妻关系、抑郁等方面比其他类型儿童性侵犯的受害者有更多问题。犹如一个魔咒,糟糕的夫妻关系及其他家庭问题往往也是父对女性侵犯发生的温床,是此类事件代际传递的高危预警(Coutois,1996;Sanderson,2006;严健彰,2002)。
除了亲密关系问题,受父性侵的女性在成年组织家庭后,往往在子女教养方面遇到诸多挑战和问题(Zuravin&Fontanella,1999;Ruscio,2001)。Schuetze和Eiden(2005)与Fitzgerald等人(2005)研究发现,这些人强烈地回避母职,对自己教养子女的能力评价差、信心低,在与子女相处时难以控制情绪。在教养方式方面,她们更多地用体罚、放任自由或过度保护;她们往往急切地希望子女成熟独立,但又容易关系倒错,在情感上依赖未成年子女。另外,这些母亲容易对自己和孩子有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否定自己的能力,较难从母职中获得满足感(Fitzgerald et al.,2005)。更重要的是,她们心中一直隐有担心,担心自己的遭遇在女儿与丈夫之间重演(Cohen,1995)。一方面她们希望家庭关系亲密无间,但另一方面她们又无法停止对丈夫行为的担心,同时她们也为这样的怀疑担心感到内疚(Kreklewetz &Piotrowski,1998)。
以上种种负面后果的出现,不仅因为父亲的性侵犯令受害者缺乏良好的亲职榜样,更因为性侵犯事件扰乱了受害者与照顾者之间安全依恋的形成,阻碍受害者心理调节能力的发展(Greenfield,2014)。当被要求去满足本应是保护者和照顾者的性需求时,该儿童的安全感与对他人的信任从根本上被破坏,而她也极可能将这种破坏性的依恋关系内化而发展出对亲子角色与责任的扭曲认知(Fitzgerald et al.,2005)。Alexander et al(1998)发现,不安全尤其是恐惧躲避型依恋类型在性侵受害者的群体中占绝对大多数,她们自我调节和社交功能方面会面临多重多样的困难。
虽然依恋类型整体来讲一旦形成则很难有根本变动,但放眼一生,生活环境的转变会改变甚至矫正现有的依恋类型(Alexander et al.,1998;Liem.&Boudewyn,1999),并且不同的关系里人们可形成不同的依恋类型(Greenfield,2014)。除专业人士(例如心理学家、社工、医生)的协助之外,友谊、婚姻、亲人的支持都能够帮助减轻受父性侵经历带来的创伤(Fitzgerald et al.,2005;Wright,Fopma-Loy& Fischer,2005)。
本文将以临床个案为例,运用以上理论分析童年被父性侵的经历如何对受害者造成短期和长期影响。笔者还将结合结构家庭治疗理论分析此类家庭的需要、所面临的困难和所具有的优势,为此类临床干预提供一些建议。
二、案例分析
本研究的案例为笔者在香港一家提供保护儿童服务的机构实习时接触和跟进的家庭。案例中的陈太(化名)主动寻求本机构的服务,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管孩子,我怕哪天我会因为虐儿被抓进去。”初步面谈对她的个人情绪状况的和家庭结构有基本了解,经审核认为符合机构服务范围,由笔者进行个案跟进,所提供服务包括个人面谈(两次)、家庭面谈(两次)和家访(一次)。
本着优势视角和系统视角,笔者探索案主的生活经验,并与她建立信任关系;案主自愿且坦诚地讲出自己的生命故事和家庭图景,为持续深入的干预和治疗提供丰富资料。后因实习期满,未能继续跟进,但此阶段获得的对此类家庭的需要、所面临的困难和所具有的优势的分析和理解,启发日后对类似个案的深入协助。
陈太今年40岁,与先生结婚18年,育有两女—玲玲(16岁)和莹莹(14岁)。两姐妹分别就读同一所中学的高二及初二,关系要好,常一起行动。陈先生在一栋大厦当保安,陈太自结婚后便做家庭主妇,一家四口住在一个不足40平米的一室一厅的公屋①公屋:香港政府房屋委员会为无法负担租住私人楼宇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共租住房屋(公屋),即廉租房。。两个女儿住房间(上下床),夫妇二人则客厅两用当卧房。
陈太常跟小女儿发生口角,甚至有肢体冲突。陈太透露:莹莹两年前被诊断为有轻微智力障碍。她在提起此事时面露厌烦,并声称认为自己“无能照顾、无能跟智障人士沟通”。一方面,莹莹独立生活能力(例如煮饭、购物、搭车出行)的不足令她担心,另一方面莹莹受同学欺凌后的“闷不做声”也令陈太焦虑。陈太的这些担心和焦虑交织在一起,常被莹莹“不听话做家务”等生活琐事引爆为愤怒。母女之间的争执和肢体冲突有时会很激烈。陈太说,她知道这样不好,但“火上来了根本忍不住”,会扇莹莹巴掌和用晾衣架抽打。多次这样的经历让她既内疚又无助,觉得自己无能照顾莹莹,能想到的唯一方法是:请求保护儿童服务机构帮莹莹安排一间职业寄宿学校。她说:这样的安排对女儿对自己都好。
(二)探索家庭图景:封闭的家庭与隐现的父亲
在笔者更详细地了解她如何、何时、何地会跟女儿发生冲突以及父亲是否介入时,陈太提到一个让人听来有些特别的情况。
她说:“不管多生气,我从不会在老公在场的情况下打她们,从来没有。”
“为什么?”
④埃米尔·瑙莫夫(Emile Naoumoff),7岁起跟随布朗热学习,曾与斯特拉文斯基、伯恩斯坦、罗斯特罗波维奇、马友友和洛杉矶爱乐、美国国家交响等合作。现任印第安那大学音乐学院钢琴与室内乐教授。
“因为不想我老公也这样对女儿”,她说。
她越往下讲,所呈现的家庭画面就越奇怪。在她的叙述中,陈先生与女儿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接触,所有的父女互动都由陈太中转。第一次面谈后,笔者进行了家访,所见也印证陈太所讲:一家人围桌吃饭,父女也不会直接对话,而是通过陈太传话。对此状况,陈太并未认为不妥,反而认为是正常现象,因为“男主外女主内”,况且“老公本身也比较沉默”。
当问及社会支持网络时,一个更令人忧伤的画面展现眼前:由于某种原因,陈太从少年期就基本跟自己的原生家庭断绝联系;由于“婆婆重男轻女”而“自己未能生个儿子”,她跟婆家关系亦不太好;玲玲出生后她就开始全职带孩子,没有工作没有朋友。她现在唯一的朋友是莹莹一个同学的妈妈,结缘于两人经常一起为孩子在学校受欺凌而投诉老师或驻校社工。每日除家务与睡觉她无事可做,总觉身体疲累、心情低落。她,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这个家,笼罩着这抑郁的氛围。
(三)真相:父亲性侵犯留下的后遗症
这一家人到底怎么了?两个女儿已经过了需要贴身保护的年龄,陈太为什么也不试图去找个工作呢?为什么她与家人和朋友断绝了联系?是什么导致和维持了父职在父女互动中“在场的缺失”?陈太对玲玲和莹莹的教养是否不同,如何不同?每一个家庭成员又是如何感知这个家庭的?笔者尝试通过深入了解,解开这些疑团。
当陈太小心地袒露她曾被自己的父亲性侵达六年时,上述疑问忽然有了一线之明。从6岁到12岁,她反复地被父亲性侵犯;到13岁,也就是她开始读中学时,便下定决心离家出走靠自己。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开始断绝与原生家庭的往来与联系。到此,笔者意识到,这不再是个简单的子女管教问题,而是一个童年曾遭受父亲性侵犯的成年女性,为人妻为人母后,在面对有智障的青春期女儿时,旧伤新痛并发的复杂伤痛。
三、受父性侵犯的旧伤新痛:基于依恋理论与系统视角的分析
此案例中,陈太的困扰一方面直接与儿时受父性侵经历相关,另一方面则与小女儿的智障有关。两者相遇,不但强化已有创伤,而且化学作用般地催生出更多烦忧。
首先,父亲的性侵犯完全破坏儿时正在建立安全依恋关系的她最基本和亲密照顾者的信任和依赖,从而发展出非常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影响她日后难以信任他人。“家丑不外扬”的家族观念以及中国社会对“性”的忌讳和污名化,使得她即使一开始就与母亲披露了受父性侵事件,也未能获得母亲信任,对他采取支持和保护的措施,更未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母亲这种无动于衷不单放任侵犯的继续发生和升级,也让陈太经历二度伤害,心里也产生了对非施害的母亲和家人的愤怒;也由于这种延迟,陈太也未能及时得到专业服务支援。陈太自上中学后,具备一定自立能力时便离家出走,将断绝与家人的联系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策略。
与原生家庭的恶劣关系不仅使她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重要的家庭支持,更严重影响她成人后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模式和为人父母后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儿时受父性侵事件让她难以完全信任丈夫,在情感上与他较为疏离;同时,性侵事件如同一个魔咒困扰她内心,让她担心此事在她的丈夫与女儿之间重演,并采取隔绝丈夫和女儿的接触的措施(这种疏离很可能是陈太潜意识的安排)。在子女教养方面,陈太也面临多重困难。她对自己教养子女能力评价差、信心低,认为自己无能照顾女儿。教养方式上多有矛盾:一方面急切希望女儿成熟独立,另一方面又过于保护,有时又倒错地情感上依赖未成年女儿。陈太在教育子女方面冲动、情绪激动,常用体罚等手段,并且对莹莹的自理能力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从家庭系统和发展的视角来看,伤痛在当下的爆发不是偶然,而是与家庭发展阶段相关。陈太幼年受父性侵的创伤后遗症在当下的引爆,加上与患有轻微智障的女儿步入青少年阶段重叠。
根据DSM-5的诊断标准,智力障碍使个体在智力和生活适应能力方面明显低于同龄群体,其概念学习、社交和实际生活能力明显受损(APA,2013)。生育、抚养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孩子对任何家庭来讲都不是件容易的事。父母往往会悲伤、愤怒,甚至心生绝望(Szymanski&King,1999),往往需要多年才能接受和平静(Haveman,van Berkum,Reijnders&Heller,1997;Ryan&Smith,1989)。另外,社会对智障人士的负面态度以及支持性社会服务的缺乏,也让智障人士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面临复杂且具挑战性的照顾责任(Eisenberg,Baker&Blacker,1998),如沉重的照顾压力和心理负担(Szymanski& King,1999;Tsang,Tam&Cheung,2003)。尤其在学业至上的华人社会,这些孩子会受到更多的歧视和压力(Chen&Shu,2012),他们长大后的就业机会也极有限。第三,家庭的沟通互动模式也会因孩子的智障而发生改变。因为多数父母只看见智障孩子的“无能”却看不到他们的“所能”(Szymanski& King,1999),这些家庭多采用简单粗暴的问题导向的沟通方式,伴随负面情绪的升级,往往给所有家庭成员带来巨大的挫败感(Costigan,Floyd,Harter&McClintock,1997)。最后,智障人士和家人(尤其是承担主要照顾任务的母亲)往往会被社会污名化,导致他们低自尊并产生其他心理困扰(Ali,Hassiotis,Strydom&King,2012)。
智障人士的需求及其家庭的互动方式会随着其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对其本身和父母而言,青少年期都是最复杂和最富有挑战的阶段(Szymanski&King,1999)。青少年阶段的智障人士,其身体快速发育成熟,但其智能、独立生活和社交技能却没有相应地快速成长,这种反差带来的混乱贯穿整个青春期(Blacher,2001),给其本人和家人都带来巨大挑战。另外,“性”是青春期智障人士的父母另一个极为担心的事情。因为这些孩子的生理性征与能力都已成熟而智能理解却相对严重滞后(Chamberlain,Passer,McGrath&Burket,1984),是被性侵犯的高危人群(Tang&Lee,1999)。
莹莹的认知水平及实际生活能力虽然只有轻微受损,但确实与智力正常的同龄人有明显差别。玲玲是陈太的重要帮手,协助母亲在学校照顾妹妹。陈太在莹莹被诊断为轻度智障一年后依然在“愤怒”与“讨价还价”的情绪中反复,她谴责命运,责备自己,对自己有极低的评价。她认为,婆婆也在责怪她没有生个健康孩子,没有生个儿子。在教养子女方面,她采用较为负面的方法,只看到莹莹“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像个废人”。她担心莹莹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因而催促莹莹学习超过她当前能力的自我照顾技巧。莹莹说,她在学校经常被同学孤立和取笑,导致心情不佳和烦躁,回到家中容易跟母亲起冲突。
青春期少女身体性征的成熟提升陈太对女儿被性侵犯的担心,尤其是莹莹,智能发展相对滞后因而可能使她比正常智力女孩更加缺乏相关性知识和自我保护技巧。由于长期的情绪困扰、不安全的依恋关系,以及有效共同亲职的缺乏,陈太在教养子女时很冲动,更多采用体罚方式,并且对小女儿的独立有过度期待。没有丰富有力的社会支持,丈夫的支持又被架空,她只能在情感上依赖大女儿;并与大女儿(而不是与丈夫)分担亲职,让玲玲(而不是亲自)教莹莹实际生活技能。这样,姐妹的关系就被母女关系缠绕。更糟的是,莹莹发展的滞后让陈太在女儿的成熟上经历一个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无论在个人面谈还是莹莹在场的家庭面谈中,她都反复说莹莹是“低能的”“没用的”。这让莹莹在其他社交场合发展的自卑在家庭中进一步强化。
香港的社会与文化特点让本已盘根错节的家庭互动更加复杂。首先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父权观念依然强势存在,它要求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和服从,在某种程度将女性置于家内性侵犯的不利境地。中国文化对性的禁忌与道德谴责,以及羞耻文化更加将污名加诸于性侵受害者身上,剥夺家内家外对她们的支持。在香港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里,智障人士及其家人都要承受许多社会歧视、孤立,社会地位较低。同时,重男轻女思想进一步加深未能生育男孩的夫妇的无助和内疚,就如陈太将婆婆对莹莹的不喜欢理解为对她未能生儿子的怨气。每个家庭成员的情感都在家内流动、交汇、互动,终于爆发出种种棘手症状。
四、讨论与建议:发现并巩固家庭力量
目前已有多种治疗性侵犯受害者的临床模式,包括混合个案辅导、小组辅导和家庭治疗。案主在不同的治疗模式中所呈现的信息和获益都会不同(Sheinberg&Fraenkel,2001),并且对儿童和成人的治疗也会有所不同。对儿童受害者而言,家庭治疗为最佳选择,因为这个创伤在本质上是关系创伤(Haskins,2003;Sheinberg&Fraenkel,2001;Stroebel et al.,2012)。对童年曾受性侵犯的成年人而言,最多采用个案辅导和小组工作的方法,协助案主处理未曾处理的创伤事件(Greenfield,2014;Sanderson,2006)。
对陈太这个案例而言,笔者建议以系统理论为基础的家庭治疗作为最主要的介入方式,配合使用其他工作手法。家庭治疗适用本案例是因为:首先,该案例的表征问题之下牵涉的本质是“关系”;第二,家庭治疗的核心——家庭关系与互动模式——正好是陈太所受性侵的创伤本质;第三,陈太童年被性侵经历和莹莹智障,同时影响到陈太家的婚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姊妹关系,这些方面相互影响形成陈太家庭目前独特的家庭结构和互动循环;第四,家庭治疗给治疗师配置一个系统视角,让他在看到每个家庭成员的角色时也看到他们间的互动,提醒治疗师注意到陈氏家庭中父职的缺失;最后,家庭治疗强调承担支撑功能的、嵌于这个家庭内外的优势、资源和抗逆力,治疗的过程就是挖掘这些正能量并协助家庭运用这些资源去进行改变(Wright,Fopma-Loy&Fischer,2005)。
受Putman(2009)与Szymanski和King(1999)等人研究的启示,介入陈太家庭的关键在于带领他们发现家庭资源,并且在整体上给他们赋权。
首先,治疗师必须对家庭保持开放和接纳的态度,与他们建立治疗联盟,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总体上,这个家庭的个体和整体都被社区边缘化和弱势化,那么,在与他们工作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自己的姿态与行为,避免评判和专断。
其次,治疗师将带着同理与关怀,通过单独面谈、夫妻面谈及家庭面谈,仔细聆听和探索个人及家庭的故事。在个人层面,应了解陈太被父亲性侵六年的经历(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发生,频率如何,她当时的反应和感觉,其他家人怎么反应等),以及她如何理解、应对这件事,又是怎样调节的。她当时跟谁披露这件事,对方的反应如何,她又是怎样理解这些反应的?在一个安全和支持的环境中重述创伤经验可以帮助性侵受害者释放积压的复杂情绪,给治疗师一个机会与案主内心的“小孩”工作,让案主在回顾自己的能力时重获力量(Courtois,1996;Liem&Boudewyn,1999)并获得一些洞见和启发。
夫妻层面,应探索陈先生对妻子童年被性侵经历的反应和解读,以及这件事对他们夫妻关系、现实家庭结构的影响。另外,这对夫妻如何相识、结婚、婚姻生活如何,他们以及双方的扩展家庭又是怎样回应莹莹的智障?这些都是理解夫妻互动、婚姻关系以及共同亲职特点的重要线索。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发现并巩固夫妻之间的相互支持及其他家庭资源,以便更好地缓冲陈太童年经历的负面影响以及照顾小女儿的沉重负担。
子女在家中的生活经验是家庭面谈时应探索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家庭会谈的环节中,如果莹莹可以说出自己痛苦、挫败或成就,她应该可以获得更多来自家人的理解、关怀和认可。随之改变的,便是父母(尤其是母亲)降低对她的期待与要求,并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关爱。对大女儿玲玲而言,她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她如何感知现在的家庭结构、母亲的童年经历和妹妹的轻度智障?治疗师应通过这样的探索,了解她看到自己在家庭中所承受的压力,肯定她对家庭的贡献,与此同时也给父母提供另一个审视自己家庭的视角。
将陈太牢牢锁住的,是陈太担心性侵犯事件在自己家庭中再次发生,以及女儿智障带来的挫败感。陈太越担心女儿被性侵,陈先生就越被推得更远,而两个女儿感受到的压力也就越大;莹莹在家内家外的经验越负面,她就越自卑,越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莹莹的能力越低且父女关系越疏离,陈太就更加抑郁、焦虑、自信心低。这是一个将每个人都卷入其中并将每个人的能量耗尽的恶性循环。那么,治疗师的当务之急便是协助家庭建立一个安全的沟通、互动平台,将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家庭互动引到新的方向上,重塑家庭结构,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真诚的情感交流与分享(Butler&Gardner, 2003;Davis&Bulter,2004)。
最后,治疗师还应时刻从发展的视角去理解家庭的特点和需求,并且看到家庭中每个人和每个子系统中具有的优势和资源。例如,虽然童年时经历父亲长达六年的性侵犯,但陈太依然表现的比较坚强、有韧性、有抗逆力。那么,治疗师要做的是,将这个有力量的成年与那个无力的小孩整合起来,用现在的她去疗愈童年的自己。另外,陈太跟丈夫之间的关系比较稳定并且相互支持,他们很少发生冲突,父女之间也比较少发生冲突,这些都是重要的家庭支持资源。第三,陈太非常关心两个女儿,她甚至可以为了保护莹莹不被同学欺凌而跟学校系统对抗。而她成功地管教玲玲,也显示她有足够的能力教养子女。需要向陈太指出并肯定这一点,并鼓励她将一些有效的方法尝试用在小女儿身上,从而提醒她作为母亲的能力感。最后,两姐妹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玲玲对母亲的支持协助,都是这个家庭重要的资源。当然,这个家庭的资源还有待在之后的工作中继续发掘。
五、结 论
童年时受父性侵的经历往往对受害者造成深远影响,困扰其成年后的精神健康、人际关系和家庭生活。困局之中的他们往往被所面对的表征问题遮住了双眼,看不见家庭症结所在也看不见自己的资源和优势。治疗师与他们同行,通过指出优势、注入希望、肯定努力,促进他们在治疗现场的转变。结构家庭治疗认为来寻求治疗的个人和家庭是被生活困住、缺乏选项,那么,治疗的目的就是将他们从固化的习惯中解放,给他们一个安全平台去创造一个新的家庭关系结构(Nichols&Schwartz, 1998)。基于对她们所受创伤与困境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家庭能力的信任,带领他们在一个充满问题的家中寻宝,并且协助他们运用这些宝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是治疗师的重要责任。
[1]陈慧女、廖凤池,2006,《家庭内性侵害受害者之性受害经验,适应症状与咨商介入情形之分析研究》,《咨商辅导学报:高师辅导所刊》第14期。
[2]简美华、管贵贞,2006,《变与不变之间:曾遭遇乱伦经验的成年女性谈母女关系》,《中华辅导学报》第19期。
[3]李长山、段亚平、孙言平、孙殿风,2005,《701名成年女生儿童期性虐待发生情况及危险因素分析》,《中国性科学》第13卷第10期。
[4]龙迪,2007,《性之耻还是伤之痛:中国家外儿童性侵犯家庭经验探索性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陆士桢、李玲,2009,《儿童权益保护:家内性侵害研究综述》,《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第23卷第4期。
[6]王小红、桂莲,2014,《国内儿童性侵犯问题研究综述》,《现代教育科学:普教研究》第4期。
[7]孙言平、段亚平、孙殿风、依明纪、王玖、高风格、仇莉,2004,《606名成年男性儿童期性虐待发生情况调查》,《中国行为医学科学》第13卷第6期。
[8]徐铭绣,2009,《乱伦被害人被害经验及因应历程—以社会工作者经验探讨》,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学位论文(台湾省台北市)。
[9]严健彰,2002,《揭开家庭的秘密:乱伦之痛》,《咨商与辅导》第203期。
[10]Alexander,P.C.,Anderson,C.L.,Brand,B.,Schaeffer,C.M.,Grelling,B.Z.&Kretz,L,1998,Adult attachment and longterm effects in survivors of incest.Child Abuse&Neglect,22(1),45-61.
[11]Ali,A.,Hassiotis,A.,Strydom,A.&King,M.2012,Self stigma in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nd courtesy stigma in family carers:Asystematic review.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33(6),2122-2140.
[12]Ansermet,F.,Lespinasse,J.,Gimelli,S.,Béna,F.&Paoloni-Giacobino,A.2010,Mild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ssociated with a progeny of father-daughter incest: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19(3),337-344.
[13]APA(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5®).American Psychiatric Pub.
[14]Blacher,J.2001,Transition to adulthood:Mental retardation,families,and culture.Journal Information,106 (2).173-188
[15]Bronfenbrenner,U.1979,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Butler,M.&Gardner,B.C.2003,Adapting enactments to couple reactivity:five developmental stages.J Marital Fam Ther 29(3),311-327.
[17]Chamberlain,A.,Rauh,J.,Passer,A.,McGrath,M.&Burket,R.1984,Issues in fertility control for mentally retarded female adolescents:I.Sexual activity,sexual abuse,and contraception.Pediatrics,73(4),445-450.
[18]Chen,C.H.&Shu,B.C.2012,The process of perceiving stigmatization:Perspectives from Taiwanese young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y(Published online 02.01.2012)
[19]Chen,J.,Dunne,M.P.&Han,P.2004,Child sexual abuse in China:a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four provinces. Child abuse&neglect,28(11),1171-1186.
[20]Chen,J.,Dunne,M.P.&Han,P.2006,Child sexual abuse in Henan province,China:associations with sadness, suicidality,and risk behaviors among adolescent girls.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38(5),544-549.
[21]Celbis,O.,Ozcan,M.E.&Özdemir,B.2006,Paternal and sibling incest:a case report.Journal of clinical forensic medicine,13(1),37-40.
[22]Cohen,T.1995,Motherhood among incest survivors.Child Abuse&Neglect,19(12),1423-1429.
[23]Costigan,C.L.,Floyd,F.J.,Harter,K.S.&McClintock,J.C.1997,Family process and adaptation to children with mental retardation:Disruption and resilience in family problem-solving interactions.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11(4),515.
[24]Courtois,C.A.1996,Healing the incest wound:Adult survivors in therapy.WW Norton&Company.
[25]Croll,M.C.2008,Following sexual abuse: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identity re-formation in reflexive therap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6]Cyr,M.,McDuff,P.&Hébert,M.2013。Support and profiles of non-offending mothers of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22(2),209-230.
[27]Cyr,M.,Wright,J.,McDuff,P.&Perron,A.2002,Intrafamilial sexual abuse:Brother–sister incest does not differ from father–daughter and stepfather–stepdaughter incest.Child Abuse&Neglect,26(9),957-973.
[28]Davis,S.D.&Butler,M.K.(2004).Enacting relationships in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a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an enactment.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30(3),319-333.
[29]Eisenberg,L.,Baker,B.L.&Blacher,J.1998,Siblings of children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living at home or in residential placement.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39(3),355-363.
[30]Finkelhor,D.,Ji,K.,Mikton,C.&Dunne,M.2013,Explaining lower rates of sexual abuse in China.Child abuse &neglect,37(10),852-860.
[31]Fitzgerald,M.M.,Shipman,K.L.,Jackson,J.L.,McMahon,R.J.&Hanley,H.M.2005,Perceptions of parenting versus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among incest survivors.Child Abuse&Neglect,29(6),661-681.
[32]Greenfield,R.M.2014,The Attachment Function of Acute and Chronic Suicidal Illness in the Psychotherapy of an Adult Female Incest Survivor.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42(1),49-60.
[33]Haveman,M.,van Berkum,G.,Reijnders,R.&Heller,T.1997,Differences in service needs,time demands,and caregiving burden among parents of person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across the life cycle.Family Relations,417-425.
[34]Haskins,C.2003,Treating sibling incest using a family systems approach.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25(4),337-350.
[35]Ji,K.,Finkelhor,D.&Dunne,M.2013,Child sexual abuse in China:A meta-analysis of 27 studies.Child abuse &neglect,37(9),613-622.
[36]Kerr,M.E.&Bowen,M.1988,Family evaluation:The role of the family as an emotional unit that governs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Markham,Ontario:Penguin Books.
[37]Kreklewetz,C.M.&Piotrowski,C.C.1998,Incest survivor mothers:Protecting the next generation.Child Abuse &Neglect,22(12),1305-1312.
[38]Liem,J.H.&Boudewyn,A.C.1999,Contextualizing the effect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on adult self-and social functioning:An attachment theory perspective.Child Abuse&Neglect,23(11),1141-1157.
[39]Ma,E.Y.&Li,F.W.2014,Developmental trauma and its correlates:a study of Chinese children with repeated familial 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in Hong Kong.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27(4),454-460.
[40]Nichols,M.P.&Schwartz,R.C.1998,Family therapy:concepts and methods(4th ed).Boston:Allyn and Bacon.
[41]Putman,S.E.2009,The monsters in my hea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the child survivor of sexual abuse.Journal of Counseling&Development,87(1),80-89.
[42]Rhind,N.,Leung,T.,&Choi,F.1999,Child sexual abuse in Hong Kong:double victimization?Child Abuse& Neglect,23(5),511-517.
[43]Ryan,A.S.&Smith,M.J.1989,Parental reactions to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in Chinese American families.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6(4),283-299.
[44]Rudd,J.M.&Herzberger,S.D.1999,Brother-sister incest—father-daughter incest:a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equences.Child Abuse&Neglect,23(9),915-928.
[45]Ruscio,A.M.2001,Predicting the child-rearing practices of mothers sexually abused in childhood.Child Abuse &Neglect,25(3),369-387.
[46]Sanderson,C.2006,Counselling adult surviv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47]Schuetze,P.&Eiden,R.D.2005,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ual abuse during childhood and parenting outcomes:Modeling direct and indirect pathways.Child Abuse&Neglect,29(6),645-659.
[48]Sheinberg,M.&Fraenkel,P.2001,The relational trauma of incest:A family-based approach to treatment.Guilford Press.
[49]Stroebel,S.S.,O'keefe,S.L.,Beard,K.W.,Kuo,S.Y.,Swindell,S.V.&Kommor,M.J.2012,Father–daughter incest:Data from an anonymous computerized survey.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21(2),176-199.
[50]Stroebel,S.S.,Kuo,S.Y.,O’Keefe,S.L.,Beard,K.W.,Swindell,S.,&Kommor,M.J.2013,Risk factors for father–daughter incest data from an anonymous computerized survey.Sexual Abuse:A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Treatment,25(6),583-605.
[51]Szymanski,L.&King,B.H.1999,Practice parameters for the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children,adolescents, and adul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and comorbid mental disorders.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Working Group on Quality Issue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38 (12 Suppl),5S-31S.
[52]Tang,C.S.K.2002,Childhood experience of sexual abuse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Child abuse&neglect,26(1),23-37.
[53]Tang,C.S.K.&Lee,Y.K.S.1999,Knowledge on sexual abuse and self-protection skills:A study on female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mild mental retardation.Child abuse&neglect,23(3),269-279.
[54]Tsang,H.W.,Tam,P.K.,Chan,F.&Cheung,W.M.2003,Stigmatizing attitudes towards individuals with mental illness in Hong Kong:Implications for their recovery.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31(4),383-396.
[55]Tsun,O.A.1999,Sibling incest:a Hong Kong experience.Child abuse&neglect,23(1),71-79.
[56]Wang,X.&Ho,P.S.Y.2007,Violence and desire in Beijing:a young Chinese woman's wtrategies of resistance in father–daughter incest and dating relationships.Violence against women,13(12),1319-1338.
[57]Wright,M.O.D.,Fopma-Loy,J.&Fischer,S.2005,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resilience in mothers who are child sexual abuse survivors.Child Abuse&Neglect,29(10),1173-1193.
[58]Zuravin,S.J.&Fontanella,C.1999,Parenting behaviors and perceived parenting competence of child sexual abuse survivors.Child abuse&neglect,23(7),623-632.
编辑/刘文彬
C916
A
1672-4828(2017)04-0054-11
10.3969/j.issn.1672-4828.2017.0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