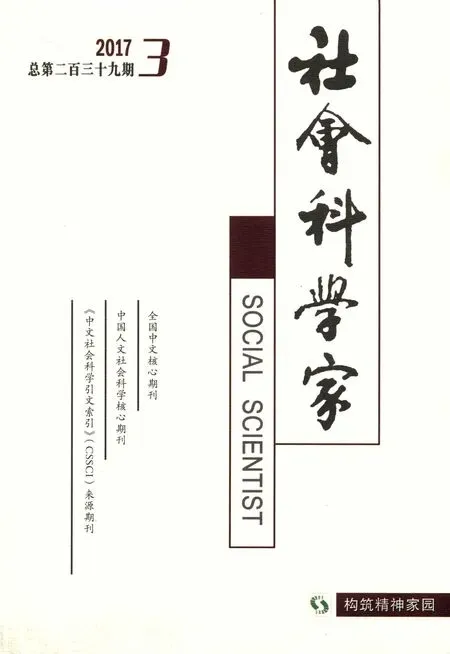现代化转型中的现实主义文学蜕变
——对改革题材小说创作的一种观照
2017-04-11张勇
张 勇
(湖南理工学院 中文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0)
现代化转型中的现实主义文学蜕变
——对改革题材小说创作的一种观照
张 勇
(湖南理工学院 中文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0)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改革题材小说发生的内在动力,也是这一题材小说走向复杂和多元的深层原因。80年代前期的国企改革文学表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愿望和理想,而农村题材改革小说则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心理有更多的反思和批判。90年代中期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由于认同了现代化语境中的欲望叙事法则,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自然主义特征,而世纪之交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则重新借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事规则。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继续前进的根本,在新的价值立场上,改革题材小说创作应该对中国社会现实表达一种整体关怀。
改革题材;小说创作;现实主义;现代化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前苏联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基本方法,中国作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创作历程中接受了这一方法。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正式确认为指导“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和“根本方法”。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正确的世界观’对于艺术创作的决定作用,要求把关于未来的完满构想加于严峻的客观现实之上,以至于把政治的、道德的说教加于生活的真实之上,因而它本身就存在着偏离现实主义的倾向。”[1]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用社会主义限定现实主义,强调理想性和倾向性,强调文艺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美学化。“文艺的政治化,即指把文艺纳入政治体制内,文艺从题材、主题到手法、形式都必须遵循政治的要求,为政治需要服务……政治的美学化,即指政治以理想化的形态通过文艺形象(形式)的途径来表现、实施。”[2]文艺为政治服务,在那个年代具体而言就是为阶级斗争胜利的需要服务。总体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于注重先验理性和理想,强调用先验主题规制现实生活,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由此而来,而这显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创始人的初衷是不一致的。恩格斯认为,作家的倾向(观点)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专门把它表达出来,他在《致玛·哈克奈斯》一文中指出:“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3]强调真实性本身所具有的批判力量,而不是用先验的观念、理性来规定生活的真实性。
由此可见,80年代前期的国企和城市改革文学确实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主题先行,先验理性,政治斗争模式,改革英雄典型形象的塑造,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都使得这种类型的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去不远。在笔者看来,这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改革文学毕竟是在改革开放相对自由的语境中作家自主选择创作方法的结果,而“文革”的文化专制主义则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唯一的选择;另外,经历过“文革”阶级斗争以及新时期启蒙思潮洗礼的作家们对人性的复杂内涵也有了更多自觉的体悟和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物的简单化和脸谱化倾向。
有意味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出现的农村题材改革小说和上述的城市和国企改革文学在创作的精神意向和审美选择上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农村题材改革小说比城市和国企改革文学能更深入地贴近生活,更具有生活的质感和实感,理念化的色彩相对较弱,对文化、历史和日常生活也有更深刻的发现和感悟。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农村题材改革小说倾向于贴近普通中国人在改革中的现实生活,反映在时代变革中普通农民心理的变化,表达他们生活的愿望,再现他们的努力与追求,对社会变革的艰难和农民文化心理痼疾也多有揭示和反思,因而从整体上呈现为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这些农民不是什么改革的英雄,他们没有豪气干云的宏伟抱负,有的只是改善自己生活、改变自己命运的朴素愿望,在时代的变革中也表现出自身与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不无关系的缺陷和毛病,这些都显得真实可信。如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将改革初期农民经济地位的变化带来的心理和精神世界的变化生动真实地揭示出来,同时也揭露和批判了农民文化心理结构中固有的苟且、自欺的劣根性。
在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者看来,“以追求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为核心,现实主义形成了三个基本特点: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现实关怀、以科学——理性精神为基础的典型化手法,以及建立在这两个特点之上的现实批判精神。”[2]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而不是先验的理念和预设的理想,从理念和理想出发来进行想象性的写作终究和现实生活是“隔”着的。作家刻画真实的社会生活是出于对社会现实的整体关怀,希望这个社会更加人道、文明和美好,可见现实主义精神本身是包含了理想成分的;而科学和理性的精神又使得作家不得不正视社会本身固有的矛盾和弊病并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80年代中期出现的农村题材改革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念先行、先验理性的缺陷,而回归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即批判现实主义。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改革小说和前述大致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城市和企业改革文学虽然都是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创作,但是二者又确实大不一样。在笔者看来,城市和企业改革文学体现的是那一时代的人们急于呼唤改革精神和改革英雄,宣扬改革理念,表达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理想和愿望,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从现实生活出发来创作的原则。当然,80年代中期的农村题材改革小说仍然具有80年代理想化的整体色彩,仍然显得不够深刻,这或许是因为80年代的改革成就是主要的,还没有产生那么多现实的问题和困境,作家也不能完全超越他那个时代,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
二
90年代以来,改革事业继续深入,然而,此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对现代化的理想化想象,现代性的后果已经充分显现。因此这一时期写实性的文学作品中似乎出现了两个“中国”社会,一个是由高尚住宅、白领、老板、酒会、豪车构成的都市风景线,而另一个则是下岗、贫困、疾病、企业改制构成的中国底层社会。其实这正是现代化的后果之一——社会的分化和分层。很显然,面对着9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严肃的作家总会勇于担当,关注和描绘中国社会改革困境和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就成了很多作家的选择。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又被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创作潮流重返现实主义,《大厂》、《乡关何处》、《年前年后》、《分享艰难》、《穷县》、《大雪无乡》等一批作品引起了文坛的强烈反响。作家用自己的创作表达了对现实的关注与担当,这本是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突出特点,我们也应该高度评价这些作家重建历史的努力。然而,如果我们用经典现实主义的原则来观照这一次重返现实主义的作品,却发现这些作品的传统现实主义特征已经模糊不清。有批评家就认为,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一方面对转型期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采取某种认同态度,缺少向善向美之心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的作者虽然熟悉现实生活的某些现象,但他们对现实缺少清醒的认识,尚不足以支撑起真正的历史理性精神。[4]
也就是说,90年代中期的所谓新现实主义不具备经典现实主义的某些基本要素和根本原则。如《分享艰难》中的地痞洪塔山强奸了西河镇党委书记孔太平的表妹,本应该将其绳之以法,但是这个洪塔山却是个暴发户,决定着整个镇子的经济,为了挽救全镇经济,孔太平甚至向舅父下跪,请求他不要追查这个流氓;而《大厂》中的吕建国为了维持工厂局面而四处求情,以苦苦的哀告、恳求、流泪来获得人们的同情,使问题得以解决或暂时停息。这些基层单位的管理者哪里还有80年代前期改革文学中“乔厂长”那样的改革家的英雄气概和强者风采?面对着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和野蛮,他们也缺少那种不妥协的批判和反抗精神,他们所关注的就是利益的分配和欲望的满足,在利益的冲突和欲望的矛盾中捉襟见肘,勉强支撑。因此,这些作品引起了前述批评家的批评也就是必然的了。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这些作品或许就是中国社会现代性历史进程中复杂性和多元性的表征。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改革事业的艰难性、曲折性和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我们原来的设想和预计。“过多的东西寻求断裂性的变化,历史的时间序列改变成共时性的空间状态。结果,被称之为‘现实’的那种东西,堆积着过多的不相协调的因素。”[5]因此,作者的暧昧态度不过是现实暧昧性的翻版而已。如果现实本身都变得无比多元庞杂而暧昧不清,那我们又如何能要求作家能够完全穿透现实呢?泛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个时代已经显得可疑,不再能成为叙事的可靠基础,而新的现实也还没来得及建构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基础。
在这种情况之下,作家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欲望叙事的法则。现代化已经充分显示了自身的后果,时代的发展对每个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人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这些作品中,考量这些基层管理者和改革者的不再是锐意改革的精神、大刀阔斧的魄力、推动历史进步的宏大抱负,而是他们如何谋取地方和企业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如何带领百姓和员工走出经济困境,在艰难中负重前行,理想主义的光彩消失殆尽。能够与时代的世俗利益追逐和欲望法则相抗衡的只是基层改革者或者管理者个人的道德和人格,而这也显得那么卑微和可怜,只是在这种沉重而艰难的底色中偶尔闪现某些光彩和亮色。当经济和利益、物质和欲望的追逐成为时代的重心之时,我们看到的是生存本身的灰色和主体精神的暗淡。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中期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或许在主观上试图以整体关怀精神重建反映改革现实的宏大叙事,但是现实本身的多元混杂使得这种目标不再可能。“这些作者在艺术上秉承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但已经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前提可以依靠,这就使他们的历史冲动与他们的具体叙事必然产生抵牾。企图建构这个时期总体性的历史叙事,都显得力不从心,历史的目的论总是在‘历史过程’中被解构。”[5]
既然在形而上层面缺乏真正的思想力量穿透混杂多元的现实,就只能在形而下层面认同时代的欲望叙事法则,因此,这些所谓新现实主义作品既没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那种雄视古今的自信,也缺少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当下现实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作品呈现出自然主义文学的某些特征。除了上述原因,这或许也受到了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写作态度和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写实主义”小说解构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执着于对“原生态”生活的描绘,而所谓的“原生态”生活不过就是人们的世俗欲望和因为欲望的争夺和受挫而带来的丑恶和烦恼,抹平了深度,放弃批判精神。很显然,“新写实主义”小说的自然主义色彩颇为浓厚,而认同了时代欲望叙事法则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中短篇小说同样具有叙事的平面化特点,缺乏历史理性和批判精神。如前所述,《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是野蛮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家致富者,他强奸了镇党委书记孔太平的表妹,而孔太平为了镇里经济的发展,置法律和正义而不顾,反而放过了洪塔山;而《大雪无乡》中的陈凤珍为了镇里的经济发展,也不得不依靠暴发户潘老五。
面对世俗化生存现实,放弃对某种政治意向和理想、先验精神和理念的承诺和表达,成为新的历史时代里文学创作的趋势。“就此而言,应当充分认识到新的写作趋向的必然性和积极意义。然而,新的写作趋向同时暴露出了相应的问题。这就是,在张扬个性的同时,放弃了对社会整体的关注;在肯定感性(情感和欲望)价值的时候,否定了精神价值;在追求真实的表现的时候,丧失了理想表达的能力。”[2]今天我们仍然不得不反思和追问,在发展经济、获取利益和坚守价值、维护公正之间孰轻孰重?或者在社会改革中这两者就必然是矛盾和冲突的?高尔基当年在谈到对自然主义的认识的时候指出:“当然,这是真实,是十分龌龊的、甚至令人痛苦的真实,必须同这种真实进行斗争,一定要无情地把它消灭掉……但是自然主义这个手法,并不是同那应该消灭的现实进行斗争的手法。”[6]尽管社会改革和转型中确实存在这种丑恶现象,但作品态度的暧昧和立场的失据却伤害了其自身应该具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
三
世纪之交,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大量涌现,代表作品有《车间主任》、《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抉择》、《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这批长篇小说因为产生时间和“现实主义冲击波”(或新现实主义)相去不远,并且也同样关注改革进程和现代化转型中经济困境的现实,因此也曾经被纳入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范围,但在笔者看来,世纪之交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和“现实主义冲击波”潮流中的中短篇小说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种区别并非仅仅表现在小说的篇幅上,而是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社会全景式的整体关怀和重建宏大叙事的努力,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基础就是意识形态的重新认同。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认定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才能完成长篇小说的宏大叙事建构和现实整体关怀的目标。那么问题的关键是,这一次宏大叙事的建构所依据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什么呢?“能够把这些文本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提出来讨论的是,它们共同具有某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曾经作为社会主义中国主流文化样式——的修辞特征:以戏剧性冲突组织起来的问题性事件、以‘英雄’形象负载某种价值功能的典型人物、以具有地域色彩或社群特征的具体空间作为基本环境。”[7]也就是说,这些改革题材长篇小说在叙事策略和意识形态实践上都一定程度上回归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然要区别的是,世纪之交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虽然一定程度上回归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和80年代前期的改革文学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书写很不一样,这些改革题材长篇小说更直接正视了改革进程中艰难曲折的现实,更加接近改革生活的实际。
没有人可以否认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现代化和城市化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然而,在如此美好的现代化图景中,我们往往忽略和遮蔽了另一幅社会图景和社会现实,即社会的分化和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弱势群体,沉默的大多数,底层社会,是我们对这一现象的命名。面对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创伤和阵痛,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必须对诸般社会现实表达自身的整体关怀,建构文学世界的形象体系,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抚平创伤,重新唤起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下文化整体结构中的力量也在于此。然而,市场化、城市化改革带来的社会阶层的分化中,利益受损害群体却主要是工人和农民——这一在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实践中居于历史主流地位的主体,这些人物在红色经典小说叙事中,绝对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但是这一次他们却是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如张宏森的《车间主任》表现了北方重型机械厂以车间主任段启明为主的一个车间工人从秋入冬几个月的生活。工人刘义山因公受伤只能在家病休而不能得到治疗,李万全因为太穷而偷卖工厂的旧机器,女工人肖岚被到美国读研究生的男友抛弃……企业改革和社会变革过程中阶层的分化更加明确了小说人物的阶级身份和意识,然而,这一次他们却是作为利益被损害的阶级出现。
有意味的是,在这里,伴随着利益受到损害而明确的阶层和阶级意识并非要导向过去年代曾经有过的阶级仇恨和斗争,而是要重新唤起这些工农群体在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主人翁意识和道德情感。尽管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尽管他们身陷贫困,但是作品试图通过借助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这些工人塑造成为新的改革时代的主体。因此,他们不应该再计较自己的生存困境和利益受损,而是继续无私奉献,兢兢业业,把自己的全部献给工厂。于是,在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可以作为典范的老工人形象——夏玉莲,她任劳任怨,不计名利,身体虚弱,卧病在床,但坚持不要工厂的医药费补助,甚至以死阻挡工人到市政府门前示威。这些作品包含的道德化情感和意识形态内涵是显而易见的。“它建立在一种重新叙述的集体认同之上,并由此抹去被管理者、利益受损害者的怨憎,并吁求他们再度心甘情愿地付出。这一新的集体认同或现实叙述,由此成为重新整合‘现实’的有效意识形态实践。”[7]事实上,唤起集体认同,抹平现实矛盾,将新的现实在想象中给予合法化,这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功能。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当年对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首先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关注是“人的完整性”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当时的卢卡契真诚地希望,作为现代文学主要形式的小说,仍能像以往的史诗那样,承担起调和物质与精神、生活与本质的关系,实现原先那种意义与生活不可分割的乌托邦理想。”[8]赋予生活以意义,重建个体与社会的联系,在时代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中获得一种整体感和认同感,这或许是现实主义文学努力的方向。然而,仅仅依靠重新借助传统意识形态似乎并不能真正地获得一种表意和穿透现实的有效话语和思想力量,文学需要不断创新和超越。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改革题材的现实主义小说应该能够找到新的观察社会和叙述生活的坚实的立场和依据,通过富有创造力的文学创作将已经分化的社会重新整合在一起,在批判和整合中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精品。
[1]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7.
[2]肖鹰.现实主义:从欧洲到中国[J].甘肃社会科学,2001(1):3-9.
[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2.
[4]陶东风,童庆炳.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J].文学评论1998(4):43-53.
[5]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92;391.
[6]高尔基.高尔基文学书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273.
[7]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230;246.
[8]盛宁.现代主义.现代派.现代话语——对“现代主义”的再审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5.
I247
A
1002-3240(2017)03-0139-05
当代文学史新时期前期的改革文学适应着“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启动而获得了巨大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资源,代表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内在的历史冲动和全体中国人的生活愿望,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效应,也因此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深刻的痕迹。改革文学的发轫以1979年蒋子龙发表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为标志,随后改革文学的创作形成了一股汹涌的潮流,《开拓者》、《新星》、《沉重的翅膀》、《祸起萧墙》、《家园街五号》等小说的出版掀起了改革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高潮。毫无疑问,改革文学所表征的是刚刚结束“文革”动荡的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历史冲动,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理想的美好向往。这似乎再次验证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往往是该时代历史愿望和社会情绪的反映这一论断。除此之外,改革文学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特征、改革家英雄形象的塑造也有助于改革文学的文学史地位的确立。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历程,当我们回首当代文学史的改革题材小说创作,可以发现,改革题材小说创作应现代化运动而起,也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而变得复杂和多元。
一
当80年代前期的改革文学大潮成为历史,随着改革事业的深入以及新时期文学自身的发展,人们对改革的艰难性、曲折性、复杂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会,改革文学也真正摆脱了当年的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因此,人们对80年代前期的改革文学所表达的现代化想象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观念和模式又有了更多的反省和思考。在笔者看来,当年的改革文学尤其是城市和国企改革文学的问题主要在于在作品内容上改革的理念先行,缺乏对改革现实的真实生活内容更多的体验,在形式上则有模式化的特点。因而从整体上来看,改革文学仍然是一种类同于新时期之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其创新可以视为“旧瓶装新酒”,而这新酒也不过是一种不同于革命年代的观念化的社会生活。我们甚至可以假设一下,套用当年国企和城市改革文学的外在形式,将其内容置换为“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似乎也非常妥帖和合拍。因此,今天看来,改革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表达了那一时期的历史愿望,鼓舞了中国人投入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信心,但相对于80年代社会生活和文学自身创新的要求而言,改革文学从观念到形式还显得比较陈旧。
2016-12-11
本论文为湖南省教育厅项目:现代化语境中的现实主义小说潮流研究(12K119)阶段性成果
张勇(1975-),湖南湘乡人,文学博士,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校:阳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