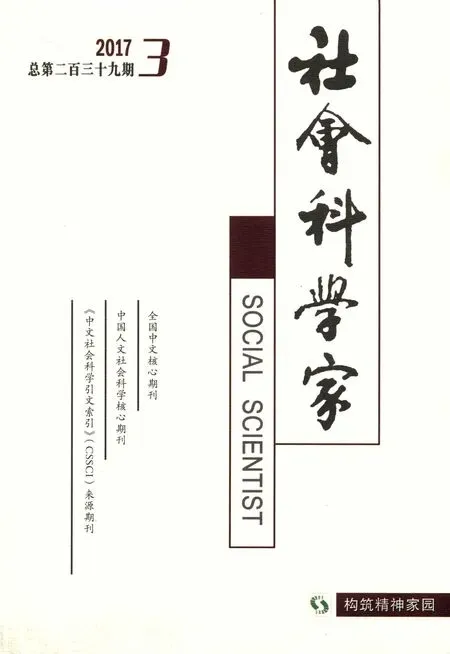思想的“奇点”暨古怪的相似性
2017-04-11尚杰
尚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博导新论】
思想的“奇点”暨古怪的相似性
尚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思想的“奇点”,指的是真实的思想状态缘起之时正在发生着的真实内容,这个内容之所以被称为真实的,是由于考虑了时间因素,它使得原样的思想是在寻求各种各样的相似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也就是类比与隐喻的过程。这个过程消解了所谓真理语言与虚构语言之间的界限,使思想处于亦此亦彼的过程之中,从而对建立在以同一性为基础上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思想的“奇点”和古怪的相似性,是对德里达关于“解构”的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并且试图从中描述微观领域的涵盖不同学科的人类精神动态,更新对人类精神的探讨渠道。
奇点;思想;隐喻;相似性解构
一
我所谓思想的“奇点”,指一切广义上的思想(包括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数学自然科学、人们的日常心思)之难以被正在思想的“思想”所察觉的、奇怪而细微的缘起点,它揭示真实的精神状态究竟是如何出场亮相的——这里的“如何”与“亮相”之间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思想总是从“亮相”起步,而完全忽视了“如何”,从而使得我们所收获的,只是遗漏了“如何”即忽视了思想细节的“宏大”思想,后者是一个现成的、被定义了的、有约定俗成含义的具有观念或者概念性质的“思想”并因此是僵死的、虚假的思想,因为它同时也忽略了一个事实:一切思想都是发生在时间之中的思想,它不考虑时间因素(即使它表面上也讨论时间,但“时间”被当成所讨论的对象,而不是构成思想本身的骨架),即它无视“一切思想不过是瞬间的思想”,并且通过化为词语的思想而重复自身。也就是说,将原本是瞬间的思想永恒化。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它是一个假推论、它宣称的“怀疑一切”并不是真的,因为它不彻底,它有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笛卡尔默认了一切思想不仅可以而且必须用语言表达出来。在表达过程中,作为追求清晰明白的观念的哲学家,笛卡尔还默认了他其实在实施“怀疑一切”的思想实验之前,自己就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我”、“思”、“在”,因此他才有能力用归纳或者排除的方法,驱除心魔即内心深处难缠的“邪恶的天才”,在隔离了一切疯狂的不理智的胡思乱想之后,只剩下清楚明白的观念,它代表了形而上学“在场”的思想。
综上,当我们赞扬一个思想家或者作者,通常会说:他思想清晰,每一步都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当然,如果读者也有如此的“清晰观”,就会与作者有思想共鸣。但是,这样的作者和读者都忽略了,引起他们共鸣的是“什么”——无论它们是什么,它们的本质特征都是“什么”,一些在含义上已经完成了的习俗或概念。换句话说,它们是一些已经被我们事先知道了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们符合我们不必每次都阐明但彼此心照不宣的逻辑规则,无论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甚至即真又假的,我们事先早就有了辨别它们的标准。我们总是用已知的东西去判断和预测未知的东西,当我们说“虚无”时,是因为我们先知道了什么是“存在”,进而事实上把“虚无”当成存在的某种极其特殊的形式,就仿佛虚无也是某种东西似的;当我们说“圆的方”,相当于圆+方,尽管就画不出这样的形状的意义上说,它不是某种能形成客观对象的东西,但我们都理解表达式“圆的方”所蕴含的意思或意义,这个意思,也可以被当成可以被思想的东西。
于是,以上的东西,都属于广义上的“清楚明白的观念”,它们之所以有如此效果,是因为思考的“脚步”停下来了:昨天和今天我都去长江游泳了,即使明天,我还得叫它长江,否则别人听我说话就会产生误解,一切交流乃至翻译都变得混乱、不可能,到此为止,我和笛卡尔一样,都没有脱离用常识思考问题,都没有理睬赫拉克利特留给后人的智慧:“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无论说话还是写作,出于交流的良好愿望,我们总是习惯地决不让思想躲藏起来,总是使用“具有观念或者概念性质的‘思想’”相互交流思想,例如“活着就是去追求幸福”,倾听者没有必要继续追问什么是幸福,因为大家似乎都已经知道了幸福的含义,但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只要去“说话”,立刻就涉及理解或者解释。但是,问题并不在于思想确实需要被理解,而在于传统哲学所谓的“理解”其实是建立在语言在开口说话之前就“已经被完成了的思想活动”,因为我们已经约定好了构成语言基本要素的词语或概念的含义,就像建筑语言大厦的一块又一块现成的砖瓦。但是,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思想的真相喜欢躲藏起来。
思想的“奇点”就是这样的真相。“奇点”来自英文singularity,意思是异常、奇怪、奇特。它是某种不可思议的X,它像是一颗没有形状的“精神种子”,只发生在偶然的奇遇场合,外表平静却隐藏着巨大能量,可以像闪电一样迅速击中人类最为脆弱的内心世界,能迅速长成思想上的参天大树。当它表达一个概念时,没有利用从前人们赋予该概念的任何已有的或现成的意思,所以此刻的思想不是从已知到未知,而是创造性的从未知到未知。它不使用逻辑的归纳和演绎的方法推进思想,而是使用种类繁多的极其罕见的类比或“好像”,位于“好像”左右两边的意思能连接起来,似乎完全来自天降灵感,这种连接像是一些创造出来的相似性,而单从外表上看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没有关系、不相似。这些相似性是微妙而敏感的想象力“凭空”建立起来的,它们来自人类非凡的心思,而决非像一只猴子敲键盘敲打出来的“诗句”。这些相似性是用“和”或“与”连接起来的应和关系,也叫做感应或者象征,它们是“兴”起来的思想,是以隐喻为特征的各种比喻——所有这些都与巴门尼德开创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传统完全决裂——例如从长头发联想到海浪、从自杀联想到美丽、从宇宙联想到抑郁……这些被连接起来的词语之间原本并不相似,靠好奇心与想象力创造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它们之所以区别于猴子敲键盘,是因为它们来自敏锐非凡的却也不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思。它们消解或解构了词语原有的定义或者界限,“美丽得像自杀”就得重新理解“美丽”与“自杀”,还有更加高难的相似性:一个青年人帅成的样子是耸人听闻的,如同一把雨伞与一台缝纫机在解剖台上偶遇——在这里,“好像”得匪夷所思,但仍旧既不是精神分裂症亦非猴子敲键盘的结果,它只是以令人目瞪口呆的表达颠覆思想的常识或常识下的思想。它不属于“用观念写思想”的形而上学传统,传统上观念总是落实到某个名词,例如“这是一块白布”,其中的本体论因素是“布”,否则起形容词作用的“白”就飘在空中无法落实。但就纯粹视觉刺激而言,我们可以暂时搁置词语(“布”)的观念性而返回词语的肉身性或者物质性,这就是印象派绘画对古典绘画的革命(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现当代欧洲哲学质疑古典哲学):“白色在它成为一块白颜色的布之前就已经是白色。绘画的快乐远大于模仿的快乐。”[1]
二
印象派绘画对古典画的革命,在于画布上画出的“白布”只返回白色本身,并且与其他颜色搭配形成美的关系,完全不考虑画面与画布之外作为物理存在物的“白布”是否相像的传统问题——同样,当代法国哲学家也如此批评传统的哲学,我这里选读德里达的“白色的神话”一文,是他的《哲学的边缘》[2]一书的第七章。
传统哲学总是试图把词语概念化、观念化,然后把思想等同于众多“什么”(即概念或者观念)之间的“加减乘除”即逻辑推理。当哲学家们相互批评时,其实是在争论对方对某概念的定义是错误的而自己的定义才是正确的,但这其实是一种假争论,因为彼此都设定了本体论(即询问事物是什么)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于是,他们认定本体论是真理的语言,它建立在广义上的逻辑证明(包括形式逻辑、哲学逻辑或辩证法)基础之上。但是,传统哲学家如此看待“哲学”时,完全忽视了哲学思考所使用的,终究是自然语言,哲学中的所谓逻辑是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的。如果哲学脱离了自然语言而使用人为规范好了的广义上的形式逻辑语言或人工智能语言,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是哲学之外的任何一个新学科,但是它从此就绝对不再属于哲学。
哲学家忽视了自己其实是用自然语言进行思考,在德里达看来,它表现为传统哲学家忽视了所谓“哲学语言”的性质其实是隐喻,其基本特征,就是想象出各种各样的相似性,然后以类比的方式建立、连接、推进思路或思想。如果哲学实际上一直在使用具有隐喻性质的自然语言,却误认为自己是真理的语言而非虚构的语言,那么,哲学语言就一直在“说谎”,因为它让人们相信哲学概念字面上传达出的意思是准确的、正确的,从而完全掩盖了其隐喻性质,掩盖了“真理语言”自身是有杂质的,而不是同一的或纯粹的。所谓杂质,就是自身已经含有朝着各种各样的相似性方向发展的潜在的可能性,哲学智慧就体现在选择这些可能性的能力,在有意无意之中将某X因素与某Y因素连接起来的能力,它是思考的艺术而非思考的规范。
柏拉图在解释什么是理念时,使用了著名的洞穴之喻。任何隐喻都是感性的、有具体的时间和场合,这是相似性本身的要求。月亮的存在有两个事实,一个事实是在没有人类之前月亮就已经存在了,但这个存在对于人类自身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另一个事实,是有人在场的情形下由人去描述月亮,在这样情形下无论人如何描述月亮,哪怕是在荒唐地描述,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其中的人性就是感性。如果有人反驳说这不符合科学的真实,但这反驳是不成立的,因为一切科学命题都有一个判断的主体,即它是人眼中的或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判断,即使是看似最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的几何公理,事实上也是人的思想去抽象组织而成的几何图像。人把自己的思想赋予看见的一切,这已经是荒谬了:客观的东西是主观的(人若没有眼睛能看见月亮吗),而主观的东西是客观的,即所谓客观事物所具有的性质,不过就是人用自己的思想强加的。怎么强加呢?一定是出于人自身的天性,这天性的第一要义,就是自发地想到各种各样的、匪夷所思的相似性,它就是人类精神的出发点:一种热情、冲劲、强烈的感情。这时还没有形成逻辑的规则(不存在“必须如此推论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这些情形下的“相似性”并不在意自相矛盾,例如我现在说“我死了”——它是有意义的,尽管按照逻辑的要求这个表达式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思想情形违反排中律,但是就像虽然芝诺说快腿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并从数学上给出了难以反驳的逻辑根据(即把一段距离切割成1/2的情形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阿基里斯在追上乌龟之前无法跑完“无限远”的距离),事实却是这个大长腿几步就追上了乌龟,这可不是比喻而是事实。思想的奇点就在于,反过来我们可以说这个事实具有隐喻性质,而隐喻本身所描述的,就是比“真”还真的真实:此瞬间与彼瞬间之间是根本无法分割的(绵延不绝的过去-现在-将来),就像心思沿着广义上的相似性方向“前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思想总是连接到某个陌生状态,以致无穷无尽。芝诺的错误,在于他用空间思维方式取代了思想的绵延即时间。也就是说,他过于相信语言和概念,他只看到形式的不变性而忽视了内容的流动性或可变性。
换句话说,哲学与科学的问题一样,往往是以转化的形式得到解决的。这个转化,就是说A与B情形相似,但有赖于思想自觉主动地建立起如此的联想,否则它就是永远的秘密,不会被人们知道。这就是隐喻的思想价值。A的真相在B那里,所以要“换句话说”。寻求相似性的情形是广义的,其情形十分繁杂,例如有些东西吸引我们,它们是我们自身所缺乏的东西,于是好奇、有兴趣,甚至产生爱,但这里要有某种或明显或隐蔽的共鸣因素,思想才会有真正的进展。相似不是等同,区别在于在置换过程中创造了剩余价值,例如,说一块金属现在被铸造成硬币,这是隐喻说法,因为其中含有相似性,但反过来说(A=A是同一性思维:硬币不过就是金属),思想就原地踏步没有进展。在这里所谓相似性,就是在原有的因素中添加新成分,但旧的痕迹仍然保留着。德里达写道:“修辞每次都在揭示隐喻,隐喻包含的不仅是某种哲学,而且是错综复杂的概念,哲学就是在这些概念中构建起来的。如此复杂的思想之网的每个思路,都是其中的一环。”[2]从修辞学(或者隐喻)思考哲学,如同将金属铸造成硬币,或者凸显硬币上的花纹,它把热情或爱的因素融入了哲学(就像金属变成了有头像和花纹图案的硬币,就像一块大理石被雕琢成一座人像),它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剩余价值即硬币,单纯的金属就什么都不是,即不属于爱出来的智慧。他继续写道:“哲学的主题是以隐喻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在哲学话语的表面实际起作用的,都是某种隐喻。”[2]于是,哲学思想并不是通过逻辑理性,而是通过隐喻之链获得进展。那么在这里,哲学使常识发生了智慧上的质变,也就是超越,一种与诗意相融的艺术,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逻辑理性。
我们用语言思考语言,而这决不同于用观念思考观念,不懂得这一点,就仍旧受困于传统哲学的思考模式。用语言思考语言,倾向于隐喻即诗意,它的思考艺术与狭义上的语言是冲突的,但是决不在维特根斯坦所谓“不能说”的地方缄口不说,反之仍旧可以说得深刻有趣,因为它将绵延即时间因素真正引入了哲学。哲学思考不再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上,而是一种性质的语言连接另一种性质的语言,不是一种语言,这是典型的隐喻性质的语言,就像普鲁斯特说的,有才华的作家的作品,就像是不间断地“用外语”写成的。所有这些情景,都被我称为“思想的奇点”或“古怪的相似性”。这里的相似性其实是在肯定差异性,思想连接起一个处于异域里的陌生的X,由小甜点的甜怎么会联想到甜蜜的笑脸,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讲,但它们之间已经实实在在地相互诱惑,彼此有了热情。趣味和思想都在于这里让两个不同的景象(包括思想事件)之间恋爱生子。也就是说,它们沉浸其中,而若是没有相异的因素,相似就不可能发生。当然,只要有微妙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类似的相似性可以无穷无尽,它们具有化平庸为神奇的能力。
传统本体论,关注点落实在名词(概念的另一种说法),它的实质是模仿,而模仿的前提是可重复性,它落实在一个点上,同一个名词在另一语句中出现,就好像位置移动,但决不影响其含义是同一的,这就是典型的空间语言,这也是数学语言的实质。至于形容词,由于是描述性的(就像白色未必落实到白布,“白”的前景莫测,就像“甜点”可能联想起“甜甜地笑着”),相当于广义上的动词——它们指形态正在发生或进行之中,尚没有完成,它们朝向还没有确定的未来,方向不明,词语的含义在绵延中有待于下一种即将发生的形态加以揭示与描述,这就将语言时间化了,它不是模仿外部事物的语言,而是用语言揭示语言的抽象而复杂的语言自身,它是不断超越某个正在发生着的词语界限的语言、永远在路上处于没有落实状态的语言,显得焦虑、沉迷且流畅。如果以文字书写出来,就是与心思处于平行而有差异的流淌过程之中,这才是事物本身状态即“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绵延),这才叫做“返回一个原样的世界”(尼采语)。
在德里达看来,凝结为观念或者概念的思想一旦在场,就掩盖了它们在场的过程经历了隐喻。也就是说,“被说出来和被想出来的意思并非是其自身的现象……思想其实是落在隐喻上面的。”[3]这就是思想的奇点,问题的关键,原样的思想就是如此不知不觉地悄悄发生着,一旦我们开始正儿八经地坐下来把“思想本身”当成要讨论的对象时,思想就变异为“什么”,虚假的思想就登场亮相了。换一个说法,一切事物的原样状态总是处于流变之中,无聊或无所事事,等于静止不动或“没有被事情所占据”的状态,此刻空有活着的形式而没有活着的内容。这个内容,无论其性质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活着同时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们总归是某种行为,也就是说,正在从事某种行为。
对于德勒兹所谓“做哲学就是去创造概念”的说法,德里达有些不赞同,因为依据他上述的观点,虽然哲学家们确实是在创造概念,也就是说,给事物命名,但是在这些“哲学活动”中真正起作用的实际过程,就是发明和建立某个新的隐喻的过程,也就是在不同的思想要素之间建立起新的相似性:一个词语被另一个词语所取代、一种思想被另一种思想揭示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思想多出点什么同时又少了点什么,就像翻译一样,其可能性是建立在不可能性基础上的,而事实发生的都是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也就是创造行为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在此种情形下,创造就是德里达所谓“解构”(消解原有事物性质的界限与结构,置换或兴起某些新的思想要素,这不是破坏与颠覆,而是思想的原汁原味状态)。“解构”的情形,使思想处于冲动与兴奋状态,它是开放的、不重复的。由于不重复而不乏味,又由于不重复而深刻。尽管我们这里还是在使用“概念”,但概念是在解构的情形下发挥思想作用的。这叫做去伪存真,事物的真相没有躲藏起来。
解构,就是把本体论的或“对象性”的思维模式,转化为思考“关系”,这有点像将某种“垂直方向的逻辑”转化为“横向的逻辑”,而后者总是活跃在异域之中的,其中有隐喻的两个基本特征:建立相似性、类比。“垂直方向的逻辑”是大脑里的、粗线条的,因为它用静止的概念作为思维的工具,给事物贴上某个归纳出来的、具有一般性质的标签,也就是命名及其基础上的逻辑演算;“横向的逻辑”是心灵里的,它灵敏、微妙、纤细,不同意思之间的过渡极其灵活多变,与其说它是纯粹的,不如说是有杂质的。
所谓杂质,就是事物自身隐含着超越自身之外的精神因素,它甚至能解释人的语音与动物的喊叫之间的根本区别、音乐之声与自然声响之间的根本区别,前者隐含着人的精神,并非是后者的简单模仿。从这些凝聚着人类精神创造出来的“声音”出发,又可以衍生出千变万化的多种语言与音乐形式,这就是人类的文明——物质的音响指向某个特殊的方向,它们决不可以是单音节或单声调的,因为正是音节之间的差异、声调之间的差异,构成并传达和转化为不同的意思与品位,而且复数的意思之间形成一气呵成的美丽。在这里,科学与美丽是相似的,当然还同时与别的什么相似,但我宁可说美丽,因为它意味着爱或者感情,后者是人类文明最本质的因素。语言与感情之间是相互唤醒的关系,这又是一种相似性:表面上是陈述或者命名,实质上是唤醒关系。唤醒什么关系呢?唤醒任意一种联想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一定之规,没有“你必须因为你必须”。同样,人类文明又是模仿的文明,没有模仿,语言根本不可能产生,但哲学思考不能止步于模仿,因为藏匿于模仿背后的是寻求相似性,也就是去创造一个新的隐喻。人类的文明并不是返回原原本本的自然状态,而是赋予自然状态以多余的或奢侈的属人的意义(卢梭在《爱弥儿》里也称这种现象是“危险的增补性”,它同时是进步的与堕落的)。
以上也区别了诗意的语言与日常语言:在日常语言的奇点上,原封不动地具有了诗意,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的文字至今还是常用汉字。这叫“化腐朽为神奇”,它极其生动地揭示了语言的隐喻性之实质,是诗意的表达,而这种表达的实质,就是思想的原貌即字词处于流动之中在寻求与之看似并不相识的相似性,这创造出来的相似性使之从陌生到有缘,进而“恋爱生子”有了第三者即新的句子之新的表达形式,但既然是亲生的,彼此之间就有血缘关系即天然的相似性,从而有天然的生动亲切的感情蕴含其中,如此沉醉其中的写作,叫做自然而然。
以上,也暗示我们——其实卢梭、尼采、萨特、德里达等人已经这样写哲学作品了——可以用广义上的诗意语言写哲学思想,所谓走在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似乎踏着这条无形的疆界线上跳着有趣且深刻的舞蹈,这已经是隐喻。当然,还有隐喻的隐喻,因为这条亦此亦彼的无形界线不再是一条想象中的直线,它在绵延过程之中消解掉自身,关于位置的或空间想象变身为时间的想象,如此等等。由于思考“时间”这一哲学领域中最诡异神秘的因素、这天然具有诗意的理性因子,思考中的真理总是在别处、在另一个领域、在异域,不仅男人的真理在女人那里,反之亦然,而且几何学的真理在数学那里,反之亦然,哲学的真理在文学那里,反之亦然……这些例子可以无穷尽地开列下去,可以称它们为隐喻的逻辑、替换的逻辑,它们也是绵延的逻辑,因此置换与被置换的“东西”之间并不类似阴阳或善恶那样的辩证法关系,不是对立统一关系,而是一种任意的应和关系,就像诗人萨尔蒙(他是毕加索的好朋友)说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无论在哪些方面,无论在那里。”[4]
于是,哲学返回了古希腊,哲学智慧的第一要义,重新成为纯粹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它们导致了形态各异的“思想的奇点”),也就是爱,而不是所谓“正确的知识”或者“科学的认识论”。
德里达批判式地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模仿”的学说,亚氏认为艺术作品是对自然界和人的行为的模仿,德里达则把模仿与隐喻连接起来,连接它们的桥梁,是相似性:“快乐,模仿和隐喻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懂得了通过相似性去学习的快乐,认识相同性的快乐。”[5]德里达在这里并不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相似性归结为同一性,而是不仅用隐喻理解相似性,更进一步把隐喻延伸到诗意的思考,思想的艺术,就建立在思想的这个奇点之上。隐喻、奇点、异域,它们都含有不同于自身的意思。也就是说,搁置存在(being)或本体论,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与勒维纳斯的思想有可沟通之处。
隐喻不再将思想的焦点放在事物是什么,“隐喻在生动活泼的目光之中,它在类比而且拖得很长,像是一种横插过来的复兴过程。”[5]隐喻重新给予一个旧叙述以新生命,因为它用“好像”之类词语转换思想的镜头,就像由于有了蒙太奇这样的照片剪接技术,“动起来”的电影取代了静止的照片。电影当然比照片更像是活着的生活与生命,哲学应该是一部关于思想的电影,每个镜头都处于转换过程之中,而且都是思想镜头。
三
上述的替换、交换过程,并不遵循同一性或等价交换的原则,它们会创造剩余价值,它是意识无法控制的,这些无意识并没有导致心思领域的“剥削”,却唤起不由自主的快乐,它不再区分生活与艺术,它使生活本身变成了艺术,亦此亦彼。它告诉我们不要相信演绎逻辑的三段论,因为建立在同一律基础上的推论不够缜密敏锐,没有看出所谓“同一”其实只是相似而已,如果放慢思想的镜头就会看清楚相似复相似,相似何其多,以至于结论不再可能适应大前提,初衷不再可能实现,承诺的实际效果,与所承诺的东西并不相符,这不是道德问题,因为原滋原味的思想过程,就是这样的:相似性不是同一性。这样的新目光可以重新审视一切以往的价值观念,例如所谓人是自私-自爱的,但只要将这种“看透人性之根本”的目光打开,就会惊奇地发现,它只是描述了人的感情就是人的亲自感受。与其说人爱的是自己本身,不如说爱自己行为的后果,即自己创造出来的有别于自身的一切,一个哲学家为自己的作品感到自豪,因为这作品就仿佛是自己的孩子。
可以把思想镜头转换本身,叫做沉醉与幸福,而不是盼望着它实现什么,专注本身就是理想,在这里,思想镜头的转换点,就是思想的奇点,在这个思想的十字路口处,区别了不同的意义。意义是由关注视角的改变而诞生的,相似性中蕴含着意义的差异,例如2+2=4;2×2=4,虽然结论相同(就像一切人都要死),但是在通向4或到达死亡的路途是不同的,这里表现为2+2与2×2的差异,我们把这种差异称为意义,没有比较就没有差异,意义已经意味着差异,也就是建立或创造出某种类比关系。风格或者个性,是“差异”的不同说法,它们都意味着生动活泼、或者说能量与生命力,如果一个婴儿的出生和死亡是同一时刻,那么我们说其意义等于零。当2+2与2×2相互替换时,研究者既可以研究它们之间的同一性(计算的结果都等于4),也可以研究它们的差异性(加法与乘法的本质差别),我们不能说其中某个方向是错的,而只能说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意义。我们务必要注意到,思想视角的转换本身、差异问题,就是时间问题,要注意似乎不同的论域之间有相似性甚至同一性。
综上可知,在哲学或者“爱智慧”传统中,几乎完全忽视了思想是以“替换”或者隐喻的情形发挥作用的,这种作用高度赞赏哲学的诗意化,例如一词多义现象。传统形而上学所提倡的建立在逻辑同一律基础上的“清楚明白”,就像磨平了思想形象与思想姿态,就像磨平了硬币上的花纹头像,就像说“硬币不过是金属”或“人类的语音不过是一种自然声音”,从而无法凸显人的精神文明及其非常复杂的精神风格。我们分析“思想的奇点”,就是凸显思想的曲折复杂,就像一词多义显示了词语自身的折叠和厚度。语言表达的思想韵味和精神品味,都在于它含有自身的秘密,就像你看见的是一张有精神气质的脸,但是你没有能力用语言把“气质”表述得清楚明白,因为语言是僵死的,而气质是生动的。
于是我们说,思想天才绝不仅仅止步于拥有知识,思想天才表现为做思想实验的能力,它包含假设、联想、类比,但这几种情形,都离不开思想或词语的替换与相似性。它们是上天赐予人的礼物,也就是智慧:莎士比亚的戏剧成就,主要在于他以极其富有诗意的语言描写人类的生活,这使他走在文学与哲学之间。爱因斯坦发现了时间的“同时性”是不同时的,这有赖于他做思想实验即提出假设的能力。记忆力对于保存知识是重要的,但记忆力对于天才的贡献,远远没有想象力那样巨大。
自然而然——爱出的智慧——例如爱屋及乌,“屋”与“乌”无甚关系,除了发音相似(尽管这个理解不完全符合该成语的原义,但望文生义也是一种解释,属于自然而然)。同样,汉语中有音谐义近现象,例如“人者仁也”,这又与一词多义现象近似,所有这些似乎得来全不费工夫,但考验人的联想能力,由一点滋生出怎样相似的念头,取决于正在处于联想状态的人的性情和智力潜质,这就形成了风格上的差异。所谓创造性,就是创造出某种不曾有过的精神风格,这才是真正的差异。同样,一词多义现象与隐喻、相似性、类比等现象之间,亦有相似性,变一种说法,思想就会在差异中延伸,会获得新思想,就像把2+2=4变换成2×2=4。同样,与这些词语相似的还有“变形”,变形同时与艺术和科学两个领域里的创新有密切关系,例如诗歌创作领域的象征派、绘画中的印象派、立体派、荒诞派、超现实主义乃至魔幻现实主义等,科学领域里的非欧几何、相对论、拓扑学等。非正常心理也是将人与事件等加以夸大或变形的结果,同性恋则是性心理的异变。
由相似联想到变形,异常心理会导致创造性,它们都与在精神细节上的敏锐与勇敢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通常人们不会那样想,而有能力那样想的人具有才华甚至是一个天才,它在效果上是有趣的,并因有趣而深刻。这里的有趣与深刻,又有在原因上的相似性,即它们都出人意料而又符合事实(无论是科学事实、思想事实,还是心理事实)。
甚至可以这样说,从以上描述与论证的“思想的奇点”及其看似古怪却是各种事实因素的情形(等同于“虽然是意料之外却处于情理之中”)出发,能描绘出一张微观领域里的人类精神地图,它是一幅与地理面貌无关的心理地图,几乎可以涵盖人类精神文明的各个领域,并且以绵延的姿态把这些貌似不同领域里的问题统一起来,实现了理解世界的全新方式。这种创新,并不在于世界的物理形态发生了改变,而是人的精神目光或观察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用一个老概念表达新意思,可以称之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于是,周围环境依旧,但我们的心态却可以从悲观变为乐观。
这种乐观心态首先消解了真理性的语言与虚构语言之间的界限,它首先取决于人类的虚构或假设的能力。它赋予文学艺术以不曾有过的重要价值,这个价值不仅是哲学的,而且是科学技术的,我们只要想想20世纪末世界科技潮流最杰出的引领者乔布斯的那句名言,也是苹果电脑和手机的广告词:“非同凡想!”它与20世纪初让毕加索兴奋不已的那句话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就是本文以上引用过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无论在哪些方面,无论在哪里。”它们确实和文学艺术有关系,但绝对不仅仅是在讲故事,而是将美好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1]MARCEl RAYMOND,From Baudelaire to Surrealism[M].Wittenborn ,1950.360 .
[2]JACQUES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M].Minuit,1972.274;276.
[3]JACQUES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M].Minuit,1972.277.
[4](英)阿瑟·I·米勒,方在庆,伍红梅.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27.
[5]JACQUES DERRIDA,Margesdelaphilosophie[M].Minuit,1972.284;285.
B15
A
1002-3240(2017)03-0016-07
2017-02-16
尚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校:赵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