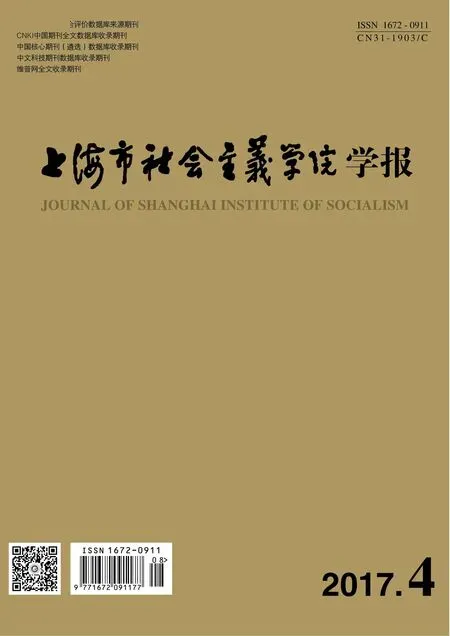作为一种可能:以政党超自主性突破国家自主性
2017-04-11杨英
杨英
(第二军医大学,上海200433)
作为一种可能:以政党超自主性突破国家自主性
杨英
(第二军医大学,上海200433)
如何处理政党自主性与国家自主性的关系?中国政党案例提供了一种本文称之为 “政党超自主性”的路径。长期执政党突破自身特殊利益而形成 “政党超自主性”,它有自然型和建构型两种。建构型政党超自主性可以起到调控国家自主性的作用。政党超自主性相对于国家自主性的优势在于其价值自主性。内容上,政党超自主性体现为对执政党同盟圈层、自身整体及各部分、多数非理性、一国特殊利益等的超越,它在中国政治中起着多重联接作用,但政党超自主性在实现上仍需要规范约束。
政党;政党超自主性;国家自主性;长期执政党;中国政治
一、突破 “国家自主性”吗
1980年,邓小平发出 “执政党之问”:“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执政党之问”发出以后,中国共产党初步开启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征程。到十六大时,十六大报告正式宣布:“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2]但是,转型为 “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以下简称为长期执政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 “政党自主性”和 “国家自主性”关系的问题。革命党转型为长期执政党,意味着行动逻辑的转换,行动要从对现有国家机器的革命和暴动,转变为在现有国家机器条件下行动。而在现有国家机器条件下,政党是有自主性的,同样国家亦有自主性,政党要实现政党目标、实现对国家组织的领导,又要在现有国家机器条件下行动,这就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长期执政党的 “政党自主性”,是突破 “国家自主性”,还是停留在 “国家自主性”之内?本文认为,作为长期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选择的是突破 “国家自主性”的路径,而解决问题所依凭的工具,则是本文所称的 “政党超自主性”。
十八大坚持从严治党,提出了 “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3]的要求。这种政党不依赖其他权力推动而超越自我的行动,突显出了政党自主性。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 “七一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使得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4]。这就又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自主性。相对于目前理论中政党自主性只是独立于外部社会势力的利益、不受外部集团利益控制,却往往被自身利益控制的理论界定而言,摆脱 “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把政党自主性提高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形成了一种内部路径的政党自主性概念。这种政党自主性,以内部的自我克制、自我超越为依皈,本文把它称作 “政党超自主性”。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 “政党超自主性”的提出,具有积极的普世性意义,尤其是对于西方 “政党衰落”的境遇而言。针对西方 “政党衰落”,西方学者提出 “恢复政党自主性”的对策[5],而 “政党超自主性”不啻为更高等的救世方略。
二、目前文献的问题
关于政党自主性,国外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只是在相对于其他组织或者社会环境的框架下,把政党自主性看作是政党制度化的一个指标,探讨政党相对于其他组织或社会的自主性,却忽视了政党作为国家政权的现实掌握者或者潜在掌握者意义上的自主性,因此,大都没有探讨政党自主性是否突破国家自主性的问题。亨廷顿是把自主性作为制度化指标之一的始作俑者[6],但由于他把自主性主要定位成了以社会势力为一方和以政治组织为另一方的两方关系,政治组织的自主性主要是相对于社会势力的独立性、非工具性以及对非政治势力的过滤和同化[7]。政党自主性和国家自主性,都被亨廷顿并入到政治组织自主性的概念中,没有作细致讨论,政党自主性是突破国家自主性还是停留在其内,亦没有讨论。当然,他对政党自主性的讨论是清晰的,如果政党只是某个阶级或者家族的工具,那么它是缺少自主性的。在利益表达上,只表达一个特定集团利益的政党,自主性比同时表达几个集团利益的政党弱[8]。安格鲁·帕尼比昂科 (Angelo Panebianco)也和亨廷顿一样把政党自主性作为政党制度化的一个指标内容,他的政党自主性概念反映的是政党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与环境的交换过程,因此,他主要讨论相对于政党外部环境的自主性[9]。罗伯特·迪克斯 (Robert H.Dix)[10]关于拉美政党自主性的分析,维基·兰道尔和拉斯·斯瓦桑德(Vicky Randall and Lars Svåsand)以结构、态度、内部、外部构成的四格模式[11],以及艾穆·欣朋(Aim Sinpeng)对泰国的分析[12]等文献,也都因循了在制度化之下分析政党自主性的框架。
把自主性作为制度化的一个指标,存在着指标测量上的误用。政党自主性并不必然是政党制度化的内容[13]。如果考虑到自主性的相对方是国家组织的情况,那么现实中既存在着政党受到控制而不自主,但政党制度化水平却很高的情况,简达(Janda)所举的英国工党的案例即是如此[14],也存在作为相对方的国家弱,政党自主性相对较强,而政党制度化水平却较低的情况。把政党自主性作为政党制度化的指标,埋没了政党自主性概念,也造成政党制度化概念的扩大。政党自主性可以反映出影响政党的各种阶级势力、国际压力、自身历史能力等因素,而政党制度化反而可能只是影响政党自主性的多个因素之一,不如让政党制度化概念回归到未被扩大以前的状态,集中地反映政党组织化、官僚化程度、例行程序等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政党制度化概念,是以西方工业民主为背景和原型发展出来的,政党自主性下设其中,被预设了极强的竞争体制背景,不利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分析,也忽视了中国这类具有长期执政党的非竞争体制案例。
国内文献中,董亚炜、程竹汝和上官酒瑞等人对这一问题作出过宝贵的探索。董亚炜把政党代表社会利益的程度看作 “政党自主性”,政党自主性强就意味着 “政党协调和综合社会利益的能力大”[15]。他以政治文明发展路径为依托,认为应当从政党自主性走到国家自主性的路径上。程竹汝和上官酒瑞也支持这一取向,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逻辑中,政党自主性是 “党建国家”模式中的逻辑,这种模式中,政党自主性是国家自主性的前提或者基础,具有优越性,但政党自主性没办法保证政党权力的 “公共性”,因此,需要将政党自主性转换为国家自主性[16]。这种取向中的 “政党自主性”概念,实际上只是政党互动性,受政党过去行为模式的束缚,没有预测到政党自身突破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没有涉及政党自主性的根本问题:是否摆脱了 “自身特殊利益局限”。没有摆脱自身特殊利益局限的政党自主性,总是会体现出各种负面特征。因此他们三位最终都把政党自主性的频谱设定在了负面,并基于负面效果主张将政党自主性转轨为国家自主性。袁峰在政党自主性的视角下集中撰写过四篇论文,对十八大提出的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作了系统的阐述,但对 “政党自主性”是否突破 “国家自主性”问题,没作讨论[17]。
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至少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回应:一个是,似乎目前的研究,均是在相对于外部其他组织、外部环境的某种代表性、独立性或者不受控制上,建立政党自主性概念,最终都滑向是否被控制 (俘获)的问题,没有考虑更为根本的内部路径,即通过摆脱自身的特殊利益而获得政党自主性。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共十六大已经明确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是 “长期执政的党”,它不同于西方竞争体制下短期化、周期性的普通型执政党。长期执政党的政党自主性不仅要求不被其他阶级和利益集团俘获,而且更根本的是要不被自身特殊利益俘获。长期执政党政党自主性的主要含义是对自身特殊利益的超越和摆脱,政党自主性的生成机制并非基于某种独立性即受控或者不受控于外部环境和组织,而是基于自我超越和自律。因此,对中国案例的分析,至少需要以 “长期执政党”为出发点,从政党自主性的内部路径做出考虑。本文即尝试在执政党与国家关系框架下,将政党自主性重心放在内部路径上,以 “长期执政党”为原点,以 “政党超自主性”作为解释工具,对 “政党自主性”突破 “国家自主性”问题作出解释。由于本文是在中国案例情境中进行解释和分析,长期执政党的政党超自主性,也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政党超自主性的指称。
三、解释性建构:政党超自主性
“国家自主性”(autonomy of the state)理论起始点为韦伯式的国家,这种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它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只要这些基本的国家组织存在,它们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18]。国家的基本组织,本文概称为强制-行政组织。国家自主性来自于这些强制-行政组织。而在执政党长期执政即执政党长期领导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国家自主性将被政党自主性吸纳,国家自主性根本上受控于长期执政党的自身特殊利益,国家自主性的实现以及实现程度均取决于长期执政党是否超越自身特殊利益以及超越程度。而政党突破自身特殊利益,也就形成了政党超自主性。执政党一旦长期执政,进入长期执政党状态,“党”与 “国”的二元体系存在着凝合,国家政治发展质量取决于执政党自觉性的高低,国家政治成长进步的空间根本上来自于长期执政党对自身的超越,这本身也意味着执政党必须具有超脱自身特殊利益的性质,因此,政党超自主性也是对长期执政党的考验和要求,它可以作为长期执政党是否执政为民的检验标准。
“政党超自主性”在实现上,以长期执政党的领导意志、组织制度和政治价值为基础,按照经由人民意志上升的政党意志,对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进行整合,但整个过程中不允许贯穿自身特殊利益。长期执政党是相对于竞争性体制意义上的普通执政党或者周期性的短期执政党而言的一种类型。虽然,“在执政的条件下,……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执政党就不能不承当利益协调者的角色,设法调和各方面的利益,鼓励社会各方的合作”[19],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执政党都具有相对于国家的超自主性。在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下,执政党只有追求自身特殊利益才能立身,容易成为各种利益团体的工具,并且由于自身执政的期限性,在历史时间维度上,无法真正抗衡国家自主性,也就摆脱不了在国家自主性之中的命运。
政党超自主性可能出现两种延伸线:一种是,由于在源头上政党不追求自身特殊利益,“国家自主性”自然过继到执政党身上,转换为执政党的政党超自主性,称作自然型的政党超自主性。另一种延伸线,则是长期执政党在超越自身特殊利益的前提下,通过作为领导党的领导意志、政治价值或者组织手段,生产、控制、调节国家自主性,从而形成政党超自主性,这种延伸可以称作建构型的政党超自主性。建构型的政党超自主性,在制度上,通过把作为调控者角色的政党组织与作为国家自主性基础的强制-行政组织联接在一起而实现,这个联接在一起的结构,就是超自主性结构。长期执政党可以通过这个结构调控国家自主性大小。这个结构的出现,改变了国家自主性的要素结构和程度,它可以使某一个限制国家自主性的要素不起作用,因而使国家自主性余地更大、程度更高,也可以使限制国家自主性的要素作用程度更强,使国家自主性程度减弱。
政党超自主性不仅创造能力上的自主性,而且还创造更为根本的价值自主性。政党的价值自主性根本上决定着政党超自主性的质量和能级。政党拥有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而政党价值自主性却可以使政党能力成本降低、能级上升、能量范围扩大。政党能力固然带来自主性的实现,但是政党的价值自主性却根本上决定了政党是不是为国家、为社会提供了相对进步的政治生活和组织方式。长期执政党体制与威权政体的区别正在于此。虽然威权政体也能实现甚至放大国家自主性,基于国家的命令、强制,使整个政治系统良性运转,但政党超自主性中的价值自主性却能创造一套自主的价值,不但驱动政治系统运转,而且还让国家运转执行的效率和自愿程度提高。长期执政党得以突破国家自主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政党除能维护、控制、生产国家自主性之外,还能创造和提供价值自主性,创造更优良的政治生活。
政党超自主性通过价值自主性,彰显出相对于“国家自主性”的优势。国家自主性体系中,国家的治理逻辑是强制,基于强制进行统治,而不是正当性,这意味着国家是不依赖价值共识和大众满意而凭借国家强制力超越社会内部冲突的。“国家自主性”归根结底,实际上只是强制-行政组织的自利性和自我保护性。由于这种自利性和自我保护性,“国家自主性”也可能扮演 “掠夺者”[20]的角色,国家借助各种条件和时机比如国际危机压力,为国家单纯地追求自利而提供便利,使国家无需重视社会大多数人是否支持,无需 “正当性”来提供保护,因为即使丧失社会支持和 “正当性”保护,强制-行政组织依然可以通过强制维持稳定,保持强制组织的存在和有效。这在结果上,往往形成国家自主性的专横。尤其是在具有强国家、弱社会传统的国度,国家自主性一旦专横,就会陷入各种困境[21],甚至带来各种致命后果:国家权力监督缺位;形成不考虑社会利益的政策;对 “被俘获”的危险过度防御,导致国家难以对社会利益主体产生根本信任,加剧社会利益主体与社会环境及国际背景的合谋,甚至操纵国际背景,形成对国家整体上的压力,进而拆解国家自主性。政党超自主性的存在,则可以为这些可能的致命后果,增加安全系数。政党超自主性结构中,长期执政党可以通过政治过程,弥补并提供价值共识或者价值主导,创造出基于价值的政党超自主性,从而,突破国家自主性的专横。
四、内容建构:政党超自主性的体现
中国案例中,长期执政党的政党超自主性在相对于国家的意义上,至少体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超越执政党同盟圈层的利益,不受同盟圈层观念、行为的主导,防止了执政仅为政治同盟利益服务或者利益被垄断于政治同盟内部情况的发生。欧美西方世界的兴起,无论是新教伦理精神为动力,还是私有产权制度为动力,最后都落脚到共同的阶级主体——代表资本力量的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虽然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后,对资产阶层实行了开放,但是,始终坚持了对各个阶层的超越。随后,以人民为本的提出,又进一步强调了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在与 “友党”的关系上,同样也保持了超越性,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法律地位上平等,但在政治上具有充分的政党超自主性,民主党派不能谋求执政利益,但可以在不竞争的条件下参政,共商国是。
第二,超越政党自身整体以及政党各部政治势力的利益,不受政党自身整体以及各部观念、行为的苑囿,不出现利益被垄断于政党自身或者政党某部分的情况。政党政治的出现,把政党前时代的家族政治、寡头政治转换为平民政治,政治因此而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广泛社会基础的同时,把民主引入党内,解决了搞民主的政党终将沦为寡头统治的组织悖论问题,既防止出现民主淹没政党,也防止出现政党侵害民主的情况。通过公务员制度改革,系统地建立了科层制体系,使得公共管理在 “管理科学化”的轨道上运行。在监督和制约弱化因而腐败滋生蔓延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高层通过强化纪律约束、纪律监察,大面积地惩治腐败,严厉打击使用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进行自我服务的既得利益集团,使整个中国共产党重回政党超自主性轨道。
第三,当民众中的大多数出现极端不理性或不能预见战略性方向的时候,能够超越 “多数非理性”,作出理性的、超越狭隘利益并符合人民长期利益的决策。政党超自主性使得中国共产党能以超然的地位,集中力量办大事,能超越眼前利益办长远的事,推进大型、深入的结构性改革。“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政治系统持续的狂热以及惯性,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重新作出理性判断后,被果断地停止。改革开放成为新的潮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当社会民众追逐私利,差距在民众之间逐渐拉大时,中国共产党政党超自主性则显示为对分配的强调,以其执政身份所掌控的公共权力,积极充当利益协调者的角色,加大对收入差距的合理控制。
第四,在相对于世界的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超自主性体现为超越一国特殊利益的政党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政党超自主性还体现为,中国共产党能超越中国执政范围而关怀世界。中国共产党已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在初建时,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世界性组织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本身带有世界政治的特征,既是国内党也有世界党基因。共产党的经典文献 《共产党宣言》颁行伊始就使用了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麦文多国语言通行于世。共产党不仅执政于中国,不仅组织中国国内政策、路线、方针的制定,同时具有对全人类的关怀,也为全人类更美好的生活、更好的制度探索而努力。在共产党的精神导师马克思那里,共产党人本身就担负着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任务。
五、政党超自主性在中国政治中的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超自主性在中国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它可以在整个中国政治体制中承担着多重联接功能。
政党超自主性将暴力的国家垄断和军队的政党指挥,通过政党超自主性而融洽地联接在一起,军队既保持了受政党指挥的社会性质,又保持了为国家服务的国家性质,同时在国家层面,实现了政党与政党领导下的国家对军队的联合垄断。按照马克斯·韦伯的概念,国家是在一定地域上垄断了暴力的合法使用的组织。国家对暴力合法使用的垄断也正是国家自主性的基础。现代国家从根本上讲,也正是凭借这一基础而得以超越领土内社会主体的利益。政党联合参与暴力合法使用的垄断,直接使政党超自主性有了稳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具备了军事功能以后不久[22],就通过 “党指挥枪”和 “支部建在连上”而逐步实现武力中央化垄断,建成国家后,政党武力则转换为政党与国家联合垄断的武力。
政党超自主性帮助中国共产党超越政党特殊利益成为社会党,实现与作为掌控国家机器的执政党身份的分离,通过政党自身身份的分离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分立,政党超自主性则是其中的联接机制,它既鼓励公民社会发展,又建设强大国家。政党超自主性的存在,使政党以自身身份分离的方式,同时运转国家和社会,在国家领域掌控公共权力,在社会领域,以其超越自身特殊利益的优势,而获得社会的拥护和支持。
政党超自主性为平衡治权与民权、建设同向型民主提供支点。列宁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消亡。”[23]中国共产党以其政党超自主性的身份,持续地选择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或者变相的资本主义作为道路,给民主的发展容留了广阔的空间,对民权和治权都给予一定的开放,同时又都有调整,发展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平衡型民主的同向型民主。通过对民权和治权的开放和调整实现同向,而非在治权内部各支系权力之间博取平衡,民权和治权通过共产党的领导而作为连接政治共同体的机制,并由共产党根据环境和时机调节快慢。治权和民权的质量同向提升,而不是一方质量的提升造成另一方质量的下降。偏离同向的各种乱象如民权放肆、治权贪腐最终也都由政党裁决、治理。
六、讨论:政党超自主性的延续和实践
政党超自主性是一种内部路径的自主性,不同于相对于环境的外部自主性理论,但在实现机制上,政党超自主性也需要严格的规范。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组织,其政党超自主性的实现、对自身特殊利益的超越,仅仅靠在精神、信仰、态度上自我超越和自律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严格的党法、党规、纪律,从整体上加以管束。目前的长期执政党还需要向纪律型长期执政党转变。但是,建构型的政党超自主性中,国家自主性的实现取决于长期执政党调控和管理水平这一基本机制不会轻易改变,政党超自主性是国家自主性的终极依托。而无论是自然型还是建构型,政党超自主性本身的实现则取决于内部路径的超越,而非依靠代表程度和相对于环境的独立程度。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超自主性的党,在执政党的意义上,主要擅长在公权力或者公权力可影响的范围内活动,社会尤其是私权、私利是政党的边界。面对私权、私利,按照 “摆脱自身特殊利益局限”的要求,长期执政党的边界可能越来越后移,这种后移可能是被动的即由私人利益扩张的压力而被迫后移,也可能是主动选择的。从目前的发展看,中国共产党主动选择了后移。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行反腐,清除与私人利益勾结的各种腐败势力和机制,并主动从一些利益深水区退出,党领导的军队也被要求主动从有偿服务中退出。这些,显示出长期执政党主动建构政党超自主性的决心。这种主动建构的政党超自主性,也将为改革蓄积势能,使得改革越来越不以结构和秩序为目的,而仅仅将二者作为自变量。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6.
[2]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6.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9.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EB/OL].(2017-05-15).http://news.xinhuanet. 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
[5]斯特凡诺·巴尔托利尼,彼得·梅尔.当代政党面临的挑战//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政党与民主[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63.
[6]Andrey Meleshevich.Party systems in post-Soviet countries: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Baltic States,Russia,and Ukraine[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18.
[7]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19-20.
[8]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20.
[9]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3.
[10]Robert H.Dix.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J].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1992,24(4):488-511.
[11]Vicky Randall,Lars Svåsand.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new democracies[J].Party politics,2002,8(01):5-29.
[12]Aim Sinpeng.Party banning and the impact on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ailand[J].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2014,36(03):442-466.
[13]Steven Levitsky.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eronism:the Concept,the Case and the Case for Unpacking the Concept[J]. Party politics,1998,4(01):77-92.
[14]Kenneth Janda.Political parties:A cross-national survey[M].New York:Free Press;London:Collier Macmillan,1980:19.
[15]董亚炜.论政治文明中制度建设的基本关系:政党自主性与国家自主性[J].晋阳学刊,2004(04):16-19.
[16]程竹汝,上官酒瑞.制度成长与发展逻辑: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政治[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201.
[17]袁峰.自主性与适应性视角下的政党自我革新能力分析[J].理论与改革,2014(04):58-60.
[18]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0.
[19]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第1辑)[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58.
[20]Xiaobo Lu.Booty socialism,bureau-preneurs,and the state in transition:Organizational corruption in China[J].Comparative Politics,2000,32(03):273-294.
[21]黄军甫.国家自主性困境及对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4(12):11-19.
[22]陈霞,杨英.比较-历史-结构:基于中国政党功能的比较政党学新分析框架[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02):5.
[23]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2.
(责任编辑:张迦寓)
10.3969/J.ISSN.1672-0911.2017.04.028
D52
A
1672-0911(2017)04-0028-06
2017-05-25
杨 英 (1980-),男,第二军医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