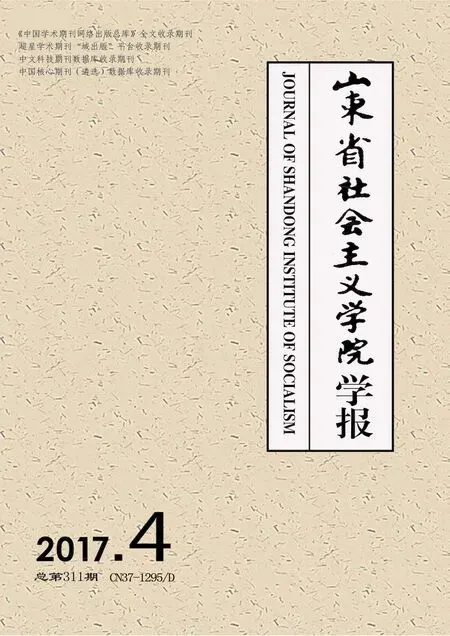人情事理的践履─《论语·颜渊》“四勿”说的意蕴及其在法治时代的意义
2017-04-11董金裕
董金裕
人情事理的践履─《论语·颜渊》“四勿”说的意蕴及其在法治时代的意义
董金裕
前 言
在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地区,我们有机会看到“四勿猴”的图像,即雕刻或绘画四只猴子,其中第一只猴子以两手蒙眼,第二只猴子以两手掩耳,第三只猴子以两手捂嘴,第四只猴子则将两手放在背后或胸前。这种图像在我国部分省市可以看到,如在台北市孔庙“万仞宫墙”旁可以看到,甚至在韩国、日本部分地方也可看到。此外,在一些工艺品店也会有这种图像的制品出售。
“四勿猴”中的“四勿”语出《论语·颜渊》所载孔子与颜渊师生有关于“仁”的一段问答: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语矣!”
可以明白看出所谓“四勿”,指的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因此有人即将此文句浓缩以简称表达,如朱熹在其《斋居感兴》二十首之十三就有“颜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朱子文集·斋居感兴二十首》)之句,而明儒湛若水则有《四勿总箴》,李贽有《四勿说》,清儒顾汝修有《四勿箴》,皆据此名篇。①注释:①另宋儒程颐有《四箴》,包括《视箴》《听箴》《言箴》《动箴》,虽不以“四勿”名篇,但显然是根据《论语·颜渊》此章所载而撰。
从上引《论语·颜渊》的记载,可以看出颜渊所问者为仁,但孔子却以“克己复礼”答之;而在颜渊进一步“请问其目”后,依然认为实行的条目在视、听、言、动等行为的合乎礼;由此可以看出仁与礼关系密切。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四勿”说的意蕴究竟为何?在现今的法治时代又具有什么意义?本文即尝试加以探讨。
“四勿”说的意蕴
根据上举《论语·颜渊》所载孔子、颜渊师生的问答,可见“四勿”说即非礼勿视、听、言、动,而为“克己复礼”的实施条目,故刘宝楠《论语正义》即将“四勿”与“克己复礼”相互联结而释之曰:
盖视、听、言、动,古人皆有礼以制之,若《曲礼》《少仪》《内则》诸篇,及《贾子》《容经》所载,皆是其礼。惟能克己复礼,凡非礼之事所接于吾者,自能有以制吾之目而勿视,制吾之耳而勿听,制吾之口而勿言,制吾之心而勿行,所谓克己复礼者如此。
对照颜渊曾赞叹孔子之道的博大高深,以及孔子对学生的循循善诱时所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论语集注》)则于“博学于文”之后所应注重的“约之以礼”①注释:①朱熹著《论语集注·雍也》:“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朱熹:《论语集注》,见《四书章句集注》,122页)按此章重出于《论语·颜渊》,但无“君子”二字(朱熹:《论语集注》,见《四书章句集注》,189页)。,正是“四勿”说的精神所在。因此要掌握“四勿”说的意蕴必须先对“礼”的含义有所认识。
综合儒家典籍及相关著作的论述,“礼”的含义,可就训诂学上的音训角度,从三方面说明:
第一方面为“礼者,体也。”意指礼必须体察人情。
人有七情六欲,必须深入了解掌握,才能制定合宜的节目仪文,将人情导入正轨,而不致于放滥无度。故《礼记·礼运》曰: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礼记·坊记》也有类似之说,曰:
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穷究人情,知其好恶,而以礼适度规约防范,即可以因势利导,使大家乐于遵循,以避免纵情肆欲而为非作歹,故《淮南子·齐俗训》说:
礼者,体情制文者也。……礼者,体也。
体察人情以制定节目仪文,所制定之节目仪文才不致于窒碍难行,如此节目仪文所寄寓的道理才能于百姓日用中显现,发挥以礼为教而使人心淳厚、风俗美善的功效。
第二方面为“礼者,理也。”意指礼必须合乎事理。
礼有其节目仪文,但节目仪文只是形式,形式背后有其意欲寄托的事理,这才是礼的真正精神所在,也是我们必须掌握的,故《白虎通义》云:
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
为实践道理而形成节目仪文,可见道理乃是制定节目仪文的依据,而为其根本,所以《荀子·乐论》说:
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掌握到根本,不是在节目仪文等枝叶上讲求,才是行礼所必须注重的,因此孔子才会对徒事虚文而不讲求本质的不良风气深致其感慨道: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节目仪文虽然不能没有,但到底是外在的,其作用乃是在于将内在的事理表现出来,故《礼记·仲尼燕居》记载孔子之言曰:
礼也者,理也。……君子无理不动。
合乎事理,节目仪文虽然简陋,依然是礼;不合乎事理,节目仪文尽管繁多,也不够格成为礼。可见事理才是我们行事的准则,也才是礼之成为真正之礼的关键。
第三方面为“礼者,履也。”意指礼必须实际践履。
礼尽管体察而顺应了人情,也合乎处事应循的道理,但如果不实地去做,一切也只是徒托空言。故《说文解字》即将礼解释为履,曰: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荀子·大略》也强调礼之所重乃在于实践,如其不然,则将导致难以收拾的严重后果,云:
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
因此当子张问政于孔子,孔子即一再阐明礼乐之所重乃在于能实际践履,《礼记·仲尼燕居》即记载说:
子张问政。子曰:“师乎!前,吾语女乎!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子张复问。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兴羽籥,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
所谓“举而错之”“言而履之”,其中的“错”(通“措”,施行)、“履”,所指皆为实践,可见礼之所重乃在于能付诸实际的行动。
综合以上三方面的说明,可知礼乃是于体察人情后,根据事理以制定节目仪文,然后透过节目仪文的形式,将所寄托的人情、事理表现出来。“四勿”说既然是以礼为依归,认为我们目之所视、耳之所听、口之所言、身之所行,皆须以礼为规范而遵循之,则其意蕴即在于将人情、事理融合为一,并于日常生活中践履出来,以约束个人的举止行为,使之皆合乎规矩。人而如此,自然可以克己修身,进而于己立己达之外更能立人达人,以形成和谐美善的礼治社会。
“四勿”说在法治时代的意义
当下为法治时代,很多行为皆以合法或不合法作为评断的准则,与“四勿”说所讲求的“以礼为教”并不相同。然而细加探究,就可发现礼、法其实有其相通之处,即两者皆兼具指导及节制的作用,只不过礼的指导作用大而节制作用小,法则刚好相反。
举例而言,“四勿”说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在告诉我们所行所为必须依循于礼,其作用乃偏向于指导。至如孔子所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集注·泰伯》)即明白指出恭、慎、勇、直等美德如果没有礼的约束,将会造成劳、葸、乱、绞等的弊害,此处所指礼的作用即偏向于节制。但一般人之所行所为能否遵循礼的指导,并接受礼的节制而不造成弊害,是无法保证的,即礼实际上是缺乏强制力的。至于法则不然,法固然强调对于人民权益的保障,带有指导意味,但是在民法、刑法当中,却充斥着多如牛毛的各种禁制或处罚的规定,在公权力的介入之下,或剥夺财产权,或剥夺人身自由,甚至剥夺个体生命,即法带有很大的强制性。
正由于礼、法兼具有指导及节制的作用,又各有偏重,则如能相互配合为用,正好可以调剂对方的不足,而发挥补偏救弊的功能。是故以礼为教的“四勿”说在现今的法治时代,仍有其重大的意义,兹就所思分述如下:
(一)防患未然,以起到正本清源之效
前已述及,礼重在指导作用,而因缺乏强制力使其节制作用较弱;法则带有很大的强制性,指导作用虽较不明显,但能充分发挥节制作用。指导偏向主动,重在事前的预为防范;节制则属被动,偏于事后的惩处补救。《汉书·贾谊传》即引贾谊上汉文帝之疏曰:
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司马迁在其《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相同的看法,曰: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一在事前,一在事后,但在事前者因缺乏强制力,而且费时较久,故“所为生难知”“所为禁者难知”,效用难以显现;在事后者则具有很大的强制力,而且可以立竿见影,故“所用易见”“所为用者易见”,成效明显。如纯就效果而论,在事前者确实远远不如在事后者,可是贾谊在其所上之疏又强调说:
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 使民日迁善远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所谓“禁于将然之前”“禁未然之前”“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所指皆为在本源上预作防范,以避免罪恶或祸患的发生。能如此正本清源就不必于事后亡羊补牢,是故《周易.既济》大象曰:
(二)操之在己,具有主动积极精神
在“四勿”说所出的《论语.颜渊》“颜渊问仁”章中,颜渊问仁,孔子以“克己复礼”答之,并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两度提到了“己”,等到颜渊请问其目,孔子即以“四勿”答之,可以推知“四勿”的关键乃在于“己”。是故何晏《论语集解》于“为仁由己”下引孔安国曰:
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则于孔子提出“四勿”之说下引申道:
视、听、言、动,皆在己不在人,故为仁由己,不由人也。
所谓“在己不在人”,即能发自内心,自觉地遵循礼的规范,而非依靠外在力量的制约而勉强为之。既然操之在己,而能发挥主动积极的精神,其效果当然比因被动而不得不然良好许多。故《论语·为政》记载: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礼记·缁衣》也有类似的记载: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
出于主动而乐意为之,自然能“有耻且格”“有格心”;迫于被动而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做,势必“免而无耻”“有遯心”。是故贾谊于上汉文帝之疏中总结道:
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至也。
操之于己,能自动自发,与操之在人,不得已而为之,效果迥异。可见以礼为教自有其使民日迁于善而不自知,驯至发挥移风易俗的莫大功用,应为我们所格外重视。
结 语
孔子的中心思想为仁,故《论语》所载师生之间以仁问答者为多,惟仁为众德的总称,难以具体指言之,故孔子皆以实际操作告晓弟子。颜渊问仁,孔子以“克己复礼”答之,而又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作为实际操作。按孔子曾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集注·八佾》)可见礼虽以仁为根本,但礼为仁的实际运用,不依赖礼就无法显现仁的精神,可见仁、礼关系之密切。
“四勿”说既然以礼作为视、听、言、动的准则,而礼则必须体察人情,合乎事理,并实际践履,此礼之名义即为“四勿”说的内涵。然而礼虽然有其指导作用,但其节制作用却因缺乏强制力而难以充分发挥。相对于礼,法的指导作用虽然较弱,却有很大的强制性,因而可以完全展现其节制作用。彼此各有所长,而亦有其所不足,正好可以互补,以发挥交相为用的功效。
现代社会仅仅凭借礼教以维持安定和谐,事实上已犹如缘木求鱼般困难,所以必须日益依靠法令的制约来保有一定的秩序,是以现代的国家无一不步上法治之途。尽管如此,“四勿”说的以礼为教,由于具有防患于未然、操之于自己的特性,在现代的法治社会中,依然可以与法治相辅相成而发挥其作用。《礼记·乐记》尝谓:
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周易·系辞传》下第五章说:“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中庸》第三十章也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与法之道虽未必尽同,却可以相互为谋,而起集功广益之效。以此用来说明“四勿”说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仍然饶具值得我们重视的意义,可谓确当。
董金裕,男,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孔孟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致力于儒学、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