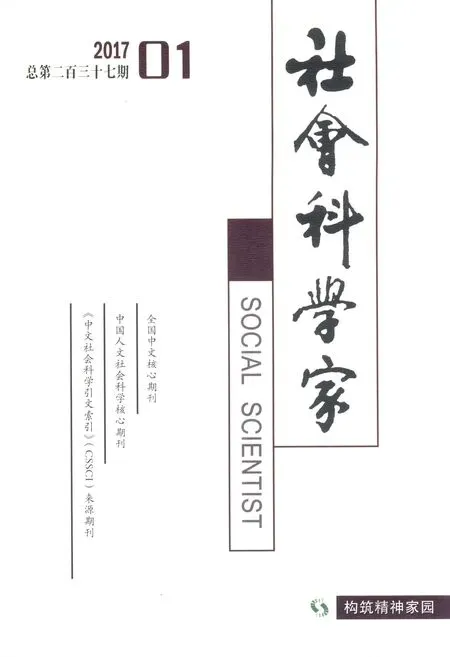预立临终医疗指示正当性的儒佛道诠释
2017-04-10李大平
左 伟, 李大平
(1.广东医科大学 生命文化研究院,广东 东莞 523808;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732)
预立临终医疗指示正当性的儒佛道诠释
左 伟1,2, 李大平1
(1.广东医科大学 生命文化研究院,广东 东莞 523808;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732)
佛教的轮回生死观可以减少人对死亡恐惧,净化临终者的心念提升觉性,通过佛教临终助念帮助临终者度过临终恐惧。道教的生死自然生死观让人明白生死是自然变化,以坦然的态度,忘掉死生复返自然,以生死智慧的领悟,转换成濒死经验中的正向成就感。儒家用“成仁取义”,来说明人生最高的价值,死亡如因为要尽力达到这个目标,同家人一起合理安排死亡,通过一套较为繁复的丧葬仪式,达到对逝者的心灵上的抚慰作用。
临终;死亡;预立临终医疗指示;正当性
预立临终医疗指示是指个人在具有清醒意识及决定能力时为其将来可能失去决定能力时的医疗目标和手段提前做出规划,其重点在于预立人通过与家属及医生充分的沟通,来确立当预立人处于临终状态时是否实施心肺复苏术,其目的是鼓励放弃不必要的心肺复苏。其包括治疗预嘱与设立永久性的医疗代理权两种形式,由末期病人及判断、自愿、医疗代理人、放弃心肺复苏的临床策略等几个主要制度构成。落实推动预立临终医疗指示需个人拥有动机在死亡时间来临之前去面对死亡的问题。但一般人仍缺乏事先预作预立临终医疗指示的观念和动机,缺乏对于预立临终医疗指示本身所具有的尊重人的自决权的价值的理解和重视,对如何为自己作好一项有效且可行的预立临终医疗指示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有所不足,所以在推动上仍有许多的困难与阻碍。有关这方面的观念的加强则有待透过落实生命教育来作积极的推动。本文从儒佛道①生死学一词英文为Thanatology,源自希腊神话死神Thanatos的名字。于1903年由法国生物学家Elie Metchnikoff所创,1912年传入美国。其探索的核心课题,若以精神医学暨生死学专家库布勒·罗斯的语辞来说,就是生命,成长的最后阶段。而生死学的出现乃是因为当时美国的行为科学家发现多数的美国人无法正视死亡,平和善终,便起而提倡死亡觉醒运动,该运动适时地与兴起于英国的临终关怀运动相互呼应,于是开展出生死学的主要内涵:死亡教育、临终关怀、悲伤辅导等。六十年代以后经由死亡教育发扬光大。参见钮则诚.生命伦理学[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2000(3).99.的视角来分析预立临终医疗指示的正当性,以期深化大家对预立临终医疗指示的认识。
一、预立临终医疗指示佛教诠释
(一)佛教轮回生死观
佛教认为死亡不足惧,死是轮回的开始,也是解脱的来临,完全看个人是否能够彻底放下而定。圣严法师曾说过:“心迷则生死轮回,心悟则涅盘解脱,生死是一如的。”[1]迷就是轮回、轮转不断,悟则能够智慧开展,如实见诸法的实相,而可以解脱生死。
佛教最关注人的有情生命,致力于消解身体生老病死现象下的种种痛苦,体会到存有的苦迫纷乱与生死流转,都是身心五蕴和合下的我见与执着,佛陀的证道与弘扬佛法,是要教导人们广观一切法空的生命本质,领悟解脱生死的真慧,进而能不断地反观自身,从离我知见中去完成生命的存有价值。[2]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佛教始终是致力于人的生命体验与生死关怀,是要指引人们洞察生命的本质与彻悟人生实相。虽然佛教的法门层出不穷,但是超越出无常生命的愿望是一致的,最终还是期待能超生了死,熄灭一切烦恼与痛苦,在精进修行中如实认识生命的奥秘,证得涅盘境界。
佛教生死观简单讲就是要渗透“生老病死”四个字,依佛教十二因缘法,人之所以会“老病死”,却是由“生”而来。生是不必喜悦的,象征的是痛苦的源头,在四大与五蕴合成肉身后,就要不断地承受三毒的缠缚与八苦的煎熬,处在剎那不断的迁流变化中,开启了苦海无边的人生历程。但是佛教认为人身的生也是难得的,要有累世修持的善报,利用此身来修行离苦得乐,在戒定慧的精进修持下,能除灭生死种子,证得解脱涅盘。
佛教以“诸行无常”来把握这个变化的实相,从宇宙观来说,就是“成住坏空”,也就是由一个世界成立、变化、崩坏,再至下一个的成立。从人生观论之,“生老病死”四苦,是指生来活着的痛苦、衰老的痛苦、患病的痛苦、死亡的痛苦,这一流转谁也无法逃避。在四苦之中,尤其是“生者必死”这个死的问题,正是自古以来一切宗教和哲学产生的原因。[3]
佛教认为人的一生就是习佛的道场,因此,活过这样的人生自有其尊贵意义,死是实现转生净土的途径,并不是空虚的,所以佛告示我们,除了现实世界,还有一个不管生死都存感激的世界。因此面对老、死、病的现实,人类要克服自我对死亡的恐惧感。
佛教对老死的关怀认为不管医生如何的高明,人们终究还是要坦然地面对老死的生命现象。佛教教导人们不要贪恋此身与此生,生命的成长过程中老与死是无法逃避的,不必贪生怕死,恐慌老迈与死亡的到来。佛教不害怕死亡,害怕的是受业力束缚的生死流转,不断的轮回中不得解脱。佛教要求人们要以此身来精进修行,彻悟人生本相,能熄灭一切烦恼,不怕老之将至。
人老了更需要生命精进修行,以体证佛法来面对老死与处理老死。首先要能放下,体念到一生的功名富贵等是不实在的过眼烟云,要重视的是自己的真心佛性,色身虽然逐渐地衰败,但是慧命可以不断地厚植与增长,更能展现出生命的存有智慧。[4]
佛教认为人的生命不限于一生,此生死后,还有来生,如此循环不已,不能从生死圈中解脱出来,成为人生一大苦恼,要想从中获得解脱,只有通过修炼,断绝情欲,归依佛门,使自己灵魂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不再投生,进入永恒安寂的涅盘世。这种生死观,通称“无生观”即以绝死亡的根源,灵魂不再转生,而以彼岸的涅盘世界为人生的归宿,它具有浓厚的出世色彩。佛教又认为人死后,灵魂就会脱离现有的躯体而与另一个躯体结合,重度另
一段生命的轮回。然而,今生的作为已为来生的命运预立了基础,所以人应当正视今生,努力行善,以求得来生的福报。不过,生命的轮回终非究竟。因为一切存在本是因缘和合而生,如梦幻泡影,剎那生灭。人若能了悟实相,就能解脱轮回的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喜乐,也就是证得涅盘净土。
佛教不追求生死,也不反对生死,而是要以有形的生命去证悟无限的生命,重点在于了生脱死,以修持来化解人的无明愚痴,熄灭一切烦恼与生死诸苦,得以真正洞察生命的本质,在缘起性空的体证下,不以色身为真实的我,更要求不以色身造种种生死之业,只求以善行来圆满生命,在涅盘的证悟中放任色身自然死,顺应世间一切,有为法的生住异灭。
(二)佛教在预立临终医疗指示的运用
佛教的临终关怀,是要让亡者与生者都能超越死亡而两相安;临终陪伴是相互感情交流,更要增进彼此的生死悟境,能相互增进对生命真谛的体验,双方都要能坦然地面对死亡,共同追求宁静的善终。佛教有一套完整的临终仪式与丧葬仪式,引领生者能陪伴亡者与护持亡者,在仪式的操作过程下能了脱生死。佛教传授的是全生教育,不抗拒疾病的疼痛,也不躲避死亡的到来,死亡只是早到或晚到的差别而己,虽然会有些感情上的不舍,但是不必恐惧与焦虑,死亡只是生命的更新,要能坦然放下,应在意的是自我修持力的解脱,若未证悟,乘愿来世再修行。这样的观念,可以让人们平安地面对临终而善终。死亡对修行者来说,也是一场悟境。[5]佛教在预立临终医疗指示的发挥以下作用:
1.积极学习正法以减少死亡恐惧。死亡恐惧是临终病人最常见的心灵课题,临终前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将死亡视为失去、分离与无望,因而增加更多的不舍与恐惧。由佛法“分段生死”的概念观之,人死去的只是这个四大假合的身体躯壳,恒常自性是常存不灭的,若能觉悟世间如梦幻泡影,并进一步将生命的长度上下延伸,相信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因果轮转,即使生命结束了,我们仍然继续的来来去去,生生死死。那么这一生的死亡只是下一生的另一个开始,对于死亡便不会心生恐惧。在面对死亡的过程中,以学习成长的心境面对生死,将有效缓解身心痛苦与处理死亡恐惧,体悟超越死亡的智慧而得到善终。
2.“四无量心”的修习净化临终者的心念提升觉性。教导临终病人修习“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将自己的苦、乐、得、失,均与无量的众生分享,愿所有众生都能离苦(悲心)得乐(慈心),对一切众生生起喜悦的心(喜心),并采取无憎、无爱平等中立的态(舍心)。有了这样的发愿及意念,往往可以产生无限的力量而克服痛苦,发散出无限的喜乐而获得心灵上的最大平安。
3.鼓励专业人员或陪伴者以慈悲的态度来关怀临终者。帮助临终病人及家属在面对死亡的过程中学习成长,并对死亡的过程做出合理规划,从而得到善终,让生死两相安,是医疗团队最重要且最终极的任务。专业人员若能学习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态度与精神来关怀病人,则将散发出无限的力量,而让临终者无畏无惧。
4.临终助念是最佳的悲伤辅导。根据佛经描述,临终的那一刻,亡者呼吸心脏虽然停止,但是亡者的意识感受仍然很清晰,仍可清楚地听到亲人悲泣及看到围绕在身边的亲友。由于内心充满着恐慌与害怕。如果家属在一旁哭哭啼啼,将使亡者心中留恋不舍,而产生极大的痛苦。此时若移动他,也可能让他因疼痛而心生瞋恨,而影响到他的未来归去。当病人出现濒死症状,进入弥留状态到往生期间,除持续提供对临终者种种的照顾与协助外,这段时间应尽可能保持亡者的平静,临终说法与助念不仅能抒解往生者的恐惧不安,对家属身心抚慰也有极大效益。尤其当助念后,若往生者表现瑞相,对家属而言是莫大的安慰与鼓励,更大幅减低丧亲后的悲伤反应,是最佳的悲伤辅导。[6]
二、预立临终医疗指示的道教诠释
(一)道教的生死自然生死观
生命问题的思考是庄子哲学思想的重心之一,他把人的生命安置在广大的天地中,提升了人的精神境界,而其生死观与他追求生命的解脱逍遥有极大的关系,可以说已经超脱了老子的思想层次。庄子勘透生死是有其理论基础的,他对生命原质的探索,采用一气之聚散离合,做为立论的基本原理,认为生命如同四季递嬗,都只是道的往复循环不同形式的展现,既然如此,面对死生,当然可以坦然,只要明白“吾身非吾有”的事实,就能明白生死亦应随顺自然变化的道理了。他又提出“物化”的想法,以为人死后就是转化为另一物,而与物融化了。此外,庄子奉劝世人,对万物的变化,要保持观照的态度,只要能够随顺变化且安于所化,不执迷于现实情状,那么就可以得解脱了。
基本上,中国的道家大师多能体悟生死之理,生者由无而生,死者由有化无。生死俱在变化之中,犹昼暮而夜至,春去而夏来,是非常自然而然的。所不同者,庄子勘透生死有较为多面向的理论基础,由“气化流布”、“物化转换”到“观化自得”,可以勾勒出其生死观的轮廓。“气化流布”透视生命衍化的普遍原理,以人气的聚散离合,为死生终始现象的形上原理。“物化转换”以“气化”之理落实到生命个别之存在,解释死生现象实为一种“物化”,至于“化自得”则是超脱生死的最高境界。
此外,庄子的澈悟生死亦有其特殊的修证途径,他教人从“丧我”着手,断绝向外的感官,然后与向内的心灵连系,由“虚”而冥合于道,就是“心斋”,再由忘掉身外之物与“堕肢体”、“黜聪明”的“去知”,以回归虚灵之心,也就是“坐忘”的修持工夫。庄子进一步说明人们悦生恶死的荒谬所在,为的是教懂人们如何培养安生忘死的齐一胸襟。庄子认为人对物“有待”,就不会自由,想要不囿于物,就必须“无待”,才能让这颗“心”真正的逍遥自在者,庄子的澈悟生死也有一套修证途径,他教人保有虚静之本心,忘掉一切身外之物,要求个体生命的超越,且站在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死亡,如此则生不足以喜,死亦不足以悲,最后提出了逍遥自在的最高境界。
庄子的生死观十分着重心灵问题的探讨,对人心有十分深刻的体认。他认为当喜怒哀乐欲忧悲惊怖等心理状态交替于心,人的生命即走向死亡。然而生命既然是自然之造化,就该寻找一个生死皆善的解脱之道。
(二)道教在预立临终医疗指示的运用
庄子提出的终极关怀是一心向道的坚持。道即是终极者,道终结了一切,一切以道为最终的依归。道做为存有自身,意即为一切存有之基础与根源。庄子透过生命个体和宇宙整体的统合,让人从知道、体道、守道、行道以至最后“合于道”的历程,实现生命的终极关怀。
庄子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形成独特的生死观,他认为生死是生命中的自然现象,人不该被现象困扰,而应回归不生不死、无始无终的生命本质,也就是"道"之中,才能开显生命个体的终极真实,如此,生命的终极不但不是常人所谓的“死亡”,反而引向生命的永恒与无限之中。庄子认为大家过度地看重与爱护生命,才导致恐惧死亡的到来。他认为人的生死与物的成毁是一样的,都是自然的变化现象,唯因分别看待,才会衍生出好恶之情,如果将生死视为一个整体,明白“万物皆出于机,入于机”的道理,对于死亡的恐惧就可大为冲淡了。体认到死亡乃人生的自然阶段,生前之负担至此卸免,一切忧劳从此摆脱,就可以视死如归了,乃至,其乐可以忘死!
人恐惧死亡,对于疾病与死亡夹杂着太多的爱恨交集,产生不少怨恨与哀伤,不能理解生命的本质,一味地只想延长寿命与逃避死亡。预立临终医疗指示是要回归到自然的本性之中,若有夭折也是自然的无常现象,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不能以豁达的心胸来对待疾病与对待死亡。如果能领悟到人的生死,有如花开花谢一般,是人们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每个人都会面临着如花般的凋落,只是早谢与晚谢的差别而已。
道家思想有助于预立临终医疗指示说明自然死亡的观念,让现代人们理解医护的职责不是单纯治愈疾病,或延长病人的生命,更要重视的是缓解症状的预立临终医疗指示,在停止维生治疗下自然死亡。人是自然而生,也该自然而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现代医学却让每个人都是病死的,被视为末期病患,在一些插管的陪伴下受苦而亡,根本无法享受寿终正寝的宁静与安详。任何生命都难逃死亡的宿命,医学再如何发达都无法改变有限生命消逝的事实,人们应该保留着自然而死的权利,即年老体衰死于安乐的权益。但是近代伴随着科学发展而成的医疗体系,结束了人类自然死亡的时代,人们丧失了断气以前的自主权,以技术死亡取代了自然死亡。
道家重生而不贪生与长生而不恶死的思想,以坦然的态度,忘掉死生复返自然,即“两忘而化其道”,视死生有如“夜旦之常”的天理运行,不要加入过多的哀乐情绪来欣生恶死,应当回归自然的常道,体会到生死都是自然的结果,认为人不必悦生,生是劳累的开始,人也不必恶死,死是安息的终点,这一切都是自然之化与当然之变。道家思想对人性的关怀是历久弥新的,灵性也包含在人的身心里面,肯定人的生命是可以与宇宙的自然规律,是可以用来化解现代人的各种生存压力,运用在预立临终医疗指示上,可以达到提高临终者及其眷属生活质量的目的,获得生死两安的和谐境界。道家思想渗入到当代的照顾理念之中,发展出具体可行的态度与方法,以生死智慧的领悟,转换成濒死经验中的正向成就感。如此人性化的善终服务,有助于临终者安然度过余生,也能延伸对其家属的心灵照顾。[7]
三、预立临终医疗指示正当性的儒家诠释
(一)儒家凛然大意生死观
1.儒家认为生与死都是自然规律,应当坦然面对
儒家系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其对于生死观之探讨自当影响后世人们巨深。儒家生死观系如何影响着现代人们于生于死的看法,视死为生的另一种形式,加以消解生死之间的距离,帮助人们从死亡的阴影中跳脱出来,在观念上了解死亡的价值,进一步达到透彻生命意义之本质。是故,死亡并非是可怕的,仅是一种宇宙天地幻化的过程,人们须要去了解死亡之意义,但无须担忧,而应系更以死作为生之动力,在人肉体上有限的期间内,去追求知识真理,使己身所言所行依循着道义,从而接近天地大道,进而追寻生命之最终价值目的。
《论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曰“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论语·阳货》),这些都揭示和说明了时间流逝不可逆转,人的生命也是一个由生到死的自然过程。“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之道”。儒家这种“安死顺命”的态度有助于消解世人死的恐惧。
2.儒家肯定生命的可贵,尊重生命,同时又对死持一种凛然大意的态度,追求死亡意义的伟大性
儒家用“成仁取义”,来说明人生最高的价值,死亡如因为要尽力达到这个目标,即使是不幸失败丧生,亦可问心无愧,这即是死有重于泰山。在孔子看来,人生所作所为要符合“仁”的原则,关心的是能否完成自己生命历程上道德使命,贯彻天命、践行仁道、天道,死而后矣。至于自我的死后命运如何,孔子认为只要在生的时候活出自己的意义与价值,就可穷尽生命的道理,也就彰显出死的意义了。因此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矣”。
为了实现“仁”的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种将死仁义的标准之下,成了儒家对于生死议题的理论根基。倘若生死决断的标准在于“成仁”,那么不排除以死取代生,而成就不朽之生命。《孟子·告子》篇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儒家主张道德为先、精神生命为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为道德而牺牲生命,其形体虽亡,但精神深植人心而与他人性命同存,因此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永存。这便是所谓“三不朽”的立功、立德、立言,通过三不朽的建立,达到生死如一的不朽永生境界。[8]
人在世上是群聚生活的,是会面临人与君臣、父母、师长、兄弟姊妹、子女、朋友,甚至与自己的种种关系,儒家思想往往就是在描绘如何正确面对这些关系,规范人应有之伦理道德行为与态度,不管对方是在生前还是死后。虽然每个都会被注定面临死亡,不管你能活多久,仍旧必须积极地完成上天赋予我们道德实践之使命,也藉由仁义道德之实践来阐扬上天所不能言之真理,进而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这也是儒家认为人存在之终极价值所在。
(二)儒家思维在预立临终医疗指示的运用
1.预立临终医疗指示尊重生命的自然轨迹,并提出同家人一起合理安排死亡过程,符合儒家的“安死顺命”的思想[8]
病人临终,常有诸多遗憾,或是心愿末了,或是亲人未遇。在陪伴时,如果帮他们透彻了解忠恕的真正意义,可以协助得到心灵的平静,忠虽言是尽己之力,但是外在因素复杂,并非每件事情都能圆满。透过生命回顾,协助当事者了解,世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尽心尽力即可问心无愧。如用传统“天地君亲师”的观点,使病人了解,居首的“天”,可以思考为不同的机遇和运气,事情的成败,不足以论断个人的价值,由此出发,不但可以容忍自己的挫败,也可以宽待别人的过错。念头的转变,于病人心灵平安的获得,常有其惊人的效果。
此外,儒家谈“恕”道,是现代社会中的一帖清净剂。病人或家属中的心结,在面临生死的关头时,如果经由医疗团队的协助和启发,使其可以推己及人,练习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对于心中的恩怨情仇,会有释怀的效果。
儒家的对待死亡态度是:生时不多睡,死后可长眠。生前无论是学习、从政、侍奉父母、操持家务、交友、务农等等,都需奋力而为,不可有喘息怠惰观望的念头。那高如堤岩的墓,才是人真正的安息之地。人生活中努力的艰辛劳累,才能反衬出人死后静息的价值。此时,人们不仅以生为幸福,亦能享受死的如释重负。
2.儒家死亡礼仪也使预立临终医疗指示有了心灵慰藉
儒家讲求礼仪,有一套较为繁复的丧葬仪式,包括死后逝者放置的方位,依亲疏不同而有轻重不一之丧服,食用的东西,说话的内容和方式,祭纪的时机和方法都有一定的规范。这些规矩,在现在的眼光来看,固然有不合时宜,但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其潜在的作用在于透过时间及仪式,进行生者的哀伤辅导,其在心灵上的抚慰作用,可能不亚于当代之心理谘商。国人现较流行之民间宗教仪式,以及和佛教观念融合的七七作法,也有类似的功能。对于逝者之至亲,有一段适宜的时间,可以暂时远离世俗的繁琐,自我沉淀,透过对亡者的迫念,开拓出自己以后的一条路,未尝不是好事。
由于儒家讲究人和人之关系,不论是病人和家属,在进行灵性陪伴时,可以就其过去行为中,择其善者而予以阐扬,让病患了解自己在求仁方面也尽了力,让家属知道病人也有些原先不为人知的长处和善举。[7]
神学家Paul Tillich所提出“终极关怀”理论,使世俗的自主与宗教精神联系起来,Paul Tillich的“终极关怀”就宗教或信仰的界定,是指以上帝之上(意即超越一切存在的客体或对象)的神为信仰的对象。“终极关怀”涵示个人为了参与存有的行动,例如为了求取永生之道,他就必须竭尽所能地投注个人所有的一切,也就是应以无限的注意力、无条件的皈依,义无反顾地去关切与投入周围的人事。田立克将终极关怀与信仰划上了等号。生死的问题似乎只有讨论到宗教这里,才能给予终极的答案。
[1]郑志明.佛教生死学[M].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1-7.
[2]郑晓江.宗教生死书[M].台北:华成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44.
[3]吕应钟.生死学导论[M].台北:新文京出版开发公司,2007:52-55.
[4]星云法师.实用佛教[M].台北:佛光文化公司,1999:167.
[5]洪启嵩.全生教育[M].台北:时时文化出版公司,1996:223.
[7]台湾安宁缓和医学学会编.安宁缓和医疗[M]:理论与实务.台北:新文京出版开发公司,2007:332-333.
[8]郑志明.道教生死学[M].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49-73.
[9]曾竞.从儒家生死观看临终医疗预嘱的正当性[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3.2(43):255-257.
D912.1;R197.1
A
1002-3240(2017)01-0122-05
2016-12-11
本论文是2016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预立医疗指示制度研究》(GD15CSH04)、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预立临终医疗指示制度研究》(15YJAZH030)和2014年广东医科大学科研基金《先秦道家生命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研究》(Z20140)的共同研究成果。
左伟(1978-),河南信阳人,广东医科大学生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医学哲学;李大平(1970-),广东医科大学生命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生命伦理、生命法学的研究。
[责任编校:周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