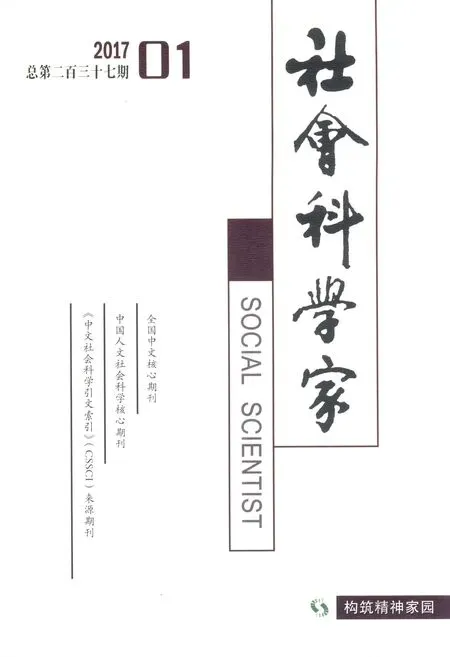物、人、需求
——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三位一体的批判
2017-04-10李恩来
李恩来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物、人、需求
——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三位一体的批判
李恩来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鲍德里亚指认现代社会已经由生产社会步入到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消费活动是不同于生产社会的,其消费目的由使用价值消费转向符号价值消费。这一消费转向并没有使得人在符号消费活动中完成人的价值实现,相反却被大量符号消费所异化。鲍德里亚将消费活动中的主体、客体以及联结主客体的需求关系都纳入到符号的秩序之中,并且将它们予以符号化,从而构建了三位一体的符号消费批判理论,本文旨在对他的这一理论作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并由此展示当下消费社会的景观,即无法终结的消费异化既是现代消费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的生存危机。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符号消费;批判
现代社会已经由生产社会步入到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本身的逻辑已通过各种现象强有力地显现出来。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正是对这一逻辑的哲学考察与批判。鲍德里亚认识到,在消费社会里人们有了消费的选择空间,消费者地位上升,并因此带来重要的社会变化和社会关系重构,他以锐利的观察力和反思精神看到了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活动和消费文化的深刻社会意义:一旦人们穿透整个消费活动的表象,即置身符码体系操纵之下的自我管控行为,就能够进一步意识到整个这一体系的威力何在。简而言之,他将消费活动中的主体、客体以及联结主客体的需求关系都纳入到符号的秩序之中,并且将它们予以符号化,从而构建了三位一体的符号消费批判理论,指出了消费社会带来的不只是经济形态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而符号对人的控制,恰恰是现代人的生存危机。
一、消费对象批判——消费异化中物的功能性区分
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消费活动是不同于生产社会的,其消费 活动多是基于对物的非功能性的欲求,其本质在于通过贬低物的使用价值以高扬物的符号价值,物被视为一种占有差异活动的对象符号化的先在条件。对物的功能性与非功能性区分,是鲍德里亚论述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逻辑前提。早在《物体系》一书,他就指出物的本体论结构中存在两个意义层次,其一是客观本义,其二是引申意义。前者是本质的,后者是非本质的,“透过后者,物品被心理能量所投注、被商业化、个性化、进入使用,也进入了文化体系”。进入《消费社会》的写作时期,他将客观本义与引申意义更为现实地表述为功能性与非功能性。功能性即能够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使用价值,非功能性则是在物质需要的范畴以外,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非使用价值,它是人们的一种期待,“或一种主体意志的发挥”[2]。
根据对物的功能性与非功能性区分,在消费层面就出现了功能消费与非功能消费的对立。物的符号性正是由物的非功能性层面衍伸出来。据此而论,这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非使用价值即是符号价值,任何非功能消费即是符号消费。我们可以注意到,当前社会的大多数消费现象其本质均已由对物的使用价值的消费过渡到对符号价值的消费上来。我们这个社会从消费活动的整体来看,已经是符号消费的时代了。
在消费社会里,被消费的对象只有在成为符号时,它才可以被消费。因此物品符号化是其被消费的一个前提。但这并不等于是说人们在消费活动中,消费对象即是符号化了的物品。因为物品成为符号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个体的符号-物并不能体现它自身的符号价值。它不是自足的。它需要在与其他符号-物的比较间被赋予差异、凸显价值,这个被赋予以及凸显出来的差异与价值方是它的全部意义。进而言之,意义唯有在不同的符号-物的等级关系里才能确立。鲍德里亚之所以说:“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就是因为关系的构建实现了价值的凸显,而这才是消费社会中人们需求的先在着眼点。“正是在对物品使用价值(及与之相联的某些“需求”)进行贬低的基础上,才能把物品当作区分要素、当作符号来开发——而符号是对消费作了特别规定的唯一层次。[1]”但更为现实的情况是:符号消费不只贬低了实用性价值,更是将物品的客观本义彻底废黜,物品由此成为一种根本无用的“摆设”。“再也没有比这更有用的了,再也没有比这更没有用的了。”[1]
同资产阶级对交换价值的掩盖相比,消费社会的消费叙事话语对符号价值的高扬反倒是一种更为强制也更为隐蔽的行为。如果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揭开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隐秘,那么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正是力图对符号价值的暴力假面去魅:“在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深刻等级化了的物品面前没有丝毫平等可言”[1]。因为在非功能消费层面,社会个体更为不知所措,更加不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这也毋庸置疑地为商家(广义)构建一个符码操控网络提供了便利。消费主体虽然不知道他们需求的所指与程度,但在一个被构建的符号体系中掺入的攀比策略,就使他们永远遗忘了具体的真实消费而完全投身到盲目的符号意义竞赛之中。
二、需求关系批判——消费异化中的驯化关系
鲍德里亚在写作《消费社会》时,“关注的不再是《物体系》中物品本体论式的功能结构了,而是对存在于消费关系中的一种新的被塑性奴役的指认。[1]”其实在《物体系》的结论部分,鲍德里亚已经初步谈到了消费问题:他明确指出只有在消费中,物品的本体论才能得到它们的真正实现。消费作为一种消费主体对消费对象的需求关系,不仅指涉了人与物,还指涉了人与人,并且只有后者才更为根本地定义了消费的实质。在符号消费的语境中,物品不是自足的,或者说仅当它成为符号本身时,毫无意义。恰恰是在符号-物与符号-物的比较之间,差异才显示出来,价值也由此被确立。根据物品凸显意义的等级逻辑,真正实现符号消费的前提是一种关系构建,以及一个体系的确立。所以,单个的消费需求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个符号消费的价值体系。
而这种需求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在消费中被建构起来的驯化关系。“我们不清楚,目前,这种有组织的、系统性的消费驯化,在多大程度上是整个19世纪对农业人口进行的面向工业劳动的大驯化在20世纪的对等和延伸。19世纪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那个生产力合理化进程在20世纪的消费领域中得到完成。工业体系已经对大众进行了社会化并使他们成为生产力,这一体系可能还会走得更远,直到实现自我完善,并对大众进行社会化(也就是说控制),使他们成为消费力。[1]”鲍德里亚的这段话是用资本主义在工业化时期对生产的驯化从而使大众成为生产力来比喻消费社会里资本主义对消费的驯化从而使大众成为消费力。而一旦大众成为消费力也就表明消费驯化在社会整体的意义上得以实施。
那么,这种有组织的、系统性的消费驯化是何以形成的呢,鲍德里亚认为这是与消费社会所出现两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分不开的:
第一个变化是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以消费社会形态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由生产决定消费让位于消费决定生产。整个社会的结构都由消费来决定。亦即当前的消费承担了以往生产的功能。然而,单纯(功能性)的消费并不足以为这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制造空缺,所以这里的消费只能是消耗性与破坏性的。换句话说,唯有如此,消费的逻辑才得以取代生产的逻辑,根植于非功能性的符号消费完全满足了这一条件。因为这个事实,国家需要消费者消费,并且教育那些不懂得消费的公民更好地消费,消费不是权利论的实现,而是义务论的责任。它在这个逻辑基点上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社会个体一旦消费,便成为消费主体,而消费主体在消费的同时也就奇妙地完成了社会规定的劳动。从前的劳动仅仅是生产,当前的劳动形式成为消费。因此,需求“不是作为被丰盛社会所解放了的消费的力量,而是作为体系自身的功能运演,即幸存以及再生产的过程所必需的生产力。[3]”
第二个变化是传统意识形态功用的式微。需求关系之为驯化关系的另一个背景,是当代资本主义对意识形态内涵的大幅调节。他们意识到“关于权利、正义的有意识的平等原则仍然相对脆弱,且永远不足以实现社会一体化。[1]”,然而消费主义却能满足这些条件。于是,消费就再一次承担起操控与组织社会的职能化效力。“和民主制度歌颂人民是为了让它待在原地(就是说让它不要参与社会政治舞台)一样,人们承认消费者的至高无上,是为了叫他们不要这样在社会舞台上进行表演”[1]。由于消费的隐蔽强制性,人们对待它不再像对待生产那样有着直观的被束缚感受(对待消费,消费者一再将它“作为奇迹来体验”)。在消费社会中,大资产者只需要对牛奶进行精妙的包装,只需要让消费者意识到他们不是被束缚而恰恰是被解放了的,就再也不用将牛奶倾倒进江河大海,也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生产的难题;而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第二个好处,那就是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也顺带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统一。
那么在消费社会里资本主义是如何来进行消费驯化的呢?鲍德里亚认为主要是通过商业诱导和道德约束这两个步骤来进行的。
关于商业诱导,鲍德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成为人的研究对象,只是在汽车的销售难于生产之后”[1]。商业诱导的主体行为是广告,首先,广告听命于当前资本社会基本矛盾所呈现的消费形态,即破坏性的消耗。广告正是在促使消耗性破坏的达成上有其现实意义。简单说来,即是令使用价值无限地贬低,使物品彻底成为屈从符号价值的一个摆设。符号价值虽然难以精确地加以量化,但这一缺陷在消费逻辑中刚好是它的“长处”。正因为无法具体量化,广告如奇迹一般向消费主体显现,向他们宣谕当前的时尚走势,流行风向等等。
时尚只是符号价值的体现,是消费话语的一个阴谋。意在使生产出来的物品迅速陈旧。虽然生产者无法实体性地销毁已然出售的商品,但令其迅速陈旧本身就是一种破坏,一种技术性销毁。时尚在此便担当了中介工具,间接地满足了资本家再生产的需求。那么,承担宣谕时尚风向的广告话语究竟是什么?鲍德里亚参照了博尔斯坦的意见,后者认为它是一种“非真非伪的劝导性论述”,而鲍德里亚则进一步地将它定义为:自我实现、自我预言的神话话语。“广告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1],其模式是反复叙事。何为反复叙事?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一个美容品的广告文案这样写道:“姑娘,要么你很美,要么让自己变得很美”。这是一个因为符合人们内心期待所以很难驳斥的律令。但它之所以难以驳斥,归根结底是由于广告话语脱离了真伪的价值范畴。
毫无疑问,顺从并不是社会全部个体的行为。有的社会个体会抗拒消费,他们以此来主动地祛除自身的消费身份,但更为普遍的是消费社会中并不少见的暴力现象。鲍德里亚由此分析道:“这种对丰盛的难以适应很可能恰恰反映了所谓渴望舒适的‘天性’并非那么自然——否则个体们在舒适中不会有那么多的恶要作,他们会双脚跃进富裕之中。这应该使我们觉察到在消费中存在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一种人们不得不受到其教育、训练甚至驯化的东西——事实上那是一种与自由统治毫不相干的新的道德心理约束机制。[1]”实际上这也暗示了驯化操作程序的第二个部分,即道德约束:将消费与否打造成一种道德价值的评判标准。
道德约束是商业诱导的逻辑必然。消费道德约束机制的内涵在于幸福的必须。就像在由四十篇日记组成的《我们》一书里,主人公开篇写到:“如果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带给他们的数字般准确的幸福,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成为幸福者。”。质而言之,消费道德的约束性体现为:以强制的“幸福”取代强制的痛苦,以强制的消费取代强制的剥削。[4]
我们已经知道,消费道德根本无法反映个人需求的本质属性,相反,需求首先是被这个社会系统根据新的矛盾创造出来的新型生产力,然后才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功能的式微事实打造的一种新型道德(从前的道德约束通过社会舆论来起作用,如今它依赖消费操纵)。它是后天被设计和给定的约束机制。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曾说:“根本没有道德现象这种东西,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5]。鲍德里亚在此给消费下了一个定义:“建立在财产必然用途之上的道德概念”[1]。如果说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招致了虚无主义,那主要就在于它以怀疑驱逐了自由责任,将道德前提穿凿为真空状态,然而这也说明了在道德的必然性一面,在激发人类道德禀性的一面,信仰是不可或缺的组成。
健全的道德都是信仰与理性的同一,消费道德亦是如此。无论是消费信仰,还是消费理性,它们均以否定道德困惑的方式指涉了需求的正当性。在消费社会中,个人的思想与道德自由之所以饱受消费话语的深度威胁,正在于消费者在橱窗前目光所及,不管他们期望什么,什么都会被允许,被制造出来。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鸿沟似乎被暂时取消,“你应当”与“我要”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而消费主体再也不能将它们分开。但从反面来看,倘若据此视消费道德为人类的正当禀性,那么人类只能愈发走入不自由的境地当中。
消费道德作为一种新型的心理图解,所有社会话语都在其支配下对消费主体反复进行着教育规劝,并且不仅在逻辑上打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凭借着消费主体的自我消费行为成功地实现了矛盾对立面的转化与消解。
三、消费主体批判——消费异化的主体心理机制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由于社会的基本矛盾,注定是一场难以终结的消耗性浪费。在消费主体这一面,它不仅意味着生存(必需)与生活(多余)两个概念的区分,也不仅指涉了理性(节约)与非理性(浪费)在功能意义上的对照,更为根本的是消费主体心理的形成和变化——心理好奇和心理欠缺。由于消费主体对消费社会的一切操纵浑然不知,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需求是自发的,而这种自主心理同时就在隐蔽的他律下自觉地刺激了一己需求的增长。他们并不知晓为何如此,正是在这里,鲍德里亚认为好奇心与缺乏了解是“指面对真相所产生的同一个整体行为,是大众交流实践普及和系统化了的行为”[1]。进而他如此总结道:“消费者把不同寻常的行为当做自由、理想和选择来体验,根本不把它视为……对规章的服从。[1]”
《物体系》的结尾部分,鲍德里亚已对这一问题做了初步回应:“在消费系统性和无止境的程序中出现的计划,其根底是遭到失望的全体性要求(exigence decue de la totalite)。在其惟心性格中,各个物记号相等同,而且可以无尽地增殖:它们必须如此,为的是随时填满一个缺席的现实。消费之所以无法克制,其最终原因,便在于它是建立在欠缺(manque)之上”[6]。这里的关键词是“欠缺”,而至于“欠缺”究竟所指为何,则是其后他在《消费社会》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揭示的。
简单地说,欠缺的不是物品,而是消费者的心理结构:这种“欠缺”(或贫困)彻底地实现在消费者寻求个性(差异化)的攀比性心理结构当中:社会个体一旦置身消费符码的体系之中,浪费就成为了“主体性”的永恒命题。因为唯有浪费,消费主体才得以占有差异与个性;唯有浪费,消费主体的“主体性”才得以确立。
“从前,出生、血缘、宗教的差异是不进行交换的:它们不是模式的差异并且触及本质。它们没有“被消费”。如今的(服装、意识形态甚至性别的)差异在一个广阔的消费团体内部互相交换着。这是符号的一种社会化交换”[1]。这种创序性的差异是封建时代等级制度的代替,人们既然将世袭的等级视为一种恩赐,那么通过消费创序的差异同样被他们这样看待。随着封建制度的灭亡,也随之带走了贵族等级体系。消费主体不知疲倦地进行着消费创序的工作,其心理在于对消逝了的等级体系的怀恋,其动机在于在全体(形式)平等的社会制度中重建饱含特权与垄断的等级体系。
因此,可以说消费主体的心理结构就是由消费创序的编码体系所塑造。置身于这个符码垄断的体系内,欠缺乃是一种现实或应当,或者说满足倒显示出非现实的面目。消费主体因为被操纵,他时时刻刻地感受到欠缺,由此时时刻刻地凭赖消费以占有差异;然而即便消费主体在刹那之间感到满足,这短暂的满足也将被欠缺心理迅速地替代。
虽然消费在当前社会中反转为主导性部分,但并不是说我们真正进入了丰盛社会,而至多只能说是较之以往宽裕得多的环境。也就是说,尽管不是真正富足的社会,现实的经济发展程度还是创造了消费之为主导性领域的条件(如消费主体购买力的提高)。从前资产阶级为了闯入有传统贵族驻守的等级森严的社会,通过奢侈品的消费获得了置身那个社会的合法性与“高贵性”。那么在当今社会中,传统贵族已不复存在,消费者之间是平等的。他们消费,是想在并不存在等级制度的社会里差别化以独占鳌头,因此他们的消费比当初资产阶级的浪费还要剧烈。消费甚至成为了人们的生存方式:由凹形的实在消耗转向凸形的意义表征。但是悖论在于:当前社会的消费者更倾向于认为后者的真实程度;他们需求什么,什么就是真实的,进一步说,就是幸福。
四、结语:消费社会的景观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早期鲍德里亚从对消费对象的功能区分到消费需求的驯化再到消费主体的心理结构的分析,完成了对消费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全方位批判,展示了消费社会中消费异化的全过程。这一批判证明了在消费社会里,消费异化是无法被终结的,因为它的逻辑就是需求与驯化的同一。不仅如此,它还承担了整个社会一体化的驯化功能,而消费本身又驯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所以,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异化无法终结的社会里,其社会道德是一个猥亵的非道德体系。“它的宁静需要对现实与历史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它的宁静需要永久性地被消费暴力来维系。这就是它自身的猥亵之处”[1]。其实这一点在凡勃伦那里也略有揭示,凡勃伦认为消费社会的炫耀性消费不符合全人类利益的道德价值,只是满足少数有闲阶级的炫耀心理。但是从现实角度观照当下这个社会,毫无疑义的一点即是大部分人都有意无意地被卷入到符号消费之中。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明不是促进文明的发展,而是反对文明,反对人性。这就是未被终结的消费异化发展至今的景观。这一景观是非道德的,只不过非道德的主体已经从凡勃伦语境中的有闲阶级转变为当前消费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任何人都在消费,任何事物与理念(即无论现实与否)也都可以被消费。诸如此类的景观旨在说明同一个事实,即消费社会的全面到来。
[1]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消费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73;5;64;78;69;53;119;175;21;11;42;77;12.
[2]戴阿宝.终结的力量-鲍德里亚前期思想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3.
[3]鲍德里亚,夏莹: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87.
[4]尤金·扎米亚金,殷杲.我们[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
[5]尼采,朱泱.善恶的彼岸[M].团结出版社,2001:80.
[6]鲍德里亚,林志明.物体系[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27.
B565
A
1002-3240(2017)01-0030-05
2016-12-12
李恩来(1963-),湖北恩施人,哲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校:赵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