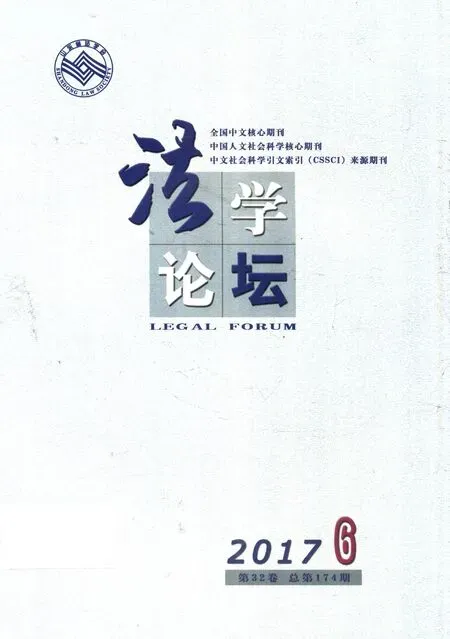商事司法对商主体法定原则的突破
2017-04-04陈彦晶
陈彦晶
(黑龙江大学 法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百家争鸣】
商事司法对商主体法定原则的突破
陈彦晶
(黑龙江大学 法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商主体法定原则为我国商法学界的通说,但该通说是我国学者对国外立法例的学理阐释,国外学理上并未有类似表达。商主体法定原则的前提是商主体的立法较为完备,不同商主体法之间的转介条款较为合理。我国目前的商主体立法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商主体法定原则不适合我国法制现状。司法实务当中对商主体原则多有突破,法院在处理商主体的纠纷过程中,常常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解决纠纷,表现为同一商主体内部、不同商主体之间和民商事主体之间的类推适用。这种突破有其合理性,商主体法定本就是学理表达,其对法院审判活动并无实际的拘束力,商主体立法大量漏洞的存在迫使法院必须放弃商主体法定原则,从结果上来看,法院对商主体法定的突破带来积极的社会效果。尽管法院的类推适用在技术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法院做法本身并不应被批评,反倒是学理上应该放弃商主体法定原则。
商主体法定原则;商事司法;类推适用;合理性
商主体法定为我国商法学界之通说,诸多著述中均将其定位为商法的基本原则,其旨趣为何,虽略有分歧,但大同小异。我国并无商法典、商法通则或相类规范,其出处多为学者著述,然而就商主体法定原则的渊源语焉不详,究竟为境外立法例明文所创,还是类似资本三原则;乃是从制度总结而来,还是纯学理之揭示。不得不察,否则将贻误学人,亦授人商法学科不严谨之口实。我国司法实践当中,法院用《合伙企业法》审理个人合伙纠纷案件,用《民法通则》关于个人合伙的规定审理公司发起人纠纷案件,用《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审理股份有限公司案件,等等,似乎并无大碍,可这与商主体法定原则之抵牾也是毋庸多言。那么何者为错?就商主体法定这一原则,其能否被突破,若能突破,需满足何种条件?甚或,商主体法定本就不应是一个原则?学理阐释与司法实践之间这一鸿沟,是应由学理之放弃还是实践之向学理靠拢而得到弥合?本文欲就这些问题进行研判,以求反思学理、回应实践、消弭冲突。
一、商主体法定原则:学理抑或制度
商主体法定原则,出现在我国绝大多数商法学或商法总论的著作当中,①参见黎燕主编:《商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林嘉:《商法总论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张民安、刘兴桂主编:《商事法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王晓川主编:《商事法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柳经纬、刘永光编著:《商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官欣荣主编:《商法原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王保树主编:《商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高在敏等编著:《商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胡志民等编著:《商法学》,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毕颖主编:《新编商法学教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李新天主编:《商法总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王建文:《商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王建文:《中国商法立法体系:批判与建构》,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徐强胜:《商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可谓我国学界之通说。有学者称为“商主体法定原则”,有学者称为“商主体严格法定原则”,也有学者称为“市场准入严格法定”。少有学者直接给商主体法定下定义,而是从外延的角度去描述,但就具体包括的内容则略有分歧,可分为四类:第一类观点认为,商主体法定主要包括了商主体种类法定、内容法定、程序法定;*参见柳经纬、刘永光编著:《商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官欣荣主编:《商法原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第二类观点认为,商主体法定包括类型法定、内容法定和公示法定,*参见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王建文:《商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王晓川主编:《商事法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胡志民等编著:《商法学》,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李新天主编:《商法总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毕颖主编:《新编商法学教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这一观点与上一类较为接近,“公示”本身可以被“程序”所包含;第三种观点认为,商主体法定包括类型法定、设立标准法定、设立程序法定;*参见王保树主编:《商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第四种观点认为商主体法定包括类型法定、财产关系和组织关系法定*参见张民安、刘兴桂主编:《商事法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财产关系和组织关系实际上能够被其他观点中的内容法定所涵盖。可见,关于外延方面,学界观点大同小异,区别就在于如何描述程序和公示的要求,商主体法定原则本身的存在被商法学界广为认可。遗憾的是,尽管商法学上就商主体法定原则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就该原则源自何处却语焉不详,毕竟我国没有商法典,关于商法基本原则的阐释基础并不稳固,因此有必要追问,学者所述的商主体法定原则来自哪里?
(一)部门法基本原则的出处
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原则,这一规则已成为法律适用的一个重要规则,而且,法律原则尤其是部门法的法律原则已成为部门法体系完备的一个重要内容。*参见周林彬、官欣荣:《我国商法总则理论与实践的再思考——法律适用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通常来讲,部门法基本原则有下列三类出处:第一,法律的直接规定。有时,法典直接在其总则部分写明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其未必使用“基本原则”的表述,但因所处法典体系中位置,而被理解为该法的基本原则。例如,《民法通则》第3条至第7条规定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第3条至第5条规定了刑法的基本原则。这类原则渊源清晰,表述凝练,成为毫无争议的基本原则。第二,根据法律的规定整理出某法的原则。在这类法律部门中,并无类似《民法通则》或《刑法》的法条来阐明基本原则,而是学者们通过整理该部门法的各项规定提炼出所谓的原则。例如,公司法上的“资本三原则”。第三,学理阐释。由于并非所有的部门法均有对应的法典,所以一些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主要靠学理阐释来完成。例如,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除了来自国家立法性和政策性文件的规定以外,还来自于行政法学理论的阐述。
(二)商主体法定原则出处的检索
商主体法定原则来自何处呢?对此,学者表述略有不同,商主体法定原则“来自各国商法强行法的规定”的说法拥有最多的支持者*参见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王建文:《商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胡志民等编著:《商法学》,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毕颖主编:《新编商法学教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黎燕主编:《商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樊涛:《我国商主体法律制度的批判与重构》,载《上海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于新循:《论商法之商主体强化原则》,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王栋:《论商法基本原则中的法定强制性》,载《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张涛:《商主体若干问题研究》,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11期。,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我国的制度*参见官欣荣主编:《商法原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还有学者抛弃了制度的根源,将其理解为“立法中应予恪守的原则”*参见张民安、刘兴桂主编:《商事法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第二种观点最难成立,将商主体法定理解为我国的制度,缺少直接的证据,毕竟,在商法典尚付阙如的情况下,认为支撑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出自我国法律,需要指出哪些法律制度及其构成的体系支持了这一结论,论者只是一笔带过,并未论证,在此也无的放矢。第三种观点容易理解,在归类上可以明确地将其归入学理阐释的范畴,因为既然是立法中应予恪守的原则,表明其并非来自对法律条文的解读,至少包含了超越法律条文之上的立法理念的内容。值得仔细检讨的是拥趸最多的第一种观点,即商主体法定来自各国商法的强行法规定。
作为一项商法的基本原则,如欲找到各国商法与之有关的规定,应去各国商法典中找寻踪迹。但是,查阅《德国商法典》《法国商法典》《日本商法典》《西班牙商法典》,找不到类似我国《民法通则》中表述基本原则那样的条款。这几个国家的商法典基本都是从商人概念开始规定,没有“商主体法定”或“商人法定”字样出现,可见,商主体法定原则并不是来自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典的直接规定。
那么,商主体法定原则是不是像公司资本三原则那样,是根据对法律规定的整理而得来?典型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典均有关于商人的定义,《德国商法典》第1条规定:(1)本法典所称的商人是指经营营业的人。(2)营业指任何营利事业,但企业依种类或范围不要求以商人方式进行经营的,不在此限。*参见《德国商法典》,杜景林、卢谌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法国商法典》第1条规定,所谓商人,是指实施商行为并以此为习惯性职业的人。*参见张民安:《商法总则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日本商法典》第4条规定,(1)本法所称商人,指以自己名义,以实施商行为为业者。(2)依店铺或其他类似设施,以出卖物品为业者,或经营矿业者,虽不以实施商行为为业,也视为商人。第52条第2款的公司亦同。*参见《日本商法典》,王书江、殷建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西班牙商法典》第1条规定,本法典所谓的商人是指:(1)具有合法的经商能力,并惯常从事营业活动的个人。(2)依本法典设立的工商业公司。*参见《西班牙商法典》,潘灯、高远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从这些法典的规定来看,商人(商主体)确实是法定的,未经商法确定为商主体,无法适用商法的相应规范。但据此就推演出商主体法定原则,略显草率。
首先,抛开商人立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别,仅从上述法典的文义出发,“经营营业”、“实施商行为并以此为业”、“以实施商行为为业”、“具有合法的经商能力并惯常从事营业活动”,均为开放式描述,经营营业或者从事商行为,便成为商主体,至于登记是否为商主体成立的必要条件,则区分商主体类型对待,对于小商人,并不要求进行登记。这与商主体法定原则的内涵无法完全重合。按照我国学者所理解的商主体法定原则,各国制定了大量的强行性法规对商主体的资格予以严格控制*参见王建文:《中国商法立法体系:批判与建构》,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但是从各国商法典关于商主体定义的规定中,并未读出严格控制的意蕴,反倒是表现的较为包容,充满了解释的空间,只要满足各国法典上所规定的条件就可以成为商主体。
其次,从商主体法定原则的外延来看,主流观点认为包括了类型法定、内容法定和程序法定。类型法定是指商法对商主体的类型做了明确的规定,投资者只能按照法定类型来设立商事主体*参见王保树:《商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这对于商法人、商合伙来讲是准确的,但就商个人而言则不甚精当,其成为商主体受商法调整有时并非自身设立的结果,而是法律强制施加的结果。商主体内容法定是指可以进行经营活动的商主体的财产关系和组织关系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创设非规范性的财产关系和组织关系。*参见范健:《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这点从各国商法典中找不到根据,但隐约可以从各国制定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商主体法上找到依据。程序法定是指商法对商事主体在设立时的程序做了明确规定,投资者欲成立商事主体必须严格按照这些法定程序和步骤进行,否则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法律后果。*同⑥。程序法定的情况与内容法定相似,但又略有不同,至少就小商人并不存在设立的特殊程序要求。可见,从商主体法定原则的外延方面还是能循到一些立法上的蛛丝马迹的,但也仅限于此,各国商法的规定并不能完全符合商主体法定原则外延的要求。此外,疑问还在于应否将其上升为商法的基本原则层面?主体法尽管是商法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随着近年来各国商事立法的发展,多数国家已经将主体法从商法典中抽离出来单独立法,再让商主体严格法定作为指导整个商法的基本原则似乎有些力不从心。
最后,从大陆法系主流商法理论来看,未见学者将商主体法定作为商法基本原则加以阐述。德国主流商法教材中无此表述,*参见Karsten Schmidt, Handelsrecht, 6.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2014.Baumbach/Hopt, Handelsgesetzbuch, 34 Aufl., C.H.Beck 2011.Hartmut Oetker, Handelsrecht,7. Aufl. Springer 2015.Justus Meyer,Handelsrecht, 2. Aufl., Springer 2011.深受法国商法学说影响的张民安教授所著的《商法总则制度研究》中有专章论述商法的基本原则,但并未有商主体严格法定原则,而代之以从商自由原则。*参见张民安:《商法总则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章。日本学者関俊彦所著的《商法总论总则》没有商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参见[日]関俊彦:《商法総論総則》(第2版),有斐閣,2006年版。畠田公明的《商法·会社法総則講義》中也找不到相关内容*参见[日]畠田公明:《商法·会社法総則講義》,中央経済社2008年版.。国内学者在论述商主体法定原则的时候,也没有外文的参考文献。
综上可以发现,商主体法定原则并非来自大陆法系立法的直接规定,也非国外学理的借鉴,而是我国学者根据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例所整理出的原则,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部分学者在论述商法基本原则时排除了商主体法定。*参见赵中孚:《商法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施天涛:《商法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郑彧:《商法要义》,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因此,很难说商主体法定原则在我国是一项制度化的原则,而只能将其定性为我国学者对国外立法的学理解释。
二、商主体法定原则应用的制度前提
按照我国学者所创设的商主体法定理论框架,类型法定较易实现,立法上提供相应的商主体类型,供投资人选择即可,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在我国商主体制度上,并不存在依据客观行为“认定”的商主体,所有的商主体必须进行登记。我国理论上的商主体严格法定原则与商事主体登记实践保持了高度一致。二者的因果关系不甚明了,不知是理论上的这一倾向导致了立法的选择,还是反之。若仅就时间来看,理论产生的时间更早一些,早在1994年,雷兴虎教授就总结了我国商法理论上对于商法基本原则的不同主张,其中在四原则和五原则说中,均有对于商主体法定的强调,*参见雷兴虎:《略论我国商法的基本原则》,载《中外法学》1994年第4期。但若将视角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主体法定也是我国立法的选择,例如,1993年《公司法》第224条规定,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的,责令改正或者予以取缔,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保留至今,为第211条。颁布于1988年的《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第2款规定,依法需要办理企业法人登记的,未经企业法人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不得从事经营活动。在我国企业制度初建之际,毋宁说,这是当时政策选择的结果,学者的论述只是为这种政策选择寻找了理论的依据而已。程序或公示法定也较易满足,我国当前的商事登记制度能够满足该原则的要求。然就内容法定而言,其要求商主体的财产关系和组织关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不得调整,需要重要的制度前提,即各类商主体立法周密、不同商主体立法间衔接紧密,以下分述之。
商主体立法周密,无漏洞。只有商主体立法对商主体的财产关系和组织关系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不存在法律漏洞,才能保证内容法定的实现。如果商主体立法本身有着大量的漏洞,商主体参与人就特定事项找不到法律依据,则其主动寻求自治或借鉴其他商主体法律中类似制度来处理问题,无可厚非。另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不同商主体立法之间衔接紧密,表现为各商主体法之间存在大量的准用性规范。所谓准用性规范是指法条表述为就某一事项的解决需要借助于其他法律,或者其他制度的规定,常常表现为“准用”、“依……的规定”等字样,例如,《德国商法典》第105条第3项,对于无限公司,以本章无其他规定为限,适用《民法典》关于合伙的规定。第161条第2项,以本章中无其他规定为限,对于两合公司,适用关于无限公司的规定。日本也有相似规定。这样就实现了商主体法之间的无缝衔接。上述两个前提的齐备才能保证商主体内容法定的实现,因为立法不可能穷尽所有商主体经营的细节,在力求周密的同时也要为可能的漏洞留下填补的方法。
反观我国商主体立法,却不能满足上述条件。首先,我国商主体立法并不完善。无论是《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还是《个人独资企业法》均有所缺憾,很多地方均留有空白。其次,我国商主体立法缺少德、日那样的准用性条款,立法衔接不畅。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中,只能找到各类商主体内部的准用性规范,例如,《公司法》第99条,类似的还有《公司法》第108条,第113条,第117条,第118条。《合伙企业法》第60条规定,有限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未作规定的,适用本法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五节关于普通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的规定。但我国规定与德、日商法典的规定有所不同,体现在:第一,我国这些条款,均是出于节约立法成本、简化立法语言的考虑,准用同一法典内部其他条款的规定,不涉及其他商主体类型;第二,我国这类条款指向的往往是某类具体事项,意在相同事项为相同处理,而德、日商法典的准用类型与我国不同,目的在于指明该部分法条没有规定的,应该适用何种法律规范,乃为一种补充式设计,通常指向一种更为普通的规范。在我国商主体立法上找不到准用其他商主体法的条文,就连公司法定代表人制度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当中关于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制度,也是学理的解释,而非公司法的规定。如此,若再秉承商主体法定,尤其是内容法定原则不动摇,将使得大量有关商主体财产关系和组织关系的纠纷得不到解决,增加商主体内部的矛盾。面对这样的制度缺陷,我国法院在实际处理商主体纠纷时是否坚持了商主体法定原则呢?
三、我国商事司法实践对商主体法定原则的突破
长久以来,人们已摆脱法秩序的全备性与无漏洞的信条,并且因为不能改变不得以无法律而拒绝审判的禁令,而赋予法官填补漏洞的创造性任务。*参见[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尽管我国并无禁止拒绝审判的规定,但由于我国并不具备商主体严格法定所需要的制度前提,法院在面临当事人的纠纷时,也并未拘泥于商主体法定的原则,而是有所突破。法院大多采取类推适用的方法解决商主体的组织关系和财产关系纠纷。所谓类推适用系就法律未规定之事项,比附援引与其性质相类似之规定,以为适用。*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用技术化的语言表述就是,将法律针对某构成要件(A)或多数彼此相类的构成要件而赋予之规则,转用于法律所未规定而与前述构成要件相类的构成要件(B)。转用的基础在于:二构成要件——在与法律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上——彼此相类,因此,二者应作相同评价。*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8页。我国法院在处理商主体的组织关系和财产关系纠纷时,常常用类推的方式以求得问题的解决,尽管在判决书行文中并未指明“类推“二字,但是此种填补漏洞的方法却潜在于判决之中。法院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解决商主体组织和财产纠纷,具体表现为如下三种类型:
(一)同一商主体内部的类推适用
我国商主体立法大致有《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个体工商户条例》等,各类主体在立法上并不十分完善,因此,法院突破立法进行裁判的现象常有发生,有时会表现为在各类主体法内部进行类推适用。例如,就《公司法》上并未规定的责任形态类推适用《公司法》上相似制度进行审判。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与四川泰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泰来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四川泰来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55号判决书。中,沈氏公司和娱乐公司是装饰公司股东,房屋公司和装饰公司是娱乐公司股东,装饰公司、房屋公司、娱乐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同,地址、电话、财务管理人员相同。虽未直接援引《公司法》,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均花篇幅研究了三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问题,并最终认为各公司之间已实际构成了人格混同,其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反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因此,判令装饰公司债务应由娱乐公司和房屋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判决引用《担保法》足以解决问题,无须拓展至人格混同层面,但该案例却被普遍理解为公司人格混同下的法人格否认问题,与两审法院在判决中对此问题的过分展开不无关系。学者一般将其解读为关联企业之间的法人格否认或揭开公司面纱。但是就我国《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而言,其只能包含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于本案,即只能判决沈氏公司与娱乐公司为装饰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房屋公司是无法由“股东”二字所涵盖的。至此,判决虽未明示,但已经是类推适用了《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关于法人格否认的规定。这超越了商主体法定理论所能包容的范畴,按照内容法定的要求,既然《公司法》只规定了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无论如何也不能要求股东的股东为公司债务或子公司为母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不同商主体类型之间类推适用
我国商主体立法类型清晰,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各个商事主体法均规定了自身的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按照我国各类商主体法的规定,每种商主体应当依照调整该类商主体的法律而设立,从设立之初便确定了其具体身份,不同商主体之间不存在相互交叉的可能。这可能是商主体严格法定作为一种立法思想的体现。然而在司法过程中,这一思想却未能得到贯彻,法院有时会用规定某一类商主体的法律来判决另一类商主体的纠纷。南通双盈贸易有限公司诉镇江市丹徒区联达机械厂、魏恒聂等六人买卖合同纠纷案*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7期。中,被告联达机械厂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实际系合伙经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合伙企业法》判决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法官将此裁判规则总结为:在当事人约定合伙经营企业仍使用合资前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且实际以合伙方式经营企业的情况下,应据实认定企业的性质。各合伙人共同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应共同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外所负债务负责。合伙人故意不将企业的个人独资企业性质据实变更为合伙企业的行为,不应成为各合伙人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参见江必新、何东宁等著:《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公司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562页。若按照商主体法定理论,未经登记为合伙企业,绝无适用《合伙企业法》的空间,否则便模糊了不同商主体之间的界限,为商主体法定原则所不容。可法院的思路却是,登记企业形态与实际经营方式不同时,应以实际经营方式为准,而不论其登记为何种商主体,*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内民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中也是这种思路,资中县八块田煤矿登记为普通合伙企业,但法院认为,系被告邹茂秀的个人独资企业。显然,突破了商主体法定的要求。
(三)民商事主体之间的类推适用
所谓民商事主体之间的类推适用,主要是指民事合伙与商事合伙之间的类推适用。我国历来区分民事合伙与商事合伙。民事合伙纠纷依据《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处理,商事合伙纠纷依据《合伙企业法》处理。对此,我国法院有着一致的认识,判决书中对此表述为:“本院认为,从原、被告经营东坡飘香川菜馆来看,其法律特征是合伙人为自然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分享收益,应为民事合伙,非商事合伙,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调整。”*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2015)蓬民初字第1237号民事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2条规定的合伙企业是依照商法部门法而设立,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属于商事合伙法律关系。本案中,张清梅与周华波合伙经营的东莞市虎门某某某饮食店并非合伙企业,而是个体工商户,如其两人之间成立民事合伙法律关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个人合伙的相关法律规定。”*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二法虎民一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
虽然对基础关系的区别法院有着清晰的认识,但民事合伙规定的不全面也是客观存在的。《民法通则》有关民事合伙的规定十分简略,表现为第30条至第3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5条至第57条加以一定程度的细化。但毕竟立法和解释出台年代久远,很多问题未能规定。因此,法院在审理民事合伙协议纠纷时,会援引《合伙企业法》进行裁判。
在王新中与李元春等确认合同效力纠纷申请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书。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签订一份协议约定,三自然人以某分公司的名义开发某综合楼(该分公司的总公司认可综合楼系三人以其公司名义合伙所建),协议中表明三人为合伙。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三人签订《协议书》的目的是针对承天商厦将被昌泰典当行拍卖而作出的虚假分割合伙财产协议,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当事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51条的规定,合伙人退货,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合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而处理了三位民事合伙人的法律关系。按照商主体法定理论,针对未登记为合伙企业的民事合伙,不应援引《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进行裁判,否则就不仅仅是不同商主体之间的混淆,而是连民商事主体之间的界限都不明晰了。但显然,法院并不这么认为。
综上可以发现,在我国商事司法领域中,并未坚持商主体法定原则,而是常有突破。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该总结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或公报案例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一现象表明,尽管样本数量有限,但司法实践突破商主体法定现象并非个案,而是我国法院的整体态度或倾向,至少,最高人民法院在以这样的方式指导着各级法院。
四、司法实践突破商主体法定原则的合理性与技术瑕疵
关于商法基本原则的意义与功能,学者描述为“商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反映一国商事法律的基本宗旨,对于各类商事关系具有普遍性适用意义或司法指导意义,对于统一的商法规则体系具有统领作用的根本规则。在法律创制中,作用在于构建法律制度的基础、保证法律系统的有机统一、法治秩序中发挥导向作用,在法律实施中,作用在于指导法律的执行、弥补法律漏洞、限制自由裁量权。”*朱羿锟:《商法学——原理·图解·实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既然谈到司法实践中对商主体法定的突破,显然关注的是在法律实施中商法基本原则的作用。当聚焦在原则的“弥补法律漏洞”功能时会发现,学理上的“商主体法定原则”下存在着一对严重的矛盾:一方面是作为一项商法的基本原则,其功能在于弥补法律漏洞;另一方面,我国商主体立法上存在大量的漏洞,若法院坚守商主体法定原则,这些漏洞将无法得到弥补。显然,我国法院于此并未过分纠结,而直接选择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商主体法定原则。原因有四:第一,所谓的商主体法定原则只是出现在学术著作上的一个表述,从未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中出现,地位上的弱势使得其对于法官的约束力较为有限。况且,其是否为一个商法的基本原则,并未达成绝对的共识,而仅能称为国内商法学的通说,仍有部分学者对商法基本原则的整理中不包括商主体法定的内容。如果通说是一种有用的论证,那么它必须在性质上被证明,而且对少数加以尊重,特别是在法律中的少数。但对于(多数的)法院而言,“通说”只是一种单纯的由相关文献中汲取而来的事实。当我们自诩为科学理论者,对于这样的一个定则——“通说是对的”——却被普遍化,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通说”这个字不经意地暴露了实务上法学的性质:这些是意见,只是意见,不是知识。*参见[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这使得法官突破商主体法定原则的做法既不明显违背任何法律的规定,也在学理上能够找到支撑。还有一个较为悲观的想法是,由于商法典的缺位,很多法官可能没有学习过商法总论,不知商主体法定为何物,在作出相应判决时根本未受到任何思想上的羁绊。第二,我国商事主体立法存在大量开放漏洞*参见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或称公开的漏洞,即法律应予规定而未予规定之内容,*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例如,公司法上的设立中公司、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等,合伙企业法上的有限合伙人出资、普通合伙人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转让合伙份额的效力等。若固守商主体法定原则,法官会发现其所面临的纠纷没有可供依据的法律规范。第三,法院解决商事纠纷的积极态度。面对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法院在处理商事纠纷时,并未采取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情况,而是审理商事纠纷的实体内容,大胆运用类推适用的漏洞填补方法,对于法律未有规定的事项,援引相近的法律予以判决,进而定纷止争。第四,结果上符合正义原则和法的统一性的要求。在法律漏洞问题上,体系正义原则和“法的统一性”原则需要加以考虑,按照这些原则,法律问题的解决不仅仅要合乎逻辑地纳入同位阶和更高位阶法律规范组成的体系当中,并且要在目的上与这个体系保持一致。*参见[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法院在处理商主体组织关系和财产关系纠纷中,类推适用其他法律规范,在结果上符合正义的要求,同时,也满足了商主体法立法目的的要求。法院基于对结果的信心判断而选择类推适用的方式来填补商主体立法上的漏洞。
但若仔细推敲,还是会发现,法院的做法有不妥之处。商主体法大都存在如下表述:“本法所称××(某商主体),是按照本法所设立的××(某商主体)”。据此,若并非按照该法所设立的该类商主体,也就不能适用该法所规定的专门调整该类商主体的具体规则。只是前文已然说明,法院于此采类推适用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解决商事纠纷的做法,乃为无奈之举,于私法领域类推适用也为学理所认可。故此,我国法院突破商主体法定原则的做法有其合理性基础,不应受到批评。尽管法院的做法有其合理性,但就类推适用的具体技术环节,则存在着一定的瑕疵,说理并不充分,结论让人感觉突兀。
(一)无对漏洞的指明
前文已指出,若要进行类推适用,必须法律于此存在公开的漏洞,即因立法者的疏忽,应予规定而未规定。然而我国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从未见指明此点,这或许与法院与立法机关或者司法解释的制定机关在我国的权力配置有关,法院不太有勇气在判决中直接指出某处存在法律漏洞。
(二)无类推方法的说明
若法律存有漏洞,法院需要予以填补,法院在援引相近规则时应指明其正在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解决当下纠纷,但我国各法院判决中从未指明此点。在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17号判决中,法院在援引《合伙企业法》的过程中,未进行任何说明,一个“另”字就完成了承上启下,说理过程中对《合伙企业法》第51条的立法目的进行了解释:退伙意味着原合伙人与其他合伙人脱离了由合伙人协议所设定的一切权利义务,将导致合伙人部分出资的返还和盈余的分配,对债权人来说,退伙将意味着减少了一个债务担保人和一份担保财产,因此,合伙人退伙时都必须对合伙企业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结算的目的就是要合伙人能够对合伙企业的财务状况全面了解,以便确定退伙人应分得的财产份额,同时也明确其应承担的债务。继而,法院将《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应用于未登记未合伙企业的涉案当事人之间,实际上完成了一次类推适用,但未能就此进行任何说明。
(三)无观察点的列示
德国法学家考夫曼提出,类推程序的有效性依赖两个因素:第一,为了扩展比较的基础,人们必须尽可能地出示许多“案例”;法律人也很尽力这样做,但大多数人无意去强调类推。第二,类推的有效性相当根本地取决于比较点(比较第三者)的选择,而且取决于确定被比较者之特征。比较点的确定主要不是根据一个理性的认识,而是很大程度地根据决断,因而取决于权利的运用,而这绝大部分都未被反思过。*参见[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第一点正是上一部分所指出的。就第二点而言,我国法院在类推适用也缺乏对于类推观察点的列示。在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与四川泰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泰来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四川泰来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中,法院类推适用了《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法人格否认规定,在说理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讨论了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和责任承担问题,认为,三公司股权关系交叉,实际均为沈氏公司出资设立,沈华源作为三公司的董事长,对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沈华源对此本应依照诚实信用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严格遵守财产分离原则,尽力维护法人制度和公司利益。但本案中,沈华源无视三公司的独立人格,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权,……的情形均表明三公司人格和财产持续发生混同。三公司在同一地址办公、联系电话相同、财务管理人员在一段时间内相同的情况,也是沈华源滥用控制权、公司人格混同的表现。装饰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大量债务,损害了贷款人的合法权益,沈华源以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利用公司独立人格来逃避债务,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反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这可以说是在类推适用上最为规范的一个案例了。在比较点上选择了滥用控制权和人格混同,在人格混同上关注了人事、财产、地址、电话的混同,只是,类推的原型应当是“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其主体是股东,沈氏公司的行为满足这一特征,但此案并未涉及沈氏公司,而是让其控制的另外两个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此时类推适用的比较点应该只是人格混同,这来自于学理对法人格否认构成要件的解析。法院在此案中的做法实际上扩大了比较点的范围,将股东的行为和姊妹公司的行为混为一谈,增加了类推适用的可能。这种做法存在不当扩大类推适用的危险,于类推适用的技术上并不高超。
结语
作为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应具备一些基本的特征:首先,其应有一定的法源基础,即能够找到该原则的法律依据,即便是根据不同的法条总结而来,方能够指导司法实践,若没有法源基础,仅仅是学理阐释,或者作为一种指导立法的理念,难免给人以空中楼阁之感。其次,其应能够覆盖整个法律部门。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能够指导该部门法的全部乃是应有之义,尽管有时可能需要作出一些让步,但至少应具有较大范围的指导意义,否则难以将其上升为整个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最后,其应具备切实的功能,即能够指导立法或法律适用,若坚持该原则会导致无法适用法律,阻碍纠纷的解决,则不宜将其作为一项原则来对待。
商法基本原则也不例外,“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参见王璟:《商法特性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如果我们用上述标准检验商主体法定原则会发现,其难以胜任商法的基本原则。商主体法定并无确定的法源依据,无论是国内法还是他国法均无类似规定,存有商法典的国家学者著述中亦无相关阐述,这一原则的由来颇有蹊跷。商主体法定没能覆盖整个商法部门。商法的基本原则是商法保障营利的基本价值理念的具体细化,其是以现有的私法理论与制度体系为基础,体现商法自身的特殊性,并贯穿于整个商事法律制度的原则。*同①。商主体法定只是调整商事主体的原则,与商行为无涉,所以其并未覆盖商法的全部,因此,才有学者将其列为商法的“次级原则”。商法的次级原则主要存在于商事主体法与商事行为法领域,这些原则不能作用于整个商事关系领域,但是分别在商事主体关系与商事行为关系领域发挥基本准则的功能,对于该领域的法律规范、制度发挥指导作用。*参见童列春:《商法学基础理论建构:以商人身份化、行为制度化、财产功能化为基点》,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170页。商主体法定原则非但不能指导司法,反而可能会阻碍法官填补法律漏洞的行为,与部门法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功能相悖,则应反思其作为基本原则的合理性了。商主体法定不应作为商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商事司法实践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司法实务对商主体法定的突破有其合理性,尽管存在技术上的瑕疵,却也不应被责难。
[责任编辑:满洪杰]
Subject:Commercial Justice's Breach of Doctrine of Legality of Merchant
Authoramp;unit:CHEN Yanjing
(Law School,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Doctrine of legality of merchant is the current expression of Chinese commerical law theory,but this doctrine is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foreign legishation by Chinese Scholars,and we cannot find similar theory in foreign countries.The doctrine of legality of merchants needs two important conditions:firstly,the legishations of merchant are consummate;secondly,there are reasonable referral articles in the laws of merchant.Since we do not have the conditions,the doctrine is not fit for Chinese legal system.The commerical logal practice often breaks this doctrine.During the process of trial,courts often resolve the commerical disputes in the way of analogy,including the analogy inside the same merchant,between the different merchants and between civil and commercial subjects.The breach is rational.Because the doctrine originally is theoretical,which cannot bind the courts indeed.And the loopholes of laws of merchant force the courts to give up the doctrine.Moreover,the breaks lead positive social effects.Even though the analogy of justice has some technical imperfection,it should not be criticized.On the contrary,the doctrine should be given up.
doctrine of legality of merchant; commercial legal practice; analogy; rationality
2017-09-06
陈彦晶(1982-),男,黑龙江延寿人,法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D913.99
A
1009-8003(2017)06-013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