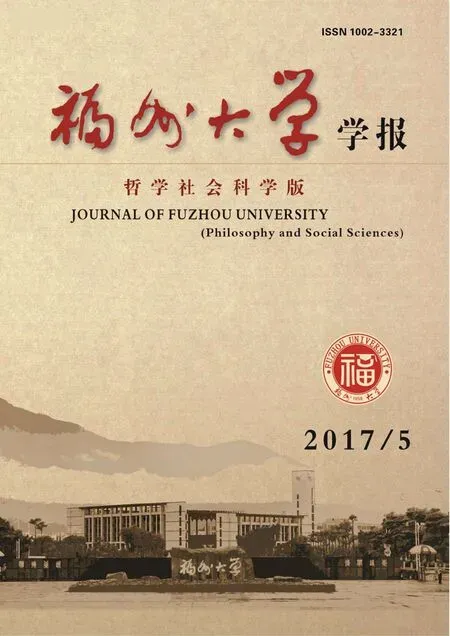杜甫五律的创变与特征
2017-04-04魏耕原
魏耕原
(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杜甫五律的创变与特征
魏耕原
(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五律是盛唐最为流行的诗体,也是杜甫写作最多的诗体。杜甫的五律创作在继承前代诗学遗产的基础上,对唐人既有的风格予以革新。主要表现为大量运用叙述与议论的手法,不以写景为意。同时,杜甫五律结构复杂多变。把五古叙事大篇与歌行体的开合纵横,施之于五律之中。因而,在盛唐众多的五律中,独出诸家之上,这也说明了杜甫兼擅诸体而能集大成的原因。
杜甫; 五律; 诗格风格
杜甫五律多达630首,比他的七律151首[1]高达4倍,不仅占其诗总数1475首的43.24%,而且在唐代诗人中为数最多。[2]由于杜甫七律名声最响,加上五古和歌行体与叙事的“诗史”相关,而且艺术性高,因而至今讨论五律者却寥若晨星。[3]其中重要原因是对五律体制原理与杜之五律如何突破而有创新,还不那么清晰。至于五律的特征,更需要进一步多方面关照。
一、五律中的“唐调”
五律是从齐梁新体诗发展而来,而新体诗建立除了声律的探究,逐渐形成规律外,其次就是以对偶作为主要手段,而表现的内容主要是山水、行旅、送别、酬赠、侍宴、应诏、咏物等,实际上是以描摹山水为主。特别是咏物描写细致精巧,风格清丽,也注意到了不同角度的配合。对偶的形式也较为多样,诸如动静、方位、颜色、山水、时态等,加上比喻的多用,风格清新生动,绮丽婉转。但由于前六句或前八句写景,只有末两句言情,景物繁杂,留给主观感情的空间狭小,也不在意于情感的抒发。加上偏居江南的压抑,缺乏宏阔的胸襟与高昂的理想,所以主观感情成了客观景物的附庸,缺乏深厚的思想内容,肤浅的情感与景物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其间谢朓的长于发端,阴铿、何逊对景物的提炼,庾信对感情的渗透,都对唐人五律起到不少的影响。
到了初唐,一方面对于齐梁芜杂写景予以“减肥”,统一强盛的时代给予诗人以高亢的情调,加上游历的扩大,无论胸襟眼光与感情的热烈都是前所未有的。题材增加,诸如登临、出塞、从军、寺观、思乡、怀人、闺怨、节令等明显有所扩大,即就是咏物也改变了以往的见物不见人的单调平庸,主观感情得到了很大的张扬。另外,对偶比前更为灵活多样,大量的流水对与跳跃性的对偶,更适宜于情感的发抒,还把前此的“比兴都绝”改变为有所寄托。无论内容与情感都显得较为深厚。加上“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形式的奠定,不仅具有齐梁的可观可读可感性,而且引人共鸣成了新的审美特征。王勃送杜少府本以言情为主,首联不过点明彼此两地,然兴象宏远,整密中有变化。尾联把散文一句话分为两句,为前此所罕见。至于颈联“海内天涯”的壮语,气骨豪爽。骆宾王《在狱咏蝉》颔联同样把散文一句化为两句,且为工整的流水对。物与人在纵横错综的结构中融合紧密,显示出五律的成熟。杨炯的《从军行》中四句全写景,颔联的“牙璋凤阙”“铁骑龙城”带有明显的装饰性,颈联的大雪蔽旗与杂乱的边声又视听结合,高华与苍凉互相渗透。加上首尾前叙后情,形成外疏内密结构。宋之问的《度大庾岭》结构亦同,中四句景物处处浸润情感,首尾哀婉,结构亦复同上,同样带有感情的张力。沈佺期的《杂诗》书写闺怨,中两联先为流水对,两句以“月”贯穿,后为倒叙摇曳生情,全诗委婉生姿。到了杜审言、陈子昂,以及张说、张九龄相与继述,而五律始盛。加上时君好尚,应制五律兴起,虽然内容雷同,兴象高远罕见,但对五律的促成与兴盛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律到了盛唐成为最为流行的诗体,而且诗人形成各自风格。高棅说:“李翰林气象雄逸,孟襄阳兴致清远,王右丞词意雅秀,岑嘉州造语奇峻,高常侍骨骼浑厚。”[4]题材也有增加,如观猎、寻访、田园、宫禁、题居、挽词、送人下第等。除了叙事、游仙等需要大篇表达者,涉及极为广泛。在写景、言情、叙事、议论中,前二者最为核心。五言句简洁,能突出景物的显明性,加上八句的限制景物不能繁多。而且句子构造灵活,主干突出,再经句与句跳跃,扩大了句数限制的空间,就显得凝练。比起七律显得明洁,同时也具有七绝言外之意的含蓄。对于五律的表现原理,时下论者说:“其主要特点是结构简单,便于大幅度的浓缩概括而缺乏叙述功能;立意聚于一点,避免古诗式的尽情陈述的创作方式,发展了思致含蓄、求新求巧的表现倾向,易导致格调的浅俗轻靡,多用于咏物、闺情、离别等主题雷同、内容单薄的题材。”其次“较少直白的抒情,而多用景物衬托,因而写景的对句成为新体诗的重要表现元素。”再次,“五律主要以实字造境,这就带来了这种题材的另一个优势:即五个字的安排组合可以突破五言古诗的语法逻辑,不按常见的语序组句。为了造境和立意的含蓄,在文字间留出更多的想象空间,五律往往追求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更大的跳跃性,从而离散文语言更远,所以在炼句炼字上比其他的题材要求更高,更便于表现出言外之意和味外之旨。”[5]这是迄今为止对新体诗发展为五律的主要特征最为详细周备的概括。杜甫五律正是针对表现原理“缺失叙述功能”的突破。以叙述为主体,不以写景为意,而且所叙述为当时大事,即以时事入律,使五律也成为适应“诗史”表述的体式。
杜集今存最早的五古《望岳》,中四句偶对写景,首尾虚写,外虚内实,是初唐以来最习见的五律结构,此为以律运古。结构之严整“已似五律”,为“古诗之偶对者”(吴瞻泰《杜诗提要》语)。《登衮州城楼》亦为内实外虚结构,首叙尾情,中二联景则由远而近,由大而小。无论章法结构,还是对偶整密,均中规中矩,只是末了言情的“多古意”“独踌躇”,有些浮泛,缺乏动人的深厚感情,犹如“少年维特之烦恼”,或如颜真卿的《多宝塔》帖,法度森整,用笔谨严,但不免有些“窘迫”,不够浑厚。《房兵曹胡马》与《画鹰》中四句赋物,前者起联还为对句,首尾前叙而后议,风骨凛然,语调高亢,气象峥嵘,且具寄托,均为早期名作,显示出开元时代赋予的蓬勃生气,充斥张力与弹性。即使比起王孟、高岑诸家,亦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夜宴左氏庄》前四句景物纤细,全首对偶,工致精雅。颈联的“检书”“看剑”又说得兴致勃发,景象静幽,带出豪纵自然的叙述,结构亦为一变,似乎把六朝鲜藻与建安的风发结合起来。胡应麟谓“五律仄起高古者”,“此则盛唐所无”(《诗薮》)。《春日忆李白》则为两截布局,前半称其才,而下半怀其人。起手“白也”“飘然”以虚词对起,气势不凡;“诗无敌”与“思不群”又是前果后因;颈联取掉动词显得坚实,且不说“清新”“俊逸”为论李诗之不刊之论。后半写景则两地共现,“春树”“暮云”即景寓情,不言怀人而缱绻之情尽注。全诗一气贯注,神骏气健,其人、其才、其神、己思、己评、己望尽融其中,洵为绝调。以上均为36岁与此前所作,已可看出杜甫五律水平已臻至“格调庄严、气象宏丽”的高度,而与时代赋予的诸家共有特征无甚区别,同时隐约看出自家的趋向,如用典与虚词偶对。但可设想,以杜甫这样多产者,升平年间诗少,而丧乱漂泊诗作剧增,真不可思议,是否忧时伤世才能引发诗兴,恐不尽然。看他在入蜀后写了那么多雨诗,固与当地多雨有关,而其中并无过多深意。所以,我们猜想,他在弃职赴陇的“一年四行役”中,或在此前困于沦陷的长安中,有所散佚。而且五律原本是对应举应试不可缺少的准备,已知杜甫就有两次考试,期间所作的五律肯定不少,而且从早期不多诗作看出,他是从五律起步的,如果推想不谬,对他“盛唐之音”的宏壮之作,会有更多了解。翁方纲曾言:“杜五律亦有唐调,有杜调,不妨分看之,不妨合看之。如欲导上下之脉,溯初、盛、中之源流,则其一种唐调之作,自不可少。”[6]所言甚是。不过杜之七律也有一分为二情况。以上五律即可谓之五律的“唐调”,至于杜之自家面貌,则在安史之乱后即杜甫45岁后方能出现。
此后杜之五律也有“唐调”,如作于沦陷之长安的《月夜》,起句平易。然鄜州与已所处以下长安对照;今之“独看”与设想将来的“双照”呼应。前四句真朴而亲切,后四句语丽而情深。因“心已驰神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浦起龙语),故“入手便摆落现境”(纪昀语),一切全在悬想拟设之中,由长安而至鄜州,再由鄜州飞翔到将来,有同时异地,也有同时同地,时空都在“月夜”中悄然转换。如此构思,很可能受到张说五律《还至端州驿前与高六别处》与七古《幽州新岁作》之启迪,但精密工致过之。如此之类“唐调五律”在以后亦有,然非居主体位置。杜之诸体都具有全方位的创革意识,起步早的五律尤其如此。他要大刀阔斧的对五律革新,走出一条自家的路子。
二、叙事与议论的介入
安史之乱对杜诗的转化有着巨大的意义,如何把升平时代题材转变为对丧乱的关注和叙写,如何把除了绝句以外的诗体去表现急欲诉说战祸乱灾,就是摆在杜甫面前的亟欲解决的重要问题。只要看看他在华州所作的七律《题郑县亭子》《望岳》其中所用的象征,就已经与前此的七律有些异样。特别是《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用了粗腔大调,把夏夜多蝎与秋后多蝇,都写进华贵的七律与矜持的对偶,而且还有“束带发狂与大叫”的粗嗓门,而与“薄书何急来相仍”作对,性质无异于破口大骂,形式则带有歌行体风味,比高适《封丘县》还要粗犷,甚至被前人判定“必是赝作”(朱翰《杜诗七言律解意》),正是追求异样的导致。如果和早期七律《题张氏隐居》《城西陂泛舟》相比,则有霄壤之别。实际华州所作三首七律是以质朴的白话对华贵诗风的强力革新,包括声调格律在内,此时的《望岳》即为第一首拗体七律,着力寻求一种从内容到形式创变,亦即“白话七律”开始创立的标志。[7]正缘于此,五古叙事诗《奉先咏怀》《北征》、三《吏》三《别》《赠卫八处士等》,都集中出现于一时,均出于同样的原因。于时,五律的革新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安史之乱前夕,所作《官定后戏赠》可以看出对五律革新的尝试。以自言自话语气说:“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用的是说话的语言,说明辞就之故。选择后者的原因是“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这才有了一点律诗的感觉。本志是致君尧舜,却做了看管兵器、门禁的小吏,所以说为了喝酒才须“微禄”,这是陶渊明做彭泽令的心情,对他来说是哭笑不得的自嘲。对句即“圣朝已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乐游园歌》)的意思。尾联的“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是说做了官就不能轻易回家,只能远望而已。全诗没有一句写景,只有满腹牢骚不吐不快。在结构上以首句领下三句为一截;第四句是上半的终结也是下半的过渡。啼笑皆非的诉说只好说是“戏赠”,赠是自赠,“戏”却是心底伤心而语气倔强。无论与王孟五律相较,还是与高岑对照,都是“别属一家”。即使与此前所作五律比较,亦迥然两样,因为以发牢骚为诗即以议论为诗,写景言情的思维方式自然就用不上了。
杜甫冒险逃离“城春草木深”的长安,投奔肃宗行在临时政府所在的凤翔,这次逃离奔窜要冒生命危险,时在肃宗至德二载(757)四月,年46,开始了以叙述为五律的创新。叛军占据长安将近一年,京华成了杀戮官员和皇亲子弟的场所,成了虎狼食人的巢穴。杜甫终于摆脱“胡骑尘满城”的处境,沿路经过艰难险阻。在《述怀》里说:“去年潼关破,妻子久隔绝;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当时危险至极,狼狈至极,到达凤翔后则兴奋至极。冒险的逃窜与喜达行在,本来可用的五古形式,采用叙事手法,表达这次重大的人生经历,他却选用了五律,叙述窜奔的艰险与来到行在的喜悦,以及痛定思痛的惊心。一来五律质朴简重,虽无五古伸缩自由,但却庄重凝炼;虽无七律错综畅达,但却亲切安恬。二来以叙述代替叙事,也就是以五律包揽五古叙事的功能。显然,他决心要做一次大胆的革新。简短的五律显然容纳不了这样复杂的内容与变化多端的头绪,而组诗选择就首当其冲。何况在天宝年间就有《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与《重过何氏五首》的五律大型组诗。有了这样的创作基础,现在的任务就是把擅长简明突出写景的五律,改为扼要的叙述,以完成这次危险而兴奋的特殊经历的叙说。
其一利用了律诗可以用一联为层次的形式,采用了逐层推进的方式叙说。这组诗是到达行在后作,故从未到达前说起,属于痛定思痛的回顾。首联“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西忆”的“西”是就所在长安而言,这句说天天希望西边的消息。次句为杂糅句,是把两句压缩成一句。是说竟没有人来,于是便决意逃出长安。“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西走前望落日,心急而望眼欲穿。其间“落日窥行人”(贾岛句)的提心吊胆,兵荒马乱担惊受怕,到了“心死”的地步。还犹望使寒灰复燃,在破灭的希望中还求一线生机。“连山望忽开,雾树行相引”,从长安至凤翔数百里,非一日徒步可达。此言夏日晨雾中的树一来如引导,二来也好隐蔽。近午雾退山貌显现,“忽”字传出喜出望外的心情。“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赶到行在,亲近者看到他还能“生还”,惊叹:老啦,瘦了,辛苦了,从“贼中来”多不容易。这是用问候的对话交代已达行在。以上以无讯思归,一路担惊受怕,早行晚止,到达行在的顺序,一路叙说而来。中两联心理与景物之描写,意在于叙述历程种种的艰辛。末尾则采用了五言古诗的对话,这在五律极为罕见,所有叙述连接一片,不仅具有叙事的功能,而且是亲切感人,凝练含蓄,而符合五律应有的特质。
其二接言到达后的欣喜。上四句说:“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愁思”领起四句,前二句回思沦陷长安的凄凉,后两句倒叙归途的艰险,当时由僻静小路奔窜,随时都有生死之危,只有到达后方知还能侥幸“生还”,此为欲抑先扬的顿挫,痛定思痛,真有些后怕。下四句言归来的喜悦:“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先说到达行在,见到大唐中兴的新气象,以刘秀光复汉业喻肃宗政权。后言中兴有望而喜极反悲,歌哭无端。终于盼到大唐有望,翻喜为悲则又为一顿挫。“其悲其喜,不在一己之生死,而关宗庙之大计。”[8]既属追思,故用回顾叙述语,倒叙与典故的化用自然精切,情感发抒得波澜起伏。其三仍是回思,基本是上首的重复,但脱险还是够激动的,值得再次回味叙说。发端“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单看似突猛,然是对上首“间道暂时人”的呼应,为再次回思而有“凭谁报”的感慨,此句就成了议论。次句言当时“正当困辱殊轻死”,急急奔窜尚当不及生死之顾,“生还”后方知死里逃生之不易,此与“已过艰危却恋生”[9]属于同样心情。这是“过来人”的情感。次联说:“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犹”字贯下两句,“喜”呼应上首末联之“喜心”。“太白积雪六月天”为周边州县流行今日的俗语,还能远瞻,此是一喜;又还能喜遇“武功天”,又是一喜。很有些今日红色歌曲中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般的高兴。复见天日又怎能不“喜”。颈联“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这是“涕泪受拾遗”作为近臣的兴奋与安适。当时肃宗草创之际侍臣不过三十,这又是兴奋的夸张。“影静心苏”正对“眼穿心死”,喜悲转换。被王夫之谓为景中有情,“自然是喜达行在之情”[10]。这两句实在是叙述,叙述生动即有景观。“苏”字用得极好,“心苏”犹言心舒,安恬。着一字而情味顿出。末尾的“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此亦为全组诗总束。同时“用光武事比肃宗,昔欲望一信而不得者,今亲见之,不觉喜极而泪下矣”[11]。
这组诗全用叙述,情事交错,感慨淋漓,对话、写景、心之惊喜、全都用叙述语气。又分别以心死、心喜、心苏为脉络照应,中心是“喜达”却反复叙说间关危苦惨惶情状,“言言着痛,笔笔能飞”(浦起龙语)。所谓“笔飞”即言非用描写,而用简括叙述,故每首每联处处跳跃,这正是叙述的魅力,也是杜甫革新五律的成功之处。再者:事分途中与到达,本可两首交代,而次首对前后两首的再叙,正符合反复诉说需要,而用语绝非相近,且次第深浅不同,如次首颈联与第三首结尾,一是“初睹”,一是今朝为拾遗之后。五律庄重简洁,直质亲切,还有安恬委婉,都可以感受到。特别是简洁,“他最能用极简的语句,包括无限深情,写的极深刻”[12],单就此而言,这三首也是高作。
作于与上诗同年的九月《收京》,叙述的是当时一件大事。杜甫在鄜州探家,因在凤翔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后来便诏放探家,这时心情郁闷。此诗全靠传闻,而且事涉玄、肃禅让的复杂敏感的背景,以及大封功臣,万方送喜所潜伏的隐患,因而用了很多典故,指向隐晦,所以前人歧解纷纭。其中亦有讹传而误记,如其二的“忽闻哀痛诏”“叨逢罪己日”,其实肃宗汲汲宣布的诏书是极力张扬“亲总元戎,扫清群孽”,又“今复宗庙于函洛,迎上皇于巴蜀”,并无“哀痛”更无“罪己”。所以比起亲历艰辛喜达行在的组诗,叙述就不那么生动感人了。
杜甫常把叙述与议论结合起来,其效果和把叙述与言情的合构是同样的感人。忧时伤乱之作常有此类之作,《岁暮》便是其中佳制。前四句为叙述:“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年之将近还为“远客”,是因中原丧乱所致,然即边隅僻地却有吐蕃之乱,哀感中有“四海十年不解兵”(《释闷》)叹息,把可以写景的“雪岭”“江城”,派作战乱的叙写。代宗广德元年(763)岁末吐蕃攻陷雪岭附近的三州,使川蜀震动。杜甫时在嘉陵江边的阆州有《岁暮》,后四句为议论:“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此年春安史之乱刚刚平息,而战乱仍然不绝。“日流血”冠以“天地”,漫长而广阔的时空充斥兵祸战灾,然朝廷却无人挺身以救危难。这两句跌而又跌,欲抑先抑,表示绝大的遗憾与忧愤。末了反问与感慨回振全篇,“寂寞”与“壮心”硬接组合,耐人寻味。又以“惊”字结句,济时无路的愤慨一点便醒。梁启超说:“工部写情,往往愈拶愈紧,愈转愈深。像《哀王孙》那篇,几乎一句一意……他的情感,像一堆乱石,突兀在胸中,断断续续的吐出,从无条理见条理,真极文章之能事。”[13]这是就整诗而言,而有时一两句也有这样的特色,如此诗末联就有这样的特点。它如《捣衣》发端的“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打头的“亦”字没头没脑,实际上“因为已撇过许多话,许多痛苦才说出来”(萧涤非《杜诗选注》),这没说出的“许多话许多痛苦”便是它的前题。《病马》的“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也是把许多话压缩成两句,“从无条理见条理”。《秦州杂诗》其七的“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多”,说出来的不少,没说出来的更不少。
咏物诗《麂》意不在物的描绘,属于借题发挥。故代物以言:“永与清溪别,蒙将玉馔俱。无才逐仙隐,不敢恨庖厨。”“蒙”字用得幽默,似乎承蒙拔擢离开清溪,登入“玉馔”,把愤恨的话说成谢词,热语包涵的是冷意。鹿是仙人的坐骑,麂是无角的鹿类,故谓无才跟随仙人隐去,以致让厨师宰割。这两种语气伸缩,属于因果关系,此属叙事与心理刻画。语气委婉的原因是出于欲抑先扬的顿挫,流水对的自然,好像无怨无悔,因厨子只是烹调,享用的却是衣冠大人。下半借此发为议论:“乱世轻全物,微声及祸枢。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乱世摧毁一切,不以活物生命为意。因麂肉略有名声故遭捕杀,这两句转到议论,暗指乱世则人命危浅,鱼肉百姓。末二句说王公大人外似官员,实则盗贼——与叛乱的军阀没什么两样。这是代麂痛骂,如此戟手詈语的愤怒,也是受尽战乱祸害的民众的愤怒。咏物不用赋笔描写,带有寓言性质,全为麂在“说话”。同时的《鸥》《猿》《鸡》《黄鱼》《白小》均不作物体本身之描绘,均为托物寓意,主要叙述动物的各自特征,以显示所寄托的用意。可以看出是对初盛唐以描写物体为主的比兴的思路更张。然物象明显不足,主题大于物象,生动不足,比起《房兵曹胡马》《画鹰》《花鸭》以描摹加上议论或言情,就有所逊色。后期大量的咏物诗均属在牝牡骊黄之外的叙述议论,而只有部分诗结合恰切者,如《孤雁》等。从总体上看,毕竟为咏物诗开创一个新局面,且对中唐与宋诗影响甚大。
三、五律之特殊结构
前人论及杜甫五律,都很看重律法的变化。如“杜公律法变法尤高,难以句摘”(高棅语),“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变幻,不可端倪”(胡应麟语),“独辟畦径,寓纵横排奡于整密之中”(沈德潜语)。杜五律之变包括各个角度,其中结构“错综”“纵横”是主要的方面。
对于杜律结构,清人投入极大的兴趣与力量,如仇兆熬、浦起龙,以及黄生《杜诗说》、吴瞻泰《杜诗提要》等,都有精切恰当的分析,但限于学术的传统规模,均属随篇而论,对整体结构规律虽有感悟,而缺乏梳理。而现时论杜诗者虽众,然注目于此者,仅见赵谦一文孤明先发,从比兴、客观、双线、绾连、比较、意象角度归类,运思精密,全面细致。[14]然还值得进一步思考。
杜甫五律结构以上景下情或议论为常调,或首联叙述,中两联为大小景,末联言情,这也是初唐五律以来的基本格局。也有全为写景或全不写景,不涉情景纯出叙述与议论的布局构架。或采用情景相间的跳跃式结构。如《送贾阁老出汝州》:“西掖梧桐树,空留一院阴。艰难归故里,去住损春心。宫殿青门隔,云山紫逻深。人生五马贵,莫受二毛侵。”贾至为中书舍人,中书省在月华西门,故从写景入手,言人去地冷。贾至坐房琯党贬,在当时是敏感的事。“艰难”表面指跋涉,实指仕途不幸。时在春天,彼此伤心,“损春心”指别时,亦深意存焉。汝州在河南,贾为洛阳人,可便道看家。同样也是对贬汝的婉言。以上是惜别。青门为长安东门,紫逻山在汝州。两句说一出东门,宫殿就看不到了,这是回头看;向前看汝州还在远处,此借景言惜别。五马为刺史的代称,故末言人生为地方长官亦为不贱,勿因犯愁发白。虽为慰言,实则抱恨不能明言,故作惋惜抚慰之词。此诗没有按照前叙、中景、后情的格局,而是先景后情、再景再情,景与情结合更为紧密,使全诗皆为惋惜之词,结构也跳宕灵活。按内容分则前六句惜别,末为安慰,眉目亦为清晰。浦起龙说:“起联破空而来,绝奇。他人用作落句,则常调矣。”[15]也感觉到结构的异样而不同于一般格局。
《长江二首》其一亦同此结构,起联先出之景:“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先言其水其地之险。接以议论:“朝宗人共挹,盗贼尔谁尊?”言人心向唐,如水趋之一门,叛乱军阀是会失去人心。然后再跳接首联瞿塘描摹:“孤石隐如马,高萝垂饮猿。”此言江水暴涨则难以乘舟而下,而垂饮之猿鸣必引人伤心,而掀动归思。故结言“归心异波浪”。难归而欲思归,滋生“何事即飞翻”之急想——怎样能生翅而飞回家。黄生认为“是八句全对格”,从景实情虚看,又是“虚实相间格”即景与情或论相间。又言:“前后语意若两截,其实‘归心’跟‘朝宗’字,‘波浪’应‘众水’字,章法仍紧关合,此皆公之律髓也。”[16]此诗写景把江水与孤石分写,景情间隔,虽就“朝宗”“归心”分言,脉络暗通,所谓“骨髓”即结构别致的精彩处。《别房太尉墓》则以叙述与写景间隔,而与上二诗先景后情或议有微调:“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惟见林花落,莺花送客闻。”首联叙别墓,次言哭墓融于景中,再叙过去对棋,言平昔密切,顺带出房之为相;“把剑”句以季扎挂剑徐君坟树,言死后不忘之谊,此为叙而带情。末以花落见孤坟寂寞,以只有莺啼送客陪衬别墓之孤独。“言下有‘叹息斯人去,萧条天地空’之感,结语拈景设色,而弥形其悲。”[17]这是以景结而有言外之意。而“一身做客之难,朋友相与之情,而名宦生前没后之德诣凄凉,无一不见”[18],这是叙景相间包容甚大的效果。总之,情景相间或叙景相间,不仅把不同景与事并置一诗,而且具有更多的容量,扩大了五律的有限空间。特别是情景或事景配合紧密自然,既打破以往景情各半与首尾叙与情而中间集中写景的格局,以情景相间的跳跃,显得更为机动灵活。其他如《季秋苏五弟缨江楼夜宴……》《陪裴使君登岳阳楼》等,均属此类。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倒叙结构,本是由此及彼,却先言彼而后言此。或是先言所观,次言行止;或先言结果后言原因,章法倒卷,矫变异常。代宗大历二年(767)在夔州入秋而追忆长安,凡作八首每篇以首二字为题,实为组诗,而与《秋兴八首》相近。首篇《洞房》前半先叙长安玉殿秋风,旧宫月夜凄凉,天宝玄宗龙池今不复睹。后半言羁舟江城,同是月夜,不觉魂飞泰陵,想起玄宗园陵月夜白露之冷寂。结构参差开合,斡旋成章,先出之遥想,再回到所处之地之夜。杨伦谓之“倒格”。“以前半意翻叙于后,颠倒互易成篇”(黄生语)。先把所想写在前边,能见逼真;再把所处见之于后,能见感慨。若按顺序,两种效果就会减弱。湖湘所作《湘夫人词》,前半言祠庙空墙,唯对碧水,玉佩已生苔薪而虫行痕迹如篆,翠帷尽落尘土而又为燕泥所污。下半才说“晚泊登汀树,微馨供诸苹”,言泊舟登君山,借岛渚水苹以达微敬。最后的:“苍梧恨不尽,染泪在丛筠”,点明二妃泪下,至今泪染丛竹。此诗没有夹带议论,而感慨尽在先倒叙的荒寂祠景中,这也是采用倒叙的原因。《空囊》则属果前因后的倒叙结构:“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此诗作于最艰苦的秦州时期。餐霞食柏是神仙的生活方式,对袋中无钱的杜甫则是无食的幽默自嘲,浪漫话透出坚毅的个性。颔联则出以庄语:世人以求苟得,好歹只要活着,我却不愿如此不分是非,那囊空无食也就自所难免。此与陶诗“世人皆得宜,我生失其方”语近。以上为无食而生理艰难。下言饥寒之忧,无粮故灶下无火,也用不上打水,无衣则床被之薄寒可知。钱袋空空,一有急用怕人见笑,硬是留下一钱做个家当。这也是穷开心的话。至此明白其所以要食柏餐霞而是因生理艰难,原因是穷极了:无食无衣又无钱。黄生说这诗的“结语本属起,转联(颈联)本属接联(颔联),前半本属后半,章法倒换”[19]。按逻辑顺序,应如黄生所言。如此倒叙先以柏霞可以疗饥自嘲自笑,然后才说出吾道维艰在于饥寒交迫。末了还要以囊之不空来写“空囊”,又是一番自戏自谑。倒叙是为了打埋伏,增加自嘲意味,这正是结构反顺为逆所取得的效果。若顺说,只是质直说穷而少诙谐,而诙谐语正是悲酸语。
还有一种倒叙把过去和现在倒置,形成昔盛今衰的对比,感慨不已,意余言外。如《滕王亭子》:“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复行。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鸟雀荒村暮,云霞过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骑把霓旌。”前六描写今日之荒凉,结二句突入昔之兴盛。以“尚思”使今昔接榫,“过客情”又带出“尚思”,即谓今之鸟雀即昔之歌吹;此时之云霞,即当日之霓旌,前后映带,使过客情起而感慨。末了以倒叙结尾,其味深长。如果一味直写今日荒凉,那么,“前六句凄凉已极,再以衰飒语结,意兴索然。七、八忽用丽句追溯盛时,翻身作结,力大思深,奇变不测”[20]。其实颔联的“犹”“自”已隐隐透出古墙竹色依旧,虚阁松声还似当年[21],而与“过客请”与“尚思”脉络暗通,这正是杜诗结构精密的地方。
再次,杜甫五律还异于常态的结构,布局奇峭,适用于种种特殊题材,发抒异于常情的心绪,风格冷峻凄凉。如《对雪》不言雪而劈空突来“战苦多新鬼”,以下写独愁,独吟乱云急雪,飘弃炉冷,枯寂愁坐。此在沦陷之长安哀伤陈陶、青坂之败。首句的背景即《悲陈陶》的“孟东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对雪愁吟即为此而叹。吴瞻泰说:“题是《对雪》,突然发‘新鬼’一句,若与题全无涉。妙在此句不即接,只将老翁独吟情景分二联,至七句始徐徐一应,所谓急来缓受也。不然,起句陡甚,又复急接,则章法太促,全无离合。”[22]简而言之,此为1∶7结构,即由少与多构成,后七句在脉络上全与首句有关。结构的不平衡,正见出心里苦痛之失常,悲哀之难奈。另外一种则以首句为发源地,以下全从此生发出来。《月夜》首句“今夜鄜州月”引发闺中独看,又推拓出儿女之不思之忧,衬出空闺中独思独忧,以至发湿臂寒而不知。然后由分离之今夜推想到将来相聚之月夜,处处回应首句,处处从“鄜州月”引发出来,彼此交映,亦属1∶7结构。这种结构在杜甫七律中多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为著例。这种结构打破了律诗以联为层次的原始状态的封闭性,使结构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于是可以“寓纵横排奡于整密中”,可以使复杂感情或意料不到的事情,以错综变化的结构,表达得更为伸缩自在,而扩大五律有限的空间。
此类1∶7结构,杜甫五律见多,可分两类,一是如上所言为表达特别痛苦心情;一类属于艺术上特别处理。前者又如上文已及的《对雪》,劈头突发“战哭多新鬼”,似与题目全然没有关系,接亦与首句不承。至中四句才说到面对“乱云急雪”,接只写出老翁与雪独吟情景,至第七句“数州消息断”。首句则为对陈陶惨败的提动,为全诗之背景,故先行点明,以下哀愁全为此发。《宿赞公房》以发问“杖锡何来此”开端,问得无端而诧异,以下却不径直回答,只写院内荒景,至第五句“放逐宁违性”以句首两字轻轻带出。《捣衣》开头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亦知戍不返”,以下全就题叙写,首句似乎很“孤零”。实则此句前蓄有深意:“望归而寄衣,常情也;知不返而必寄衣者,至情也,亦苦情也。安此一句于首,便觉得通篇字字是至情,字字是苦情”[23]。为了表达如此特殊“苦情”,独立出首句,就特别必要。《秋野五首》其三发端突来一句“礼乐攻吾短”,即放下不管,以下由“山林引兴长”引出帽歪、曝背等懒散行为,以及收松子、割蜜、山林赏花,实际是对“礼乐”世法的反唇相击。1∶7结构使绷紧的激昂更具张力。属于第二类的如《房兵曹胡马》,乍看应是“上半写马之状,下半赞马之才”,然首句“胡马大宛名”是写马之来历,以下方是分别言其状与才。即虚笼一句,引发下文。此为早期所作,对后来的五、七律影响较大。再如《客旧馆》首句“陈迹随人事”开门见山直奔题目,以下却从“初秋别此亭”说起,引发“重来”所见景况。回看首句则属“单提通首”。《左宿春省》首句“花隐夜垣暮”,写“春”只此一句,以下七句全都写“宿”,以宿而“不寝”见出恪尽职守。其他如《一百五日夜对月》《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四员外绾》《遣怀》(“愁眼看霜露”)《苦竹》《赠别郑炼赴襄阳》《巴西闻收宫阙,送班司马入京二首》其二等,均属此类。
把1∶7结构倒过来则为7∶1,一般用来借彼言此,以深化主题。如《除架》前七句叙写秋至瓠叶零落,虫与雀有炎凉之感,末了突发一句“人生亦有初”,谓瓠之始盛终衰,而人的一生也有这样的情况,此为杜甫居陇最艰苦时的感慨。这末句就很耐人寻味,也使人很感慨。此种结构是6∶2布局略加变化而来,而后者则是杜甫五律结构的大宗,前边写景或议论,末二句则结以时事或思归,以夔诗居多。在7∶1结构基础上再加变化,可以出现多种形式,如《更题》,题目是就前诗《夜雨》的再题诗,以足前诗“天塞出巫峡”离夔未尽意而申言,前半说巫山多雨让人心情不快,决意出峡“发荆州”。后半接言忽然说到“群公苍玉佩,天子翠云裘,同舍晨趋侍”,与群公同舍共觐至尊。动起归朝之念,此为所想,属于第二层。末句却言“胡为淹此留”:谓同舍皆在朝廷,自己何必留在此地。此为怪叹之词,自问自嘲,旋转一篇主意,如截奔马,斡旋有力。此诗则呈4∶3∶1结构,则为通首单结。
还有把1∶7结构再加变化,而成为1∶5∶2布局。《铜瓶》先突起一句“乱后碧井废”,然后却追溯升平“时清”时“未落水”再叙写到沉落井底。结尾又说到铜瓶流落人间,瓶上金饰蛟龙剥落,还能换取“折黄金”。以一铜瓶悲叹大唐由盛转衰,由一小小题目关涉到大主题,就是与在结构上把今与昔几经倒置有关,以1∶5∶2结构旋转出一番大感慨。《雨四首》其四首联“楚雨石苔滋,京华消息迟”,京华消息与雨滋苔生互不干涉,次句撇开首句,使人不能预测。以下五再写“山寒”“江晚”的凄寂,暗承首句。尾联言“繁忧”而雨多,分别回应首联。就构成1∶5∶2结构,把阴雨中的担忧国事的烦乱心情,很有波折地发抒出来。
杜诗五律早年先行,而且多有名篇,对初盛唐先叙后景再颂圣或言情的应制诗2∶4∶2的结构模式,率先予以大刀阔斧更张。在结构处理上,或根据感情的起伏变化,或为了突出主题,或为了集中笔墨突出中心,或相题制宜,极尽变化之能事。在盛唐众多的五律中,独出诸家之上,亦与结构多变有关。其所以成功的原因,当与把五古叙事大篇与歌行体的开合纵横,施之于五律之中。这也说明杜甫兼擅诸体而能集大成的原因。
注释:
[1] 据浦起龙《读杜心解》两体各卷统计数字合计。
[2] 孙琴安说:“我们统计了唐代所有诗人的五律,没有一个人的数量能超过杜甫。白居易是唐代今存诗最多的诗人,五律也不过四百一十余首,尚不及晚唐诗人齐己。齐己五律为四百六十余首,数量仅次于杜甫。这就是说,杜甫是唐代创作五律诗最多的诗人,为唐人之冠。”见孙琴安:《关于杜甫五律的评介问题》,《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第4期。
[3] 近三十多年相关研究主要有1.金启华:《论杜甫的五律》,《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又收入所著《杜甫诗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其主要按杜甫创作的五个阶段论述。2.赵 谦:《杜甫五律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功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分起兴、客观、双线、绾连、比较、意象连接结构,分析审美功能。3. 孙琴安:《关于杜甫五律的评介问题》,《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第4期。孙琴安文从风格梳理六种,并指出较多数量的原因,以及谓王、孟、李以古入律,杜则格律细密严谨。4.葛晓音:《杜甫五律的“独造”和“胜场”》,《文学遗产》2015年第4期。葛晓音认为五律句序灵活,跳跃性强,炼字炼句要求高,以写景为体段,容易造境,故主要从写景造境功能的拓展与穷理尽性的表现深度方面讨论。
[4] 高 棅:《五言律诗序目》,《唐诗品汇》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06页。
[5] 葛晓音:《杜甫五律的“独造”和“胜场”》,《文学遗产》2015年第4期。
[6]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7] 魏耕原:《杜甫白话七律的变革与发展》,《安徽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8] 吴瞻泰:《杜诗提要》,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154页。
[9] 此句出自韩偓《息兵》。说见萧涤非:《杜甫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79页。
[10] 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50页。
[11] 吴见思:《杜诗论文》,见萧涤非主编:《杜诗全集校注》第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第829页注4。
[12][13] 梁启超:《情圣杜甫》,见陈引驰编:《梁启超学术论著集(文学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9,324页。
[14] 赵 谦:《杜甫五律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功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9期。
[15] 浦起龙:《读杜心解》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1页。
[16][19][23] 黄 生:《杜诗说》,《黄生全集》第2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1,218,214页。
[17] 李因笃:《杜诗集评》卷九,见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第6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123页。
[18] 赵兴海:《杜解传薪》卷三之五,见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第6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124页。
[20] 黄 生《杜诗说》引吴东岩(瞻泰字东岩)语,《黄生全集》第2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2页。
[21] “自”与“犹”对文义同,参见魏耕原:《杜诗习见词诗学与语言学的双向阐释——热点词“自”的个案考察》,《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22] 吴瞻泰:《杜诗提要》,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150页。
2017-01-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项目(13FZW059)
魏耕原, 男, 陕西周至人, 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I206.2
A
1002-3321(2017)05-0062-08
[责任编辑:陈未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