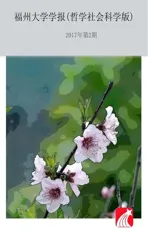语言·叙事·黑人性
——帕西瓦尔·埃弗雷特小说《抹除》之解构主义阐释
2017-04-04吴晨倩张晓红
吴晨倩 张晓红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深圳 518060)
语言·叙事·黑人性
——帕西瓦尔·埃弗雷特小说《抹除》之解构主义阐释
吴晨倩 张晓红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深圳 518060)
美国当代著名的黑人小说家帕西瓦尔·埃弗雷特的小说《抹除》是一部具有典型性自我意识的小说,该小说通过多元变化的叙事策略以及戏拟的手法对小说的语言、传统的叙事模式以及类型化的黑人形象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在小说中,语言与意义、作者与文本、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得到重新解读,并展现了埃弗雷特具有解构主义思想的创作理念和种族观。
《抹除》; 帕西瓦尔·埃弗雷特; 解构主义; 叙事模式; 种族观
出版于2001年的《抹除》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黑人小说家帕西瓦尔·埃弗雷特(Percival Everett)最受人称道的一部作品。该小说入围了当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十佳小说之一,且荣获了2002年的赫斯特/赖特遗产奖。《抹除》是一部颇具实验色彩的小说。在小说中,帕西瓦尔·埃弗雷特与文学艺术传统开展了一场解构主义批评式的对话,话题涉及种族,小说形式的修正和消除、删除与替代,探讨了语言与意义、作者与文本、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
一、《抹除》对传统语言观的解构
书名《抹除》(Erasure)即可见出埃弗雷特的解构主义意识。所谓抹除,既可以是擦除痕迹的行为或例子,也可以是痕迹被从纸张中擦除后的踪迹或记号,它包含着抹去和保留的双重含义,是解构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按照德里达的观点,“抹除”是一种“在删除号下写作”的行为,具体而言,就是在某些关键性的词语上加上一个删除号X。据德里达解释,删除号“是切断所指同能指间的联系,使人看到符号,却不必去想它所表征的概念。[1]这里,能指和所指这两个二元实体所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被解构了。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语言是一个由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构成的稳定统一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符号系统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意义的产生取决于语言系统内部符号之间的差异。然而德里达却认为,这样稳定整体的符号系统并不存在,由于符号的意义总需要借助语言中其他符号来规定,所以能指背后总是指向另一个能指,意义不断被推延,所指成了一种空想。小说《抹除》的标题所要表明的正是这样一个意义缺失,永远处于不确定之中的漂浮能指。但正因如此,小说标题也成了一个开放的场域,提供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
在小说的开篇部分,主人公特娄涅斯·蒙克·埃利森(以下称蒙克)在一次新小说学术会议上报告了一篇以戏仿罗兰·巴特著名的文论《S/Z》为特色的实验性学术文章《F/V》。这篇颇具解构主义色彩的文论表明了多元批评的可能性和意义的多重性。繁复深奥的《F/V》探讨了《S/Z》中作为主体的S和Z的概念。“显然,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在构建其主体时,就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文本本身实际上就是主体。但《S/Z》告诉我们,文本本身当然不是主体,其主体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形式,而萨拉辛可以被视为是这种形式的表征。”[2]在巴特的文论中,充满象征意义的标题S/Z暗含了否定、消除、解构的意味。根据巴特的解释,S是Sarrasine 萨拉辛的首字母,Z是Zambinella赞比内拉的首字母大写。至于斜线“/”,它具有多重的意指功能“它是表示删除的斜线,镜子的表面,幻觉的墙,对照的边界,界限的抽象,能指的倾斜性,众聚合体的定位标志,因此亦是意义的诸如此类。”[3]
蒙克认为,“/”这个空洞的能指符号,既分割了字母“S”与“Z”,同时又是这两个字母的链条。它代表了萨拉辛和赞比内拉之间既区分又相互渗透的关系。而且“S”和“Z”之间处于书写符号的相反方向关系中,就如同一个字母自镜子对面看过去呈现出的样貌。这种对照关系,其实也体现在叙述者蒙克和作者埃弗雷特中,呈现为蒙克/埃弗雷特之间既互相区分又同为一体的关系。在小说中《F/V》是身为创意写作和文学理论教授的蒙克撰写的。但实际上,这篇《F/V》却是同样身为大学教授的作者埃弗雷特本人于1999年创作的同名学术文章《F/V:评实验小说》。那么究竟是谁在分析《F/V》中的主体问题?是作者?还是主人公蒙克?此时叙述主体蒙克与作者埃弗雷特似乎融为了一体。当蒙克在报告这篇文论时,实则是作者埃弗雷特本人在重现自己对巴特文论的解读。而这里,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又被重新强调了,作者作为一种话语和语言的功能并没有消失。通过对主体的消解以及解构了在《F/V》中探究主体问题的作者身份,埃弗雷特向我们揭示了个体在定义主体而完成语言意指过程中的影响作用。
埃弗雷特对语言的解构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主体上,而且还体现在词语的定义上。在探讨语言交流背后说话者主体性问题时,埃弗雷特通过蒙克之口声称,说话者的意图是无法完全定义词语的意义的,词语的定义不是固定稳定的,而是捉摸不定的,“一个句子能被理解简直难以置信。句子不过是一连串的声音罢了,是说话者想要意指某事物时的发音行为,但句子意义本身不需要也不会框定在那个意图之中”[4]。在蒙克看来,听话者对言语的理解是相当主观的,其所理解的意义很可能会不同于说话者所要表达的意义。也就是说,言词与其主体的思想意图是分离的,就像语言符号系统中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断裂一样。语言主体所发出的只是一连串符号,而符号的意义又不存在于本身之内,其意义的产生必须依靠语言客体的理解和阐释,但因为语言客体的阐释又带有主观性,通过言词而获得的理解又可能产生新的意义问题,所以就不再存在所谓唯一一致的确定意义,而是存在多种意义的可能。蒙克通过对比四个相似的陈述句继续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他将视角聚焦在这些句子中动词意义的差异上并探析了这些差异的产生如何依靠读者、听者以及说话者之间的理解和认识。他写道:“我时常盯着镜子,脑中思忖着这些陈述句间的差别所在:(1)他看上去有罪(He looks guilty)。(2)他似乎有罪(He seems guilty)。(3)他显得有罪(He appears guilty)。(4)他有罪(He is guilty)。”[5]
蒙克列出的这些句子,其意义模棱两可,充满歧义,因为这四个句子所使用的动词包含了多种含义的可能。“他看上去有罪”就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福柯曾指出,“动词最终指定的是语言的表象特征,是在思想中有一席之地的事实,即能穿越符号的边界并向符号提供基础的独一无二的词实际上只是达到了表象本身。”[6]因此,在福柯看来,动词的功能就是语言存在的方式,即是说,言语就是借助符号进行表征。动词“看上去”可指主语通过面部表情、行为举止或动作姿态表现出有罪的倾向。“他似乎有罪”这一陈述比第一个句子更加含混,动词“似乎”既可指视觉的因素,也可指非视觉因素如语音等让信息的接收者产生他有罪的印象。“他显得有罪”与第一个句子一样其意义的不确定性在于质疑了致使主语显示出负罪的具体表征。尽管动词的差异区分了不同句子的意义,但由于词语本身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歧义性,又导致了这些句子意义的不确定。罗兰·巴特就曾表示,意义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或一次性给定的东西,它只是作为“闪烁”不定的东西及种种可能性而存在。[7]通过对四个相似句子的考察,蒙克表达了他对意义一致性和确定性的深刻质疑。在蒙克看来,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和解构本质使词语产生“言此意彼”的效果,人们很难通过言语来获得对世界的正确理解,恰如阻隔在S/Z之间的那条斜线,语言和思想(意图、概念)、语言和现实之间总是横亘着一道无法逾越的栅栏。语言永远都会是传情达意的障碍,即便是通过语言表达了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因无法得到正确理解,最终以误解收场。正因如此,任何语言的表述都会产生歧义。
小说中虚构了这样一段对话,著名历史人物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问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一个令人费解的谜题:
维特根斯坦:巴赫为什么要卖了他的器官?
德里达:我不知道,为什么?
维特根斯坦:因为他很巴洛克。
德里达:你是说因为他创作的音乐被打上了华丽典雅、怪诞离奇的标志?
维特根斯坦:嗯,那不是我理解的。这不过是关于词语的游戏而已。
德里达:哦,明白了。[8]
这段难以捉摸充满喜剧色彩的对话以风趣幽默的口吻对语言表达思想、揭示现实本质进行了调侃和戏谑。埃弗雷特在这里对语言“自身”意义的确定性进行了拷问,他有意让读者意识到语言不过是词语的游戏,是一系列任意符号组成的漂浮能指,我们的语言不可能真实传达说话者的本意,在使用的过程中,语言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正如斯皮瓦克在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擦除下的书写正是对语言形式的一种曲解。”[9]
二、《抹除》对传统叙事形式的解构
此外,小说《抹除》还对小说的叙事形式进行了解构。《抹除》是一部具有明显自我指涉和元小说特征的作品,在小说中埃弗雷特采用了故事嵌套故事,文本内含文本的中国套盒式叙事结构。一开始小说就采取日志形式进行叙述,主人公蒙克开门见山地向读者宣告,“我的日志是比较私人的事,我不晓得我哪天会死。我又不处理这些内容。可不幸的是,考虑到个体总有一天会走向终点,(为此),我因其他人会看到这些内容而感到忧心忡忡。”[10]作为日志的写作者蒙克担心有一天他的日志会公开于众,可事实上,日志却已经以《抹除》为名出版。那么到底《抹除》是虚构的小说还是蒙克的日志?作者的受众会将《抹除》视为一部虚构的小说作品,然而叙事的受众则可能根据主人公蒙克在小说开篇的那段自白式声明而确定这本小说是蒙克的日志,且认为日志中的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一歧义之处的可能结论是小说既为日志,同时又作为小说。大卫·赫尔曼写道:“故事世界里的参与者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同时既为叙述的主体又为叙述的客体。”[11]根据赫尔曼的理论,蒙克既为创作日志的主体又是埃弗雷特小说书写的客体。此外,小说的叙事也体现了德里达“抹除”的概念。小说一反传统的线性叙事手法,采用碎片化的零散叙事策略。《抹除》的故事由几条线索贯穿,日志主体讲述了蒙克在其整个写作生涯中,看着自己的家庭分崩离析,他做医生的姐姐被反堕胎活动家给杀害致死。为此,他不得不搬到华盛顿照顾犯有老年痴呆的母亲。与此同时,日志还以倒叙的形式描述了蒙克对其父亲的回忆、对家庭生活场景、清单、信件(如在他父亲的私人文件中发现的信件)的回忆。作者把这些回忆穿插到描写叙述者的爱好(钓鱼、木工)、叙述者对小说的看法、对电视节目的评论,以及沉思的段落中。同时,小说还穿插了多种文类碎片包括小说笔记,自传,哲学思考,著名画家与哲学家之间的想象性对话。这些段落违背了传统的文学惯例,颠覆了以往小说故事连续性、封闭性与完整性的传统,使得非学术的读者感觉难于理解,例如著名艺术家罗斯科和雷乃之间的对话:
罗斯科:我厌恶了画这些该死的矩形。雷乃:难道你不知道你在追随着绘画的物理极限吗?你所谓的灵感破产其实已经成为了抹除艺术中的冒险。背景和情景都是你绘画中的细节,这些细节使绘画相互独立。一个消解另一个,但奇怪的是,现在只剩下细节,但事实上这些细节其实是不存在的。[12]
罗斯科与雷乃对艺术的探讨,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抹除》这部小说的解构性质,阐明了小说的中心主旨即抹除传统与创新实验之间的相互关联。小说中最能道明这一中心要点的是艺术家德·库宁与劳森伯格之间的对话。埃弗雷特/蒙克写道:
劳森伯格:这花了我四个橡皮,但我还是做成了。
德·库宁:做成了什么?
劳森伯格:擦掉了你画给我的画,然后以10美金卖了。
……
劳森伯格:你的画没了。如今剩下的只有被我擦除的地方还有一张本来属于我的白纸。
……
德·库宁:你把我的画卖了?
劳森伯格:没有,我只是擦掉了你的画。我卖掉的是被我擦除后的画。[13]
在上述对话中,罗森伯格的意图是找出是否能通过擦除的形式画出一幅画作,他使用橡皮作为作画工具在旧画的基础之上创作了一幅新的作品。此时,德·库宁创作的画作已不再重要,劳森伯格已经将其变成了自己的艺术作品并成功地通过该作品获得了经济利益。如同劳森伯格,蒙克抹除了埃弗雷特的作者身份,充当起文本的作者,将小说《抹除》变成了自己的叙事。以读者的经验而言,蒙克是小说的主人公,埃弗雷特笔下的虚构人物,化名为斯塔格·雷利,写了内嵌于日志中的小说《我的帕夫洛基》,其笔下人物兼叙述者凡·戈·詹金斯讲述了该小说的整个故事情节。从蒙克为主线的故事到詹金斯为叙述者的子文本呈现出“叙述中嵌套叙述”的多层次叙述结构,展现了在非叙事层面中的叙述者视角的转化,这种多层叙述结构与插入式叙述,构建了错综复杂的文本结构,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
三、《抹除》对类型化黑人形象的解构
“种族作为一个分析范畴仍很重要,种族主义仍是当今美国生活中的严重事实,白人优越论仍是这个时代心照不宣的主流意识”[14],种族主义不仅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产物,也是白人中心主义的产物。埃弗雷特通过写就一部主人公蒙克因美国主流社会控诉自己“不够黑”而愤怒对抗的经历挑战了传统黑白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解构了所谓文化塑造出的类型化黑人形象。
小说主人公蒙克是一位黑人作家和大学教授,为了抹除美国社会对黑人作家固有的成见,他特立独行,从不通过种族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对贴标签式的褊狭行为,他总是嗤之以鼻,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主人公蒙克到华盛顿城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的空档时间里,到一家名为Barne&Noble的书店闲逛,却失望地发现自己的书没有按他预想地正确归类和摆放:
我走到当代小说这一区域,没有找到我写的书,可当我往后退了几步,却发现我的四本书竟整齐有序地摆放在非裔美国文学研究这一区域的书架上,而且上面赫然写着“勿扰”这个字样。更可笑的是,这四本书中的其中一本《波斯人》里唯一可称得上符合非裔美国研究特征的不过是我的一张夹克照。此刻,我感到怒不可遏。那些想要研究非裔美国文学的读者定然不会对我的作品感兴趣,他们会疑惑为什么这些书会摆在这。而那些想找关于重写古希腊悲剧作品的小说读者也不会跑到这里来找书。其结果是,我的书怎么也卖不出去。该死的书店端走了我的饭碗。[15]
对此,蒙克起初的反应是愤怒,书店按照他的外表来归类他的作品,把他的作品放置在黑人作家一栏,而他的作品却与黑人或种族毫无瓜葛,这无疑严重地影响了他作品的销量。诚如他自己所言,在他那些小说中唯一能够提供所谓“黑人信息”的内容无外乎是封面上一张他本人的肖像照。他无奈地意识到将其作品进行归类的不是作品本身的艺术内容而是他作为黑人作家外在的生物特征。令其感到沮丧的不仅是因为他的作品没有被正确的归类,还因为他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媒体、出版界的压力而重新定义他的作品与创作理念。更令蒙克失望的是,他最新创作的一部实验小说再次被出版商拒绝,其理由是作品“不够黑”,不能满足社会对一个黑人作家的期待。
蒙克意识到,正因为他是黑人,是有着 “扁平鼻子、卷曲头发、茶褐色皮肤和一些为奴隶的祖先等这些所谓的种族特质”[16]。因此,他被贴上了“黑人作家”的标签。这意味着他所创作的作品不得不反映人们所认定的 “真实的”黑人生活与经历,即展现黑人贫穷粗俗、愚钝无知、道德堕落与色情暴力的“黑人性”。因为这样的作品会吸引大批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带着种族优越感的白人读者,出版商为了获利,所以他们宁愿出钱发行那些毫无新意、陈词滥调的贫民窟小说(以反映黑人贫苦生活为特点的“类型小说”)而不愿出版与种族无关但却真正具有文学艺术价值的实验作品。
诚然,在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盈利才是王道,小说的内涵和质量逐渐被忽视。为此,相对于创作大有市场的“类型小说”,蒙克则热衷于创作以戏仿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和重写古希腊神话的实验小说。他执着地追求表现纯粹的文学艺术,努力成为一名认真的作家,结果却遭到了出版市场无情地边缘化,这让他愤慨不已。
在此期间,非裔美国新秀女作家胡安妮塔·梅·詹金斯创作的伪黑人小说《我们在贫民窟的生活》大获成功,更加激怒了蒙克。这部所谓的黑人小说仅是詹金斯根据其年幼时到哈莱姆走访亲戚的一次经历打造而成,却能畅销于世,且广受大众媒体、出版商以及文学界的一致认可和好评。愤愤不平的蒙克,于是化名斯塔格·利创作了一本极具反讽意味的小说《我的帕夫洛基》(My Pafology),后干脆将其更名为《操》(Fuck)。
这部内嵌小说是蒙克对理查德·赖特《土生子》的戏仿。蒙克通过抹除了原文本《土生子》,以重写的方式建构了一个新文本《操》。小说《操》以最辛辣的讽刺猛烈地抨击了美国主流社会对黑人的歧视与偏见,并对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爱丽丝·沃克的《紫色》《阿莫斯和安迪》等这类经典的类型化黑人小说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挞。由于这些文学作品所塑造的黑人形象都是处于美国主流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和受害者,恰恰迎合了整个社会对黑人带有歧视的想象,反倒使得“黑人性”的僵化形象得到了强化。对此,埃弗雷特在一次采访中说:作家不是问题所在,出版商才是。面对决定作家成败的出版商时,迫于生存压力的族裔作家们不得不有意“撒谎”,尽可能地按照主流文化的意愿来表述自己。而蒙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创作了他视为下三滥的类型小说《操》,他本想借此机会揭露所谓类型化“黑人小说”创作的虚伪性和种族主义倾向。可不料小说一经问世并一举成名,成了最畅销的作品。评论家和媒体们一致认为它是 “最真实”“最权威”的黑人小说。制片商们争相购买这部小说的电影版权,最后小说还被推举到全国图书奖的奖坛。
《操》的商业成功使蒙克认清了大众的确相信所谓的“黑人性”,相信主流文化所塑造出的黑人形象。然而讽刺的是,这部被认为“真实地”再现了黑人生活与经历的小说恰恰是最“不真实”“最不可靠的”。其作者蒙克的生活经历与他所杜撰的黑人生活根本就毫无关联甚至是大相径庭。出身于中产阶级的蒙克,其祖父,父亲,哥哥姐姐都是医生。他即不擅长篮球也不会跳舞,却喜爱听马勒、阿雷萨·富兰克林、查理·帕克的音乐作品。他擅长数学,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成了一名作家和大学教授。生活中,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非常尊重他身边的女性。蒙克的形象实际上也是埃弗雷特本人的真实写照,埃弗雷特曾对采访者说,蒙克的经历大部分也是我本人的经历,尽管我与他不完全相同,但在现实生活中我的确受到过类似的来自白人编辑与批评家的困扰。[17]《抹除》这部小说通过塑造了蒙克这一“普通的”黑人知识分子形象,成功地抹除了传统中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黑人性。
四、结语
通过《抹除》这部小说,埃弗雷特对传统的语言观,叙事模式和类型化的种族观念发出了质疑和挑战,小说通过碎片化,文体混杂、多层的叙事结构以及戏拟等解构式写作手法,对语言、艺术、写作、种族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充分体现了埃弗雷特具有解构主义思想的创作实验。
注释:
[1] 陆 扬:《德里达的幽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3,150 页。
[2][4][5][8][10][12][13][15][16] Everett, Percival.Erasure, New York: Hyperion, 2001, pp.14, 44,207,191-192,1,222,277-278,28,1.
[3][7] [法]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9页。
[6]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29页。
[9] Jacques Derrida,OfGrammatology, translated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1976, p.3.
[11] David Herman,StoryLogic:ProblemsandPossibilitiesofNarrativ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2002, p.130.
[14] [美]雷蒙·萨迪瓦尔:《美国长篇小说的第二次提升:当代叙事中的种族、形式与后种族美学》,《叙事》(中国版),2013年第5期。
[17] 罗 虹、王明月:《从盖茨意指理论看〈抹除〉的黑人意指性修正》,《当代外语研究》2013年第7期。
[责任编辑:陈未鹏]
2016-09-21
深圳大学创新项目基金“‘后种族时代’下的当代非裔美国作家Percival Everett小说美学研究 ”(000360023426)
吴晨倩, 女, 福建南平人,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晓红, 女, 湖南怀化人,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I106.4
A
1002-3321(2017)02-007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