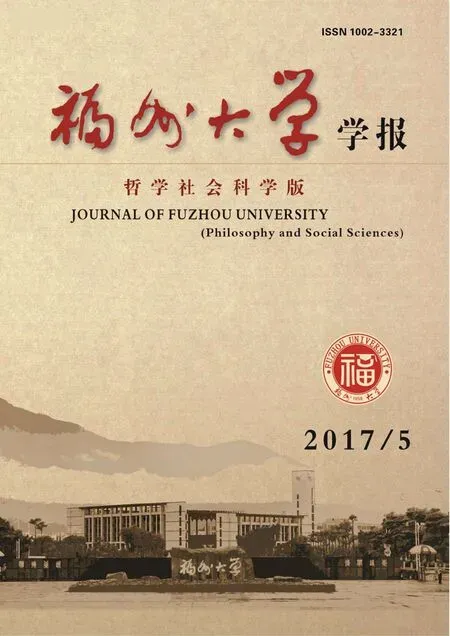被凸显的“文学”与“艺术”:民间信仰非遗化的路径
——以绍兴宣卷为例
2017-04-04王姝
王 姝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3)
被凸显的“文学”与“艺术”:民间信仰非遗化的路径
——以绍兴宣卷为例
王 姝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3)
在宣卷纳入非遗项目的过程中,从知识界到官方,都有意识地凸显宣卷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分别形成民间文学大类与曲艺大类的两大申报体系。以绍兴宣卷为例,考察宣卷在近现代是如何与戏曲曲艺互为影响,开始娱乐功能的分化;在当下又是如何回归到民俗信仰仪式的本体,造成宣卷内容的日益集中单一。产生民间文艺的民俗信仰、民族心理的文化生态是如何在官方、民间的双重合力作用下变得日渐单一瘠薄起来。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才能重建当代民间文学与文化生态场,还原宣卷的民间信仰本质,以期获得真正长久的生命力。
绍兴宣卷; 民俗信仰; 非遗化路径
在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有“曲艺”类别中的“宣卷”,如绍兴宣卷、浦东宣卷、锦溪宣卷等,侧重表演;也有“民间文学”大类中的“宝卷”,如河西宝卷、靖江宝卷、吴地宝卷等,侧重宣卷的文本传承。但河西宝卷、苏州吴地宝卷的表演活动亦非常兴旺,绍兴宣卷、浦东宣卷也都有数百本的宝卷积累。宣卷究竟属于民间文学,还是民间曲艺?同一事物,何以出现一重文本,一重表演的割裂?如何去全面地理解、研究宝卷、或曰宣卷?本文通过绍兴宣卷的实践与历史的考察,探讨宣卷的民间信仰本质,以及其在非遗化中如何通过凸显文学性、艺术性,从而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一、2015年绍兴宣卷的田野调查
笔者于2015年7月18日、9月11日先后两次至绍兴市柯桥区实地考察了绍兴宣卷的全过程,随行的还有柯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是在柯桥区马鞍镇童家塔村长地道,由绍兴宣卷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华鑫任班主的班社举行宣卷,宣卷师是包括陈华鑫在内的四位男士。这次宣卷是一次公众邀请的宣卷,由39位信佛的老太太集资发起,宣卷的地点即在该村的土地庙。宣卷的原因是当天(农历六月初三)是当地土地娘娘的生日。所宣内容为三包龙图,即《割麦龙图》《卖花龙图》与《卖水龙图》。土地庙是村中与其他民房相邻的普通建筑,只有门前一个铁制的大香炉标志着庙宇的性质。土地庙内除供有土地娘娘之外,还有黑白无常等多位神佛。因为要宣卷,土地庙前的空地上已经早早搭起了临时的棚子,院中靠近大门中间是宣卷师的座位,再外面则摆放供桌。宣卷师从早上七点半就开始书写神位与宣卷文疏,由众人布置祭桌,张贴宣卷文疏。约八点左右,装香、请寿的仪式之后,开始正式宣卷,至十一点半方歇。下午从一点开始,到三点多宣卷结束,开始散花、解结与焚化的仪式。在整个宣卷过程中,原来“一唱众和”的形式已经没有了,改由四位宣卷师自己“和佛号”。这与顾希佳先生在1998年的调研情况相同,但顾先生认为这一演唱形式的改变使得“宣卷班演唱宣卷的时候,现场的气氛就显得比较轻松,有人在静心聆听,有人在闭目养神,有人在和边上的同伴窃窃私语,拉着家常话,也有的人甚至在打毛线、做针线活”[1],说明绍兴宣卷已经世俗化,成为一种表演艺术,观众趋向于纯粹的欣赏。
但据笔者观察,尽管众人已经不再参与到“和佛号”的大合唱中,宣卷并没有失去它的仪式性。宣卷师宣卷时,众人(以众位发起的老太太为主,也有从外面赶来的)几乎全程都在念经,折各式纸锭、元宝,每折一个纸锭都要用嘴对着纸锭念一遍心经,有的专门用一张纸或一个本子记录是否念足了遍数。折好的纸锭挨个折叠起来,挂在一起准备焚化。整个宣卷过程中,不时有老太太来上香烛、拜祭。她们或至庙中神位前上香火,或携带已经折好的纸锭、元宝挂缚在一起,或至庙前大香炉中清理香灰。虽然偶有私语,总体还是具有很强的宗教仪式氛围的。在散花、解结时,众人与宣卷师一同起立祈福,焚化时更是围着焚化的纸锭、元宝与神位多次转圈拜祭,十分虔诚。把宣卷当成曲艺静心闭目欣赏的反而没有。宣卷师与所有参与宣卷的妇女在当天都要吃素,不能喝酒。宣卷结束后,我们采访了班主陈华鑫,他介绍说这次宣卷是一次小规模的宣卷,一般中等规模的宣卷在一两百人,就是做寿等家庭宣卷也能达到一百多人。而大规模的宣卷人数可以达到将近四百人。陈华鑫班社一年约有一两百场宣卷演出,这在班社众多的马鞍镇并不算频繁。宣卷生意一般都是找班主,再由班主召集大家,班社人员基本固定,但偶尔也有人有事,可另外叫人顶替。宣卷以农历正月、二月、四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最频繁,三月不宣卷,因为民间流传三月桃花不做寿,而五月六月也因为天气炎热次数减少,十二月间也少起来,大约是忙着过年的缘故。如此一年到头,好的宣卷班社会做到三四百场之多。
9月11日的宣卷是一次私人宣卷,是由柯岩街道余渚村大江下的何秀福单独发起的宣卷,并没有如做寿、乔迁、入学等特殊目的,他只是觉得要敬一下神,因此委托钱清江墅村行义庄里的宣卷师做一场宣卷,地点则是在宣卷师家中的家庙举行。这位宣卷师是省级非遗传承人叶传友的中年女弟子。因而这次宣卷的班社即由叶传友为班主的班社举行,宣卷师包括叶传友在内,是两男两女。这位女弟子的家庙供奉的是朱天大君,这是一个流传在江南一带,以明代崇祯皇帝为原型的地方神祇。据女弟子的丈夫介绍,他家的家庙十分灵验,香火很盛。从他奶奶时就传下来,现在由他姑妈主持。每年四月二十三朱天菩萨生日那天,前来做会宣卷的参与者可以达到一两千人。家庙是一间一面临水的大平房,里面空间很大,正中供奉朱天大帝,旁边还有几个其他民间神祇。由于这是临时发起的一次私人宣卷,没有老太太来专门念佛,只有发起宣卷的斋主,宣卷师的家人,还有几个邻居老头时不时来串门聊天。虽然参与宣卷的人少,宣卷班子还是十分认真地演唱,每两句必和唱佛号,所有仪式亦一丝不苟。
因为笔者与非遗中心工作人员的到来,叶先生唱得格外起劲,我们也感觉到这次的宣卷演唱,越唱越放开,特别到下午,叶先生嗓音更加宏亮,表演投入、声情并茂。宣卷的内容仍是三包龙图。宣卷时大家并不专门坐着,而是很随意地走动。但我们采访宣卷师的丈夫时,他表示,宣卷的内容他从小听到大,非常熟悉,并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宣卷的故事内容。听到某句,就能告诉我们现在宣到哪个情节了。采访一位邻居老人时,他十分肯定地说,宣卷后神佛就会保佑我们,绍兴这个地方有宣卷,所以才风调雨顺、无灾无祸。别的地方为什么有地震水灾呢,就是因为没宣卷。可见当地人的信仰还是十分牢固的,他们把宣卷视为重要的功德,而不是怀着欣赏表演的态度。宣卷师演唱得好,神佛会更加满意,宣卷的佑护作用就越大。解结时全体宣卷师和参与者起立,到最后焚化时,就只有斋主本人与家庙的老姑妈两人参与仪式了,其他邻人则在一旁观看。宣卷结束后,我们到叶老师家中采访,看到两个书柜都装满了叶传友宣卷比赛、培训的照片,还有十分珍重地收藏着的省级非遗传承人证书。叶老师儿子表示,他们支持父亲宣卷,完全是因为父亲爱好宣卷。家里经济情况很好,不需要靠宣卷来赚钱。
两次宣卷的文疏都是由宣卷师书写在黄裱纸上,格式相同。但第一次宣卷还另有一张更大的红榜,除了供奉神主土地娘娘之外,还向“大成至圣先师文宣圣王兴儒盛世天尊、天地神祇、诸佛诸祖、诸真诸帝、诸圣诸贤、南斗北斗星君、济世佑民诸大道祖、十方诸大菩萨”祈福,包括了儒释道各类神佛,说明绍兴民间信仰的驳杂状态。要求保佑的除了常见的“平安”“发财”“无病无灾”之外,还包括小孩读书上大学,出国留学等内容。第二次宣卷写得十分生动具体:“保小人读书天天向上步步高升名牌大学考进出国做了留学生回到北京城做了中央干部接班人来接合家老小游北京”,另有“又全家大小人人出入平安路上开车太平回家”则与时俱进,要求保佑私家车的驾驶安全。可见,宣卷文疏的格式虽然固定,内容却随发起人、发起性质的不同而转变,还加入了许多当下人们的需求。这说明,在民众眼里,宣卷活动主要还是信仰的功能。
而陪同我们一起考察的非遗中心的工作人员则不断提醒,要求我们看淡宣卷的民俗色彩,因为他们觉得这稍有不慎,便成为宣扬封建迷信。并强调宣卷是作为曲艺类别申报非遗的。在主要由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人员编写的《绍兴宣卷》中,对于绍兴宣卷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列入首条的就是“宣唱技巧普遍不高”。[2]为了与封建迷信区分开来,非遗中心努力强调宣卷的“曲艺”性质,虽然在“曲艺”类别中成功申报,但在两次绍兴宣卷的实地考查中,我们发现,很少人将宣卷当成象莲花落、绍兴滩簧那样的曲艺去欣赏,民众还是看重宣卷的信仰功能。因而政府部门的倡导与民众对于宣卷的实际需求之间,产生了微妙的裂隙。
二、是民俗还是曲艺:历史路径的考察
车锡伦先生在《“非遗”民间宝卷的范围和宝卷的“秘本”发掘出版等问题——影印〈常州宝卷〉序》一文中,特别回溯了他自己不同时期对宝卷的认识,并颇具反省精神地更正了早期的定义。他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宝卷研究论集》所收《中国宝卷概论》中称:“宝卷是一种十分古老而又同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相结合的讲唱文学形式。”[3]2001年至2009年间,车老对宝卷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宝卷研究》中,车老认为宝卷是“在宗教(主要是佛教和明清各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演唱宝卷称作‘宣卷’(或‘念卷’‘讲经’)”[4]。直到2011年,在长期阅读各地宝卷,并对吴语地区宣卷活动进行实地调研之后的车老,纠正了自己将宣卷视为说唱文学和说唱艺术形式,将宝卷视为说唱文本的定义,提出“宝卷一直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一般称‘做会’)中演唱,这就造成其演唱形式仪式化(最初是接受佛教忏法的形式),必须按照一定仪轨演唱”,强调宝卷是“用于仪式活动的卷本,不是文学作品”,“宝卷演唱不能离开它存在的信仰文化背景”。[5]
还原宣卷的民间信仰本质,才能避免“民间文学”还是“曲艺”的两难选择。但这又无疑将政府部门置身于宣传封建迷信的钢丝之上,如履薄冰。考之宣卷的发展历史,对宣卷民俗性的有意忽略,是官方政府与知识阶层的一贯态度。如明嘉靖年间徐献忠撰《吴兴掌故集》载:“近来村庄流俗,以佛经插入劝世文俗语,什伍群聚,相为唱和,名曰‘宣卷’,盖白莲教之遗习也。湖人大习之,村妪更相为主,多为黠僧所诱化,虽丈夫亦不知堕其术中,大为善俗之累,贤有司禁绝之可也。”[6]崇祯时徐守刚《乌程县志》亦言:“当道宜严禁之。”[7]清光绪初年惜花主人的《海上冶游备览》一书中这样描述宣卷:“一卷二卷,不知何书,聚五六人群坐而讽诵之,仿佛僧道之念经者。堂中亦供有佛马多尊,陈设供品。其人不僧不道,亦无服色。口中喃喃,自朝及夕,大嚼而散。谓可降福,亦不知其意之所在。此事妓家最盛行,或因家中寿诞,或因攘解疾病,无不宣卷也。此等左道可杀。”[8]民国曹允源等纂《吴县志》引江苏按察使裕谦于道光十九年(1839)十二月所作“训欲示谕”说:“苏俗治病不事医药,妄用师巫,有‘看香’、‘画水’、‘叫喜’、‘宣卷’等事,惟师公师巫之命是听。”[9]可见明清至民国,从知识阶层到官方政府,一直将宣卷视为“巫觋”之道,抱有极大的敌意,欲除之而为快。但即使在这样的敌意中,宣卷之民俗性始终不褪,民间宣卷的盛行亦很难被完全禁止。
首先为宣卷正名的是发现了“宝卷”的文学价值的郑振铎。早在1928年,郑振铎就在《佛曲叙录》中,介绍了41种佛曲,其中就有宝卷33种(当时称变文、宝卷均为佛曲)。1934年4月3日,郑振铎刊出的《苏州近代乐歌》一文中对苏州宣卷作了介绍,指出“宣卷是宣扬佛法的歌曲,里边的故事总是劝人积德修寿”,宣卷的听众主要是妇女,请到家中来唱,“做寿时更是少不了的”。[10]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中,他更将宝卷归为俗文学五大类中的“讲唱文学”单列一章。郑氏对“宝卷”为“讲唱文学”的定义,一直为后人所沿用。“讲唱文学”的限定,使得受郑氏影响的“俗文学派”至今偏重于“宝卷”文本的研究,而无法涉及其民俗背景,亦难以形成综合性的立体研究。
郑氏有关“‘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儿孙”[11]的论断,也长期被后人未加思索地引用。其实这一论断,既缺乏对明清之际民间信仰嬗变的梳理,亦未对清末至民国的宣卷做民俗学的考察,更谈不上将田野调查与文献考证相互映证。郑氏失之粗疏而流传甚广的结论,已为李世瑜、车锡伦等学者的研究所纠正。李世瑜认为宝卷服务于白莲教等明清民间秘密宗教的传播,[12]并由此将宝卷分为明清秘密宗教“前期宝卷”和同治、光绪之后以上海、苏州、杭州、绍兴等城市为中心的,“由布道发展为民间说唱技艺”的“后期宝卷”。[13]与之相似,车锡伦以康熙年间为界,将宝卷分为“前期宗教宝卷”和“后期民间宝卷”,[14]提出“宋代佛教悟俗化众的活动孕育了宝卷”,“宝卷继承了佛教俗讲的传统,而同南宋时期勾栏瓦子中出现的说唱技艺‘谈经’等无关”。[15]并认为:“从吴方言区民间宣卷的发展来看,它是一种历史上曾受过佛、道教及民间宗教的影响,并已纳入江浙民间信仰文化系统的民俗信仰活动。宣卷人既有民间迷信职业者的身份,同时又是民间的说唱艺人。”[16]
宣卷的娱乐化,与近现代各种“地方戏”和地方曲艺的形成、成熟同时并进。宣卷作为古老的民间信仰仪式,其长期积累的演唱、表演、音乐等元素,孕育了与之相关的地方戏曲与曲艺。徐宏图特别强调中国戏剧与宗教的关系,他在《内坛法事外台戏》一文中认为:“几乎所有的剧种均被宗教仪式借用过,仪式藉演戏以增辉,剧种藉仪式以生存。”[17]自明代以来,与民间宗教仪式相伴共生的宣卷活动自然而然成为孕育江南地区各类地方戏曲的祖母。“宣卷对江南戏剧的产生和发展影响巨大。杭剧和越剧都直接来源于宣卷。另外,沪剧、甬剧、姚剧、苏剧、锡剧等都来自于滩簧,而滩簧的曲目和曲调的重要来源之一即是宣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宣卷称得上‘江南戏曲之祖’。”[18]
如杭剧的前身就是“宣卷”。清末民初,杭州民间宗教十分兴旺,每至神诞、得道、升天等宗教纪念日都举行盛大的庙会,善男信女往往在前一夜便前往各寺庙参加诵经、拜忏仪式,念佛参拜,赶烧头香。漫漫长夜中与他们做伴的就是宣卷。杭州早期宣卷艺人多为丝织业工人。近代沈云在《盛湖竹枝词》注解中提到:“织墉蚕时休业,二人为偶,手持小木鱼,一宣佛号,一唱《王祥卧冰》、《珍珠塔》等,名‘念佛出’,妇女多乐听之。”[19]1923年,叶少梅、裘逢春等一批出身丝绸工人的宣卷艺人成立了杭剧第一个科班——民乐社。受淮扬文戏的启发,他们在宣卷的基础上,自编戏文、唱词,初步分出行当,开始进行高台演出。1924年1月31日,民乐社在杭州大世界游艺场西二层楼以“武林班”的名义首演“化装宣卷”,剧目为《卖油郎独占花魁女》。宣卷艺人职业化,宣卷班社专门化,由宣卷演变而来的这一剧种后正式改名为“杭剧”。越剧的早期形态——落地唱书,也是宣卷。早期曲调〔四工合〕就是直接从宣卷调的“和佛”演化而来。绍剧、越剧或鹦哥戏(即绍兴滩簧)的演出中,凡有祈神拜佛内容,一般都会唱“宣卷调”。如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唐僧的唱段“弟子东土唐三藏”、越剧《玉蜻蜓·后游庵》中王志贞唱的“宣卷调”等,还会加上帮唱。
近现代地方戏产生时,进入上海、苏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大城市的宣卷,渐渐孕育出具有地方风格的地方剧种和曲种。与此同时,地方戏曲与曲艺又用其更为丰富的音乐与充分发展的表演技艺回过头来反哺日渐职业化的宣卷,进一步促成宣卷的娱乐化。光绪年间,江南便出现了宣卷班社,一般四人为主,他们在各集镇的茶馆中挂牌招揽生意,或乘船到“斋主”家演唱。后来宣卷班社进入城市,光绪末年,苏州地区出现了宣卷艺人的行会组织“宣扬社”(宣扬公所)。据顾颉刚先生回忆,滩簧盛行后,过于朴素的宣卷难以吸引观众,宣卷艺人被迫“改变旧章”,曹少堂始倡为“文明宣卷”。改革传统的“木鱼宣卷”演唱形式,加入丝竹乐器伴奏,吸收民间小调俗曲,如〔单双〕〔阴世调〕〔行聘调〕等,称为“丝弦宣卷”。“妇女们既喜滩簧的洋洋盈耳,又喜宣卷的好说吉利话,故到现在仍极盛行。”[20]宣卷演唱苏滩的传统剧目,如《马浪当》《卖橄榄》《荡湖船》等,并出现了以女宣卷人演唱的“女子宣卷”。据说苏滩艺人还为此同宣卷艺人打了一场官司,后经官府判决,宣卷演唱只许用一把胡琴,以与苏滩区别。宣卷也受弹词影响改变演唱形式,李世瑜先生在《江浙诸省的宣卷》中,以民国五年(1916)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红楼镜宝卷》(又名《金枝宝卷》)为例,说明清同治、光绪以后,江浙地区民间宝卷的突出特点是说、唱文标出演唱脚色(生、旦、丑、杂等),并有演唱提示(唱、白、夹白、嫩声等)。[21]这种增加了丝弦伴奏,模仿弹词说唱“出脚色”的宝卷演唱形式,被称为“书派宣卷”。
宣卷的娱乐化,也即进入车锡伦所说宝卷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清及近现代民间宝卷”,[22]正是在近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受到都市娱乐业与大众传媒发展的影响,是与地方戏曲、曲艺的形成、成熟大致同步的,在演唱形式与音乐曲调上彼此相互借鉴影响。至今,绍兴宣卷中的〔阴四平〕〔佛莲花〕〔启奏调〕〔五更调〕,有着明显的绍兴调腔特色,都采用“一唱众和”的形式,但没有保留调腔曲牌的原名,唱法已经宣卷化。“宣卷已渐趋于一种表演性较强的民间讲唱样式。这种表演性也就是娱乐性,与神歌古朴原始的仪式性特征大为不同。”[23]这种被剥离了宗教仪式,向曲艺表演趋同的宣卷,更容易得到官方认可。
在宣卷剧目上,佛教、民间宗教的内容大为减少,而改为大量搬演与戏曲曲艺同内容的世俗故事与民间传说。如与绍兴调腔同目的有《琵琶记》《西厢记》《循环报》《粉玉镜》等,与绍剧或越剧同目的有《三官堂》《凤凰图》《碧玉簪》《龙凤锁》《双金花》等,与苏州弹词、绍兴词调同目或来自民间传说故事的有《玉蜻蜓》《珍珠塔》《玉鸳鸯》《碧玉钗》等。[24]像《梁山伯宝卷》《雷峰宝卷》《李三娘宝卷》《珍珠塔宝卷》等都来自戏曲、小说或民间传说故事,在不同的剧种、曲艺以及宣卷中并存。1940年前后,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城乡民众的祈福攘灾、庙会社赛活动大大缩减,宣卷班社也随之萎缩,从业人员骤减。1950年以后,宣卷被认为是迷信活动,在城乡几乎消失。[25]但是如果我们关注当下绍兴宣卷的情形,就会发现,这样一种娱乐化,也就是为政府文化部门所乐意推崇的,作为曲艺形式存在的宣卷,也在逐渐褪却。民众请宣卷与其说娱乐自己,不如说是为娱神而做的功德。
三、回归民俗信仰仪式:现实路径的考察
需要指出的是,“文明宣卷”或曰“丝弦宣卷”盛行之后,并不意味着木鱼宣卷就消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宣卷的“花卷”(丝弦伴奏)与“平卷”(木鱼清唱)并存。据笔者这次在绍兴对陈华鑫的采访,以前都是清唱的,后来在改革开放以后,宣卷也开始改革,加入二胡、三弦、月琴等丝弦以及锣鼓伴奏。陈华鑫18岁开始学习宣卷,恰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说明那时的绍兴宣卷仍是“木鱼宣卷”为主。可见从清末至近现代以来,宣卷的娱乐化是有限的。民间宣卷进入城市以后,宣卷发展为地方戏曲、曲艺,表演娱乐的成分被提炼掉了,宣卷与戏曲曲艺之间发生了一重信仰、一重娱乐的功能分化。一方面,宣卷向自己孕育滋养出来的地方戏曲与曲艺学习表演形式,搬演相似剧目,日渐娱乐化和世俗化;另一方面,随着地方戏曲与曲艺的兴盛壮大,宣卷又渐渐将娱乐功能让渡给了这些专门的剧种和曲种,重新回到乡村信仰的固有土壤中,回过头来强调自身特有的民俗仪式的一面。
由于民间信仰的顽固性,即使在“文革”期间,乡间仍偶有人偷偷请人宣卷。远在将宣卷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之前,即“文革”后期,绍兴宣卷已经在民间恢复活动。陈华鑫的回忆已经说不清具体的“改革开放”是何时,据他口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恢复宣卷了。从宣卷经历“文革”的沉寂,很快就恢复生机来看,宣卷依然深深扎根于民间信仰的土壤中。无论是集资发起的公众宣卷,还是单独出资的私人宣卷,动因都是在做功德、行善事。
倒是宣卷师本人之所以选择宣卷,有更多的自娱成分。叶传友、陈华鑫等班社的宣卷师,平时都是喜爱吹拉弹唱的,鹦歌(绍兴滩簧)、越剧、绍剧、莲花落都会唱。有的是曲艺世家,比如陈华鑫的姑父徐子安以前也是宣卷师,陈华鑫正是拜他为师学习宣卷的。叶传友一家人在业余时间,常应老父亲的要求,有时合唱,有时各自表演,完全是自我娱乐的性质。在政府文化部门的引导下,他们有了更为自觉的曲艺艺人的身份,并以此为豪。陈华鑫说,他在报纸上读到宣卷是绍兴五大曲种之一,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后,这才大胆地唱起十多年前因为自己公职教师的身份而放弃的宣卷。他这次宣卷还专门穿了唐装,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标志牌放置于宣卷桌上显眼之处。两次宣卷,两个班社的演唱风格也不尽相同。其中陈华鑫班社的《卖水龙图》运用越剧的曲调演唱,有着很强的戏曲风格。叶传友班社的“和佛”是最多的,严格遵守每两句结束四人一起和唱佛号,宗教色彩更为浓郁。表演上虽然仅仅是坐着演唱,但都通过各自的演唱风格,音色的转换,曲调的抑扬顿挫,表现出人物的活灵活现,使得讲述的故事绘声绘色,简单质朴却极为传神。
由此可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宣卷,已经进入又一个新的阶段,在民间与政府的双重合力作用之下,一作为民间信仰活动,一强调曲艺表演。作为信众的宣卷发起人、参与者仍然重视宣卷的信仰功能,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富裕的绍兴农村,大家都愿意请宣卷来谢神、做寿(又分做活寿与阴寿)、贺迁、祭奠、还愿,“‘唱大戏’还是一种富裕的象征”。[26]
宣卷演唱者则一方面以宣卷演唱自娱,一方面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象叶传友、陈华鑫等省、市级传承人,意识到自己宣卷艺术传承人的身份,广收徒弟,自觉将宣卷演唱艺术传承下来。宣卷曲调简单流畅,易于上口,演唱时可翻阅卷本、照本宣科,无须记诵背读,爱好者稍有基础即可开始正式宣卷,入门并不难。宣卷在绍兴、萧山、上虞一带农村很有市场,有的班社一年到头会宣三四百场,经济收入在当地可达到中上水平。根据2010年首次“绍兴宣卷交流演唱会”的演出统计,绍兴宣卷较为固定的班社达到三十余个,演员达一百三十余人。而据柯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王雷主任介绍,还有许多班社忙着在乡间宣卷挣钱,根本不愿参加政府组织的非盈利的演唱活动。实际活跃的绍兴宣卷班社与演艺人员还要高于这个数字。
不过,在繁荣的表象下,仍可见出宣卷的危机。一是宣卷的参与者皆为老人,二是宣卷演出的卷本不复当年的百花齐放,已经过度地集中于“三包龙图”,即《割麦龙图》《卖花龙图》与《卖水龙图》。笔者两次调研都是宣“三包龙图”。叶传友、陈华鑫等人都收藏有几十本宝卷,据陈华鑫说,他这次宣卷也带了《双状元宝卷》等卷本,但宣卷内容大多由发起人、集资人决定。由于“三包龙图”广受绍兴百姓的欢迎,所以现在绍兴地区除了考上大学唱《双状元宝卷》外,基本上都是以宣“三包龙图”为主。2010年9月,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的首次“绍兴宣卷交流演唱会”上,由来自绍兴县、越城区以及萧山区、上虞市的38个班社近160位艺人参加,其中演唱“三包卷”的就有11组。即使进行参赛性质的交流演唱会,许多宣卷班还是不避重复,以演唱“三包卷”为多,可见宣卷中“三包卷”受欢迎的程度。
当笔者问及为什么现在都是宣“三包龙图”时,陈华鑫的解释是,宣了三包宝卷,死后到阴司也会受到保佑的。据他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宣卷的内容,要广泛得多,与戏曲、弹词同目的《珍珠塔》《碧玉簪》《玉蜻蜓》《龙凤锁》等,都是常宣的。现在宣卷师的宣卷虽在政府的引导下,成了独立的曲艺演员,但民间宣卷还是得根据民众的需求,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两次宣卷演出的场地,土地庙与家庙,彰显着当下绍兴宣卷强烈的民间信仰色彩。土地庙与家庙均由旧民宅改建而成,并没有修建大屋檐之类的传统建筑风格,说明当地民间信仰贴近日常生活,并不需要特殊的标志。应该说是宣卷人、发起人、念经人共同完成了整个宣卷活动,宣卷当天所有人员都要全程吃素,有很强的参与感。演出过程中参与者的折纸绽、念经活动都是宣卷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三包龙图”多宣,观众早已熟知宝卷故事,并不在于欣赏宣卷的吟唱,他们重视的是,宣卷是否认真,有没有跳脱字句。陈华鑫说,年轻人组成的宣卷班社马虎,常常会有脱漏,因此老百姓不信任。笔者在土地庙旁听宣卷时,念佛老太太一再跟我们强调,这里的土地娘娘很灵的,宣卷是宣给菩萨听的,脱漏就不虔诚了,影响了宣卷的效果就会导致神祇失灵。
至今绍兴宣卷依然保留着从装香、请寿、宣卷、散花、解结、焚化,六个完整的程序。除了宣卷部分由宣卷师完成之外,其余都是宣卷师带领大家共同完成的。即使宣卷时,已经不再一唱众和,但一旁念佛的老太太依然念经、折纸锭不缀。鲜明的仪式感,“是为维护这些信仰的生命力服务的,而且它仅仅为此服务,仪式必须保证信仰不能从记忆中抹去,必须使集体意识最本质的要素得到复苏。通过举行仪式,群体可以周期性的更新其自身的和统一体的情感”[27]。对土地娘娘神诞的庆贺,对朱天大君的香火供奉,都籍借宣卷这一仪式,复写着民众的信仰记忆。宣卷固然还有做为曲艺的娱乐性,因为“倘若宗教没有给思想与活动的自由结合留有余地,没有给玩耍、艺术以及所有能够使精神得到放松的娱乐留有余地,宗教也就不能成其为宗教了”[28]。但由政府文化部门刻意支持的曲艺性质,与宣卷的民俗信仰仪式性质相比较,完全是附属的成分,并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回归民俗信仰仪式功能的绍兴宣卷,为什么今天只宣“三包龙图”了呢?首先,从内容上来讲,三包龙图宝卷虽然与戏曲、曲艺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却加入更大程度的果报、因缘等信仰色彩。如《卖水龙图》讲的虽然是《血手印》的故事,却比戏曲中多了很多神道色彩。每一步情节的推动,都与天上神道有关,主人公遇到的挫折,也起因于他们忘记敬神;困境得以解决,也是因为主人公的善心与哀求,感动了天神来相助。这与其说是一部公案戏,不如说是神道戏。宝卷中的包龙图与公案小说、包公戏中的形象相比,加强了神化的色彩。《割麦龙图》《卖花龙图》《卖水龙图》中的包公,其能力并不在明察秋毫的查案能力,也不象戏曲那样强调他不畏强权、为民申冤、廉洁公正的形象。宝卷中的包公不需要明察暗访,他查知案件的真相,都是通过鬼魂告状、诉说冤情,甚至还有起死回生的能力。[29]经由宝卷神道化处理的包公完全成为民间信仰中的神祇形象。
最重要的是,绍兴当地对包公信仰的程度决定了“三包龙图”宝卷在绍兴宣卷中的独特地位。绍兴的包公信仰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包氏八世祖随宋室南迁,九世组的两支,分别迁往绍兴、萧山,其后向诸暨、台州、象山、东阳、嵊州等地迁移散居。绍兴的包公殿分布甚广,鲁迅笔下提到的绍兴迎神赛会,就是于每年农历六月十六包拯生日举行。迎神赛会时,场面浩大,各路菩萨都被抬出游行,又有走高跷、调无常、嬉彩瓶、扛台阁、擎高照、戏趟叉、轻音班、大敲棚、排衙、放铳、套大架、肉蜻蜓、水流星、火流星等民间表演。迎神赛会在绍兴城乡均有举行,以孙端镇(即鲁迅笔下“赵庄”的原型)的最具代表性。一位萧山(原属绍兴)年轻人告诉笔者,至今在萧山一带,还有给包公寄名的传统。小孩出生后,家长怕孩子养不大,或为祈福,多至包公殿里寄名,寄拜包公做爷爷,因而绍兴人多呼包公为“包爷爷”。寄名的仪式十分简单,到包公殿点香烛叩拜后,洗过手,从红漆描金托盘中随机抽取一个小纸卷,纸卷上就是包爷爷给的名字,再冠以包姓。这个孩子就有两个名字行世,其中一个就是寄名的包姓名字。这就表明他已经是包公的子孙,从此没有妖魔鬼怪敢来打扰,可以平安长大。这位包公寄名的子孙若遇到什么困难,也可以随时来包公殿祈求包公佑护,必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包公信仰的“实用性”,“使之与民众形成面对面的交流,帮助民众追求生的平安富足,规避人生的种种苦难,紧密联系现世生活”[30]。
“三包龙图”在返归信仰仪式的绍兴宣卷中,占绝对的优势,进一步说明绍兴宣卷与民间信仰的密切关系。绍兴宣卷今日的娱乐化,是政府部门刻意强调其曲艺性质的结果。考之宣卷的发展历史,验之宣卷的当下实践,这一强调,未免也有些榫卯不接。其实,民间信仰正是产生民间文艺的生态土壤,如果人为加以净化,宣卷被斩断与民间信仰的联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如上述“绍兴宣卷交流演唱会”上的宣卷,每个班社的表演时间仅限8分钟,唱惯了一整天宣卷的艺人表示,喉咙还远远没放开就要结束了,唱不过瘾。再如2011年在绍兴举办的“水乡曲韵”第七届中国曲艺节上演出的《绍兴宣卷》完全变成一种曲艺演唱,被剥离了民俗信仰仪式的功能,这样的宣卷还是原来的宣卷吗?尽管政府扶持的宣卷演出活动,保存了“三包龙图”之外的多种宝卷本的演唱,但我们也要进一步反思,今天的绍兴宣卷,之所以局限于“三包龙图”,是否与当下民间信仰生态的恶化、单一有关呢?在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是否可以对民间信仰给予更大的宽容度,对宣卷这样复杂的民俗事项,少一些简单化的处理,进行更为综合、全面、立体的科学考察呢?
政府文化部门欲振兴宣卷,远不是办几个交流演唱会,或者让宣卷脱离原来的民俗背景,到如今新兴的文化节(如安昌“腊月风情节”)、庙会(如新恢复的舜王庙会)上唱几番,就能了事的。尽管民间宣卷活动兴盛,但其实已经失去了当初与戏曲、曲艺同步变革时的创作生命力。清末民初,宣卷也会“唱(说)新文(闻)”,如《秀英宝卷》就把民国初年上海阎瑞生图财害命的故事(即电影《一步之遥》的故事原型)搬入宣卷。还有讲述光绪年间福州陈氏遭雷击的《妻党同恶报宝卷》等。1981年,上海商榻乡宣卷队在县文化馆的帮助指导下,先后创作排练了《懒阿新遇仙》《阿塔卖茶》等一批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勤劳致富的宣卷剧目,其中《懒阿新遇仙》参加上海市业余曲艺创作节目交流演出被评为优秀节目。[31]但是,缺乏民俗根性,为评奖而创作的宣卷没有太大的生命力。宣卷先生从前从戏曲、弹词中改编戏文,增加宣卷的娱乐性,现在娱乐功能已经分化出去,宣卷参与者的重点也不在听宣卷,宣卷先生也失去了创作改编的动力。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连现有的卷本都不能广泛流行,只有“三包龙图”、《双状元宝卷》因为民俗实用的原因,在反复演唱。虽然采访中像叶传友、陈华鑫等人都表示,其他宝卷他们也很熟悉,完全会唱,但请宣卷的人家只认“三包龙图”。长此以往,宣卷的生态会日趋单一,更加失去活力。
因而,只有重新还原宣卷作为民间信仰仪式的丰富性,特别是将“表演作为实践(performance as practice),也即表演作为处于特定情境的日常实践,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praxis)概念来的观点”[32],使宣卷真正存在于民间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中,恢复其民间信仰的本质,才能给予扎根民俗信仰、民族心理的民间大众文化生态更为宽松、自由的生成氛围,也才能使像宣卷这样的文化事项重获真正长久的生命力。
注释:
[1] 顾希佳:《绍兴安昌宣卷调查》,《民俗曲艺》第127期,(台北,2000)。
[2][18] 王 彪、冯 健:《绍兴宣卷》,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2年,第116,8页。
[3][14] 车锡伦:《中国宝卷概论》,《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台北:台北学海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4] 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自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5] 车锡伦:《“非遗”民间宝卷的范围和宝卷的“秘本”发掘出版等问题——影印〈常州宝卷〉序》,《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6] [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二“风土类”,台北: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第764页。
[7] [明]徐守刚:《乌程县志》卷四,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94页。
[8] 陈汝衡:《说书史话》,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128页。
[9] 曹允源等:《吴县志·风俗(二)》,苏州:苏州文新公司排印,1933年,卷52下,第14A页。
[10] 郑振铎:《苏州近代乐歌》,《歌谣周刊》1934年4月3日。
[11] 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文学》第2卷6期,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第6页。
[12] 李世瑜:《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文学遗产增刊》1957年第四辑。
[13][21] 李世瑜:《江浙诸省的宣卷》,《文学遗产增刊》1959年第七辑。
[15] 车锡伦:《中国宝卷的渊源》,《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16][25] 车锡伦:《清及近现代吴方言区民间宣卷和宝卷概况》,《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7] 徐宏图:《内坛法事外台戏——论中国戏剧与宗教的关系》,《戏曲研究》2004年第1期。
[19] 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2页。
[20] 顾颉刚:《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48-349页。
[22] 车锡伦在《形成期之宝卷与佛教之忏法、俗讲和“变文”》(《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中认为宝卷形成于宋元时期,经历了早期佛教宝卷、明清民间教派宝卷和清及近现代民间宝卷三个发展阶段。
[23] 赛瑞琪:《文学叙事在民间信仰语境中的生成、变异与展演形态——以芦墟刘王庙会为个案》,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第44页。
[24] 车锡伦:《形成期之宝卷与佛教之忏法、俗讲和“变文”》,《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
[26] 矶部佑子:《地方戏曲的复兴及其意义——以莲花落、鹦哥班、宝卷的演出为论述中心》,《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
[27][28]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 东、汲 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5,501-502页。
[29] [清]《张氏三娘卖花宝卷》,光绪十年(1884)明台经房刊本。
[30] 张 灵、孙 逊:《从宝卷对小说的改编看民间多神信仰的历史生成》,《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2期。
[31]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宣卷》,2015年11月8日,http://www.shzgh.org/renda/node7737/node8168/node8174/node8176/u1a1451205.html,2017年5月8日。
[32] [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2017-06-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故事与当代民间话语嬗变”(12CZW082)
王 姝, 女, 江苏南通人,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K892.24
A
1002-3321(2017)05-0018-08
[责任编辑:石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