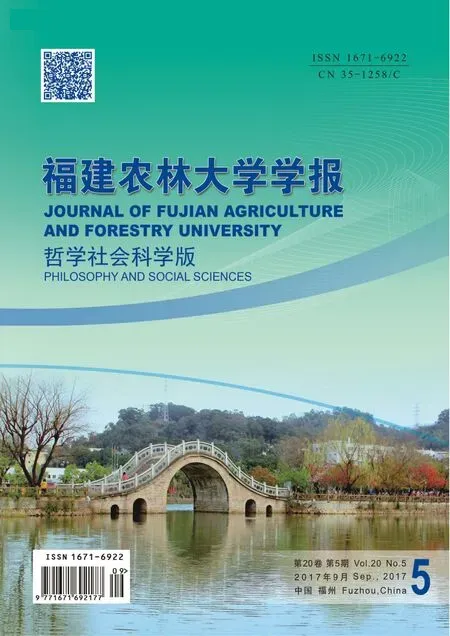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
——以清代秋审成案机制为鉴
2017-04-04冯义强
冯义强, 王 剑
(1.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4)
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
——以清代秋审成案机制为鉴
冯义强1, 王 剑2
(1.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4)
我国尚未建立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而清代秋审成案机制对清代司法官适用死刑起到较大指引作用,可资借鉴。在对清代秋审成案的产生主体、具体类型、论证方式、司法效力以及时间效力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现有案例指导制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存在基本问题认识不清、司法实践困难等问题。建议借鉴清代秋审成案机制的相关制度,从案例制度本身和司法适用2个方面构建我国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
清代秋审成案机制;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
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在于指导定罪及量刑,而死刑的司法适用具有较强的政策性,更加需要通过案例进行指导[1]。目前,我国学者对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已有所关注,但较少研究清代秋审成案机制对我国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的借鉴意义。在清代,秋审中成案的适用,不仅对地方司法官员适用死刑具有指导意义,还对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清代秋审成案机制对我国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清代秋审成案机制进行研究,同时结合我国当前案例指导制度的现状,探索构建我国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的具体方案。
一、清代秋审成案机制研究
秋审成案机制主要是指成案在秋审中产生和运行的具体过程。该过程主要涉及成案的产生主体、成案的具体类型、运用成案判案的论证方式、成案的司法效力以及成案的时间效力等。笔者拟从以上几个过程对清代秋审成案机制进行研究。
(一)成案的产生主体
从对清代相关案例的考证来看,会审大典过后,刑部会领衔以参加会审的全体官员的名义将触犯死刑的案件向皇帝具题,由皇帝阅览具题后进行最后裁决。因清代所有死刑案件都需要经过皇帝裁判,故成案的产生主体是当时最高统治者,即皇帝。经过皇帝裁判的案件作为成案可以在下一次判案中援引。虽然将死刑裁判权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过于专断,但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这有利于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出现。并且,对于地方司法官而言,参考由皇帝作出裁判的死刑成案,不仅可以借此理解统治集团所传达的立法意图和审判思路,还可以转移因死刑裁量产生的心理负担,使死刑“正当化”。
(二)成案的具体类型
清代成案的内容较为全面具体,既还原了案件的真实面目,也对适用死刑的裁判过程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2]。从清代秋审成案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作用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2种类型。(1)创制型成案。该类成案是在制定法存在空白或过于抽象的情况下产生的,其本质是立法。如雍正年间发生的“丁乞三仔案”[3]。当时丁乞三仔年仅14岁,其与丁狗仔在同一个地方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就让其挑重的筐子,并扔土块击打丁乞三仔。丁乞三仔捡拾土块回击,恰好打中丁狗仔小腹,导致其丧命。该案中,由于丁乞三仔已满10岁,不能适用减刑的上请条款,且《大清律例》对因互相斗殴致人死亡有专门条款规定。因此,按照查明的案情,应该对案犯适用绞监候的刑事处罚。但雍正在阅览具题之后,认为丁乞三仔致人死亡情有可原,不宜适用死刑,应当对案犯从宽减等处罚,并赔偿死者丁狗仔丧葬费用[3]。此案填补了清代因致人死亡而触犯杀人罪中对未成年人进行从宽减等处罚的法律空白,在实质上起到了创制法律的作用[4]。(2)解释型成案。此类成案是对法律条文以及法律概念等的解释与细化。如道光年间发生的“山西郝全子殴伤赵庭科因风身死一案”[3]。郝全子先用拳头打伤赵庭科左眉,赵庭科揪住郝全子衣服不放,郝全子又用拳头打中赵庭科上唇,并将其一齿打落。赵庭科因左眉伤口处进风,过了6天之后,抽风死亡。案中声明,郝全子打中赵庭科左眉仅导致其皮破,并非致命之伤,且其用拳头打中赵庭科虽然导致赵庭科牙齿被打落,但也非致命伤。如果将此案按照斗殴处理,则因其并未殴打致命之处,又未造成极重之伤,并且被害人是超过5日因抽风死亡的,应当将殴打之人杖一百,流三千里。道光皇帝在审理此案时,对该案的关键性问题,即“折齿”能不能被包括在“损骨”之中有所疑惑。但当时相关成案较少,且进行注释的学者也没有议及。刑部为了对 “折齿”和“损骨”的关系进行释明,从生理和司法先例2个维度进行了阐述:从生理分析,刑部认为,牙齿会随着人的不同成长阶段而生长、掉落,并且因为磕碰导致牙齿掉落的事也时有发生,但从未听说过因为牙齿掉落而伤害生命的事。故“折齿”不能被包含于“损骨”之列。从司法先例而言,刑部列举了乾隆五年发生的相似案件,即“福建省庄佛被邱协锄柄撞落牙齿越三十五日身死案”,该案件仅对案犯仗责六十,并判处一年徒刑。最后,此案没有把“折齿”认定为 “损骨”的一种,而对其适用保辜的规定。在此案之后,“损骨”的范围得以进一步明确,特别是将“折齿”从“损骨”的范围中排除[5]。
(三)引用成案判案的论证方式
清代司法官援引成案的方式,主要是将问题案件与成案进行连接,然后利用一定的推理方法适用。具体包括情节类比、归纳援引及轻重相权等方式。同时,为了进一步明确成案适用的界限,司法官还结合采用个别情节类比等区别技术进行排除适用[6]。
1.情节类比。情节类比是指分析问题案件及成案的基本案情,并找出两者在基本情节方面的相似性或相关性,使问题案件得以援引成案的裁判原则。如道光二年,刑部在处理 “贾氏通奸案”时,援引“四川李陈氏案”[3],并将二者从死者年龄、案件情节、被害人身份等方面进行了类比。从死者年龄来看,两案死者都是14岁;从案情来看,两案的作案手段都较为凶残;从被害人的身份来看,两案死者都是童养媳。在“四川李陈氏案”中,案犯陈氏被判处永久监禁,而“贾氏通奸案”与该案情节相似,故刑部认为应当将贾氏判处同一刑罚,以免造成“同案不同判”。
2.归纳援引。归纳援引包括2种情况:(1)对于成案中已明确归纳出的原则,可直接援引;(2)对于成案尚未明确归纳,但已蕴含在成案基本情节中的原则可以作重新归纳,再行援引。就第一类而言,在大多数清代成案中,重要裁判原则已经被司法官归纳于成案中,所以在遇到问题案件时,可直接援引,不必再行归纳。如 “张王氏纠抢阎兆书家使女转妮案”[6],该成案已对案件的裁判原则进行了归纳,后世可直接援引。就第二类而言,为数不多的清代成案并未将裁判原则归纳于成案中,而在遇到问题案件时,司法官需要对成案的基本情节进行归纳总结,从而得出裁判的基本原则。如嘉庆年间,有一人名曰黄生,黄生之妻因患重病,痛苦不堪,不愿继续存活,黄生遵循其意愿,将其杀死[6]。刑部在审理此案时援引了4个类似成案,但这些成案并未将裁判的基本原则归纳其中。刑部在对这些成案的基本案情进行分析之后归纳出了应当适用的裁判原则。
3.轻重相权。轻重相权主要指的是通过“举轻以明重”和“举重以明轻”的方式来对量刑进行选择。如乾隆五十四年“湖广戴才五案”[3]。案犯与其弟因琐事发生纠纷,被其弟砍伤,随后,案犯将其弟戳伤致其死亡。刑部在审理此案时,援引了乾隆四十八年和乾隆五十四年的2个成案,并对2个成案的基本案情进行了比较,发现2个成案虽有相似之处,但关键案情和最终处罚均不相同。本案之案犯将其弟戳伤致死是因被其弟砍伤,而乾隆四十八年案之案犯仅被其弟出言顶撞。如果按照《大清刑律》的规定,对本案案犯处以流放之刑,则不符合轻重相权的原则。因此,刑部认为应当参照乾隆五十四年的成案对案犯判处徒刑。
4.区别技术。区别技术是指将问题案件区别于成案。司法官主要通过个别关键事实的不同来排除成案适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成案在司法论证及适用的过程中都表现出显著特征,即将情与法融合在一起,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我国留养承嗣制度。
(四)成案的司法效力
在清代,成案处于从属地位,其效力始终未获得制定法的正式认可[6]。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在援引次序上,制定法较成案而言具有优先性。刑部在处理案件时,均须依据律例来定罪量刑,如果新颁布的律例和旧有律例相冲突,以前者为准;如果律例对所涉案件尚无规定,则可以详细检视最近几年发生的相似成案,仿照其裁判原则处理[3]。即在定罪量刑时,优先适用律例,在律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再参考适用成案。
2.当制定法与成案出现冲突时,制定法效力优先,成案被归于无效。即便是钦定成案,亦可能失效。如嘉庆年间,有“陕西李氏兄弟合谋勒死其母案”[3]。该案中的案犯身患重病,依照当时律例不能将其“杖死”,但主审该案的地方知县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直接将其“杖死”。该行为违反了当时的律例,知县应当受到处罚。但嘉庆皇帝认可了该知县的处理方式,使其并未受到追究。然而,之后援引该案的司法官却因“援案杖毙,殊属不合”而受到处罚。其理由为,该案中知县的做法仅仅是“权宜之法”,不符合律例规定。如果发生类似案件,司法官皆援引该成案,将案犯杖死,难以维护公平正义。
3.当成案中所蕴含或归纳的裁判原则存在冲突时,应当回归制定法。通过对制定法中所蕴含的基本原则进行探究来明确问题案件应当适用的裁判规则。如 “张四财勒死大功堂弟张开言案”[3]。在处理该案时,就存在成案之间相互冲突而难以适用的问题。最终该案通过阐明成案中的关键案情,并“申明例义”,从而获得妥善处理。虽然成案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在司法实践中的效力却较大。其原因如下:(1)由于清代律例较为缺乏,立法滞后,使得成案在实践中被赋予和律例同样的法律效力;(2)成案可以作为适用法律的依据,即将其作为判决中法律适用的说理依据。
(五)成案的时间效力
在时间效力上,清代成案具有周期性。如道光六年“贵州小何田氏因为训责儿子导致婆婆老何田氏自杀”案等案例,在判决时均有“复查存馆十年档案内亦无似此之案”的记载。从这些案例来看,清朝刑部司法档案存放在律例馆中的时间约为10年, 10年之后,成案会被销毁,其效力也归于消弭[7]。虽然有的成案中所含的规则会被上升为条例,在10年的期限后仍然有效,但其已不属于成案的范畴。因此,10年存续期是清代成案时间效力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肇始于2010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该规定强调了案例颁布的主体以及案例的指导性作用,并对指导性案例与不具备指导意义的案例作了明确区分。至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已公布15批共84例指导性案例。但涉及死刑如何适用的案例仅有2012年公布的两例,即“李飞故意杀人案”和“王志才故意杀人案”。这两例案件的主要指导方向分别是死刑适用的条件与限制减刑两大问题。而其他关于死刑适用的疑难问题则没有相应的案例指导。因此,系统化构建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显得极为迫切。目前,我国死刑适用指导性案例数量较少,且并未对案例指导制度进行类型化区分,因此,对我国当前案例指导制度进行研究,并挖掘其存在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认识性难题:相关基本问题存在争议
1.性质认识不统一。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对案例指导制度性质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尚无统一定论。主要有2种观点:(1)认为从案例指导制度的形式、内容、效力等来看,其属于案例编纂制度向判例制度发展的中间制度;(2)认为我国案例制度的发展前景并不明确,可能与案例编纂制度合一[8]。
2.效力定位不统一。案例指导制度的效力直接影响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当前,其争论的焦点主要在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的效力位阶上。二者效力标准不明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出现。多数学者指出,二者的制定主体相同,功能和作用相似,因此,其效力位阶应当相同[9]。但另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司法解释的效力等同于制定法,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应低于司法解释的效力[10]。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指出,对于指导性案例,应该参照适用,但“应当参照适用”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该如何具体操作仍存在较大争议。
(二)实践性难题:自身缺陷与实践障碍
1.案例指导制度自身存在缺陷。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数量和质量存在问题。数量问题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没有固定日期,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虽然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的频率保持在每半年一批,每批数量基本稳定,控制在10个以内。但我国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正快速上涨,指导性案例的发布速度与其难以平衡。质量问题是指现存指导性案例大多缺乏指导作用,难以发挥其应有功能。如“李飞故意杀人案”,有学者就指出其仅重复了原有的法律规则,并未起到补充或解释法律的作用,缺乏相应的指导意义[11]。(2)案由和地区分布失衡。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公布15批共84例指导性案例。从案由分布上来看,民事类占55%,刑事类占17%,行政类占22%,知识产权类占4%,其他占2%。可见,各类案件在指导性案例中所占比例差异较大,发展不协调。从地区分布来看,这些案例大多来源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江苏、浙江等经济较发达的一线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少数来源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中西部广大地区,存在地域失衡问题。(3)指导性案例发布的基本内容存在缺陷。2016年12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3条指出,指导性案例的内容分为关键词、裁判要点、相关法条、基本案情、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等部分。但其存在2个问题:一是基本案情是由原判案例被裁剪后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了其他人为因素,可能使得其所传达的意志与原判案例不完全吻合。二是在基本案情之前增加的裁判要点是由该案件原审法官以外的其他专家事后总结而来的。基于此形成的裁判要点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审判原意,均值得商榷[12]。
2.司法实践存在困境。就目前各地法院的相关司法实践而言,指导性案例在实际适用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将问题案例与指导性案例加以连接。究其原因无外乎2点:一是对类似案例的识别技术缺乏。虽然我国法律体系既不同于大陆法系也不同于英美法系,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受大陆法系的影响较大。这点在法官对案例进行识别时表现得尤为明显。部分法官缺乏准确适用指导性案例的能力和技巧,在相同事实和不同事实之间,必要事实和非必要事实之间,以及关键事实的细微变化是否会对指导性案例的适用产生影响等方面,常常难以判断。二是法官惯有的演绎推理思维和适用指导性案例所需的类比推理思维相冲突。类比推理思维是准确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必要思维方式,即通过归纳的方式制造出特殊规则,然后再将这个特殊规则运用于相同或类似的个案之中,并得出结论[13]。可以简单概括为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过程。而演绎推理模式表现为从抽象再到具体的推理过程。具体指的是,法官立足于现有法律规范,通过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将事实囊括于法律规范之中,从而完成“规则加事实等于结论”的推理过程。将两者进行比较分析可发现,类比推理思维与我国惯用的演绎思维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这使得法官在援引指导性案例进行案件裁判时将遇到较大的现实挑战。(2)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同类型案件时,没有明确地将指导性案例列在判决书中,而是仅在进行推理的过程中参考指导性案例。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法官在审判中难以获得独立性,因此,其在工作中表现得较为谨慎,没有直接对指导性案例进行参照[14]。这不但难以提升法官的审判水平,而且会导致案例指导制度形同虚设。
三、我国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
系统化、专门化构建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既可以使我国死刑的适用更加准确和公正,同时也可以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综合以上对清代秋审成案机制以及当前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现状的考察,笔者认为,我国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应当从案例制度本身和司法适用2个方面入手。
(一)案例指导制度的自身建设
1.产生主体。《实施细则》第4条规定,死刑适用指导性案例的产生主体应为最高人民法院,且由其直接产生。从我国目前司法现状来看,因审级的限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审理的案件较少。若发布主体限制为最高人民法院,则需最高人民法院深入地方调研、重新梳理和审查案情,会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因此,有学者提出将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放权至高级人民法院[15]。笔者认为,该观点针对其他案件可以借鉴使用,但对死刑适用的案件则不适宜。原因有2点:(1)所有适用死刑的案件都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最高人民法院掌握死刑适用的第一手资料,因而无需重新调研和审查,这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2)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可以确保案例筛选和适用标准的严格统一,从而保障死刑适用的严肃性。因此,死刑适用指导性案例的产生主体应明确限定为最高人民法院。
2.案例归类。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指导性案例进行归类时,可以根据案件中被告人的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所地不同,以省为单位来创建分类。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若针对同一行为,各地均采用统一的适用尺度,可能会影响司法公正。因此,采用该种分类方式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导量刑,特别是指导死刑缓期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区分适用。如在我国贪污贿赂案件中犯罪数额对量刑的影响较大,在司法实践中,因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别,法官针对同样的犯罪数额,在其他犯罪情节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量刑往往会不同。故应对指导性案例的来源地作出区分,分别归类。
3.具体类型和内容。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禁止法官造法。因此,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的具体类型只能为解释型案例。其主要作用应是在刑法条文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模糊的情况下对条文进行说明和解释。虽然指导性案例说明和解释的内容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存在争议,但其重要功能在于为某类案件的解决提供相对统一的标准。对于一些疑难复杂且法律存在空缺的案件,确定的标准实则更为重要。同时,在案件内容选择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可能选择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较为统一的案件,这有利于提高裁判的认可度。且指导性案例仅提供事后由专家总结的简单裁判要旨,不利于法官对该案的理解与适用。因而,提供能还原案件真实面貌的法官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是对指导性案例有效使用的重要途径。
4.司法效力。学术界和实务界一直对指导性案例的司法效力争论不断,争议焦点主要有2个。(1)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之间效力大小的权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所解释的对象是我国现行法律,即将法条具体化。因此,司法解释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可以援引司法解释作为判决的依据。而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有所差别。从指导性案例的产生方式来看,指导性案例中所抽象出的裁判规则是由部分专家事后提炼、总结的,这与法律有所不同。从运用指导性案例的目的来看,指导性案例的主要作用在于最大可能地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出现,而非运用判例来判案。《实施细则》第9条规定,相关案件“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即指导性案例可以作为法官审理案件时说理的依据,而非裁判依据。因此,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应低于司法解释的效力。(2)指导性案例与现有案例编撰制度之间的效力差别。我国案例编撰的主体具有多样性,既有学者基于学术研究目的而编撰的案例集,也有法院编撰的典型案例集。虽然各类案例编撰均有其合理性,但这些案例是否可被援引为法官说理的依据却无法可依。因此,案例编撰应不同于指导性案例,无法律效力。
5.时间效力。目前,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并不存在时间效力的相关规定。由于目前我国指导性案例的数量较少,对该方面的研究不是特别迫切。但也正是由于该方面的研究缺失,才会导致最高人民法院有意限制指导性案例的数量。指导性案例的数量限制使得司法实践中很多疑难问题无法被全面覆盖,法官判案存在困难。同时,指导性案例所援引的法律规范变化,必然导致指导性案例丧失拘束力,不能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参照。对其时间效力进行规定是建立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从两方面进行规范:(1)可以借鉴清代秋审成案机制中时间效力规定,将其时间效力统一设置为10年,以应对经济社会的发展;(2)指导性案例的时间效力应与刑法修正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相同步。即刑法修正案通过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应使相关指导性案例当然失效。
(二)案例指导制度的司法适用
1.论证方式。论证方式即将问题案件和指导性案例进行连接的方式。应主要采用类比推理的方式。但在进行类比推理时应注意,因基本情节的类比不具有可操作性,故应注重对关键事实和争议焦点的类比,以便准确判断问题案件和指导性案例的联系。但在关键事实和争议焦点的把握上,应切忌主观臆断。此外,在量刑考量方面,应结合适用“举重以明轻”和“举轻以明重”的推理方式。
2.明示使用。针对目前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对指导性案例明示适用较少的问题,在构建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时,需要提高明示使用率。即宜规定法官应将指导性案例的运用体现在判决书中。这一方式可以提高法官在应对一些政策性较强或社会关注度较高案件时的司法独立性。但应注意,明示使用是指在判决说理部分对指导性案例进行援引,而非将其作为法律依据来适用。
[1]陈兴良.死刑适用的司法控制——以首批刑事指导案例为视角[J].法学,2013(2):43-57.
[2]柏桦,于雁.清代律例成案的适用——以“强盗”律例为中心[J].政治与法律,2009(8):131-140.
[3]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112,369,813,1364,1598,1618.
[4]宋伟哲.清代青少年杀人犯罪的分析与启示——以《刑案汇览》《历代判例判椟》《驳案汇编》为中心[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5(6):75-80.
[5]胡兴东.中国古代判例法模式研究——以元清两朝为中心[J].北方法学,2010,4(1):115-124.
[6]王志强.清代成案的效力和其运用中的论证方式——以《刑案汇览》为中心[J].法学研究,2003(3):146-160.
[7]胡兴东.清代成文法典下判例机制原因及特点[N].人民法院报,2011-07-15(5).
[8]陈兴良.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09.
[9]朱建敏.构建案例指导制度的几个具体问题——基于效力定位的视角[J].法治研究,2008(7):35-39.
[10]泮伟江.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J].清华法学,2016,10(1):20-37.
[11]周光权.判决充分说理与刑事指导案例制度[J].法律适用,2014(6):2-9.
[12]刘作翔.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最新进展及其问题[J].东方法学,2015(3):39-46.
[13]邓志伟,陈健.指导性案例裁判要旨的价值及其实现——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研究对象[J].法律适用,2009(6):40-43.
[14]张骐.再论类似案件的判断与指导性案例的使用——以当前中国法官对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经验为契口[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21(5):138-153.
(责任编辑: 何晓丽)
Constructionofcaseguidancesystemtodeathpenaltyapplication—TakingthemechanismoftheautumntrialinQingDynastyasreference
FENG Yi-qiang1, WANG Jian2
(1.SchoolofLaw,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9,China;2.Schooloflaw,ZhejiangUniversityofTechnology,Hangzhou,Zhejiang310014,China)
China has not established a case guidance system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yet the mechanism of the autumn trial in Qing Dynasty has played a large role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to the judge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main body, specific type, way of argumentation, judicial effect and time effect of the autumn court in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case guidance system in our country and points out problems including the vague understanding of fundamental issues, difficulties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etc. Therefo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relevant system of the autumn trial mechanism in Qing Dynasty, and we should use the case system itself and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to construct the case guidance system of death penalty application in China.
mechanism of the autumn trial in Qing Dynasty; death penalty application; case guidance system
DF718
A
1671-6922(2017)05-0088-06
10.13322/j.cnki.fjsk.2017.05.014
2017-05-04
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CLS〔2016〕C15)。
冯义强(1990-),男,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