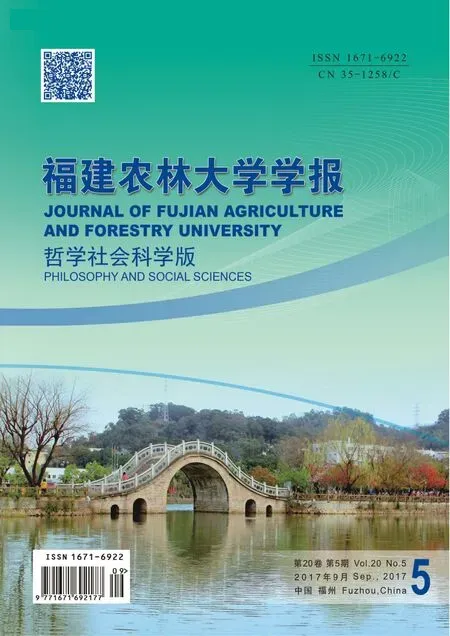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问题分析
——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视角
2017-04-04张腊梅
刘 艳, 张腊梅
(1.安徽行政学院政法社文教研部,安徽 合肥 230059; 2.九三学社安徽省委,安徽 合肥 230001)
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问题分析
——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视角
刘 艳1, 张腊梅2
(1.安徽行政学院政法社文教研部,安徽 合肥 230059; 2.九三学社安徽省委,安徽 合肥 230001)
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之间的逻辑联系是建立在农村土地融资功能发挥的基础上的,发挥农村土地的融资功能亟须构建立体化的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当前,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既存在现实困境,又存在法律制约,必须从制度完善、流程再造、平台搭建和风险防控等维度构建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农村土地金融服务方式,切实保障农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
新型城镇化;农村土地改革;金融服务;供给体系
新型城镇化发展之“新”关键在于摆脱对土地城镇化的过度依赖,建立全新的土地资源利用方式,使之更好地发挥要素功能。当前,农村土地改革也必须围绕发挥土地要素功能这个中心任务,通过落实农村土地财产权保护,有效平衡农村人地关系,解决农村人口流动与农村土地产权固化的结构性矛盾。在农村土地改革中,创新金融服务是缓和农村人地矛盾的重要抓手,也是有效盘活农村土地财产权的基本手段。因此,有必要以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创新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方式,构建完善的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使农村土地改革成为支撑城镇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
一、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的逻辑联系
当前,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融资受阻、保障不全、信用缺失不仅制约了农村土地产权的实现,而且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正确理解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之间的关联性,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创新农村土地金融服务方式的首要任务。
(一)新旧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的倚重不同
无论是以土地城镇化为发展路径的旧型城镇化,还是以人口城镇化为发展路径的新型城镇化,本质上都是要通过城镇化发展消除城乡之间的要素流通阻隔。而新型城镇化区别于旧型城镇化的最本质要义在于发展路径的重大转变,集中表现为对待土地资源的态度发生根本扭转。旧型城镇化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中,更多地将土地作为单纯意义上的生产资料,遵循以土地扩张为手段的造城建市轨迹,以土地城镇化拉动人口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发展则是要摆脱土地的依赖性,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利用土地要素的辐射作用拉动人口、资金和产业的集聚,遵循人口城镇化带动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轨迹。换言之,旧型城镇化对土地的利用侧重在其资料性,土地的融资功能仅是通过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体现出来,农村土地的融资功能则受到限制。新型城镇化对土地的利用则突出其要素性,充分发挥城乡土地的资本功能,尤其是提升农村土地的融资能力。然而,农村土地的要素功能发挥显然掣肘甚多,农村土地资本性的融资功能基本处于受抑制状态,这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提升农村土地融资能力,重中之重是加强农村土地的要素流通性。要素流通首先要依托市场平台,遵循市场平台运行规则才能实现要素无障碍流转。于人口而言,就是必须依托劳动力市场,在城乡间实现劳动力自由、有序的转移;于土地而言,就是要依托土地交易市场,实现城乡土地财产权的公平交易。依托市场交易的要素流转,核心要义是实现要素价值。在要素流通环节,金融服务的供给不可或缺。重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必须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解决城乡土地供给与利用结构的突出矛盾,应从服务生产经营需要的融资担保、服务风险负担需要的保险保障、服务监督管理需要的信用评价和服务借贷对接的中介沟通等4个方面加强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的构建。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土地融资功能发挥的需求
只有改变对城镇化发展遵循土地城镇化路径的认知,才能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土地融资功能发挥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以人口城镇化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依靠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农村人口的有序转移。发挥农村土地融资功能,创造就业机会,可从以下2个方面着手:(1)通过农村土地融资为小城镇发展提供产业资金支持,从而增加就业岗位和就业选择,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出路问题;(2)通过农村土地融资解决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资金需求,在提高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效率的同时,解放农业人口对土地的人身依附性,解决城镇化发展中所需的非农产业劳动力来源问题。因此,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土地融资功能发挥的需求并不单纯体现在土地本身对产业发展的支持上,更多地体现在附着于土地之上但又脱离土地本体的要素集聚作用。具体而言,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土地融资功能发挥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土地融资的产业支撑功能。农村土地融资功能的发挥对农业发展起到支持作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承包地的融资为土地经营者解决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2)未发包地的融资可以充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实力,使本已被虚置的集体组织能够发挥实体作用;(3)土地融资还能为小城镇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来源,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事实上,农村土地融资的功能发挥对城镇化发展最直接的作用是为产业发展提供资源补给,补给土地供应和人力资源。人口城镇化主导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必然使乡村土地脱离土地“物的性质”,而逐步“资本化”[1]。也唯有此,方能真正凸显农村土地推动城乡产业发展的资本功能,这是农村土地发挥要素作用的关键所在。
2.土地融资的价值保障功能。农村土地实现可融资是对农村土地财产价值的肯定,前提是农村土地财产权利可以通过市场平台实现自由公平的流转。在实现农村土地融资过程中,只有农村土地财产权作为一种可担保物权存在时,方能真正消除资金供贷方债权实现的顾虑。也就是说,农村土地融资过程的顺利进行必须依赖于农村土地财产权与债权的价值对等性。农村土地融资的价值保障功能得到实现,有利于解决新型城镇化发展对资金和土地的需求问题。
3.土地融资的人口转移功能。之所以要摒弃过去单一依靠土地扩张发展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主要是因为这种方式忽略了土地的拉动效应,没有带动人口的同步城镇化。农村土地作为一种静态要素,即使其性质改变为国有,也不能把单纯的土地城镇化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只有将人口这种动态要素城镇化,通过人口城镇化建立起与之匹配且规模适度的土地城镇化,这才符合土地集约利用的基本导向。简言之,新型城镇化必须是建立在土地城镇化规模与人口城镇化规模匹配的条件下,通过土地融资带动产业发展,从而间接引导人口有序转移。在这个意义上,新旧城镇化倒置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因果关系。
(三)农村土地融资功能发挥对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的要求
农村土地融资功能的发挥是城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而这一功能的发挥又依赖于农村土地金融服务的同步支持。缺失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农村土地融资功能就缺少了对应的实现渠道。具体而言,农村土地融资功能发挥要求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必须具备3个基本条件。
1.制度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出发,改革要素供给方式和供给结构,对各类资源进行重新排列组合,所有的供给侧改革首先要依托的是制度平台。因此,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的创新首先是制度供给的创新。健全的农村土地金融服务制度有利于构建畅通的土地要素流通渠道和严密的土地金融风险防控措施。完善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制度,必须围绕科学性、可行性、均衡性和统一性等原则进行制度优化。
2.市场化的金融服务平台。农村土地金融服务的供给过程必须依靠市场化平台运作,方能实现要素流通通畅和资源集聚效应。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之所以存在政策落实难的尴尬处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市场的平台效应缺失,从而造成土地财产价值实现难、土地财产权流转难、资金融通风险保障难的“三难”局面。具体来说,因农村土地要素流通市场不健全,导致土地财产价值实现难,并直接影响土地财产权的流转;因农村土地经营信用评估市场缺失,导致农村土地流转过程监管难度大;加之相应的农业经营保险措施不到位,直接加大了资金融通风险。在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市场化平台中,必须把农业经营产前、产中和产后所需的融资、保险、评估、信用乃至市场监管等环节列入其中,方能真正实现要素流通无障碍,土地财产价值有度量。
3.规范化的金融服务方式。如前所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就包含要素供给方式改革之义,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除了制度创新和平台重构外,尚需要规范化的金融服务方式衔接,主要是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和服务手段,对接农业生产经营和城镇化建设的需求。尽管当前各地陆续有不同的创新金融产品推出,但与农业经营的实际需要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如都市农业作为农业发展的一种新业态,休闲旅游和乡村旅游是其重要的产业形态。但目前很少有政策性保险对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和景观产品进行风险保障,导致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经营者风险无从转嫁,经营积极性受到挫伤。
二、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融资类金融服务供给的困境
当前,农村土地遭遇融资瓶颈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土地财产价值实现难。受制于法律和市场两方面的条件限制,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村其他建设用地的使用权难以真正融入土地交易市场。出于规避自身经营风险的考虑,金融机构对价值实现渠道受阻的担保物往往采取退避三舍的态度。目前,除政策性小额贷款外,资金需求强烈的大宗农村土地经营者难以通过土地融资满足实际经营需要。从全国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试点地区情况看,绝大多数农村土地经营者获得融资都附加了政府信用、企业股权出质等脱离土地财产权之外的其他融资担保物,真正意义上的土地融资少之又少。造成这一局面的现实因素很多,但直接相关的原因是农村土地财产权流转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担保在政策松绑后,土地融资依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政策尚未松绑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实现土地融资更是难上加难。据笔者调研,从安徽农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的试点情况看, 2016年全省农村住房财产权担保贷款的不良率逐月攀升,农村土地使用权融资市场发展前景堪忧。
(二)保障类金融服务供给的困境
保障类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的主渠道是农业保险。现阶段的农业保险多为政策性保险,保障面小,且理赔额度较低。加上农业经营者参保意识较低,在面临自然灾害时,经营者的受损获赔比例甚小。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保险品种结构不健全,针对农业发展新业态的相关保险险别尚未建立,对农村土地经营方式创新没有起到相应的保障作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者的创新能动性。根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办公室对外公布的数据,2016年全国的31个省份(除港澳台外)均遭受不同程度自然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926.67万hm2,洪涝灾害损失达到3661亿元[2]。但同时,农业保险在2016年洪涝灾害中总赔付金额为348亿元[3]。尽管不能以绝对数简单衡量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低,但从农业保险赔付金额的计算方式和理赔程序上看,农业保险公司坚持的成本导向与投保农户预期的收益导向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也就形成农业保险公司因高赔付率导致运转艰难与农户因理赔难导致参保意愿不高的矛盾格局。
(三)监管类金融服务供给的困境
农村土地监管类金融服务供给主体既包括保监会、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农业监督管理职能部门等政府监管部门,又包括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基金理事会等非政府监管组织。当前,农村土地金融服务监管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过程监管不均衡、偏重事后监管、风险应对监管重于风险预防监管。农村土地流转经营中,因拖欠农户租金或拖欠银行贷款而撂荒土地等现象屡见不鲜,融资借贷的安全风险边际没有实时指标提示,从而降低金融机构开展农村土地融资贷款业务的积极性。
(四)评价类金融服务供给的困境
评价类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1)信用等级评价体系不健全。目前,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中,对土地经营者的信用等级评价标准采用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主要是从银行信用的角度对经营者进行信用等级评价,主要考评贷款人还贷情况,但从经营者资质、能力和业内声誉等其他信用角度进行的信用等级评价很少。(2)信用等级评价机构空缺。基于银行信用角度进行的农村土地信用等级评价一般由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而其他土地经营者经营信用等级评价机构空缺。评价类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造成了农村土地经营过程中失信行为屡有发生,不仅损害了农村土地权利人利益,也损害了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利益,乃至对关联产业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面临的法律制约
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困境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的是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存在不足,导致金融服务供给不畅,资金融通遭遇阻力。法律上对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化、城乡土地融资功能差异化和农村土地用途管制化等。
(一)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化导致农村土地融资功能弱化
虽然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均对农村土地产权作出了规定,但仔细分析法律规定,不难发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还是比较模糊的。(1)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并排除了公共利益需要的国有化征收、征用外的其他改变土地性质行为。由于公共利益的法律边界模糊,导致征地行为时常会侵害农村集体和农民利益,不仅引发较多的社会纠纷,而且容易使金融机构产生融资顾虑。从本质上说,正是由于这种边界模糊的法律设置,导致农村土地财产权属性弱化,进而影响农村土地产权融资功能的发挥。(2)我国《土地管理法》尽管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设计了明确的经营管理者,即“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但仍然存在2个问题:一是集体经济组织的边界不明;二是村民小组代行经营管理权在理论上并不具有合法性,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主体性质的界定相悖。综上所述,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并没有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从中分离出来的农村土地经营管理权设置明确的权利主体,由此导致的农村土地权利虚置问题为农村土地融资行为设置了障碍。
(二)城乡土地融资功能差异化导致农村土地财产权虚化
从我国《担保法》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中,可以看出城乡土地融资功能的差异化安排。《担保法》第36条和第37条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担保,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除“四荒地”外)和宅基地使用权均不可设置抵押。《物权法》尽管承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但同时又在第184条作出了类似《担保法》第37条的规定。由此可见,在发挥农村土地融资功能的途径上,法律为国有土地和农村土地进行了迥然相异的制度安排,使农村土地产权基本无法实现对外融资。进一步说,当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受阻、融资无望时,其财产权利属性也就无法得以实现,此时的农村土地财产权利不过是一种被虚化了的财产权而已。
(三)农村土地用途管制化造成农村土地价值实现渠道垄断化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条规定,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尽管除农用地以外的农村其他用途土地(即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没有在该条规定中予以直接的用途管制,但由于《物权法》中并未承认农村建设用地的财产权属性,且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受到诸多现实条件制约,其价值实现的途径也十分有限。同时,农村未利用地因其存量极小和天然用途受限,其价值也难以实现。因此,《土地管理法》第4条规定用途管制的对象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农村土地。这一规定在保障农用地规模的同时,又在事实上造成另一个后果,即对农村土地的用途管制使国有化征收变成了农村土地价值实现的唯一渠道。由于农村土地缺失相应的价值实现平台,《宪法》为公共利益需要征地的行为设立了合法性依据,农村土地财产价值的实现只有先通过国有化征收改变所有权性质、再置已转变性质的土地资源于国有土地交易市场交易这样的“曲线路径”来进行。但此时最大的问题是,交易后的土地已并非为原来的农村土地产权人所得,其财产价值既不为原自物权人所有,又不为原他物权人所有。理论上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私权既得状态,过去城镇化发展中通过政府强征集体土地、改变土地所有权支配状态的做法,事实上更有公权挤占私权之嫌,故集体私有的农村土地应该比国家所有的城市土地享有更可靠的财产保障[4]。但在农村土地价值实现渠道单一化的条件下,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不但管制了农村土地的用途,而且限制了农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
四、构建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的路径选择
(一)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
构建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必须从制度优化、流程再造、平台搭建和风险防控等4个要素建设入手,改革金融服务供给方式,方能实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
1.构建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必须进行一系列制度优化。制度优化是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构建的基础,不仅涉及到顶层设计的合理性问题,也关系到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的顺畅运行。针对当前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中存在的制度瓶颈和法律制约,金融服务制度优化重点应集中在以下8点:农村土地产权清晰化的法律安排,农村土地财产权流转障碍破除,农村土地他物权担保限制排除,农村土地经营信用等级评价制度构建,征地行为限制标准细化,农业保险制度完善,农村土地市场交易制度完善和农村土地财产权价值评估制度确立。
2.构建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必须进行金融服务流程再造。农村土地金融服务流程再造主要是为了使金融服务与农业生产周期相契合,减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的中间环节,降低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融资成本。同时,还应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方式,推广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平台,推行便利于农村土地经营者的快捷服务方式。
3.构建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必须进行金融服务平台搭建。当前,农村土地金融服务平台比较薄弱的环节是交易平台和中介平台。尽管农村土地流转平台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但其运行的市场化程度不足,且与金融服务供给的衔接性不强,运行模式单一。必须在农村土地市场中介入风险防控监测系统和金融服务对接系统,确保平台要素完备。此外,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应依托中介平台进行,适度转嫁金融机构的风险,减轻涉农融资金融机构的运营负担。国家财政补贴资金应择优支持基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开发的融资平台和平台类公司,以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开发公司[5],而不应仅限于农业生产性经营补贴。
4.构建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必须进行金融服务风险防控。服务供给的末端形态是风险防控,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的特殊业态发展体制决定了必须充实评价、监管和保障等环节的措施补给,并以此起到风险防范的作用。建立科学的金融服务指标评价体系在当前显得尤为紧要。农村土地金融服务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应该本着既依托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又有别于金融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突出农村土地经营的业态特点和实际需求,尤其要加强事前评估和事中监测,设置风险提示红线。农村土地金融服务的监管应突出立体化和多元化的特点,除目前的政府管理部门监督外,应切实发挥社会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我监督的职能。农村土地金融服务的保障措施应定位在基础保障的目的上,除发展现有农业保险事业外,也应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事业提升农户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探索建立农村金融风险基金制度,确保金融服务安全。
(二)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构建的具体路径
1.完善农村土地产权的法律设计。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构建的前提是解决现有农村土地产权边界模糊的法律制度安排问题。任何一项财产,只要产权不清晰就无法实现自由流转,其价值也就不可能通过市场环节得以体现。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边界,应从以下方面入手:(1)明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仅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进行确权登记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将这一权利落到主体上去。因此,除应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法人资格确认外,还应进一步细化法人的权力结构,建议在农村集体组织内部建立起权力机关、管理机关和监督机关,形成分权制衡的权力配置结构。(2)明确农村土地用益物权的权利边界。最主要的是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权能配置的调整。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按照权能分置的思路,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适度分离,对通过流转方式取得农村土地经营权的个体应进行流转经营权确权,确保农村土地经营的可持续性和可再次流转性。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事实上也可以仿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分离的方式开展确权工作,分离宅基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鼓励农村空宅入市流转。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入市必须针对当前实践工作的难点,建立起动态的经营性确认制度,在控制总体规模的基础上,适时调整对农村建设用地经营性的认定,确保农村建设用地在满足农村自身建设需要的基础上,开展存量建设用地指标的流转。
2.建立健全农村土地经营信用体系。健全的信用体系是降低融资风险的先决条件,这是适用于所有金融服务供给的基本规律,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亦不例外。但与一般金融服务不同的是,农村土地金融服务既扶持土地经营,又依托于土地经营。因此,在提供农村土地融资性金融服务过程中,除了要考量服务对象自身的信用状况外,更应该考量服务对象作为农村土地经营者的经营信用。面对当下频发的农村土地流转经营人弃逃撂荒、拖欠土地租金等失信经营行为,必须尽快建立起完备的土地经营信用体系,并将信用考评的结果作为经营准入和融资准入的依据,主要包括流转主体资格、流转方经营范围和信用记录等方面;建立农村土地经营与融资服务中失信行为的“黑名单”制度;构建农村土地流转诚信体系和农村信用数据库平台,提供流转行为信誉担保服务[6],防范农户土地财产权益和金融机构资本财产权益受损。
3.建立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中介平台。农村土地财产权价值实现难和度量难是加剧农村土地金融机构资金风险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前农村土地金融机构涉足农村土地担保意愿不强的最主要原因。农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有效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即通过供求体系与价格机制科学衡量农村土地财产权益。但是,长久以来靠计划安排配置农村土地资源的方式和靠自给自足安排农村土地经营的生产模式,导致农村土地市场难以培育,金融资本下乡缺乏投资担保中介,农村土地融资缺少科学的价值评估服务。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中介平台的建立,可以借助国有土地价值评估机制的资源。在服务要素共享的基础上,将平台资源中的审计、评估、鉴定、法律等第三方中介服务及机构引入农村土地财产权益交易过程中,从而为城乡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创造先决条件,为解决农村土地资产估值难和处置难提供基础条件,减少金融机构的投融资顾虑。
4.建立风险共担的投资担保体系。在农村土地融资过程中,必须从农村土地金融机构的企业化性质出发。通过有效降低农村土地金融机构融资风险,提高其开展农村土地金融服务的积极性,实现金融机构获利与农村土地经营者获益的双赢。可见,建立风险共担的投资担保体系能够有效调动农村土地金融服务的多方积极性。实践中,为刺激农村金融机构向农村土地经营注资,常常由部分乡(镇)政府出面为土地经营者提供担保,这种做法于法无据,于理则会加大了基层政府的债务风险。《担保法》第8条对政府作为保证人主体资格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风险共担体系构建中政府处于无为状态,而是政府应该将职能严格限定在引导、管理和服务环节上,即通过提供政策支持、融资人信息服务和融资合法性监管等服务,保障农村土地金融服务的顺利运行。而只有直接介入投融资过程的土地流转双方、金融服务机构以及第三方服务机构才是真正的风险共担主体。农业作为受自然条件影响甚大的弱质产业,其融资风险相对较高,应鼓励农村土地经营者在正常经营年景里提取少量收益作为风险储备金。在遭遇突发情况时,可以发挥风险储备金的“蓄水池”作用,帮助分担金融机构的债权实现风险。
5.进一步理顺农村土地市场体系。多数时候,政府主导下建立的农村土地市场体系并非完全遵照市场规则运行,在此条件下形成的农村土地市场体系并不健全,因而通过市场作用实现农村土地价值往往也困难重重。在农村土地融资过程中,必须完善农村土地财产权从入市到出市的全过程市场链条,加强土地流转的过程管理,在市场准入、专业化服务提供、市场信息公开、流转合同规范化、信用等级评价、财务资料审计与公开以及经营过程跟踪服务等环节发挥市场的作用,克服暗箱操作、随意操作和无序运行的弊病,使农村土地市场在规范、公开和诚信的环境中运行。(1)在市场准入上,工商资本下乡带来的农村土地经营风险已经屡有显现,但农村土地经营又需要依赖工商资本的扶持。因此,必须对工商资本下乡行为进行严格的资信等级评估,辅之以农业项目经营承诺制,规定不具备相应资信条件和承诺要求的,不得经营农村土地。将失信经营者列入失信“黑名单”,并设定今后若干年内的从业禁止,以此培养出工商资本下乡经营农村土地的行为理性。(2)在过程监控上,应该着力建立完整的经营情况监测制度,建立预警警示制度,适时监测农村土地经营者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对经营和财务状况不良的经营者应采取必要的分级预警与约束措施,防止农村土地财产权益受损。
6.适度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农村集体产权融资难的最主要原因是其产权的资本活力不足,大量沉睡的农村土地财产权亟待盘活。其中,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沉睡资产中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盘活宅基地资源是直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和间接壮大集体经济的新增长极。除鼓励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外,还应该推进闲置宅基地以合适形式进行交易[7],适度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是一项比鼓励农民退出宅基地更具有可行性的盘活举措。当然,流转宅基地让农民在一定范围和期限内通过让渡宅基地使用权取得更多的财产收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通过放开农村宅基地的流转限制,允许一部分产业资本以租赁、入股等方式取得一定期限内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能够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条件下,解决当前农村产业发展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问题,吸引产业资本积极参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只有农村集体经济得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有能力成为承担农村土地融资风险的担保主体。
五、结语
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的构建对解决当前农村土地财产权流转不畅、城乡产业发展资金短缺等问题,以及促进三大产业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必须引起政府管理部门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供给并不单纯是土地和资金要素的简单排列组合,而是农村土地经营乃至整个农业产业经营所需的全要素优化组合的服务供给系统。破解农村土地金融服务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难题,一方面,依赖于土地要素功能发挥,突出农村土地要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辐射和集聚作用;另一方面,以金融服务供给为手段,在农村土地金融制度完善、流程再造、平台搭建和风险防控等环节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发挥金融资本在农村土地经营方面的积极作用。
[1]毛伟华.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制度安排的政策选择研究[J].甘肃理论学刊,2014(5):166-169.
[2]陈博.国家防总:全年洪涝灾害损失3661亿元[EB/OL].(2016-12-22)[2017-06-14]. http://news.cctv.com/2016/12/22/ARTIEgp4dLFAD0UmkQzwp8fu161222.shtml.
[3]项俊波.去年农业保险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348亿元[EB/OL].(2017-02-22)[2017-06-14]. 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170222/4109193.shtml.
[4]张千帆.城市化不需要征地——清除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宪法误区[J].法学,2012(6):19-24.
[5]张云.农村土地产权改革背景下“三农”金融服务创新的思考[J].当代农村财经,2015(10):56-61.
[6]金保彩,郑义.加快推进农村土地资产经营的政策研究[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4(1):39-41.
[7]刘同山.资产化与直接处置: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J].经济经纬,2016,33(6):42-47.
(责任编辑: 林小芳)
Analysisonthesupplysystemofrurallandfinancialservice—Basedontheperspectiveofnewurbanizationdevelopment
LIU Yan1, ZHANG La-mei2
(1.Departmentofpoliticalandlegalandsocialculture,AnhuiAdministrationInstitute,Hefei,Anhui230059,China;2.JiusansocietyofAnhuiprovincialpartycommittee,Hefei,Anhui230001,China)
The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supply of rural land financial services is based on playing the financing function of rural land. Playing the financing function of rural land needs to construct the three-dimensional supply system of rural land financial service. At present, there are real difficulties and legal constraints in the supply of rural land financial servic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supply system of rural land financial service, reform the rural land system and create the mode of rural land financial service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 improvement, process reengineering,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risk preventi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new urbanization; rural land reform; financial services; supply system
D668
A
1671-6922(2017)05-0001-07
10.13322/j.cnki.fjsk.2017.05.001
2017-02-28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AHSKY2014D04)。
刘艳(1978- ),女,教授。研究方向:民商法学、经济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