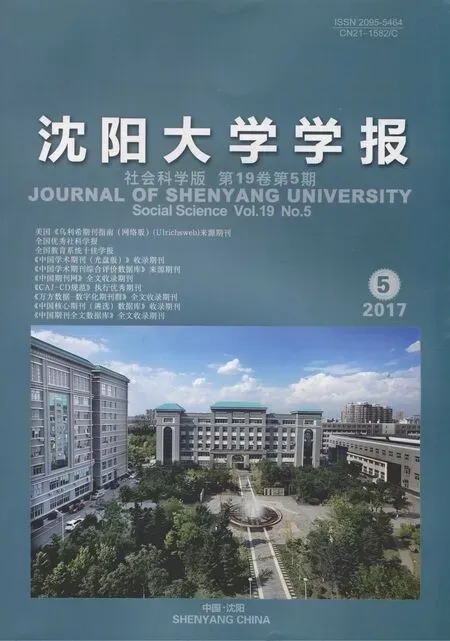Moment in Peking的文化自觉哲学观
2017-04-03王绍舫
王 绍 舫
(沈阳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41)
MomentinPeking的文化自觉哲学观
王 绍 舫
(沈阳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41)
阐释了文化自觉的定义,指出:生存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应深刻了解本身文化优缺点,有“自知之明”,主动开发自身文化,承担与主流文化接轨的历史责任,论述了MomentinPeking除了活化庄子,还隐藏着维特根斯坦身影,其言说框架充分体现了弱势文化向主流文化靠近时“知彼”与“扬我”的“文化自觉”哲学观。
MomentinPeking; 文化自觉; 哲学观
一、 文化自觉的定义
文化自觉是指生存在一定文化中的人,深刻了解自身文化的优缺点,有“自知之明”,主动开发自身文化与主流文化接轨,担当发展文化的历史责任。100多年前西方列强用大炮敲开我国国门,国人放弃天朝大国的夜郎自大思维,开启了文化自觉时代,主动学习西洋科学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自觉得到历史性发展,胡适之先生的“整理国故”、鲁迅的“拿来主义”、林语堂的“送出主义”,都体现出不同维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20世纪末,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概念,文化自觉理念得以确认,并得到众多理论研究者支持。
林语堂(1895—1976)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毕生游走在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以其独特慧眼透视出古今圣贤灵魂的对接轨迹,为文化自觉哲学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将中国古代庄子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两位时间上相隔两千年、空间上跨越两大洲的“语言与世界同构”融会贯通,产生充满梦幻性东方色彩的哲学思想。作为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不应该建构理论,而应该提供关于世界、思想和人生的表现形式。他的哲学观念概括起来包括三个方面:研究世界的本质;研究人生的本质;给思想和语言划界。他认为现实世界之外是神秘“不可说”的,提出语法研究和概念研究,提倡哲学只追问人类已经知道的事情,逗留在日常语言当中。批判世人忙于贪新求知,与庄子言说的“天下皆知求其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极为相似。
采集东西方共同的哲学之光,林语堂旅居巴黎时用英文创作出小说MomentinPeking(《京华烟云》)。MomentinPeking在文学上的贡献是积极的,讲述了清朝灭亡后,民国时期北平牛、曾、姚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40年间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有历史演义,有风俗变迁,也有军阀混战,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画卷。此书的哲学意义在于将庄子和维特根斯坦哲学观念有机结合,犹如请西洋人进来,随林氏东西散步,观赏风景,同中国人一起过日子,一起欢快、愤怒和逃难,最终成功将中国社会介绍给西洋人。
MomentinPeking充分体现了弱势文化向主流文化靠近时的“文化自觉”哲学观,在世界舞台“争夺话语权”,展现了“知彼”和“扬我”的特点。MomentinPeking实现了在语言层面“发出中国声音”,并得到了接受声音的受众,有回音,有应声。MomentinPeking在卷首献辞和他者与自我形象言说大框架内的文化自觉表现为两大特征:中西文化对举的理想主义和生命哲学的“不可说”,将中国的家庭和睦、军民融合、民族团结、民族复兴等方面发挥到极致,语言优美,没有说教痕迹。
二、 Moment in Peking的道与体道
MomentinPeking在文本整体框架设计、情节发展、精神升华等方面,表现为“道”和“体道”一明一暗的双线条形式,为道家文化以情节模式编织入文本结构搭建平台。文本背景虽处于社会动荡年月,双线条结构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给读者带来“痛并快乐”“神奇化险境”的艺术体验。“道”是MomentinPeking的核心思想范畴,作为明线在文中直接刻画为主人公姚木兰从小鸟依人到支持革命的精神成长历程,贯穿全文始终,以故事情节层层展开“生活的艺术”;“体道”需要读者去观察、发现和把握“道”之存在方式,表现为暗线:从侧面处理人物活动、情节和场面。道与体道巧妙编织出摇曳多姿的文章,表达耐人回味的审美意象[1]。这种双线条形式小说拓展了人类生命故事的内涵和外延,是一种具有深邃意蕴的表现形式。
“体道”具有超验性,是道家独有的认知方式,体现精神对现实物质的超越过程。“体道” 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能够获得超越现实的精神自由[2]。主人公姚木兰的丢失→获救→婚姻→丧女之痛→逃难等系列情节环环相扣,呈现出道家“体道”的精神之旅。木兰出生于富裕的“道家”观念家庭中,受家风影响,灵魂深处想往回归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年少涉世较浅和无忧无虑的富裕生活暂时遮蔽了她内心的精神需求。恋爱与婚姻仅是她于红尘中的插曲,豆蔻年华女儿阿满的惨死让她开始思考自我和生命的存在。她发现自己内心厌倦浮华喧嚣的城市和物质生活,热爱自然,于是定居杭州农村,融入自然山水。而面对意气风发的儿子阿通与其他中国青年一起勇敢地奔赴战场,用青春和鲜血抵挡日军的疯狂侵略时,木兰开始生与死的深邃思考。她深深认识到,个体仅仅是永恒社会的一个构成要素,现世利益的得失只是幻影而已。在向内地逃难途中,木兰用自己身体丈量神圣的土地,感知生活的冷暖,完成人生朝圣,精神得到完全升华,进入无我状态,“失去了空间和方向,失去了个体感”,以从容淡定的大智慧微笑面对命运。她小我精神被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完全蝶化且锤炼为永恒,真实到达“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撄宁状态。木兰的体道不是“顿悟”,而是于生活一步步深入认识中实现“自我”,感受到天地人神的一体而获得对生命价值的真正体悟[3]。
木兰“体道”这一暗线,是东方人生命哲学独有的表达方式。林语堂找准自己民族特有的东西,发掘出西方文化的优美与荣华,返回东方,将人生问题、伦理学问题排除在科学问题之外。与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即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有了答案,依然没有触及到人生问题”如出一辙。
木兰的“体道”建构了现代东方女性主义:乐观、健康、知性。她置身于充满智慧与知识的家庭教育中,从小就有与男孩争取平等权利的强烈愿望;长大后成了知识女性,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具备节俭、勤劳、谦让等传统美德;出嫁后积极参与曾家家庭事务,会享受财富,却从不依赖金钱。木兰秉承道家“乘物以游心”理念,欣然接受父辈的包办婚姻,履行为人妻女之义务,内心却一直为暗恋的立夫留有位置。木兰是“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的东方新女性形象:既具备传统女性温柔贤顺的美好品行,又具有特立独行和追求浪漫新鲜情趣的热情,没有陷在宿命的泥潭里[4]。“现象界”的虚幻、残酷与无奈刺痛了木兰,也唤醒了她对“本体界”体道之不倦求索。木兰的“体道”是生命之思、存在之思、理想之思。她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和对宗教的理解,在物象-心灵隐喻模式下开启了中国文化的一扇新视窗。
三、 Moment in Peking的文化自觉框架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MomentinPeking是传统与现在、西方与东方一纵一横两个文化维度上特定文字语汇的选择。MomentInPeking是象征中国文化之美的符号,背景设置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时间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起,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结束,是反映中国文化与北京风土人情的小说[5]。作者通过献辞与主题、“自我形象”和“异国形象”进行言说,向西方介绍中国的集体感情色彩,反映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同时,言说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镜像,并且让西方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是一种“可说”方式的小说变体性国际宣传。
1.卷首献辞
MomentinPeking没有采用传统章回体小说撰写形式,而是运用西方文学创作的特有形式----献辞。献辞往往是古代文士、学者对庇护人或赞助人的感恩表达。献辞是西方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普遍存在。莎士比亚和康德分别在十四行诗和哲学著作中写有献辞。尽管林语堂没有国内和国外的赞助人,但他在英语著作中自觉地借用了献辞形式,是文化自觉意识的行为表现。采用英语文学的呈现方式,既尊重西方读者,又表达了作者的爱国热情。当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历史文献性献辞给读者一种真实感觉,以一种正式而庄严的仪式,突出小说MomentinPeking的抗战主题,感情表达充沛,引导力强。台湾学者张振玉(以下节选皆出自张振玉译本)曾将献辞翻译为诗体格式:
献词
全书写罢泪涔涔,献予歼倭抗日人。
不是英雄流热血,神州谁是自由民。
作为必要组成部分的献辞属于副文本,是全书的精神向导,与全书格调保持同一。献辞引导情节言说基调,经过三卷“现象界”演绎,直通结尾处的木兰融入人群大潮,成为抗日军民洪流的一份子。首尾呼应,体现军民融合、民族团结和民族复兴的思想,扣紧中国现代革命内涵变化的脉搏。
2. “异国镜像”与“自我形象”
MomentinPeking跨越历史时段长,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展现了丰富的生活内质。由于特殊的故事背景,小说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西方人形象的塑造与描写。西方人形象在八国联军入侵北平、义和团抵抗西方列强中得到充分描绘,反映出中国民众集体对西方充满恐惧、敌视与轻蔑。MomentinPeking以“毛”称呼西人,如“大毛子”“洋毛子”或“老毛子”,使用了当时中国对西方的“套话”。中国人自古就用“毛”称呼外邦民族。《庚子使馆被围记》的作者朴笛南姆威尔曾在书中写道“毛乃禽兽之毛,予等野人未曾剃头”,一语道破中国人称呼西人为“毛子”的原因。由此,毛化的西方形象,作为中国人集体文化无意识原型[6],给西方读者一种变形的镜像,他们自然乐意接受这种“套话”,并且戏称自己为“番毛鬼”。
“异国镜像”创作重心是描绘日本残忍的侵略形象:杀光、烧光和抢光,奸淫妇女,在中华大地上演了一场空前绝后的罪恶惨剧。目的是告知和警醒中国广大民众,呼唤他们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抗日大潮中;同时撕开日本欺骗世界的假面具,激起全人类的愤慨,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小说的第四十四章,作者插叙了日军屠杀手无寸铁的村民,揭露了日军的野蛮、凶狠与残忍,客观地再现了凶蛮的日军本性:“日本兵在村中各处泼煤油,把全村房子都烧起来。居民想逃命,但是全村都被日本兵包围,谁逃跑就射杀。全村都烧毁了,人都死在火里……”[7]808如此这般的文字在抗战篇章中随处可见,令读者悲愤、落泪。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文化开始交汇,传统观念和现代意识相互碰撞,中国社会经历了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变化。国人迷醉于新时代新生活的大潮,同时紧紧抓住历史传统,如婚丧礼宴、冲喜守寡、赋诗作对、中医中药、古董字画之类的中华民俗文化。在洋人形象的描述中,外国侵略者的先进科技“望远镜”被义和团拳民称为“法术”(a devilish thing)。林语堂通过拳民之口塑造了被观看者----他者“异国镜像”,也是对中国“自我”形象的映射----国民的迷信、无知与落后,还有对科技的追求与率真。
言说使文化自觉得到充分实现。也就是说, “自我形象”和“异国镜像”在MomentinPeking中不能只被看作实现外在意图的“工具”,而更应视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进入“不可说”领域的梯子,是人类生命的情感模式。这些镜像符号与庄子“得兔忘蹄”“得鱼忘筌”中的“蹄”和“荃”的比喻在实质上毫无差别,是“言说”之文学理想主义表达,带有维特根斯坦主义色彩,是观察世界和理解生命方式的新视界。
四、 Moment in Peking中庄子与维特根斯坦共存
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MomentinPeking中语言构建出的道家思想,是庄子与维特根斯坦“语言与世界同构”融合视阈下的道家思想,明显偏离出中国传统道家文化轨道。庄子的“出场”和维特根斯坦的“隐身”,共同演绎了“语言与世界同构”主题,达成两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1.生命哲学、人文世界的“不可言说”
庄子具有独特的言意观:“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点出了道家的主旨观念----“道”。此语包括三个层次:“道”是真的,可以验信的;它本身似乎无形无迹,不可以目见,但可心得,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果自现,吸引人类一代代追随它;它自为本自为根,不能用高、低、久、老为衡量标尺,存在于天地之前,鬼神天地都出自它。“道”超出了人类直接经验感知的限度和逻辑思维的范围,因此任何精妙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即:人们可以言说、可以观察的,只限于物质现象世界范围之内----“期于有形者”(《秋水》) ,对于言意无法达到的世界本原“道”----万物之所由(《渔夫》),有限的语言和思维是无法企及的。正如木兰在逃难中丢失,巧遇曾家而获救,开启了与曾家“有数存焉于其间”的姻缘之门,体现生命哲学的神秘“不可说”性。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与世界同构,语言命题可以描述世界中的实在,事实是“可说”的。以探究物质世界为对象的自然科学命题,是可以言说的。但他同时认为,人生、伦理、美学命题处于事实世界之外,是一个超验的、不可言说的领域“独立于我的意志之外”[8],“凡是不可说的,只可不说”。在他看来,上帝存在涉及的是经验世界之外的问题,上帝并不显现于世界之中,“只能意会”而“不可说”。由此可见,无法用逻辑语言言说的关于世界的本质问题(道)是维特根斯坦和庄子的出发点和终点。隐身幕后的维特根斯坦,其“不可说”理念无声地做了西方读者接受MomentinPeking书中庄子思想的“接引佛”。
童年的木兰在全家逃难途中意外丢失,巧遇曾家获得救助,踏入与曾家缔结姻缘的红尘旅途。木兰丢失与婚姻体现的正是“知识所不及的剩余领域”,超乎人类理性逻辑之外,“它是天主所赋给,是无条件的,是高高在上的,是一个命令”,是不可说的直觉体验认知方式。
2.语言表达困境的主体因素是语言主体“矛盾”性存在
语言主体“人”是语言行为的执行者,带有很强的主观矛盾性。庄子曰:“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齐物论》)“吊诡”体现语言主体的主观矛盾。世人皆是“矛盾”统一体,心智遭到“矛盾”绑架,用带有“矛盾”的语言去言说“道”,语言主体必定陷入到表达世界的困境之中。语言受众也必然误解和扭曲“道”的本义,而使“道”“失其常然”,(《骄拇》)导致“言”“道”疏离。
维特根斯坦深信,现今的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们对语言边界内“不可说的东西”进行语言滥用造成的。维氏指出,语言和认知都存在局限性,人们只能表达能够表达的实在,强行表达“不可表达”的世界,就会产生语言滥用现象。这些言外世界好似“美人如花隔云端”,超出了语言正常逻辑范围,属于逻辑形式无法达到的领域。
林语堂巧妙运用“矛盾”和“语言滥用”观点,在MomentinPeking里演绎出《庄子·胠箧》的名言:
说也奇怪,人类的心理对偷窃一个国家的领土,比偷窃一个妇人的皮包,多少看作更为光荣,更为对得起良心,辩论起来也更为振振有词。古时庄子就写过: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7]780。
林语堂运用庄子的“矛盾”论和维氏的“语言滥用”论,通过对比偷窃国家领土的“荣耀”与偷窃妇人皮包的“卑劣”,真实指出当时的日本军政府利用“不可说”与人类主体作用下的语言缺陷,宣扬“大东亚共同圈”,粉饰侵略中国的卑劣行为和罪恶。显然,“光荣”“振振有词”是幽默性反说,揭露日本军政府的野蛮行径,在英美世界获得了极大舆论支持。
3.语言之外充满理想主义的传奇色彩
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是我的世界,这表现在语言(我能理解的那种语言)的边界意谓着我世界的范围”,与庄子思想异曲同工:“可说”与“不可说”界限的黄金分割点是语言。《则阳》篇说: “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语言和知识的极限探索,谁也说不明白,所以不说为宜;“极物而已”意谓着经验无法超越具体认知对象,是悟透人生的四字真言,是面对命运“风吹云散思不乱,水转山移心是锚”的那份自在。《庄子·知北游》言“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化”也,是以内在认知机制为依托,规定天地万物与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生死由命,修短随化。可以说,语言表达的界限透露出认知的极限,就是“存在”的极限。“神奇”和“臭腐”可以互相转化,“道”的神秘和“不可说”推动生命循环往复,变化无穷。
既然“不可说”,所以“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则阳》)。悟道的人看似谈论物质世界,谈论的实质却是玄学;不悟道的人整天谈道,谈论内容仍然困囿于物质世界之内。道在物质世界之外,谈也罢,不谈也罢,都无法表达出来。道是展示、是意会、是模糊概念。道充满神秘不可问,问道也不应做出解答。问道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本不应回答而回答也是徒有其表空洞无内容。维特根斯坦也有着相似的人与自然共通感:“我们不能思考我们不思考的东西,因此也就不能说我们不能思考的东西”。
不可说的“道”是理想主义境界,站在现实主义的对立面。《牛津高阶英汉词典》对理想主义(idealism)定义为“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仍坚信能够实现美妙的生活”。理想主义是精神追求和人生信仰。理想(ideal)有三个特征:理想高于现实;理想是美妙的;理想是动力的源泉。柏拉图是西方理想主义的鼻祖。苏格拉底相信,为梦想而拼搏是世上最令人欢畅的事。雨果断言,人类的精神需要梦想支撑远远大于物质需求。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理想世界才是天堂,现实世界仅仅是理想世界的映射----这为西方理想/现实二元对立基本模式奠定了基础。为弥补不完美的现世世界,基督教理想主义意志沿用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建设圆满的上帝天国。西方近现代理想主义的立足点逐渐从神转化为人,强调人的价值,即祈祷上帝的救赎,转变为人类自身拯救,建立“人间天国”。在20世纪,西方对东方充满好奇,理想主义蓬勃发展。中国式理想主义起源于庄子,庄子主张:“不物于物”,即不能做物质的奴仆,与天地合一,保持精神的超越性。木兰柔美、持家和定居杭州“荆钗布衣”的生活,展示了追求理想生命的浪漫情怀。林语堂怀揣文化自觉意识,借助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送去与之匹配的东方哲学,中西方理想主义式的“语言与世界同构”正式结缘,打造出亚里士多德相信存在的一个“幸福国度”。
MomentinPeking充满爱、美、富、福、乐,阐述“道”的境界。理想主义化身、庄子的虔诚信徒姚思安,摆脱物质现实的羁绊,云游圣地寻找“自我”,寻求“大道”,十年后在归家之时以僧人的面目出现,对于其中缘由,作者并无一字说明,维氏“不可说”理论赫然出现,获得巨大文学空间。
那个老和尚走进来,静静的站着。和尚们忙着念经,也没人注意他进来。念完经,为首的和尚走向前来,准备到院里去烧纸,有几个人跟随着他到院里去。在屋里的人这才发现这位老和尚。他走到供桌前,背向他们,合掌为礼,口中念念有词。
……老和尚慢慢转过身来,面对大家,蔼然微笑说: “我回来了。”……老爷回来的消息全家都知道了。仆人们……都来看这位长者……恭维他是“高僧转世”[7]705-708。
具有庄、佛双重身份,超凡脱俗的“高士”姚思安,回到阔别已久的子孙中间。和尚的物质外表与在家的子孙们拉开距离,产生鹤立鸡群的视觉效果,与全书的思想架构密切呼应。不仅如此,姚思安的“寻道”还附有几分理想主义的神奇色彩:
宝芬的二女儿问: “爷爷,您到普陀岛,是不是在水上走过去的?”姚老先生说:“也许是在水上走过去的,也许不是。”他话说得那么严肃,脸上那么脱俗,小女孩儿真觉得祖父是个神仙圣徒。姚老先生从容微笑说: “在华山我从一只老虎前面经过……它望了望我,它偷偷溜走了。”[7]707
作者这里的语言很狡猾。祖孙二人的对话用了“也许”之类的淡化语言,既保持超凡入圣的理想主义空间,又避免了佛门“一苇渡江、与虎为伴”的神迹受到攻讦。落发、高僧的物质空间安排,使姚思安“体道”和神秘不可说性产生了强大思想张力。由此可见,林语堂安排庄子的衣钵传人落发为僧,是文化自觉性有意为之,是“不可说”的延伸。姚思安的葬礼描写充满“黑黝黝的袈裟与鲜明职业乐队制服”并存的幽默,是生命体悟的升华,意味着死亡的黑暗将成为光明,最深的阴影将是光源所在之“道”。精神空间的搜寻,使全书宣扬道家的整体构想与维氏“不可说”达到高度化境。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自觉化育出文化共享性,其中蕴含的文化因子具有东西方乃至全人类共同理解和认同的特性[9],以文学形式实现了庄子和维特根斯坦两人“可说”与“不可说”的哲学判断。语言是道得以澄明的重要载体。为了到达“不可说”之境,首先要“说”。MomentinPeking99%的内容通过遣词造句、结构安排实现“言说”,汪洋恣意“言之不已”,且纵横捭阖近五十万言。但真正重要的,恰恰是那1% 没有被说出的东西,孕藏着庄子所寻找的精神开阔地,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要通过明确地表达可说的东西来指谓不可说的东西”的文学空间展示。穷尽“可说”的目的就是为了昭显“不可说”的东西,所有“可说”的故事情节只是明线,世界之外“不可说”的东西弥补了明线条单薄的弊端,使MomentinPeking思想厚重,显露出“为学必无谬悠影响之谈,始无颠倒支离之患”(严复《救亡决论》)。林语堂将维氏“不可说”和庄子之“道”演绎得几近琴瑟和鸣。
五、 结 语
MomentinPeking存在维特根斯坦的身影,有着深厚的哲学渊源。林语堂在著名的演讲《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里提到这位哲学家,并言简意赅地概括其哲学精髓:Wittgenstein认为哲学生根于狂妄,包括自己的名著《逻辑哲学论》在内,都是胡说。该演讲首次对比维氏甩掉术语、去疑辨惑的哲学宗旨与庄子“为是不用,而寓诸庸”观点,完成两位东西方哲学大师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MomentinPeking以活泼生动的日常语言,颠覆了秩序平板的语法逻辑,可说与不可说的共存,既拓开广阔的历史生活信息量, 又提炼西方想象中的中国形象:清峻、通脱、华美、壮大。作品呈现出“大的风景”“磅礴的气势”,映现着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折光。林语堂通过对语言的充分重视凸显作品的丰富内涵和广阔的生命空间,将庄子和维氏从逻辑语言的灰色沙漠带入人文主义的绿色世界。在MomentinPeking中,林语堂将庄禅和维特根斯坦融成一道,通过想象力对表象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和再创造,并将重组后的表象通过神奇的语言文字加以记录,完成三个目标:哲学的现代价值;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与评价;抗日爱国宣传功能,达到了“一气化三清”的效应。
现今,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观念转型,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泛滥,导致国人内心常常充满困惑,活得“累”。 在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财富积累大踏步进步的背景下,幸福指数却出现反常性扭曲现象。MomentinPeking蕴含着哲学治疗功能。此书如清风拂面,使“幸福指数”扭曲得到哲学光照,给人以活出自身价值的体悟,萌生民族文化自豪感。 文化自觉孕育着希望,流淌着理想主义基因,是对生命的奇异与丰盈的守望,倡导“知彼与扬我”,值得深思。
[1] 王绍舫.《追风筝的人》双线条蝶化模式哲学解读[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89-92,121.
[2] 罗坚. 生命的困境和审美的超越:庄子美学的生命意义[J]. 社会科学, 1998(12):66-70.
[3] 谢辉. 道家思想在《京华烟云》中的建构[J]. 时代文学(下半月), 2012(8):200-201.
[4] 付春明. 禹光勋小说《兰芝》女主人公爱情宿命论解析[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104-108.
[5] 江慧敏. 修辞学视角下MomentinPeking中称谓语的汉译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3):125-133.
[6] 周宁. 天下辨夷狄: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J]. 书屋, 2004(6):12-19.
[7] 林语堂. 京华烟云[M]. 张振玉,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8]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王平复,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7:185.
[9] 吴慧坚. 文化传播与策略选择:从林语堂著《生活的艺术》说起[J]. 福建论坛, 2007(9):85-89.
OnCulturalConsciousnessofMomentinPeking
WangShao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ya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41, China)
Cultural consciousness refers to “self-knowledge” of people who live in a certain culture and can take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developing its own cultural essence to converge with mainstream culture. Different from Zhuangzi, Wittgenstein stands in the shadow ofMomentinPeking. The scaffolding of novel’s language fully embodies the philosophical view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hen the weak culture gets close 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MomentinPeki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philosophical view
2017-05-02
王绍舫(1971-),女,辽宁营口人,沈阳大学副教授。
2095-5464(2017)05-0584-06
I 106
A
【责任编辑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