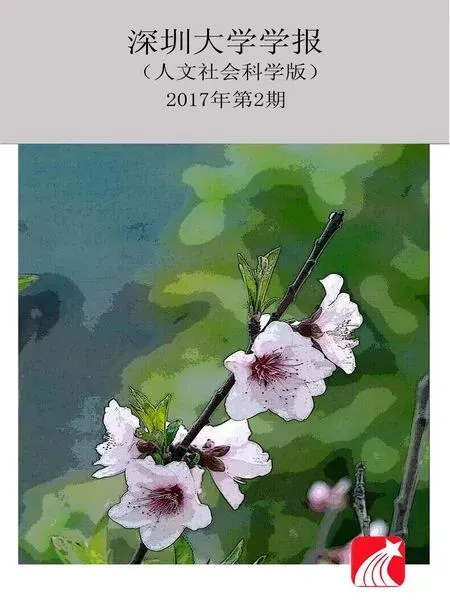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现实瓶颈及应对策略
——基于器物文化传播视角
2017-04-03张晓刚
张晓刚
(巢湖学院艺术与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8000)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现实瓶颈及应对策略
——基于器物文化传播视角
张晓刚
(巢湖学院艺术与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8000)
器物文化传播是突破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现实瓶颈的路径选择,其符合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且契合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语境。进行器物文化传播,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器物文化进行海外传播的成功案例与内在机制,充分考虑海外受众的心理需求,避免器物文化传播中对文化符码的误读和对抗性解读,同时建立起有效的器物文化传播效果反馈机制,实现和观念文化传播的有效协同。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器物文化传播;应对策略
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现实瓶颈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提升中华文化的海外影响力显得尤为迫切。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正是基于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提出的现实命题。新世纪以来,我国“采取政府与民间并举、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并重、走出去与请进来并行,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文化交流开放格局,提升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亲和力、竞争力与影响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检视我国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传播模式,是一种以中华观念文化输出为核心利益诉求、一贯到底式的“自内而外”扩散传播的路径模式。其特征为:第一,其传播的组织策划者以中国政府及其相关下属机构为主导,进行战略性的推广规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并投之以大量的财政资金做保障,而民间文化组织则充当配角,目的性和控制性强;第二,在文化传播层次上,侧重于观念文化(文化的精神形态)的传播,而较为忽视基础性的器物文化(荷载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器物层面)的传播;第三,其文化传播内容侧重于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的精髓及其相关的古典形式载体,如书法、茶艺、太极拳、陶艺、民族舞蹈等;第四,在传播方式选择上,主要采取文学传播(如翻译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语言和教育传播(如不断创办孔子学院)、活动传播(如在相关国家举办大型的文化活动)等;第五,在目标受众上,主要面向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知识精英群体,受众面较为狭窄,一般难以渗透到目标国大众百姓的日常生活。
不容否认,这种“自内而外”的传播路径可以保证传播信息的权威性和到达率,形成意识形态上的高度统一。其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中,可以充分整合国家智库的力量对传播对象、传播形式、传播效果等进行整体性的战略规划,分步实施,取得较为理想的传播效果;但历史背景、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社会风俗的跨文化差异,加上受众对象的非受控性、分散性,也使得这种传播路径存在着现实瓶颈。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是务“虚”不务“实”。 “虚”与“实”是相对而言的,并无意义上的褒贬之分。美国学者托马斯·麦格奈尔认为,文化有表层和深层之分。按价值的大小排列,“表层”意味着低价值而“深层”则意味着高价值[2]。所以在许多文化学者看来,表层文化肤浅而深层文化深奥,前者不如后者重要。其实,从文化符号学角度分析,文化作为人类的符号系统,所谓的表层和深层之分,其实就是符号表现和符号内容的区别,也即日本设计学会会长原田昭指出的价值意含和意象意含之分[3]。以工业产品为例,产品由造型、结构、材质、色彩、装饰等构成的整体形象是产品的符号表现(价值意含);而产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感受和体验,就是产品的符号内容(意象意含)。例如万宝路香烟的价值意含是万宝路牛仔的感性形象,意象意含(引申的涵义)是粗犷的个人主义的美国人。
从受众的认知来看,文化表层的饮食起居、制器造物活动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非常紧密,也更为直观、实用,属于非常“实”的部分,也就是说文化表层的价值意含是较为容易理解的。它们极具价值,部分是因为它们已为人们所接受,且往往是人们所喜欢的;部分则是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参与某个特定群体的文化实践,那么他将被看做没有教养、没有文化[2]。相对而言,虽然潜藏在文化表层深处的信念和价值观等深层文化元素是构建整个文化气质的中坚力量,但由于需要唤起受众更多的感知和思考来把握其较为抽象的内容,就显得不那么容易,属于有点“虚”的部分,就像恩格斯所说的属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4]的意识形态形式。
回顾新世纪以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历程,我国相关对外文化传播机构的着力点在精神观念等深层文化层面,而对易于构成文化认同的文化表层如器物文化重视不够。我们总是过于直白和单刀直入,试图让外国人直奔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精神内核,由于语言、地域和社会制度的隔膜,对中华文化知之甚少的外国人而言,这很容易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人力物力)将中华文化的精髓如数家珍般地一一展示给外国人看,外国人却并不领情,甚至会激起其意识形态方面的警惕性[5]。这就是文化传播中务“虚”不务“实”的后果。
第二是能“上”不能“下”。即我们的文化传播内容主要集中高雅艺术文化方面,如中国戏曲、绘画、书法、电影、经典图书等,热衷于进入国外音乐厅、美术馆、展览馆、博物馆、电影展等高雅场所,虽然目标高端,但毕竟曲高和寡,到最后变味,结果成了少数领导“文化政绩”和某些艺术家的文化“镀金”行为,也即所谓的“文化面子”工程。例如近些年国内多个艺术团组织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登台演出,但实际上很多演出艺术水准并不高,有的甚至赠票都没有人来看,要靠演出团体之间相互捧场、互当观众来避免冷场。文化部为此专门发文,对国内各级各类艺术团到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演展场所或国际组织总部办公场所“镀金”现象予以坚决制止。这种“赔钱赚吆喝”“自唱自买”式的所谓“文化输出”,非但不能弘扬中国文化,反而损害国家文化艺术尊严,其背后是不正确的“文化政绩观”在作祟[6]。
“阳春白雪”固然可贵,“下里巴人”则更接地气。其实真正的跨文化传播,必须放下身段,少些自我炫耀和作秀成分,真正进入国外的寻常百姓家,使其由知之而好之,由好之而乐之。那些看似“下里巴人”遍布全球的“中国制造”产品其实正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有效载体。而我们对这一点则缺乏清醒的认识,从而导致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的上下脱节,陷入能上不能下的尴尬。
第三是厚“古”而薄“今”。也就是说,一提到传播中华文化,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亮亮中华五千年文化的雄厚家底,以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为主要宣传对象,而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当代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醒觉。美国营销大师米尔顿·科特勒在《中国国家品牌缺失的原因》一文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品牌要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品牌本身,以及它背后的企业,还取决于原产国和基础市场的价值,即中国品牌的形象。”[7]而当前我国的国家形象塑造还处在亮家底、展示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遗产阶段(如所谓的“中国风”),对当代中国艺术文化的独特性缺乏提炼和省察。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中国要从一个传统的工业形象过渡到一个高科技、崇尚生活和娱乐的现代化国家形象。而这需要从世界各国都钦佩中国的抱负、对学习的追求、技术敏锐性、经济增长、国家财富、中国人民的勤劳等正面价值中仔细甄别,精心塑造,描绘一副现代的、有魅力的社会蓝图,全面呈现中国品牌的现代化形象。
第四是“重”传播者利益诉求,“轻”受众心理需求。文化作为人类认识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包含了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其因环境的不同而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作为“跨文化传播”形式,其复杂性在于要冲破国别、地域形成的文化壁垒,拆除不同文化间的藩篱,形成交流交锋交融的体制机制,使中华文化在海外受众群中获得广泛的认同感,进而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因此,究竟是基于传播者本位还是受众本位必须有清醒认识。从传播者立场而言,总是期望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将自身文化优越性一股脑儿地灌输给传播目标地的人群,主要考虑的是自身的文化利益诉求。如果从受众本位出发,那我们则要充分考虑到传播目标地人群的国别、地区、民族、历史、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的差异性,在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上做到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使之更乐于接受。遗憾的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所采用的“由内而外”的传播路径,往往更多的是以“我”为主,重视传播者的利益诉求,而对受众群关注得不够。典型的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国外媒体在发出“难以想象”(unbelievable)、“精彩绝伦”(amazing)等惊叹的同时,也有“感觉到中国人要强起来的决心”[8]之担忧。
二、器物文化传播:突破现实瓶颈的路径选择
为突破上述现实瓶颈,本文提出器物文化传播的新思路。器物文化传播是以器物等物质产品为载体的文化传播,区别于前述以精神产品为载体的文化传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器物更多是以在世界各地广泛销售和使用的商品形态得以便捷地流通,使其成为传播某种文化的最佳载体。并且,当代器物在其生成的那一刻起便被创造者和设计者们赋予了深刻的文化艺术寓意,具有精神性与物质性深度融合的特征,天然地具有文化和审美属性[9]。其流通过程其实就是文化传播过程。因此,器物文化传播不仅基于通常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文化三分法的理论预设,更是出于当下跨文化传播实践的综合考量,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10]的重要环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符合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
从中西文化传播史来看,一个重要的传播规律就是器物文化传播先行原则。也就是说,在跨文化传播中,首先从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器物文化传播开始,才能逐步消除异质文化间的隔阂,进而将相应的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融入其中,方能真正实现观念文化核心层获得受众认同的突破。这是跨文化传播中普遍存在的“由外入内”的传播路径。
当代著名文化史学者武斌曾总结了历史上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四次大的高潮,它们发生的时间分别为汉代、唐代、宋元和明清之际。而这四次传播高潮的标志均以器物文化的传播为代表,遵循着先器物文化传播再到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畅通于海外的普遍性规律[11]。海外各民族首先是通过那些体现着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物质产品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的。中国的许多重大发明和日常生活用品,如火药和火器技术、雕版印刷术、指南针以及丝绸、瓷器、漆器等,都是在这几个时期大规模西传,并在欧洲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曾对这些伟大发明的世界历史意义给予高度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2]确实,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华器物文化不但是改变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而且在西方的传播意义远远超出其自身的技术领域,对世界历史的演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保障计划能具有正确的、执行下去。在资金支出活动中明晰资金的去向、额度范围、花销明细、支出方式、受理对象等内容,并且安排相关的专业人员将银行账单和资金余额进行核对。结合合作方的目的要求,完善会计核算制度,强化会计核算质量,成立投资管理体系。对筹资费用进行详细的计算,保证筹资费用与筹资计划相融合,若双方出现不相符合的情况,应及时找出问题并进行解决。最后,强化企业内部的信息系统,制定监控条件和警告要求,避免支付环节中出现差错,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这种规律同样体现于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整个进程。梁启超曾提出过著名的文化传播“三期”论,认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观念的渐进过程[13]。进一步往前追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从器物文化开始。例如,利玛窦是西方第一批入华耶稣会传教士中最具历史影响的人物。他于1582年进入中国,期盼进京叩见万历皇帝,恳请皇帝恩准自由传教。他耗时19年,历尽磨难而未果,反被囚禁在天津,差点丢掉性命。后来,万历皇帝听说他要进贡自鸣钟的新奇之物,于是颁旨召见。从此,利玛窦得以留居帝都,并深入皇宫[14]。他通过器物文化撬开了传播观念文化的大门。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传播规律,是因为文化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常常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模式,表现为一种持续运动着的各个部分相互作用的模式。各层面文化要素的传播并不是平行推进和平衡发展的,通常器物文化总是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最易于向外渗透和传播,并且“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的输出,间接地传达了这种物质产品所包含的精神内容和文化内涵,因而也就使其成为文化整体的代表而传播并发生影响。”[11]
(二)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
相对于精神产品的文化传播,器物文化传播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美国建筑与设计大师乔治·奈尔森曾说:“器物是文化遗留在它专属时空中的痕迹。”[15]它总是象征着一定时期特定的规范,人们制造、使用某种器物表明了人们对特定的政治原则和价值的追求。需要指出的是,当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器物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设计文化,消费者使用的有形物质产品,具有价值意含和意象意含。当消费者为产品的功能、操作方法、安全性、可靠性、耐久性等价值意含所吸引时,其隐含的意象意含如审美情趣和文化象征意义,诸如思想意识和观念形态,也在悄无声息、潜移默化地对消费者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为我们探寻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新路径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在跨文化传播中,采用“由外入内”的器物文化传播有可能会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有学者指出,与借助精神产品的文化传播相比,器物文化传播具有“三性”:无所不在的渗透性、潜移默化的影响性、令人依恋的吸引性[16]。这三种特性可以突破观念文化传播所存在的语言隔阂、意识形态钳制等障碍,拓展着庞大的受众群,“对于器物文化来说,正常使用某种器物的消费者就是该器物所荷载的文化的受众。”[17]据市场研究公司IDC提供的数据,苹果手机 2015年销量达到2.315亿台,也即意味着全球每年有2亿多苹果文化 (美国文化)的受众。这确实是一个数字惊人的受众群体,要远远高于精神文化消费者的基数。恰如《苹果设计来自加州》这则广告所传达的创新设计理念——“这会帮助谁?它会否让生活更好?它有存在的意义吗?”以及设计者的价值追求——“我们是工程师,也是艺术家;是工匠,也是创造家。我们为作品负责”那样,当亿万“果粉”为苹果手机的每一次新品推出翘首期盼并在日常的人机互动中为之沉醉痴迷时,以苹果手机为代表的高度智能化时代的美国创新文化就会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直观,化冗思为体验,在无形中悄悄渗入使用者的脑海深处。试问又有哪一件精神文化产品具有如此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呢?
(三)契合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语境
以器物文化传播作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现实路径契合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语境,具有强大的动力学基础。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现在中国制造已经遍布全球,制造业产值已占我国GDP的50%左右,但是还没有在国际市场打造出类似阿玛尼、耐克、芭比娃娃、奔驰的知名品牌。我国政府正努力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制造业在转型升级中对文化创意的需求尤为迫切。国务院在《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18],可谓抓住了根本。既然我们的物质产品出口销量位居世界第一位,为何不能通过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在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有效载体呢?这是我们进行中华器物文化海外传播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器物文化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基础和极好的载体。富含文化创意的物质产品不仅能够极大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而且能够成为本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无孔不入的通道。如果当代中国器物(工业产品)在传承古代光辉灿烂的手工艺设计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之发扬光大,通过设计创意提升其文化含金量,那么将使得已经离不开中国制造的全球消费者更为深切地感受到当代中国器物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创新本质,为国人的创造力所深深折服。在某种意义上,华为、海尔、联想等率先走出国门的创新型企业不仅为海外消费者提供有形的产品和服务,更是传递着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创新、超越、活力、进取等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柏林的一次演讲中曾指出:“我相信,当‘德国制造’和‘中国制造’真诚牵手合作,我们所制造的将不只是高质量的产品,更是两国人民的幸福和理想。”[19]正在迈向“工业4.0”的“德国制造”深深镌刻着严谨理性的德国文化精神。“中国制造”不仅应该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而且更应该展现中国人的理想,成为中国梦的载体,将中华文化传遍世界。
三、我国进行器物文化海外传播的应对策略
(一)提高认识,强化器物文化传播的顶层设计
器物文化传播可以强有力地提升中国的国家品牌形象,建构起“中国”作为国家品牌在全球竞争中的领导者形象,进而实现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目标。必须充分认识到“由外入内”的器物文化传播的重大意义,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整体战略中予以重新定位,结合器物文化传播特征进行顶层设计,确立发展目标,展开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由于器物文化传播牵涉面广,不单是文化宣传部门的工作,更是涉及到“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攻坚战。多个职能部门间的功能协调显得尤为重要。应在国家层面开展系统化、科学化的研究,制定中长期战略规划,出台具有延续性的发展政策,加强宏观引导,促进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
其路径设计和传播目标可以简要表示为:“中华器物文化的内涵凝练 (古典与现代交融的新型中华文化)—中华器物文化的海外传播,通过物质产品建构起强有力的国家品牌形象—改变海外普通大众对中华文化的刻板印象—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掀起历史上的第五次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高潮(同前四次一样,要有标志性的器物产品或创新服务影响到全球的众多消费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这一进程中,只有回到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逻辑原点—器物文化层,从最基础做起,通过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不断提高工业产品的文化含量,实现文化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有机统一,才能让器物文化传播有牢固的根基,才能真正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才能进一步向观念文化层不断拓展,逐步形成立体的、全方位的文化传播体系,真正使中华精神文化的内核在海外生根发芽,切实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二)加强研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器物文化进行海外传播的成功案例与内在机制
美国学者高丁(Godin)指出,从事产品制造和服务的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创造出产品背后的故事,即品牌叙事[20]。我国学者在研究中也发现,“企业可以通过品牌故事的传播来树立自己独特的品牌形象及品牌主张,通过故事中感性的渲染在消费者理性的思考中来铺垫感性的前提,使品牌更人性化,让人们能够通过品牌故事了解和记忆品牌,提升品牌价值。 ”[21]
就制造业而言,品牌叙事主要体现为器物的叙事功能,而这需要通过与文化创意的深度融合来实现。而西方在知名产品与文化创意深度融合的叙事策略方面有许多的成功案例,像“迪斯尼因特别采用了全球核心策略‘讲故事——系列人物形象’来培养长期的粉丝和消费者而大见成效。”[22]因此,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器物文化进行海外传播的成功案例与内在机制,对我国器物文化传播路径及其与文化创意深度融合的具体方式会有极大的启发。
同时对诸如可口可乐、苹果产品、哈雷摩托车、麦当劳、星巴克、耐克鞋和其他耐克产品、芭比娃娃、利维牛仔裤等西方著名的产品,研究它们与文化创意深度融合的途径,其融合的策略和机制以及美国文化如何通过这些产品在世界上广泛传播,这种传播的力度和特点等等,将对我国相关产品与文化创意深度融合的路径和可操作的机制形成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促进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内容创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深化,从而提升我国器物文化的海外传播效果。
(三)充分考虑海外受众的心理需求,避免器物文化传播中对文化符码的误读和对抗性解读
法国已故学者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曾出色地运用符号学观点对大量的社会现象进行解剖分析,把符号学引入复杂的非符号领域,如服装、饮食、汽车、家具等。“巴尔特通过对各种生活符号的破译向人们表明: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由纯粹事实所组成的经验世界,而是一个由种种符号所形成的意义世界,我们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不停地对这些符号进行编码和译码,而全部人类的事务如衣食住行都渗透着编码行为。”[23]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信息传播过程并非简单化的“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受众的“解码”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时意义不是传播者“传递”的,而是受众“生产”的。也就是说,受众在传播过程和传播关系中具有主动性,受众本身是积极的、“生产”意义的、选择性接受信息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信息被传送不等于被接受[24]。也即器物文化所具有的显性意义以及隐含意义会被受众以不同的方式解读,而受众的解读方式,即对接收到的信息的解码过程,与他们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技术环境相关。
这就提醒我们,在中华器物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应针对受众年龄、教育程度、艺术素养以及国家或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进行文化编码,并在传播方式上贴近受众的民族特性、生活习俗和理解习惯。有效的文化传播,只有在传播者和受众的语码系统相似时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意义能够顺利并准确地被解读的前提是受众的社会文化规则与传播者相对应。否则,受众不仅会对传播的文化涵义产生误读,甚至可能在语言理解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对其隐含的意义产生对抗解读。因此文化传播者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受众如何理解文化符号表面意义的问题,还应该深入研究受众的社会文化惯例以及利益。传播者要想把自己的文化一路推广下去,必须重视受众,增强相互角色的交流和了解,避免盲目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传播。这就要求传播者尽可能超越本我文化意识,了解不同文化,避免文化中心主义[24]。
(四)试点运行,建立起有效的器物文化传播效果反馈机制
德国特里尔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教授将中国的体制改革模式命名为“学习中的威权体制”。他认为,中国的决策机制重视适应力,是稳定与灵活的结合体。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反复试验,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一套灵活多变的政策工具和机制,比如政策出台之前先试点,然后再由点到面,逐步推广试点中比较有成效的做法等等[25]。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路径的探索中,器物文化海外传播路径不可或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若干行业的重点企业进行试点、创新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在探索出物质产品与文化创意深度融合、具有中国特色、较为成熟的器物文化海外传播路径的基础上,再逐步推广,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武库”,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力度和影响力是一种有效方式。
我国曾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中国形象宣传片,耗资450亿元,滚动播出20天,对过往人群进行了8000多次的密集“轰炸”。然而美国人的真实反馈却是“(我们看到)除了展现出中国丰富的人群和他们的成就外,我不太清楚它们想传达怎样的信息,(短片)并没有彰显出中国充满活力的国家形象”[26]。没有效果评估反馈机制,就没有决策和调整的科学依据,就不能从失败的案例中总结出成功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将我国体制改革中的成功模式运用到器物文化传播的实践中,尽量少走弯路和回头路。
(五)双管齐下,实现器物文化传播和观念文化传播的有效协同
前已指出,“由外入内”的器物文化传播和“自内而外”的观念文化传播构成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体系中并行不悖的两种基本路向,各有特点,各擅胜场,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有学者提出在国际传播中“巧用力”的观点值得重视。所谓“巧用力”,是指在“调动软硬实力”基础上“设计出来的切实可行的传播方案和巧妙实施的策略行动”[27](P21)。
按笔者理解,这种“巧用力”,就是双管齐下,做到器物文化传播和观念文化传播的有效协同。其最终的愿景是实现器物文化、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有机融合(或称三位一体化),完成中华文化的海外协同传播,以打造中华文化的“软权力”即“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对相关国家的影响力”[27](P22)。应该说,器物文化传播与观念文化传播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两条主要路径,当它们遇合于制度文化传播,形成中华文化的海外协同传播效应时,完成从古老中华文化向现代中华文化苏醒、转型乃至伟大复兴的征程,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和号召力,也便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了。这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终极目标。而其能否有效实现则依赖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新路径——器物文化传播近期目标的达成,进而与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形成有机融合的机制,发挥出协同效应,促进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的广泛认同。
[1]欧阳雪梅.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现状及制约因素[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3):68.
[2](美)托马斯·麦格奈尔.表层文化、深层文化和文化认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8-26(02).
[3]凌继尧主编.艺术设计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31.
[4](德)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3.
[5]郭镇之.国际传播要巧用力[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75.
[6]吕梦琦,李建平.赴“金色大厅”现眼是扭曲文化政绩观[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7/09/c_11115393 43.htm.
[7]米尔顿·科特勒.中国国家品牌缺失的原因[EB/OL].http:// www.3158.cn/news/20110112/13/87-33925974_3.shtml.
[8]王受之.初谈北京奥运会设计[EB/OL].http://blog.sina.com. cn/s/blog_4bdabb490100a9lj.html.
[9]凌继尧,张晓刚.经济审美化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304.
[10]新华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OB/E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 c_118164235.htm.
[11]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规律[N].光明日报,2008-08-21(11).
[12](德)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674.
[13]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上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476.
[14]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译著集·导言[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2.
[15]徐燕斌.器物之礼与权力的正当性——以唐代为中心[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67.
[16]凌继尧,陆兴忍.器物的文化传播功能[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107-109.
[17]凌继尧.我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新路径——从中国瓷器的海外传播谈起[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6):40.
[18]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3/14/content_8713.htm.
[19]付碧莲.有一种制造叫德国[N].国际金融报,2014-06-03(04).
[20]Godin S.All Marketers Are Liars:The power of Telling Authentic stories in a low-trust world[M].Ponguin,2005.18.
[21]汪涛等.讲故事塑品牌:建构和传播故事的品牌叙事理论——基于达芙妮品牌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1,(3):122.
[22]花建.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四大路径[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4):28.
[23]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42.
[24]张春燕.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和内容选择[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4,(1):8.
[25](德)韩博天.中国政治体制具有高度适应力[J].求是,2013,(3):65.
[26]刘峰.中国文化“走出去”:为什么?如何“走”?[J].民主,2011,(7):18.
[27]郭镇之,冯若谷.“软权力”与“巧用力”:国际传播的战略思考[J].现代传播,2015,(10).
【责任编辑:周琍】
Practical Barrier and Coping Strategies for China to Conduct Cultural Dissemination Overseas:Based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Artifacts
ZHANG Xiaogang
(Research Center of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y,Chaohu College,Hefei,Anhui,238000)
Dissemination of artifacts is a way for China to break the barrier in overseas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t conforms to the basic law of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has its own disadvantages,and fits into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Chinese society.To conduct dissemination of artifacts,we need a good top design,to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using artifacts for overseas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their internal mechanism,to give due considera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overseas audience,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and confronta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code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artifacts,in the meantime to establish effective feedback mechanism regarding the effect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artifacts,and to achieve progr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concepts.
Chinese culture;overseas dissemination;dissemination of artifacts;coping strategies
G 125
A
1000-260X(2017)02-0055-07
2016-09-28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器物文化走出去内涵与路径研究”(XTCX150620)
张晓刚,文学(艺术学)博士,巢湖学院艺术与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从事设计创意产业与器物文化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