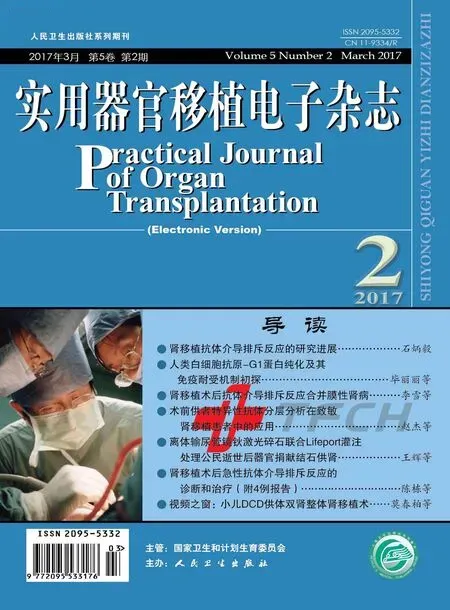肾移植术后急性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的诊断和治疗(附4例报告)
2017-04-01陈栋卢峡朱兰宫念樵魏来王大卫陈刚明长生陈知水张伟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30
陈栋,卢峡,朱兰,宫念樵,魏来,王大卫,陈刚,明长生,陈知水,张伟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30)
由于强效免疫抑制剂的广泛应用,肾移植后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显著降低,而急性或慢性抗体介导性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 AMR)正逐渐成为移植物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也是影响移植物长期存活的主要障碍[1-2]。本研究回顾性总结分析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近期发生的4例急性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cute 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 AAMR)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以期对肾移植术后AAMR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1 临床资料
病例1:女性,术前群体反应抗体(panel reaction antibody,PRA)Ⅰ类为30%,Ⅱ类为3.6%。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DCD)来源的肾移植,术中及术后应用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进行免疫诱导治疗,连用3 天,术后采用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MMF)+泼尼松的三联免疫抑制方案。术后第8 天,受者血肌酐开始出现上升,且尿量迅速减少。术后第9天,血肌酐水平升高至487 μmol/L,无尿,并开始血液透析治疗。术后第9天,检测PRA Ⅰ类为49.5%,Ⅱ类为0.4%,复查移植肾彩色超声检查显示移植肾血流减少。术后第12天,PRA Ⅰ类为74.6%,Ⅱ类为2.7%。术后第14天,移植肾穿刺活检显示,移植肾广泛缺血和局部出血,同时检测供体特异性抗体(donation special antibody,DSA)结果阳性,诊断为AAMR,术后15天切除移植肾,维持血液透析治疗。
病例2:女性,移植前PRA Ⅰ类为13.3%,Ⅱ类为1.7%,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合试验为阴性,接受DCD来源的肾移植。使用25 mg ATG 进行免疫诱导治疗,连用5 天,每日预防使用丙种球蛋白20 g。受者术后发生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elayed graft function, DGF),接受规律血液透析治疗。免疫抑制方案采用他克莫司+MMF+泼尼松三联免疫抑制方案。术后第4天,复查PRAⅠ类为60.6%,Ⅱ类为65.9%。术后第5天行DSA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术后第13天,复查PRA Ⅰ类为65.6%,Ⅱ类为78.9%。DSA Ⅰ类为阳性,DSAⅡ类为阴性。诊断为AAMR,使用2次硼替佐米(3.5 mg/m2),3次血浆置换,以及持续使用丙种球蛋白20 g/d治疗。最终受者的移植肾功能恢复正常。
病例3:男性,术前PRA I类为 1.7%,Ⅱ类为5.6%,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合试验为阴性,接受亲属来源的肾移植,供体为其母亲,未使用诱导治疗,采用他克莫司+MMF+泼尼松三联免疫抑制方案。术后4天受者尿量逐渐减少,发生DGF,接受规律血液透析治疗,术后14天仍未恢复,移植肾彩超提示移植肾血流减少,考虑发生AAMR,予以甲泼尼龙共2 000 mg冲击治疗后血流未见明显改善,检查PRAⅠ类为1.2%,Ⅱ类为93.4%,DSA阳性,移植肾穿刺提示移植肾广泛缺血性坏死,出血,移植肾微动脉血栓形成,C4d染色阳性,考虑发生AAMR,予以血浆置换5次,每日应用静脉注射用免疫球蛋白20 g,复查PRAⅠ类为3.8%,Ⅱ类为88.7%,移植肾彩超和移植肾穿刺活检提示血流未见明显改善,尿量每日约为500 ml,未能脱离血液透析治疗。
病例4:女性,术前PRA为阴性,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合试验为阴性,接受DCD来源的肾移植。未使用诱导治疗,术后第8天,血肌酐升高到360 μmol/L,使用甲泼尼龙共1 800 mg冲击治疗后,血肌酐下降到135 μmol/L。术后第14天,血肌酐水平再次升高到166 μmol/L,检测PRA Ⅰ类为3%,Ⅱ类为70%,检测DSA为阳性,术后第16天,行移植肾穿刺活检,结果显示移植肾急性抗体和细胞介导的混合性排斥反应。经过4次血浆置换和静脉输注丙种球蛋白后复查DSA转阴,移植肾功能恢复正常。
2 讨 论
移植肾AMR通常发生于术前PRA阳性的高危患者,本组病例中病例1和病例2均为PRA阳性的患者,术后出现少尿和血肌酐升高,首先考虑发生AAMR,病例2经过积极治疗后得以成功。但对于PRA抗体阴性的患者,特别是同时伴有DGF,对AMR不易诊断,从而容易导致移植肾的丢失。在本组研究病例3中,虽然为亲属肾移植患者,术前配型良好,依然发生严重AAMR,虽然诊断明确后积极抢救治疗,依然未能挽救肾脏。因此,对于术后出现少尿和血肌酐升高的患者,无论是否存在高危因素,都需要高度警惕AMR的发生,规律性检测PRA和DSA,及早性移植肾穿刺明确诊断。
AAMR的诊断通常需要检测患者术后PRA和DSA的变化情况,并结合移植肾穿刺活检组织学表现予以诊断。Banff 2013关于AMR的诊断标准,包括急性或慢性损伤的组织学证据、抗体与血管内皮间的相互作用证据以及存在DSA的血清学证据[3-4]。并将AAMR可主要分为两类:① AMR类型Ⅰ型,即术前预先致敏的移植患者术后早期出现的AMR;② AMR类型Ⅱ型,即因免疫抑制不足移植后延迟产生DSA所诱发的AMR。虽然DSA、微血管损伤的组织学改变以及C4d在毛细血管周围广泛沉积成为AAMR的诊断依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急性或慢性AMR表现为C4d沉积阴性的病例,提示C4d对于诊断AMR来说并非是一个敏感的指标。在本组病例中,仅病例3移植肾穿刺病理出现C4d阳性的表现也说明了这个问题[4-5]。
DSA是直接抗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或其他内皮细胞抗原的抗体,而这种抗体的存在是诊断AMR的要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移植术后新生DSA对于急性或慢性AMR及移植物功能丧失是独立的风险因素[6-7]。值得强调的是,并非所有DSA均能与补体结合并诱发AMR,也并非所有合并小管炎及C4d沉积的急性移植物损伤病例都可用常规方法检测出DSA的存在。事实上,大部分产生DSA的患者会与非致敏的患者一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良好的移植肾功能。
AMR治疗的主要目的是清除已存在的抗体和阻止其再次生成。治疗方案包括,血浆置换、IVIG以及抗补体、抗B淋巴细胞和抗浆细胞在内的治疗方案。一旦发现PRA升高,增加基础免疫抑制药物的剂量,抢先使用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中和抗体,发现DSA升高或病理检查显示有AMR的表现,采用血浆置换清除抗体,联合硼替佐米抑制浆细胞产生抗体,如果治疗效果不佳,再加用艾库组单抗阻止补体系统活化[8-9]。贝拉西普、利妥昔单抗等用于缓解期防止DSA再生。通过血浆置换、IVIG和硼替佐米等联合治疗,增加AMR的治愈率,提高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10-12]。
AAMR的预防重于治疗,继续严密监测高风险受者,坚持足量的免疫抑制剂以期达到良好免疫抑制效果是减少AMR风险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