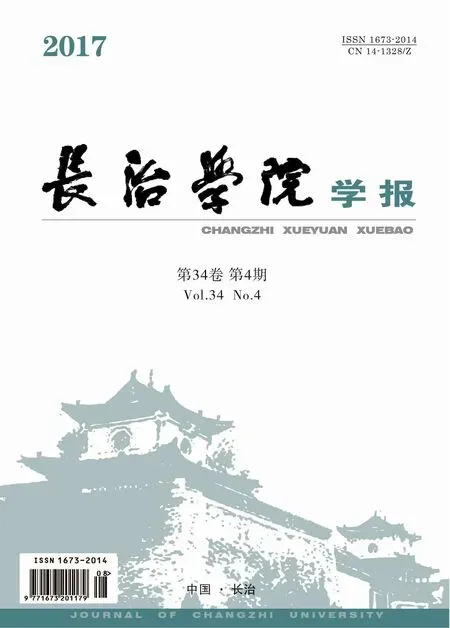“私”在夏目漱石小说《心》中的关系及意义
2017-03-30李德平廖志翔
李德平,廖志翔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私”在夏目漱石小说《心》中的关系及意义
李德平,廖志翔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在夏目漱石的小说《心》中,“私”(日语“わたくし”即“我”)因其指涉的对象不同而具有不同含义。作为学生“我”的“私”是一位心路历程的见证者和希望的寄托者;作为“先生”的“私”则是一位告白者、忏悔者。同为知识分子的两个“私”之间表现出一种授受关系和精神父子关系。这一关系不仅具有新旧更替的意义,它还连接着作家的社会期待和对人生道路探索的哲学思考。
《心》;“私”;“我”;“先生”;夏目漱石;关系及意义
夏目漱石被誉为日本的“国民作家”,他的作品历来深受读者的喜爱,也不断被解读,表现出无穷的魅力。作为他后期三部曲之一的著名长篇小说——《心》,尤其深受读者的青睐,对其进行的研究也经久不衰。从国内对该作品的研究来看,从“先生”的角度来分析探讨其自杀原因及内涵反映的文章比较多,但从文本中的人物即“私”的叙述角度来分析“我”和“先生”两者关系及其意义的文章还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也将试图从这一视角来进一步探讨作为叙述者的“私”在小说《心》中的关系及存在意义。
一、“私”的指涉对象
小说《心》由上、中、下三篇构成。它们分别为上篇《先生和我》、中篇《双亲和我》、下篇《先生和遗书》。从小说的整体来看,文本中出现了两个叙述者“私”,其所指涉的对象不同。第一个“私”是指上、中篇里出现的叙述者即作为学生的“我”。第二个“私”是指在下篇中作为遗书的叙述者“先生”以第一人称方式出现的“我”。这两个叙述者“私”的存在,具有深刻的内涵,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
二、“私”之间的关系及意义
小说《心》中的两个“私”之间,体现为一种叙述与被叙述、见证与告白的关系。这一关系包含着一种经验授受和精神父子的关系。
小说从现时的视角叙述过去还是年轻大学生时的“我”在镰仓与“先生”相遇,对“先生”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从而逐渐与他熟识起来并常去他家中拜访。先生最开始对我尽量保持着一种疏远和怀疑的态度。他每月到杂司谷公墓供奉亡灵一事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但他不能告诉他人的理由使“我”感到奇怪。他重复讲说他是一个寂寞的人,他对跟太太之间“我们应该是人世间天生最幸福的一对”[1]24的表达也使“我”充满疑问。他认为恋爱就是罪恶,他表现出的对全人类都不信任这一所谓来自他实践的认识,也让“我”难以理解。他的一些话,如“平常都是好人……至少都是普通人,就是这种人,在发生什么事情时,会一下变成坏人。这才可怕呢,所以不能大意呀”[1]68、“我从别人那儿收到的屈辱和损害,过上十年、二十年也绝不会忘掉的”[1]73常常让“我”感到意外和不得要领。这一系列的疑问只有等到下篇中“先生”给“我”的遗书之后才得以解除。在下篇中,“先生”向我告白了他的过去。他从小失去双亲,被叔父欺骗了财产后从此决心永远离开家乡,认为别人都靠不住的观念也浸透到他的骨子里。“对于金钱,虽然我已怀疑了全人类,但是对于爱,我还没有对全人类发生怀疑”[1]159的他,对寄宿房东太太的女儿“静”产生了爱恋之情。当他发现被自己邀请来一同寄宿的好友K也对“静”产生苦恋后,“先生”由于独占意念和嫉妒心理,对一向追求“精进”和“道”的K,他用K原来用过的话语“在精神方面没有进取心的人,那是混蛋”[1]222来堵塞好友K通向恋爱的道路,之后装病并趁机提前与房东太太取得和她女儿“静”的婚约。好友K由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和“先生”的背叛而自杀。自此“先生”深感自己的罪孽,一直生活在忏悔和阴影笼罩的孤独生活中,最终以“殉死”的托词而自杀。在此,“我”成了“先生”命运的见证者,“先生”也以遗书的方式向“我”告白了他的心路历程。文本至此也完成了“我”的叙述与“先生”的被叙述书写。
在“我”与“先生”的交往、“先生”向“我”告白的过程中,实际上蕴含着一种经验授受关系和精神父子关系。
在日语中,老师被称作“先生”,而能称之为“先生”的人则是能给予学生或年轻人以必要指导的人。表示“我”的“私”在日语发音中除了“わたし、わたくし”等以外,还有发音“し”。而能表示“先生”的“師”其发音也有“し”。如果说作为“先生”的“私”能够真正成为老师的“師”,那么“先生”就能给予作为学生“我”的“私”有益的指导。从文本的叙述我们可以得知,“先生”是明治时期的一位知识分子,而“我”当时是一名大学生,可以算作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然而,因为受到“金钱”和“恋爱”这两个事件的影响,“先生”变得既不工作也不到社会上去活动,逐渐变得讨厌和人见面,对“我”毕业论文也不打算担负指导的责任等。但是,当他发现“我”想认真地从人生获得教训时,他才准备把自己的过去毫无保留地“讲”给“我”。正如他在遗书中描述的那样,“我要把黑暗的人世的阴影,毫不客气地投在你的头上。……你要定神注视着这个黑暗的东西,从这里边抓住可以供你参考的东西。……所以对于要在今后有所发展的你,我想也许有几分参考价值吧”[1]137、“我现在正在自己剖开自己的心脏,要把它的血泼到你的脸上去。如果当我心脏停止搏动的时候,能够在你胸脯里孕育着一个新生命的话,我就满足了”[1]138。由此看来,这时的“先生”已把“我”当作真正的传授对象,准备把他的个人实践和经验转接到“我”身上。毕竟,当时的“我”太年轻,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正如“先生”自认为年轻时既无经验又不能区分好坏那样。“先生”所传授的东西,也是“我”在和他交往过程中想要获取的。“我”在小说的上篇里有讲到,“每逢回忆起那个人,立刻就要说‘先生’。在我提笔写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一样”[1]1。这里称呼“先生”,跟“这就是第一次从我嘴里唤出来‘先生’”[1]7的感受不太一样。除了同样表达一种对长者的尊敬外,还表达了一种获得经验教训后的感激,因为这里的“我”是在回忆过去,而回忆能加深对过去的认识和理解。
精神父子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召唤力量和精神对话的关系。
作为学生的“我”一开始对作为“先生”的似曾相识,也就是一种所谓的“既视感”。“我”对“先生”充满好奇和无数次的“预期”,加之“先生”对“我”的认真态度进行多次确认之后,“我”成了他告白人生经历的期望对象。况且他自嘲遭受“天罚”而不能生子,来自外界的且又表现认真的“我”则可成为思想的寄托。当“我”回到故乡,对于“无知”的父母,“我”还把他与“先生”进行比较,而当收到先生遗书、得知先生恐怕已不在人世时,“我”却不顾病危的父亲而奔赴东京关注“先生”的安危。“先生”对于“我”,从更大程度上来讲,具有一种精神层面的召唤力量。毕竟“我以为先生的谈话要比学校里的讲义有益,先生的思想要比教授的意见值得感谢”[1]32。最终“先生”在几千万日本人中特别选择了“我”作为他的告白对象,这似乎也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安排。
朋友K自杀之后,“先生”是孤独和忏悔的,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而生活在不安、寂寞和罪孽之中,尽管后来有太太“静”的陪伴,可是“先生”由于对人的讨厌和不信任,他跟太太缺少真正的交流,这常常使他们彼此之间产生误解。他对太太的爱是一种近乎“神圣”的爱,他不愿让太太知道他的过去,是为了想尽可能地让太太对他过去的记忆能纯洁地保存下去。另外,“先生”又不愿与社会接触,更是缺少了能真诚对话的对象。然而,当时作为青年学生的“我”的出现,则让“先生”看到了希望,“二者展开的是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与渴望得到人生指导的两代人之间的对话”[2]91。这种对话的形式,后来因为“我”父亲的病危,则转换成了书信这一书面的对话形式。不过,这种对话形式则能更好地把“先生”的精神生活和心路历程用文字表达出来,对寂寞、忏悔的“先生”来说,也能更好地得到解脱和安慰。
三、“私”与作家的关系及意义
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里曾说,“小说里的名字决不是无的放矢的,就算它们是再平常不过的名字,它们肯定也有特殊的意义”[3]43。在小说《心》里,作家用叙述者“私”替代了“先生”和“我”具体的名字,使其成为两者的代名词。小说文本也隐去了两者所处详细地址的名称,而且也没有明确那站在现时角度来叙述的“我”的职业身份。诚然,第一人称的叙述是常用的手法之一,但对于《心》这部小说来讲,这一特殊设置应具有特殊的含义。作为“先生”的“私”,不仅代表个人,还代表了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这一类人。作为“我”的“私”,也不仅代表个人,还代表了要改变前一种精神状态的希望的寄托者。对于“先生”和“我”两者的关系,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其关系即二人并不只代表‘个人’也寓意着‘时代’”[4]91。这两者的关系也都最终走向了所指对象的不确定性,即具有了泛指的意义,而且,两者的关系更蕴含着新旧事物之间的哲学思考。
正如大家所知,明治维新实行全盘西化,而这种西化完全是一种“外化”,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内化”。“文明开化”反映在精神层面,最为推崇的就是西方思想体系核心的“个人主义”思想。开化以来,社会对那种“自由、独立、自我”的“明治精神”极力推崇。在这急剧变化的时代,这种“明治精神”对传统的重伦理道德和人情的东洋文化构成了巨大冲击。然而,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变化往往是比较敏感的,但也常常是无力的。他们一向生活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维新后的自我觉醒,使其逐渐摆脱传统文化而转向西洋文化。但这一西方倡导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却与作家漱石先生倡导的“个人主义”是有区别的。漱石先生提倡的“个人主义”是既要尊重自己,又要尊重别人。在行使“个人主义”时,要避免向“恶”的方向即向“利己主义”方向转化。从小说《心》中“先生”在寄宿中自朋友K出现后的命运变化历程来看,它正体现了“个人主义”已经“开始一步步向利己主义转化”[5]52,其后果是不仅害了朋友K也害了自己。正如“先生”在信中所言,“我们这批人诞生在充满了‘自由’、‘独立’、‘自我’的现代,恐怕谁都要成为它的牺牲,不得不尝尝这种寂寞的味道吧”[1]34。作家也同样是明治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正是通过剖析以“先生”为代表的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彷徨与孤独的精神世界,从而对“明治精神”进行批判。
那么,批判之后的解决之道何在?除了作家提倡的那种既要尊重自己又要尊重他人以外,在小说《心》中也已经有了暗示。作为另一个“私”存在的“我”就是一个希望的寄托。正如前文所述,“我”是“先生”心路历程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他传授经验教训的对象,还是精神召唤和精神对话的应对者。从文本内容可知,“先生”早已把自己当作死了似地在生活,认为“我们受到明治的影响最深,此后生存下去,总归要落后于时势”[1]253,既然如此,那么,作家就选择去“旧我”而换“新我”,用新时代的青年代替旧时代的“木乃伊”似的存在。如果说去旧“私”(“し”)就是选择“死”(“し”),那么,换新“私”(“し”)就会是选择新的开“始”(“し”)。两者的更替,不仅仅是两个时代的更替,更具有哲学上永恒意义的新旧事物之间的更替。同时,也体现出作家的一种社会期待和人生道路探索的哲学思考。
[1]夏目漱石.心[M].周大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2]邓传俊,李素.夏目漱石的《心》中的称谓艺术[J].名作欣赏,2014,(27):91.
[3]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卢丽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4]张博.夏目漱石对明治“时代精神”的反省—兼论《心》的天皇制批判[J].日本研究,2016,(01):91.
[5]常骄阳.夏目漱石的“自我本位”思想[J].外国问题研究,1998,(02):52.
(责任编辑 史素芬)
I106
A
1673-2014(2017)04-0053-03
2017—05—16
李德平(1985— ),男,四川宜宾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廖志翔(1992— ),男,四川资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