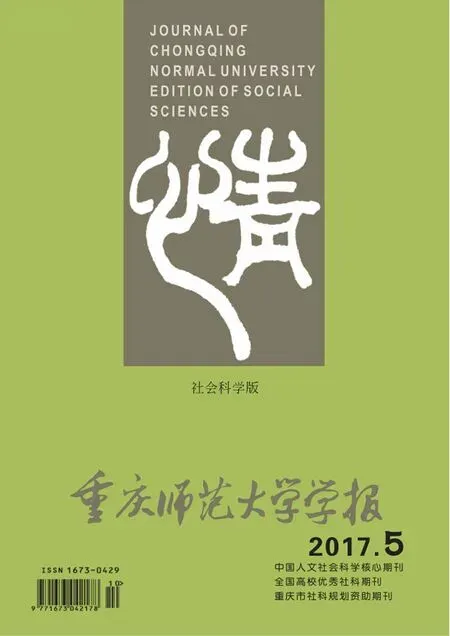从王国维的悲剧美学看《玩偶之家》的真善美
2017-03-29赖志成
赖 志 成
(香港教育大学 文学院,中国香港)
2017-03-10
赖志成(1967-),男,文学博士,香港教育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语文教育。
从王国维的悲剧美学看《玩偶之家》的真善美
赖 志 成
(香港教育大学 文学院,中国香港)
王国维运用西方“美学”概念,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美学理念,对“悲剧”进行继承和改造, 形成新的中国式悲剧美学思想,并把中国式的“美学观”推向世界。本篇主要从“真”——“人之大患在我有身”的体验,“善”——无用之用及道德崇高的美学体现和“美”——“彻头彻尾”及“第三种”悲剧的营造这三方面分析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真善美。
王国维;悲剧美学;《玩偶之家》;真善美
挪威话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年)及其剧作《玩偶之家》为中国人所认识,始于清末民初的中国启蒙运动。1918年6月,《新青年》杂志出版了《易卜生号》,刊登了《娜拉》(《玩偶之家》)全剧剧本,把此剧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随之而来的“易卜生热潮”深深影响国人。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对人生观和艺术观之关系的思考,以及从中产生的美学思想。对于人生观与艺术观,乃至人生与美学的关系,王国维在《静庵文集·自序》中有道:“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1901年至1902年)之间。癸卯(1903年)春始读汗德(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1804年)之纯理批评。”[1]469。后来,王国维读到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年)的著作而“大好之”,因此从1903年的夏天到1904年的冬天这一年多的时间他都以此为伴。“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此意于《叔本华及尼采》一文中始畅发之。今岁之春复返而读汗德之书,嗣今以后将此数年之力研究汗德,他日稍有所进,取前说而读之亦一快也,故并诸杂文刊而行之,以存此二三年间思想上之陈迹云尔。”[1]469而其在《〈红楼梦〉评论》第一章一开始就引述老子的“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和庄子的“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这两句话语来阐述其人生观与美术(艺术)观的关系。[2]350从这里,可见其美学思想受康德、叔本华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等西方哲学家、美学家的影响非常大,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王国维利用老庄学说去分析、解释、演化他的美学思想。《〈红楼梦〉评论》,代表着王国维所奠基的现代中国美学思想精华所在,是中国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批评理论之鼻祖。
悲剧是美学理论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它是随着社会矛盾冲突而产生,是人类在大自然、社会组织以及自身历程中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之记录。它通过“丑”对“美”的暂时压伏而赞扬“美”的不屈态度,从而展现人类奋斗的精神,歌颂人类那崇高悲壮的审美感受。[3]133-135王国维把西方的美学概念, 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相互结合,对“悲剧”进行创造性的改造, 建立新的中国式悲剧美学思想。在这里,我们试图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真”——“人之大患在我有身”的体验、“善”——无用之用及道德崇高的美学体现和“美”——“彻头彻尾”及“第三种”悲剧的营造这种“化西”的美学角度去欣赏《玩偶之家》的真善美。
一、“真”——“人之大患在我有身”的体验
王国维以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和“生存欲求”论为出发点,在第一章论述道:“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痛苦与倦厌之间者也。”[2]351其对人生的本质作了悲观的阐释,不仅在第一章的开始就引用老子和庄子的话语, 并将它们融合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之中, 得出“人生就是欲望与痛苦的循环”的结论。在王国维看来,无论是从西方叔本华的观点,还是中国老庄的理论,痛苦是无可避免的,它是伴随着人生而来的,人生的基本问题就是“欲望——生活——痛苦”“三者一而已”的问题。
悲剧的“真”就是源于“人之大患在我有身”的体验,“欲望——生活——痛苦”三者不断循环所产生的痛苦。就如在《玩偶之家》里,女主人公娜拉和常人一样,拥有众多而平凡的愿望:希望家庭幸福美满,夫妻和睦,丈夫事业有成,子女健康成长……但是,人生是不会一帆风顺的。几年前,丈夫海尔茂得了一场大病,为了给丈夫治病,娜拉悄悄伪造自己刚离世父亲的签名去向柯洛克斯泰贷款,这就犯了伪造签字罪;而海尔茂,他也如常人一样,想升官发财,家庭美满。多年后,在海尔茂升任经理之时,他站在道德高地,开除知道自己太多背景,而声誉不大好的老同学柯洛克斯泰;柯洛克斯泰想挽回声誉,保住工作,就拿娜拉伪造签名的借钱字据要挟娜拉,叫她劝海尔茂不要开除自己;海尔茂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痛骂娜拉是“坏东西”“伪君子”“犯罪的人”等等,更指责她和她父亲一样,不信宗教,不讲道德,没有责任心,把自己的一生幸福、前途都葬送了;当危机解除后,海尔茂又立刻恢复了对妻子的甜言蜜语。阮克医生怕死,怕孤独,既极需海尔茂这位老朋友的友谊,又想得到海尔茂太太娜拉的爱,和她相好。林丹太太,为了自己家人的生活,嫁给了自己不爱的男人;丈夫死后,被生活所迫,其拜托多年不见的同学娜拉帮忙介绍工作。后来为了摆脱孤单,又想和旧情人柯洛克斯泰重温旧梦……但是才刚刚在不久前,她还想夺走柯洛克斯泰的工作。这些,都是世上普罗大众最普通,最“真”的“欲望”,这些“欲望”,每天都在我们的身边上演。而就是这些最普通,最“真”的欲望,导致了他们的痛苦,并成为整部话剧的矛盾冲突之所在。叔本华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求生的意志”。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相互厮杀的战场,它永无宁日, 永无休止,所有人都为了生存,为了满足欲望而需要不断挤压别人的生存空间, 直到共同毁灭。在人世间,叔本华找不到一丝曙光, 更找不到幸福和自由,叔本华说:“我们既已在无知无识的自然界看到大自然的本质就是不断的追求挣扎,无目标无休止的追求挣扎……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除的口渴相比拟。”[4]213他认为自从人来到这个世界,就一直伴随着生命之欲,永远不会满足——若是暂时得到“满足”,就会寂寞、空虚、无聊,于是又产生新的欲望。王国维认同叔本华的观点,他认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籍,终不可得也……”[2]351这些无穷无尽的欲望,为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欲望、生活、痛苦,三者是共生的,这也是生命的“真”。
怎样才能脱离痛苦呢?就是放弃私欲,不要对人世间的功名利禄看得太重,对生死处之泰然,如老子所说的“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突破“小我”;以及叔本华的克制欲求,与世无争,堵塞痛苦以升华自我等。王国维把老子、庄子和叔本华的哲学观念相融合, 并加入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加以改造, 使之“著我之色彩”。王国维指出生活之苦是由人的私欲所造成的,其解脱之道也应该由人自己去探求。他提出的解脱之道有两条:第一就是“存于观他人之苦痛”,第二就是“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第一条解脱之道是“唯非常之人, 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 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2]356-357这条解脱之道是一条宗教之道,但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例如曹雪芹形容惜春的“看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就是说惜春看破了大观园的盛景不会长久,于是用黑色尼姑衣服换掉了自己原来的红装,以遁入空门作为解脱的途径。第二条解脱之道是从“自我”出发,在痛苦中觉悟,最终弃绝意欲,这是“觉自己之苦痛”,这条解脱之道是一条审美之道,而王国维认为这条审美之道更为重要,因为它更接近普通人,更为自然,更人性化,它可以成为一般人的解脱之道。这就是“以美灭欲”,通过欣赏、领略艺术之美,使人们“忘物我之关系”,从审美中得到暂时的解脱。王国维有道:“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2]357因此,文学艺术可以使人们暂时离开为了欲望而斗争所产生的痛苦,得到解脱。而在《<红楼梦>评论》里,王国维向人们指出了解脱的终极方法:和惜春的因看破了大观园的盛景不会长久而出家不同,宝玉最后的削发皈依沙门,是因为他因身边的金钏、尤三、尤二、司棋、晴雯等人,特别是黛玉的悲剧,洞察到宇宙人生之真实面貌,明白到整个人世间就是一出循环往复的悲剧,领悟到一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渺小, 于是撒手红尘,进入佛门。王国维认为宝玉的解脱方式极具“壮美”,是一种融合了自然、人类、艺术的解脱, 其层次远远超越了惜春。回到《玩偶之家》,娜拉“啪”的一声关门离开了“家”,除了给了我们无穷的想象空间,也似乎预示了这种“解脱”。
二、“善”——无用之用及道德崇高的美学体现
在美学的角度上,“善”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指事物“非功利性”的“无用之用”的美学观;第二,是指在道德意义上崇高善良之美学体现。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中指出:“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2]352这一物就是“美术”,它之所以能使人“解脱”于人生之苦痛,就是因为“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2]352在艺术的面前,鉴赏者应该去除功利物欲,用最纯粹的审美态度去领会艺术的美,否则,艺术就会被添加了艺术之外的杂质,失却了艺术品原来的真义,而观赏者也会被种种的杂念、虚荣、欲望等所蒙蔽,使他们面前的艺术品变质。因此,王国维主张要用“忘物我之关系也”的态度去欣赏艺术的美。
“无用之用”,出于《庄子》。《庄子·逍遥游》有云:“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遨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嫠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无用之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庄子思想中的“无用”,是以形体上的“无用”来追求真正的解脱和自由,不为外物所羁绊。但是,天生万物,必有各得其所之用,所以在庄子的心中,他是追求契合心灵的“用”之大道,“乘道德而浮游”,不为“一时之用”而使自己陷进痛苦烦恼之中。庄子的“无用之用”与老子的守朴见素,不肯固执思想互相呼应。
《玩偶之家》在当今世界掀起的波澜之一,就是妇女解放运动。对于这个问题,易卜生在1898年挪威妇女权利协会(Norsk Kvinnesaksforening/Norwegian Association for Women’s Rights)的一场著名的演讲中说:“must disclaim the honor of having consciously worked for the women’s rights movement, … (since I wrote) without any conscious thought of making propaganda … (my task having been) the description of humanity. ((我)必须否认曾经有主动积极地为女权运动而出力这个荣誉……(我在这方面)并没有做过任何有意识的思想宣传……(我的任务是)对人性的描述。)”[5]563可以说,或许易卜生真的没有主动为女权运动做过任何有意识的思想宣传,也没有想过《玩偶之家》这出话剧要为妇女解放贡献什么,但无可否认,易卜生的作品在现代“女权运动”的推动上引发了巨大的影响。娜拉和海尔茂的“斗争”,引起轰动的“离家”,在这一百多年来不断鼓舞着无数的妇女为“独立自主”而斗争,而这些斗争,为妇女们攻陷了一个又一个阵地,争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一切,或许都是易卜生当年没有想到的,这就是预料之外的功用,也是本部分所谈的“无用之用”。
王国维在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中谈到悲剧中“善”的层面之伦理价值。善,在“美学范畴,指善良的行为。意谓文艺的功能在于劝勉善良的心理、惩罚丑恶的行为。”[6]98在这里,王国维“无用之用”的美学观已经演化为一种带有功利性的导人向善——赞美道德崇高的美学体现。这种演化,和“无用之用”审美观非常吻合,并以展示世俗人伦的忠孝道德为尚, 把忠孝道德的体现——“善”作为人生最重要的道德之一。这种“善”的范畴,《玩偶之家》也有深刻的展示。娜拉是一位有爱心、善良、坚强的女性。她为了挽救病危的丈夫,瞒着他去借贷;另外,她非常关心父亲,为了给垂危的父亲省却烦恼,在借债的时候冒名签字;她为了丈夫和家庭受尽委屈,最后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和名誉。她在经济上出现困难的时候,也努力牺牲自己,使家人的生活能尽量过得好一点;对于儿女,她的关心爱护是无微不至的;另外,娜拉对在她家里工作的人,例如孩子们的保姆安娜、女佣人爱伦和脚夫也是和蔼可亲,从不摆架子。当知道同学林丹太太孤苦无依,没有工作的时候,娜拉也非常热心地帮助她渡过难关,拜托丈夫海尔茂替她在公司里找一份工作。易卜生把“善”渗透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让读者忘却物我利害,有所领略感悟,进而把这些领略感悟演化为审美的快乐,融进“善”的美学境界。
三、“美”——“彻头彻尾”及“第三种”悲剧的营造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把艺术的美分为“优美”和“壮美”两种。所谓“优美”,就是能够使人的心境变为平和宁静之状态的艺术之美,普通的艺术作品就属于此类。 而“壮美”则可以使人意志为之破裂,令人悲怜、畏惧、痛苦,产生巨大的冲击,再转化为审美的快感——这就是一种悲剧的美学。虽然“优美”和“壮美”都能使人忘记物我的利害关系而产生快乐,但很明显,“壮美”这种悲剧美学的格调远远超越“优美”,正如歌德的诗歌曰:“What in life doth only grieve us. That in art we gladly see.(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于美术中则吾人乐而观之。)”[2]353这也是王国维所开创的结合中西文化之“悲剧美学”,并以此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学的美学特质。他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2]358认为这种空幻的乐天色彩,不但令文学作品失“真”,更损害其艺术的“美”,批判传统文学审美观念缺乏对现实世界的正视。王国维极力推崇《红楼梦》“彻头彻尾之悲剧”及“第三种悲剧”的特色,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当中,《红楼梦》最具有“厌世解脱”的精神,他指出,“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2]359,毋庸置疑是“彻头彻尾之悲剧”。另外,王国维的“第三种悲剧”说,是受到叔本华的悲剧说影响的。叔本华在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德语:《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英语:TheWorldAsWillandIdea,1819年)里,把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因恶人所启,第二种是因盲目的命运,第三种是由于当中人物的位置和关系,不得不如此所造成的,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王国维认为《红楼梦》这个悲剧,就是这种“第三种悲剧”,他说:“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2]359因为人生之最大的不幸,并不是“例外之事”,而是人生所固有的,“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2]360
在《玩偶之家》里,的确能展示出王国维的“彻头彻尾”及“第三种”的悲剧模式。《玩偶之家》非常典型地展示了“由于当中人物的位置和关系,不得不如此所造成的”的“第三种悲剧”特色,话剧当中没有一个角色是所谓大奸大恶的坏人,也没有所谓的“盲目的命运”,所看到的,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不幸。娜拉最后的离家出走,并没有为笔者带来所谓“解放的喜悦”,有的只是那更为深重、更深一层的悲凉效果。从全剧来看,剧中人物可以说都是悲剧人物。虽然娜拉在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后有了顿悟,发现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玩偶,之前是属于父亲的,现在是属于丈夫的,自己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当发现丈夫的“爱”也是“虚伪的”之后,就“毅然地”抛夫弃子,离开家庭,这样的现实和结局,在传统的视野看来的确是十足的悲剧。林丹太太,首先为了家庭经济的原因,无奈嫁给一个非自己所爱的男人。丈夫去世后,她孑然一身,孤独、贫穷,生活毫无目的。为了生存,她被迫到克立斯替阿尼遏(Christiania,现在改名为奥斯陆)找工作。最后因为她想脱离这种极度孤单、空虚的人生状况,于是“投靠”身败名裂、走投无路的旧情人柯洛克斯泰。林丹太太对柯洛克斯泰的“爱”并不是真诚的,而是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如此”,随意、急切地为自己找一个“支撑”而已。正如话剧中她的台词道:“现在我一个人过日子,空空洞洞,孤孤单单,一点儿乐趣都没有……尼尔,给我一个人,给我一件事,让我的工作有个目的。”[7]245两人重新走到一起,或许日后对柯洛克斯泰,甚至对她自己来说都是另外一场悲剧的开始。而柯洛克斯泰,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原因,身败名裂,失去一切,而且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后来他更成为林丹太太摆脱空虚的工具。笔者认为柯洛克斯泰其实是本剧当中最被人误读,最不被人体谅的悲剧性人物——其实,在话剧当中,柯洛克斯泰也是一个好人,在得到林丹太太的“爱”之后,他就有了寄托,有了人生的意义,就马上放弃了对娜拉的勒索,这不能不说他也是一个内心善良的人。但一百多年来,他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奸角,这,也是非常可悲的。阮克医生一出生就被风流成性的父亲传染了恶疾,缠绕一生。他一直守候着近在咫尺的心爱的人,暗恋着好朋友海尔茂的太太娜拉,但这种爱是极不现实的,也没法实现的,在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孤苦伶仃,这是何等的悲哀!甚至孩子们的保姆安娜,年轻时遇人不淑,现在年纪老了,仍然无依无靠,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她是何等“命苦”!
笔者认为,本剧当中最可悲的人物是海尔茂。因为跟其它人相比,海尔茂完全是一个受害者,而且最后可说是一无所获。例如娜拉获得了自我解放,林丹太太有了生活目标,科洛克斯泰也获得了林丹太太的“爱”,阮克医生和安娜都得到娜拉真切的关心。但一直养妻活儿,为家庭不断奋斗的海尔茂最后只落得妻子的责备和离弃——其实所谓的夫权思想,只不过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普遍文化,或许海尔茂自己也不认为这是一种错。因此,这出话剧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悲剧性人物,所有人都活得很痛苦,而痛苦伴随着人,一代又一代永无止境,可以说, 人的一生就是一段痛苦的旅程。
在《红楼梦〉评论》里,王国维汇合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美学以及老庄学说,高超纯熟地催生了中国“化西”悲剧美学思想,以真、善、美的完美结合论证了其对悲剧的独到见解,使人们能够从悲剧美学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这的确是国人在美学理论方面的一次创举。王国维开创性地运用现代西方的哲学思想、文学意识和美学理念,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来评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这种尝试极具理性、富有逻辑、哲学基础深厚以及理论论证严密,使现代中国在学术研究上具备了现代文学批评的技巧,填补了在现代美学方面的空白,为中国的现代美学理论和研究贡献巨大。而通过这种“化西”的美学去检视、解读《玩偶之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当中的“真”——“人之大患在我有身”的体验、“善”——无用之用及道德崇高的美学体现和“美”——“彻头彻尾”及“第三种”悲剧的营造,《玩偶之家》的确是可以通过王国维悲剧美学进行欣赏的一个典型。
[1] 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原本《红楼梦评论》(1904年)收入《静庵文集》(1905年))[G]∥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2]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G]∥载王国维著,傅杰编.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 王向峰主编:文艺美学辞典[Z].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4] [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 Ibsen Henrik, “Speech at the Festival of the Norwegian Women’s Rights League, Christiana,” 26 May 1898; in Dukore, Bernard F., ed.DramaticTheoryandCriticism:GreekstoGrotowski(Florence, KY: Heinle & Heinle, 1974).
[6] 林同华主编.中华美学大词典[Z].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7] [挪威]易卜生著.潘家洵译.潘家洵译易卜生戏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ABriefAnalysisofADoll’sHouse’sTruth,GoodnessandBeautyfromWangGuowei’sTragicAesthetics
Lai Zhiche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Wang Guowei used the concept of western aesthetics, and combined it with the aesthetic idea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ited and transformed the tragedy, formed a new Chinese-style tragic aesthetic thought, and promoted the Chinese tragic aesthetic to the world.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Ibsen’sADoll’sHousemainly from the three aesthetic aspects, they are the truth, “people suffering from own body”, the goodness, “the aesthetics of uselessness and lofty morality”, and the beauty, “the outright tragedy aesthetics and the third one”.
Wang Guowei; tragic aesthetics;ADoll’sHouse;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B83
A
1673—0429(2017)05—0046—06
[责任编辑: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