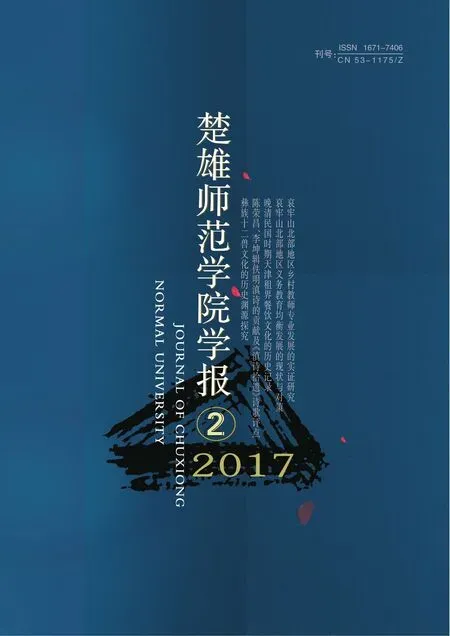清代闺秀赠妾诗词中的德、才崇尚
2017-03-29骆新泉王佩瑶
骆新泉,王佩瑶
(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清代闺秀赠妾诗词中的德、才崇尚
骆新泉,王佩瑶
(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满族入主中原后,对汉族妇女思想和行为的束缚较之明代有所松动,而清代社会风气的渐变及闺秀文化水平的相对提高,使得清代闺秀文学创作的视野逐渐开阔,这其中就包含将身份、地位低下却品德高尚的侍妾纳入到诗词创作中来;同时,清代闺秀社交范围的限制则使她们对富于才华的侍妾产生惺惺相惜之情。解读清代闺秀赠妾诗词,可以看出她们的创作动机基本缘于对所赠侍妾懿德的敬佩与才情的称赏。
清代闺秀;赠妾诗词;德才崇尚
明清两朝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是男性以放荡为快,奢靡纵欲的世风愈演愈烈,纳妾之风渐由贵族阶层向士人、商人乃至普通百姓阶层扩散;另一方面则是对妇女的约束更为苛酷,这从明清两朝妇女守节、烈妇统计数据上得到佐证。据董家遵统计,明清两朝守节妇女人数分别为27141人和9482人,烈妇人数分别为8688人和2841人。[1]但清朝毕竟是满族统治的天下,尤其是在清初,对妇女思想和行为的控制较之于明朝反有松动,而晚清时期又因西方民主思想及妇女解放思想的东进,对妇女思想和行为的制约也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气中,清代闺秀的交游开始逐渐打破性别壁垒和阶级壁垒,前者表现为大家闺秀向男性文人拜师学艺、与男性文人交游,如乾嘉时期的随园女弟子群;后者表现为大家闺秀与比自己身份低下的妾、婢乃至与更为低贱的妓女交往,如席佩兰、曹贞秀、汪端等人的赠妾诗,梁兰漪、张纨英、骆绮兰等人的赠婢诗,吴绡、徐德音、骆绮兰、钱孟钿、鲍之芬、吴藻等人的赠妓诗等。清代闺秀赠妓、赠妾诗已分别在拙作《明清女性文学新变(一)——闺秀赠妓诗词论稿》《明清女性文学新变(二)——闺秀赋婢诗词论稿》中予以论述,本文仅就清代闺秀赠妾诗词中所凸显的才德崇尚加以论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闺秀”的含义系指广义,既包含旧时有钱有势人家未出阁的少女,也包含这类人家的妻子和侍妾。之所以用“闺秀”而不用“才女”称之,是因为“才女”侧重才学,“闺秀”侧重修养和身份。
笔者广泛翻检清代闺秀诗词作品,辑得清代闺秀近20人的赠妾诗词约60首。为何清代会有如此之多的大家闺秀将写作视野投射到侍妾身上?笔者认为,这与清代女学的兴盛及社交范围的相对狭窄有关。首先,清代女学在开明士人的提倡、名家望族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及女性自身对文化的强烈渴求的合力作用下,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和发展,工诗善文的闺秀们希望能像男子那样拥有广泛的社交圈子来展现自己的才情。但实际情况是,虽然有极少数闺秀有幸得以与男性文人交游唱和,但毕竟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闺秀是没有这种幸运的,甚至连与同性的交游唱和都难以实现。在此情境下,闺秀们就极有可能对同性中的佼佼者产生惺惺相惜之情,尤其是在所接触或听闻的侍妾拥有高尚品德和丰赡文才时,这种惺惺相惜的情感更是令闺秀们自发地为其赋诗填词,加以传播颂扬。
其实,闺秀赠妾诗于明末已初露端倪,如徐媛《中山孺子妾歌》,此诗虽是模仿古乐府的同题之作,但作者性别已然改变,主旨亦有所改变。男性文人是借写宫中妃嫔宠辱不定、身不由己的命运来抒发士人仕途穷通之理,徐媛则舍曲笔而直抒其对侍妾“红葩有消歇”“中道恒相遗”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清代闺秀赠妾诗的创作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以数量多寡依次排序是:席佩兰诗10首、词1首,曹贞秀诗8首(另含逸事1篇),汪端诗6首,沈彩诗5首、词1首,张纨英5首,江珠、徐德音各4首,刘荫3首,骆绮兰、彭玉嵌、唐庆云各2首,黄媛介词2首,朱中楣、顾太清、熊琏、方荫华、郑兰孙各1首,俞庆曾词1首。这还不包括题为“美人”“丽人”及部分题为“姬人”的作品(虽然事实上这类称呼往往就是对侍妾的指称,但笔者仍持谨慎态度,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未将此类诗词纳入本题中),也不包括主妇与侍妾、长妾与小妾的联句诗。在清代闺秀赠妾诗词中,既有对他人之妾的题赠,也有对自己夫君之妾的吟咏,还有同为一夫之妾间的题赠,笔墨触及对侍妾懿德的赞美、才情的褒扬、美色的夸说、亲情的抒发、夭亡的伤悼等。本文仅就懿德的赞美和才情的褒扬这两个方面加以讨论,因为在品德、才情、美色、亲情和悼亡诸种关系中,德与才的关系最为密切,懿德需要才情表述和传达,才情需要懿德促成和显现,“‘才’是完成‘德’的一种手段和凭借。”[2]
一、敬佩懿德
文学是人学,文学创作总缘于某种动机。明清闺秀创作赠妾诗词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但前提是侍妾必须具有一般闺秀或女性应有的传统美德。“闺秀”本指大户人家德才兼备的女子,地位远在侍妾之上,倘若一名侍妾无德无行,就绝无可能引发闺秀的创作欲望,无论“她”是别人的侍妾还是自己夫君的侍妾。在诗歌中流露出对侍妾懿德敬佩的清代闺秀主要有席佩兰、汪端、沈彩、唐庆云、张纨英、俞庆曾等人。
席佩兰(1762―1831后),生活于乾嘉道三朝,江苏昭文县(今常熟市)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仕宦大家,15岁嫁同邑翰林院庶吉士孙原湘为妻。席氏自幼聪慧,富于诗才,勤于学,是袁枚最为得意的女弟子,曾得袁枚“诗冠本朝”“字字出于性灵”之美誉,著有《长真阁集》。孙原湘曾在《天真阁集·自序》中说自己“十三时不知何谓诗也,自丙申冬佩兰归予,始学为诗。”[3]可见席佩兰对丈夫诗歌创作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孙原湘《怜才》诗中也有“绛帖愿称诗弟子,红楼许拜女先生”的诗句,说明自己学诗得益于妻子。做人德为先,才华丰赡的席氏对侍妾的人品德行看得很重,其《侍书簪花图·李松云太守姬人》中的姬人“不簪金雀不花冠,只爱同心一朵兰”(其二)的贞静朴素及其为主人“裁笺捧砚日身亲”(其三)的举动,虽是侍妾分内之事,但无疑也是妇女懿德的体现,否则,席佩兰不会赋诗歌之。《李宁圃观察姬人孟心芝课婢灌花图》4首中的姬人孟心芝“紫衣亲侍卫公旁”(其一)的行为深深打动了席氏,使她放下闺秀身价而自愿为之写诗。世俗认为,“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为第一义,容貌端庄为第二义”,[4](P629)以上5首赠妾诗中的两位姬人皆符合这个标准。席氏还有1首《琵琶仙·席芍阶姬人黄花比瘦遗照》词,虽是见姬人遗照而写,却同样是因为这位姬人生前的懿德美行。我们不知道这位“席芍阶”是何许人(从姓氏上看,也许是作者娘家的某位亲人),更不知道这位“姬人”是何姓名,但我们知道她具有公认的妇德。她在女性最美的韶华嫁人为妾,而主人却罹病难医,感动作者的是姬人“称药添香,为夫婿沉疴礼星汉”的任劳任怨与辛勤服侍,以至于消瘦憔悴,竟至于在“锦瑟”“年华刚满”时就不幸早逝。
与席佩兰同时代的钱塘闺秀汪端(1793―1838),字允庄,号小韫,钱塘人。8岁时母早卒,15岁与一代文儒陈文述之子陈裴之订婚,16岁交由姨母梁德绳抚养,18岁完婚。由于汪端自幼体弱,次子孝先也形质孱弱,再加上翁姑在汪端婚后的第9个年头双双罹病,汪端与丈夫立愿持斋3年,诵《观音经》,夫妇分室居住。分居次年(嘉庆二十五年),汪端便以子嗣不广为名请为丈夫纳妾秣陵王子兰(字紫湘,一字畹君)。从一般层面上讲,这本是妻子的无奈,但就汪端本人而言,却又未必如此。她一半是出于夫家香火延续的考虑,一半是忙于她毕生的事业——选辑《明三十家诗选》,才做出这个决定。这既是她的大度,也是她的自愿。紫湘婚后不但与主人陈裴之情感极笃,与汪端亦和谐融洽,主动帮助汪端照顾舅姑。不幸的是,两年后紫湘病卒,让汪端伤痛不已,汪氏遂作《紫湘词》哭吊。在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一千一百多首诗中,《紫湘词》是较为特殊的一组诗,序中毫不隐瞒自己对紫湘的喜爱,将之比为韶华美颜的碧玉和桃根、慧性的绿珠和花蕊,既切合紫湘的年龄相貌特征,又点出紫湘的灵秀聪慧心性。诗中尤其是称赞紫湘“兰秀佐馂”“燕寝怡颜”“椒颂流馨”“洁奉兰羞”的淑女风范和“性厌铅华”“鸾台浴德”的美德。汪端在序中回忆自己于道光元年(1821)卧病殊剧时,紫湘“伫苦哺糜,含辛调药,中宵结带,竟月罢妆”的竭力服侍,直至病愈,“姬颜始解”,令自己感动不已。没有料到的是,紫湘却因照顾自己积劳成疾而扶病、归宁,最终卒于母家。故此汪端不由发出“呜呼!贤矣”之感慨,且一气作成七律8首,读来令人唏嘘。其中第4首详细叙写紫湘于寒夜侍疾迟迟不得休息、药囊细意烹煎,立春日和挑菜节也无意佩戴彩胜、无暇梳洗簪环、无心观看试灯的细节,颔联直称紫湘之贤良一如晋代李络秀。络秀者,西晋安东将军周浚妾。周浚出猎遇雨,止络秀家,见络秀而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晓之以理,父兄从之。后络秀生子及嵩谟,并列显位,李氏家族亦得正当礼遇。后因以指有才识之女子(事见《世说新语·贤媛》)。尾联特别点到紫湘在世时勤勉操劳,为丈夫和自己手制寒衣之事,并在诗末自注:“太夫人及余夫妇御寒襦褐,频年皆姬手制。”我们知道女红是中国古代妇女最重要的谋生手段,因为女红不仅是家庭生计和物质需要的一种技术性活动,更象征着女性的人格和美德。“一个女性的所有生活内容和她的精神追求几乎都通过‘女红’这个文化符号表达出来。”[5]至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汪端创作《紫湘词》的动机了。
沈彩(约1751―?),字虹屏,号扫花女史,亦号青要山人,乾隆时长兴(今浙江湖州)人,清代藏书家、书画家陆烜(生卒年不详,字子章,号巢子)侍妾。沈彩本是主妇彭玉嵌出嫁时带来的陪嫁丫鬟,通常情况下自然也就是大妇的心腹。而清代有点身份、地位的丈夫大都想纳一个侍妾,有些大妇在明知不能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就改变思路主动将陪嫁丫鬟送给丈夫做妾。这其实也是一种女性智慧:“与其妻不如妾,不如妻妾如姊妹”;[6]与其嫉妒自伤,不如惺惺相惜。妻妾相安无事,互相牵扶携带,总比让丈夫纳一个素昧平生的侍妾要好。以主妇随嫁婢女做丈夫的侍妾,还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避免或减少丈夫在外拈花惹草;二是可以约束丈夫,所以《红楼梦》中的凤姐才会把平儿送与丈夫做妾,“一则显她贤良名儿,二则又叫拴爷的心,好不外头走邪的”;三是省下一笔买妾的钱。一举三用,故而清代有不少主妇这么做。事实上,清代家庭生活中妻妾共处一室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相安无事、不失融洽的,纪晓岚所言“妻妾同居,饮忍相安者,十或一焉;欢然相得者,千百或一焉”,[7](P82)只是强调矛盾的一面。沈彩在《春雨楼书画目》后序云:“主人少好书画,所著……盈卷矣。……壬子之秋,主人以病疟瘳后,余与飘君日侍奇晋斋,进茗添香之次,日展法书名画为消遣,……时夫人在座,莞尔而笑。遂书之以为后序。”从中可以窥见清代上层社会大家庭妻妾共处一室的融融情状,也可窥见飘香辅助大妇和长妾沈彩共侍丈夫的美好品德。沈彩本就是一位极其聪俊的女子,诗、词、文、赋、题跋皆工,书、画兼善,能丝竹,且精于书画鉴赏,可谓才女中之才女,又兼得到主妇彭玉嵌热心指教,既教唐诗,又授《女诫》,想来言行举止一定符合时训规范。但陆煊在纳了沈彩妾这位得力助手之后的若干年,又纳了一位年龄更小、名为飘香(姓氏不详)的二妾。沈彩诗词中以“飘香”为题的作品多达5首,倘若飘香人品不佳,沈彩就绝不会与之“笑携手”(《秋夜偕飘香妹小园步月》),亦不会“一日三秋费梦思”(《送飘香妹》),更不会“问讯平安竹,清江双鲤鱼”(《春日寄飘香妹》)。沈彩还有《晚听飘香妹品箫》诗及《念奴娇·为飘香妹催妆》词,另有若干首与主妇、主君的诗歌“同作”及“和作”。如沈彩夜晚临欧帖时灯花掉落导致纸上留下烧痕,主妇作诗一首戏之,诗中充满关爱之情,沈彩则和作《夜临欧书忽灯烬落成烧痕余恚甚夫人有诗因和作一绝》;沈彩作《春夜琴兴》,主妇则同作一首;沈彩作《秋感》《春晓》,主妇皆予以和作;主妇作《秋夜怀梅谷主君客越》《醉花阴·和漱玉词》《蝶恋花·和漱玉词》,沈彩则分别与之同作《秋夜怀梅谷主君客越同夫人韵》《醉花阴·和漱玉词同夫人作》《蝶恋花·和漱玉词同夫人作》。沈彩还与主君、主妇共作联句诗《春日联句效伯梁体》。试想,如若沈彩无才而无德,怎会深得主君和主妇的共同爱怜。
妻妾制的实行必然会受到妻子的嫉妒和阻止,所以男性要求妻子“不妒”。“不妒”“就是容忍爱情的竞争者与侵犯者,把自己的权利割让给对方一部分,甚至全部割让。”[8]这样的顺从和忍让表现出东方女性病态的克制。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张纨英(1800―1881),适太仓王曦,早寡。张纨英有《邻云友月之居诗初稿》四卷,存诗210余首,中有《遣婢碧芹赴聊城旅邸侍夫子以诗送之并寄夫子》组诗4首、《送姬人碧芹自武昌之杭州》1首。这位碧芹因为得到主人及主妇的认可而完成了由婢而妾的身份转换,这从诗中“柳枝传艳曲,桃叶送行舟”(其一)两句及“千秋络秀名”(其四)的用典可以证明。《送姬人碧芹自武昌之杭州》诗中“差同大令迎桃叶,绝似坡老携朝云”两句也明示碧芹的身份是侍妾。张纨英遣碧芹赴聊城(今山东聊城市),是派她去为丈夫“温酒需红袖,添香理翠裯”的。送侍妾去服侍丈夫,却要为侍妾写4首诗,是因为碧芹妾具有“礼仪知有自,情性略能同”(其三)的妇德,故而作者言:“忆汝最难忘”(其二)、“一晌牵衣泪,苍茫百感生”“相期吾与汝,白首听鸡鸣”(其四);言“束装草草送汝行,握手牵衣涕如雪”“何日乡闾重结宅,白头相对欢无极”(《送姬人碧芹自武昌之杭州》)。晚清女诗人俞庆曾(1865―1897),字吉初,德清(今属浙江)人,近代藏书家宗舜年继室,晚清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俞樾(字曲园)孙女。俞庆曾在其诗词集《绣墨轩诗词》中虽无直接赠妾的作品,却有一首祝贺丈夫纳妾的贺词《高阳台·书贺瑟庵置媵》。此词中,她明明心里失落到极点,却还要装作很高兴:“移得明珠,聘来碧玉,须知我见犹怜”;想象丈夫从此之后会移情别恋(“一斛香螺,替描十样眉尖”),但还要为丈夫祝福:“为它更祝宜男佩,慰含饴、笑卜堂前”。作为“通情达理”的妻子,俞庆曾要为夫家香火延续着想,不管她是刻意装作若无其事还是本就心安理得地为丈夫祝贺。可笑的是,“姑为买妾,妾生杨梅疮,未即纳。翁问之,则诡言庆曾不容也。”公公不知事情原委大骂庆曾,庆曾为减少家庭矛盾,曲从姑意,竟不自辩。这样的隐忍温顺,读来令人心动。
江苏吴县(今属江苏苏州)闺秀唐庆云(1788―1832),字古霞,乾、嘉、道三朝元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阮元三妾。唐氏能诗善画,工花卉虫鱼,著《女萝亭诗稿》,在451首诗稿中,有多达70余首与主人、大妇、长妾、二妾的联句诗和赠答诗。这些联句赠答诗,将一个封建高级官僚家庭生活中融洽和乐的夫妻、夫妾、妻妾、妾妾间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妻有“妇德”,妾有“妾德”,而这样的夫、妻、妾关系和感情也是封建婚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反映。阮元家族中女眷及其与其他女性诗人的诗文唱和活动主要通过“曲江亭”唱和来体现,《将入京师留别书之宜人》中的宜人是阮元长妾刘文如,身为三妾的唐氏在留别长妾时不忘叮嘱“独力持家还教子,身孱也要惜精神”;《留别月庄姊》中的月庄姊是阮元二妾谢雪,字月庄。唐氏在留别二妾时不忘“莫愁书卷难销闷,好把余闲自课儿”,这是妾与妾之间的关爱,完全符合封建妇德的要求。
二、称赏才情
清代闺秀不仅对侍妾的懿德嘉行大加赞美,对其丰赡的才情也热情夸奖。
清代闺秀大力夸奖女才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受男性文人尚才的影响,男性文人还将才女视为“有情欲和情感表达能力的个体,从而对男性产生了感官和心理上的吸引力。”[9]如历代男性诗人都有咏乐府古题的传统,“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的同题之作就很多,南朝谢朓、唐朝李白、南宋曹勋、宋末元初赵文、“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高启、明代徐祯卿、元末明初的刘基等人,他们对此类富于才华的“赵女”的命运深表称赏和同情,“才女”已然“成为封建文人墨客抒发白我情绪之工具。”[10]其二是清代闺秀自身本就能诗善文,但在同性交游中很难遇到才情相当的才女与之对应,于是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倘若遇到才情丰赡的侍妾,就会不由自主地对侍妾的才华大加赞赏,以间接表达自爱自赏的情感。
对侍妾才华称赏的源头亦可追溯到明末徐媛和陆卿子两位闺秀身上。徐媛对才女的夸说可以扩大到任何阶层,比如对丽人“眉黛妒芳春,眼波横秋月”(《赠丽人二首》)、“艳发朝霞色,芳从歌扇回”(《咏美人雨中观荷》)的由衷喜爱,对才女“鸣琴坐文石,幽响发轻商”(《赠美人》)的歌唱,甚至为一位富于才情的女子错嫁庸夫而愤愤不平,并创作了《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妇》,诗中称厮役为“竖子”,对不幸才女的恻隐之心昭然若揭。而徐媛闺蜜陆卿子也创作了拟古乐府诗《邯郸才人出为厮养妇》,虽是咏古题却能别出新意,诗中以“红颜委野草,惆怅一身怜”来表达自己的惺惺相惜之情和愤愤不平之意。在诗歌中流露出对侍妾才情称赏的清代闺秀主要有黄媛介、曹贞秀、徐德音、沈彩、江珠、陈蕴莲、汪端、席佩兰等人。
明末清初女诗人、女画家黄媛介(约1620―约1669),字皆令,浙江秀水人,出身嘉兴望族,后嫁作士人杨世功妻。黄媛介曾在钱谦益侍妾柳如是的住处度岁题画,离别时创作了两首同调同题的赠别词《眼儿媚·谢别河东夫人》。词中作者直言“黄金不惜为幽人,种种语殷勤”;“曾陪对镜,也同待月,常伴弹筝”;“半帆微雨,满船归况,万种离心”。之所以有如此难分难舍的情感,除了黄媛介和柳如是二人志趣相投外,更在于二人皆是名盛一时的才女,故会在分手时难免产生惺惺惜惺惺的“几处暗伤神”。俗话说,送人以物不如送人以言,因为前者固然使被送者有睹物思人的效果,但其深刻度和客观效果还是比语言逊一筹:“盖物之意有尽而文之意无尽,酒之味有穷而言之味无穷也。”[11]黄媛介深谙其道,所以她要用赠词表达自己对柳如是的谢意。
曹贞秀(1762―1822),字墨琴,安徽休宁(今隶属安徽黄山市)人,侨居吴门(今苏州市),清乾隆年间文士王芑孙继室。曹氏有《写韵轩小稿》诗一卷、文一卷、续增二卷。曹氏工书,尤擅小楷,世称海内闺阁第一,时人藏之以为荣。曹氏有赠妾诗5首,其中《题汪兵部亡姬杨丽卿海棠写生》《沈姬藕香却扇词二首》3首单从诗题看就知道是出于对汪兵部亡姬和沈姬诗画才能的赞美。曹贞秀还有一篇赠侍妾的记叙文《书宝香逸事》,虽非赠妾诗,但对于了解清代闺秀崇才心理很有帮助。《书宝香逸事》中的宝香妾是作者幼妹澧香丈夫沈绮云的亡妾,姓姚,名允宜,华亭(今属上海市)人,本儒家女。颖敏多慧,家贫而随其母入沈家教诸女女红,年及笄而不他适,愿留事绮云。绮云得之欢甚,然为大妇所困。宝香宛转屈意,弥缝其间,善抚大妇诸子女,黾勉上下,辛苦十年,最终死于肺结核病,享年二十有八。澧香是在宝香殁后始往沈家为继室的,与宝香前后不相接,又无一昔话言之好,而澧香却坚持要求姐姐曹贞秀为宝香作记,按照曹贞秀的说法是:“犹能使澧香心折而力为之请,是其人有可想见者。”[12](P427―428)倘若宝香妾无才也无德,怎能打动澧香和曹贞秀的恻隐之心。
徐德音(1681―1758年后),字淑则,号绿净老人。清初康乾年间钱塘著名女诗人,有《绿净轩诗钞》五卷和《绿净轩续集》一卷。中书舍人许迎年妻,早寡,复罹火患,艰苦持家,教子成立。徐德音《赋得自是寻春去较迟为金阊吴媛作》组诗4首,诗前有一篇较长的序,从序中看,金阊(今属苏州市)吴媛本是“性钟夙慧,技擅多能”“资本无双”的姑娘,被自己的丈夫相中,“乌丝襕空贻赠句,白团扇未即迎归”而欲纳为侍妾,而吴媛本人亦与徐德音的丈夫许迎年“美要眇以目成”,不期“乃有塞上健儿、浙西戎帅,恃其巨镪,谋置小星(妾之代称。笔者注)。”按照常理分析,丈夫要纳的侍妾如此才色无双,徐德音应该嫉妒才对,但她却要为丈夫未能纳成而惋惜,并对吴媛赞不绝口,除了受时俗影响外,吴媛的“技擅多能”不能不说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侍妾虽然出身低微,但她们中往往有不乏才富情饶者,有的甚至远超大家闺秀,比如沈彩就是一个典型。沈彩本是吴兴(今浙江湖州市辖区)故家女,自幼聪慧异常,陆煊在《春雨楼集》序中有“清华端重,智慧聪俊,荆妻玉嵌,即授以唐诗,教以《女诫》,稍知文义,浏览书史,过目不忘”[13](P6)的记载。沈彩也自言“十三娇小不知名,学弄乌丝写未成。即拜良师是大妇,横径曾作女书生”(《戏述三首·其一》)的经历。如此聪慧的女子,纳为侍妾后又经主人陆煊及主妇彭玉嵌指点教授,学问渐精,于是成为陆煊的贤内助,陆煊著作大多为其抄录。沈彩创作颇丰,诗、词、文、赋、序、题跋皆工,《春雨楼集》十四卷,计诗七卷334首、词二卷66阕、题跋三卷61则、文二卷10篇、赋7篇、序2篇,另有《春雨楼书画目》一卷167件,以及题词、补遗、附录若干。除此之外,沈彩书画兼善,能丝竹,且精于书画鉴赏,可谓才女中之翘楚,在当时名气远播,陆煊题序中就有“诗传日下,书达海陬”的说法。沈彩《有日本人索余书者戏作》的诗题及《减字木兰花·纪事》中“拟刻牙章,细字簪花格一方。……几笔残兰,小婢偷将换素纨”的词句亦见此言非虚。陆煊正妻彭玉嵌对沈彩的才情亦是称赏不已,一次沈彩夜晚临欧帖,因注意力集中而没有注意到灯烬落在了书帖上,致使书帖留下烧痕,沈彩不由气恼而口出骂声,彭玉嵌听到后赋诗一首:“秋风瑟瑟夜悠悠,翠袖天寒尚写欧。忽听莺声呼可惜,灯花小烬落银钩。”银钩者,比喻遒媚刚劲的书法,可见沈彩书法刚柔相济,水平非同一般。还有一次,沈彩创作七绝《秋感》,彭玉嵌和作1首,后两句是:“丹青只有骚人手,画出伤心一片月。”这是夸说沈彩非凡的绘画才能。虽然彭玉嵌与沈彩是妻妾关系,二人基本上平分了丈夫的爱,彭玉嵌也承认丈夫“本是多情种子”,并说过“香草美人轮到自”的醋话,产生“懒卸妆梳,和衣而睡”(《鱼游春水》)的愁情,但她对沈彩的才情仍赞不绝口。试想如果沈彩仅有懿德而无赡才,就算她是自己喜欢的丫鬟、主人宠爱的侍妾,也不会经常与她互酬互唱的。
汪端才华过人,《名媛诗话》有“博学强记,颖悟非常”的记载。汪端主动为丈夫陈裴之娶的侍妾紫湘也是一位不凡的女子。据汪端《紫湘词》序言载,紫湘是一位“绿珠慧性”的女子(《紫湘词》其四),是“夙耽词翰”“椒颂流馨”的才德兼善的美妾。椒颂事典出自《晋书·列女传·刘臻妻陈氏》:“刘臻妻陈氏者,亦聪辨能属文,尝正旦献《椒花颂》。其词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阳散辉,澄景载焕,标美灵葩,爰採爰献,圣容映之,永寿於万。’”[14]后遂用为典实,指新年祝词。可见这位紫湘是一位善属文的姑娘,且具“解歌芳草朝云慧”之才艺。该诗末尾作者自注“太夫人及余夫妇御寒襦褐,频年皆姬手制”,既是紫湘妇德的表现,亦是紫湘女红之才的表现。这里汪端显然将紫湘的才情与懿德结合在一起加以吟颂。汪端还有1首《林秋娘词》,序中介绍这位秋娘是吴地人,年十五时为巨室侍姬,不久即遭大妇妒而被遣。这位侍妾不仅“明艳善歌”,并且“兼耽翰墨”,汪端还有幸听过她的歌。作为才女的汪端,对秋娘的遭遇深表同情,感叹“鸧鹒疗妒叹无方”,以传说中能治妒的鸧鹒鸟入诗,用意显然是憎恶大妇对秋娘的嫉妒,并希望秋娘的侍妾生涯能够继续下去,对女子才情的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明末文学家叶绍袁在为妻女所编的《午梦堂集》作序时明确提出女子要有“三不朽”:“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15]德、才、色兼备而“昭昭乎鼎千古”的清代女子,妻妾皆有。江珠、陈蕴莲、席佩兰等闺秀笔下的侍妾都是这样能诗、善画、善歌、善舞的慧性女子。
乾嘉朝江苏甘泉(今扬州)闺秀江珠(1764―1804),字碧岑,号小雅摩。诸生吾学海妻,受业余萧客之门,通经史。江珠与张滋兰、尤澹仙等闺秀结社联吟,有“吴中十子”之美誉。江珠《题储香岩姬人香卿红莲小影》一组4首,所咏姬人名为香卿。其一首联次句言姬人“亭亭出谢家”。“谢家”既可指有咏絮之才的东晋才女谢道韫,也可指富于才情的唐代歌妓谢秋娘,但从末句“人貌美于花”判断,当指其美貌与谢秋娘的,这样看来,此姬人的出身应该是歌妓。但无论是哪种含义,皆是称赞姬人的才情。其二又不由赞叹姬人的“独擅容华美”且“偏教福慧齐”,姬人的“慧”是“鼓瑟”,技艺非同一般,否则就不会用“偏”这个副词。其三首联直言姬人“彩笔工辞赋”,既然工于辞赋,那就更符合才女的标准了,所以作者才说姬人“妆台韵事多”。可见,倘若姬人仅仅擅琴而不能工辞赋,那就无韵事可言。尾联“展图惊一室,争欲礼姮娥”中的“图”,当然指诗题中的“红莲小影”,这个小影不是照片,而是香卿的画作,这样看来,香卿的才情更是非同一般了。其四末句以“莫教频采摘,满子更堪怜”作结,或是照应香卿所画的红莲小影图让人看了爱不释手,更有祝愿其“满子”(儿女满堂)。
江阴闺秀陈蕴莲(生卒年不详),字慕莲,号蓉江女史,江苏江阴人,常州武进左晨妻。工绘能诗,曾从夫仕宦津门(今天津市),常凭画资以补家用,有《信芳阁诗草》五卷,诗余一卷。道光辛丑年(1841),浙江石门人、平谷知县方廷瑚在《信芳阁吟稿》序中说陈氏诗词诸作“天分人功,铸辞命意,实乃兼有众长”“绘事绝人”“手录吟稿,全帙楷法清劲流丽”。[12](P389)陈氏自身才华丰赡,故其对有才华的女子亦生怜惜之情,哪怕她是一名地位低下的侍妾。她的两首《题某参军姬人美人纨扇》中的姬人就是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子,其才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五言韵更妍”(其一)、“何殊通德伴伶元”,用汉代大臣伶元(又名伶玄,字子予)事典。伶元是《赵飞燕外传》的作者,年老时曾得一位名为樊通德的小妾,二人情笃意深,并经常谈诗论赋,议古说今,时人称为“刘樊双修”。陈蕴莲借用此典显是称夸姬人的诗赋才华。二是擅长绘事,诗题中的“美人纨扇”就是其所画,故而陈氏感慨“休怕秋风藏笥箧,大都一见即生怜”(其二),明里说扇,暗中夸人。
席佩兰在《侍书簪花图·李松云太守姬人》其三中以“翰墨姻缘”来褒扬李松云太守姬人的文学才华,以“小蛮腰态朝云曲”来赞美她的歌舞才艺。《李宁圃观察姬人孟心芝课婢灌花图》中的姬人擅长绘画,她画的课婢灌花图就是明证。该诗一题4首,其一用唐传奇《聂隐娘》中智勇双全的聂隐娘喻孟心芝,赞美其“福慧兼全”。其四用唐代邺侯事典称美李松云太守的藏书之多,而以“邺侯家有女相如”喻指姬人的非凡才情,虽有溢美之嫌,但也绝非空穴来风。
从以上作品来看,清代闺秀赠妾诗词中流露出的德、才崇尚是显而易见的,在称颂其德时,往往带出其才;而在称颂其才时,又往往暗含其德。二者相较,懿德是主要的,才情是次要的。也就是说,一位侍妾倘若既有懿德又有才华,就必然得到闺秀们的褒扬;仅有懿德而无才华,亦可得到闺秀们的褒扬;仅有才华而无懿德,则未必得到闺秀们的褒扬。换一种说法,即便闺秀们在赠妾诗词中只言“才”而不提其“德”,但实际上大多已经包含了“德”,否则,无论侍妾有多么丰赡的才华,品德低下就绝不会得到闺秀们的青睐,甚至不会得到闺秀们的原谅。之所以如此,乃是中国古代两千余年封建社会对妇德和女才的倡导使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中,拥有话语权的男性不遗余力地倡导妇德,并用奖惩结合的手段恩威并施,长期的浸染也使女性对男性提出的妇德标准加以认同,并身体力行,渐成风气。但“妇德”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早在汉代之前,妇德的提倡散见于《礼记》《仪礼》等书籍中。东汉的班昭则是将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思想经典化、标准化的第一人,所著《女诫》从“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7个方面系统地阐述妇德的具体要求,历来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妇德著作。南北朝时的《北史列女传》序曰:“盖妇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16](P1985)将女子贞节置于妇德之首,并以此作为女性留名青史的首要条件。唐时的《女论语》对女性行为有了更加琐碎而严苟的规定。宋代司马光的《家范》明确要求“妇人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将女性的柔美恭顺作为妇德的基本要求。明代建国之初便强调“礼法国之纪纲,礼法正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17](P5)更是把妇德教化与国家兴盛和社会安定紧密相连,并出现以“女四书”为代表的女教读本,促成全民崇尚妇德的大气候。而朱熹所提出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18](P1)的著名论点,在明代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更兼以明代中晚期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快速壮大,使得社会各阶层的思想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从明代拟话本小说中得到证实。清代的女教书籍更加丰富,一些大家族还自编“女范”一类的小册子来训导家族的女性。妇德作为国家意志和百姓意愿,从社稷层面上讲,身为“臣民”的女性,爱国是最美的品德;从家庭层面上讲,身为“人妻”的女性,忠贞是最美的操守;身为“母亲”的女性,贤良是最美的德行;身为“女儿”及“媳妇”的女性,孝顺是最美的品质。那么,清代闺秀在诗词中大力推崇妇德就理所当然了。
至于女才崇尚,往往是和女德相联系的。如果单就女才而言,历来都有“才多防命”“才厚福薄”的偏见。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明代,虽因明代尤其是明末青楼文化的猖行,工诗擅词的妓女日益增多而导致一部分人戴上女子有才则“淫词丽语”坏了德性的有色眼镜,但同时期才子与才女的风流佳话及才子佳人小说,却对女子才情的尊崇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社会思潮的主阵地。开明人士则认为才和德是女子身上和谐共存的属性,清初王相之母在《女范捷录·才德篇》中就提出“德以才达,才以成德”的观点。《闺秀诗话》则是以情作为才与德的中介,推崇才为德的基础,突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见解独特,难能可贵。明末文学家叶绍袁甚至在《午梦堂集序》中指出:“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19]如此看来,清代闺秀赠妾诗词大力褒扬侍妾的丰赡才华就是顺理成章的行为。
[1]董家遵.历代节烈妇女的统计[A].鲍家麟主编.中国妇女史论集[C].台北:牧童出版社,1988:112―112.
[2]程君.清代闺秀诗人的“才”“德”之辩[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72―76.
[3](清)孙原湘撰.天真阁集[M].嘉庆五年刻增修本影印原书版.
[4](清)钱咏著.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胡平.文化之帛中国女红文化四论[D].南京: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6]刘强.地方志中所见清代广东妾的形象[J].中国地方志,2005(5):37―41.
[7](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8]周俐.封建妻妾论——以《三言》为例——小说与妇女之三[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3).
[9]钟军.“女子无才便是德”——清前期文人之女性才德观辨析[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0]杨洁.历代诗词中的“赵女”形象解读[J].邯郸学院学报,2011,(4):80―83.
[11](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上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8.
[13]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三编(上)[M].合肥:黄山书社,2012.
[14](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十六)[M].珍仿宋版印.
[15](清)叶绍袁.午梦堂集·序[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6](唐)李延寿.北史·卷九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宋)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六·家道[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9]叶绍衰.午梦堂集序[A].午梦堂集[C].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6:1.
(责任编辑 王碧瑶)
The Pursuit for Virtues and Talent in Poems Written for Concubines
LUO Xinquan & WANG Peiyao
(SchoolofHumanities,XuzhouInstituteofTechnology,Xuzhou, 221008,JiangsuProvince)
After the Manchu entered and hosted the Central Plains,compared with the Ming Dynasty,the ide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nstraints of the Han Nationality Women was loosen.The gradual change of social atmosphere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lative improvement of young ladies’cultural level,make a broader horizon on literary creation.This includes bringing concubines with low status but noble characters into poetry creation.At the same time,the limits of social interaction made young ladies in Qing Dynasty have freemasonry feelings with concubines.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young ladies’ poetry for concubines in Qing Dynasty. After interpreting the poems for concubines in Qing Dynast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ir creation motivations originate from appreciation for concubines virtues and talent.
elegant society ladies of Qing dynasty;poetry and Ci for concubines;appreciation for virtues and talent
2017 - 01 - 29
骆新泉(1959―),男,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I207.22
A
1671 - 7406(2017)02 - 0105 -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