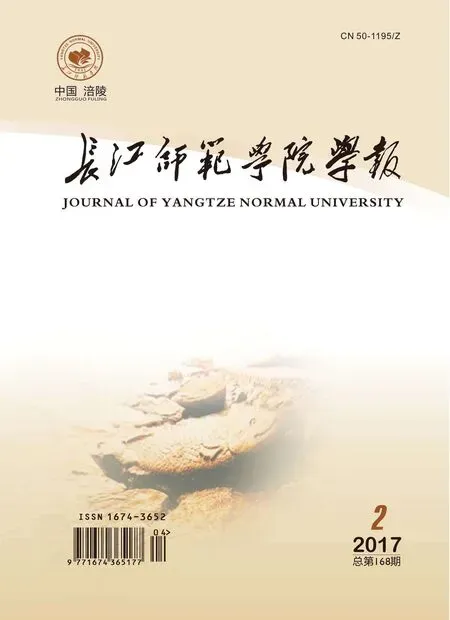加里·斯奈德诗歌中的禅宗意识
2017-03-29邱食存
邱食存
(1.四川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2.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加里·斯奈德诗歌中的禅宗意识
邱食存1,2
(1.四川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2.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美国后现代性思潮受到了禅宗特别是“离两边”思维与“空无”理念的重要启发。兴起于1950年代的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普遍沾染了强烈的禅宗意识。加里·斯奈德是这一派诗人最为重要的代表之一。作为禅宗“平常心是道”的具体体现,斯奈德诗歌大多来源于日常生活,体现出一种身心合一的生活态度。其次,斯奈德诗歌少有自我主体意识,缺少西方传统诗歌中的内在理性逻辑,结构松散,这种“无我”之空性意识使得万事万物在斯奈德诗歌中自然呈现。
加里·斯奈德;禅宗;“平常心是道”;“无我”;后现代性
每到一个社会的重大转型时期,那些渴望突破传统而又没有多少话语权的人们总会把目光投向异域文化,从中汲取可供改造、转化和吸收的养料与启发,从而创造出足以对抗传统的新的理论与实践。美国的1950年代就是这样的重大转型时期。“垮掉派”“黑山诗派”等新一代诗人在美国时下严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实之下奋起反抗,发动旨在反叛象征型现代主义诗歌的变革运动,拉开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大幕,这与他们普遍从佛教禅宗中找到各自的精神旨归有很大关联。为了对抗美国现代主义中强势的欧洲传统,“垮掉派”等新一派诗人们在把目光回溯到庞德-威廉斯“美国本土主义”的同时,更注重吸收海外那些契合美国当下后现代时代精神、可以为其所用的思维和理念。毕竟,“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后现代主义可能被看做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最近的思潮。而从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则常常被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来源。”[1]而中国文化中最具有后现代性特质的莫过于禅宗了。在反二元对立思维方面,禅宗中的“离两边”与“空无”等思维和理念同后现代性思想颇具“异质同构性”[2]。加里·斯奈德是新诗人中最具有禅宗意识的诗人之一。
一、“离两边”思维与“空无”理念
对“垮掉派”诗人影响最大的禅宗经典主要是《金刚经》《坛经》和《心经》。《金刚经》是佛陀通过回答其十大弟子中号称“解空第一”的须菩提的提问而宣讲的佛法,全文不着一“空”,但通篇都是关于“空”的智慧,如“不住于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不应住色生心”[3]。
《坛经》把观念分成36对,包括“邪与正对、痴与惹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慈与毒对”等,这似乎也是一种二元对立式的划分,但《坛经》接着说:“出入即离两边,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4]《坛经》又云:“佛法是不二之法。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舆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5]这种“离相亦离空”的“不二”与“离两边”思维,对待万事万物不断然肯定,也不完全否定,不执着于是非善恶。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即《心经》,也注重“离两边”与“空无”等思维和理念。经文中提到的“四谛”(“苦、集、灭、道”)、“五蕴”(“色、受、想、行、识”)、“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及其对应的“六尘”(“色、声、香、 味、触、法”)所统摄的大千世界、万事万物,无一不具有“空性”,就连“空”的概念本身也是“空”。既然都是空,还有什么值得执着?所以要破除“我执”以求得“无明”境界。这样,《心经》强调万事万物都存有各种可能性,看似对立之物也可以相互转化,如“正即是反,反即是正”(《心经》中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与“不正不反”(《心经》中的“不生不灭”)[6],这种思维打破二元对立思维,即令二元混同。正是在这一点上,解构主义“呼应了禅宗反逻辑的、断裂式的思维”[7]。德里达对强调超验所指和自我身份定位的逻各斯(Logos)(指“原初意义”“中心”),“绝对”概念的解构也必然会导致一种“去中心”“无中心”的现实图景。
二、平常心是道
后现代主义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同“实现人的美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应的批判活动也就成了“一场生活和艺术的游戏”[8]。从“垮掉派”诗人所普遍看重的禅宗“空无”理念来看,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说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完全远离现实世界、摒弃所有意识思维的“空虚”,相反,禅宗注重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体验,强调的是“平常心是道”。马祖道一禅师曾说:“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贤圣行,是菩萨行。’”[9]这里所说的“平常心”可以说是排除“二元对立”思维的自然之心,崇尚天然自在的状态,反对人为的浮夸矫饰的言行态度。正如史特伦(Frederick J.Streng)所理解的那样。
“空无”是对日常生活的认知,但又不依附于日常生活。它认识到各具特色的实体、自我、“善”与“恶”以及其它实践中的方方面面;但这种认识是基于这些事物的空无品性。这种智慧并不是某种神秘性的入迷状态,而是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享受。[10]
说到底,“空无”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加里·斯奈德诗歌大多来源于日常生活,可以说是禅宗“平常心是道”的具体体现。日常生活中的劳作是斯奈德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对于诗人而言,专注于日常劳动是“艰辛而又愉悦的任务”[11],与修行无异,体现的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活态度。
换地漏、擦水龙头、参加集会、收拾屋子、洗盘子、查油表——不要认为这些会干扰你从事更重要的追求。我们为“道”而进行修行,但这样一轮家务活并不是我们基于此而希望能逃离的困扰——日常劳动就是我们的道。[12]
这种身心合一的生活态度在诗歌《篱笆桩》(“Fence Posts”)被发挥到了极致。
我可以加点煤油
70美分一加仑
这是你在酒馆附近买油的费用
达到防水效果得用3.50加仑
外加半罐5加仑的,6美元,
来涂刷120个篱笆桩
选用液材的话,我可以节省30美元但你得算上你的时间成本[13]
诗人絮絮叨叨,用平淡无奇的口吻细述如何做篱笆桩这一“小事”,没有任何象征性暗喻。对于斯奈德,写诗和做篱笆桩一样,都是劳动,都要放空自己的各种欲望、不求深刻,专注于万事万物的“真如”实性,才能身心合一。
日常生活中,粗俗语也是一种真实,难以回避。在《浆果宴席》(“The Berry Feast”)中,他写道:
“去他妈的!”郊狼号叫着
跑掉。
……
唱着歌,一个酒鬼突然来个急转弯
靓妞!快醒来!
要夹紧腿,把邪恶
从胯下挤出来
瞪着红眼的家伙快来了
软的勃起了,假装虔诚的哭泣
滚到太阳下,晒干你僵直的身体![14]
在《作为一名诗人你应该知道些什么》中,他写道:
亲魔鬼的屁股,吃屎;
搞他角状带倒钩的鸡巴,
搞女巫,
操所有的天使
和金灿灿芳香的少女——[15]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在被视为高雅的诗歌中使用粗俗话具有强烈的反叛破坏意味,表达了他们真实的内心感受。
三、“无我”之空性
斯奈德对禅宗观念的接受首先源于其出生于对基督教持强烈批判态度且在政治上也一直有反叛倾向的家庭。斯奈德认同“局外人”身份,对待美国资本主义和西方形而上学等主流话语往往采取一种边缘人的心态,其诗作往往颠覆二元对立思维,强调差异之中的和谐一体性。斯奈德对禅宗思想的信仰,打破了“柏拉图—笛卡尔的主观/客观、身/心、人/自然、自然/超自然的二元论”[16],让诗人可以跳出诸如内在世界/外在世界、理智/非理智与主体/客体等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斯奈德诗歌少有自我主体意识,缺少西方传统诗歌中的内在理性逻辑,结构松散,有种“浓厚的非我论倾向”[17]。这种“无我”意识使得万事万物在斯奈德诗歌中自然呈现:随意并置,没有阐释,缺乏意义,现代主义那种线性时间意识也不见踪迹。对于诗人,事物就是事物本身,而暗喻、象征、结构等等不过是现代主义强加之物,只会让诗歌陷入僵化的定式思维,扼杀诗歌的生命活力;诗歌就是事物的自呈现,即“自然而来”[18]。这种开放性的诗歌赋予了读者更多的想像空间。
有学者认为“无我”意识具有很强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不少后现代诗人发现,要想写出最能表达自我真实的诗歌,先得放空武断的自我,因为夹杂着人的各种复杂角色的各类文明因素早已把自我真实变得模糊了。”[19]斯奈德对“空无”颇有体悟,对“空”的翻译使用过不同的英语词汇,如“emptiness”“empty”“nothing”“void”等等。斯奈德曾在日记中写道:“形式——在恰当的点把事物省掉 /椭圆,空(emptiness)。”[20]在之后的另一篇日记中,他写道:“空(empty)水杯与空无一物(full of nothiing)的宇宙一样空 (empty)。”[21]
《心经》篇幅简短且意蕴无穷,可能是斯奈德最为钟意的禅宗经典了。斯奈德一直推崇玄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玄奘当年从印度带回并翻译了梵文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他在诗中写道:“佛教学者——朝圣者,带回了著名的《心经》——这一页浓缩了全部超凡智慧的哲理经典——在他的背囊中。”[22]
斯奈德也曾谈及他对《金刚经》的体会:昨夜几乎悟到“无我”。我们可能认为,“自我来自于某种普遍的、无差别的事物,也会回归其中。”事实上,我们从未离开过,何来回归。/我的语言慢慢消退,意象变得模糊。蕴含着万千变化的事物从未改变;恒久未变,时间也就没有意义;没有时间,空间也就消弭。我们随即归于空无。/“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你做菩萨,我做出租车司机,送你回家。”[23]
斯奈德体悟到的“无我”体现的正是《金刚经》所反复宣讲的“空无”(斯奈德使用的是void)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万事万物真正的“实相”是“无相”“空无”才是一切法、名、色、相的本性,独立于时空之外,既然人们“从未离开过”,所以也无需执着于“回归”。正如斯奈德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伟大的诗人不仅要表现自己的自我,还要表现出所有人的自我。为此,诗人必须超越自我。恰如道原禅师所言,‘探究自我是为了忘却自我。忘却自我,便能与万物融为一体。’”[24]
斯奈德诗歌大多体现了一种摈弃各种先入之见的“空性”诗学,“无我”意识在斯奈德诗歌中随处可见。《八月中旬沙斗山瞭望哨》(“Mid-August at Sourdough Mountain Lookout”)是诗集《砌石》中的第一首诗,分为两节:“山谷中烟云迷雾/五日大雨,三天酷热/松果上树脂闪光/在岩石和草地对面/新生的苍蝇成群。//我已经记不起我读过的书/曾有几个朋友,但他们留在城里。/我从铁皮杯子喝寒冽的雪水/越过高爽宁静的长天/遥望百里之外。”[25]该诗将“叙述者置于远离文明的高山之巅。代词 ‘我’直到第二节才出现,这反映出了叙述者的避世心态。‘我’在同一行中再一次出现后,就没再出现过,似乎自我已成了负担。”[26]这样,主语的省略和延迟体现了诗人有意改变“以主体观客体”这一惯性思维,使诗歌呈现出“以物观物”的视角,让读者对于诗中展现的自然有种直观的感受,从而生发出更多的联想。而且,叙述者强调说他读过的书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也没有尝试着去回忆起来,这莫不是斯奈德对禅宗“空无”观的参悟在其诗歌中的具体体现。
并置结构的使用往往会加强诗歌阅读过程中多义联想的催发。据美国学者墨菲(Patrick D.Murphy)观察,并置结构增加了多重意义的可能性。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许多词语的意义取决于读者如何调整该词与其前后词语的顺序。最有效的解读方式常常是对并置结构所产生的多重意义做出同步回应[27]。这种并置结构在斯奈德诗歌中处处可见,如上面所引用的诗歌中的山谷、雾、雨、热、松果、树脂、岩石、草地、成群的苍蝇,等等。这种没有人类“主体”参与的自然景物并置似乎是在展示诗人“为赋予土地自身代理权”而“远离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28]的决心。
《道非道》(“The Trail Is Not a Trail”)这样写道:
我开车下了高速公路/开出一个出口/顺着公路/来到一条小路/沿着小路开/我最后开到了一条土路/到处坑坑洼洼的,停了下来/我走上一条小径/小径越来越崎岖难行/直到消失——/来到荒野之上,/处处可行。[29]
诗人从高速公路一路下来,似乎道路越行越窄,直到无路可行,但“路”这一绝对概念上的“无”恰恰成就了一种“无中心”的“有”,反倒是处处有路可行了。诗人似乎在表明,去除我执、放空自己,方能明心见性、畅“行”无碍。
这种“空无”理念在《表面的涟漪》中也有类似表达:
广袤的荒野/房子,孤零零。/荒野中的小房子,/房子中的荒野。/二者皆忘却。/无自然/二者一起,一所大的空房子。[30]
头两行中的“广袤的荒野”与“小房子”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从第三、四两行开始,诗人借助《心经》中的“色空”思维,看到了两者之间转化的可能性。可以说,诗人正是通过这种禅宗思维来解构包括基督教神学在内的西方传统的理性思维模式的,人造世界与自然万物具有可以相互转化的和谐一体性,并不存在与人类文明完全对立的自然。
同样,诗集《龟岛》中的《松树的树冠》(“The Pine Top”)也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体性。
蓝色的夜
有霜雾,天空中
明月朗照。
松树的树冠
弯成霜一般蓝,淡淡地
没入天空,霜,星光。
靴子的吱嘎声。
免的足迹,鹿的足迹
我们知道什么。[31]诗歌前六行景物罗列并置、自然呈现。第七行人未见,但闻“靴子的吱嘎声”,非主体性自我(靴子)乃是融于自然之中的普通一物,所发出的声音更加衬托周遭之幽寂。“兔的足迹,鹿的足迹/我们知道什么。”进一步体现了主体超脱自我、凭直觉感悟自然的禅境,即消除了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等二元对立界限的澄明之境。
而长诗《蓝色天空》(“The Blue Sky”)[32]更是这种“空性”诗学的绝好诠释。该诗以佛教中的药师佛(Old Man Medicine Buddha)①药师佛,也称药师琉璃光如来、大医王佛、十二愿王等。为众生解除疾苦,他享有极高威望。但这种威望在主流佛教中却受到了压制,似乎被边缘化了,这也许是药师佛受到斯奈德关注的主要原因。为切入对象:
从这里向东方
远在佛家世界之外 十倍于
恒河沙粒
有一块称作
琉璃光净土
里面是痊愈之佛
琉璃光如来
你要花上一万二千个夏季
没日没夜地开车向东
才能抵达琉璃光净土的边界
药师琉璃光的净土——
“花上一万二千个夏季/没日没夜地开车向东”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欲念和痛苦等生命体验,诗人将这种生命体验同没有疾苦、和谐一体的琉璃光净土联系起来,强调了终极目标的无止境性和追求过程的重要性。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什么统一的“中心”可供读者作为其解读的根据,因为哪怕读者发现某个能指似乎可以作为解读依据,另一个不太相关的能指却又接踵而来,令人难以确定某种单一结论。《蓝色天空》就像是万花筒,充满了各种故事、曼特罗颂词和单词连缀,最终导致诗歌意义上的不确定性。
天上的 穹盖……卡姆
天堂 赫曼……卡姆
[同志:在同一片天空/篷帐/曲线之下]
卡马拉,阿维斯陀,腰带卡姆,一把弯曲的弓
爱神,欲望之神“玛雅之子”
“花之弓”
以上诗句所涉及的各种“空”(天空、篷帐、曲线、弯曲的弓、花之弓等等)都可以理解为是禅宗“空无”(Sunyata)理念的具体化。及至诗歌的末尾,
蓝色天空
蓝色天空
蓝色天空
是净土
药师琉璃光的净土
那里鹰
飞出了视界
飞。
此处,诗人一再强调“蓝色天空”,似乎是在表明所谓的“意义”仍然像蓝色天空的“蓝色”那样难以捉摸,因为,蓝色天空不再是一种颜色,而是一种“空”,在广大的空间中,意义是难以确定的。那只飞进这片“蓝色”消失不见的鹰似乎暗示了万物本无确定本质的品性,同时,天空也因为有了这只不懈飞翔的鹰的存在而凸显了其“空”的品性,这样,“空无”也可以说是“真如”(tathata)①大乘佛教认为,一切存在之本性为人。法二无我乃超越所有之差别相,故称真如。例如如来法身之自性即是。真如乃一切现象(法相)之实性,与一切法相非异非一,非言语、思维之所及。。总之,万物相异而相依,即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参悟其中奥妙,便能超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欲望执着、到达和谐一体的境界。斯奈德借助禅宗的“空无”理念解构了强调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以“空无”之说点明日常生活中各种“中心”理念的虚幻性。
对德里达而言,任何超验性的所指都不构成中心地位,这无疑“无限制地延伸了意义的边界和戏谑性”[33]。而斯奈德对自然的理解充满了德里达式戏谑性的解构倾向。
自然是一大套惯例的集合,完全是源自于瞬时形成的各种随性的模式和指定;完全可能在
任何时候都会消失;仅仅是作为一种戏谑的形式继续存在:宇宙的/喜剧性的乐趣。[34]
斯奈德诗歌表现的主要也是这种“宇宙的/喜剧性的乐趣”,大多具有戏谑性,而这种戏谑性跟斯奈德对禅宗公案的参悟紧密相关。对于禅宗公案及其背后思维特性,钟玲曾有这样的总结:
公案大抵是禅师为了启发徒弟,而采用非直接的答话,采用非平常的行为方式,因为徒弟通常会陷入平常的理性思维,或陷入二元分法,钻牛角尖而不自知。公案思维基本上是颠覆性的,颠覆平常用的思维方式,因此它常是突然的、断裂的、跳跃式的、不合事实的、不合逻辑的、不合常理的、答非所问的、或藕断丝连的、密码式的,而且不能,也不应该用逻辑语言来解释的。[35]
著名的“赵州无字”公案体现的就是典型的公案思维,常为研究者所征引。该公案是赵州从谂禅师(778-897年)与弟子之间的对话。据《五灯会元》卷四记载:“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师曰:‘无。’曰:‘上至诸佛,下至蝼蚁,皆有佛性,狗子为甚么却无?’师曰:‘为伊有业识在。”[36]按照任继愈的理解,从谂禅师在对话中“以通过狗有无佛性的讨论,打破禅师僧的 ‘有’‘无’执着和相对认识。”[37]看似不合常理逻辑,实则含有大智慧。
斯奈德对“赵州无字”公案深有参悟,多次直接化用。《神话与文本》(Myths&Texts)中,诗人就曾明确提及对该公案的体悟:
三月里的风
吹来拂晓的光
吹落杏花朵朵。
炉子上的咸火腿冒着烟
(坐思赵州无字我的双脚睡了)[38]
前夜,诗人苦思“赵州无字”公案,于入神、释怀之中安然地坐着睡着了,这似乎是“无”,醒来时,春风、春光、春花等自然景致以及火炉、咸火腿等日常生活事物犹在,这好像是“有”。诗人似乎在暗示“有”或者“无”乃自然实在,不可执着。
斯奈德还曾写道:“野兽/有佛性//所有都是/除了郊狼”[39],这似乎是对“赵州无字”公案的转化。按照西方逻辑学来理解,野兽有佛性,郊狼属于野兽,在这大小前提均成立的情况下,必然会推出郊狼有佛性这一结论,而诗人却说郊狼没有佛性。这是公案式的反逻辑思维。
斯奈德诗歌的戏谑性还体现在万事万物“真如”实性的强调。斯奈德注意到禅宗和基督教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基督教太过于强调超验理性,而禅宗则不然。
在超验之外是伟大的戏谑和转化。顿悟到脑洞大开的空之理念之后,时隐时现的百万小宇宙之空性就在于能单纯且充满爱心地认识到耗子及草籽的无限美好和珍贵品性。[40]
总之,加里·斯奈德是新诗人中最具有禅宗意识的诗人之一。作为禅宗“平常心是道”的具体体现,斯奈德诗歌大多来源于日常生活,体现出一种身心合一的生活态度。其次,斯奈德诗歌少有自我主体意识,缺少西方传统诗歌中的内在理性逻辑,结构松散,这种“无我”之空性意识使得万事万物在斯奈德诗歌中自然呈现。
[1]王治河.后现代主义辞典[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3.
[2]邱紫华,于涛.禅宗与后现代主义的异质同构性[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4:(3).
[3]张燕婴,陈秋平,等.论语·金刚经·道德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9:334-335.
[4]李申.六组坛经[M].[中国台湾]高雄: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198.
[5]丁福保.佛学大辞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93.
[6]释从信.心经[M].台北:圆明出版社,1990:46、60.
[7]钟玲.中国禅与美国文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2.
[8]高宣扬.后现代:思想与艺术的悖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04.
[9][北宋]道原,著;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全五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2252.
[10]Frederick J.Streng.Emptiness:A Study in Religious Meaning[M].Nashville:Abingdon Press,1967:159.
[11]Gary Snyder.Axe Handles[M].San Francisco:North Point Press,1983:85.
[12]Gary Snyder.The Practice of the Wild[M].San Francisco:North Point Press,1990:153.
[13]Gary Snyder.Axe Handles[M].San Francisco:North Point Press,1983:25.
[14]Gary Snyder.The Back Country[M].New York:New Directions,1971:5.
[15][美]埃利特奥·温伯格.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革新者和局外人(下)[M].马永波,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511-512.
[16]Rudolph L.Nelson.Riprap on the Slick Rock of Metaphysics:Religious Dimensions in the Poetry of Gary Snyder[J].Soundings,1974(5):210.
[17]Bob Steuding.Gary Snyder[M].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75:41.
[18]Jon Halper.Gary Snyder.Dimensions of a Life[M].New York:Random House Inc,1991:125.
[19]Dan McLeod.The Chinese Hermit in the American Wilderness[J].Tamkang Review,1983(1):170.
[20]Patrick D.Murphy.Understanding Gary Snyder[M].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1992:5.
[21][23][34][40][42]GarySnyder.EarthHouseHold:TechnicalNotesandQueriestoFollowDharmaRevolutionaries[M]. New York:New Direction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69:19、308、21、128、128.
[22]Gary Snyder.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M].Washington D.C.:Counterpoint,1996:160-161.
[24]Gary Snyder.The Real Work:Interviews&Talks 1964-1979[M].New York:New Direction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0:65.
[25][美]加里·斯奈德.八月中旬沙斗山瞭望哨[M]//[美]埃兹拉·庞德.美国现代诗选(下).赵毅衡,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554.
[26]Patrick D.Murphy.Understanding Gary Snyder[M].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1992:45.
[27][28]Patrick D.Murphy.A Place for Wayfaring:The Poetry and Prose of Gary Snyder[M].Corvallis: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0:45、46.
[29]Gary Snyder.Left Out in the Rain[M].San Francisco:North Point,1988:127.
[30]Gary Snyder.No Nature[M].New York:Pantheon,1992:381.
[31][美]加里·斯奈德.松树的树冠[M]//[美]埃兹拉·庞德.美国现代诗选(下).赵毅衡,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566-567.
[32]Gary Snyder.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 Plus One[M].Bolinas:Four Seasons Foundation,1979:38-44.
[33]Jaques Derrida.Structure,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M]//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280.
[35]钟玲.中国禅与美国文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46-247.
[36][宋]释普济.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84:204.
[37]任继愈.佛教大辞典[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887.
[38]Gary Snyder.Myths and Texts[M].New York:Totem Press,1960:38.
[39]Gary Snyder.A Range of Poems[M].London:Fulcrum Press,1971:73.
[责任编辑:志 洪]
I106.2
A
1674-3652(2017)02-0090-08
2016-12-30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中美后现代诗歌发生学比较研究”(16SB0224);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硕士生参与性教学模式研究”(yjg143047)。
邱食存,男,湖北黄岗人。博士,主要从事中美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