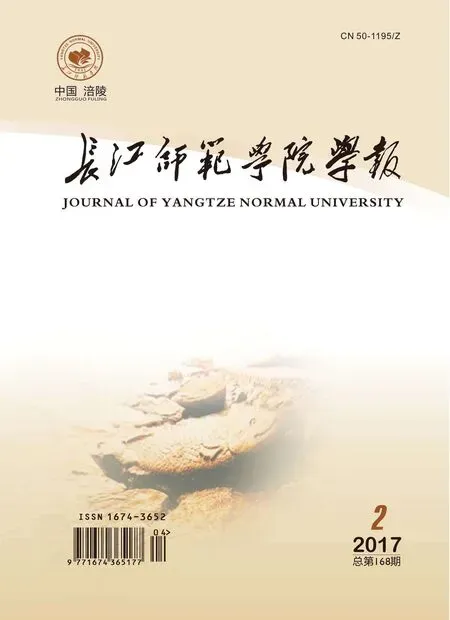朦胧诗人与地下沙龙、归来诗人和现代主义
2017-03-29李胜勇
李胜勇
(铜仁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朦胧诗人与地下沙龙、归来诗人和现代主义
李胜勇
(铜仁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朦胧诗的产生是合力的结果。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贵州诗人黄翔的成长经历与北岛的写作经历都有很强的代表性;地下沙龙是哺育朦胧诗人成长的文化思想来源之所,相互间的鼓励是他们度过难关的动力,也助力他们诗艺的成长。虽然归来诗人的人生经历与朦胧诗人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又完全不同。对朦胧诗人而言,倾心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策略和技巧的选择,而是生存镜像的潜在要求。朦胧诗人以他们深邃而多样的写作,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构成,给后来的文学以深远的影响,并在持续的影响中奠定了他们不可动摇的地位。
朦胧诗;黄翔;北岛;归来诗人;现代主义
朦胧诗的出现是时代综合影响下的产物,其书写内容、风格倾向与朦胧诗人们所置身的文化环境关系莫大。我们拟从其童年出生、地下沙龙的滋养、与归来诗人的不同、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投契几个方面,作一番考察和梳理。
一
“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39。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在100多年前说的话,用在朦胧诗人的身上同样适宜。朦胧诗人的写作是如此地与众不同,如此地挑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这与他们独特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朦胧诗人不像归来诗人那样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洗礼,经历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并在那种喜悦中发自内心地歌唱新的生活和畅想新的未来。朦胧诗人成长于个体生命备受压抑和摧折的历史时期,这个万马齐喑的历史时期也是归来诗人命运最为坎坷的多舛时期,在这一点上朦胧诗人与归来诗人是相同的——他们共享了同一段“历史背景”,这段相同的历史背景都给他们的生命施加了重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影响。但是,这只是相似。这个时期对两代诗人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对归来诗人而言,他们此时已步入人生的中年或者老年,成长与塑型于他们青年时期的人生观及其艺术理念已经完成;而朦胧诗人此时却处于一片嫩叶刚刚出土正欲伸展的少年、青年时期,在即将伸展的时期他们即遭受到了暴雨的打击,“文革”一体化所带来的压抑与黑暗覆盖了他们的整个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段。而我们知道,在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中,童年经验往往对他的心灵世界和经验世界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文革”时期注定对朦胧诗人的写作产生决定性的、深层次的影响。这突出表现在朦胧诗人写作调子的低沉、价值理想的迷惘、对现实的反叛,以及对历史的沉思上。
在以文化为敌的“文革”时代,朦胧诗人的精神成长依赖于潜行于各地的地下文学沙龙。依据朦胧诗人的构成,我们先来看看“在朦胧诗酝酿和崛起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却因为朦胧诗论争而被人为遗忘的贵州诗人”[2]178-202的成长情况。“文革”时期的贵阳郊区野鸭塘是当时的一个诗歌重镇,诗人们在那里谈论政治、文学、哲学和艺术。这个“野鸭沙龙”曾被当代诗人誉为“文革”地下沙龙中临空闪耀的“双子星座”①另一个是指当时成为诗歌重镇的北洋淀:“北洋淀几乎与此同时也成为北方的一个诗歌重镇,北岛、芒克、多多等人曾在那里聚首并催生了文学刊物《今天》。”《今天》于1978年创刊,1980年停刊,共出版了9期。之一,沙龙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黄翔的经历颇有代表性,他的身世及其写作颇能说明时代对朦胧诗人施予的残酷压迫,以及这种残酷压迫对于诗人反抗精神的强烈的塑型作用。黄翔出生于1941年,由于出生于“剥削阶级”,仅勉强念完小学,就随养母干起了繁重的农活。8岁时他从一口水井里捞出死鱼,被作为投毒嫌疑分子抓起来五花大绑当街示众,关进牢房差点判刑,后经化验井水无毒才脱干系。18岁时爬上一辆火车去大西北,梦想会迎来一个“美丽的姑娘”,却迎来一张“畏罪潜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逮捕证而被“劳教”3年;“文革”中因从手稿、书信中发现其“恋爱信件”中的诗歌流露出绝望和痛苦,即被判为“现行反革命”关入拘留所;恰在此时,医院又拒绝为他刚刚出生的儿子治病,致使孩子不久死去。黄翔崩溃;之后又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麻木神经的“政治治疗”[3]35-37……黄翔如上“简短的”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政治压迫、迫害的历程;政治的压迫与迫害给他的童年“绑上”巨大而恐怖的死亡阴影,把他青春期少年的热血和冲动“箍上”不由分说的大帽子押入惩罚的“铁窗”,让他心中的痛苦和绝望不能得到渲泄,让他的儿子死去,让他的神经死去……政治如同一块黑色的巨大的命运之伞在黄翔的头顶徐徐展开,笼罩了他的所有人生道路;他无法拒绝,只能接受,接受这只能面对的一次又一次的被摧残毁损的命运。“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一个时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这是黄翔写于1968年的《野兽》,恰似他命运的真实写照。一个诗人的写作总是会打开一片时代的天空,时代的影子往往会从其笔下流出,就像一个论者所说的:“一个一流诗人在书写个人命运时,他也就书写了一个时代的命运。”[3]37我们从“追捕、捕获、践踏、扑倒、踏、撕、咬、啃”这些凶悍的动词上可以读到,这是黄翔一生颠踬的命运的准确书写,而且这种书写是我们除了在黄翔这里看到之外的任何人那里都无法看到的一种“命运书写”。诗中的“野兽”“斜乜”“骨头”,指向时代个体的异化和嗜血的疯狂,以及压抑、恐怖、仇视的时代气氛及其内与外的赤贫。黄翔的书写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广大而普遍的命运。
黄翔的例子是一个生动例证。它鲜明地说明了一个作家的写作受到其生长环境的影响,哪怕这种影响在他的文中是以一种反面的、批判的立场出现。同时,黄翔的对抗式的写作风格还预示了一种时代的“普遍”风气。“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4]1钱钟书对作家与时代关系的精敏解析还预示了朦胧诗人的写作风格的多样,因为也有人不是采取“正面”的对抗,而是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但总的来说,正如压迫必然滋生反抗,黑暗必然滋生对光明的追求一样,“文革”史无前例的压迫暗哑了朦胧诗人的青春,却也激发了他们不甘热血冷却理想沉沦的反抗精神,正像非常的环境“塑造”了黄翔的勇猛反抗一样:“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毋庸讳言,一种如黄翔式的对抗式的写作风尚已悄然扎根在朦胧诗人的心间,而正是这种不堪晦暗命运压迫的反抗精神,为一个时代种下了灿烂的艺术火种。
二
作为理想无处安放青春遭遇放逐的一代,朦胧诗人在人生中正值求知的大好年华,只能凭任自己在敌视文化的时代大潮中感受命运的颠簸和荒诞。他们“受的是驯服工具论的教育,又欣逢不许读书的年代”[5]9,连些微的文化活动都面临被监禁的危险。哺育他们精神成长的,是处于潜在状态下的读书活动,来自于地下沙龙的西方现代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及同龄人的创作和激励,成为他们精神成长的养料和写作勇气的来源。下面的文字是黄翔写的一篇有关诗人哑默及其野鸭沙龙的名为《末世哑默》的文章,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那个时代独有的气息和特征。同时,这篇文章还透露出一种在追忆中蓦然回首时的地下文学的一种特殊的传奇之美。
早年的时候,哑默在野鸭塘的房子是个独间。在我的记忆中窗口栽着一棵仅有几片嫩叶的小树,或一簇美人蕉。日照中影子投入房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哑默气氛。房间里有一架小床,靠床的小茶几上总是整整齐齐地撂着一堆用彩色画报纸包着的书。这些书是哑默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惠特曼、泰戈尔、罗曼·罗兰、斯·茨威格和早年的艾青。还有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后来又挤进了意识流大师伍尔夫和普鲁斯特。靠墙的一角堆着几堆《参考消息》,从桌子一直堆齐天花板,颜色多半早已发黄。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那些年代,哑默就从这些报纸的文字缝隙中窥探“红色中国”以外的世界。有时一小点什么消息就会让他激动不已。如肖洛霍夫或帕斯捷尔纳克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小则报道……当尼克松访华、叩击古老中国封闭的铜门时,他同他的朋友们兴奋得彻夜不眠,在山城贵阳夜晚冷清清的大街上走了一夜。他们手挽手壮着胆子并排走(这在那种年代是要冒风险的,这种行为立即被视为“异端”,若被夜间巡逻的摩托车发现,就要被抓起来),青春的心灵跳动着梦。他们静听着自己的脚步声,仿佛中国已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一个崭新的世纪已经来临……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的处女诗作《火炬之歌》(我的《火神交响诗》的第一首,写于1969年)闯进野鸭沙龙……我第一次朗诵《火炬之歌》的那天是个夜晚。屋子里早已坐着许多人。我进来的时候,立即关了电灯。我“嗤”地一声划亮火柴,点亮我自己的一根粗大的蜡烛,插在房间中央的一根独木衣柱顶端。当蜡光在每个人的瞳孔里飘闪的时候,我开始朗诵。屋子里屏息无声,只偶尔一声压抑的咳嗽。许久许久,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我才发现整个房间还没有人从毛骨悚然的惊惧中回过神来,我这才听到街上巡夜的摩托车声。[3]38-39
本是正常年代随处可见平常无奇的阅读与诗歌朗诵活动,在那个年代竟然成了一种冒险行为,竟然与牢狱之灾相连咫尺。这篇让人如临其境的文字,因为过程的惊心动魄和事件本身所摇曳出来的精神之光及其莹洁品质,而别具一种让人心跳的传奇色彩。可是,任何人在这传奇的背后,都能够看到一种使人愁惨的现实境况。
在面临深渊般的处境时,人们是渴求得到抱慰的。黄翔的如上叙述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叙事(按照刘小枫的说法)依然是人们抱慰自己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选择之一。那些地下沙龙之所以能够在黑暗中顽强地存在,那种尽管惊惧却依然不愿退却的坚持着的倾听,正是因为地下沙龙能够提供各种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文革”时期是人民伦理的大叙事挟裹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时代,一体化的要求抹杀了个体的生命感觉,人们喜欢叙事,是因为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正如刘小枫迷人而深邃的论述:“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人们围在一起,被“他人”或明亮或晦暗的故事所吸引,仿佛感觉生活在另外的时空,“叙事编织出另一种时间和空间,给个人的生命被遗弃的长夜带来光亮,构造出玻璃般的言语世界将恐怖隔离开……现实的历史脚步夹带着个人的命运走向无奈他乡,在叙事的呢喃中,‘我’的时间和空间却可以拒绝历史的夹带,整饬属已的生命经纬。”[6]3-7正是在这种叙事的哺育下,一代诗人横空出世;也是在这种叙事中,贵阳野鸭塘横空出世,成为当代诗人眼中的“文革”地下沙龙中临空闪耀的“双子星座”之一。
由白洋淀诗歌群落(“双子星座”的另一代表)走出来的《今天》诗人群,遭遇到野鸭沙龙相似的压迫处境。多年后,北岛回忆起自己在工地上写作小说《波动》的过程,非常政治气候笼罩下的日子同样的“惊心动魄”。
下了班,我忙于转移书信手稿,跟朋友告别,做好入狱准备。我去找彭刚,他是地下先锋画家,家住北京火车站附近。听说我的处境,二话没说,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到新侨饭店西餐厅,为我临别壮行。他小我六七岁,已有两次被关押的经验。席间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对付审讯。皮肉之苦不算什么,他说,关键一条,绝对不能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新侨饭店门口分手,风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叹了口气,黯然走开。
那年我二十六岁,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它无所不在,浅则触及肌肤——不寒而栗;深可进入骨髓——隐隐作痛。那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结局的到来,无论好坏。夜里辗转反侧,即使入睡,也会被经过的汽车惊醒,倾听是否停在楼下。车灯反光在天花板旋转,悄然消失,而我眼睁睁到天亮。[7]39-40
北岛还记叙了“走后门”请一周病假,扛着折叠床乘长途车去朋友黄锐的远在昌平县城的大妹黄玲家修改《波动》时的“惊险”。
我刚写下一行,有人敲门,几个居委会模样的人隔窗张望。我把稿纸和书倒扣过来,开门,用肩膀挡住他们的视线。领头的中年女人干巴巴地说:“我们来查卫生。”无奈,只好让开。她们在屋里转了一圈,东摸摸西动动,最后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纸上。那女人问我来这儿干什么,答曰养病,顺便读读书。她抚摸稿纸一角,犹豫片刻,还是没翻过来。问不出所以然,她们只好悻悻地走了。
刚要写第二行,昨晚领路的男孩轻敲玻璃窗。他进屋神色慌张,悄悄告诉我:刚才,我听她们说,说你一定在写黄色小说。他们正去派出所报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动,摸摸他的头说:我是来养病的,没事儿。还得谢谢你了,你真好!他脸红了。给黄玲留下字条。五分钟后,我扛着折叠床穿过院子,仓皇逃窜。[7]41
北岛记叙中的带着稿子“仓皇”地“逃窜”,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它不仅是北岛“文革”时期生存状态的生动反映,也是一代朦胧诗人的生存状态的生动写照(在黄翔那里,这种“仓皇”地“逃窜”状态多次直接转变成“逃窜不及”的后果),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精神文化的处境的生动隐喻。“逃窜”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文革”时代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惧”,让所有的精神文化行为都只能“仓皇”地“逃窜”。
但是这是一伙勇敢的青年。他们没有被这种“恐惧”吞灭。他们办起了无论从精神视野还是艺术形式都开创一个全新天地的刊物——《今天》。197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这天晚上的十点半,《今天》全部印好,决定第二天贴出去。“二十三日出发前大家都来道别,很悲壮,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劲头,事实上我们确实也都和亲人朋友作了交代,万一出了事如何如何。”[8]236这是芒克关于去张贴《今天》创刊号时的记述,与贵阳野鸭沙龙的诗人们的处境一样,一种无处不在的高压管制让监禁变得随时可能。思想宵禁的“文革”时期,爱诗与独立思想往往要付出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但他(指郭世英,郭沫若之子,引者注)确实是死了,只是因为爱诗,爱用自己的脑袋独立思考而已。”[9]95中学时代即表现出杰出才华的张郞郞在此说的是另一位文学青年之死,他自己因与友人组织成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而被捕入狱近十年。
三
地下文学沙龙“给予”朦胧诗人以与归来诗人不一样的阅读。因为代际关系,除了外国作家作品,归来诗人的作品也是朦胧诗人的阅读对象(如前述贵阳野鸭沙龙中有早年的艾青)。相对来说,北京诗人(《今天》诗人前身“白洋淀诗歌群落”)由于“地利”优势而比贵州诗人的阅读“先锋”一些;而且“白洋淀”相对宽松的“自由空气”给北京诗人“馈赠”了更好的诗歌交流氛围,由此也就带给北京诗人更多的相互激励和写作上的磨砺。这是北京诗人的一份阅读书单:“一九七○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灰里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10]88可以看到,相对于贵州诗人,北京诗人的阅读已经有与时代状况更贴近的荒诞派和存在主义倾向,外加一个郭路生。此外,同龄人之间的相互激励和创作影响,北京诗人似乎比贵州诗人更积极主动,更具自觉意识。(这注定了北京诗人成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多多在一篇文章中充满激情地回忆了岳重对自己的影响:
一九七二年春节前夕,岳重把他生命受到的头一次震动带给我: 《三月与末日》,我记得我是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我……青年时代我俩形影不离,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的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10]89-90
同龄人之间的交流与激励,使他们在困难年代得以相互砥砺,获得诗艺的进步。譬如北岛曾与芒克相互不服气[11]228,芒克与多多相约每年年底,要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10]91;舒婷在读到北岛诗歌时,震惊溢于言表:“一九七七年我初读北岛的诗时,不啻受到一次八级地震。北岛的诗的出现比他的诗本身更激动我。就好像在天井里挣扎生长的桂树,从一颗飞来的风信子,领悟到世界的广阔,联想到草坪和绿洲。我非常喜欢他的诗,尤其是《一切》。”[12]133诗人们之间的交流,除了带来信息的共享与思想的碰撞外,还有晦暗生活中对于生活信心的激励。地下文学沙龙把抱团的温暖传递给了寒冷中的每一个参与者,让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在黑暗中得以潜滋暗长,在帮助朦胧诗人完成自我塑造的同时,也为时代留下了艺术的火种。此外,理想暗哑时风偏执的时代反向塑造了朦胧诗人的英雄主义气质,贝克特的荒诞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使他们更深透地看清了自己所置身的世界,也暗地里丰富了朦胧诗人的写作表现手法及其关照世界的方式。
与归来诗人普遍的身陷囹圄不能写作相比,朦胧诗人的写作则开始于“文革”中期甚至更早。北岛的写作开始于 1972年以前[11]228,芒克开始于1971年甚至更早[8]234,多多开始于与岳重的交往(约1971年左右)[10]89,顾城则在少年时代即开始写作——这使他们在与拥有成熟诗风的归来诗人相比时,在写作技艺与经验上并没有多少落差,相反因受惠于更多现代主义诗人和更与时代相贴近的思想而拥有一种归来诗人所没有的先锋与深邃。朦胧诗人多受惠于外国诗人作品的影响,比如北岛早期受叶甫图申科影响很大[13]126;顾城喜欢但丁、 惠特曼、 泰戈尔、 埃利蒂斯、帕斯,其中最喜欢的是洛尔迦和惠特曼[14]473;多多把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的中外近现代的诗抄录在一个大本子上,这个大本子曾在朋友们中间传阅,给大家很大的启发、帮助和借鉴[13]117——这些影响使他们的写作明显区别于归来诗人中受现实主义影响较深的诗人的写作,而与归来者中的现代主义写作的九叶诗人有着天然的接近和亲缘关系。20世纪80年代唐祈在兰州大学教书,北岛等去访问他,几个年青诗人在翻阅上半世纪的现代主义诗集时,发现了其灰尘满面、劫后余生的20世纪40年代的诗作,为之震惊,他们说:“这些诗正是我们想写的”[15]333。如此的交往与写作风格的相近,以至于使郑敏如此定位朦胧诗:“朦胧诗是40年代诗歌风格的再现,这不光指我们 ‘九叶’的诗,而是指40年代诗歌的再现。”[16]郑敏从诗歌风格传承的角度关照朦胧诗,也相当于指认朦胧诗是现代主义在新时期的重新“归来”,暗示了朦胧诗对诗学传统的接续。写作资源与采用手法的不同,已经预示了后来朦胧诗人与归来诗人中偏向现实主义一脉的诗人(如艾青等)的分歧。
对艺术审美认识的不同使朦胧诗人偏离主流意识形态所希望的轨道,二分法的时代思维定势及因袭而来的对于现代主义的敌意,使朦胧诗人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支持。顾城的父亲顾工深刻地看到了他与顾城两代人艺术观念的不同;出自顾工眼中的与他争论的顾城的艺术观念,我们庶几可以当作是朦胧诗人的艺术审美自白:“我是用我的眼睛,人的眼睛来看,来观察。”“我所感觉的世界,在艺术的范畴内,要比物质的表象更真实。艺术的感觉,不是皮尺,不是光谱分析仪,更不是带镁光的镜头。”“我不是在意识世界,而是在意识人,人类在世界上的存在和价值。”“表现世界的目的,是表现 ‘我’。你们那一代有时也写 ‘我’,但总把 ‘我’ 写成 ‘铺路的石子’‘齿轮’‘螺丝钉’。这个 ‘我’,是人吗?不,只是机械!”“只有 ‘自我’的加入,‘自我’对生命异化的抗争,对世界的改造,才能产生艺术,产生浩瀚的流派,产生美的行星和银河……”[17]49-51朦胧诗人突出“人”的位置,突出“自我”在写作中的至高点,这与归来诗人中突出“国家”“民族”的位置,把“人民”“集体”放在写作中的至高点完全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归来诗人中被打压的,正是朦胧诗人所标举的,在归来诗人中被排挤的,正是朦胧诗人所倡扬的,在归来诗人中所倡扬的,正是朦胧诗人所否定的。朦胧诗人明确地用“我的眼睛”来否定“光谱分析仪”“镁光镜头”;用“自我”来否定“铺路的石子”“齿轮”和“螺丝钉”,认为其只是“机械”,不是“人”。
“我先读了些浪漫派的诗,感触不深,我觉得他们有些姿态是作出来的。”[14]474顾城的看法透露了朦胧诗人与浪漫主义疏离的秘密。应该说,浪漫主义是朦胧诗人最为熟悉的诗歌体式,由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编织成的颂歌与战歌,是展开在朦胧诗人成长过程中的诗歌现实。“在 ‘四人帮’时期,人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好像文艺只是印得漂亮点的政策说明书,是近乎于起扫盲作用的 ‘多种形式’。诗呢?也变成了给这社会妆点韵脚的竞赛活动。”[18]482如此的诗歌现实,自然为朦胧诗人所反对。由假大空的陈词滥调和一味高亢的激情所“填充”的浪漫主义,已经引起朦胧诗人的厌恶:“自从上高中以后,每月都有一次诗歌朗诵课,在课上,同学们找来各种诗歌朗诵,可惜没有读过一首能叫做 ‘诗’的东西。只有一些夸张的、虚假的词句在蒙蔽着我们的眼睛,僵化着我们的思想,钝化着我们的感觉。”[13]102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朦胧诗人的审美取向偏向现代主义的诗歌作品,偏向抒发真情的诗歌作品,时代充当了重要推手。朦胧诗人艺术观念的形成和价值取向,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因素。
四
郭路生是在朦胧诗人的成长路上有过重要影响的诗人,其名作《相信未来》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某种意义上,郭路生的诗歌打破了一贯假大空的单调和沉闷,重新唤起了人们一直被压抑着的真实:内心的脆弱、孤独和苦闷,离别的忧思、伤感和怀念,时光逝去的哀愁、落寞和绝望,都是不可避讳的正常的感情。毕竟,阶级、民族、革命不能代表人们全部的日常生活,相反,上述情感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绝对的比重,人们无法做到避而不谈;长久的知青生活已给人们带来了理想的失落和价值的迷惘,生命充满了迷失后的无聊和苦闷,“往常激烈的信仰,日渐流失,人们平静下来后,更加感到往日的荒唐。”[5]6此时郭路生出现了,正显得恰逢其时,其充满真诚和真情的写作疏解了人们心头长久积郁的苦闷。1970年春天,北岛听到有人朗诵郭路生的诗,并得知其是知青,震动不小:“原来是我们中的一个,真不可思议。我的七十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7]32虚假的年代,人们渴望真诚,朦胧诗人其实反对的并不是浪漫主义,只是反对其中的作势和虚假;受教于何其芳门下的郭路生,其诗歌体式基本为格律体,形式整饬,琅琅上口,“使我们感到如此荡气回肠的,不是他诗歌的形式,而是他诗歌的内容。就其内容而言,他主要表现的是青春、幻灭、抗争和固执的希望。这正是当时知青们共同的思想情感。郭路生是他们的代言人。”[13]102郭路生诗歌的出现,也表证了其时政治环境的稍显宽松。此外,前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的政治抒情诗对北岛深有影响。《回答》《一切》《宣告》中对非人道的政治的抗议,对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呐喊曾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
当然,朦胧诗人的写作更多受惠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现代主义对非个性、客观对应物的强调,使朦胧诗人注意与书写对象保持一段审视的距离。因为与所观对象有一定距离,作者与对象之间便少了功利的关联,作者也就能够比较客观地观照世界,丰富的审美性就此产生。朱光潜曾说:“我们何以有情感而不能表现于艺术作品呢?这就由于不能在自己和自己的情感中留出 ‘距离’来,不能站在客观的地位去观照自己的生活。凡艺术家都须从切身的利害跳出来,把它当作一幅画或是一幕戏来优游赏玩。”“艺术家和诗人的长处就在能够把事物摆在某种 ‘距离’以外去看。”[19]15-20这种站在普遍的艺术立场上的立论,确实也是朦胧诗人的高明之处;当然这也是人们往往用来批评现实主义的理由:不冷静,作势般的热烈和过分的直白。这些因素注定了朦胧诗人立身于时代的制高点,但也注定了他们将会受到意识形态及其规训之下的习惯势力的抵制,并且埋下了习惯势力将籍意识形态之手施行压制的种子。这将使我们看到现代主义在中国行走步履的踉跄和艰难。
基于广大的政治压迫而滋生的反抗意识,同时也“馈赠”了朦胧诗人作品中浓烈的政治色彩。在朦胧诗人笔下,即便是爱情书写,也脱离通常意义的缠绵悱恻,而与生离死别有了直接相关,一种悲壮色调隐含其间:“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北岛《雨夜》)。生离死别不是朦胧诗人一种写作上的虚构,是一种生存实境,“在我早期的作品中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当时的具体的个人经验也很有关系,当时就是整天面临着生离死别,就是这样,所以它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压力。”[11]233——北岛的自述透露了朦胧诗人写作心境的晦暗,在此我们也能隐约体会到,他们为何选择现代主义的理由。
以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标举精英意识著称的现代主义,对朦胧诗人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策略和技巧的选择,而是生存镜像的潜在要求。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主题是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传统的声音批评朦胧诗人唯西方现代派是从,这的确是一种冤枉;在一定意义上,朦胧诗人选择现代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的表达,是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孕育开花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对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一种反拨,与政治意识无关。而在中国,政治文化构成了现代主义的生成背景,朦胧诗的反抗也就主要体现于对政治压迫和意识形态的反抗。
总体而言,在朦胧诗人的成长时期,地下文学沙龙、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前苏联政治抒情文学、郭路生的诗歌,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抱团取暖和相互激励,构成他们成长营养的来源。来源的“多样”塑造了他们“多样”的写作风格。朦胧诗人以他们深邃而多样的写作,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构成,给后来的文学以深远的影响,并在持续的影响中奠定了他们不可动摇的地位。
[1][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2]李润霞.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重评“朦胧诗论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3).
[3]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4]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2.
[5]王学泰.监狱琐记[M].北京:三联书店,2013.
[6]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6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7]北岛.断章[M]//七十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9.
[8]唐晓渡.芒克访谈录[M]//刘禾.持灯的使者.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9]张郞郞.“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M]//宁静的地平线.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多多.1970—1978北京的地下诗坛[M]//刘禾.持灯的使者.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1]刘洪彬.北岛访谈录[M]//刘禾.持灯的使者.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2]舒婷.生活、书籍与诗[M]//刘禾.持灯的使者.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3]宋海泉.白洋淀琐忆[M]//刘禾.持灯的使者.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4]王伟明.顾城访谈录[M]//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15]郑敏.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M]//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6]郑敏.遮蔽与差异——答王伟明先生十二问[M]//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7]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J].诗刊,1980(10).
[18]顾城.“朦胧诗”问答[M]//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19]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5-20.
[责任编辑:志 洪]
I206.7
A
1674-3652(2017)02-0083-07
2017-02-10
李胜勇,男,贵州铜仁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