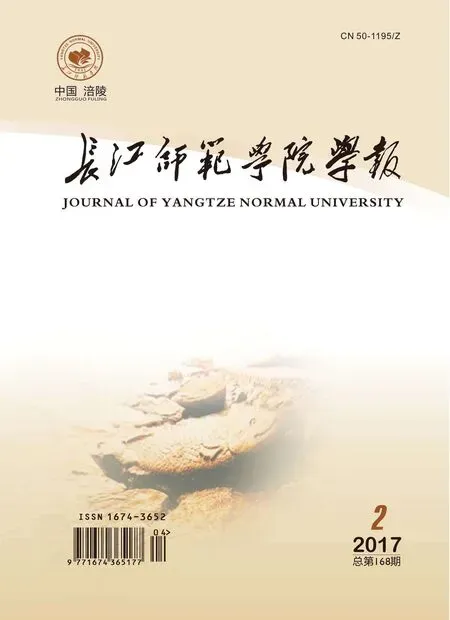宋末川江涪陵蔺市浮桥争夺战研究
2017-03-29罗美洁黄权生
罗美洁,黄权生
(1.三峡大学 机械与动力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2.三峡大学 水文化研究所,湖北 宜昌 443002)
宋末川江涪陵蔺市浮桥争夺战研究
罗美洁1,黄权生2
(1.三峡大学 机械与动力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2.三峡大学 水文化研究所,湖北 宜昌 443002)
从交通而言,川江联通巴蜀和荆楚;从军事而言,川江就是长江的咽喉。涪陵作为川江中的节点之一,是南入武陵的入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南宋时期,发生在涪陵的蔺市锁江浮桥战,是影响了整个蒙宋对峙战局的一场历时半年的重要战役。该战宋军获胜,进而占领重庆,夹击合川,造成蒙古主帅和蒙哥意外死亡,从而造成在欧亚大陆四处出击的蒙古军队收缩,回到蒙古大漠,争夺汗位,进而影响世界局势。撬动这个世界格局支点的是钓鱼城,但让支点失去平衡的则是蔺市浮桥战,故该战役是影响整个巴蜀甚至全国战局的战役。故涪陵蔺市锁江浮桥战是整个蒙宋对峙时期重要的一战,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军事价值。
川江;蔺市;浮桥;桥战
一、跨江古桥关系国家社稷安危
在古代跨越长江的大桥有两种,即浮桥和索桥,其用途基本上为军事之用。这些古桥都设在长江险要之地,如宜昌荆门山和虎牙、宜昌西陵峡口、瞿塘峡夔门、涪陵蔺市等处。茅以升指出:“(各种桥),在我国数千年历史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军事上,两军对敌,有因一桥得失而见胜负,甚至可以影响到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在任一朝代统治下,交通运输的通畅与否,都与政权的命脉有关,而桥梁正是交通运输所依赖的重要工具。”[1]32“桥是交通要道的咽喉,形成一个 ‘关’……桥在历史上的作用真不小,往往一桥得失,影响到整个战争局势。”[2]274历史上,在长江建造了多座跨江大桥,而这些大桥的军事战争实践也检验了茅以升的论断。古代长江跨江古桥确实关系着国家社稷安危,这不是没有科学道理的。
有人研究指出:长江上建有大量的军事桥梁,其中历史可考的最早的军事浮桥是东汉初公孙述所建的荆门虎牙军事浮桥,该桥为中华“长江第一桥”。三国末期,东吴在西陵峡口建有军事索桥,为目前可考的长江最早的军事索桥。南北朝和隋初在三峡东面西陵峡口也多次建有锁江索桥。从军事战术上看,长江军事桥梁需要攻防矛盾相平衡,水陆军事结合运用,水攻(舟战)火攻相机妙用结合,彼此不可偏废[3]。杨光华指出:“长江三峡,素来为江上交通咽喉,兵家必争之地。有不少王朝或割据政权恃险自安,在此修建关城,搭设浮梁、素桥,悬缀铁索,作为御敌工事。如今,那些设施只在历史的记忆中依稀可见,不时唤起人们的追思。”[4]在南宋时期,巴蜀是宋蒙(元)战争的主战场,对长江孔道川江的争夺尤其激烈。在川江上的涪陵蔺市就曾架设一座军事浮桥,该桥成为蒙宋双方争夺的焦点,由于宋军获胜,进而影响到重庆争夺战,直接支援了合川钓鱼城的保卫战。由于蒙古统帅蒙哥大汗在钓鱼城久攻不下,宋军在涪陵蔺市突破蒙军锁江桥后,占领重庆,对钓鱼城形成了反包围。蒙军该战的战败使蒙哥焦虑,力求速战而意外受伤死亡,统帅一死,蒙古内部争夺汗位,最终内乱,导致了整个蒙军战线的撤退和溃败。可见,赢取钓鱼城保卫战胜利的关键点就在于涪陵蔺市浮桥争夺战的得失。
二、南宋涪陵的军事地位和宋蒙长江军事态势
涪陵虽然没有夔门那样险峻,但它是乌江和长江交汇之地,获得涪陵,便可沿着乌江进入武陵地区,如进入酉水和沅水,这样就可以形成对宋的战略包围之势,打破蒙宋以长江为军事天险的拉锯态势。《华阳国志·巴志》曰:“涪陵,巴之南鄙也。从枳县入溯涪水,秦司马错由之取楚黔中地。”[5]卷1,41《读史方舆纪要·四川四》记载涪陵:“州南通武陵,西接牂柯,地势险远,人兼獽蜑。”故涪陵为南通武陵的孔道,自古在此置兵防守武陵蛮夷北入大江。“今自州以南,山川回环,几及千里。唐、宋时,尝以黔州(即今重庆彭水)控扼形要,往往置镇设兵,以兼总羁縻州郡(唐以黔州为都督府,督思、辰、施、播等州,兼领羁縻数十州。宋亦置军镇,领羁縻州至五十六个)。明初以黔并入于涪,州之险实倍于前代。《四夷考》云:‘武隆一县,为州之要地。牂柯、黔、楚,指臂东西,北枕巴江,南通贵竹,三面皆界于土司。所谓酉阳之咽喉,石砫(柱)之项背,而真州则尤胸腹之患也。南蛮有事,全蜀之患,武隆实先当之 (《志》 云: ‘武隆难先全蜀,险扼诸蛮’)。然则州之形胜,益可知矣。’”[6]卷69四川四,3294
由上可知,涪陵为乌江、长江交汇之地,其作为出入武陵之孔道是非常明显的。其实,长江北岸各府州县均为出入武陵的各种交通节点,更是长江沿线水陆安全的节点,是防止武陵“蛮夷”北入巴蜀的军事防线的链条。以忠州为例,《读史方舆纪要·四川四》指出忠州“东通巴峡,西达涪、渝,山险水深,介乎往来之冲,居然形要。万历(1573-1620年)中,奢崇明陷重庆,石砫(柱)女官秦良玉趣援,留兵守忠州,以为犄角之势。兼令夔州设兵防瞿唐 (塘),为上下声援云。”[7]卷69四川四,3290
对蒙宋双方而言,控制涪陵,除争夺长江外,还具有争夺进入武陵腹地入口的作用。蒙军如果完全控制涪陵,向西可控制巴蜀,向东可控制荆楚,向南可入武陵,利用酉水和沅江对宋军形成包围之势。故涪陵是重庆唇齿之战略要地,是巴蜀南部和整个南宋西南的腹地,涪陵如果丢失,蒙古可能会重演秦灭楚国的军事历史。
宋蒙之交,蒙古与南宋使用浮桥的战例更加频繁。蒙古善于陆战,南方善于水战。南宋得以在数十年战争中不速亡,与南宋利用长江天堑有很大的关系。如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蒙军董文炳指出:“长江天险,宋所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其气不可。”[8]卷175宋纪理宗开庆元年,4787《读史方舆纪要·湖广二》转载董文炳之语曰:“长江天险,宋所恃以为固,宜夺其气。”[9]卷69四川四,3559在长江及其支流建设浮桥,让天堑之险失去军事效应,这无疑是蒙军消弭南宋水军优势的重要手段。例如,理宗宝祐五年(1257年)蒙古董文蔚“城光化、枣阳,储糇(餱)粮,会攻襄阳、樊城,南据汉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领兵于湖水狭隘处, 伐木拔根, 立于水, 实以薪草为桥, 顷之即成。”[10]卷175宋纪175理宗宝佑五年,4766-4767这是蒙古军队在汉水流域以木为桩,以薪草为桥。这虽非完全意义的索桥或浮桥,但这也体现出此时蒙古军队因接纳大量的非蒙古军队,在南方的江河作战技术方面已经有很大的提高。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三月蒙古阿珠与刘整上言:“‘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诏许之。于是造战舰五千艘,日练水军七万人, 虽雨不能出, 亦画地为船而习之。”[11]卷175宋纪179度宗咸淳六年,4894这说明到蒙宋战争后期,蒙古已经有了强大的水军,仅汉水流域就有水军7万余人。南宋所擅长的水战优势逐渐丧失。
蒙古军队重要战将汪德臣文韬武略,一直得到蒙古大汗蒙哥的倚重,如理宗宝祐六年(1258年)十月,“蒙古主(蒙哥)进次宝峰。癸未,入利州,观其城池并浅恶,以汪德臣能守,赐卮酒奖谕之。遂渡嘉陵江, 至白水, 命德臣造浮梁以济, 进次剑门。”[12]卷175宋纪175理宗宝佑六年,4777-4778蒙古大汗对汪德臣赐酒嘉奖,这应是蒙古军队在巴蜀地区使用浮桥的战例。此时蒙古兵分3路,东路攻江南,欲取杭州;中路攻襄阳,力图荆楚;西路为蒙古统帅蒙哥亲率,围攻多年不下的合川钓鱼城。合川钓鱼城为嘉陵江、涪江、渠江3江汇合处,上可与3江各寨堡相呼应,下可与重庆互为犄角。故该城不仅是宋军的指挥中枢,也是整个长江上游防守主力所在地。为此蒙古出动主力部队,由蒙古大汗亲自统帅以进攻之。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蒙哥“自鸡爪滩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万余。(壬)坚力战以守,蒙古主会师围之。”[13]宋纪175理宗开庆元年,4783此时汪德臣为围攻钓鱼城的前锋主帅。蒙哥欲攻破该城,占领整个巴蜀,然后顺江而下以图荆楚,力图一举灭亡南宋。
重庆为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不仅上应合川,而且下应三峡(川江)各州县,与荆楚襄阳中路防线相策应。此长江—嘉陵江连同长江防御体系是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蒙古军队企图掐断重庆与三峡下游各州县联系,进而使长江上游巴蜀宋军与荆楚宋军失去联系。
三、涪陵蔺市浮桥争夺战及其影响
蒙古大军兵分3路进攻南宋,其中西路由统帅蒙哥率领,蒙军为何不直捣南宋的京都杭州,却舍近求远而远攻巴蜀呢?宋代军事理论著作《虎钤经》言:“欲夺敌之力者,先夺其水。得之上流者,美莫大焉。”[14]卷5料水第四十一,90这种舍近求远的战法是由历史上的军事实践给予证明的。如战国末,秦国司马错和中尉田真黄对秦惠王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15]卷3蜀志,191历史事实确实是“得蜀则得楚,得楚得天下”,故明末清初的军事理论家顾祖禹总结说:“三峡为楚蜀之险,西陵又为三峡之冲要,隔碍东西,号为天险,可不知所备欤?”[16]卷69湖广一西陵、三峡附,3515巴蜀据长江之上流,对下游具有极大的军事震慑之优势,历代统一中国多从巴蜀顺江而下,或逆流而上统一中国。故对荆楚而言“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汎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17]卷58陆抗传,1860川江是长江的咽喉孔道,是宋军巴蜀和荆楚的“生命线”,建桥切断宋军长江通道就成为蒙古军队的重要手段之一。
由于大量汉人加入蒙古军队,最为重要的是蒙古军队虽然多有屠城之举,但蒙古对工匠一般都保留下来。此时蒙古军队已拥有大量的桥梁工匠人才。如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蒙古主(蒙哥)遂命大将珲塔哈以兵二万守六盘,奇尔台布哈守青居山,命耨埒(纽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蔺市,以杜援兵。”[18]卷175宋纪175理宗开庆元年,4783浮桥锁住长江, 让下游援军不得入川, 久被围攻的合川钓鱼城必然独力难支。合川一旦被攻下,蒙古军队自三峡而下,与汉江流域的蒙古兵会师荆楚,南宋天堑之地利尽失,整个蒙宋战局必然会朝着蒙军预设的方向发展。宋太常寺博士王应麟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指出:“淮戍方警,蜀道孔艰, 海表上流, 皆有籓篱唇齿之忧。”[19]卷175宋纪175理宗宝佑六年,4780此时蒲择之所帅重兵攻打成都惨败,川西、川北大部分地区不是战败就是投降,加之蔺市浮梁断江,宋军生命线被掐断,钓鱼城所在军队孤悬川中,孤掌难鸣,形势十分危急。面对生死存亡之际,南宋朝廷还是给予了积极的应对。
开庆元年(1259年),南宋政府撤掉在蜀无功的蒲择之,以吕文德代之,任命其为四川制置副使、重庆知府。同年,吕文德还兼任湖北安抚使,这样他就有了地跨巴蜀、荆楚的统辖力和调配权限,其职责自然是保障荆楚湖北与巴蜀川江宋军的生命线。假如能够攻破浮桥,入重庆,溯嘉陵江,达合川钓鱼城,势必造成对钓鱼城蒙古军的夹击。但要取得如此效果的前提就是突破蒙古军设在重庆附近的涪陵蔺市浮桥。如开庆元年(1259年)三月“命有司悬重赏,募将士毁蔺市浮梁。”[20]卷之五十九事纪六,227但未能成功。
吕文德所率援军西进,可蒙古军队据长江上流,很显然从下游进攻的援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而浮桥架设为开庆元年(1259年)一月,此时长江还是以西北风为主,风向对上行船只不利。在浮桥阻隔宋军半年后,进攻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首先,进入春夏,巴蜀多雨,仅仅在被围的钓鱼城就下雷雨20余日。蒙古军中大疫,军士思北还,士气低落,“宋将吕文焕 (德) 攻涪浮桥,时新立成都,士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纽璘忧之。”[21]卷129纽璘传,3145纽璘忧之, 蒙哥更忧之。
其次,此时宋军钓鱼城主帅王坚受到朝廷嘉奖,越战越勇,多次击败蒙古军的围攻。
第三,吕文德被任命为湖北安抚使,可调集荆楚宋军以赴四川救援。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此时六月,东风盛,军处长江下游的吕文德援军可乘风逆流破袭蒙军浮桥。万事俱备,东风也备。
开庆元年(1259年)“六月,吕文德乘风顺,攻涪州浮梁,力战,得入重庆,即率艨艟千余溯嘉陵江而上。”[22]卷175宋纪理宗开庆元年,4784吕文德借东风, 攻占浮桥,打通川江生命线, 且战舰千艘, 溯嘉陵江而上,对蒙军形成了战略夹击之势。川江是宋军长江中下游联系的纽带,也是长江各支流(嘉陵江、沱江、汉江等)间兵员粮草运输和互相策应的通道,川江间的蔺市浮桥的架设无形中扼住了宋军的长江交通命脉。故《宋史·向士璧传》 指出蒙军“夹江为营,长数十里,阻舟师不能进至浮桥。”[23]卷416向士璧传,12477浮桥不破,宋室不安。经过半年争夺,吕文德领兵激战,双方争夺惨烈,但到夏季,吕文德借东风,攻破浮桥,整个战局因浮桥被破,战局形势顿时逆转,吕文德入重庆“诏谕四川军民共奋忍勇效死。”[24]卷之五十九事纪六,227战争走势向有利于宋军的方向发展。
吕文德逐元军,毁浮桥,入重庆,知重庆府,达到战前用重庆策应合川之战略目的。但其溯嘉陵江而上,包抄钓鱼城,并没有迅速击溃蒙古军队。史载:“蒙古史天泽分军为两翼,顺流纵击,文德败绩,天泽追至重庆而还。”[25]卷175宋纪理宗开庆元年,4784吕文德虽然夹击合川失败,但其向北威胁蒙军态势的警报却并未解除。不仅迅速减轻了巴蜀主战场钓鱼城的战争形势,而且由于连日阴雨、蒙古军中大疫,更加加剧了蒙军的士气低落,严重打击了整个蒙古军队前锋主帅和蒙古大汗的信心。让蒙古骁将汪德臣和蒙古大汗更加着急,甚至失去了理智。
涪陵蔺市浮桥战的影响是深远的,宋军获胜,川江连成一片,宋军向北夹击钓鱼城虽然失败,但却坚定了王坚死守钓鱼城的信心。“王坚固守力战,蒙古主屡督诸军攻之,不克。”[26]卷175宋纪理宗开庆元年,4785前锋主将汪德臣,气急败坏,希望速战速决,选兵夜登钓鱼城外城,王坚率兵逆战。该战斗从晚上一直打到天亮,蒙军死伤惨重,毫无战果。
苦战一夜,汪德臣气急败坏,犯下了军中大忌,只身单骑来到宋军城下,企图劝降王坚,大呼曰:“‘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 语未既,几为飞石所中,因得疾卒。”[27]卷175宋纪理宗开庆元年,4785此时,因涪陵蔺市浮桥战获得胜利,宋军扭转了局势,掌握了军事主动权,士气高涨。在交战状态下,前锋主帅汪德臣处于宋军炮矢射程下,只身犯险,宋军抓住战机,飞石伺候,蒙军骁将陨落,让蒙军雪上加霜。
蒙古大汗面对颓势,不是整休再战,而是急于为前锋主帅报仇,全力攻城。“会天大雨,攻城梯折,后军不克进而止。”[28]卷175宋纪理宗开庆元年,4785面对失败,蒙哥生病, 时值酷夏, 蒙古军队地处大漠, 十分害怕南方酷夏,而军中大疫,又丧主将。钓鱼城蒙古大汗蒙哥受伤,也有说是生气致病。史载:“秋,七月癸亥,蒙古主殂于钓鱼山,寿五十二。后追谥桓肃皇帝,庙号宪宗。史天泽与群臣奉丧北还,于是合州围解。”[29]卷175宋纪理宗开庆元年,4785忽必烈闻蒙哥薨,并没有马上北返,而是希望通过在荆楚获得战功以便在争夺帝位中获得先机。吕文德为整个重庆、川东、湖北战区负责人,当巴蜀危机一缓解,马上挥师东下。《元史·本纪第四》记载:“顺天万户张柔兵至。大将拔突儿等以舟师趋岳州,遇宋将吕文德自重庆来,拔都儿等迎战,文德乘夜入鄂城,守愈坚。”[30]本纪第四世祖一,62与忽必烈相持数月,元军无功,加上其他各路汗王北返,而宋贾似道亦遣宋京请和,忽必烈顺水推舟,就此北返,荆楚之危顿解。
此战功劳最大的不是钓鱼城王坚,而是吕文德,于是朝廷“奖吕文德断桥通道之功,命兼领马军行司。”[31]本纪第四十四理宗四,866该战役决战在钓鱼城,让钓鱼城保卫战成为载入史册的战役,其战役结果不光影响到巴蜀战局,还影响到全国战局,甚至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变化。蒙古军队北返,向南征宋之荆楚中路军和征江南的东路军也北返,征欧洲、征北非、征南亚的3路大军的各个汗王也返回大漠。因蒙哥突然死去,蒙古内部出现了权力真空,各种力量在大漠角逐,南宋和欧亚各国得以喘息。这里仅仅以忽必烈所帅中路军返回漠北,看其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
《元史》记载:“元宪宗末年(1259年)世祖南伐,自黄州阳(杨)罗洑,横桥梁,贯铁锁,至鄂州之白鹿矶,大兵毕渡,进薄城下,围之数月,(闻蒙哥殂) 既而解去,归即大位。”[32]志第十五地理六,1523-1524此处所载是忽必烈在荆楚长江上也建造浮桥,截断了长江中流的交通,与巴蜀蔺市浮桥相呼应。准备攻取整个荆楚,蒙哥薨,忽必烈撤军,在大漠争夺汗位,最后夺取了权力,这种结果是因巴蜀战况的影响促成的。显而易见,如果蒙古主帅蒙哥不英年早逝,整个南宋早就灭亡了,世界格局也许真的会被改写。撬动这个支点的是钓鱼城,但让支点失去平衡的则是蔺市浮桥战。
我们认为成就合川钓鱼城之战的是川江上的蔺市浮桥援助战,这是启动蒙宋时期整个世界格局的“多米罗骨牌”的第一块牌,而钓鱼城只是第二块牌。
明末清初军事理论家顾祖禹指出:“宋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主蒙哥攻合州,命其将纽璘造浮桥于涪州之蔺市,以杜援兵。吕文德攻浮梁,力战得入重庆。”[33]卷69四川四,3297在这里,正是在蒙古军的“围点打援”战法中,打援失败,造成合川钓鱼城“围点”失败,从而影响到了整个战局。
由此可见,每次长江浮(索)桥之战,从军事角度而言,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它虽然只是一个战略点,但其卡住或掐住的是中国“黄金水道”长江的生命线,其每一个关卡点都是长江之“七寸”。守关之险,在于人心。《孟子·公孙丑下》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至理名言,在宋元此次巴蜀军事斗争中又一次得到了验证。故顾祖禹总结道:“设险以得人为本,保险以智计为先。人胜险为上,险胜人为下。人与险均,才得中策。”[34]卷69南直一,918险固需要人守方固。
汪德城曾对钓鱼城喊话曰:“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蒙军说此话的前提是宋军不投降,城破蒙军屠城,而宋军必殊死抵抗。汪德臣和蒙哥均命陨巴蜀,在天,在地,更在人也。此时元军没有拾取南方之人心,其败也是偶然中的必然。克罗齐指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35]2以史为鉴,得民心得天下也。
四、小结
南宋涪陵蔺市浮桥战的影响是深远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事实上正是宋军涪陵蔺市浮桥战获胜,才得以进取重庆,夹击合川,才让钓鱼城保卫战获得最后的胜利。蒙军因为涪陵蔺市浮桥战战败,蒙古将帅面对不利的军事态势,失去了理智,主帅和蒙古大汗先后死亡,造成了蒙古军队的整体撤退,否则整个南宋早就灭亡了,世界格局也就被改写了。撬动这个世界格局的支点是钓鱼城,但让支点失去平衡的则是蔺市浮桥战。
[1]茅以升.中国古代桥梁[M]//茅以升选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2]茅以升.茅以升文集[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
[3]黄权生,罗美洁.东汉至隋朝三峡军事浮(索)桥及其攻防战[J].军事历史研究,2013(2).
[4]杨光华.长江三峡的浮梁、索桥[J].文史杂志,1993(6)
[5][晋]常璩,撰;任乃强,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7][9][16][33][34]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8][10][11][12][13][18][19][22][25][26][27][28][29][清]毕沅,撰;“标点《续资治通鉴》小组”校点.续资治通鉴[M].中华书局,2012.
[14][宋]许洞.虎钤经[M]//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15][晋]常璩,撰;刘琳,注.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17][晋]陈寿,撰;赵幼文,校笺;赵振铎,等,整理.三国志校笺[M].成都:巴蜀书社,2001.
[20][24]蓝勇.万历重庆府志(残卷)[M]//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上).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21][30][32][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3][31][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5][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英]道格拉斯·安斯利英,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责任编辑:丹 兴]
K207.7
A
1674-3652(2017)02-0070-05
2017-01-2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川江与荆江流域水利史研究”(12YJC770041)。
罗美洁,女,江苏泗洪人。主要从事三峡水利史、水利旅游研究;黄权生,男,重庆巫山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水文化和移民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