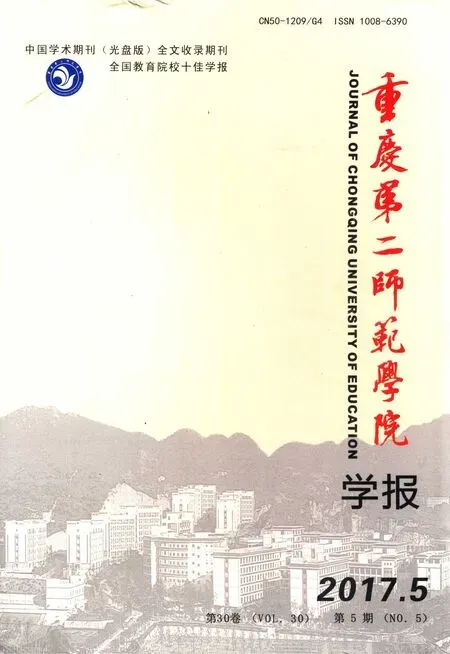《周易》“利用安身”与李白“功成身退”
——易解李白刍议之五
2017-03-29康怀远
康怀远
(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 万州 404100)
《周易》“利用安身”与李白“功成身退”
——易解李白刍议之五
康怀远
(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 万州 404100)
“利用安身以崇德”既是《周易》的重要哲学思想,也是其回归现实世界、关注现实生活的重要命题。“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这种对人的身体的极力推崇确乎成为西方实用主义者的先声。在李白的诗文中,身体的分量同样不可等闲视之,并与功成相联系,在人生存亡、安危、福祸、得失、取舍、屈伸和进退的选择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风格。如果进行深层的文化追踪,就会发现李白的功成身退似与《周易》的“利用安身”不无关联。
周易;利用安身;李白;功成身退
一、李白“功成身退”与《周易》“利用安身”的文化关联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既是《周易》重要的哲学思想,也是其回归现实世界、关注现实生活的重要命题。《周易》宣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对人的身体的极力推崇确乎成为西方实用主义者所谓“人类灵魂的最佳图画”[1]35、“浩瀚宇宙里所有结构中最美妙的”[2]252先声。身体在《周易》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如“君子安其身而后动”、“身安而家国可保”、 “君子以反身修德”、“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不远之复,以修身也”、“艮其背,不获其身”、 “藏器于身”、“言出乎身”等。无独有偶,在李白的诗文中,身体的分量同样不可等闲视之,并与功成相联系,在人生存亡、安危、福祸、得失、取舍、屈伸和进退的选择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风格,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以立功为不朽,如仰慕鲁仲连、侯嬴、郦食其、张良、韩信等建功成名的人;二是时时抒发求功成而不得的惆怅和慨叹,如“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三是设想功成后隐身而去归山藏名,如“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四是汲取历史教训,一旦功成便应抽身隐退,如“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等。这种具有渴望功成且功成后即远离官场隐身而退的人古已有之,不乏其例。但是,李白的功成身退却非同寻常,颇具特点。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明确提出:“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这是李白功成身退的自我宣言。很显然,李白的自我宣言,气势豪迈,义胆薄天,把屈原式高远的美政理想和庄子式自由旷达的生活理想融为一体,集中宣示了自己功成身退的人生追求。诚如龚自珍所云:“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
但是,如果再进行深层的文化追踪,就会发现李白的功成身退似与《周易》“利用安身”的哲学思想不无关联。 “利用安身”见《周易·系辞下》。《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这是讲人的思想要宁静,不要胡思乱想。天地的规律是日月交替产生光明,寒暑往来形成年岁;生活的规律是能屈能伸可以获利,像软体虫子为伸展而曲体,像龙蛇为保身而冬眠;以此类推,研究精义就是为了实际运用,君子安养身心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美德。往事如烟,未必都明明白白,但如果穷究其理,通晓变化之道,那就是盛大的美德了。
二、“利用安身”包蕴的人生大智慧
考查“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一句,原是《易传》引用孔子的话来阐述《易经·咸卦》九四爻辞“憧憧往来,明从尔思”之义的。对此,晋韩康伯注曰:“利用之道,由安其身而后动也,精义由于入神以致其用,利用由于安身以崇其德,理必由乎其宗,事各本乎其根,归根则宁天下之理也。” 唐李鼎祚释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将有为也,问之以言;其受命也,应之如响。无有远迩幽深,遂知来物;故能穷理尽性,利用安身。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自然虚室生白,吉祥至止。坐忘遗照,精义入神,口僻焉不能言,心困焉不能知。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斯之谓矣。”宋朱熹解曰:“引咸九四爻而释之。言理本无二,而殊途百虑莫非自然,何以思虑为哉。必思而从,则所从者亦狭矣。言往来、屈信皆感应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则入于私矣,所以必思而后有从也。因言屈伸、往来之理,而又推以言学亦有自然之机也。精研其义,至于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适不安,伸之极也,然乃所以为入而崇德之资。内外交相养,互相发也。利其施用,无适不安,伸之极也,然乃所以为入而崇德之资。”
《周易》的核心功能是“利用安身”四个字,它讲利,讲趋吉避凶,但绝不主张为求安身而逢迎丧德,充当小聪明的角色。尽管先贤的说法持见各异,但就“安身”与“崇德”的关系理解上倒有共同之处,那就是:第一,“利用安身”的前提是“精义入神”;第二,“精义入神”方可有所作为;第三,“崇德”的物质利益是“安身”的生存或生活基础。这就告诉我们,在义与利、身与德的选择中,中国文化在肯定人对物质利益正当追求的同时,强调人在满足物质利益过程中把“义”与“德”的实现作为最高理想或最终目标,即“安身”是为了进一步修德进业。故而南怀瑾《孟子旁通》一方面说:“无论东方或西方,任何一种文化、一种学术思想,都是以求利为原则。如果不是为了求利,不能获利的,这种文化、这种思想,就不会有价值。从哲学的观点看,一切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离苦得乐’……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易经》上的‘利用安身’,也就是现代观念想办法在我们活着时,活得更好。”另一方面又说:“《易经》也是讲利,而且告诉我们趋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于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诉人们以积善的因可以得余庆的果,积不善的因便得余殃之果。所以积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为。”
这是一种东方智慧,一种中国式的人生大智慧。有学者认为,“利用安身”诚乃《周易》所揭示的“精义入神”于“内时空”操作所产生的生命安顿作用。“利用安身”为生命的外时空形而下的生命安顿,主要依赖于生命之外的某种存在以为支撑,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有待”。“有待”则不得逍遥,不是生命之自在,不是最高的德行。而《周易》给出的“利用安身”则不依赖于外物,而是依赖于生命内在的,依赖于内时空的“精义入神”来实现,是完全的自得与自在,无待于外在,从而摆脱了外在束缚而得生命之大逍遥,大自在。这是属于生命的形而上安顿,是与道相合的生命安顿,是为得道。具体来说,就是将“精义入神”用之于内时空,因神守于内,神凝则气聚,并逼使精化为气,即道家所谓“炼精化气”;而气更养神,是为“炼气化神”,从而精、气、神交融统一于“内时空”之中,即为达于“内时空之形而上”。由此“精义入神”,而于内时空实现“利用安身”,即为生命与道合一,达于生生之自在,故能使生命安顿,此方为真正之德行,最高之德行。故为“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可见“精义入神”作为一种高境界的哲学精神,其要义就是天理、地理、人理、物理诸理融合而成宇宙之理、万物之理、人生之理。《周易》以朴素的直观的同时又是辩证的思维传达出实用获利和静心养身的人生哲理。老子借以发挥为“功成身退”或“功遂身退”:“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娇,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从《周易》“利用安身”到《老子》“功成身退”,人生的哲理就完全生活化、实际化了,人身的小宇宙与天地日月、万千世界的大宇宙默契连通,使得中国式的根身文化在有修养的文化人身上一脉相传,李白则为其中的佼佼者。其“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灭虏不言功,飘然陟蓬壶”、“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傍”、“功成拂衣去,归于武陵源”、“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等诗句,不是诗人无由实现功成的牢骚与无奈,也不是仕途不遇的调皮与戏谑,而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清醒与优选。
值得注意的是,“精义入神”、“利用安身”和“致用”、“崇德”的人生哲理沟通的是中国士人“安身立命”的人生信条。
首先,《周易》所谓“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给我们描绘的是天地运转、人世沧桑和往来互动、屈伸有致的生命图景。尺蠖、龙蛇的生存凭其本能,而万物之灵的人则通过精研义理而把握屈伸相感的宇宙规律和生命脉搏,进入内思义而外利用的人生实践,达到身心安顿而德行弘扬的理想之路。
其次,《周易》引孔子之言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孔颖达在韩康伯以归根由宗、以静制动的玄学思辨注解“安其身而后动”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说:“欲利己之用,先须安静其身,不须役其思虑,可以增崇其德。‘利用安身’,是静也;‘崇德’,是动也。此亦先静而后动,动亦由静而来也……‘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后动’者,言欲利益所用,先须自安其身。身既得安,然后举动,德乃尊崇。若不先安身,身有患害,何能利益所用以崇德也。‘精义由于入神,以致其用’者,言精粹微妙之义由入神寂然不动,乃能致其用。‘利用由于安身,以崇德’者,言欲利益所用,先须自安其身,乃可以尊崇其德也。”他认为归根即静,静是道的本来和自然状态,“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则是儒家对人生理想的预设。于是由利用静善而至于增崇德行正是立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张载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再次,虽然在《周易》中没有“立命”一词,其言“命”多与德行相关联,“崇德”以“立命”可视为要义。如大有卦《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竭恶扬善,顺天休命”;无妄卦《彖》曰:“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鼎卦《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巽卦《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说卦》曰:“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毫无疑问,“立命”既可以理解为对生命的肯定,也可以理解为将生命献出。故而《周易》困卦象辞说:“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兑(泽)上坎(水)下,意为泽水枯竭干涸,有困顿之象。但只要君子面对困顿、勇于奋斗,以至于不惜生命,下定立命之志而成就自己的理想,就会由困顿转为亨通。这种道德完满的奉献精神,诚如孔颖达所疏:“‘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之人,守道而死,虽遭困厄之世,期于致命丧身,必当遂其高志,不屈挠而移改也,故曰‘致命遂志’也。”可谓最高层次的立命,与孔子将“见危授命”的德行视作“成人”的基本要求和孟子将“修身”与“立命”并举一样,当为同一正理。
三、李白“利用安身”的人生选择
李白读易,把“利用安身”结合为“功成身退”的智慧选择,文化的、哲学的、政治的、生活的、人生的,高扬生命的悲悯情调。李白生活的时代,且不说他年轻时热烈拥抱的大唐社会天宝前后开始朝着下山的路走去,也不说他长安被谗赐金放还所负载的痛苦与悲愤,更不说他面对家国破败、朝纲紊乱、生灵涂炭、豺狼冠缨的黑暗现实的呼天抢地,单就同代辅国之臣惨遭迫害的残酷与血腥、不平与愤懑,都可能沟通了自己对人生追求的几分保留与理智及其对生命目的的预测与判断,因为 “不考虑手段就表示不严肃对待目的”[1]282。《周易》以“占事知来”、“遂知来物”的简易之理所提供的手段,使李白保持了自我保护的警觉:“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的清醒与优选,李白的保留与理智,首先来自强烈的与安身和立命紧密相连的忧患意识。他把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叫作幽愤。在《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中,李白说:“吁咄哉!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变,玉颜已缁,何尝不扪松伤心,抚鹤叹息?”李白要“挥斥”的“幽愤”,就是内心埋藏得很深很久的积愤和幽怨。“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终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壮士伏草间,沉忧乱纵横”、“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等等,李白的大愁、大忧、深悲、深愤,折射出他所面临的充斥着风险与劫难、竞争与恶斗的生命难题,昔日的明时、明朝、明君不复存在,当年笔下展现的“弦歌咏唐尧,脱落隐簪组。心和得天真,风俗犹太古。牛羊散阡陌,夜寝不闭户……举邑树桃李,垂阴亦流芳。河堤绕绿水,桑柘连青云。赵女不冶容,提笼昼成群。缲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讼息鸟下阶,高卧披道帙。蒲鞭挂檐枝,示耻无扑抶。琴清月当户,人寂风入室。长啸一无言,陶然上皇逸”这种桃花源式的和平与静穆也荡然无存。 “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1]1“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李白岂能坐以待毙?故而“《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周易》把这一生活世界中的生命难题总结为“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去凶悔吝者,生乎动者”。就是说,身体与行动、困难与凶险并存于个体生命之中。因此,忧患生命的不安全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终极思考。《周易》在提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惧以始终”警告时,又特别强调“险以动,动而免乎险”、“危者使平”、“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履虎尾,不咥人”,提醒世人面对困难与凶险不能畏葸不前、无能为力,而要敢于化险为夷,智于逢凶化吉。李白的功成身退,不也可以当之乎?
李白被谗离京后,又有幽州探险、三入长安、入幕永王、请缨参军等一系列行事,应当说都是继续为功成而努力,不过这种努力,统统是 “动乎险中”,是“生乎动者”,是“险以动”“履虎尾”的“致命遂志”,也可视为“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不得不寻求安全”的人生选择。只是李白的“寻求安全”,力图以动脱险,与白居易的进退观不可同日而语。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说:“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显而易见,白居易持守的是“时”,“时来”则“陈力以出”;“时不来”则“奉身而退”。在“进”与“退”中,享受心理的平衡与“自得”。李白不是这样,他没有白居易那样“运交华盖”、当朝任官,也没有白居易那样“闲适”、“自得”。他是不得其时而行、凌空飞翔的大鹏,一生“紫绶不挂身”,一生都在“履虎尾”,一生都在险中求功。就政治理想而言,李白未能如愿,够得上悲剧式的诗人;但就生活理想而言,他追求的功成身退却不乏诸多人生智慧和清醒。这不能不说与李白读《易》有关。
众说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或理想主义诗人,这是有其理由的。其实,除此而外,李白也是很现实的诗人,很讲实用的诗人。詹锳先生说:“因为从李白的创作经历看,他还是一个布衣诗人。诗仙李白终究不是‘仙人’,他也是人间的泛众,是民间苦难过滤了的普通之人。”实现生命的目的关键要看实效,一如杜威所言:“寻求认识上的确定性的最后理由是需要在行动结果中求得安全。”[1]36《周易》倡导“变动以利言”,在“乾”卦之初九讲“潜龙勿用”,原因就是“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一切以实效为标准,合目的的实效行动就有大用。“吉凶者,贞胜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君子以果行育德”等等,无一不是明言目的实效性的。李白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仰天大笑出门”入长安,“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事君”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以至于饱受坎坷、屡遭挫折而“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李白“长相思,在长安”,这是一种有耐心的执着,实用的目的浸透着其苦心经营。当然,李白苦心经营所付出的代价是其始料未及的,但其孜孜以求、自强不息的文化品格却给后世留下了很宝贵的精神遗产。
以上通过对李白“功成身退”的文化追踪,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人生抉择,饱含着《周易》“利用安身”“精义入神”的哲学智慧,并在“安身立命”的生存和生活实践中更多地体现为对高远理想追求的执着与忧患。可以说,几多清醒与优选,几多保留与理智,造就了诗人特立独行的人格形象。
[1]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M].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017-04-06
康怀远(1946 — ),男,陕西岐山人,教授,研究方向:唐代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
I206.2
A
1008-6390(2017)05-0064-04
[责任编辑于 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