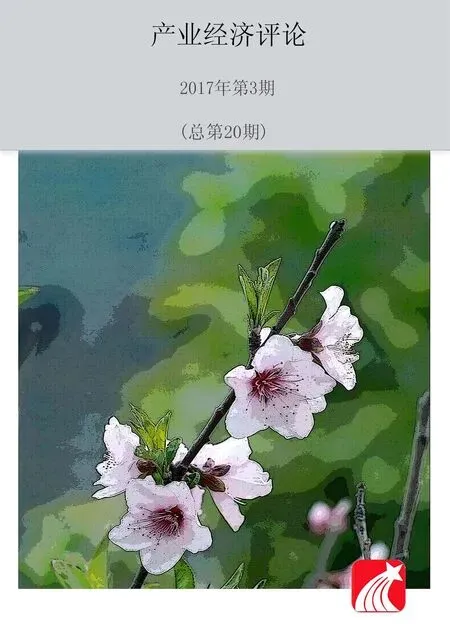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制度分析与安排
2017-03-28谢康刘意
谢康,刘意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制度分析与安排
谢康,刘意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中国既有研究中缺乏针对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制度安排的研究,理论上对于药品安全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制度安排有何区别存在研究盲点。本文从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免疫-治疗”三级协同制度安排构建框架出发,分别对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预防”体系的制度构建、“免疫”体系的制度构建及“治疗”体系的制度构建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研究表明,无论在“预防”体系还是“免疫”体系下,或者在“治疗”体系下,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制度安排的行动主体、行动情境、交互模式和潜在结果,都呈现出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不同的制度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构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制度安排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结论可为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从侧重事后“治疗”体系,向事后与事前“预防”和“免疫”体系平衡监管的方向转型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和策略依据。
药品安全治理;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制度分析;制度安排;协同管理
一、引言
食品药品安全治理是一项世界性难题(Opara,2003;柯文,2013;Chen et al.,2015)。药品安全指消费者服用药品后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涉及药品生产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使用安全。与食品安全事件不同,药品安全事件一旦发生便成为全国性事件,影响程度深范围广,对国民生命安全造成的威胁重。例如,2014年,浙江省台州天台公安破获一起生产、销售毒胶囊案件,查获可疑空心胶囊1.355亿粒,涉案金额135万余元。经侦查,早在1999年,嫌疑人郑某夫妇就在新昌县制售毒胶囊,黑色产业链持续17年,大量毒胶囊发往全国。2016年度中国再次爆发“山东毒疫苗”事件和“重庆毒疫苗”事件,使药品安全治理尤其是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再次成为国民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政府公共管理的难点问题。2016年3月,山东济南市公安局查封大量非法疫苗,涉及24省份17家企业,涉案金额超5.7亿元。2016年6月,重庆又出现了“毒疫苗”事件,地方医院疫苗被掉包,严重危害儿童生命健康,对现阶段中国药品安全治理能力形成挑战,进一步凸显出中国政府大力推动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肖静华等,2014)。
与食品安全治理相比,药品安全治理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从供应链视角分析,药品供应链指由药品制造商、药品批发商、药品零售商、医疗服务机构和药品使用者等一系列环节链接而成的网状链条结构。食品供应链则包括食品原料种植养殖、采购、生产、流通加工、配送、消费等环节。药品与食品供应链管理存在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首先,供应链上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食品药品的安全。药品安全三大环节与供应链的节点是一一对应的,药品安全问题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药品供应链安全问题。同理,食品供应链每一节点发生的问题也会随着供应链扩展到整个市场。其次,供应链纵向一体化程度不高,管理上各自为政,难以保障食品药品安全。食品药品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大多存在规模小、数量多等特征,使环节之间协调和管控不足,造成供应链流通效率低、成本高、安全隐患大等问题。最后,食品药品供应链的公共管理与相关监管缺位,制度执行漏洞较多。由于食品药品供应链涉及环节众多,易于发生安全问题且不易发现,加之监管体制存在漏洞,相关部门协同管理能力有待提升,导致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发。
一般地,药品与食品供应链管理的主要区别是:第一,与食品供应链相比,药品供应链的链条更长,结构更复杂。药品从出厂后要经过大量批发商、零售商、医院或药房等,才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中间容易出现假药、劣质药流进药品供应链中(沈凯和李从东,2008);第二,伴随着政府推行“廉价药”的压力,药品行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许多企业不得不通过各种办法压低成本,导致企业通过牺牲药品质量来维持生存(张舒怡和王远强,2012)。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拟从药品安全与食品安全治理的相似性与差异角度入手,根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免疫-治疗”三级协同管理的制度分析框架(谢康等,2015,2016,2017a,2017b),探讨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制度分析与安排。现代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配置药品监管机构的职能,以避免职能交叠和监管盲区。同时,在事前与事中两个维度强化药品监管(梁晨,2015),即对应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制度构建中的“预防”体系和“免疫”体系。这样,“预防”体系和“免疫”体系与“治疗”体系协同,可以帮助监管部门对内提升监管能力,对外加强企业自控与行业自律。该监管体制能够鼓励监管部门监管措施创新,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并通过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强制公开来形成社会共治的制度安排。
二、“预防”体系的制度分析与安排
世界药品安全问题经历了“假劣药”、“化学药”和“新特药”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药品安全监管制度经过数次变迁,1998年行政体制改革大幅提升了药监机构能力,药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以往药品安全监管多强调以“问题解决”为导向,这种监管体系优点在于将更多精力放在药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药品安全问题。但是,这种监管制度安排的不足之处在于,监管部门容易忽视药品事件发生前的潜在风险。近年来,中国药品安全监管体制从事后“治疗”体系向事前“预防”和“免疫”体系转型,即更强调药品安全风险的监管。
根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免疫-治疗”三级协同制度构建模式(谢康等,2016),下面将对药品安全社会共治中的“预防”体系进行制度分析,依次从制度安排的行动主体、行动情境、交互模式和潜在结果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预防”体系制度的行动主体
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体系制度安排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体系制度安排存在较大不同。食品行业进入门槛较低,食品加工生产制造技术含量低,因此需要政府监管部门和社会主体对广大中小企业进行宣传教育。通过提高企业主体的法律意识和科学意识,起到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预防作用。对于药品行业而言,所有进入药品行业的企业均属于“重资产”企业,拥有较高的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此外,药品生产制造属于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行业,对于药品企业的预防机制构建,需要依靠强大的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
现阶段,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体系制度安排依然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主体和社会主体为辅助行动主体。与食品监管部门相比,药品监管部门对于行业企业的监管话语权更重,主导权更强。药品监管部门不仅掌控药品行业的审批和准入,而且对于药品价格存在决定性作用。因此,相对于食品企业而言,药品企业规模更大,服从监管的可能性更大。
政府主导下的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体系的制度安排存在三种类型:一是推动药品行业快速整合形成良性自律的制度安排。药品行业强调企业准入门槛,当企业达到监管部门许可标准时,则后续日常监管的成本相应较低。例如,2016年中央政府在促进医疗行业健康发展的相关文件中提到,进一步推动小型药品企业整合,建立药品流通领域的新格局。2016年中央政府对药品生产监管进一步加强许可,强制要求生产企业主动申请并接受监管部门资质检查。二是推进政府监管能力建设的制度安排。与食品安全监管相比,药品安全监管更强调科学监管的重要性。例如,2016年中央政府关于仿制药的监管中,提到要提升一致性评价的公信力和有效性,共同推动一致性评价工作。2014年中央政府推动药品安全监管体系改革,将卫计委的部分职能划归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使药品安全监管保持基层活力和主动性。三是加强社会公众药品安全教育宣传的制度安排。教育宣传是药品安全监管的重要一环,只有当消费者清晰知道药品安全的相关知识才能真正起到“预防”作用。
政府主体在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体系中,主要通过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药品监管体制来发挥作用,形成对药品违法犯罪行为侥幸心理的震慑。政府通过规范药品市场和企业行为构建“预防”体系,但与食品安全治理不同的是,政府主体在药品安全“预防”体系中更多地承担宣传教育职能,这部分职能在食品安全“预防”体系中主要由社会主体承担,因为药品行业具有较高的专业性,政府在这方面具有绝对权威,因此需要承担更多职责。
与食品安全“预防”体系构建基本类似,企业主体在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体系中主要推行对内的药品安全管理能力建设。例如,太极药业大力推动药品生产和质量安全,通过透明化生产打造药品安全天然的预防防线。又如,扬子江药业执行“三不申报”,产品质量从源头抓起,力争做到中国制药行业质量管理典范企业。又如,九芝堂将“重质量、讲诚信”的经营理念灌输到企业每一个人的心理及行为中等。总之,社会主体构建的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体系,主要是关于社会公众教育宣传的制度安排。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打造《食品药品安全播报》电视专栏,宣传药品安全,通过监管部门和新闻媒体的结合,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对社会共治形成推力。
(二)“预防”体系制度的行动情境
行动情境指行动主体相互影响、交换物品与服务、解决问题、相互约束或斗争的社会空间,侧重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因素的描述(Ostrom,2011)。结合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体系制度的基本特征,我们采取Johns(2006)提出的分类方式,将行动情境划分为两类:一是“预防”体系普遍性情境。在普遍性情境下,“预防”制度安排构建目的是帮助政策制定者完善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制度,对社会监管体系具有长期影响。一是“预防”体系特殊性情境。在该情境下,制度安排构建目的是帮助政策制定者解决不同组织形成的突发性问题,主要针对组织层面的短期行为。
普遍性情境指针对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制度体系本身的情境,如当前药品生产制造门槛相对西方国家较低,需要进一步提升准入门槛。这类情境需要政策制定者采取影响制度体系本身的策略才可以有效解决。特殊性情境指针对药品安全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对象,通常情况下包括区域、组织或个体等,如医疗领域机构改革较为缓慢,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如西药一致性评价公信力与有效性不足,则需要进一步加强等。
由于药品行业是一个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附加值和相对垄断的行业,药品安全生产、流通、零售等不同环节均有非常详细的监管说明和规定。例如,药品企业生产一款药品,从实验室研究到新药上市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要经过合成提取、生物筛选、药理、毒理等临床前试验、制剂处方及稳定性试验、生物利用度测试和放大试验等一系列过程,还需要经历人体临床试验、注册上市和售后监督等诸多复杂环节,且各环节都有很大风险。大型制药公司每年合成上万种化合物,只有十几、二十种化合物通过实验室测试,最终可能只有一种候选开发品通过严格检测和试验而成为临床新药。因此,“预防”体系制度安排主要针对普遍性情境。针对特殊性情境的制度安排而言,政府主体主导的制度安排依然占据大多数,如针对中小型药品企业过多的问题,政府监管部门通过行政命令强行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药品下游企业集约度等。当前,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体系制度安排,总体仍然处于构建初级阶段,针对普遍性情境的制度安排依然过少,未来需要通过制度层面提升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水平。
(三)“预防”体系制度的交互模式
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各行动主体间交互模式,分别是“命令控制”式交互模式,和“参与合作”式交互模式。当前,由于中国药品安全监管制度依然处于单一监管制度,以政府监管部门为核心,采取的交互模式更多的以“命令控制”式为主。然而,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体系制度安排,更多需要强调对药品安全事件的自发性监督机制,因此,理想情境下,社会主体和企业主体应该更多依靠“参与合作”式交互模式。
如果行动主体以企业主体和社会主体为主,且重点聚焦在药品安全教育宣传领域;如果行动主体以政府监管部门为主,核心内容包括用行政力量改革药品采购制度,实现流通监管新秩序;或者运用行政手段优化产业结构,提升集约发展水平。在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体系中,政府部门对企业主要采取“命令控制”式交互模式,因为药品安全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只有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对企业各个环节采取有效控制,才可以实现真正的“预防”体系构建。例如,2016年政府采用行政力量要求所有药品生产企业改革药品采购制度,实现流通监管新秩序;2015年四川省政府通过改革GMP药品认证流程,将所有安全生产流程都以强制内容告知企业执行。但是,根据社会生物学的核心思想,专业的“预防”体系构建不应该仅仅依靠政府监管部门,而应该交给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承担。
(四)“预防”体系制度的潜在结果
潜在结果指制度安排在具体执行后产生的潜在影响或预期结果(Ostrom,2005)。根据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体系制度安排的定义,我们将制度安排的潜在结果分为长期结果和短期结果。长期结果指该项制度安排追求的是对中国药品安全治理体系产生长远影响的制度结果,如鼓励药品创新、提升药品质量,规范药品流通秩序,提升医药行业创新能力,保障药品供应能力等。短期结果指的是该项制度安排追求的是对药品安全“预防”体系中不同行动主体产生影响,对治理体系不产生长远影响。例如,共同推进一致性评价工作,健全评审质量控制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
由于特殊性情境下的制度安排主要应对组织层面产生的药品安全问题,因此,制度安排追求的是短期结果为主。同理,由于普遍性情境下的制度安排主要应对制度层面产生的药品安全问题,制度安排追求的是长期结果为主。
三、“免疫”体系的制度分析与安排
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免疫-治疗”三级协同制度安排中,“免疫”体系制度构建是关键难点。为适应食品行业低门槛、低投入和低技术含量的行业特点,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免疫”体系更加强调监管力量的广泛分布性。通过联防联控、有奖举报、舆情黑名单、自愿者小团队等方式,将大量分散的、随机形成的社会自组织整合起来,发挥着类似人体组成免疫系统的血细胞和蛋白质那样的防御能力,从而较好地解决食品安全事件的随机性和隐蔽性问题,提高执法资源的配置效率。然而,药品行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高技术含量等特点,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免疫”体系更强调专业性和职业性。通过行业协会、媒体等专业性组织的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形成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随机打击。在这方面,消费者难以发挥较大作用,只能够依靠专业化团队如药品行业协会等作为药品安全的社会监督主体。
(一)“免疫”体系制度的行动主体
政府主导下的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免疫”体系制度安排,也存在三种类型,分别是调动基层政府监管部门参与积极性的制度安排、调动企业积极参与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制度安排,及调动社会公众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制度安排。社会主体主导下的“免疫”体系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即通过为监管部门提供相关线索加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及加强药品行业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
政府主导下的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免疫”体系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第一,推动药品可追溯体系构建的制度安排。其中,可追溯体系、纵向一体化和双边契约责任传递三种制度安排的联动,构成产业链层面的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协同模式的主要内容(谢康等,2015):一是通过有效的组织形式与可追溯体系的混合降低可追溯体系的成本,二是通过可追溯体系与双边契约责任传递的混合降低各方的道德风险,三是通过双边契约责任传递与有效组织形式的混合降低一体化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此构建更为有效的社会共治模式。例如,2016年中国政府提倡药品行业构建药品安全追溯体系,希望追溯体系建设的规划标准体系得到完善,法规制度进一步健全。
第二,推动专业社会组织检举揭发的制度安排。构筑基于社会基层组织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督体系,包括消费者参与的司法保护、消费者举报监督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机制,进一步强化消费者参与食品药品安全治理的司法保护和细化消费者举报监督机制,前者如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合理界定销售者责任、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等,后者如统一食品药品经营者违规举报受理制度、明确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者违规举报受理制度,完善消费者有奖举报制度、强化对举报人的保护等(Grunert et al., 2011;刘广明和尤晓娜,2011)。但是,与食品安全治理不同的是,药品安全检举揭发更加强调专业性揭发,如行业协会的内部治理和举报,社会公众在药品安全举报上更多的是有心无力。2016年,中国政府推动企业内部人员举报,双倍奖励,单起最高奖励金额可达20万元,民众在激励之下会更大程度地参与药品安全社会共治。
第三,加强基层药品安全监管力量的制度安排。这部分内容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免疫”体系类似。例如,2015年吉林省政府强化基层药品安全管理责任,推进药品安全监管工作重心下移,联防联控药品安全工作新机制,提升全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又如,河南日报在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下,定期举办新闻讲座,研究建立信息发布机制,营造良好的食品药品安全舆论环境。又如,中国药品协会立足社会关切探索和实践社会参与、多元共治,完善行业考评制度,强化行业协会对成员单位的规范管理,缓解监管力量与监督任务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引导公众参与监管,加强药品行业自律管理。企业主体只有一项制度安排,如湖南红网主要是建立了食品药品安全线上专栏,向公众提供快捷的药品安全信息,认真答复网友的咨询,妥善处理网友的投诉,从而更好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可以认为,社会主体和企业主体构建的药品安全“免疫”体系主要核心机制,是加强药品安全信息公开,通过专业信息的处理加强药品安全监管。此外,药品行业协会则是通过协会机制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形成行业自律。
(二)“免疫”体系制度的行动情境
药品安全“免疫”体系制度安排的普遍性情境,指该制度安排主要针对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免疫”体系制度层面,且影响范围较广,属于完善制度层面的政策措施。典型情境包括江苏政府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理顺内部工作流程,将江苏省12331热线、南京市12345热线整合,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继续大力做好群众投诉举报处置工作;广东省政府依靠社会共治提升食品药品监管能力,成立药品行业协会等协会,制定行业协会章程,立足社会关切探索和实践社会参与、多元共治,强化食品药品监管能力。
药品安全“免疫”体系制度安排特殊性情境,指该制度安排主要针对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免疫”体系实施过程中的区域、组织或行动个体,影响范围与普遍性情境相比较窄,属于应对组织层面药品安全风险的政策措施。特殊性情境包括上述提及的中国政府根据标准对检举揭发危害药品安全的违法行为予以奖励,生产经营单位内部人员举报的,双倍奖励,单起最高奖励金额可达20万元等。
(三)“免疫”体系制度的交互模式
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免疫”制度安排的交互模式,主要以“参与合作”式为主,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免疫”制度安排的交互模式,则主要以“命令控制”式为主。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药品行业存在较高准入门槛,且“预防”体系构建相对完善,药品安全“免疫”体系重要性不如食品安全“免疫”体系高;其次,药品行业企业基础与食品企业相比相对较好,响应政府监管部门号召的可能性较高,政府监管部门不需要采取“命令控制”式交互模式也可以达到预期效果;最后,药品行业存在较高技术门槛,监管部门知识技术水平与药品企业相比略显不足,需要依靠药品企业配合才可以提升监管效能。
(四)“免疫”体系制度的潜在结果
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免疫”体系制度安排类似,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免疫”体系制度安排的潜在结果也可以分为长期结果和短期结果。特殊性情境下的制度安排,主要应对组织层面产生的药品安全问题,制度安排追求的是短期结果为主。普遍性情境下的制度安排,主要应对制度层面产生的药品安全问题,制度安排追求的是长期结果为主。因此,需要将“免疫”体系下长期结果与短期结果、特殊性情境与普遍性情境进行匹配和协同,长期结果与普遍性情境相匹配,短期结果与特殊性情境相匹配,形成最佳的“免疫”体系制度安排效能。
现实中,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免疫”体系的构建程度比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免疫”体系的构建程度要稍微滞后,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药品行业长期属于高度管制的行业,企业与政府部门在制度博弈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利益分歧,监管部门将较少监管空间让渡给药品企业。另一方面,药品行业同时属于高度专业化的行业,普通消费者难以对药品形成自然监管,需要依靠行业协会、媒体等专业团队实行监督。但是,药品行业协会、媒体等组织由受到政府监管部门高度管制,容易与地方利益形成合谋格局。因此,实际情境中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免疫”体系构建存在种种困难,构成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制度安排的难点。
四、“治疗”体系的制度分析与安排
药品安全事件一旦发生,其影响面和危害性比食品安全事件更广和更严重,因此,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的打击力度和频率,一般会比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更强,以对药品安全事件违规主体形成更强有力的震慑。与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体系和“免疫”体系制度评估类似,我们依然根据行动主体、行动情境、交互模式和潜在结果,对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制度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治疗”体系制度的行动主体
政府主导的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的制度安排,也存在三种类型:一是针对药品申请许可环节违法犯罪行为的制度安排。例如,2015年,中国政府针对药品评审审批过程中存在的弄虚作假,制定相应制度安排严肃查处违法犯罪行为;又如,2015年,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实施《云南省食品药品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将违法违规企业信息通过网络公开,通过信息公开和“黑名单”政策进行行业整治。二是针对药品生产过程中违法犯罪行为的制度安排。例如,2016年中国政府加大生化药原辅料飞检力度,进一步督促企业持续合规生产;又如,2014年浙江省政府在全省范围组织开展春节和省“两会”食品药品安全专项行动,加大执法抽检、市场巡查和现场突击检查力度。三是针对药品流通环节违法犯罪行为的制度安排。例如,四川省在2015年强化药品安全形势评估及时防控药品质量安全风险,加大对流通领域专项整治力度,提高飞行检查比例等。
企业主导的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对问题药品的查处和召回,避免药品安全问题迅速扩大。例如,2015年华润三九旗下产品“舒血宁”被曝质量问题,华润要求召回问题药品,同时停产停售并进行整改。同时,相关部门通过整顿措施对药品安全问题进行整治。又如,2014年广药集团发现其原材料经过工业硫磺熏蒸,而且成分与实际不符,立即停止销售维C银翘片,并对相关产品进行封存等。
(二)“治疗”体系制度的行动情境
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的行动情境,指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主体在解决药品安全问题中不同主体相互影响的社会空间,侧重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因素的描述。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制度类似,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制度的行动情境也存在两类,一类是“治疗”体系制度安排的普遍性情境。在普遍性情境下,“治疗”体系制度安排的目的,是帮助监管部门和企业主体完善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制度,侧重在制度层面进行问题发现与解决,对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具有长期影响。另一类是“治疗”体系制度安排的特殊性情境。在特殊性情境下,“治疗”体系制度安排的目的,是帮助监管部门和企业主体解决组织面临的突发性药品安全问题,侧重在组织层面进行短期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对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具有短期影响。
普遍性情境下制度安排的典型例子,如中国政府为加强查收违规产品,加大对生化药原辅料的飞检力度,责令召回已销售产品,对企业违法违规生产行为立案调查,进一步督促企业持续合规生产等。特殊性情境下制度安排的典型例子,如修正药业又一明星产品肺宁颗粒因原料部分霉变引发药品安全质疑,相关部门通过收回相关证书对药品安全问题进行整治等。
(三)“治疗”体系制度的交互模式
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的交互模式,指企业监管部门与企业主体之间根据不同食品安全事件影响程度采取的治理方式,属于“治疗”体系制度安排的核心部分。我国药品安全监管交互模式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政企合一监管阶段(1949-1978),市场经济时期的发展型监管阶段(1978-1998),以及统一体制时期的地方负总责阶段(1998-至今)(王波和江春芳,2016)。因此,根据不同阶段的监管体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不同的交互模式。
当前,中国药品安全监管已经向精细化方向发展,且逐步完善不同环节的法律法规。第一,药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完善。《药品管理法》已经构建起严谨的药品安全监管制度安排,对于造成重要社会影响的不良药品安全事件,也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责任界定,对于规范药品安全生产行为和相关主体责任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建立事前风险预警机制。药品安全事件的影响范围一般比食品安全事件要广泛,危害性也较大,且不易察觉,需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科学预测出潜在药品安全风险,才可以提高药品安全事件应对能力。第三,建立健全药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理能力。药品安全事件发生不可避免,政府与企业的应急能力至关重要,只有快速应对药品安全事件发生,及时采取紧急措施,才可以避免药品安全问题的快速蔓延。第四,危害药品召回机制。政府受限于人力、物力、财力,不可能对所有药品企业实行实时监管,需要药品企业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监管,一旦发生违反药品安全规定的行为,药品企业需要积极主动应对危机。
综上所述,在交互模式方面,现阶段中国药品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均采取“命令控制”式交互模式,对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这对于中国药品安全治理的阶段性需求而言是必要的。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制度安排应该在以下三方面进行加强:首先,强化药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地位,建立起权责统一的管理机构,减少监管执法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其次,继续完善药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提高监管执行力,防止监管权力滥用;最后,重视药品安全监管人才队伍建设,使得监管人员在业务熟练度上接近世界水平。
(四)“治疗”体系制度的潜在结果
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是社会共治“预防-免疫-治疗”制度设计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当药品安全事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时才会启动。“治疗”体系制度安排的潜在结果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对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惩罚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从而形成短期结果;另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形成震慑信号发送,使得药品生产制造者、消费者和其他主体清晰认识到,监管部门对待违法行为绝不手软,通过震慑信号发送形成价值重构。因此,我们将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制度安排的潜在结果分为长期结果和短期结果。
追求长期结果的“治疗”体系制度安排数量较多,典型例子包括吉林政府查处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提升全省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云南政府将违法违规企业信息通过网络公开,通过信息公开和“黑名单”进行行业整治。追求短期结果的“治疗”体系制度安排数量较少,典型例子包括上述提及的中国政府了解到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中存在问题日益突出,严肃查处注册申请弄虚作假行为等。又如,修正药业的明星产品肺宁颗粒因原料部分霉变引发药品安全质疑,地方政府收回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证书等。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践中,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正在从侧重事后“治疗”体系,向事后与事前“预防”和“免疫”体系平衡监管的方向转型,通过预防和增强社会应对药品安全风险的角度加强监管。理论上,药品行业的特征决定了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免疫-治疗”三级协同的制度安排需要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制度安排不同。无论在“预防”体系还是“免疫”体系下,或者在“治疗”体系下,制度安排的行动主体、行动情境、交互模式和潜在结果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制度安排,既需要体现药品行业监管的特征,也需要兼顾社会共治发展的普遍要求,通过政府主导下的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制度的有序推进,形成符合中国情境的药品安全共治的制度体系。
在这种制度体系下,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制度安排实践,应侧重强调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制度安排下的协同策略的特征。首先,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体系制度安排初步成熟,且针对普遍性情境的制度安排占多数。针对特殊性情境的制度安排虽然占少部分,但这部分制度安排通过组织层面的制度构建,可以推动制度层面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其次,目前,与“免疫”体系和“预防”体系相比,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的建设相对较为完善,且“治疗”体系中特殊性情境的制度安排超过普遍性情境的制度安排。在特殊性情境下,政府主体实施的制度安排约占40%,企业主体实施的制度安排约占20%,意味着企业主体尝试配合监管部门加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疗”体系制度安排建设,这是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制度安排应当继续推动的方向,也为中国政府推动药品安全社会共治三级协同策略奠定了良好的社会行动基础。中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预防-免疫-治疗”制度安排,强调通过三级协同的策略组合来提高药品安全事件发生前、发生中和发生后三个阶段的监管有效性。因此,本文建议:在研究和制定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制度安排时,可以根据药品安全事件发生前、发生中和发生后三阶段,分别采取“预防”体系、“免疫”体系和“治疗”体系来构建社会共治制度体系。实践中,这三种体系的三级协同策略组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随着监管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动态调整。
[1] 柯文. 食品安全是世界性难题[J]. 求是,2013,(11).
[2] 梁晨. 对转型时期我国药品监管体制的宏观思考[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5,(4).
[3] 刘广明,尤晓娜. 论食品安全治理的消费者参与及其机制构建[J]. 消费经济,2011,(3).
[4] 沈凯,李从东. 供应链视角下的中国药品安全问题研究[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版),2008,(3).
[5] 王波,江春芳. 我国药品安全监管改革路径探析[J]. 中州学刊,2016,(7).
[6] 肖静华,谢康,于洪彦. 基于食品药品供应链质量协同的社会共治实现机制[J]. 产业经济评论,2014,(5).
[7] 谢康,肖静华. 食品安全、社会系统失灵与公共政策——兼论产业政策、腐败与雾霾治理[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a,(1).
[8] 谢康,肖静华,赖金天等著.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困局与突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b.
[9] 谢康,赖金天,肖静华,乌家培. 食品安全、监管有界性与制度安排[J]. 经济研究,2016,(4).
[10]谢康,赖金天,肖静华.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下供应链质量协同特征与制度需求[J]. 管理评论,2015, (2).
[11]张舒怡,王远强.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药品安全问题治理[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19).
[12] Chen E, Flint S, Perry P, et al. Implementation of non-regulatory food safety management schemes in New Zealand: A survey of the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J]. Food Control, 2015, 47.
[13] Grunert K G, Scholderer J, Rogeaux M. Determinants of consumer understanding of health claims[J]. Appetite, 2011, 56(2).
[14] Johns G. The essential impact of context 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31(2).
[15] Opara L U. Traceability in agriculture and food supply chain: a review of basic concepts, technological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J]. Journal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 2003, (1).
[16] Ostrom E. Background on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11, 39(1).
[17] Ostrom E. Self-governance and forest resources[J]. Terracotta reader: A market approach to the environment, 2005,(12).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of Drug Safety Social Co-governance in
China
XIE Kang, LIU Yi
(Business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lack the attention on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drug safety social co-governance in China, and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food safety and drug safety should have difference. This paper uses the“ Precaution-Immune-Treatment” co-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ramework, and analyze the “Precaution”System、“Immune”System and “Treatment” System individually. Result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food safety social co-governance, all the three co-governance system show the difference in actor, contest, interaction and outcome in drug safety social co-governance. What’s more, we come up with the policy suggestion for drug safety social co-governance in China.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China Drug safety social co-governance is transforming from concentrating on“Treatment”System to “Precaution” System and “Immune” System.
Drug safety governance; Drug safety social co-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Co-management
F063.2
A
2095-7572(2017)03-0005-10
﹝执行编辑:韩超﹞
2017-2-26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制度安排:需求、设计、实现与对策研究”(14ZDA074)的阶段性成果。
谢康(1963-),男,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信息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信息经济学、企业互联网创新管理、食品药品安全治理;刘意(1991-),男,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企业互联网创新管理、食品药品安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