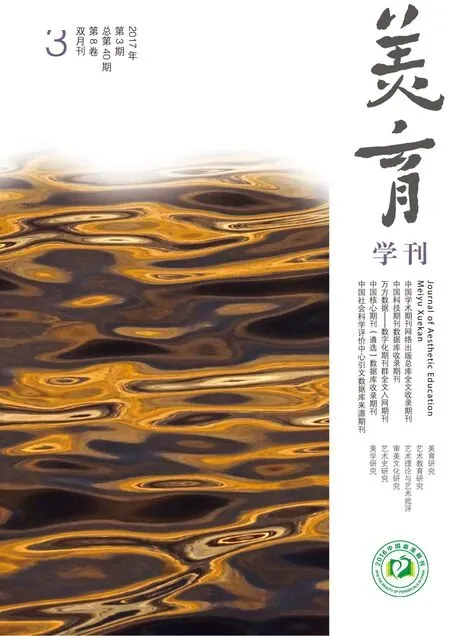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源与流
2017-03-25罗凌
罗 凌
(绵阳师范学院 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源与流
罗 凌
(绵阳师范学院 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我国传统乐教思想强调社会教化功能,近代音乐美育思想倡导“以美育人”,新中国成立初期突出“音乐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从“以审美为核心”走向对多元文化教育观的认同。从其发展历程来看,既有对传统音乐教育观念的继承与批判,也有对国外教育思想的借鉴与融合,既有对社会文化生态的被动适应,也有对中外教育思想的主动选择,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文化适应与文化自觉交互作用的特点。
中国音乐教育;教育哲学;演变源流
我国人类学、社会学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而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从音乐教育的发展来看,音乐教育哲学观念对音乐教育具有重要的引领与指导作用,因此明确中国音乐教育观念的变化发展轨迹,总结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探索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构建之道,获得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文化选择与自主发展的意识与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形成、发展、变化过程进行梳理,并探明影响其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以期加深对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发展内在规律的认识。
一、“礼乐教化”——中国古代传统乐教思想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重要内容。根据音乐考古成果与已有文献资料表明,我国传统乐教起源于古人的宗教祭祀活动,在上古时期乐教已是先民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到西周时“乐教”已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部分,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化体系,并成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2]。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背景下,乐教逐渐淡出官学体制教育之外,乐教思想源于这一时期诸子百家说“礼”论“乐”风潮,并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思想得以传承与发展,其中以儒家乐教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了西周的礼乐教化传统,而荀子的《乐论》和两汉时期的《礼记·乐记》则以人性论为基础对儒家乐教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与总结。[3]7
(一)乐以安德——以道德教化为基础
“乐教”一词最早出自《礼记·经解》篇,其形式与内涵不同于后世专门的音乐教育;同时古代的“乐”与“礼”,始终相须为用,因此传统乐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礼教的性质。美学家祁海文认为:周公制礼作乐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于“精神自觉”,并首先表现在“敬德”思想的提出。[3]62因此,西周乐教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并用“六德”“六行”“六艺”以教万民[3]77。可以说“以乐立德”是自西周以后礼乐教化的核心内容。
荀子认为音乐既能满足人们娱乐需求,同时也能表现德行,他的《乐论》就是以“性恶论”为出发点,主张发挥乐教在陶冶性情、修养德行方面的作用,通过“以道制欲”达到“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的境界。[4]29而后世的《乐记》则对乐教的道德伦理教化功能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归纳和总结,认为“礼乐皆得谓之有德”[5]11,通过乐教能够提高人们的内心修养,使“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从而达到“乐终而德尊”的功效。[5]19
(二)乐和民性——以人伦教化为途径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乐从和”的观念,《国语》中载伶州鸠谏周景王铸无射时说:“夫乐象政,乐从和,和从平”,认为只有“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才能“神是以宁,民是以听”。[3]16而他所说的“中音”与春秋时期孔子所推崇的雅乐是一样的,而只有这样的“中正平和”之乐才能使人心境平和。根据《乐记》的观点,乐能够体现社会伦理规范,即“乐”与“伦理”相通。因而通过乐教可以让受教者明了人伦事理,使其举止行为符合相应社会角色的规范,从而使君臣“和敬”、父子兄弟“和亲”、乡里族里长少“和顺”[4]29。
(三)乐与政通——以“完备王道”为归旨
中国古代诸子百家、文人政客但凡谈论乐教,必然与治国安邦息息相关,而“礼乐教化”则是诸子百家和有识之士抒发政治抱负的重要内容。据《论语·季氏》中记载,“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4]8。在孔子看来,礼乐教化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途径。即便对礼乐谈论较少的孟子,在其政治主张中也把体现“仁德”的乐教作为实施“仁政”的重要手段,认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6]《乐记》更是把乐教的重要性提到“国之兴亡”的高度,提出“乐与政通”的观点*“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见蔡仲德《〈乐记〉〈声无哀乐论〉注译与研究》,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8页。,认为“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性”[5]6,“礼”“乐”“刑”“政”最终的目的通过“同民心而出治道”,而先王制礼作乐就是为了“完备王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见蔡仲德《〈乐记〉〈声无哀乐论〉注译与研究》,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由于传统乐教始终与“礼”形影相随,因此传统乐教的价值与功能主要体现在道德教化、人伦教化、政治教化等方面。虽然也认识到音乐具有愉悦身心的审美功能,但是大多采用“以道制欲”的方式,忽视对受教育者个体情感宣泄、个性张扬的积极作用,缺乏对受教育者精神需求的人文关怀。虽然以嵇康为代表的道家乐教思想倡导通过“自然之道”实现乐教之功用,但是在乐教价值与功能的认识上则与儒家思想基本一致。
二、“以美育人”——近现代音乐美育思想的萌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抵抗外侮,富国强兵,以“洋务派”“维新派”为代表的大批有识之士,主张学习外国的政治、科学、文化、技术,并把“兴学育才”作为首要任务。从此中国开始借鉴西方学校教育理念、模式,开办新式学校,音乐课程逐步在学校教育中取得一席之地。伴随着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启蒙,我国近代一大批政治家、教育家、学者在西方教育、美学思想的基础上,通过继承中国传统乐教思想,构建了我国近现代美育理论雏形,并促进了音乐美育思想的萌芽。
儒学大师、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1858—1927)是我国倡导学校音乐教育的第一人,他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的倡导,建议清政府把音乐课作为学校教育中的一门课程[7]3。在《大同书》中,他以维新派“育德”“养体”“开智”的教育理想为出发点深入地论述了学校教育的价值,并强调音乐教育具有“涵养其性情,调和其气血,节文其身体,发越其神思”的作用[7]7。从其对音乐教育价值的认识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思想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启示,认同音乐教育在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著名思想家王国维先生以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关于人的精神分为“知、情、意”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德、智、体、美”四育并举主张。他认为通过美育能陶冶人的“情感”,美育在培养“完全之人物”的教育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7]9-11。他的美育思想既深受德国近代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同时又融合了我国古代乐教思想的传统,从他1904年2月发表在《教育世界》上的《孔子之美育主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印记。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以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唯意志论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悲观主义哲学,以及康德、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美育理论,阐明美育对于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性。同时引用了孔子、荀子等先哲们的乐教思想,认为孔子的教育“始于美育,终于美育”,认为孔子“无人无我”的审美境界,从而达到以美育人的目的[7]12-13。也正是受到西方美育思想的启示,他在《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中强调音乐形式美的价值,认为音乐教育作为情感教育、审美教育有其独立的教育价值,不应依附于德育[8]229-230。可以说,王国维的音乐教育思想表现出欲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乐教思想融合的倾向,既认同美育“立德树人”的社会功能,同时更注重美育所具有的“超功利”“超现实”的审美特性。
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是我国美育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人,他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为基础,主张通过“德育、体育、智育、美育”培养健全人格,树立人的“共和精神”。其主要思想体现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美育》《以美育代宗教说》《美育实施的方法》等论著中,他对美育(包括音乐教育)价值功能的论述也反映出对西方美学思想与教育理论的借鉴。蔡元培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8]234,其学理在于“美的对象”具有“普遍性”与“超脱性”,“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之见,又以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因此美育的价值可以达到“小之可以怡情悦性、进德修身”,“大之可以平天下”的功效[9]33。对于音乐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在生理上具有调节呼吸、活络血脉的作用,在心理上可以通过音乐领会人生、社会,乃至宇宙的各种现象与变化,从而达到“移风易俗”“感人至深”的目的[9]37。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德国哲学家康德、席勒的美学思想以及西方近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借鉴,同时又继承了我国传统乐教思想的内涵,表现出把中国古代乐教思想与西方美育原理有机融合的倾向。正由于他对美育思想的宣传与鼓动,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12年颁布的《教育宗旨》中提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方针[10],从国家政府的层面确立了美育在教育中的地位,音乐课程最终成为民国时期中小学的必修课。
从我国近现代教育(包括音乐教育)文献资料看,在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方面,主要借鉴了欧洲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近代德国的康德、席勒的美育思想,而这种主动学习与借鉴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与思想反思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对中外文化比较基础上的文化选择的过程。笔者以为,虽然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模式与内容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音乐学体系之上的,但是在音乐教育价值观方面,既借鉴了西方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理论,同时又糅合了中国古代乐教思想的内涵,既有借鉴,也有继承与拓张。“借鉴”表现在运用西方美育理论为实施音乐教育的价值寻求一种学理上的支撑。“继承”表现在对“道德教化”“移风易俗”“陶冶性情”等传统乐教价值的延续。“拓展”实施把音乐教育作为培养“完美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音乐教育的“人本化”价值取向。
三、“以政治为中心”——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音乐教育思想的异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厉的经济与文化封锁政策,中国在教育、经济、科技等方面确立“以俄为师”发展方针,提出“全心全意向苏联学习”的口号[11],从而开始在教育思想与理念、教育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借鉴苏联的经验。在音乐教育方面,对苏联“共产主义教育学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全盘照搬,促使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异化,逐步使音乐教育偏离美育的轨道,最终沦为德育与政治的附庸。
(一)共产主义教育思想的机械照搬,导致音乐教育沦为政治的附庸
在教育思想方面,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是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N.A.Kaiipob)的教育理论,他的教育著作《教育学》曾在50年代初多次被翻译成中文,作为中国教师的必备理论读物。凯洛夫的教育理论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哲学的基础之上,特别强调教育和政治的联系。他认为“教育在阶级社会内是具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以共产主义教育来代替和消灭资产阶级的教育[12]10。在美育思想方面,凯洛夫特别重视艺术教育的思想性与社会意义。他认为美育是培养学生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品行,促进学生个性全面发展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学校美育的首要任务是通过艺术的形式帮助学生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与道德观[12]358。
在20世纪50年代初,凯洛夫的教育理论占据了中国教育的主导性教育思想,其关于教育本质论与价值论,成为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学校教育的教育学理论基础,以他为代表(包括马卡连柯、加里宁)的前苏联“共产主义教育学思想”影响到我国五六十年代对音乐教育性质、价值以及目标的定位。从我国这一时期有关音乐教育的论著以及相应的史料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影响。
1955年的北京市《初中音乐教学参考资料》中明确规定:中学音乐课“要通过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音乐作品(主要是歌曲)来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劳动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自觉纪律教育;以形成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13]。可以看出,当时音乐教育突出的是政治性与思想性,强调的是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意识。
在1960年召开的全国音协代表大会上,赵沨在谈到音乐院校的教育时指出:“音乐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音乐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音乐教育的过程是实现思想改造,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艺术观的过程,其最终目的在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又红又专”的音乐工作者[14]。这种对音乐教育性质、目的、任务的论述,在20世纪6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虽然凯洛夫教育思想后来在中国受到批判,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从1972年出版的《浙江省中学试用课本音乐教师用书》中,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出当时音乐教育仍然强调政治性与思想性。该教师用书的“教学要求”部分特别强调了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任务,其内容包括“培养对中国共产党与领袖的热爱与忠诚”,“树立文艺必须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以及“提高阶级斗争意识和革命觉悟”等方面[15]。由于过分地重视音乐的政治工具价值,致使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完全失去了美育的功能而完全沦为了政治的附庸。从其文化根源看,虽然这与我国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但是对苏联共产主义教育思想的机械照搬,也是导致音乐教育逐步蜕变为“以政治为中心”的根源之一。
(二)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移植与传统乐教思想的批判
音乐教育思想和美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对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美学思想的学习与移植,间接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音乐教育的观念,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出版了前苏联以及波兰等国家的美学著作与译文集*其中包括日丹诺夫·赫连尼柯夫的《苏联音乐问题》(1950),克列姆辽夫的《音乐美学问题》(1954)、《音乐美学问题概论》(1955),万斯洛夫的《论现实在音乐中的反映》(1955),格·阿普列相的《音乐是一种艺术》(1957)、《论音乐形象》(1959)、《论标题音乐》(1960),以及卓菲亚·丽莎的《音乐美学问题》(1962)等。,其中以苏联音乐美学家尤里·阿·克列姆辽夫(juli·a·kremlev)的《音乐美学问题》、波兰美学家卓菲亚·丽莎(Zofia Lissa)的《音乐美学问题》影响最大。克列姆辽夫的音乐美学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基础上,并深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他特别强调艺术的阶级性,认为音乐艺术应体现出革命的现实主义艺术价值取向[16]。而卓菲娅·丽莎*在20世纪50年代卓菲娅·丽莎曾两次访问中国,我国音乐美学前辈于润洋曾于20世纪50年代随她学习音乐美学。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的“党性原则”,认为社会主义艺术应服从于党的路线与方针,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17]。因此,音乐作品应该成为该时代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我国的音乐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美学理论借鉴的基础之上的。1959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编写的《音乐美学概论》提纲(草案)中明确提出,“研究音乐美学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向各种资产阶级音乐美学思想进行斗争”,并把阶级斗争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18]。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音乐史学与美学领域关于“德彪西音乐”“无标题音乐的阶级性”的大讨论,以及针对李凌先生、钱仁康先生“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都反映出以克列姆廖夫和丽莎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音乐美学思想与西方唯美形式主义音乐美学的思想冲突。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在文化领域对阶级斗争意识的刻意强调,导致了我国教育界对传统乐教思想以及美育教育思想的彻底否定与反叛。
从相关音乐文献资料看,对传统乐教思想的片面理解与歪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孔子为代表的礼乐思想从内容到形式都“反映着奴隶主阶级的‘仁’、‘德’、‘孝’、‘忠恕’等思想”,因此,孔子提倡礼乐教育实际上是想复辟奴隶制度[19];第二,以《乐记》为代表的古代乐教理论所彰显的“心平德和”价值,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在本质上否认阶级斗争存在,调和当时存在的激烈的社会矛盾,从而“麻痹人民群众,维护奴隶制的长存”[20];第三,认为古代乐教思想,以及近代西方美育思想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抹杀音乐作品阶级性的修正主义谬论,是在新形势下反动的文艺“超阶级”论的翻版,是资产阶级用反动的唯心史观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的武器。
当时对我国古代乐教思想的批判,是我国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冲突在音乐教育领域的反映,从音乐文化领域看,则是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以及过分强调音乐艺术政治标准的结果,其理论的片面性在于夸大了古代乐教思想所具有的阶级性和政治功能,否认音乐教育所具有的“愉悦身心”“陶情冶性”“以乐教和”等美育价值,致使音乐教育彻底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四、“以音乐审美为核心”——改革开放后音乐审美教育思想的确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国家经济与科技强国上,“科教兴国”逐步成为国家发展的大政方略,作为美育的音乐教育在培养高素质人才中的独特作用逐步得到认可。从国家层面来看,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明确提出各级各类学校要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21]103,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美育在学校教育中合法地位的初步确立。此后在1989年颁布的《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年—2000年)》[21]154、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1]194、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2]中,都充分肯定艺术教育具有“陶冶高尚道德情操”“培养审美观念与能力”“促进智力发展”的重要作用,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立。
可以说,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能够逐步恢复与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包括音乐家在内的诸多文艺界有识之士的呼吁与努力,而在各种刊物与会议发表有关美育(包括音乐教育)重要价值的文章与言论是重要的途径。为了使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美育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我国音乐界的前辈们一方面从古今中外教育发展史中寻求证据,从近现代中西美育理论以及中国古代乐教思想中寻求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主动吸收国外教育学、心理学、音乐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逐步形成适应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音乐审美教育哲学理论雏形。在1985年召开的第三届音乐美学座谈会上,姚思源先生提交了《音乐审美教育应当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核心》的论文,作者通过回顾中国古代乐教、古希腊斯巴达教育、雅典教育、近代现代中国学校教育中重视音乐教育的史实,梳理孔子、梁启超、蔡元培、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马克思、恩格斯等古今中外思想家、教育家对美育和音乐教育性质、价值的已有成见,同时针对当时中国教育界对美育价值理解方面存在偏重“辅德”“益智”“娱乐”等功能的误区,在苏霍姆林斯基(В.А.Сухомлинский)美育理论的基础上*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感知和领会美是审美教育的基础和关键,是审美素养的核心。”见蔡汀、王义高、祖晶《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4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38页。创造性地提出音乐教育应该“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理念,认为音乐教育最本质、最核心的任务是引导学生通过对音乐美的感知、理解、体验、评价、鉴别和创造,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素养[23]51-57。1987年,作者再次撰写论文《音乐艺术的本质特点与教育价值》,以音乐美学理论为基础对音乐作为“声音艺术”“听觉艺术”“表演艺术”的特点进行了阐述,进一步充实了“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理论基础[23]20-26。1991年又在全国第四届美学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论文《学校音乐教育应努力向审美境界追求》,着重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实施路径提出建议,进一步完善了“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理论构架[23]70-75。
在姚思源先生系列论文发表后,音乐教育应该“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观点逐步得到我国音乐教育界的认同,部分学者试图构建一个“音乐审美教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框架。其中,廖家骅的专著《音乐审美教育》(1993年)的出版,是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理论的进一步诠释与拓展。在这部专著中,作者以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理论为指导,以音乐美学和近现代美育理论为基础,同时吸收当代音乐心理以及教育学的研究成果,对音乐审美教育的“性质”“任务”“特点”“原则”,以及“心理结构”“心理功能”“实施途径”等方面进行了阐述[24]69,在音乐教育的性质上,作者明确指出“音乐审美教育是以音乐为媒介,以审美为核心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音乐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提高音乐审美能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24]69-72。该专著和作者1992年发表在《音乐研究》第一期的论文《音乐教育的哲学思考》是这一时期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重要著作。
另外,在曹理先生主编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1993年)中,首次明确从音乐教育哲学的视角,对于音乐教育的本质、价值、目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归纳,勾勒出中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框架。作者首先阐释了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教育”具有的“情感性”“技艺性”“形象性”和“愉悦性”,同时指出音乐教育具有“培养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发展思维与启迪智慧”“全面提高音乐修养”“促进身心和谐发展”等多重价值[25]25-26,最后强调音乐教育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完善人的自身品格”,而其核心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审美感情和审美情趣。[25]32-33在音乐教育性质、价值与目标的认识上,既有对中国近现代美育思想的继承,也有对美国音乐教育哲学家本奈特·雷默(Bennet Reimer)的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观点的借鉴*该书第14、17页引用雷默专著《音乐教育哲学》中关于音乐教育的论述:“音乐教育的本质和价值取决于音乐艺术的本质和价值”,“音乐教育是通过培养对音乐的审美因素的反应来进行的感觉教育”。,还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认同,同时又合理吸收了当代心理学、教育学、音乐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姚思源提出的“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观念,并不等同于雷默的音乐教育审美哲学理念。因为从上述理论著述中可以发现,这里的“音乐审美”包括对音乐美的“感知”“鉴赏”“表现”“创造”等多种维度,也包括对音乐社会价值、道德伦理价值的判断,而雷默的音乐教育审美哲学是建立在绝对表现主义美学理论基础上的,强调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审美因素的反应”,是一种忽视音乐文化语境,侧重于对纯粹音乐形式美的感知与体验。可以说,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提出的“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理念,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乐教“礼乐教化”思想和近现代美育思想的传统,又合理地吸纳了苏霍姆林斯基美育理论*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是乌克兰卓越的教育家、教师、思想家和作家。从80年代初期,他的著作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其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与雷默音乐教育审美哲学的合理因素,并整合了国外心理学、教育学、音乐美学的研究成果,把“涵养美感”“以乐育德”“以乐启智”等多种音乐教育价值取向融入“音乐审美教育”的旗帜之下,形成了适应当时中国文化生态环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念,并成为2001年《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中“以音乐审美为核心”课程理念的重要理论来源。
五、走向“文化多元”——世纪之交中国音乐教育哲学发展趋势
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随着全球一体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世界经济、文化、教育、思想的交流日益频繁,教育理念、哲学思潮、音乐美学理论的更替可谓日新月异。就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看,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外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译介;二是关于中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的选择与构建。
在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方面,对我国音乐教育影响较大的包括“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实践哲学”。其中,美国音乐教育家本奈特·雷默(Bennett Reimer)的“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对中国的影响较早。在1985年,他就应中国教育部和文化部的中美艺术交流项目邀请,来华讲学、访问长达两个月,介绍了其“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MEAE)。1998年又再次到中国参加了“第七届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特别是2003年、2011年他的《音乐教育的哲学》第二版、第三版在中国的正式出版*90年代中期,熊蕾应当时音协艺教委李妲娜之邀翻译了他的专著《音乐教育哲学》第一版的中译本,但译稿仅以油印本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音乐教育学教研室参考资料。,他关于音乐教育是“审美教育”“感觉教育”的教育理念,为中国当代普通学校音乐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我国200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把“审美体验价值”作为音乐课程的首要价值,并明确提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课程理念,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着重引导学生把握音乐作品的形式要素和情感体验[26]。我国音乐教育对于音乐教育审美哲学理论的借鉴,对于走出过分强调“辅德”“益智”功能的误区,重视音乐教育的审美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音乐教育学者们对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管建华、樊祖荫等为代表的音乐教育学者翻译了大量的相关论著*包括《中国音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推出的“全球视野的音乐文化研究”“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教育”“国际音乐教育与音乐人类学”“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专集”等系列特刊,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的《音乐教育与多元文化——基础与原理》《音乐教育的多元文化视野》等译著。,组织多次相关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介绍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与发展态势,促进中国教育工作者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的认同,并推动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中国教育中的实践进程。作为一种教育观念,“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认为: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音乐的意义、价值、功能是不一样的,只有将音乐与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才能获得最佳的理解和评价;世界上各个族群的音乐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应该得到尊重与传承,而通过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既有利于保持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有助于增进不同国家、族群人们之间的互相理解与认同[27]。
就中国音乐教育发展而言,对于音乐教育多元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其积极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从理论层面来看,主要是对自近代以来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理念与实践进行反思。在1996年召开的全国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上,针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长期以欧洲音乐理论体系为重点,忽视对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体系的构建,在音乐教育价值取向上存在“重西轻中”,甚至“以西否中”的倾向[28],我国部分学者提出构建“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是指“以中华各民族各地区不同音乐风格内容组成的,并有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心理、行为、艺术、思维方式、审美理想及价值等深厚的文化哲学基础”的音乐教育体系。见管建华《以中华文化为母语音乐教育的性质和意义》,载《人民音乐》,1996年第1期,第31页。。而从实践层面来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与方法已逐步融入学校音乐教育中。在我国音乐专业教育领域,全国许多音乐专业院校陆续开设了《世界音乐》《音乐人类学》等课程,通过专业音乐教育介绍世界不同文化中的音乐,树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价值观念。在基础教育领域,2001年颁布的我国《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就已明确提出“理解多元文化”的课程理念,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则从多元文化的视角对音乐课程的人文性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音乐课程中的艺术作品和音乐活动,皆注入了不同文化身份的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和参与者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主张,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文化发展脉络以及民族性格、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展现,具有鲜明而深刻的人文性。”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世纪之交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美国音乐教育家戴维·埃利奥特(David J.Elliott)的“音乐教育实践哲学”*他本人曾于2006年、2009年先后两次应邀到中国讲学,而他的专著在中国的出版,为中国学者全面了解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料。,他认为“音乐是多样性的人类实践活动”,音乐教育在本质上是多元文化的特性,而音乐教育的价值在于“自我成长”“自知自觉”与“音乐享受”。在其专著《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中,他立足于音乐的多元文化语境,对雷默的“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认为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只专注于对作品的审美感知,轻视对音乐表演、音乐创作等音乐创造性活动的关注,把音乐学习与相应的文化语境人为地隔离,因此不能为音乐教育实践提供有力的哲学支持。并主张音乐教育要为学生提供包括欣赏、表演、创作等多样化的音乐实践活动,强调要把音乐与特定的文化语境相联系,通过文化理解音乐[29]。
正是基于埃利奥特对音乐教育审美哲学理论的批判,我国音乐教育理论界在21世纪初也曾出现了围绕“以音乐审美为核心”音乐课程理念的学术争鸣。我国部分学者针对中国基础音乐教育“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课程理念提出质疑,认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课程理念是建立在“认识论的普遍哲学基础之上”的,忽视了音乐的多元文化语境,把音乐教育限制在了“审美的牢笼”之中,建议构建“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以实现学生在文化中学习音乐,并通过音乐学习理解文化的目标[30]。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音乐教育课程理念中的“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课程理念不同于西方康德、席勒所推崇的“纯粹审美”哲学观念,而是立足于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语境,既借鉴了音乐教育审美哲学中突出音乐教育审美价值的合理部分,又继承了我国古代乐教思想“以乐立德”的传统内涵,同时也涵盖了近代美育思想中“美善合一”的价值取向,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多元文化特性的课程哲学理念。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从不同的视角,探索提出构建富有创意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雏形。其中,以王耀华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以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理念[31];以张业茂为代表的学者试图构建以传统乐教理论为基础的“以乐教和”音乐教育价值体系[32];以董云为代表的学者则尝试运用文化生态理论提出“生态视野下的音乐教育”[33];以朱玉江为代表的学者则尝试运用后现代哲学交往理论,提出构建“基于交往理论的音乐教育”[34]。
在21世纪初的近10年间,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视野,为进一步更新音乐教育的价值观,合理定位我国音乐教育的性质与目标,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从实践层面看,我国201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音乐教育课程标准》认为,音乐课程具有“为学生提供审美体验,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开发创造性发展潜能,提升创造力;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增进对世界音乐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和理解;促进人际交往、情感沟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35]等多方面的价值。在音乐教育哲学方面,既继承了我国古代乐教思想与近现代美育思想“以美育人”的传统,又吸收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包括“音乐教育审美哲学”“音乐教育实践哲学”“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思想”“创造教育理念”等多种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出“多元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价值取向。
六、结 语
通过对我国不同时期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演变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其一,在自近现代以来的中国音乐教育发展历史中,“以美育人”的音乐美育思想始终是音乐教育哲学的主线,并且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新的意义,其理论内涵在不断地充实与拓展之中,可以说既不等同于近代德国康德、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也不等同于当代美国雷默的“音乐教育审美哲学”,体现出音乐教育对“育德”“怡情”“益智”等多种教育价值的兼容。
其二,传统乐教思想作为中国教育哲学之源,传统乐教思想始终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并在近代实现了与西方美育思想的融合,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淡化甚至被批判,但是在改革开放后之当下,其文化价值观、传统教育观念能够被传承与认可,其主要原因在于乐教思想蕴含有“人文教化”这一教育价值与功能的永恒主题,能使教育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突出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从而适应不同社会发展之需要。
其三,中国音乐教育的历史经验表明,在音乐教育哲学理论的构建方面,既要考虑不同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要考虑符合音乐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盲目照搬政治或文化理论代替音乐教育哲学,会对音乐教育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在对待中外音乐教育哲学方面,合理地继承与借鉴是音乐教育哲学发展和创新的必由之路,全盘否定已有理论体系或墨守成规故步自封,都无助于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
[1]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88.
[2] 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8-25.
[3] 祁海文.儒家乐教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4] 孔子、孟子、荀子乐论[M].吉联抗,译注.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59.
[5] 蔡仲德.《乐记》《声无哀乐论》注译与研究[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
[6]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283.
[7] 俞玉姿,张援.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选(1840—1949)[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8] 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1840—1949)[G].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9] 伍雍谊.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10] 孙继南.中国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43.
[11]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纪(1949—1982)[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4-8.
[12] 凯洛夫.教育学:上[M].沈颖,译.北京:新华书店,1950.
[13] 北京中小学教学参考资料编辑委员会.初中音乐教学参考资料[G].北京:音乐出版社,1955:2.
[14] 音乐出版社编辑部.论音乐为工农兵服务[G].北京:音乐出版社,1966:143.
[15] 浙江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浙江省中学试用课本(革命文艺音乐部分)教师用书[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2:374.
[16] 高明星,郁正民.克列姆辽夫音乐美学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J].学术交流,2013(2):140-143.
[17] 丽莎.音乐美学问题[M].廖尚果,廖乃雄,史大正,译.北京:音乐出版社,1962:92-63.
[18] 范晓峰.移植、萌生、解读(续)——20世纪初至1978年中国音乐美学学科性质研究叙事[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2):22.
[19] 沈阳音乐学院评论组.“复乐”是为了“复礼”——批判林彪和孔老二利用音乐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罪行[G]//批判孔老二的反动音乐思想论文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5:55-56.
[20] 丘振声.从音乐思想看孔丘的反动面目[G]//批判孔老二的反动音乐思想论文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5:36.
[21] 姚思源.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献(1949—1995)[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2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2002中国教育信息化绿皮书[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89.
[23] 姚思源.论音乐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24] 廖家骅.音乐审美教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25] 曹理先.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
[27] 管建华.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234.
[28] 王耀华.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得失[J].音乐研究,1994(2):13-15.
[29] 埃利奥特.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M].齐雪,赖达富,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42,288,28.
[30] 管建华.“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J].中国音乐,2005(4):6-16,30.
[31] 王耀华.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M].中国音乐教育,2007(7):7-11.
[32] 张业茂.音乐教育价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01-125.
[33] 董云.生态观视野下的音乐教育[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1):160-165.
[34] 朱玉江.交往音乐教育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98-245.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责任编辑:紫 嫣)
The Origin and Course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usic Education Philosophy
LUO Ling
(College of Music and Performing Arts, Mianyang Normal Institute, Mianyang 621000, China)
China′s traditional music education emphasizes the function of social rectification. Modern music aesthetic education advocates "cultivation of character with beaut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new China "music for political service" was highlighted and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shift from "aesthetics as core" to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was encouraged. From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music education was inherited and critiqued and foreign educational ideas were also borrowed and incorporated. On the one hand there was passive adaptation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cology,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as also active embrac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educational ideas, displaying a combination of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cultural awareness.
Chinese music educatio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source and course of evolution
2017-03-08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文化生态语境下的中国音乐教育学哲学研究》(14SA0101)、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在基础教育中的现代转换研究》(BHA140085)的研究成果。
罗凌(1967—),男,四川绵阳人,绵阳师范学院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音乐教育理论研究。
G40-02;J60-02
A
2095-0012(2017)03-0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