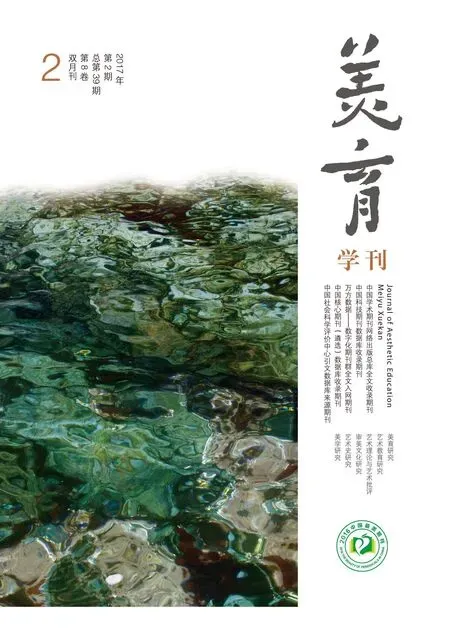八大山人艺术的情感张力
2017-03-24梁宏安周纪文
梁宏安,周纪文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八大山人艺术的情感张力
梁宏安,周纪文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八大山人的艺术作品流传300多年而不衰,以独特的“怪诞”风格流芳后世,至今仍有大批艺术家在模仿他、推崇他。八大作品的时间穿透力和经典化与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密切相关,而艺术品的魅力和价值判断始终离不开作品中凝结的审美情感。八大艺术创作中的审美情感实质,绝不止于他无法直接言说的家国哀思,但也不能盲目拔高,把八大审美情感实质归于他纯然地对个体生命本真的沉思和关照,我们应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介入八大艺术创作中的“怪诞”与“悖谬”,从他飘零的个体际遇与生存本真叩问之间峙对的“情感张力”来把握其艺术内蕴。
八大山人;家国之思;生存叩问;情感张力
文艺作品表达情感无可否认,但是表谁的情?达谁的意?对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就有多种观点,甚至彼此互不相容。大而概之,主要有两种说法:“自我表现说”认为文艺作品就是作家本真感情的显露,中国传统文论一直走的是这个路数,近代西方浪漫主义更是奉其为圭臬,英国华兹华斯的“诗是情感的强烈流露”和王国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都是自我表现论的宣言;也有学者对“个人表现论”提出质疑,甚至提出与之相对的理论,例如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主张,曾在欧美文艺评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反对张扬个性、显露自我的浪漫式批评观,认为作家与人类普遍感情的共振才能催生合格的作品。这两种观点孰优孰劣,也不能简单立判高下,虽然这两种理论本身的高下之较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但为本文探讨八大山人创作的审美情感问题或艺术感染力成因提供了方向。
一、遗民身份——审美情感的底色
八大山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本名由桵,字雪个,号八大山人、个山、人屋、道朗等。其祖父朱多炡,字贞吉,号瀑泉,其父朱谋觐,字太冲,号鹿洞,二人均精通书画。明天启六年丙申(1626),八大山人出生于江西南昌弋阳王府。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闯王李自成在西安称帝,随后攻入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上吊,大明王朝土崩瓦解,此时,八大山人年满十九,亲历了自家江山从风雨飘摇到大厦倾塌的全过程。明清易代,开启了中国第二次异族统治的时代,清政权建立初期采取残酷高压政策,“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清政权用最原始的方式震慑汉人,尤其是残余明朝势力,同时对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明朝宗室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和追剿,八大作为王公贵族被迫走上逃亡之路,昔日王谢堂上的燕子便做飞鸟散了。
八大山人一生颠沛流离,从王子公孙被迫逃入禅林,又落魄街头,“曳长领袍,履穿踵决”,潦倒至被市井小儿嘲弄的地步,这一切自然是由清军入关、代明而立造成的,所以遗民身份是八大一生的标签。因此,后世谈论八大的创作时无不将其家国悲痛联系起来,大加抒写。郑燮的题画诗“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不多泪点多”成了八大身世哀恸的写照。把艺术家的心理状态与艺术作品直接挂钩,八大的书画作品成了其身世悲剧的摹写。从艺术心理学和个人表现论角度来说,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中直接指出:“在我看来,有这样的可能性(绝非肯定),那个被创造出来的形式的感人之处在于它表现了创造者的感情,大概艺术品的线条和色彩传达给我们的东西正是艺术家的感受吧。”[1]也就是说,作为物质实体的“文本”是艺术家内心情思的外化物,这和我国传统绘画所倡导的“外事造化,中得心源”十分契合。
相当一部分学者把八大的“心源”和他的遗民身份联系起来,认为八大胸中有块垒,盘踞着“兴悲禾黍”的家国之痛,从这个角度解读他在创作中的审美情感问题。这类观点自然不是捕风捉影。甲申之乱后,八大剃度受戒,隐身佛门,期间在进贤介岗灯社和奉新耕香庵等地习法,在1666年作《墨花图》一幅,现藏于北京故宫。画上题诗一首:“洵是灵苗茁有时,玉龙摇曳下天池,当年四皓餐霞未,一带云山展画眉。”[2]148诗人自喻灵苗,在等待茁壮之时,亦把自己比作天龙下凡,沉潜于深渊。诗中很显露地表达了自己当前的处境,并不忘自己王室遗民的身份。“画为心声”,在这里八大的心声不需要靠隐喻式的图像来传递,心声直接以诗为证了。在民国《安义县志》宗教志载:“时八大山人、南昌万时华、奉新彭文亮、邑诸生涂凤稷、黄之侃常集社于此,至于康熙间罗致狱兴,文令以寰,变而为禅院。”[2]149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彭文亮、万时华等,都是明朝遗臣。也就是说,八大隐居期间参加过遗民诗社,并与其中一些遗老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些学者看来,这正好指明了他在《墨花图》题画诗中所谓心声的实际内容。
临川其间,八大的思想出现了很大波动,癫疾复发之后,他离开佛门,返回世俗世界。在1680年末到1684年这段时期里,八大开始使用带有自辱性质的“驴”号,例如“驴屋”“驴屋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这一时期的作品也表现得满腔愤恨,用语直白。在《个山小像》中,八大破天荒地钤上“西江弋阳王孙”印,这十分罕见,对自己的王孙身份毫不避讳。此像出现也在“驴印”时期,诸多迹象都能印证这位往年的“灵苗”不再压抑自己内心的身份认同,“玉龙”也无法安心潜在深渊了。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古梅图轴》正创作于此时,这幅古梅图有别于八大的同类作品,八大几乎不画整株梅花,在其他同类作品中,梅花都是一支旁出,而在此画中,梅花根部裸露,紧紧扣住地面,粗壮的躯干硬挺挺地直立起来,整体看上去有饱经风霜之态。古梅上方有先后三段题识,前两首分别写了失国后吴镇画梅和郑所南不为北音两件事,这两人都是宋遗民,南宋亡后,两人拒不仕元,所以这里八大确实有借古喻今之意,狷介愤恨的遗民情感倾向明显。八大山人研究专家王方宇在《八大山人的生平》中便认定了这幅作品是八大故国情怀的隐射。
八大的创作和思想处在故国情感的挣扎中,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由于有这样一层底色存在,后世在评论或研究他的艺术时总脱离不了王孙情结和遗民情感。尤其对个人标示色彩鲜明的名号、印章、斋号问题研究都被抹上了浓重的身世色彩,甚至发展成一种解码游戏。例如对“八大山人”白文印,有人解读为这是表示从朱权至明亡,江西南昌王室共繁衍了八支,到八大这里就截止了,因此说是“止八大山”。“止八大山”是在1682年《瓮颂》中出现的,之后才一直使用“八大山人”,所以一些学者就做了这样的推理。山人还有一“八还”印,杨新认为一方‘八还’的印章,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即第八代子孙回来了,可以延续香火不至斩先人祭了。类似的名号解释很多,大都不脱对八大个人身世情愫的渲染。
诚然,如果八大没有遭遇家国之变,那他的诗歌创作、绘画风格、题材选择、精神气质绝不同于现实的八大,但过于强调八大对自我情感的表达是不是就能说明凝结于其作品中的审美情感实质?尤其值得考量的是遗民身份背后所传达出的民族对抗意识和失势王孙的落寞情绪到底能不能撑起八大的艺术魅力?
这些问题必须被回答清楚,否则我们无法对八大的艺术造诣做出公允评价,更无法建立八大艺术审美情感的“合法性”。朱良志曾说:“八大的遗民情感问题有明显被扩大化的倾向,这影响了对八大艺术研究的深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搅乱了八大的研究格局。八大在世时,他就被塑造成一个愤怒的艺术家,艺术只是传达其抗清复明的方式……八大所画的鸟,有冷眼向人之态,那是对清人的痛恨,八大的梅和菡萏有利剑一样的角,那是投向清人的匕首……这样的研究其实在降低八大的艺术价值,将其丰富的艺术世界说成是简单的民族仇恨的传达物。”[2]146-147这样的说法基本上否定了八大山人的创作只是个人家国悲愤的表现,认为八大艺术的旨归不在于此,应该有更丰富的艺术价值,这也暗示八大作品带有了某种超越性。
二、生存叩问——八大艺术审美情感的另一种解读
符号美学家苏珊·朗格在《哲学新解》中说:“纯粹的自我变现不需要艺术的形式”,“以私刑为乐事的黑手党徒围绕着绞架狂吼乱叫;母亲面对病重的孩子不知所措;刚把情人从危难中营救出来的痴情者浑身颤抖,大汗淋漓或苦笑无常,这些人都在发泄着强烈的感情,然而这并非音乐需要的东西,尤其不为创作所需要”,“发泄感情的规律是自身的规律”[3]。她对艺术所蕴含的审美情感问题的观点和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讲的“非个人化”很契合,他说:“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诗不是表现个性,而是在逃避个性。”[4]他们的说法和华兹华斯、托尔斯泰讲的“个人情感表现说”基本是对立的。那么,这种“非个人化”情感究竟是什么?苏珊·朗格给出了她的答案:“艺术家表现的绝不是他自己的真实的感情,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感情。”[5]25依她的观点,现场性很强烈的个人情感并不是艺术表现的对象,而是处理过的情感概念,这种情感概念是属于人类的,“艺术品表现的是关于生命、情感和内在现实的概念,它既不是一种自我吐露,也不是一种凝固的‘个性’,而是一种较为发达的隐喻或一种非推理性的符号。”[5]25所以艺术能够引起人类审美情感共鸣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一种典型而普遍的情感。正如王国维评价李煜词时就对其“非个人化”的审美情感表达表示了赞赏,他说:“词至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6]王国维认为李煜提升了词的格调,由伶工表达个人情绪的艳词变为“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感慨寄托之词,上升到了对个体命运的关照的层面。很显然,这比李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失落帝王梦更有境界。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有同样失国遭遇的皇族八大,其创作确实可以做这种类比解读。
朱良志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八大是一位以‘孤’见称的艺术家,并不意味着他只是为孤独无依的生存状态而哀思,也不是因为他强调孤,突出自己是王孙……更不是由孤独来证明自己鹤立鸡群,高于凡俗,他是将个体‘孤’的体验上升到对人存在命运的思考,由个体存在状态的感叹,发而为人类存在的玄思。”[2]58-59这段话不正是苏珊·朗格所说的“艺术家认识到的人类的感情”吗?也就是说,八大的艺术创作具有了超越性,把失落愤懑的个人遗民情绪转化成了对命运无常的直视与沉思,没有一味地放纵对自己悲剧身世的感慨,而是把这种感情隐匿起来,化为一种对生命存在本真状态的冷峻思考,所以八大艺术创作有一种理性的克制,很多作品意象简单、构图精炼,在简笔中有大气象。确实如此,“孤”几乎是八大的创作的一个母题,“孤鸟”“孤鱼”“孤石”“孤草”“孤花”等等,八大的大量作品都是这样的主题,通常画中只有一两个意象,有的甚至几笔就勾成了,像《河上花歌》那样的大幅作品在八大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孤鸟图轴》,纵102厘米,横38厘米,画中仅有两个意象,一支虬曲别致的树枝从画面底部左侧探出,一只小鸟单脚独立于枝头,眼睛如豆,小而有神,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当然,八大画一只孤鸟不只是为了栩栩如生地临摹一只立在枝头的小鸟,而是为了传达一种情感,只不过他没有采用直接描写的方式,而是通过客观的对应物来表现,是一种符号化过程,需要接受者看到能指背后的所指。正如苏珊·朗格所说:“一种客观的符号将一个主观的事件或活动表现出来。任何一件艺术品都是这样一种形象,不管它是一场舞蹈,还是一种雕塑,或是一幅画、一部乐曲、一首诗,本质上都是内在生活的外部显现,都是主观现实的客观显现。这种形象之所以能够标示内心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乃是因为这一形象与内心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含有相同关系和成分的缘故。”[5]8-9这种“异质同构”的观点很能说明八大的“孤鸟”意象,它不单是一只独立枝头的孤鸟,还是一个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灵魂写照,有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唯有枝头孤鸟立空境的气象,所以即使没有题画诗或文字注解的辅助阐释,接受者单凭符号组合而成的特殊意象也能够唤起内心的情感,此时创作者与接受者的想象、意趣、情感被连通,在欣赏者对孤鸟立别枝的凝视中体悟出人类共通的情感。“孤鸟”“孤鱼”“孤石”等形成的“意象群”足够成为八大具有个人特色的隐喻式表达,这些孤的“意象群”所尽的意不就是艺术家对生命存在本真状态的关照吗?
三、八大山人艺术作品中的情感张力
八大艺术的审美情感到底是“山河残破不堪思”的身世之叹,还是“人生忽如寄”的超越性思考?因为在前文的论述中这两种审美情感都得到了承认。但是,本文认为单从审美情感的“个人化”还是“非个人化”角度都无法击中八大艺术创作价值的要害,也无法理出审美情感的实质。需要注意的是,同时承认这两种审美情感的存在并不是简单地将它们并置起来,或者认为八大在不同时期被两种情感非此即彼的影响八大艺术感染力形成的真正原因是这两者之间形成的对峙和撕裂,是它们相互之间既渗透又排斥造成的张力,正是这种“情感张力”再现了八大内心生活的统一性、个别性和复杂性。
“张力”这个词本是物理学的概念,后来被引渡到文学理论中,成为一种诗学概念。在文学领域,最早使用“张力”概念的是美国批评家艾略特,他在《论诗的张力》中说:“我们公认的好诗,具有某种共同的特点,我们可以为这种单一性质造一个名字,……这种性质我称之为‘张力’。”[7]自此以后,张力论成为新批评的重要诗学主张,是新批评派对康德“二律背反”在文学领域所做的一次移花接木。“张力诗学”是在对立、冲突,相互抵牾、拉伸的二项式基础上形成的,并通过悖论式的逻辑达到某种出人意料的效果,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就是张力的典范,以“恶”来写“美”。金健人在《论文学的艺术张力》中说:“唯有充满张力的文学作品,才能让作者把他们的艺术之箭射向读者的心灵深处,从时间向度,打开世世代代先后衔接继承的人的心扉;从空间向度,穿越地区、民族、国界、人种的疆域。”[8]38-44的确如此,优秀的艺术创作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八大的作品也是如此,审美情感的悖论式纠缠渗透了他的创作,在这巨大的张力中我们才能认清八大艺术的本来面目。
虽然张力说在文学领域被普遍运用,但它本身具有的辩证法基因照样可以使它在别的艺术领域生效。例如,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书中引入了张力论,将其定义为“把人类视觉、知觉捕捉到一幅作品中的两种相互对抗的力相互较量之后产生的后果”。[9]里奇拉克从美学的角度指出:“最典型的就是,人们发现,艺术经验要求一种‘对立的紧张’,因为,在这种紧张中经验的整体内涵着一些具有审美因素的内在冲突。”[8]38-44八大的创作就是在两种相互对抗的情感中完成的,这两种情感可以转化成一系列处于紧张对立的二项式,“了悟/不悟、出世/入世、生存叩问/家国哀痛”,因此把八大看作一个天生的悟道者和把他看成只是借诗画抒发愤懑的遗民艺术家一样不得要领,会造成对八大艺术创作的单向度解读。
这两种对立紧张的情感张力支配了八大的整个创作生涯,甲申之乱后,八大逃往西山(在南昌近郊),在顺治戊子剃度出家,师从弘敏,期间在南昌东南的进贤介岗灯社和西北的奉新耕香院礼佛,这样的生活持续到1647年弘敏圆寂。在这十几年里八大研习诗画以抚慰失国后的惶恐不安的情绪。在1666年创作的《墨花图》中有“白云自娱”“潇疏淡远”“耕香”等印章,八大借以显示自己在禅林中的逍遥淡泊。如果仅从这个角度解读,就会得出八大的作品一开始就有超凡脱俗的品质,这样的结论既不符合八大的创作事实,也无法解释临川其间的病癫和“驴期”的愤怒。其实遗民情感一直潜藏在八大心中,只不过在早年这两种情感的张力不够大,对持不够紧张而已,那首“灵苗茁有时”和“玉龙下天池”的自喻诗不就很明显地暗示了八大心中隐藏着一股复国的个人激情吗?
临川癫疾和出佛还俗,这两件事对八大的创作影响很大,强烈的遗民身份认同情感与叩问生存本真的智性思考之间不断搏斗,造成了八大身心的巨大撕裂。在临川期间,八大结交了许多带有强烈故国情思的文人,在与这些文人的往来唱和中,八大对自己遗民身份的认同感不断加强,并在《个山小像》中首次公开自己“西江弋阳王孙”的身份,并创作了不少表达个人身世感慨的诗歌。在时任临川县令胡亦堂修的《临川县志》(康熙十九年刊)中收录了八大的十首咏物诗,主题都是借临川故迹来抒发“身世浮沉雨打萍”的心绪。如在《金柅园》中写道:“白云红叶醉青霞,皂盖朱幡两门华。官酿葡桃川载酒,亭开金柅玉为茶。瑶琴几弄麻山雨,诗卷还携梦水涯。惆怅秋风茂陵客,到来惟见海棠花。”[10]30-38从诗中可以看出,虽然有皂盖朱幡、诗朋酒友,但仍抵不住八大的愁绪,像司马相如一样,是一个千里酸风茂陵客罢了。
这种愁绪在“驴期”得到了释放,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遒劲似利剑的《古梅图轴》外,八大还有很多诗歌和绘画都在集中表达个人激烈的情感,甚至写出“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鱼扫虏尘”这样直白显露的诗句。在《个山人屋花卉册》中,有一幅兰花图,画面仅有一丛兰花,如果仅从绘画语言解读,我们根本无法确定作者所要表达的内涵。所幸画上有题诗,解码后的文字便是图式意象的所指。诗云:“写竹写兰吴仲圭,兰何佩短竹叶齐?还家宋远思童子,卫适狂歌听马蹄。”诗写得极其隐晦,朱良志在《八大山人研究》中是这样解读的,他认为:“前两句以探问吴镇为引子,写竹兰同齐。‘还家宋远思童子’,用《诗经·卫风·河广》意:‘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八大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个在外漂泊的宋家童子,归心似箭。”[2]161由此可见,八大思念故国之情昭昭,但是这种激烈的个人情感并没有完全主导八大的创作,我们仍然能清晰地看到与这股愤懑情绪相互撕扯的另一股力量,一种与个人化情绪相对立的思考。例如,同是“驴”期的《瓮颂》,里面共收录六首诗,都是写酒。其一曰《毕瓮》,诗云:“深房有高瓮,把酌无闲时。焉得无闲时,翻令吏部疑。”[2]218此诗化用典故,讲晋元帝时吏部郎毕卓之事,他是生性好酒,在《世说新语·任诞》中有记载:“毕茂世云:‘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10]30-38前人常用“毕卓生前酒一杯,曹公身后坟三尺”来形容其嗜酒洒脱的气度,山人在此引毕卓的典故,怕不是无心为之吧。可以看出,在八大遗民情感最强烈的时期,这种愁恨情绪也没有完全遮蔽和压倒对生存本质的反思,正是由于这两种极端情感的张力状态才避免了八大的艺术滑入无节制的个人情感宣泄或者只是空洞的玄思,它提供了一种“综感(synaesthesis)”*“综感(synaesthesis)”是瑞恰慈、奥格顿、伍德三人合著的《美学原理》中提出的美的定义,借鉴了朱熹中庸的思想,认为“一切以美为特征的经验都具有的因素——对抗的冲突所维持的不是两种思想状态,而是一种。”认为真正的美是符合中庸的“综感”。的审美经验,一种感情反应的对立调和。
八大的写意花鸟和山水画在晚年的时候达到了化境入微的境界,这是后人公认的事实。八大晚年艺术创作水平的精湛不仅指笔法上的老道,更指作品艺术价值的稳定,保持稳定的原因正是他对艺术张力更加恰当而精妙的把握,能够更好地处理两种充满对抗、冲突、撕裂的情感。现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物馆的《安晚册》,是八大晚年的代表作品之一,全册共22幅,其中第13幅,整个图幅上只有一条小鱼,横卧在画面当中,画上题诗一首,诗云:“到此偏怜憔悴人,缘何花下两三旬。定昆明在鱼儿放,木芍药开金马春。”[11]定昆池、金马门、木芍药指的是皇家奢华繁盛的派头,这首诗的大意是,在繁华的定昆池边,牡丹竟放,池鱼欢跃,只有一旁观者独自憔悴。
从诗面上解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落寞憔悴的旁观者,在一宣盛一清冷的对比中自伤自悼,但实际上八大化用了袁中道的“君不见金谷地、定昆池,当时豪华无与比,今日红尘空尔为!”一尾悠哉逍遥的鱼,一首口是心非的诗,达到了张力十足的“反讽”效果。所谓反讽,则“是对假相与真相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无所知:反讽者是装作无知,而口是心非,说的是假相,意思暗指真相。”[12]八大佯装了一次“可怜人”,调侃了自己一回,“幽默感”十分高妙。表面的忧伤自怜,内里的冷峻幽默,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审美情感达到了圆润的结合,这无不得益于八大恰到好处的张力把握,把反讽技巧用得出神入化。类似的作品在八大晚年作品俯拾皆是,例如《安晚册》之二十《鹌鹑图》《鸟石鱼图轴》等。从历时性角度看,八大晚年的艺术创作比早年禅林时期和临川期间前后都要成熟,这和他作品内含的审美情感张力成熟程度相吻合,所以单从家国之痛或者生存叩问来解读,八大的艺术都是单向度的、扁平化的。
四、结 语
构图的反常规、意象的怪诞以及诗文语言的晦涩难解都是八大艺术的特征,但又不是其艺术审美价值的根本。八大并不是为怪而怪,更不是以晦涩为能事。作为组成艺术文本的材料和语言,它们以一系列能指符号来充当作品审美情感的表征,八大作品表象的“怪”在本质上是内层审美情感的“张力”,所以从家国哀思的个人愤恨或超越性的生命叩问角度都不能完整地把握八大艺术的审美情感实质,执其一端必然使得八大艺术面貌平面化,审美情感狭窄化。
[1] 贝尔.艺术[M].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2008:546.
[2] 朱良志.八大山人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3] 童庆炳.自我情感和人类情感的相互征服——论文学艺术中审美情感的深层特征[J].文艺理论研究,1989(5):20-30.
[4] 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11-12.
[5] 朗格.艺术的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6] 王国维.人间词话[M].彭玉平,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284.
[7] 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9.
[8] 金健人.论文学的艺术张力[J].文艺理论研究,2001(3).
[9] 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573.
[10] 朱良志.八大山人遗民情感的发展过程[J].美苑,2008(3).
[11] 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5:816.
[12] 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148.
(责任编辑:紫 嫣)
Emotional Tension In Zhu Da′s Artistic Works
LIANG Hong-an, ZHOU Ji-wen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Still imitated and held in esteem by many artists, the artistic works of Zhu Da, with their grotesqueness, have stood the test of time for more than 300 years. The reason these works still speak to lovers of painting across the centuries and have become classics is their artistic appeal. Meanwhile, the aesthetic emotion is essential to evaluating their charm and value. The aesthetic emotion in his works is not limited to his inexpressible nostalgia for his lost home and country, nor should it be elevated to a genuine contemplation and revelation of the truth of life.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we should approach the grotesqueness and absurdity in his artwork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tension of Zhu Da′s artworks produced i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his wandering life and the inquiry into the true existence of life.
Zhu Da; nostalgia for his lost home and country; inquiry into the true existence of life; emotional tension
2017-01-13
梁宏安(1989—),男,甘肃张掖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周纪文(1969—),女,山东菏泽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研究。
B83
A
2095-0012(2017)02-007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