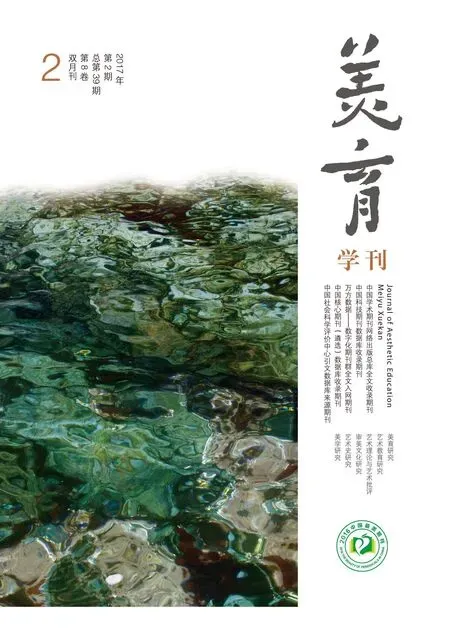慈禧太后的肖像画:Portrait与“圣容”
2017-03-24游佐徹著唐卫萍译宋武全校
[日]游佐徹著,唐卫萍译,宋武全校
(1.日本冈山大学 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2.杭州师范大学 艺术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慈禧太后的肖像画:Portrait与“圣容”
[日]游佐徹1著,唐卫萍2译,宋武全1校
(1.日本冈山大学 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2.杭州师范大学 艺术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经驻清公使夫人康格提议,美国女画家卡尔为慈禧绘制了肖像画。这幅肖像画先是被送往1904年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展览,后赠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慈禧而言,一方面这是向西方展示其权力的绝佳时机,同时也是一种重塑国家形象的政治外交战略。作为肖像画的“身体”由此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政治性。
慈禧;圣容;政治身体;权力
距郭嵩焘现身伦敦,并出现在古得曼画笔下25年之后,又有一位中国人端坐在西方画家面前。她在巨大的油画布上留下了自己的“化身”,此人便是西太后慈禧。这幅肖像画是在慈禧斥巨资为自己修复的舒适居所——颐和园乐寿堂绘制的。
慈禧之所以让西方画家经手制作肖像画,是因为清政府将参加次年,即1904年4月30日举办的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为一般通称,其正式名称是“纪念购得路易斯安那州万国博览会”。1903年是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100周年,美国为此举办了此次万国博览会。开幕式,届时肖像画须如约送到开幕式展出。
本文将对慈禧这一史无前例的奇妙举动*当然,众所周知,西洋画家们也曾为清朝的皇帝们绘制过肖像,但对清末来说,这可谓时隔久远。而且,慈禧在美国女画家卡尔(下文将会提到)为其制作肖像画之后,1905年又请荷兰裔美籍画家华士·胡博(Hubert Vos)为其作画。关于此次肖像画的绘制可参见邝兆江《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1期。及其产生的影响展开分析,同时对绘制肖像画的情况及其运送至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的过程展开审慎的考察。
绘制慈禧肖像画的缘由及经过,可从肖像画的提案者、画家本人及其周边人物的相关回忆和证言中获得详细的了解。
时任美国驻清公使夫人康格(Sarah Pike Conger)向慈禧提议绘制其肖像,并建议将之送往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展出。绘制肖像画的画家是康格的旧识——美国女画家卡尔(Katharina Carl)。康格和卡尔将其在中国的经历和记忆各自写成了回忆录:《来自中国的信》(LettersfromChina)[2]、《慈禧写照记》(WiththeEmpressDowagerofChina)[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肖像画的作者,卡尔留下了其独有的翔实记录。此外,还有德龄、容龄姐妹*德龄、容龄姐妹的父亲曾为驻法公使,她们从光绪二十五年到二十八年随父在欧洲生活。的回忆录:《清宫二年记》(TwoYearsintheForbiddenCity)*Princess Der Ling. 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New York, Maffat, Yad.1911.本书已由太田七郎、田中克己译为《西太后に侍して》(世界ノンフィクション全集,第18卷,东京:筑摩书房,1961年)。此外,井出润一郎摘译了《素顔の西太后》当中的两节。、《清宫琐记》*《清宫琐记》采用的是容龄、德龄《慈禧与我——晚清宫廷私生活实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收录版本。,此二人因有欧洲生活经历而成为慈禧的御前女官,也近距离地见证了肖像画的绘制过程。
还可参看有关此次肖像画绘制及展出的公开档案资料。幸而我们能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的《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中窥得相关资料的全貌[1]。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收录的仅与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相关的档案就达276件。
康格记录了慈禧同意让西洋画家为其绘制肖像画的经过:
数月以来,画报上刊载的太后漫画形象,已经让人出离愤怒了。这些漫画对太后的形象进行了可怕而又夸张的描绘。对此,我逐渐产生了一种要让世人看到太后真实形象的强烈愿望。因此,我期望获得太后的应允,能与之讨论制作肖像画的事宜。我给卡尔小姐写信,她表示乐于协助这项工作。觐见之日无疑是提案的绝佳时机……太后聆听了我的提案,表露出女性所具有的独特兴趣和顾虑,并提出了诸多疑问。最终太后同意了,承诺她为圣路易斯博览会而准备的肖像画将由一位美国女艺术家完成。肖像的绘制工作将从8月开始。[2]
康格提到的觐见之日是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1903年6月15日),后文也将提及,实际上康格从前一年的冬天便开始频繁地觐见慈禧了。
总之,康格感受到了慈禧的亲切之情。她试图将慈禧的肖像画作为理想的“身体”,以改善慈禧在西方世界被广为认知的负面视觉形象。
慈禧的形象提升战略,绝非仅仅出于康格个人的好意。考虑到康格作为美国公使夫人的身份,此提案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自1870年以来,随着美国排斥中国移民运动的高涨,清政府与美国的关系也随之起伏不定。而康格觐见慈禧并向其建言绘制肖像画的1903年,正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时间点,因为有效期为10年的“移民限制条约”(《清美华工条约》)将于这一年失效。
康格提案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包揽了肖像画的绘制与该肖像画在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的展出这两项任务。这一安排意味着并非等到肖像画绘制完成后再寻找展览场所,而是从一开始,康格就计划将肖像画在美国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展出。换言之,正是康格促成了慈禧的“化身”呈现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面前。
此时,人们的脑海中还残留着有关义和团战争的鲜活记忆。康格自然十分清楚,当时被视为蛮族统帅的慈禧以“真实”的姿态出现在文明世界的人们面前时,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意味。而且,肖像画的展示舞台并非西方某个微不足道的展馆,而是万众瞩目的万国博览会会场。
已有许多优秀的论著指出,博览会作为“资本主义的文化装置”和“帝国主义巨大的展示装置”,是一个极具现代性的“现世物”*即展示,译者注。空间。尤其是万国博览会,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作为其价值基准,推行殖民地统治的正当化,并以贯彻所谓“人类的展示”及社会进化论的意识形态为基本特征,而尤其将后一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3]
1904年的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同样也具备上述特征。随着美国对菲律宾和夏威夷的实际占有,其帝国主义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此次万国博览会在“将美国国家的‘帝国’意识推广到广大民众的集体意识层面,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
因此,康格的提案意味着,要将慈禧的“身体”置于以上述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优越性和正当性为前提而建立的世界秩序之中。是否可以认为,慈禧接受该提案,将自己的身体“呈现”在非特定而人数众多的外国人面前,这一行为本身也是基于一种政治考量呢?
要解答这个疑问,有必要考察以下两点:
一、慈禧此前有过将自己的形象直接呈现在特定而人数众多的外国人面前的经历。
二、当时的清政府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关于万国博览会的知识和经验。
首先看第一点。我们须意识到,康格的提案是在慈禧接见诸位外国公使夫人之际提出的。也就是说,在慈禧被众多外国人目光关注之时,又被宣告其“身体”*即肖像画,译者注。将接受更多外国人目光的关注。
事实上,自清政府承认西方列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制定的国际秩序以来,对于西方诸国(后来也包括日本)提出的派遣外交使节觐见皇帝的要求,清政府一贯采取拒绝的姿态。但这一态度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发生了转折:清政府迫于列强各国的压力,同意在皇城西苑的紫光阁接见各国外交使节。此后这一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了,但清政府对列强的要求始终不予积极回应。促使这一姿态发生重大转变的是因处理义和团战争而与列强缔结的《辛丑条约》(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该条约明文规定(条约第十二款)了觐见方法的变更,相关细节也以附加条款的方式确定了下来。*鸦片战争后清朝有关觐见的事宜可参考李岫《〈辛丑条约〉与晚清外使觐见》,载《北方论丛》1991年第2期;秦国经《清代外国使臣觐见礼节》,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2期;王洪运《论外国公使觐见清帝制度的确立》,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田涛《同治时期的觐礼之争与晚清外交近代化》,载《历史教学》1999年第7期;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第4至7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随着条约的缔结,慈禧决意向列强求和,走改革路线。她从避难之地西安返回京城的途中,下发了一道皇帝接见外国公使,而自己接受公使夫人觐见的懿旨。*《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第490卷记载:“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一月,甲申。又谕,朕亲奉皇太后懿旨,国家与各友邦讲信修睦,槃敦联欢。现在回銮,京师各国驻京公使,亟应早行觐见,以笃邦交而重史事。俟择日后,皇帝于乾清宫觐见各国公使。其各国公使夫人,从前入谒宫廷,极称款洽,予甚嘉之。亦拟另期于宁寿宫觐见公使夫人,用昭睦谊。著外务部,即行预备,请旨定期,一并恭录,照会办理。”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2年2月1日),慈禧在紫禁城养性殿接受各国公使夫人的觐见,这也成为慈禧与康格等人其后多次会面的开端。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1903年6月15日),慈禧在接见各国公使夫人之际,康格进谏了上文所述的肖像画提案。*《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第492卷记载:“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二月,乙卯。上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御仁寿殿。美国使臣康格及其夫人等觐见。”
从“国家与各友邦讲信修睦、槃敦联欢”*同⑩的记述中可以断定,慈禧接受觐见的行为是十分明确的政治决断。慈禧将以往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她十分清楚要将自己的“身体”送到外国人面前。
慈禧同意肖像画的提案也可放在上述背景下来理解。其实慈禧对于将自己的“化身”呈现在非特定而人数众多的外国人面前的抵触感,从一开始就由于政治原因而软化下来。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深谙在“看”与“被看”这一组关系中存在植入了的“政治”的西方人,与单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看”与“被看”的关系而置身其中的非西方人之间,彼此心照不宣,共同促成了慈禧肖像画的产生。
再看第二点。慈禧是否意识到其“化身”之旅的目的地正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力量交织的政治空间?
有关清政府与万国博览会关系的研究,可谓成果颇丰。*清朝与万国博览会的关系可参考以下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晚清赴美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史料》,载《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董增刚《晚清赴美赛会述略》,载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铃木智夫《万国博览会与中国——1851—1876》,载《人间文化》第11号,1996年;楠元町子《万国博览会与异文化交流——以1904年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为中心》,载《异文化交流研究》第5号,2002年;久本明日香《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与清末中国》,载《宁乐史苑》第49号,2004年;楠元町子《万国博览会与中国——以1904年万国博览会为中心》,载《爱知淑德大学现代社会学部论集》第10号,2005年;久本明日香《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的娱乐街「パイク」》,载《人间文化研究科年报》第22号,2006年;楠元町子《从国际关系史看万国博览会——以1904年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为中心》,载《法政论丛》第43卷第2号,2007年;马敏《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载《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汪岳波《晚清政府参加国际博览会述略》,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赵祐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1866—1911)》,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1997年,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2年;王正华《呈现“中国”:晚清参与1904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之研究》,见黄克武主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视觉文化表述与文化构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语所,2003年。研究显示,中国的产品“自1851年第一次伦敦万国博览会以来,就常常出现在万国博览会的展台上”。另外,清政府自1866年正式受邀参加次年即1867年第二次巴黎万国博览会以来,就不断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博览会,包括万国博览会的邀请,但清政府一直避免积极地参与。按照此前的惯例,“作为海关长官的总税务司赫德受清政府委派,负责万国博览会以及各种国际性博览会的一切相关事务。”*参见铃木智夫《万国博览会与中国——1851—1876》,载《人间文化》第11号,1996年。但随后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再加上清政府对博览会的制度以及对参加博览会意义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如从“炫奇”到“商战”,从“邦谊”到“商利”),进而对参加博览会的标准和条件制定了明确的条文[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制定的《出洋赛会通行简章》二十条],由此清政府重新调整了对博览会和万国博览会的定位*参见赵祐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1866—1911)》,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1997年。。
可见,清政府一直与万国博览会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接触,也由此积累了与之相关的知识和经验。
而为了参与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清政府投入75万两白银的巨额经费,举官民之力倾力参与,更指派一名宗室贝子(清朝皇族的一种爵号)溥伦率正式使节团前往。清政府积极参与此次国际盛会,对其重视程度可谓史无前例。据说慈禧亲自干预了参加万国博览会的决定,对此次盛会表现出强烈的关注。*董增刚《晚清赴美赛会述略》,载《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此外,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三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给庆亲王奕劻的复函中写道:“总税务司”赫德为申复事,奉到十一月初一日钧劄内开,查美国将于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即中历光绪三十年,在散鲁伊斯城开设万国博览会……此次拟请旨简派正监督一员,并本部拣派副监察二员。惟副监察二员内,应用税务司一员派此充任,尤以美国人为合宜,相应劄行总税务司、即于各关税务司美国人中择一精细妥实之员、开具衔名迅速申复本部,以凭奏明派往等因。奉此遵即于现任税务司中拣……东海关税务司柯尔乐,美国人,尚属精细妥实,该员在关已阅二十二载……。”(《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收录)根据这段回复可知,总税务司要从海关抽调人员。本文所记关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处理与博览会相关事务的这一惯例的延续得以确认——这名被抽调的副监督官是美国人卡尔,他就是为慈禧画像的(在这里确切地说,是将要为慈禧画像)的画家卡尔的兄长。
这就意味着,慈禧(包括其周边的人)不仅清楚地知道肖像画将去往何处,也非常清楚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是何种性质的盛会。也可断言,慈禧(包括其周边的人)在接受康格提案时就清楚地意识到,其肖像画将在异国被大众的目光打量。
以此为前提,进一步追问慈禧对其肖像画的理解及其是否包孕政治性含义,就能解答上述问题。
为此,我们不妨再次回顾此前提及的回忆录和证言,以此管窥在绘制肖像画的过程中,慈禧做出的政治决断及其所要表达的政治诉求。
慈禧接受康格提案时的情景,德龄留下了一段夹杂着解说的回忆:
尽管我向太后解释了一切,但我知道她并不清楚何谓肖像画,毕竟当时太后连照片都还没有拍过。我必须说明,在中国,人们只会为死去的人画像,以纪念死者,供后世子孙祭拜。我注意到,当时太后听到该提案时多少有些震惊。[4]
这段记述中还有一个注目点,即慈禧与照片的关系,后文还会提及。读完这段文字,首先就会联想到郭嵩焘看到自己的肖像画时的反应。当然,他的姿态非常清晰,是英国画家虚构出来的。但对中国人来说,这种将肖像画与“死亡”关联的民俗文化情感还一直延续着。
然而,康格的回忆以及现存的慈禧肖像画表明,慈禧果断地摆脱了中国民俗文化的魔咒,下定决心绘制自己的肖像画。
一旦做出决定,慈禧就对画家的创作提出了各种要求。具体的要求和当时的情形,可参看卡尔和德龄的回忆录:
太后期望的是,无论如何,必须是一幅巨大的肖像画……[5]
这幅画要送往美国,我不希望那里的人认为我的脸是半白半黑的。[4]*此处为卡尔引用慈禧的原话,译者注。
我刚刚在新工作室安顿下来,太后就迫不及待地让我再作一幅肖像画。而且这幅画要足够大,要能够容纳随驾之物(包括雉扇、三折屏风、九羽凤凰、天竹)、堆积如塔锥的苹果,这些都是具有寓意或是象征性的物品。[4]
画像刚刚开始,我就遇到了“王座”的问题。太后的王座是其子同治帝所献,在义和团战争中“丢失”了。但太后认为可以通过描述以及见过此王座的宫廷画家所绘制的草图进行复制和再现,而我并不满足于按照人们的记忆或者其他画家的草图来创作,只能“退而求其次”(faute de mieux),绘制另一个深得太后喜爱的用柚木雕刻的王座。[4]
福柯写道:“传统观念认为,权力是可见之物,自我展示之物,自我夸耀之物。”[6]这一观点应用到慈禧身上非常贴切。摆脱了肖像画与“死亡”关联的阴影的慈禧,专注于展示自己绝对的权威和无上的权力,想必也乐于见到其理想的“化身”早日完成。
而另一方面,试图按照西方美术思想和创作技巧来塑造理想的慈禧形象的卡尔,常常陷入困惑之中。她在回忆录中吐露了这种心情:
随着肖像画绘制工作的推进,我发现自己不断地陷入与中国绘画的传统习惯相冲突的局面中,他们追求细节的丰富而又不能出现阴影。如果只考虑太后个人的意愿,依照她的艺术眼光和开明态度,我会拥有更多的创作自由。但太后也不得不遵从传统,天朝皇太后的肖像容不得半点想象。遵从严苛的传统是第一要务。[5]
确如卡尔所言,慈禧固守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和绘画样式(她在后宫组织了一个称之为宫掖画家的女性画家团体,自己也提笔作画,据说达到了一定的造诣和水平)*关于慈禧对绘画的关注及其绘画作品与宫掖画家的关系,可参见李湜《晚清宫廷绘画》,收入吕成龙主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慈禧执意要把象征皇太后权力的种种仪仗,也包括同治帝赠送的、显示其权威正当性的王座描绘在肖像画上。所以,最终完成的油画肖像的上部中央位置刻有象征其长期执政的称号——多达16字的匾额,*关于慈禧称号的形成过程可参见万依《关于慈禧太后的称号》,载《文献》1986年第2期。慈禧太后拥有的16字称号在其死后又前后加了9个字,她拥有在清朝历代皇太后之中最长的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并在匾额的两端钤阴、阳方印各一枚。在卡尔眼中,这些做法*参见李湜论文《晚清宫廷绘画》及《慈禧款绘画及宫掖女画家》(《故宫文物月刊》第16卷11号,1999年。)中指出了慈禧在自己的作品(包括代笔)上的署名(款题)、押印(钤印)的样式特点,能够确认与卡尔所作的肖像画上的处理有一定的关联。或许只能理解为令人费解的东方世界的王朝文化了。
我们显然无法简单地赞同卡尔最后的结论。因为前文已经提及,慈禧敢于打破悠久的民俗文化传统,将自己的“化身”送到万国博览会展出。而万国博览会正是世界各国汇聚一堂,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方面相互博弈、讨价还价的场所。
卡尔将慈禧对肖像画的要求,视为一个开明专制君主提出的要求,而实际上恐怕也有必要理解为慈禧的高超政治手腕。
换言之,慈禧对其“身体”的管理乍看起来给人以保守、刻板的印象,但实际上偏于开放的外向型。也就是说,慈禧正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让他者看见自身,由此而意识到他者观看的目光——这种自觉的意识充分印证了福柯“权力是可见之物,自我展示之物,自我夸耀之物”的观点。
对卡尔而言,慈禧的种种要求构成了绘制其心目中理想肖像画的阻碍。但在慈禧看来,这些要求是为了绘制出具有政治意义的理想“身体”的必备条件。
对慈禧来说,将自己的肖像画送到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展出,无疑是向其他强权夸耀自身权力的绝佳时机。而权力这个终极伙伴也促使她在这一特定时期做出了又一个政治决断。
卡尔完成肖像画后,离正式宣告完成还有十几天时间,慈禧邀请康格和其他各国的公使夫人、领事夫人一道提前观赏画作,康格写道:“太后提出要将肖像画送到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展出,其后将之赠送给美利坚合众国政府。”[2]
也就是说,慈禧告诉驻清公使夫人康格,这幅肖像画的最终目的地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实际的情形是,肖像画在万国博览会会场中心的第18展示室“美术宫”展出[7],在半年展期内接受大众参观。1905年1月15日,万国博览会闭幕,该肖像画被送往白宫,在罗斯福总统的见证下正式赠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画像即将完成之际,即光绪三十年二月三十日(1904年4月15日),外务部向在圣路易斯的溥伦发出指示,展期结束后,将该肖像画赠送给美国:“榷算司呈为咨行事,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内廷口传现在恭绘皇太后圣容告成交外务部,袛领饬总税务司敬谨寄至美国,即由赴美赛会正监督恭迎至散鲁伊斯会场俾共瞻仰,俟该监督观会事毕,应令出使美国大臣转达总统、敬谨赉送美国国家等因。除照会美康使转达美政府外,相应咨行贵正监督,大臣钦遵可也。须至咨者。”见《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之后肖像画赠呈之事便依此指示实行。
尽管慈禧的这一安排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绝非一时兴起做出的决定。
不妨再来参看卡尔获准进入紫禁城内慈禧的寝宫时,出于好奇所做的观察记录。
卡尔发现,在慈禧寝宫墙壁的显眼位置,悬挂着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家族的肖像画。
在显眼的位置悬挂着两枚巨大的铜版印刷画,左右两侧的吉旗对称排开。其中一幅是身着盛装的维多利亚女王,另一幅则是被儿孙环绕的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5]
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肖像画为何会出现在慈禧的私人空间,又如何变成此处的装饰物*根据德龄的说法,慈禧十分关注外国报纸刊载的新闻以及路透社的电文。通过前者可了解尤其是欧洲各国国王的动向(见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XVII. The Audience Hall),而且慈禧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知识十分丰富,据说她也阅读了女王传记汉译本的一部分(见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XIX. The Sea Palace)。,但至少可确认以下两点。
第一,使用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家族的肖像画、肖像照片装饰房间的做法在当时并不罕见。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在插图新闻和照片流行并被大量消费的时代,登上大英帝国王位的首位国王”,面临着其政治影响力逐渐减弱的现实。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本人在国民眼中的形象,对于君主制的存续至关重要”,因而他们采取了各种提升形象的措施。将女王的肖像设计在流通广泛的货币和邮票上,修缮和扩建白金汉宫,举办中世纪风的假面舞会等等,这些都是为提升皇室的形象而服务的。其中,王室尤为重视“以王室肖像画来传达信息”,期望能够达到这样一种效果:“皇宫到处都装饰着肖像画,随着日后肖像画的市场商品化流通,普通民众在自己家里就能直接‘观看’女王的肖像所传达的信息。”
由于“日臻兴盛的插图新闻、照相技术与随之产生的大量的消费需求的共同推动”,这一策略不仅远远超出了王室当初的预期,还产生了扩散效应。*见川本静子、松村昌家编《ヴィクトリア女王——ジェンダー·王権·表象》(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年)第2章《笑わない女王 ヴィクトリア——“王室肖像画像”再考》(谷田博幸)。可以认为,装饰着远东统治者居室一角的维多利亚女王肖像,正是承担其政治使命的众多“身体”当中的一个。
还有更为重要的问题:这两幅肖像画为何会出现在紫禁城的皇宫之中?
现代外交制度建立以后,西方世界延续着过去宫廷间的外交形式,将互赠元首的肖像画、肖像照片作为国家间友好关系的象征。而且,这种外交礼仪也随着“现代”的扩张而渐渐波及非西方世界。例如日本从明治六年(1873年)开始,就将明治天皇的肖像照片赠给“来访的外国人,特别是以皇族和元首为代表的国外政要及驻日外交官等”*参见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第四章《御真影の誕生》,岩波新书,1988年。,这便是新兴国家遵循这种外交礼仪的一个范例。由此看来,装饰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私人空间,也正是紫禁城里的维多利亚女王肖像承担的又一重要政治职能。
当然,至少可以说,在卡尔创作肖像画的过程中,慈禧对肖像画的政治意义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因为在同一时期,慈禧已经与除英国之外的各国外交官、皇族互赠了肖像照片。*根据容龄的回忆录记载的“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又据《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所记录的“八月二十日”(1903年10月10日)可推定,当年8月慈禧在接见俄国公使夫人普朗森时,从公使夫人处获赠了沙皇和皇后的照片。参见林京编著《故宫藏慈禧照片》,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据说,当时慈禧一接过照片,马上就向普朗森夫人出示了沙皇通过俄驻清公使赠送的一模一样的沙皇和皇后的照片(见《清宫琐记》15,俄皇赠照)。当时充当公使夫人翻译的德龄也留下了关于这件事的记录(见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IV. A Luncheon With the Empress, V.An Audience with the Empress)。另有左远波《清宫旧影珍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所记,不知照片新旧,目前故宫博物院还藏有这位俄国沙皇和皇后的照片。另外,也有慈禧赠送其肖像照片的例子,1904年,她委托正在中国访问的德皇威廉二世的三皇子阿达尔贝特将自己的照片转交给德国皇后。见《中国摄影史1840—1937》第3章(胡志川,马运增主编,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
由此就能解释慈禧将其肖像画赠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根本原因。而且,从这时起,慈禧的肖像画就从单纯理想化的个人“身体”,变成了清政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需要的政治“身体”。
以上的分析表明,映入卡尔眼帘的维多利亚女王包含了两个“身体”:一个是随大众社会的到来及复制技术兴盛而产生的“身体”;另一个是在国际政治领域代表着国家和权力的“身体”。拥有这两个“身体”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庞大的紫禁城内占据一隅。而在这两个“身体”之中,慈禧显然对后者更感兴趣。她绘制了自己理想的“化身”,并将之送往国际政治的舞台。
无疑,这是中国人理解身体与政治关系的划时代事件。中国人也能赋予身体一种新的政治性,或者说发现这种政治性。然而,慈禧发挥的作用并不仅止于此。她在不知不觉中,也创造了类似维多利亚女王的另一个“身体”,即为大众社会及复制技术所塑造的“身体”。
对此,还可根据慈禧拍摄的肖像照片来验证。德龄在回忆中曾经提到“太后此前从未拍摄过照片……”不过,就在德龄还对肖像画的绘制能否实现心存疑虑之后不久,慈禧就拥有了自己的肖像照片。
慈禧的新“化身”,也是由现代视觉技术创造,并在大批量复制成为可能的前提下实现的。而我们不再从艺术品而是从物的属性来看待肖像画的话,也能从中解读出“身体性”。
中国人称慈禧太后的肖像画为“圣容(也称为御容、慈容)”,“圣容”当然首先是一幅肖像画,但也意味着,与肖像画相关的一切都具有了“圣”的性质。很显然,人们将“圣容”与它的原型人物一视同仁——也正因为如此,肖像画在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中能够成为人们对死者的寄托。卡尔所绘制的“portrait”,已经被当成是慈禧本人或是她的“身体”来看待了。
对此,同样可从与慈禧肖像画有关的回忆、证言、档案等资料中获得证明。
下面这则材料屡被研究者引用,这是卡尔回忆录的开头第一段:
我们觐见的时间被安排在十点半,开始为太后绘制肖像的时间则安排在十一点。这是太后首次画像的吉时。这个时刻、这一天,乃至这个月份都是经过反复查阅历书后精心挑选出来的。[5]
可见,慈禧“圣容”的绘制,绝非单纯的绘画工作,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展开的一项特殊的任务。
通过查阅历书选取时间,是一种占卜之术,也就是所谓的“择吉(择日)”。具体而言就是综合考虑历书(时宪书)上记载的天文、地理、神煞(掌管吉凶的神灵)等各种信息,来测算未来行为、行动的吉凶、祸福的占卜技术,在宫廷和民间都被广泛地使用。这种占卜之术可理解为是一个既受皇权支持,同时也将皇权推行至全天下的制度。*“择吉”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有关择吉之术的全貌可参阅刘道超、周荣益《神秘的择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关于“择吉”与皇帝权力的关系,可参阅川园秀城《“正朔”を頒つ——皇帝による暦の管理》(见佐藤次高,福井憲彦编《ときの地域史》,东京:山川出版社,1999年)。这就意味着,卡尔基于西方美术技法进行的肖像画创作,恐怕从一开始就统摄在大清帝国皇帝的权威之中了。
既然肖像画制作开始的时间有特别的规定,其结束的时间当然也不例外。据卡尔称,宣告肖像画完成的时间经过“择吉”之后,定于光绪三十年三月五日(1904年4月19日)四点之前。*卡尔在回忆录中记述:“咨询历书后确定,肖像画在4月19日下午4点之前完成是最吉利的。”见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XXXIII. Continuation of the St. Louis Portrait。卡尔当然遵从了这一规定。
被要求在“特定的时间”制作肖像画的卡尔,没过多久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项“特殊的任务”:
肖像画从制作伊始就被视为圣物,正如虔敬的祭司对圣杯深怀敬意一样。甚至连我的绘画材料也被赋予了某种神圣性。太后感到疲惫时,宦官便会拿走我的画笔和调色板,然后从画架上取下画像,恭恭敬敬地送往指定的房间。[5]
“圣容”就如同慈禧本人,受到恭敬地对待。这并非比喻性的修辞,而是实有所指,意味着“圣容”真的被当作有血有肉的“身体”来看待。
对此,还可从“圣容”完成之后被送往圣路易斯之际所采取的措施当中获得印证。在容龄的回忆录中有相关记述:
慈禧下令运送画像时,必须立着放,不准横放和倒放。伍廷芳议论说,运到上海这一段可以如此实行,但从上海出口之后就没有办法了。为了执行慈禧的命令,把画像从颐和园一直抬到车站,火车有顶棚放不下,只好放在敞车里先送到天津再运往上海。[8]
还有一种说法,为了运送“圣容”,从外务部到正阳门特意铺设了一条专用铁路。因为若用人工搬运,用手担负画像前行的样子看起来就像送葬的队伍,这是慈禧尤为忌讳的。[9]
“圣容”的出发仪式肃穆庄重,就像慈禧本人亲赴国外一样。根据卡尔的记述,着盛装的外务部官员和京城显宦将“圣容”送到车站。*卡尔记:“外务部的官员和北京的高官们着盛装抵达车站为这幅神圣的肖像画送行,它将要经过漫长的旅程到达圣路易斯。”参见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XXXIV. Finishing and Sending off the Portrait。据为肖像画送行的外务部官员那桐“光绪三十年三月六日”(1904年4月20日)日记:“卯正到外务部,花衣補褂跪送皇太后所画圣容,辰初归。”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像这种将“圣容”视为有生命的人而进行的迎接和送行仪式,在“圣容”接下来的“旅途”中还在不断上演。
可从当时的新闻报道中窥知具体的情形:
光绪三十年三月七日(1904年4月22日)《大公报(天津版)》“中外近事”一栏报道:
迎接御容。昨纪皇太后御容过津一则。兹闻袁宫保率同阖城印委文武各官、皆穿花衣補褂、于昨日下午二点钟齐集新车站茶座俟火车、到时恭接恭送云。*参见《大公报》影印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83年。
光绪三十年三月十日(1904年4月25日)《申报》报道:
敬迓慈容。昨日……皇太后慈容、由新济轮船敬谨赍送来沪。午前钦命议约大臣吕海寰尚书、会办电政大臣吴仲怿侍郎……同乘海定轮船至吴淞恭迓。迨抵金利源码头、各官恭请圣安毕、排齐卤薄、送至城内万寿宫敬谨供奉、侯美公司某轮船。出洋时派员送至美国圣路易博览会、恭悬以慰海外人民瞻仰之意。*参见《申报》影印版,上海:上海书店,1982—1985年。
据说,如此兴师动众的送迎仪式,在“圣容”到达美国后仍在继续。对此,可从时任清朝驻美公使梁诚送外务部的书简判断:
光绪三十年五月四日(1904年6月17日)驻美大使梁诚致外务部丞参信函……适接金山总领事电禀、沈道恭奉皇太后圣容由金启程不日可到。诚即随伦贝子驰回会场、一面订定专车前往迎迓、一面商妥会场总理佛兰息士等择定美国国家画院正厅为恭奉圣容之所。二十九日傍晚、专车行抵散鲁伊斯、先经诚等布置借用会场铁轨、三十日直送至画院门首。其时佛兰息士及各总办执事人等均具礼服随同。诚等督率夫役数十名、经历五时之久、敬将圣容奉入厅事。当中悬挂时已子夜、中外男女翘首瞻仰、皆以幸得瞻就云日、为希有之遭逢也。[1]
显然,梁诚在描述外国人对“圣容”的反应时,语气稍微有些夸张。
在中国人眼中,“圣容”等同于慈禧真身,无论将其视为何种神圣的存在,都在情理之中。然而在外国人眼中,这不过是一幅肖像画而已。对此,卡尔冷静而透彻地分析道:
数日之后,悬挂着太后肖像画的美术宫开始对公众开放,肖像画第一次失去了其从绘制以来就被赋予的半神圣的属性。只有在此时,它才重新获得了其作为肖像画的品质,真正成为肖像画作品中的一员。同样也是第一次,当它和博览会上其他所有的作品一样成为被品评的对象时,它才真正成为普罗大众观赏的对象。然后,它才真正向那些低俗目光的打量以及嘲笑者的评论敞开。[5]
确如卡尔所论,慈禧肖像画的魔法解除了,它经受着各式各样目光的注视与打量。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G].扬州:广陵书社,2007.
[2] CONGER S P. Letters from China: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Empress Dowager and the Women of China[M]. Chicago: A.C.McClurg&Co,1909.
[3] 吉见俊哉.博览会的政治学[M].东京:中公新书,1992.
[4] Princess Der Ling. 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M].New York: Maffat,Yad,1911.
[5] CARL K. 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M].New York: KPI,1986.
[6] フーコー.監獄の誕生——監視と処罰[M].田村俶,译.东京:新潮社,1977.
[7] 王正华.呈现“中国”:晚清参与1904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之研究[C]//黄克武.画中有话——近代中国视觉文化表述与文化构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语所,2003.
[8] 容龄,德龄.慈禧与我——晚清宫廷私生活实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9] 左远波.清宫旧影珍闻[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刘 琴)
The portrait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Portrait and "Sacred image"
Toru Yusa1, tr. TANG Wei-ping2, rev. SONG Wu-quan1
(1.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kayama University, Okayama, Japan; 2.Institute of Art Education,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Proposed by the wife of Ambassador of United States, Sarah Pike Conger, the American artist Katharina Carl finished a portrait for Cixi. The portrait firstly sent to 1904 St.Louis World′s Fair for exhibition, then as a gift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Cixi, the making of the portrait means a chance showing the political power to the western country, meanwhile as a strategy to rebuild the image of Qing government. The portrait as the "body" was endowed with a new political character.
Cixi; Sacred image; political body; power
2017-02-03
游佐徹,男,日本北海道人,日本冈山大学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文学部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研究;唐卫萍(1984—),女,湖北荆门人,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艺术史、文艺理论研究;宋武全(1981—),男,黑龙江梦北人,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日本冈山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日本近现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主要从事芥川龙之介研究。
J22
A
2095-0012(2017)02-006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