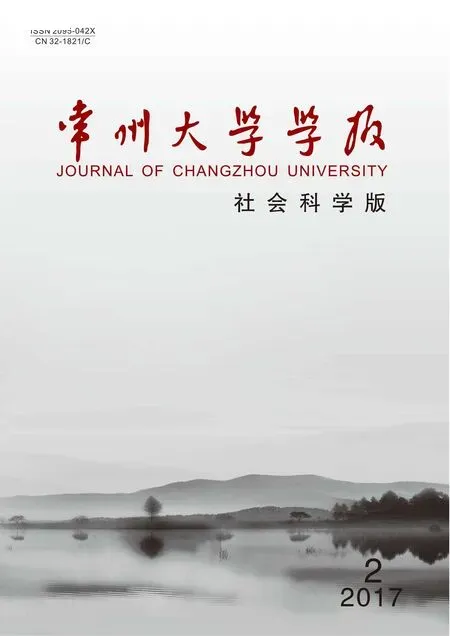西方选举制度的经济哲学解读
2017-03-24段周燕
张 斌,段周燕
西方选举制度的经济哲学解读
张 斌,段周燕
商品化时代的来临为新兴资产阶级寻求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通约提供了可能,社会契约和自由平等思想的本质基础在于私有财产权,对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的确立为西方选举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新财富观的资本至上及其逻辑是西方选举制度形成的重要支配力量,也是西方选举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全面认知西方选举制度离不开对其诞生的经济哲学基础的解读,这也是对整个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困境揭示与批判的重要思路。
选举制度;资本主义;商品化;经济哲学;私有财产权;财富;资本
随着闹剧式的美国总统大选帷幕的降落,人们在反思美国社会发生巨大裂变的同时,也对以西方选举制度为代表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衰败进行了不断深入思考,无论是以福山等为代表的学者,还是诸如《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等知名媒体无不对西方民主出现的“新”问题感到忧心忡忡。事实上,西方选举制度暴露的问题并非是“新”问题。恰如郑永年所指出的那样:“在西方,近代以来一直就是资本主导政治的,而政治则是对资本逻辑的反应。”列宁早就这样判定,即“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整个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1]。立足经济哲学的方法论视野可以助推我们对西方选举制度的深入分析和有力揭示,从而为全面把握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提供新的认知资源。
一、商品化:西方选举制度形成的时代背景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正是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前提,商品化时代的来临为建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切可能的资源,作为其主要表现形态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等由此孕育而生。
(一)商品的普遍化与新兴资本家的形成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萌发与成长。封建制度的逐步解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商人阶层和新兴资本家的初现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元素。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城镇再次兴起,封建性质的手工小磨坊出现。市场的扩大、需求量的增加、特许权和特惠权兴起等因素让许多小作坊渐渐冲破行会的限制,扩大了生产规模。在竞争原则的控制下,部分作坊的行东获得了较多的财富,成为了最早的资本家,而他所雇用的学徒、帮工则逐渐演变为雇用劳动者。经营不善破产的行东连同自己的帮工学徒一并成为另外较富裕行东的雇佣者,由此手工工厂和较大的资本家出现。城镇商业的繁荣,造就了一批深谙市场且拥有一定货币的商人,这些商人通过对商场销售渠道的了解,通过低价购买小生产者产品的方式成为了包买商。随后,包买商经营形式进一步变化,他们通过雇用小生产商,进行原料的加工,并且通过对市场营销渠道的控制,控制着小生产商,然后将分散的小生产商集合起来,形成了手工工厂。至此,包买商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资本家,同时,他们的出现使得原先分散、简单协作的手工工厂转化为集中的工场手工业。除了这些,个别城乡的个体手工业者通过在独立的竞争领域获得了经营利润并成为资本家,而破产的手工业者则成了雇佣工人。封建主本身也向市场经济制度中的资本家身份转化。市场经济的兴盛带来了分工水平与规模经济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与农村封建强制经济相比起来越来越高的经济效率,这也诱发了封建主对市场经济的参与,部分封建主可能变卖土地后直接参与城市工商业,其身份也直接转化为城市中的资本家,而另一部分封建主则可能将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或自己成为农业资本家进行资本主义式(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性质)的农业生产。这种景象为斯密后来所描绘和总结:“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相当限度内,一切人都成了商人,同时,社会本身亦就成了所谓商业社会。”[2]可见,商品普遍化助推了新兴资本家的普遍形成,在一切人成为商人的意义上说,商品普遍化与新兴资本家的形成是一体化的过程。
同时,新阶层的出现使封建原有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壮大与定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形成的初期就展现了它与众不同的一面,即成为力推商品化浪潮的强大动力。在15—17世纪,新生资本主义迫切需要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地点,直接导致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而这反过来又促进西欧国家进一步开拓原料市场和商品交易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发展。自由贸易及在此基础上催生的殖民主义帮助新兴资本家获取了巨大的财富,积累了原始资本。商品的普遍化促进了市场及市场机制的发展与日渐完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竞争机制,市场化体系预示着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最终完成,也标志着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基本形式。商品普遍化塑造了经济自由的信条,而新兴资本家的出现则不断对这个信条进行强化,直至使其成为新型政治制度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
(二)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深度勾连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型的历史进程有着与前时代生产关系形成的共性,更有着与前时代生产关系形成期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颠倒。“政治统管经济的顺序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标志,现在它要求颠倒顺序,让政治服从经济。”[3]这种变化在理论上的回应犹以斯密“富国裕民”的新国家观构建为标志。“分辨前工业国家和现代工业国家最有效的办法是以汲取(财政努力)作为国家能力的最有用的指标。”[4]商品化时代的来临,使得新兴资本家的财富呈几何式增长,渐强的经济实力势必会要求政治上的权力。事实上,政治权力一开始便是新型资产者所觊觎的“宝贵财富”,从一个贵族称号的标签获得开始,新兴资产者凭借手中积累起来的资产特别是通过货币的通约功能愈加灵活地操纵权力,进而获得对政治领域的全面渗透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以更好地进行资本积累,最终获得全面统治。
新兴资产阶级追求政治权力的斗争旗帜是自由、民主、人权,内容指向则是打破贵族血统限制,争取选举权和参与享有国家治理的权力。资产阶级追求政治权力所采用的策略和方法则是多元的。对封建王权,资产阶级运用疏通、购买及武装斗争等形式实现经济对政治的渗透,而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充分运用财富的杠杆来约束、限制、控制无产阶级对经济、政治权力的获得。历史证明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是克服双向的、双重困难而立足的。一部资产阶级的“斗争史”,也是封建王权的“衰败史”,又是无产阶级的“突围史”。
二、财产权:自然权利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本质
商品化时代背景下,新兴资产阶级对于摆脱封建(神学)统治,掌握政治权力的渴望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达到高潮。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从自然权利出发,把个人私有财产权利与政治权力相联系,将财产权利嵌入到政治制度设计的框架中。作为一切政治制度建构的前提与基础,作为一切权利背后的权利,私有财产权利的确定对于资产阶级权力观的形成与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确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自然权利与个人私有财产权利的链接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确立,使得支配着物质资料生产的资产阶级必将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理论家利用在私有财产权利基础上形成的近代“自然权利”和“自由平等”思想实现了政治自由在口号旗帜上与经济自由在利益本质上的互通。“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思想体系始终具有经济属性,那些最后演变为经济理论的资产阶级言论构成了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3]
源自自然法的自然权利是近代欧洲启蒙思想的理论起点,在界定社会、国家与政府的关系中,自然权利更是其主要理论基础。在霍布斯和洛克的国家学说中,自然权利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霍布斯认为国家政府甚至道德与法都是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在自然状态下,权利的尺度就是利益”[5],所以国家政府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保证人们的私有财产权不被侵犯。霍布斯强调,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就是无休止地追求个人利益,而自然权利正是人们获取自己的一切的一种权利。洛克与霍布斯的契约思路与设计不同,但所秉持的立场却是一致的。洛克认为自然权利就是保护人们私有财产权的权利,国家或政府以订立契约的方式成立是人们将这一种自然权利同意交付的结果。我们不难从他们的自然权利与契约理论中看出,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个人,而不是神权或者王权,这一切理论的转换与演变,均来自于当时社会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契约行为在商品交换中出现,商品经济若想得到发展和繁荣,市场经济发展的各要素若想要得到持续、完善的发展,就必须要创造适宜其生存的条件,建立一套与之适应的制度体系。源于商品经济活动中的契约行为原则被资产阶级理论家所提炼和升华,创立“社会契约论”,用于指导人们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确立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总体上,这种以自然权利为论证起点的社会契约理论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王权,确立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一般的政治研究逻辑中,社会契约只与政治权力相关,事实上,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有一个主要的前提预设即抽象的人性论和财产权保护。而后者更是其核心和本质所在。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构造中,人性论最终被财产权所置换,只不过,这种置换是以更隐蔽的、合法的方式实现而已。
(二)自由平等思想传播的经济权力诉求
商品经济的发展,将人从狭窄、孤立的地点中解放出来,它迫使人们之间物的联系被货币关系所取代,它打破一切血缘关系,将人从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还以人的独立自主的现实性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确立了资本主义商业机制,它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保护个人正当利益,为个人追求经济利益提供了条件的同时也使人的个性和独立性得到充分发挥。作为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商品交换要求人们必须承认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地位,任何一方都不能有超越经济的特权,当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准则,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等级、出身、身份、特权等不再发挥主要作用,权利平等和人格独立观念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平等意识由此产生。正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打破了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冲破了封建社会狭隘生产方式对人类发展的严重束缚,使人们摆脱了依附于人的关系,也正是在商品经济这种经济形式中,人们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政治要求才有了经济基础。这种自由平等的观念被资产阶级思想家充分吸收,形成了指导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王权的有力理论武器。伏尔泰就将自由平等的思想融入到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之中,他认为自由是人最重要的自然权利,是自然法的起点,按照自然法,就应该“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而霍布斯则认为,除了法律限制之外,个人享有一切行为的自由。同时,根据人民自由的原则,他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封建专卖制度。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状态”,“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是自由的,人人都可以用自己合适的方法决定自己的行动。同时,人人又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享有多于他人的权力,一切权力与管辖都是相互的”[6]。但是,不管是洛克还是霍布斯,都认为私有财产是一个理性社会所必须的,人人平等并不包括私有财产的平等。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英国的还是法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国家政权的确立,人民权利获得的前提都要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他们最大程度地发挥了自由平等的学说,立足于人的政治平等与政治解放,但是并没有丢弃经济不平等这个基点,它摘掉了“君权神授”的面纱,用公民选举制度选出国家机构的领导人,使国家机构的领导人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行使自己的权力,受到了法律、规章、制度的严格约束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制约,他们再也不可能像封建帝王那样以“朕即法令”的王威为所欲为。民主政治的建立使西方国家步入了法治社会,封建主义的“人治”社会被送入了历史的陈列馆。然而,若是站在“人民民主”的立场上看,这种自由与平等却并不是真正完全的自由与平等,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与平等,这种“平等的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7]。当然,这也是资产阶级不可避免的缺陷。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资本家追求利润和占有财富最大化的动机与“人民民主”是相矛盾的。这种在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下的民主政治与人们所追求的人民民主相距甚远。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的政治资源不能被平均地分配,经济上的不平等损害了政治上的平等原则,只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的政治平等就不可能会实现。
不管是“社会契约论”的形成还是“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它们的唯一来源都是资产阶级的商品经济,这些思想理论全部隶属于资产阶级,他们只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物质观念在观念上的表现。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试图掩盖他们的阶级本质,他们将这些理论同资产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理论独立化,撇开这些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将他们描绘成超阶级、完全独立的、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而这些思想理论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表达着资产阶级的意志与愿望。“一个重大的悖论寓于人权的中心:权利都是在西方的法律传统中发展起来的,而西方国家却声称它们都是普遍的。”[8]
(三)私有财产权法律地位的确定
在早期的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家看来,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建立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个人私有财产权利如何得到保护而免受侵犯。不管是霍布斯所坚持的绝对的君主专制理论,还是洛克的分权制思想,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实施公正、保护私人财产的正义行为。沿着这样的思路,在资产阶级国家确立的过程中,私有财产权利法律地位的确定就至为关键。我们看到,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税收的控制权问题逐渐演变为一切政治斗争的焦点,所以考察私有财产权利的确定进程可以从关于税收权力的斗争中探析线索。不仅如此,税收争斗还涉及到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主张问题。
税收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其第12条和14条规定,除传统封建捐税外,任何赋税必须经过“全国公意许可”,(国王)将不能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赋金,当然这个全国公意落实到制度与法律层面就是得到议会的同意[9]。《自由大宪章》第一次确立了被征税人不同意就不允许征税的原则,从宪法原则和政治制度设计上构成了近代私有财产权利的原则起源。到17世纪,英国议会主权的彻底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在宪法和制度中最终确立。1789年,法国颁布《人权宣言》,同样也规定了这个原则。《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10]同样,这个原则也在美国宪法中得到体现。在《独立宣言》中,美国谴责了英王不得到美国允许就向他们强迫征税,确认了不经纳税人同意不征税的原则。私有财产法律原则的确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频繁出现,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私有财产权利保护的确立是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同步进行的,在它形成之初,主要是针对封建专制王权,但是当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它的针对对象就转向了资本主义政府。在资产阶级理论家理想设计蓝图中,限制政府、使政府无为而治是最为理想的状态。他们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发展和确立,使资产者对财产的安全尤其是长远的安全充满了信心。问题的实质在于这种蓝图是否能够实现。我们认为这种政治建构的基本原则部分程度地成就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但是深层解读私有财产法律地位的确立过程及其后果,可以这样判定,即西方早期政治学家的设计最终滑向了乌托邦的尴尬处境。对资本主义而言,私有财产权法律地位确定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提升了私有财产权在整个社会和国家中的原则地位,更在于通过它的确定而完成了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面确认。由此,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对政治与经济、私人与公共、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等概念的重新定义与调整,也同时意味着对现代而言是一种框定与设计。这种框定与设计已经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早期政治学家以及国民经济学家们对这个新生社会的预期,而这恰恰是考察当下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困境不可缺失的重要历史和思想通道。
三、新财富观:西方选举制度形塑的意识形态
商品化社会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渐成型并主宰整个社会。伴随而至的是在整个西方社会形成的新财富观,即资本至上。这个新财富观导引并支配着西方选举制度的发生、发展与演绎,是西方选举制度的至高意识形态。新财富观的现实演进逻辑也成为考察西方选举制度形塑的内在逻辑。
(一)资产阶级新财富观在嬗变中形成
从15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的社会经济出现了从农本到重商的转变,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中世纪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对封建制度的强势改造,使得商业资本获得良好的发展,商业资本与货币资本成为经济社会的主宰,人们的财富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1500—1750年期间的重商主义阶段,金银货币被认为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并且整个社会极力鼓吹商业的生产性。在随后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和资本主义扩张的时代,重商主义者将财富与货币等同,积极鼓吹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银货币。伴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晚期重商主义者在认同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的基础上,开始用资本家的眼光去看待货币,他们认为货币并不只是单纯的货币财富,同时也是增加财富的手段,这就为货币转化为资本奠定了基础。不同于重商主义学派,重农主义学派将对财富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认为农业生产的剩余即生产环节中产生具有使用价值的“纯产品”是财富的来源。他们将财富转移到生产劳动中去,认为劳动是财富的主体。而在其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与资本主义经济上升的阶段所构成的重要时期,为适应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在资产阶级理论家看来,劳动是创造一切财富的来源,而这种财富表现为商品的堆积,这也衍生出人们后来对商品的疯狂崇拜。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财富观变化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财富观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经济的细胞形式”的商品表征了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的本质不同,它内含了人的逐利欲望,是市场逻辑的抽象表达。货币作为一种通约功能强大的利器造就了一个货币化的生存世界,“每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11]51。但是这还不够,“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11]90。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其中商品、货币、资本恰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观演进的不同阶段。资本作为全部财富的聚集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所在,展现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全部想象。资本的核心内涵不仅仅只是货币数量的多寡,它逐渐变成马克思所认为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的代名词。资本家对资本的疯狂追求从一开始就包括着生产领域及其以外的诸多领域,特别是在政治领域。早在通过对商品二重性的剖析,马克思就指出近代社会转向的深层次根源即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所有政治立场都可以从经济生活中寻求答案与依托。当资本逻辑充盈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时,财富的最终形态能且只能是资本。至于财富的现实形态反而愈加眼花缭乱了,它是商品,是货币,是政治权力……凡是能够最终转化为资本并有利于资本进一步攫取超额利益的都是合乎财富的形态定义。资本主义选举制度的设计正是资本获取更大财富的一个重要动因,它的存在使得资产阶级通过手中的资本成功换取政治权力,然后再运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获取更加丰厚的财富,这是资本主义财富观支配选举制度的本质。“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这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就用这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又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权力有没有资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而且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1]可以说,资本作为新财富观是包括资本主义选举制度在内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至高意识形态。
(二)代议制度的形成与选举制度的确立
近代以来,当资产者阶层的财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迅速积累之后,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机构去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即财产权利益,以选举方式形成的代议制制度就被提出来。代议制的形成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以英国为典型,财产上的共同利益驱使权贵们结合起来,借助议会的权力限制国王的权利尤其是随意征税的权利。可以说“无代表不纳税”是近代代议制度形成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动力。每当陷入财政危机的封建君主要求权贵们纳税时,来自于权贵们基于财产权的抵抗便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为抗议国王未经同意直接征税的做法,贵族们联合起来拟定《自由大宪章》,迫使国王签订。同时,《自由大宪章》的颁布判定拥有财产的阶级应该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确定了贵族及新兴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权利,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即有产者因财产而执掌权力正式开始。
我们看到,虽然代议制形成之初并不是新兴资产者所主导,但是源自商品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财产保护意识与历史的分权传统一结合则产生了持久的斗争动力。在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资产阶级逐渐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表征着民主、平等的等级会议,以选举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宪政、君主立宪的代议制会议开始确立。在这之后,美国和法国也通过不同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形成了资产阶级代议制度。代议制度的初步奠定为现代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提供了重要制度保证。其本质是:作为支配社会资源的“财富”在民主制度上的表达方式。因此,作为选举制度核心的代议制度的形成同时也标志着西方选举制度的形成。
代议制民主制度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框架,作为其实现方式的西方选举制度的形塑也同样在于保护私有财产权利。西方选举制度在现实操作层面的具体表现在于以下方面。在制度上体现为一揽子制度规范,主要表现为候选人资格限制、选区的划分、选票的计算等。而候选人的资格限制主要体现在财产资格的限制,这就为资产阶级充分占有国家政治权力提供了保障。在物质形态上体现为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系列法令制度。对私有财产的的法律保护是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确立的物质基础,只有在确认选举制度所具备的功能是确保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运行时,选举制度才可以被长期的接受。西方选举制度在意识形态上标榜为对自由、平等、人权的呼应。我们知道这种自由的本质是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平等是形式和程序上的平等,人权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包含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系统的结合。由此,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选举制度正式形塑,并成为西方民主社会的重要制度支柱,为资产阶级追逐更大的利益提供了合法、文明的佐证。
四、结语
经过对西方选举制度的经济哲学分析不难看出,由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条件与阶级基础,西方选举制度从其成立之初就摆脱不了它的阶级本质,即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超阶级的、合乎理性的制度设计只是为了掩盖其阶级统治的假象,由于对经济基础的绝对依赖性,必将使得西方选举制度不能代表着所有人的利益,它只是表达资产阶级意志与愿望的工具而已。“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1]可见,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政治制度一直以来的承诺存在着价值本质的失陷,也即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自由、平等、人权的抽象政治口号和承诺被商品交换的自由平等所兑换。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实现必然停留在一定程度上。
[1]列宁.列宁选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
[2]亚当·斯密.国富论: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17.
[3]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M].彭姝祎,贾瑞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
[4]琳达·维斯,约翰·M·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M].黄兆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5.
[5]霍布斯.论公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9.
[6]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77.
[7]列宁.列宁选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4.
[8]科斯塔斯·杜兹那.人权与帝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
[9]齐延平.自由大宪章研究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327.
[10]耶里内克.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M].李锦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67.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A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Western Electoral System
Zhang Bin,Duan Zhouyan
The coming of commercialized era provides a possibility for the commensur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s sought by the newly rising bourgeoisie. The essences of social contract and freedom and equality are based on the private property right.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private property righ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western electoral system. The capital supremacy of the new wealth concept and its logic are dominant power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elector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logic of its evolution. The comprehensive recognition of the western electoral system requir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which also provides significant ideas for revealing and criticizing the dilemma of the whole western democratic and political system.
electoral system; capitalism; commercialization; economic philosophy; private property right; wealth; capital
张斌,哲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段周燕,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本—福利—信息时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困境与历史局限研究”(13&ZD035);安徽财经大学重大科研项目“从《资本论》经济哲学思想透视当代西方政治制度困境”(ACKY1502ZDA)。
D08
A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2.003
2016-12-12;责任编辑:沈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