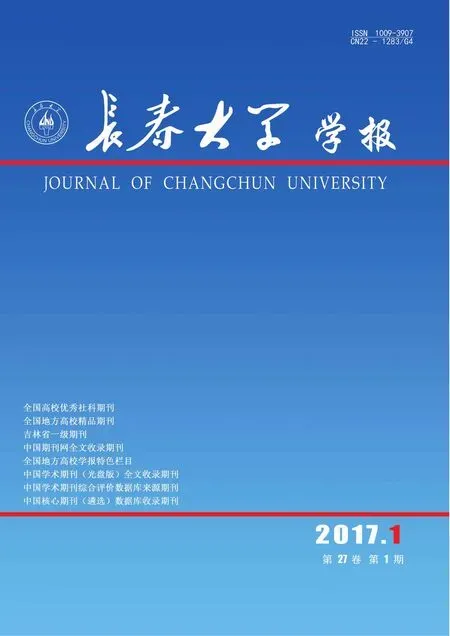“倭”国号论考
2017-03-22于姗姗
于姗姗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亚欧语系,福州 350202)
“倭”国号论考
于姗姗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亚欧语系,福州 350202)
因缺乏明确的史料,人们未能弄清日本于何时开始使用“倭”作为国号。本文试通过对中国史书的分析和对“倭五王”政权的性质、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和飞鸟时代改革成果的探讨,推论在“倭五王”时代日本暂不具备使用“倭”作为国号的条件。日本正式以“倭”为国号,似应在飞鸟时代。
日本;“倭”国号;考证
在展开论考前需明确两个概念。第一,国号包含两个意思:一指含有表示政体意义的国家名称,如“帝国”、“王国”、“大公国”、“酋长国”、“共和国(民国)”等;二指不含表示政体意义的国家名称。我们讨论的问题与二有关。第二,今人对古代国号产生的定性标准存在不同认识:它或出于某国自我意识;或依据国际社会认同;或依赖法律文书记载。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日本有了国家意识并得到国际社会认同这个意义上的国号问题。因为历史可能存在以下情况,即某族群或某地区政权有名号意识,但因它们尚不足以成为国家,那么这个名号意识是否即国家意识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会牵扯出更多的问题。当然如有法律文书记载更好,但没有直接记载,通过旁证推论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应该也不失于某种意义。
日本何时使用“倭”作为国号尚无定论。“中国知网”显示,我国的论文不关心此话题*笔者输入“倭国号”此关键词检索,未发现有论文涉及此话题。。著作方面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汪向荣在其著作《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倭五王和日本的统一”一节中似乎流露出“倭”是“五王”的国号的意思[1],但未确说。日本方面对此似乎也无明确的结论[2]。即使是在2010年底日本某网站转载的一篇说法较为肯定的论文,也仅认为“稻荷山古坟铁剑铭文*原文是: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其児多加利足尼其児名弖 已加利获居其児名多加披次获居其児名多沙鬼获居其児名半弖比(表) 其児名加差披余其児名乎获居臣世々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 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练利刀记吾奉事根原也(里)。附注:铭文为古汉语体,但人名等用万叶假名标注。中汉字记述的大王,可以推定是雄略天皇。根据这个史实可以判断,在公元471年,诞生于狭义的YAMATO*即“倭”字,原文为假名。为便于中国普通读者阅读,自此开始一律改为罗马拼音字符。国的YAMATO王权的支配范围已扩大到日本列岛的相当范围”,“有极大的可能将这个新的支配范围称作YAMATO国。雄略天皇在给刘宋的表文中将本国称作倭国,将自己称作倭国王,结果就从刘宋那里获得了倭王的称号。”另外,“《宋书·东夷传·倭国》也记述了我国统治者中所谓‘倭五王’*“五王”分别为“赞”、“珍”、“济”、“兴”、“武”。据《古事记》转引《帝纪》记载,履中天皇和反正天皇属兄弟关系,与《宋书》的记述一致,故“赞”即履中天皇,“珍”即反正天皇;允恭天皇和安康天皇乃父子关系,与《宋书》的记述又相一致,故“济”即允恭天皇,“兴”即安康天皇;安康天皇和雄略天皇又属兄弟关系,与《宋书》的记述也相一致,故“武”即雄略天皇。此“五王”受到《宋书》的重视,可能缘于他们自公元421年到478年先后10次遣使朝贡刘宋王朝。对此,日本史学家佐野大和有不同看法,他引用前田直典的研究,认为“赞”是应神天皇,于421年和425年两次遣使赴宋,430年死去。而“珍”即仁德天皇,于439年死去。结论是当时的中国人将此二天皇说成是兄弟乃误听的结果。至于履中、反正二天皇,因在位时间过短,没有遣使,因此在中国史料中没有出现。“济”即允恭天皇(与履中、反正二天皇都属兄弟关系),于443年即位。其余说法与《古事记》或《宋书》相同。参见佐野大和:《日本的古代文化—考古学要说—》,小峰书店1965年版,第198页。的情况”,所以“至少可以说在《宋书·东夷传·倭国》记述的时代,我国的对外公文已正式自称为倭国”,彼时“必定使用汉字‘倭’标注。”*佚名:《倭·大倭氏考(大和国造氏)》,http://www17.ocn.ne.jp/~kanada/1234-7-39.htm. 2010年,下载于2011年5月21日。含此,正文和注释中的译文均由笔者翻译。这段话似有“倭国”乃国号的意思,但措辞亦较委婉。
1 《宋书·东夷传·倭国》
由于汪向荣和上述日本学者使用的论据都来自《宋书·东夷传·倭国》,但未伴有具体的分析,不免武断,而且都属于孤例,无法对照证明,所以有必要对该史料和其他中国史料再做分析。
《宋书·东夷传·倭国》对除正“五王”的记述颇详尽:“赞万里修贡……可赐除正”。“弟珍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诏曰……可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诏除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在对此史料作出分析前需要交代一个问题,即古汉人所说的“倭”尤其是“倭国”的含义为何。至唐以前,“倭”或“倭国”为汉人对广义的古代日本人或政治势力*我们这里所说的“广义的日本人”等,不是指沈仁安和王勇说的在中国境内和朝鲜南部等地的“泛倭人”,而是指古代活动于日本列岛的居民或各原始族群。的总称。比如“魏略云,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渡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前汉书》);“恒、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后汉书》);“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三国志·魏志》);“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请愿见”;“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晋书·安帝记》);“倭者……距带方万二余里”(《梁书》)。其中所说的“倭”或“倭国”,都并不特指统一后的日本这个国家。此外,有时中国史书亦将某“倭国”或某“倭”混说于整体的“倭国”之中。比如“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帝赐以印绶”(《后汉书》);“魏正始元年春正月,东倭重译纳贡”(《晋书·宣帝纪》)。人们在阅读成书较晚的《隋书·东夷传·俀(倭)国》时仍可发现,撰者或在总提时用“俀国”指称日本全国,或用“俀”特指其中的某“国”(似为大和政权)。由此可见,“倭国”这个词汇的意思并不固定,指的或是当时汉人模糊认识的日本这个“国家”,或是该国的某“国”(政权)。既然如此,那么从相反的角度说,日本当时各政权在向汉王朝输诚纳贡时都可以自称“倭国”,而不管自己是全国性政权还是地区性政权。
接下来要分析的是,《宋书·东夷传·倭国》的“五王”在奉表中以“倭国”自称仅仅是顺着汉人的口吻?还是已经对这个中国词汇赋予了新的含义,使之具有今人所理解的国号意义?为此须考察日本当时的情况和刘宋王朝等对“倭五王”政权的态度。
先看刘宋王朝的态度。《宋书》对第一个王“赞”的记述极简略,未说除正什么,而说“珍”、“济”、“兴”、“武”都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括号表示有的缺“加罗”,有的被《宋书》删去“百济”)六国或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并且说刘宋以“自称”为由,对“珍”“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要求不予认可,仅“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对“济”是先认可“安东将军、倭国王”的称号,后来追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对“兴”是仅“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对“武”是“诏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之所以《宋书》将“武”升格为“安东大将军”,是因为后者罗列了一堆理由,其中最让刘宋满意的是其表示愿意配合进攻高句丽——刘宋急欲除去的一个军事对手。仔细分析后可以认为,刘宋对“五王”“使持节都督X国诸军事”这个要求多有疑虑,并否决了“珍”、“济”、“兴”加封“安东大将军”的要求,只“诏除安东将军”,而对武王是因为有求于他才改“诏除安东大将军”(此时武王才和高句丽王平级)的。这显示出刘宋此前并不看好“五王”,而将他们置于高句丽王之后的心态。然而,刘宋在赐给“倭国王”这个称号上却很痛快。理由何在?其实这个称号对刘宋来说并不重要。其原因如前述,过去的中国史书都将日本的各政权视为“国”,故《宋书》的撰者或在传统认知的基础上,按前人所说诏除他们为“倭国王”并不感到困难。此外,我们从上述史料中也很难看出“五王”时的“倭国王”称号与之前“帅升”的“倭国王”称号相比有多大的意义变化。
其次的问题是,“珍”至“兴”都受封了“倭国王”称号,而最有实力且被刘宋开始看好的“武”却仅被授予“倭王”,其称号丢失了“国”字。这说明什么?笔者认为可作两种推测:一是将“武”诏除为“倭王”是漏写了一个“国”字。不过这对讲究用字的诏书而言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故此推测较难成立。二是这或反映刘宋对当时日本的情况不了解,故说法有反复,或说明刘宋在武王时已逐渐摸清日本的情况,对他的“国家资质”有了疑问,认为此时的日本只存在许多大型聚落,而武王仅是其中一个超大聚落的王,故不认可他的“国家体制”,只看重他的军事才能可为己用,最终在改封他为“安东大将军”的同时仅给了一个“倭王”的称号(退一步说,即使加了“国”字,其意义亦与上述无大差异。因为日本的各政权都是“国”)。
值得注意的是,之后的《南齐书》(502—519年)继承此笔法,亦不写武王为“倭国王”,仅将其受封情况记作“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为镇东大将军”;《梁书》(636)甚至干脆将日本写成“倭者”,连“国”都不说,记述为“除武持节督新罗、任那、伽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镇东大将军。高祖即位,进武号征东将军”。不仅少掉了“倭国”名,而且连是否“倭王”也不提。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当时或许“倭国”这个称号并不固定,时有时无,否则《隋书》就不会另造一个国名“俀国”来表示日本。“俀”字义为“软弱”。写作“俀”是何用意一时无法说清,但至少可以认为不是笔误。也许当时日本某政权(从《隋书》的写法可以看出,裴世清的终点站是今天的奈良一带,也就是过去“五王”曾活动的区域之一)向隋示好,表现温顺,故被称作“俀国”。又或为隋朝对日本的另一个“倭”政权感到失望,所以故意创造一个新词“俀国”以区别于该“倭”。以此观之,当时武王等在与中国联系时很有可能是顺着汉人的口吻,将自己统说为“倭国”的。
2 “五王”政权的性质及其可能有的国内自称词
在分析刘宋王朝的态度之后,还要考察日本当时的国内情况。为此要就日本古代史中所谓的“政权”、“王权”、“朝廷”和“国家”的概念作些说明。按日本学者的理解,所谓的“政权”,是指当时在日本国内诸多政治势力中掌握一定权力的某个政治势力。而当权力集中到政权内部某个特定人物,且众人皆应为此人物服务时,这个政权就可以被称作“王权”。当然,“政权”和“王权”在组织形态上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如果这个政权的内部成员并不仅限于服务某一个特定人物,那么这个政权就可以被说成是由多种势力组成的“联合政权”。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联盟”。王权局面中的大王出现后,有可能凡事皆须通过他的直接决断,但是否因此就能说他的政权是“朝廷”呢?似乎还不能。因为按常理,只有在一面将大王作为政权的核心人物,一面又不事事依靠大王的直接决断和命令,而能依据大王所制定的大政方针独立开展工作的“组织体系”建立起来之时,才能称之为“朝廷”。而对“国家”的概念,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甚至是同时代的人也都有不同的认识,但按笔者的理解,则其似乎应该是由一定的支配权力进行组织并统一起来的、居住在一定区域内具有朝廷机构的人的聚合体。
以此对照“五王”时代的情况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五王”势力强大确实不假,作为其最后一个王的武王,除了仿照中国皇帝用语,在“稻荷山古坟”等出土的大刀铭文上刻有“治天下大王”的字样和获得刘宋赐给的“安东大将军、倭王”称号外,还使自己的政权具有一定的“朝廷”规模和“国家建制”,有了“内廷”和“外朝”的区别。前注铁刀铭文等中分别出现的“杖刀人”和“典曹人”的官职名称就是例证。所谓“杖刀”,就是“正仓院”保存的天平胜宝三年(752)《东大寺献物帐》所说的举办仪式时使用的大刀。“杖刀人”即守卫在大王近侧、手持仪式大刀的警卫长官,可谓内廷官员。而所谓的“典曹人”,据《三国志·蜀志》对“典曹都尉”官职的说明,就是在皇帝身边从事记录工作的文官,可谓武王时代的外朝官员。此外《日本书纪·雄略纪》还记有“厨人”、“川濑舍人”等官职名称。这种官僚制度被日本史学界称作“人制”。并且武王还在未征得刘宋同意的情况下就仿照高句丽已获得并使用的国家行政部门名称,“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皆假授,以劝忠节”(《宋书》)。从这些举措可以看出,武王政权已大致走出前国家形态,进入准氏族共同体古代国家的发展轨道。由于这个原因,日本史学家平野邦雄认为,在武王时代,YAMATO朝廷已经形成。因为“以王权为核心,通过一定的臣僚集団组成的政治机构形成的时候,就是‘朝廷’形成的时候”[3]。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性质和程度的差别,自封的和被众人认可的,雏形期的和成熟期的往往不是一件事情。除平野邦雄等几人之外,很多日本史学家都不同意将“五王”政权看作是“朝廷”。比如关和彦就说过,“朝廷”一词,原义是指天子处理朝政或举办朝礼等仪式的官厅,之后转指具有以天子为核心的官僚组织的中央集权政府或政权。若彼时该政权不打出“天子”或“天皇”的君主名号,并且在各官职设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使用“朝廷”一词是不恰当的。为此他将“朝廷”定义为“天皇的政治场所”[4]。鬼头清明以“盘井之乱”为例,说明在当时的近畿地区有多个王权并立,并以继体朝之前的政权与“天皇系统的直接祖先YAMATO朝廷没有关系”为由,力说“YAMATO朝廷”一词必须在继体天皇之后从6世纪开始才能使用[5]。佐佐木健一认为,到5世纪中叶日本尚未统一,在吉备、筑紫、毛野、出云等地还存在许多独立的“地域国家”,在那些地方都建有大型的前方后圆形墓,其中冈山市的“造山古坟”(坟丘总长360米)在日本名列第四位[6]。这表明各地豪族虽然从属于YAMATO王权,但在各自的地域还拥有自己独立的势力,他们和YAMATO王权处于一种并立或联合的关系。
上述反方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五王”时代还处于多种政治势力并存、有着许多独立“地域国家”的阶段,该政权带有联合王权的性质,尚无“天皇”或“天子”的名号,官职设置还十分不完备,权力来源与之前的YAMATO政权没有关系。用笔者的话加以补充,就是“五王”政权虽然进入准氏族共同体古代国家的发展轨道,但因其缺乏健全的朝廷形态和正常的行政作风*有关此点,从成书较晚的《隋书·东夷传·俀国》中仍可看出:“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毎,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难尔,遣使旨阙。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由此可以反推出“五王”时代的行政作风。《二十五史》,《隋书》卷八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第219页。,且没有通常与国号伴生的年号,其谥号WAKE(详见后文)和官职名称(“XX人”)仍未脱离前国家形态的传统聚落习性。简言之,武王等只是一个联合王权的大王,并非真正意义的国家领袖。他可以有自己的国内名号和对外自称词,但后者决非今人所理解的国号。
在此基础上,还要结合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对“五王”政权的性质和该政权可能有的国内名号,以及后者和对外自称词“倭国”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日本最早的古坟“胜山古坟”建在今奈良县樱井市,坟丘总长约110米,用年轮年代法测定其出土的丝柏年代,可知其建造的时间为公元3世纪*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报告,2001年5月30日。。这表明在奈良一带很早就建立了一个较为强大的政权。日本史学界通常将此政权看作是天皇系统直接祖先的大和王朝前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又出现了许多规模更大的古坟。在日本现存的10座坟丘总长超过 280米的大墓中,位于前三位且分别属于第16代仁德“天皇”、第15代应神“天皇”和第17代履中“天皇”的古坟,以及位于第五、第八位但所属不详的古坟和位于第九位属于应神“天皇皇后”即仁德“天皇”母亲仲姫命的古坟都建在大阪。而位列第六属于第29代钦明“天皇”、位列第七属于第12代景行“天皇”(?)、位列第十属于卑弥呼(?)的古坟都建在奈良;另一座即在上述的冈山。由上述“天皇”代数可以看出,建于大阪的超大型古坟多半建于“五王”或稍早的时代。对此现象,日本史学界有不同解释。一种说法是“王朝更替说”。比如水野佑认为,相对于4世纪集中建在奈良三轮山的是5世纪建于“河内”(今大阪府)的大古坟。从这种现象来看存在着王朝交替的可能。此外,从《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和式“天皇”谥号来看,4世纪的“三轮王朝”(崇神王朝)带有IRI(详见后文)尊号,而5世纪的“河内王朝”(应神王朝和仁德王朝)则有WAKE尊号,从中也可看出存在王朝变更的可能[7]。上田正昭力挺此说,认为倭国在4世纪曾将政权建在“三轮”,而到5世纪即“五王”时代又将王朝搬迁到“河内”,故该王朝应称作“河内王朝”[8]。井上光贞因此亦提出“应神天皇新王朝论”[9],另一种说法则是“王统连续说”。和田萃认为,4世纪后半叶和5世纪的大和势力与河内势力实为一个政权,为此提出了“大和、河内联合王权说”,否认存在王朝更替[10]。而重视大和王权在大和川流域间移动的白石太一郎的见解基本与此相同[11]。此外还有吉村武彦的“历代迁宫说”。吉村认为“古坟建造是否意味着政权和国家的建立存在问题”[12],说要对过去将政权的基础放置在古坟所在地的观点重新进行审视,其根据就是《记纪》都记载王宫和陵墓是分离的*实际上《记纪》有关王宫和陵墓分离的记载不完全正确。因为“河内”除了建有超大型王陵,还建有许多大王的宫殿,比如应神“天皇”的大隅宫,仁德“天皇”的高津宫,反正“天皇”的丹比柴篱宫,雄略“天皇”的志几宫,显宗“天皇”的近飞鸟宫等。这说明王陵和王宫同在一个区域的传统并未有所改变。。并因此提出,如果在特定区域行使影响力的集团酋长只在特定的狭小区域拥有地盘,那么《记纪》中所谓的“历代迁宫”现象就不会发生,所以,大和王权应该通过迁离特定的政治地盘才能得以确立。
我们倾向于“王朝更替说”,认为“五王”政权的性质是一个新政权,活动于大阪一带。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其对内自称词就不会是YAMATO(即后来的“倭”),而会是另一个名称。那么要如何证明王朝发生更替了?我们认为,虽然上古时代的史料不多,但以下资料可作证据补充:
一是亡灵信仰。“河内王朝”之前的古坟多半建造在山丘和山脊突出部向平地延伸的地方,也有的建造在独立的山丘或台地上。这种亡灵信仰据说来自“山上清净思想”。而到“应神、仁德两陵时,高耸的坟丘则横亘在平原中央”。这时坟墓中“已建有……大石室,安置带盖的长方形石棺”。“与横穴式石室出现相表里”,“人们[在墓中]可以见到釜灶合一的小型陶偶。……送葬时人们的心思已完全从封土上或坟前转移到石室内部”,“过去摆在坟上的陶偶等当然就此隐踪匿迹”[13]。另外,亡灵信仰的变化还表现在奈良和平安时代天皇即位后第二年举办的“大尝祭”*指天皇即位后举行的“新尝祭”,亦即天皇亲自将当年新收获的谷物奉献给天照大神以及天地诸神的、一任天皇才举办一次的盛大仪式。和在其翌年举办的“八十岛祭”上*指在“大尝祭”翌年,天皇选择吉日,派遣勅使前往“摄津国”的“难波”(今大阪),祭祀住吉神、大依罗神、海神、垂水神、住道神,感谢国土生成,祈祷治世平安的仪式。也称“八十岛神祭”。。简单说来,后一个仪式就是让敕使把天皇的衣服拿到大阪湾的淀川下游,使大八洲的“御灵”(死魂)附着在天皇衣服上。为什么敕使要特意将天皇的衣服拿到大阪湾?上田正昭的回答是与“河内王权”有关。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新政权在一个新地方产生了新信仰,让人有后来的大和政权之根反而在“河内”的感觉。
二是大王的和式谥号(以下简称“谥号”)。前面说过,4世纪的大王谥号含有IRI尊号,而5世纪的则含有WAKE尊号。为便于人们将此现象看得更清楚些,我们在此特意将第1代至第26代具有区别意义的“天皇”谥号全部标出(斜体字部分表示其具有的相同尊号)。
第1代为神武“天皇”,谥号是“ハツクニシラススメラミコト”*自此开始用片假名标注。因为其中多数字符具有可辨读的意义。,即“治理初建国家之皇”的意思。《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认为神武其人就是大和朝廷和皇室的肇始者。另外,《日本书纪》将他之前的时代定为“神代”,之后的时代定为“人代”。
第2代绥靖“天皇”(カムヌナカワミミ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3代安宁“天皇”(シキツヒコタマテミ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4代懿德“天皇”(オオヤマトヒコスキトモ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5代孝昭“天皇”(ミマツヒコカエシネ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6代孝安“天皇”(ヤマトタラシヒコクニオシヒト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7代孝灵“天皇”(オオヤマトネコヒコフトノニ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8代孝元“天皇”(オオヤマトネコヒコクニクル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9代开化“天皇”(ワカヤマトネコヒコオオヒヒノスメラミコト)
以上8位“天皇”中有4位“天皇”的谥号都带有ヤマト(YAMATO)的尊号,说明截至第9代“天皇”,他们的根在近畿YAMATO或九州YAMATO一带。因此或可说他们的政权是YAMATO政权。不过由于第2代至第9代的“天皇”皆未见于史书,他们被称作“缺史之八代”, 所以无法在此多作介绍。
第10代崇神“天皇”有两个谥号,一个是“ミマキイリビコイニエノスメラノミコト”,另一个是“ハツクニシラススメラミコト”,即“初治天下之皇”的意思,故被人视为实际存在的“天皇”。
第11代垂仁“天皇”(イクメイリビコイサチ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10代“天皇”和第11代“天皇”的谥号都带有イリ(IRI),而都没有ヤマト(YAMATO)的尊号,说明从此开始情况有了变化。
第12代景行“天皇”(オオタラシヒコオシロワケ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13代成务“天皇”(ワカタラシヒコ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14代仲哀“天皇”(タラシナカツヒコ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15代应神“天皇”(ホムタノスメラミコト、ホムタワケノミコト)
第16代仁德“天皇”(オホサザキ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17代履中“天皇”(イザホワケ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18代反正“天皇”(ミツハワケ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19代允恭“天皇”(オアサヅマワクゴノスクネ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20代安康“天皇”(アナホ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21代雄略“天皇”(オオハツセノワカタケルノミコト)
第22代清宁“天皇”(シラカノタケヒロクニオシワカヤマトネコ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23代显宗“天皇”(ヲケ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24代仁贤“天皇”(オケノスメラミコト)
第25代武烈“天皇”(オハツセノワカサザキノスメラミコト)
从第12代到第25代14位“天皇”中有7位“天皇” 的谥号都带有ワケ(WAKE)或ワク(WAKU)或ワカ(WAKA)的尊号,尤其是从“五王”时的“赞”即履中“天皇”到“武”即雄略“天皇”时,更集中使用过WAK- 的尊号。想来上田正昭通过这种现象,将“五王”政权命名为“WAKE王朝”不无道理。
第26代是继体“天皇”,谥号为“オオドノスメラミコト”,自此开始那种带有相同尊号的现象消失。《日本书纪》记载继体为“应神五世孙”,出生于近江国(今滋贺县)高岛,在其母亲的故乡越前国(今福井县东部)高向长大,后来因大伴金村等人的推举成为“天皇”。故在此有皇统断绝和未断绝两种见解,此不赘述。
从上述亡灵信仰和谥号中的尊号改变至少可以推测出,至“五王”为止的政权性质仍旧是一个流动的王权。既然信仰有了改变,谥号中的尊号也出现了变化,政权所在地亦改变了,那么即使按照王统连续的观点,其国内自称词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有可能一道发生改变,而不会再是过去的YAMATO了,而或是 IRI或是WAKE什么的。因此,后来的“倭”字就不会被顺理成章地训注在“五王”的非YAMATO名号上,他在给刘宋的奉表中使用的“倭国”也不太可能是他国内名号的汉译,而很可能是仿照前人,用汉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加以灵活运用的产物罢了。有必要重申一遍,在当时,倭人政权在与中国联系时都可以用“倭国”自称,而在汉人看来,所有的日本政权也都可以是“倭国”。综合上述,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即便“五王”有了本政权已是一个“国家”的想法,但他们的想法是一回事,刘宋王朝等怎么看是另一回事,他们本身所处的状况更是另一回事。
3 “五王”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和《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
至此还需要就“五王”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作些分析,以便与飞鸟时代*这里所说的飞鸟时代的概念,在日本史上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指在奈良盆地南部飞鸟地区建都的推古朝前后的时代。在政治史和文化史上一般指6世纪末到7世纪前半叶这段时间。的情况作个对比,知道在何时日本才可能使用一般意义上的国号。首先,“五王”是主动要求加入东亚朝贡册封体制的,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对刘宋的向往,而主要是希望获得刘宋的支持,以确保自己在朝鲜半岛的支配地位和获得那里的铁矿资源,加强自己在联合王权内部的政治地位;其次,“五王”的活动地点在大阪而不在大和,除了让人窥见其目的是便于与中国等联系和对高句丽作战之外,还暗示着“五王”及其后人的国内征程远未结束,换言之即“五王”时日本并未真正统一。武王在奉表中对自己的战功做了诸多宣传,但故意漏说了位于北九州岛的“筑紫政权”(=古倭奴国?)。而这,也是一个其未彻底征服的“国家”,同时还是一个比大阪更好的出海联系和作战通道。由于《日本书纪》由胜利者大和王朝书写,所以该史书对“筑紫政权”的情况讳莫如深不难理解。实际上,作为一个早先能与大和铜铎文化圈抗衡的九州铜鉾、铜剑文化圈中的“筑紫政权”,从未从“五王”及之后的历史中淡出。有关此点,我们可以从“魏正始元年春正月,东倭重译纳贡”(《晋书·宣帝纪》。这里所说的“东倭”,似有区别于九州“倭”的用意)、“自竹斯国[筑紫国]以东皆附庸于俀”(《隋书·东夷传·俀国》)、“倭国者,古倭奴国也。……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旧唐书》)和“日本,古倭奴也。……后稍习夏音,因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並,故冒其号”(《新唐书》)等记述反推出来。这种近畿政权与九州政权的争斗在继体“天皇”进入大和后的527年仍在继续。比如某次争斗,按照以大和政权为正统的《日本书纪》记载属于“盘井之乱”,即北九州岛的豪族“筑紫君”盘井与新罗联手对YAMATO政权展开的一次军事进攻,但在我们看来,它似乎仍然属于当时日本国内两个“国”的战争。
从文物和其他史料也可以对此事加以有效的推测和证明:①东汉光武帝赐给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不是被发现在大和,而是在筑紫。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那里长期存在着一个重要而强大的政权;二是这个政权曾被汉人命名为“倭奴国”。②法隆寺早先不建于奈良,其前身的X寺建于筑紫,后来是因为“筑紫政权”败于大和政权,才被拆卸后按原样重建在今天的地址的。据称,该寺的建筑法度和尺寸乃中国南朝法度和尺寸,有异于大和王朝的其他佛教建筑[14]63。与此相关的还有日本最早的佛书《法华义疏》和“上宫王”等身佛像。《法华义疏》乃中国南朝高僧法云法师(?—529)为《法华经》所作的注释书,现保存在法隆寺,其首页注有“大委国上宫王私集”字样。“上宫王”为何人不见于日本天皇谱系和任何一部史书,日本学者川端俊一郎认为此人就是“筑紫国王”。或许此书连同原X寺一道被大和政权掳掠到奈良。过去,人们对上宫王等身佛像(该王死后有人以其模样塑造的观世音菩萨像,1884年被美国人E.F.费诺洛萨强行起出)为何长期密藏于法隆寺八角佛殿(也称梦殿)一直迷惑不解,但若将其与X寺和《法华义疏》等联系起来,就会悟出其中的奥妙[14]58。“大委国”一词还证明,“倭”的称号早期也被“筑紫政权”而不仅仅被近畿政权所用,这可以增强我们前述的说服力。③“筑紫政权”曾与中国南朝保持过友好关系,在南朝的陈国被北朝的隋灭后仍情系南朝,对北方的隋唐皆无称臣之意。有人推测,《隋书》中所说的引起隋文帝不悦,带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字样的国书,就发自“筑紫政权”*日本有学者认为此国书乃亲中国南朝的“筑紫王朝”发出,因鄙视代陈而起的隋朝而有以上写法,但也有学者认为此国书乃大和王朝的圣德太子发出。但从历史逻辑上看,圣德太子在此时发出此国书是不符合常理和不智的。。
而从反映当时情况的《隋书》和《旧唐书》的记述来看,中国新皇帝似乎对“筑紫政权”也无好感。《隋书》记载,裴世清在达到目的地“俀”(大和政权?)前仅仅是经过“竹斯国”(“筑紫政权”),后来在“俀国”却受到隆重的欢迎,“俀王遣……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而《旧唐书》所说的“高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更暗示着中国与“筑紫政权”(《旧唐书》原文为“倭国”。如前述,该国在《旧唐书》中与“日本国”并列)间在这时已埋下战争的种子。日本学者古田武彦等人也主张在7世纪时九州北部还存在一个代表日本列岛的王朝,在白村江作战的不是畿内的大和军队,而是奠都大宰府的九州王朝军队[15]。虽然武彦等人的主张不被日本主流学界认可,但我们认为,日本在法隆寺被整体搬迁不久前应该仍存在两大政权并立的局面。现在人们对此缺乏认识是《日本书纪》撰者的“运作”结果,因为该史书在编撰时也经历过对之前存在的各种版本的《帝纪》和《旧辞》*《帝纪》也称《帝皇日继》,《旧辞》亦称《本辞》),二者都散佚不传,但从《古事记》的序言可以推知在该史书成书之前曾有此二书。该《帝纪》是记录古代日本皇位次第的书籍,与《旧辞》一道,都成为日后编撰《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资料。“讨核”和“削伪”的过程,自然其得出的结论有让人怀疑的理由。反过来,过去被人诸多存疑的《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为可靠。因为在隋唐两代,中国已有多批使者去过日本,白村江之战后,唐代朝散大夫郭务悰甚至还带领两千人的军队驻扎在筑紫,不会不通过当地人了解到日本尚处于分裂的情况。而彼时日本来华的使者和学者也很多,亦会向中国方面通报日本的情况。因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说日本当时分裂,有两大势力并存绝非毫无根据。隋唐如此,“五王”时代的情景由想可知。
以上史料和分析都说明,在“五王”及之后的较长时间内,因日本的不统一会导致“倭”国号的归属和采用都无从明确,因为他们都是“倭”。至少在“五王”时期,近畿政权或“筑紫政权”等在国内对“倭”国号都难以产生真正的兴趣,即使对外使用也很可能是顺着汉人的口吻灵活运用而已。日本只有在大致实现统一,成为一个完整意义的国家,才有使用国号包括年号的愿望和要求。反之,在日本古代各“国”相互攻伐期间,要证明谁是真“倭”,又是否真以“倭”为国号,不仅存在困难,而且缺乏意义。
4 飞鸟时代的改革成果
日本亚洲史学家宫崎市定曾发表过《关于天皇称号之由来》一文[16],推断古代日本在制度上用“天王”的称号当在雄略“天皇”即“倭武王”前后,而转用“天皇”则在圣德太子摄政的推古时代。理由是从圣德太子之后,日本开始与中国直接交往,称号问题便会排上议事日程,迫使日本寻求合适的称号。他还认为,日本5—6世纪的政治领导人曾自称“大王”,但这个称号应当是沿用汉文的习惯用法。在当时的中国,因沿用古代的叫法,故所谓的“大王”只是尊称而不是正式的称号。同时他又猜测,“天皇”这个称呼来自“天王”(引者按:二者的日语读音一致)。这个称呼在公元4—5世纪中国北方石勒等政权曾使用过。而且在中国“五胡十六国”那个流行“天王”的时代(天王冯弘之燕国灭亡于436年,即日本允恭“天皇”二十五年),日本有可能通过高句丽和百济将这个称呼引进日本,并将过去的“大王”或“王”升格为“天王”,再由“天王”升格为“天皇”。笔者认为这个洞见极具眼光,同时还认为,在直接交往时,当时的日本不仅需要明确自身领导人的名号,还需要一个国号。这是判断日本于何时产生第一个国号的重要依据。此外,从圣德太子在推古朝(593—628)及其后人在后推古时代所采取的措施也可以反推出,日本此时强烈需要一个正式的名号——国号。这些措施是:
第一,改革政治体制,摆脱豪族联合政权的掣肘,向统一的中央集权天皇制律令国家目标迈进。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603)和“宪法十七条”(604),派出遣隋使,引进佛教,打压神道教空间,就是这些改革措施的具体体现。大化元年(645)夏,中大兄皇子(此后的天智“天皇”)联合中臣(藤原)镰足等革新派豪族消灭了苏我大臣家族,又进行了程度更加深刻、范围更加广泛的改革。
第二,强化国家意识,而此点最为重要。推古“天皇”二十八年(620)圣德太子等人开始编撰《天皇记》和《国记》*指后世推测的推古“天皇”二十八年(620)圣德太子与苏我马子一道编撰的两部史书。但此二史书的内容如今不很明了。《日本书纪》记载,645年苏我本宗家族灭亡之际,苏我虾夷家中保存的此二书被火焚烧。是船史惠尺从火中将《国记》的一部分抢救出后交给中大兄皇子的。。此时的《国记》中的“国”,已不再是原先表示地区或属国意义的“国”,而带有明显的独立国家的含义。如果《日本书纪》所说的《国记》乃叙述国家成立由来之一书的情况属实,那么,可以认为此举具有空前的意义,表明大和王朝已有了明确的国家意识和与中国的对等意识,非“五王”政权可以相提并论。而此时的《天皇记》也开始取代过去所说的《帝纪》,在思想和外交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虽说奈良时代之前所谓的天皇汉式谥号都是后人模仿唐朝宫廷礼制和皇帝名号创设的,并且出现的时间很晚,大约是在公元8世纪后半叶由以淡海三船*淡海三船(722—785),奈良时代的贵族和文人,大友皇子曾孙,历任“大学头、文章博士、刑部卿”,着有《唐大和上东征传》等。据传是他选定了自“神武天皇”到“光仁天皇”的中国式天皇谥号。为代表的御用学者根据《日本书纪》的传说,给过去的大王分别追加安上的,但“天皇”称号首次出现的时间,却不在天皇汉式谥号被追记的奈良时代,而是在飞鸟时代。因为人们能看到的最早写有“天皇”这两个文字的,是在奈良县明日香村飞鸟池遗迹出土的天武天皇(673—686在位)朝代木简上(不排除此前已开始使用“天皇”这一称号)。另外,日本的第一个年号“大化”(有学者说之前似乎使用过“法兴”等年号,但未被广泛接受)也需注意,它出现于孝德天皇年代,时间是645年。668年,中大兄皇子即位为天智天皇,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有第一个年号、天皇称号和第一部成文法的出现,说明在此之前不久或当时应该产生了国家意识和国号。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武王十年(670)12月条说:“倭国,更号日本。”这个“更”字,似乎也说明在670年之前,日本使用过“倭”作为国号。
第三,改革经济和国家管理体制,建立和充实官僚机构。大化二年,中大兄皇子颁布了“改新”诏书,宣布废除私有地和私有民,采用“国、郡、里”制,将地方行政权力集中到朝廷。并于大化五年仿照唐代官僚行政制度,设立左大臣、右大臣和内大臣,制定八省百官制和冠位十三阶,开办大学寮,培养和任用了大批官员,以服务于建立户籍和统一税制,在调查耕地的基础上,实施“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的目的,初步建立了日本最早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另须说明,中大兄在拥立孝德“天皇”后又将国都搬迁至大阪,其目的似乎仍在于试图通过海路加强与中国等的联系及便于与“筑紫政权”的对峙。
第四,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即在这个时期,“筑紫政权”等最终被大和王朝消灭,日本只剩下一个“倭”了。人们由此可以想象,此时的大和王朝迫切需要一个印章,以为上述改革成果和与外部世界的对等愿望及自己的最后胜利背书。这个印章,就是之后不久成书的《古事记》(712)中的“倭”国号。
5 结语
“倭”是古代汉人对当时的广义日本人或政治势力的总称,并非对某一个日本古代部族或政权的特指。因“五王”受其政权性质和活动范围不在大和地区以及国际国内条件的限制,不太可能以“倭”作为自己的“国号”。也许“五王”在自己的“奉表”中使用过“倭国王”的词汇,但我们猜测那也并不具备正式国号的意义,而仅仅是根据需要,用汉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写出的。正式的“倭”国号则或是要等到其后人转战到大和地区并在那里建立起政权,或是在大和地区出现的另一个政权,在战胜其他政权包括拥有“倭”名号的其他政权,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当时的日本,有固定的国都,并在那里建立起官僚制度齐备的强大朝廷,制订了法律条文和年号,有余力和自信向东亚各国表明我乃正宗的“倭”后才可能正式以“倭”国号来表示其国家的。具体说来,虽然其时间仍不很明确,但较有可能是在飞鸟时代,这比在“五王时代”产生“倭”国号的说法更容易为人接受。
[1] 汪向荣.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17-126.
[2] 铃木靖民.古代国家史研究的历程[M].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83.
[3] 平野邦雄.世界大百科事典[M].东京:平凡社,1988:500.
[4] 关和彦.YAMATO王权何时建立,焦点的日本历史: 2 古代编[M].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90:53-54.
[5] 鬼头清明.大王与有实力的豪族:日本的历史 1 原始和古代[M].大阪:朝日新闻社,1989:250.
[6] 佐佐木健一.关东地区的后期古坟群[M].东京:六一书房,2007:27-29.
[7] 水野佑.増订日本古代王朝史论序说[M].东京:小宫山书店,1968:95.
[8] 上田正昭.大和朝廷——古代王权的建立[M].东京:角川新书,1967:67.
[9] 井上光贞.日本国家的起源[M].东京:岩波新书,1960:126.
[10] 和田萃.大系日本的历史: 2 古坟的时代[M].东京:小学馆,1992:62-96.
[11] 白石太一郎.古坟和YAMATO政权:古代国家是怎样形成的?[M].东京:文艺春秋社(文春新书),1999:72.
[12] 吉村武彦.倭国和大和王权.岩波讲座日本通史: 第2巻 古代1[M].东京:岩波书店,1993:177.
[13] 佐野大和.日本的古代文化:考古学要说[M].东京:小峰书店,1965:184.
[14] 川端俊一郎.继承中国南朝建筑式样的日本法隆寺[M] .郭凤英,译.东京:中日关系史研究,2003.
[15] 古田武彦.消失的九州岛王朝:天皇家以前的古代史[M].东京:朝日文库,1993.
[16] 宫崎市定.关于天皇称号的由来[M].东京:岩波书店,1993:303.
责任编辑:沈宏梅
Textual Research on Japanese State Title “Wo”
YU Shanshan
(Eurasian Languages Department, Fuzho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rade, Fuzhou 350202, China)
Due to the lack of definite historical materials, we could not know when Japan adopted “Wo” as its dynasty tit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ation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gime natures of Five Kings in Wo Dynasty, the 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and the reform results of Feiniao Times, we gained a deduction that Japan had no conditions to use “Wo” as its title in Five Kings Times. “Wo” as the title of a dynasty is likely to be adopted officially in Feiniao Times.
Japan; state title “Wo”; textual research
2016-08-0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础项目(12YJA75012);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16264)
于姗姗(1983-),女 ,福建三明人,讲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研究。
K313.2
A
1009-3907(2017)01-00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