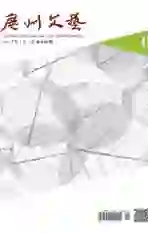广州大剧院惯演追记
2017-03-21陈世旭
花城广场在广州新中轴线的核心节点,数十万平方米的面积,数百棵参天大树,数十幢现代摩天高楼,悠长的木栈道和广阔的浮岛湖,構成充满现代意识的“城市客厅”。这些年客居广州,节假日与家人出行,或每有广州以外的朋友来访,我首选的游览地,总是花城广场。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广州大剧院一次观看演出的经历。
广州大剧院,一座世界性的现代建筑杰作,一座有着魔幻色彩的恢弘的艺术殿堂。
身边是中国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CBD,隔江是广州人叫作“小蛮腰”的广州塔,对面是广州图书馆新馆和广东省博物馆新馆,世界建筑界解构大师哈迪德把总建筑面积七万平方米的广州大剧院像两块体量不一的巨石随意摆放在珠江边上,整体的浅灰色极为低调,非几何形体的结构却又极为奇特多变,深刻反映出都市建筑繁复的特质。这个从屋盖到幕墙都几乎看不到横平竖直的一体化结构,没有一个节点相同,天知道是怎样完成的。以恣肆大胆造型享有盛名的哈迪德充满奇思妙想的设计图纸大多只能躺在她的抽屉里而难为世所用,但魔幻般的广州大剧院却同样魔幻般地成为现实。打造剧院声学系统的则是全球顶级声学大师哈罗德·马歇尔。广州大剧院的视听效果因此近乎完美。作为广州新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是南中国最先进、最完善和最大的综合性表演艺术中心。
两块巨石中,大的是一千八百座的大剧场及其配套设施;小的是四百座的多功能剧场。巨石峭壁下广阔的场外平台高踞在岸边,在夜里更让人眼花缭乱的珠江奔流着万紫千红。从城市的四面八方匆匆赶来、总算摆脱了交通拥堵的观众在地下车库停好车子,就直接搭乘电梯上到平台,直奔小剧场的入口,来不及去感叹珠江的流光溢彩。
那是广州大剧院几乎每年都要举办的国际艺术节。那天晚上小剧场演出的剧目是《空的记忆》,主题是“云端冒险”。这是台北文化周的一个组成部分。编导者声称用影像和舞蹈构筑了一个立体的记忆空间,即“记忆盒子”,装进对记忆空间的种种思考。仅仅是这样的说明,就足以让人心生无穷好奇。
剧场里一层层平缓下行的弧状梯台上几乎没有空位。近于黑暗的空间中,舞台依稀可辨。
舞台区由一片高起的木地板铺盖。台前并排五座巨型白色铁框绷纱屏幕,将深远的后方舞台暂时遮蔽:好像有光,有灯具,有吊杆,有即将上场的道具,有影子在暗中移动。
观众席灯暗。
一个黑衣女子在人们不经意间出现在观众席前面。天棚上有一支光线微弱的聚光灯照到她没有化妆的脸上:
“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来继续一段《空的记忆》的旅程。让我们的心静下来,让我们完全放松下来……”
全场寂静如空谷。
在一片幽暗的混沌中,一束光没来由地出现,带来了影子。随着光和影,人们隐约看见,一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不知从哪里半梦半醒似的游走到观众席中间,颀长、清瘦、苍白、忧郁,最普通的白棉布衬衫挽着袖子。也许他一开始就在这里,只是人们没有发现。
舞者手中的光束打在他的臂上、手上、明暗之中,也映照在头上。他似乎在检视自己,又像是在唤醒自己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胞。透过光束,巨大的影子、手的影子、手臂的延伸、转动的头的影子投射在剧场的空间中。然后,借着光,他的影子滑落到舞台上。
光和影,开启了第一道叙事线。
偌大的空间,就那么一束光和几缕似有或无的烟,与舞者做着光影的游戏。影像作为记忆的载体,来自投影机的光束。光束投射的对象,是影像,也是记忆,是影像与记忆的互文。透过光,它们解释彼此,相互补充。舞者用身体、四肢、手指,切割光、梳理光、雕塑光、变换光影的形式,一路上引领着一场探索,像是一盏探索自己也探索空间的灯,成为一把开启空间的钥匙。
我想起《圣经》的“创世纪”: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也许没有必要谈论宗教,只是情境颇为相似。
灯光不只是提供照明,而是相对于舞者的另一个被观者,时而与影像对话,时而呈现舞者当下的感受,时而营造舞台的氛围,成为表演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使得作品有了一个微妙的性格,同样在告诉人们一些远大于技术与设计层面的人生道理。
慢慢地,影子流动到立在舞台最前面的五座纱幕上。舞者飘忽进入缓缓开启的纱幕,进入一个与观众隔离的世界。
一个没有梦的梦境。梦尚未出现。舞者,是记忆的拥有者,又是记忆本身,还是被记忆的那个个体。
舞者坐上舞台左上方一把普通木椅。说话。说话的方式绝对真实。观众就在现场。只是隔了巨大的纱幕。
嘴唇的影像出现在纱幕。大气一样的音场中有一连串可以感知的喃喃自语:
“我要讲一个故事。”
深邃的空旷中,话语本身没有绝对的逻辑。语言随着情绪如同舞者使用肢体一般滑入身体。一道纱幕为他打开,他走进记忆之门,或者,梦的入口。
有椅子的区间灯光转暗。城市影像进入。
远的,大的世界。开始是宁静的,平稳的。
然后,出现了一些裂缝。每个切面上时间开始不一。
然后,舞者在半透明的纱幕后舞动。那是另一个时空,一个过渡空间。无限复制的环景影像,移位莫测的巨大纱幕,投射出遥远的海岸线、楼房中空的泳池、无人的地下道、行进的列车、极其简单的单人房间、工地和大卖场……动作。私语。曾经听过的一首外国歌曲……绵延无尽。城市亦如密室。舞台上的木桌、木床、木椅与虚像的车厢、车窗一样,也是一个移动的载体,沉浮在光影与呼吸间。透过影像所构筑的世界,超越了现实的存在感。虚实交错的流动中,舞者也成了一道流光,梦境一般混杂在日常生活的浮光掠影里。
个体的存在感和幻影同时在舞台上被建构起来。人们无法区分真实的实体和幻影之间的差异。
纱幕闪烁着完整的移轴镜影像,与后面的舞者呼应。这些半透明的纱幕时而空白一片,时而贴着影子,时而载着影像,像是记忆的片段,也像梦一般地在舞台上飘来流去。这形式其实就是这作品的本质。难以控制的游弋状态,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没有更多的奇幻场景和道具来打断作品梦境般的流动,使得观众在不恰当的时候“醒”来。一杆挂着数字符号的衣帽架,一格会发光的抽屉,一柄透光的雨伞,一捆好似拉不尽的线团,以及大把凌空飘落的碎纸花……出现又消失在演出现场。随着演出的进行,时光的流转,有的逐渐淡了,有的逐渐浓了,有的看不见了——虽然依旧存在。时间也许是冷色,因为房间很暖。
一座纱幕出现了海的波纹,渐渐向两边扩散。海的平面有落差。舞者像弓一样躺在地上。辗转反侧。站起。另一座纱幕上,舞者在夜里离开家。地上有水的倒影。枯树。有人走过。
窗口。可能是车窗,也可能是建筑走廊的落地长窗。外面的时间宛若某种车窗世界。某扇窗上有用移轴镜拍下的一个男子。漫步和疾走。
洞穴。深长的,永无尽头。一个茫然的男孩,侧面,越来越小的背面。洞壁疾速后移。
舞者在环景中。缓缓移动的投影纱幕创造了异质空间的意象。在那个空间里,舞者透过现实世界与他空间进行凝视。光与影像模糊了真实世界之间的界限,观众面对一个夸大的意象,进入冥想中的个人的微观世界,并在其中徘徊、阅读大千世界呈现出的万花筒般的繁复意象。半透明的投影纱幕,时而投射影像,时而投射舞者的剪影,增生出多重意象迷惑着观众的感官,让人们难辨虚实。舞者用轻柔的肢体回应人在日常生活里的心绪流变,在一片光影交错的谜样空间里引领人们进入他的微观世界看到最细微的真相。他观察影像中穿梭在家里、城市街道、车站月台、车厢里的自己,他或坐或卧。好像除此之外,他对影像中的“我”一无所知。那个“我”是梦境呈现的证据,而真实的“我”,反而更像梦幻。梦与真实混淆在同一个梦里,躯壳是主体,内在却是抽离的客体,相互映证,相互制约或无从制约。环绕舞者的一切场景似乎都是他的一部分。而他用近乎无意识的梦游舞动着身体进入忘我状态,让身体像想象力一样天马行空地诠释他的梦境,轻盈的肢体表现的不是喜怒哀乐,而是传达出独特的生命体验。
这是一个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世界。记忆流动,影子摇晃、颤抖。空间不断变化,试图拉远,拉长。舞者其实等同所有的人,“他”是中性的。“他”,是他,他们;也是我,我们。“他”没有诞生,没有死亡,没有前因后果,甚至,没有“故事”。一种“没有落地”的状态。
这是一场关于生命的复活与苏醒之事。
舞者穿梭于空间。我们想……我们说……我们去……我们跳舞。那些户外拍摄的影像,都转译成此刻舞者的内心风景。现在的舞者与影像中过去的舞者共舞。移动的纱幕与影像,一次次重新排列组合,试着重组记忆或者记忆衍生出来的感受。
目不转睛地盯着在光影中飘忽的舞者,我陷入一种错综复杂的情绪:这是一幕戏?一场独舞?一个影像魔术?没有清楚的逻辑在走,每一件事情都是暧昧的,必须自己去看到一些东西。
镜子,窗户,飞行的云,漂浮的世界。极梦幻也极真实。一道斜后方投出的立体光墙,加上烟的效果,使舞者在游走于两边时,发生了肢体在穿越时空时被切割的错觉,令人震惊。
质朴的吉他弹拨声,让人听见了一次旅行,听见了流动的风景。编导者预先在排练场录下了舞者跳动的声音、纱幕滑动的声音,音乐和这些真实采集的声音以及那些听不见却存在着的声音融汇,活化了关于记忆的听觉想象,贴近了《空的记忆》的质地。观众可以自由地在看到的东西里有自己的想象和诠释想象,与此同时,感受艺术家们想要传递的意蕴。
环景影像同时在四个纱幕上出现。突然加入了高频声响,打破了肃穆。观众进入一种身体被颤动的紧张。
前面出现过的所有片段一再重叠出现。
瞬间是永恒的相对。记忆的瞬间空白。瞬间想不起来,一片空白。一首流动在极简事物的微光长廊、像梦幻一样往复层叠的影像剧场的诗篇如歌如诉。
五座纱幕全体向前推进,再推进。环景影像也在某种神秘的作用下向前推进。
数次出现舞者若有所思的脸部。
失序的象限。离开的时刻。时间穿越。风,还有树影。列车旋转,失去方向:上或是下?舞者向前走去,与记忆道别。蓝天?雨天?巨大的车窗与现场渺小的人……
戛然而止。
当观众的目光游移在等比例甚至更绵延的视觉空间里,不由自主地跟随舞者的身体摇荡,虚实流畅交替,一种新的语言风貌、一种相互矛盾冲击的审美经验油然而生。
舞者回到白色的巨型纱幕后面。
剧场灯光亮起。
一个小时的演出结束。
全场掌声。不是那种雷动的,是克制的,激情沛然。
演出結束了,又好像没有。没有所谓“故事”。在一个抽象的作品中一定要挤榨出某种“故事”,比如一个人在房间里醒来,然后外出,遭遇了种种,之类。这是一趟透过感性的观赏经验来探求最基本的哲学命题的旅程。在这趟旅程中,人们听从一个有如仪式中的祭师一样的独舞者的引领,放弃语言,放弃逻辑判断,依靠感官和梦的经验,在一个洞穴中穿越虚实,进出时空。以至于相信,这是一趟没有终点的旅程,即便散场之后,还会在同一个洞穴中追逐自身的光影。
观众静静坐着,似乎凝固在《空的记忆》里。
真是一场华丽而成功的“云端冒险”。作品的语言,不管是影像、光、身体等等,很难用文字表达,必须到现场来感受。整个演出旅程,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文本可以跟随,而像是在分享彼此对于记忆的一些感觉和想法,以及自己过去的经验,聊天式的交流是创作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是一种加入了电影感的新媒体表演形式。艺术家们试图用舞蹈将不同时空的影像缝合,把看似不同的范畴关系交融于观众眼前。延续近年透过剧场、影像对记忆的探索,以“空”和“记忆”为核心发展主轴,运用环景摄影、即时影像处理、感测器与无线舞台装置的整合,创造出一个虚实并存的“空的空间”,借由表演者驱动外在物质世界的变形,呼应其内在抽象的心理状态,呈现出心灵景观的有机流动……
而剧场,为这一切的实现提供了最充分的可能。
对我个人的艺术欣赏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经验。我因此对广州大剧院有一种特别的好感。一有机会,我都会特别向朋友们介绍这座世界性的现代建筑杰作,这座有着魔幻色彩的恢弘的艺术殿堂。
责任编辑 高 鹏
陈世旭:著名作家。上世纪80年代以《小镇上的将军》一举成名。近年其作品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灵魂漂泊、精神成长进行了精当描述”,连续推出两部表达当代知识分子焦虑的长篇巨著——《边唱边晃》《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白色》。先后出版长篇小说《梦洲》《裸体问题》《将军镇》《世纪神话》等以及《风花雪月》《都市牧歌》《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陈世旭卷》等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等。发表有关先秦诸子、中国小说史及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并多被转载。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惊涛》获全国第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马车》获全国1987年—1988年优秀小说奖、《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