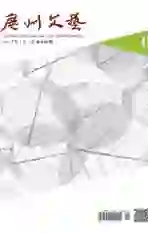狐狸跑过雪地
2017-03-21赵柏田
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语言
南方的冬天如同春天,小风轻寒,花自开落,空气里都是恋爱的气息,如此好天,正宜于讀诗。2015年的开卷阅读是穆旦的《诗八首》,这组诗作于1942年初春穆旦在西南联大时,时年24岁,正是光华四射的年龄。“静静地,我们拥抱在用言语能照明的世界里,而那未形成的黑暗是可怕的,那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那窒息我们的,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语言……”这组诗因印于金宇澄的《繁花》封底,所知者渐众。这是新诗里最有光芒的一首,我见之心喜,是因为诗里出现了那些日子我经常在想的一些词:“言语”“照明”“爱”“秩序”。这是一个怀爱之人说出的话,“从这自然底蜕变程序里,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他说过往的影像里的你已不是你,并为之黯然神伤。其实我们所爱者,都是时光里一个“暂时的你”。所以我们写信、读信,都是为了让这一个“你”站在“言语能照明的世界里”,那个言语构成的世界,“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可是我们向往的,更是在言语所不及的黑暗里——“你底年龄里小小的野兽,它和青草一样地呼吸,它带来你底颜色,芳香丰满,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
着 魔
年初坊间新书还不是很多,侦探小说依然是最大的遣兴读物,劳伦斯·布洛克《繁花落尽》的好感仍在,又读了《小城》。严格意义上,这不是一部侦探小说。他让凶手——一个在“9·11”死去了亲人的白人老头,在全书三分之一处就早早出了场。透过这个老人的眼睛来看纽约,这个城市是一个怪物,它需要生命的献祭,无数牺牲者的灵魂进入城市的躯体,让它变得更伟大也更丰富。这个熟悉纽约城所有掌故的老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暴虐的凶手?劳伦斯·布洛克告诉我们,他在报复这座城市,他是在用血与火完成一幅杰作。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被一股魔力控制了——他们都着魔了一般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走。前警察局长为权力着魔,作家克雷顿为金钱世界着魔,美丽不可方物的画廊女主人苏珊为深不见底的情欲着魔。这股魔力卷着他们跌入到城市不可究诘的深处。这部小说如果另起一个名字可以叫《着魔》。
我只想欺骗死亡
《入夜》是布洛克的前辈、悬疑小说作家康奈尔·伍尔里奇的未完成作品(由劳伦斯·布洛克续写完成)。这个大萧条时期的小说家是个制造惊恐的高手。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他都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去世后他的写作也停顿了下来。有位小说家朋友如是描绘他的晚年:“原本有棱有角的地方,现在都变成软绵绵的胶状物质,按下去,都不会反弹。”但是他的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略带湿润,就像孩子一样好奇与脆弱。”
小说女主玛德莲误杀了一个年轻女性,陷入了自责的折磨中,她循线索找到了女性生命中的两个冤家,一男一女,决意代为报复。她迂回在两个人的世界中,活着的目标就是伺机摧毁他们。这个小说证明,即使在生命最后的凄苦岁月,他也没有丧失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神奇笔触。伍尔里奇去世十七年后,出版商把这部残缺的书稿交给布洛克,请他整理后出版。现小说五章,前二十几页约半章是布洛克补写。小说的结尾,也是布洛克扣准伍尔里奇的结构、调子,画下了完美的句点。“伍尔里奇笔下的主角不是饱受罪恶感的折磨,就是浸泡在酒精之中”,布洛克这话实是夫子自道。
在遗稿中伍尔里奇曾有这么一段话:“我只想欺骗死亡,我只想在我生命中最熟悉的黑暗即将席卷而来将我吞噬之前,克服一点点,在我已然逝去之后,我也只想再短暂地活一会儿。写作者可以凭着他的作品在人们心中长久留痕,这是写作最大的酬劳。”
写作的暗黑与不可知
许多作家都有笔名,笔名和现实世界中的本名放在一起简直是两个人,他们用笔名写作就像穿着一件隐身衣一样,有时候笔名甚至成了“一个秘密的逃生舱口”。如同斯蒂芬金《黑暗的另一半》书名所揭示的,笔名就是作家“黑暗的另一半”。小说的主人公赛德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在以本名出版了几本不温不火的小说之后,又化用“斯塔克”的笔名写了几部罪案小说,未料名声大起。男主后来决定放弃笔名,然而这引起了他的化身斯塔克的不满,这个本来只是虚构的人物竟然从墓园里跑了出来,到处追杀导致作家放弃这个笔名的经纪人、记者和编辑,他给作家本人打电话,还跑到作家的家里威胁他的妻儿,目的只是为了让他答应继续以这个笔名写作小说。虚构的人物突然活生生地出现,并以充满暴力美学的杀人手法制造一个个凶案,这个小说披着恐怖小说的外衣,实则是在为小说家吐槽:是人控制小说,还是小说控制人?小说家们不过是被笔下人物控制着的傀儡。斯塔克的杀人手法干净利落,且别出心裁,当他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拖着一具腐烂的身躯(“一具快要烂掉的稻草人”)到处晃来晃去时,真是会让胆小的读者惊声尖叫——斯蒂芬·金说,这本小说,只适于“神经粗壮”的重口味读者。小说最后一幕,成千上万只麻雀(它们是死亡灵魂的摆渡者)抬着一个男人被啄空的身体飞上天空,去了他该去的地方,就如同一个邪恶的童话。
一部恐怖小说居然是一部探讨写作秘密的小说。斯蒂芬·金认为,写作者笔下的这一个和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个总想要吞噬另一个,这就是写作的暗黑与不可知。
母猪吞吃了自己的猪崽
东欧作家,犹太人,这是丹尼洛·契斯身上与生俱来的标识。短篇集《栗树街的回忆》,是一组写童年生活的短故事,讲一个男孩安迪和一只叫丁哥的狗住在一个叫栗树街的地方,他写了各种充满童趣的生活:放牛、尿床、初吻、捡蘑菇、马戏团。他片断式的书写很有一种抒情效果,类似叙事曲集,有诗意——那种冷静、克制的诗意。契斯的另两本短篇集《达维多维奇之墓》《死亡百科全书》更显功力。《达维多维奇之墓》写极权制度下人的毁灭。背景是大清洗这段历史。这个短篇集由七个短篇组成,叙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个职业革命者的命运。他们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据说小说的故事来自卡尔罗·希塔伊奈尔的回忆录《在西伯利亚的七千个日子》。这些革命者和知识分子,他们的生平充满传奇,暗杀、暴动、参战、流亡、被捕、审讯,最后无一例外遭到自己阵营的清洗,受尽折磨后走向死亡——母猪吞吃了自己的猪崽。
丹尼洛·契斯的最大辨识度在于对真实材料的运用。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历史学家,在档案、回忆录、传记和新闻报道里爬梳。他在歷史的预设框架结构下,建立了一个由想象和细节组成的文学世界。契斯认为,在经历了这个世纪的历史之后,幻想以及浪漫主义已经失去了意义,现代历史创造的是这样的现实:作家只能赋予真实的事件以艺术形态,在必须的时候要创造它,就是说,用真实的资料作为原始材料,运用新的形式并通过想象来成就它。
这是一个有着强大的理性思考能力的作家,他要在薄薄的几册短篇小说集里概述和检讨二十世纪欧洲的全部历史。在写了纳粹和苏联制度下的残废后,他陷入了对形而上的残废的迷恋。《死亡百科全书》打通了神话、文献与想象的边界,九篇微缩纪事的主题是探讨无神论者的死亡。
《达维多维奇之墓》写审讯者与被审讯者的角力。最后主人公在多年的监禁后越狱,面对前来搜索的队伍,纵身跳进钢铁厂的熔炉,他曾经想要摧毁一个旧世界,如今却不想再看到这个新世界。这是一个关于毁灭与自我毁灭的故事。他以一种现代主义的超然风格和反英雄形象,告诉读者这些残酷的悲剧是多么没有意义。另一篇《西门·马古》,写一个渎神者对上帝的质疑,基督教建构的世界秩序在他的质疑中消失了。
东方悟道者
2005年写过一个王阳明自画像的小长篇《岩中花树》后,经常会有人来找我谈谈王阳明。年中,重庆出版社推出了冈田武彦先生的三卷本《王阳明大传》,责编女士早早寄来了书,要我作些推荐。我读此书,欲先知其人,因为坊间有关王阳明的书实在太多了。
冈田武彦先生是个东方悟道者,真正的阳明心学的践行者,八十多岁了还多次来中国寻访阳明遗迹,贵州、南昌的许多古迹修复,包括王阳明故居的修复,他都捐助了。他的这部《王阳明大传》最出彩处,是对阳明《拔本塞源论》(即《答顾东桥书》)一文的逐句解析,这一解读基本上厘清了心学的脉络。大道至简,愈简易愈是贴近内心,不须枝枝叶叶外头去寻。这种观照对现世自有一份醒示在,现代人更要有这种对人生的清醒观照。
此书是一部关于十六世纪一个思想家的严肃传记,也是一部人的正剧。中国传统思想家,从孔子时代起,都是向后看的,他们对传说中的三王时代的政治和纲常伦理有着一份天然的亲近,总觉得当世是礼乐崩坏了的,最好的制度就是恢复到那个传说中的时代,所以人家向孔子问礼,他说“吾从周,吾从周”。从这个大背景来看,王阳明也无法超越。他不可能重建一套道德和话语的语境。王阳明童年时代说他的人生理想是成为圣人,然后格竹格物,上下求索而碰壁。但为什么作为中古时期的思想家他能奇峰突起呢?他在二十七岁那年检讨自己的人生,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他“初溺于游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辞章诗文、神仙之习、黄老佛家。游侠是春秋的风习,骑射是战国的武力,辞章诗文对应两汉,神仙、黄老和佛家,则是魏晋和六朝以后的风习,说是检讨,实际上是自得的,他实际上是以一己之身,完整演绎了一遍早期华夏文明史。“至良知”的思想学说由他发轫,离不开他独特的、跌宕的人生轨迹,尤其是人生困境中的自拔,但这种思想、学养和累积,也是不可忽视的,它使一个人在荒凉的时代里,在贫瘠的时代山岩上,开出了灿烂的良知之花——它实际上是从困厄的时代向内转,从心灵里生长出来的,所谓“大道在人心,千古未尝改”。这是一次儒学的内部中兴,一种向内转的道德和伦理规范的改良,这种改良的实质就是给心一个位置,给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一个位置,“尔心底一点良知,便是尔自家的准则”。
以前读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写戴笠的传记《间谍王》,魏斐德说,他打量传主的一生时,就像与毒蛇对视,老是会感到被魅惑。王阳明这个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所有接触他的人感到的“魅惑”首先会是一种“思”的力量,继而是近乎完美的人格力量,那都是生命中向善的一种牵引力。此书很好地传达出了这一心学精髓发生、形成及至大成的惊心动魄的经过,可作“信史”来读。也因为作者与传主实现了心灵的接通,它不是枯燥的高头讲章,自有一份生命的情意在。
美学乃伦理学之母
2014年《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推选年度好书时,我对王洪波兄说,有两部新书因年底刚出,许多榜单多有遗珠之憾,一本是裴士锋(台版名史蒂芬·普拉特)的《太平天国之秋》(此书我已撰文《近代史的黯淡一刻》专门介绍),一本是布罗茨基的《小于一》。今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趁着《小于一》的良好走势,推出了布罗茨基另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布罗茨基引用阿赫玛托娃的话说,诗从垃圾中生长出来,散文之根也并不更高贵一些。岂止不高贵,他是看不上散文的。但在英语世界给他带来巨大声名的正是他看不上的这些散文。全书二十一篇,细分有回忆录、旅行笔记、演说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文类,其叙事之繁复,有如帕慕克描述过的细密画中的东方地毯图案,而其细腻、规整、韵律感,又非诗学大家不可为。尤其是其中有关诗与散文的言说,正是通向布罗茨基的诗歌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伦理观和世界观的一把钥匙。
这本《悲伤与理智》和之前的《水印》《小于一》,是我一直想写又没有力量写出的那种文论。桑塔格所谓好的文论须得有艺术的感受力、批评家的力度、文论家的文体意识,布罗茨基在这本书里基本做到了,诗歌给了他热情和形而上的支撑,散文给了他表达的自由。好的文论,在布罗茨基看来就如罗盘,他在这本书里自制了一个罗盘,一片特定的海域,和映照在海面上的或暗淡或明亮的星座。文论家的境况,布罗茨基以其才力与笔力分作三类,一类是无知无识的雇佣文人式,一类是对某种特定的写作方式有偏好的牟利者,第三种,也是布罗茨基最为看重的,是天才作家型,如同博尔赫斯这般,这样,他的评论文字就成了兼具诗与散文之长的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读者会止于阅读这些文字而不须再去阅读那些书籍了。《理智与情感》正是这样的天才作家方能写出的文字。
此书开篇《战利品》,布罗茨基写战后出生成长的一代人在西方物品的涌入中确立的对西方的爱。他们一进入世界就被各种各样的外来物品包围:肉罐头、收音机、唱片、电影、明信片上的欧洲、轿车、军用暖壶和手电……他爱这些东西,爱它们所来的西方。“人就是人所爱的东西,他之所以爱那些东西,因为他就是那些东西的一部分。不仅仅是人,物也一样。”这些东西成了他成长中自身的一部分:“我们在西方、在文明中认出了我们自己的某些东西。”早年坊间有一本布罗茨基的选集,取名《文明的孩子》,也是具来有自吧。
布罗茨基的卓立不群在于他不合时宜的骄傲,他如是申明一个诗人的伦理学观点:美学即伦理学之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好与坏的概念首先是一个美学概念,先于善与恶的范畴。“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是不幸。”世界可能是不堪拯救的了,但个体可以,而拯救个体的正是美,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美拯救世界。这可以视作布罗茨基面对世界的立场,一个诗人的立场。
男性迷宫小说
今年的外国作家文论,值得推荐的还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好奇的追寻》。这是谈她自己和别人小说的一部札记性作品。阿特伍德评帕慕克的《雪》,说土耳其民众读他这个小说,“就像触摸自己的脉搏”。她把这类小说称作“男性迷宫小说”。其主要元素为:命运的扭转、辗转落到自己身上的阴谋、复杂微妙的诡计、越是接近越往后退的神秘事物、暗淡的城市、夜间巡游、身份失落感、流亡的主人公。“它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德·昆西,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康拉德,其他类似的作家还包括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唐·德里罗和保罗·奥斯特的小说,还可以算上哈米特·钱德勒的惊悚小说。”
创造灵魂的那些人走了
2015年,有几个喜爱的作家离开了这个世界。4月13日,87岁的君特·格拉斯去世,同日去世的还有《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作者加莱亚诺。一直以为我和格拉斯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死讯告诉我,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同一个世界。2006年春天,有一周时间在波兰,他们说格拉斯就住在格但斯克(他小说中的但泽),但最后还是没去那个港口城市,去了米沃什最后居住的城市格拉科夫。这是我与格拉斯相距最近的一次。这个作家的伟大不只在于唱碎玻璃或在五条裙子下做爱的想象力,更在于启蒙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我曾经像喜欢《铁皮鼓》一样喜欢他的回忆录《剥洋葱》。
7月21日,84岁的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在纽约去世,广州一家读书杂志的稿约,让我有机会回顾将近20年读他的历程。套用一句话说,在1997年夏天阅读了《拉格泰姆时代》后,我可以宣称与E.L.多克特罗及他的作品有一种很私密的关系了。书是收在译林出版社“后现代主义文学丛书”里的一种,封面好像是好莱坞某种老电影的剧照。一个县城里的青年小说家找这样一本不起眼的书来看,完全是一桩意外,他根本不知道E.L.Doctorow是何方神圣。他或许只是想看看一种别样的人生,或许是寻找写作的灵感。他没有想到,此后对这个作家会有将近二十年的持续关注。
《拉格泰姆时代》这个小说写的是一战前的美国生活。这个小说让我着迷的,是多克特罗对声音的迷恋。写出这个小说十余年后,在纽约92街YMHA演讲厅与《巴黎评论》的一个对谈中,他谈到,触发他小说的,总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声音,一个影像,也可能是背水一战的深刻体验,反正什么都有可能。2007年,多克特罗写美国南北战争的新长篇《大进军》(The March)由国内素负声望的99读书引进出版,这个小说让我迷恋的依然是声音,战争巨兽发出的巨大喘息——“他们有六万人,挥舞着一把三十英里宽的毁灭性的大镰刀,横扫过一片曾经物产丰富的土地”——它迈着笨重的、摧枯拉朽的步子,拉动着小说向前飞奔。
诚然这两个小说里交汇着多种声音,有着美国精神引导下对人性的追寻。作为作家同行,我更看重的是后现代作家进入历史书写时,传达出的方法论的新鲜气息。我在第一个长篇小说《赫德的情人》中表达了对多克特罗(另一位是尤瑟纳尔)的致敬,历史的尽头是小说,正是他对我的启迪。
往往,他写一本书时是因为听到有声音在头脑里响起,而等到书写完了,“这本书它自己发现了自己的声音”。“每本书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不是作者的个性。它在自说自话,而不是作者在说话。每本书都与众不同,因为作者并没有赋予每一本书同一个声音。”他是那种让声音听得见、让语言看得见的作家。
在刚刚出版的《买办的女儿》的“跋”里,我引述了多克特罗的一句话,写作“就像在夜里开车,你永远只能看到车灯那么远,但你能这样开完全程”。他是一个洞悉写作秘密的人,他知道灵魂如何被创造。因为他明白,写作所带来的馈赠永远都不在你的掌控之中,它不仅仅是某种想要表达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你在写作的过程中才会发现自己在写些什么。现在,这个创造灵魂的人已经走了,他的新工作,或许就是去记录天堂里的声音。
从小说里寻找历史
阅读老马尔克斯是每年的例行功课,继去年虐心的《族长的秋天》的阅读之后,今年夏天读的《苦妓回忆录》,是他晚年最后一部作品。从小说开端引述的川端康成《睡美人》中一个句子看,两个小说还是构成了互文性。这个老套的故事框架之外,马尔克斯还是保持着蓬勃的创造力。妓院、内河码,这些场景还是让我联想起《霍乱时期的爱情》。加缪的《第一个人》也是一次新鲜的重读,读至“贫穷是一座没有吊桥梁的城堡”,我甚至可以回忆起九十年代读这段时那个夜晚的细节。夏天有过一次北大之行,因正读彼得·盖伊《感官的教育》,路上带了他的另一本《施尼兹勒的世纪》去读。《感官的教育》从一个少妇的情爱日记着手,写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爱风气。《施尼兹勒的世纪》则是一本谈论19世纪中产阶级趣味和内心生活的书,彼得·盖伊让那个时代的作家、浪荡子施尼兹勒引领着我们,去一一领略布尔乔亚的客厅、居室、家庭关系及性与爱,让我们看到维多利亚时代拘谨表象下的开放与坦率,着墨尤多的是对施尼兹勒疯狂逐爱生涯的记述。这位新文化史家是一个难得的打通了历史和小说的家伙,他的方法是从小说里寻找历史。我犹记得十年前读他的另一本书《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时的愉快心情,“只要适当说出事实,则一切罗曼史黯然变色”,他引述的惠特曼这句话,曾是我一个时期写作的方法论的渊薮。
格式化背后人伦世界
今年秋天,赵园先生清癯的身影多次出现在北京大学课堂和“北大博雅论坛”,那是她的《父子家人》出版后不久。承她看重,书出版后就亲笔签赠。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到明清之季的思想文化,赵园先生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的关怀与兴趣。《明清之季士大夫研究》把士人置于易代之际这一历史的关隘来考察,探究他们生死存亡之际的种种选择,和行藏出处背后的深层动因,已成为思想史的经典著述,紧随其后的《制度·言論·心态》则从士人言说的态度与方式来考察他们的“精神气质”,这一本《家人父子》,以“父子”“夫妇”为入口,由家庭伦理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
人伦,家庭伦理,或曰伦常,是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面,也是维系社会秩序的一个基本支点,即梁漱溟所说,“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用赵园自谦的说法,从伦理、或者家庭关系进入思想史,是“非严格”的,因为经院式的思想史,大抵是在向着观念史的方向走的。赵园先生是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进入明清士人世界的,她以文学对人的关怀进入思想史,这一治学经验是她迥异于从史到史的其他学者的,也是她的明清史写作宝贵的异质性。此书探讨的是伦理的规范性要求内外、知识人如何处置其家庭内部关系,从方法论上来说,比之伊沛霞、高彦颐等汉学家或许并无颖异之处,但赵园先生的研究一向重视对原典的考辨,此书取材,和她先前的著述一样,大多从明人文集及墓志铭、家传、年谱、家谱、族谱、日记等抉取资料,从中读出人情,读出人的世界,使我们从格式化的古典文学和文化史的叙述背后,得以一窥士大夫的家居情景,发现古代中国人曾经如此丰富的生活世界与情感世界。
此书附录去年赵园在香港中大的讲演,可知她目前用力尤勤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由伦理的方面加以考察”,已经完成初稿的,有关于“文革”中人伦的变与常,有关于“文革”中私人信件、日记,有总题为《有限视角下“文革”中的私域与公域》的关于“文革”之于私人财产与公共财产的分析,其内在的研究思路,还是她一以贯之的对“人”的观照与关怀,从明清思想史到当代政治文化的考察,她所遵循的,不过是“严守学术工作的伦理规范”。
人的情感的历史
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估计中国的媒体第一时间也是瞬间木掉了。我从“豆瓣”还有什么地方读了她一些作品的片断。我读了,不想了,不再为村上春树叫屈。我觉得,他今年输给这个白俄老太太没什么好说的。上个月北京九洲社的朋友来宁波,带给我老太太的三本书。书是九洲社出的,实际出品的是磨铁公司。我断断续续读了,很受刺激。为什么说“刺激”这个感性的词呢,因为老太太写的对我的视觉和内心的撞击太大了,她对战争和灾难的呈现,太残酷,也太真实了。
她有一本书《锌皮娃娃兵》,写阿富汗战争,苏联每年出动10万士兵进入阿富汗,那些陣亡者被装在小小的锌皮棺材里运回国。当局欺骗说,这些阵亡的孩子是参加阿富汗的社会主义建设,修路造房子工伤死的,或是开心了喝酒喝死的。老太太写了这本书,阵亡士兵的母亲们无法接受他们的孩子参与了一场残暴而无意义的战争的事实,一次次把她告上法庭。她里面写一个战后归来的士兵,“整整有一年时间我不敢上街,身上没有防弹背心,头上没有钢盔,肩上没有冲锋枪,活像一个光着身子的人走在大街上。”还有,“子弹穿入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听见轻轻的击水声。”她记录一个小伙子的话:“您知道吗?人死的时候可难看了,他在战场上死的时候,可不像书本里写的那个样子。他已经被打死了,可是有几秒钟他还在奔跑,还在抓自己的脑子。”她写恐惧:“恐惧比勇敢更有人情味,因为害怕,你就会怜悯,即使是怜悯自己。”她还有一本写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新闻是这样叙述这一事件的:“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选择了让一名女性说,“我丈夫回家,把消防帽扔给儿子,不久后,我儿子得了脑癌死了”。前者是苍白的新闻体,看不到人,后者的表述是文学的。
她写他们的相信与不相信,写他们的幻觉、希望与恐惧,她写的不只是事件的枯燥历史,而是“人的情感的历史”。这种勇气和担当,是足以让中国作家惭愧的。除了道德意义上的担当之外,阿列克谢耶维奇更大的贡献是丰富了文学自身。她笔下那些战争的片断,让我想到巴别尔的《骑兵军》。“从文献走向形象” “记录声音”“不是事件本身的历史,而是人的情感的历史”,这是她的方法论。在她眼里,虚构和非虚构是相互流动的,见证者也不是完全中立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一直在寻找一种体裁,它将最适合我的世界观,传达我的耳朵如何倾听,眼睛如何看待生命,我尝试这,尝试那,最后选择一种体裁,在这种体裁里,人类的声音自己说话”。她说她是人们的耳朵。这种从文献中发现形象、打上自己独特的“灵魂的标记”的方法,与丹尼洛·契斯庶几近之,老太太自己也杜撰了一个“文献文学”,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打通了虚构与非虚构,经典与俚俗,这是文学的新传统。这种新传统,我们可以在博尔赫斯、埃柯以的福楼拜的《布瓦尔与佩居榭》里看到端倪。长久以来,正统的文学观都以为文学是杜撰出一些人物、情景、故事,以为虚构是达至文学真实的唯一路径,该是到了检讨和修整这种陈旧的文学观念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 姚 娟
赵柏田:1969年生。当代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赫德的情人》《买办的女儿》《让良知自由:王阳明自画像》,短篇小说集《万镜楼》《站在屋顶上吹风》,文集《南华录》《历史碎影》《岩中花树》《帝国的迷津》《明朝四季》《时光无涯》《我们居住的年代》《远游书》《双重火焰》等十余种。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十余年,主要涉足方向有明清江南文化研究、近代口岸城市现代性研究、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等。曾获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现居浙江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