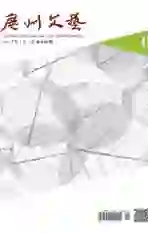经过一段时间的现代遗忘之后
2017-03-21弋舟
弋舟
一
《夏蜂》这本集子被收入“现代性五面孔”这套书系。动手整理书稿,循着编辑的思路以及自己对于“现代性”蒙眬的意会,我挑出了这十二篇小说。
编辑的思路大致是清晰的:作品首先要有“现代性”的指归。这个思路遵循起来并不容易。对于那个“现代性”的理解,不想不知道——尽管常常会挂在嘴边,可一旦要用它来落实自己的创作,才会发现,它是如此的复杂、如此的不可捉摸甚至空洞;它的边界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你若是真的要在它所规定的版图里行动,就会发现,你将很难给自己一个确凿的方案。
所以我说它“蒙眬”,所以对其我只能勉强地称之为“意会”。
在这种“蒙眬的意会”指导下,我所挑选出的这十二篇小说,大致上,无可辩驳,的确佐证了我对于“现代性”的理解。然而,定稿之时,我又对这个结论充满了犹豫。它们真的是我所理解的那个“现代性”吗?事实上,这样的一份结论是如此不能令我满意。我的不满意,并不是对于自己作品水准的遗憾——它们当然不是完美的。更多的,我是对自己兑现“现代性”时的无力和混乱而感到震惊。在这种无力和混乱之下,我想我一定是必然片面地、却难以纠正地误解着“现代性”。
整理作品时,蒙眬指导着我的,是这样一些词语——先锋、实验、早期、探索、破碎、跨文体乃至容忍有缺陷……这些,难道就是我所“蒙眬意会”的那个“现代性”?在我“蒙眬的意会”里,落实在小说实践中,原来“现代性”就是一个天然带有“早期实验性质的有缺陷并且在文体上都可以模棱两可的东西”吗?
天啊,如果它是,那么,我只能承认,如今我反对这样的“现代性”。
我从未给自己的集子写过序言,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第一次”里,我想冒点儿险,以一种“现代性”的方式,大段引用别人的论述:
对于艺术作品来说,没有哪个词比“探索”更没有意义的了。它掩饰了苍白、内在空虚、真正创作意识的缺失和低级的虚荣。“在寻找的艺术家”这一说法是何等庸俗的对贫乏的特赦!艺术不是科学,无须强迫自己进行实验。假如实验只是停留在实验的层面上,没有进入到使艺术家制作成品的隐秘阶段,那么就永远无法达到艺术的目的。关于这一点,瓦雷里在他关于德加的随笔中说得颇有趣味:
他们(德加同时代的几个画家)把练习和创作混为一谈,把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这就是“现代主义”。“完成”作品——意味着要把所有的创作痕迹隐藏起来。艺术家(按古老的要求)应当只能以自我风格肯定自己,应当不断努力,直到作品消灭了创作痕迹。然而,当对个性和瞬间的重视逐渐胜过对作品本身和其持久存在的思索,作品的完成性不但显得多余和羞于启齿,而且与“真理”“敏锐”“天才的显现”这些词相抵触。个性开始凌驾于一切,甚至对大众而言亦如此!速写获得了与画作同等的地位。
的确,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艺术已经失去了神秘感。今日艺术家要求一时而全面的肯定——给予他精神领域的及时回馈。从这个角度而言,卡夫卡的命运更令人震惊:他生前没有出版任何作品,在遗嘱中要求遗嘱执行人销毁所有手稿。从精神层面来说,卡夫卡的灵魂构成是属于过去的。因此他与自己的时代格格不入,万分痛苦。而号称当代艺术的东西大多是展示自我,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方法能成为艺术的意义和目的,当下大部分艺术家都践行这种有点存在主义色彩的自我展示。
先锋主义这一概念在艺术中是没有意义的。我能理解,它有点接近体育运动的意思。接受艺术中的先锋主义,意味着承认艺术可以进步。技术进步我理解,它意味着有了能更好完成任务更加完善的机器。艺术怎么能变得更先进:可以说托马斯·曼比莎士比亚好吗?
谈及实验、探索的说法,通常和先锋主义有关。但艺术中的实验指什么呢?尝试,看看是否成功?可如果不成功,就用不着去看了,这是失败者个人的事情。由于艺术作品具有美学和世界观上的价值完整性与完成度,所以这个机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法则生存并发展。可以把生孩子当作实验吗?这是不道德的,也是无意义的。
可能是那些主张先锋主义和实验艺术的人不辨良莠?他们迷失在新的美学架构前,被这些超出他们习惯和理解的概念弄得晕头转向,只求不出错,以至于找不到自己的准则?可笑的是,有人问毕加索所做的“探索”,对此他显然很不满,不过机智而得体地回答:“我不探索,我发现。”
千真万确,探索的概念能用在诸如列夫·托尔斯泰这么伟大的人身上吗?看到没,老人在探索!真是可笑!虽说某些苏联文艺理论家差不多就这么说了:他在找寻上帝和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也就是说,他在探索中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
探索是一个过程——不可能有其他理解——同作品的完整性来说,它们就好比一个人提着篮子在森林里徘徊着采蘑菇与已经采到满满一篮子蘑菇的关系。只不过后者,也就是那满满一篮子蘑菇,才是艺术作品:满满的一篮子蘑菇是真实不虚的成果,而森林里漫步只是一个爱好者个人的事情,只是散散步,呼吸下新鲜空气而已。在这个层面上的欺骗是蓄意的阴谋。瓦雷里在《达·芬奇体系导论》中尖锐地指出:“惯于愚蠢地将换喻当作发现,隐喻当作证据,把连篇废话当作妙语连珠,把自己当作先知,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恶。”
相较于一则“自序”,我引用得可能太多了一些。可我太想这么干了。我想以此来表明我对这一大段话的赞成和重视,立此存照,时刻提醒自己——某些我们自以为是的写作观念,会遭到多么雄辩的驳斥,甚至,對其的指控会严峻到“与生俱来的恶”!
这段话出自前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塔氏在电影艺术方面与费里尼、伯格曼并称为“圣三位一体”,其作品以如诗如梦的意境著称,主题宏大,流连于对生命或宗教的沉思和探索。伯格曼评价“他创造了崭新的电影语言,把生命像倒影、像梦境一般捕捉下来”。瞧,就是这样一位大师,对于他的一切评价都可以盛放在“现代性”的筐子里,但是他却如此激烈地驳斥着“探索”“先锋主义”和“实验艺术”。
“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艺术已经失去了神秘感”,它在相当程度上抹去了艺术那“神圣”的过程与结果,以一种“半成品”的方式怂恿、蒙蔽着创作者和欣赏者,于是,我们“迷失在新的美学架构前”,就像塔氏所严厉指责的那样,对“先锋、实验、早期、探索、破碎、跨文体乃至容忍有缺陷……”作出了“何等庸俗的特赦”。
可这十二篇小说的确又是我写下的。
如今,我应当为之汗颜吗?不,当然不。卡林内斯库在那本《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写下了这样一个章节:古代巨人肩膀上的现代侏儒。我觉得,用这个指称来认领自己今天的角色,是我所甘心的。我承认我的“侏儒性”,就像无从辩驳我是一个“现代人”一般;我也承认我视古代有着“巨人”的品性,这就是我今天难以容忍自己侏儒一般见识的根由。
王春林先生将我新近的作品评论为“不动声色的现代主义”,不管我是否真的在创作中兑现了这个评语,我都愿意将其视为写作的目标。因为,目睹了太多的“大动声色的现代主义”表演后,我这样一个“现代小说家”,实在是渴望重回古代的怀抱,按照对于一个艺术家那“古老的要求”,回到艺术那些亘古的准则里去。
“后现代主义者欢庆现代性的终结,让人们注意传统的新颖性(经过一段时间的现代遗忘之后),注意新事物的衰退甚至是腐朽!”这段话同样出自《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在这里,我无力再去辨析“后现代性”,我只愿懒惰地、按照我一己的情感,用直觉捕捉这样的语词——注意传统的新颖性(经过一段时间的现代遗忘之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现代遗忘之后!
这句话,竟令我这样一个小说家百感交集,几欲眼涌泪水。
二
感谢这套书系的策划者张鸿女士。至少,在我创作多年后,她给了我这样一个严肃的机会,让我直视那个似乎已经习焉不察的“现代性”,重新辨析,重新廓定自己的方向。那么,当我反省了自己“形式上”的“现代性”后,我必须从精神上,再次盘点一番自己对于现代性“蒙眬的意会”。
塔可夫斯基的那段话里提到了卡夫卡——“从精神层面来说,卡夫卡的灵魂构成是属于过去的。因此他与自己的时代格格不入,万分痛苦”。我想说的是,这段话,大致就是我对“现代性”偏执而又顽固的精神想象。
身为一个小说家,我还是愿意以一篇小说来说明我的这个想象。这篇小说,就是卡夫卡的短篇《判决》。
《判决》是卡夫卡写得较早的一个短篇,亦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品。这个短篇写于1912年9月22日的晚间。卡夫卡生于1873年,也就是说,《判决》这个短篇是他即将三十岁时写下的东西。
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判决》所写的大致内容: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是个商人,自从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一起生活,如今生意兴隆。这天早上,他在房间里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写完信后,格奥尔格来到父亲的房间,意外的是父亲对他态度非常不好,怀疑他根本就没有一位迁居到俄国的朋友,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着自己早死。突然,父亲又转了话题,质疑格奥尔格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位朋友,而父亲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并早已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了人家。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父亲骇然判独生子去投河自尽。于是独生子真的便去投河自尽了。
我们看看卡夫卡是如何开篇的——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美不胜收的初春星期日,年轻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在自己房间伏案给友人写信。
这是一个相当朴素的开头,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位“友人”只是某个抽象化了的概念,我们便会立刻进入到“现代性”的阅读语境之中。当然,读懂这样的作品很困难,我们饱受所谓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熏陶,想要重新建立一套阅读方式,注定艰难至极。为此,我特意查找了一些资料,对于这个短篇的解读非常多,但是论述者全部避开了小说中那个关键的“友人”,而这位缺席的“友人”,却是结构这个短篇时最不可或缺的要素。关于这篇小说的内核,卡夫卡自己说的当然最为可信,我们只需引用一下他的日记就行了:
乘修改《判决》的机会,我写下就我目前所认识到的觉得在这个故事中看清楚了的所有关系。这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从我身上自然而然生下来的产儿,满身污垢和泥浆,而只有我具有可以通过污泥触及躯体的手,也只有我有兴趣这么做——
那位朋友(文中那个在彼得堡的朋友)是父与子之间的联系,他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性。独自坐在窗前时,格奥尔格喜不自胜地玩味着这一共同物,以为已经赢得了父亲,一切在他眼前都显得那么安宁,包括那一闪即逝的伤感。现在故事的发展表明,父亲是怎样从那个共同物,即从那个朋友那儿突出自己,并把自己放在与格奥尔格对立的地位,他通过其他那些较次要的共同点而加强自己的地位,诸如通过母亲的爱和依从,通过对母亲的始终不渝的缅怀,通过最初确实是由父亲为商店争取到的顾客。格奥尔格则什么也没有,那个未婚妻在故事中只是由于父子同那个朋友,即同那个共同点的关系的存在才存在,同时由于尚未结婚,她不得进入那父子的血缘范围,因此轻而易举地被父亲排除了。那共同点的一切都是环绕着父亲耸立起来的,而格奥尔格只是觉得它是一种陌生的独立而形成的,他所保护得不够的,受到俄国革命之害的东西。正因为他除了看着父亲以外,别的一无所能,所以父亲对他的最后判决才会对他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
在这里,卡夫卡通过描写一个与父子俩共同关联的“对象”,来象征他们的某种“共性”,并且由此来结构小说。这时候,这个“对象”已经不是平常意义上的人物了,只不过,卡夫卡给了它一个“友人”這样的身份外衣。实则,它或者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干脆就是虚无本身和那个外在于我们的“世界”。于是,和这个“对象”默契与否,是否能垄断这个“对象”,才导致了父子俩的那一番争论,才使得冲突以及冲突的强度成立起来,并且,这一切的一切,才致命地荒诞起来——瞧,对于“对象”的缺失,最终导致了儿子的自尽。
卡夫卡把这个作品说成是一个“夜晚的幽灵”(它写于夜间而且是通宵),他说:“我写下它把它固定下来,因而完成对幽灵的抵御。”这个“幽灵”,在我看来,就是那位缺席的、造成对抗的、实则却是莫须有的“友人”。在这里,我更愿意将这位“友人”称为“对象”。它即是那个充满敌意的、包围着现代人的“他者”。而卡夫卡固定下来的,只是“一种陌生的独立而形成的,他所保护得不够的,受到俄国革命之害的东西”。
我们再来看看对于这个短篇标准的、教科书式的解读——
作品所描写的在父子两人的口角过程中,清白善良的兒子竟被父亲视为有罪和执拗残暴,在父亲的淫威之下,独生子害怕、恐惧到了丧失理智,以致自尽。父亲高大强壮而毫无理性,具有一切暴君的特征。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是卡夫卡负罪心态的生动描述,父亲的判决也是卡夫卡对自己的判决。主人公临死前的低声辩白——“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则是卡夫卡最隐秘心曲的吐露。这种故事的框架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是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具象化之后的产物。然而作品的内涵显然不在于仅仅表现父子冲突,更在于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生存在怎样一种权威和凌辱之下。另一方面又展现人物为战胜父亲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儿子把看来衰老的父亲如同孩子般放到床上后,真的把他“盖了起来”。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是出于孝心。在深层含义上,他则是想埋葬父亲,以确立自己作为新的一家之主的地位。小说在体现了卡夫卡独特的“审父”意识的同时,也表现了对家长式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与此同时卡夫卡还通过这个独特的故事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性和非理性。
不错,这样的答案标准极了,面面俱到,如果是高考答题,差不多可以得满分。但在我看来,它却粗暴地将一切简单化了,尽管它其中还含纳了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法这样的复杂趣味。尤其最后的那段句子——“与此同时卡夫卡还通过这个独特的故事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性和非理性”——这种句式,恰恰正是现代性所反对的,它强加给了这个短篇以某种需要达到“谎言”一般的力度才能得逞的道德感。当然,我在这里如此“化验”《审判》,同样具有着类似的风险。在我看来,现代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是排斥过分阐释的。这或者是我的偏见——面面俱到的分析,恰恰是对现代性最大的伤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悖论——现代性排斥“定论”,而“给万物下定论”,却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劣习。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卡夫卡是如何给这个短篇结尾的。当主人公令人惊悚地果真跳河之后,卡夫卡如此写道——
在这一瞬间,来往的交通从未中断。
多么绝望!荒谬之后,世界依旧荒谬地运转下去,于是荒谬便成为常规本身。
此前,卡夫卡几乎用了这个短篇百分之八十的篇幅,描写了父与子之间的辩论。这其实是卡夫卡一贯的创作手法——在整体性的荒诞之中,每个细节却是煞有介事地非常现实。这个短篇甚至可以看做是卡夫卡对于这个世界的申辩。这一番申辩,也可看作是一种自我的辩难。在这个短篇里,辩论的对象其实并不是父子俩,毋宁说,卡夫卡与之激辩的,就是虚无本身。于是,辩论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应当看重的,是“辩论”这样一个姿态。卡夫卡借用“友人”这一象征性的“对象”,完成了与世界还有那个内在的自己的激辩。尽管一切荒谬,尽管一切注定无望,但此番激辩,因为了人的执拗和煞有介事而具有了意义。作为一个内在的人,卡夫卡必定是一个经常有着不同的声音在内心激辩的人,他那些作为一个现代性的人的经验,就是这种内心激辩的真实写照。
德国学者G·R·豪克在《绝望与信心》中阐释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当今时代而言,绝望的存在可能是一个无以辩驳的事实,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绝望的背后,还有微弱的信心,还有希望的存在。两种声音的辩论,绝望与信心的交织,就构成了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一种有重量的文学,就应该多关注这些内心的争辩和较量,就应该在作品中建构起这种独特的内在经验,惟有如此,文学才能有效地分享存在的话题,并为当下人类的存在境遇作证。
这正是卡夫卡给予我们的信心和盼望。这也是我对于“现代性”精神的想象。在这个想象中,我不愿将“现代性”偏颇地视为一副颓废的面孔(它恰是卡林内斯库所开列的“现代性五面孔”之一)。今日之小说,之所以不能够令人满意,很重要的原因,除了因为小说过度做回了故事和趣味的囚徒,不再逼视存在的真实境遇,进而远离了那个内在的人,还因为其因因相循,在另一个方面,片面地放大了虚无与绝望。
一个内在的人,一个有存在感的人,一个勇于与世界和内心激辩的人,他的书写,代表的是对存在的不懈追索,而“不懈的追索”这一积极的态度,这一命定了的“徒劳的姿态”,这种“与世界和内心激辩的热情”,在我看来,却构成了现代小说的精神基石。而这样的基石,也许同样被我们正在“现代遗忘着”。
三
小说家给自己作序在我看来都是一件艰巨的事情,遑论试图给自己一个清晰的、经得起写作实践检验的立场。我知道我可能什么也没想清楚,知道我可能顶多依然身陷“蒙眬的意会”里,知道我的写作本身完全有可能还会和这个自序南辕北辙。好在,卡林内斯库自己也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译本序言中如是写道:
这些面孔说到底只是对我的研究假设的一些隐喻,我选择它们是为了更有启发性地表述清楚现代性这个关键概念的复杂历史,依我们看待它的角度和方式,现代性可以有许多面孔,也可以只有一副面孔,或者一副面孔都没有。
(本文为花城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现代性五面孔”“70后”作家中短篇小说集系列之一——《夏蜂》的序言)
责任编辑 梁智强
弋 舟:小说家。曾获郁达夫小说奖、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鲁彦周文学奖、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青年文学》《十月》《当代》《西部》《飞天》等刊物奖、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提名。著有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等五部、小说集《刘晓东》等八部、随笔集《犹在缸中》等两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