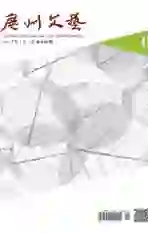暂借
2017-03-21葛亮
有这么一种说法﹐张爱玲的小说﹐是电影改编的陷阱。大意是﹐张文是参不透的文字圈套。再得心应手的导演﹐身在庐山﹐都从游刃有余变成捉襟见肘。李安让这番话成了局部真理。历数下来﹐最为让人耿耿于心的还有《倾城之恋》﹐目前触电的张氏小说中关乎香港的一部。
数年前﹐“皇冠”出版了张爱玲的遗稿《重访边城》,这部稿件的发掘实出偶然,起因仍是大热的电影《色·戒》。张爱玲的好友宋淇﹑邝文美伉俪之子宋以朗先生﹐应邀为“张爱玲、《色·戒》与香港大学”专题展览整理资料﹐发现了这部1963年张重游台港两地的中文手稿。这本是一桩好事﹐却让张爱玲与香港间的暧昧关联更添了一重雾霭。
在港大若干年﹐每天走过张爱玲走过的老路﹐其实并无太多的知觉。曾几何时﹐港大捧在手心里的是孙中山、钱穆和饶宗颐。张与港大的两不待见﹐的确饶有意味。
张对香港不即不离﹐有雄辩的理由。因为战乱﹐失去了去伦敦求学的机会﹐勉强留人于斯。香港说到底﹐只是一个暂借地。小说之外﹐张爱玲以散文立世﹐写到港大的﹐唯有一篇《烬余录》,这文章的基调﹐是灰黯阴冷的﹐透着恨和遗憾。事实上﹐这所背景显赫的殖民地大学﹐对张爱玲即使算不得礼遇﹐也并没有薄待。张爱玲自己也写过﹕“港大文科二年级有两个奖学金被我一个人独得,学费膳宿费全免,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这两个奖学金﹐分别是“何福奖学金”与Nemazee Donor Scholarship。两个奖学金都是颁给当年成绩最优秀的学生。然而﹐也正是这个两个奖学金造成了后来张在美国求职过程中与港大间的纠纷﹐都是后话了。
刨去以上世俗种种,港大对于张爱玲的爆发式的成名﹐算是一根引线。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开始于港大,她的处女作《天才梦》﹐其中一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几乎定下了她后来小说的基调﹐张迷们耳熟能详,这其实是篇学生征文,她念港大一年级时所写﹐那时候是1941年﹐还因此得到《西风》月刊三周年的纪念征文奖。张在1943年发表的小说中﹐八篇里有一半关乎香港﹐《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与《倾城之恋》。最末一篇几乎成了她的短篇巅峰之作。
香港在这些小说里﹐算不得是个值得称颂的意象。张特地为集子《流言》写了序言《到底是上海人》﹐其宣言式的表白显出十足的暧昧气﹕“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这大约就是问题所在。张对香港的书写﹐其实在演绎她个人的“双城记”。其间有点忿忿然﹐又有点讨好。这也难怪﹐一个骄傲如斯的人﹐在殖民主义氛围中仰人鼻息﹐确是不爽﹐到头来是要回到家里求认同。张无形间造成了两种文化形态的对峙﹐也是出人意表。《第一炉香》里﹐张将香港定义为殖民者观照下的客体﹐以一味奉迎的姿态扮演着“寡廉鲜耻”的角色﹐试图给“英国人”一个具体而微的中国,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在张爱玲的笔下﹐葛薇龙的堕落﹐多少是随着香港的堕落滑下去。葛薇龙是来自上海的好儿女﹐成了婊子﹐也是因为香港是个妓寮﹐清者难自清。
在香港生活逾五年①的张爱玲﹐对这座城市有着可触可感的认识。抬高到书写策略的层面﹐会发觉其在叙事中频繁地模仿殖民者的限知视角﹐对城市进行物化呈现﹐反讽之意不言自明。然而﹐张主观上又同时凸显了自己作为上海人的注视。以上表述饶有兴味处在于﹐“上海”对“香港”的优势﹐最终以殖民情境中的民族主体意识作了画皮。李欧梵解释道﹕“對张爱玲来说﹐当香港在令人无望地全盘西化的同时﹐上海带着她所有的异域气息却仍然是中国的。”而当张爱玲将之内化为一种文化优越感﹐指出 “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时﹐却时以边缘化的且带有利己主义色彩的小事件作为佐证﹐形成内涵与外延的落差。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篇散文﹐《烬余录》写在1944年﹐可说是张氏“小说香港”的脚注﹐也是篇让张爱玲落笔踌躇的文字。此时香港已沦陷﹐是二战时的围城。张在文中写﹕“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不相干” 恰是张爱玲最擅长的东西﹐无涉民族大义﹐自然亦非关“正史”。“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如此开宗明义﹐已为张的香港印象定下了基调﹐即宏漠的政治大格局之下的人生琐感。
这文章背景之下的张爱玲﹐正在港大担任了学生看护的职责。每日直面生死﹐职责本有高尚的面目﹐张看到的却是绝望与鄙俗﹐并且与种种“不相干”纠缠不清。张文中提及的“临时救护中心”﹐最早设在陆佑堂﹐位置在港大的本部大楼。这建筑曾经也在电影《色·戒》出现﹐是王力宏和汤唯们演练爱国戏剧的地方。可惜张不逢时﹐看到陆佑堂生生被炸掉了尖顶。后来“救护中心” 便转移去了“梅堂”(May Hall)一带﹐曾经是港大男生宿舍,这也是《烬余录》身后灰扑扑背景的原型。“梅堂” 其实并不黯淡﹐一百多年的红砖老建筑﹐现今还没什么破落相。黄昏的时候﹐从“仪礼堂” 拾阶而上﹐经过那里﹐还看得见夕阳里头有三两个男孩子在拱廊前的空地上打篮球,那局面﹐几乎可称得上静好。
张爱玲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自己说得极到位﹕“是像一个人走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其间对于她个人﹐最大的事件大约是历史老师佛朗士被枪击误杀。这老师是她所爱戴的﹐在其散文中频频出现﹐几乎影响了她的人生观。张对她所经历的种种“不相干”却有着可怕的清醒,文字交接之下﹐可称得上触目惊心﹕“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地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在死难者的身后﹐“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而此时有关港大的回忆﹐是 “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对“大”的冷漠规避与对“小”的念兹在兹成就了张爱玲的香港镜像。
“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这结论是十八天的围城历练给张爱玲世界观的馈赠。“男女”自不待言﹐已经成为《倾城之恋》中的白刘苏和范柳原﹐及一切自私的男人与女人的人生宝典。而饮食一项﹐张爱玲也自有服膺的小细节﹕大约在战争的压榨下﹐所有的本能都披了罪恶的皮囊。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
数年后的《重访边城》﹐背景也是微妙的。1963年﹐内地形势﹐是山雨欲来。大跃进后的大饥荒大逃亡﹐香港再次成为南下的避难所。张爱玲曾置身于罗湖关卡的人潮﹐带了些许惶恐,倒还没忘记冷笔写下人物皆非的景象﹕
这次别后不到十年﹐香港到处都在拆建﹐邮筒半埋在土里也还照常收件。造出来的都是白色大厦﹐与非洲中东大海洋洲任何新兴的城市没什么分别。偶有别出心裁的﹐抽屉式阳台淡橙色与米黄相间﹐用色胆怯得使人觉得建筑师与画家真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族……这种老房子当然是要拆﹐这些年来源源不绝的难民快把这小岛挤坍了﹐怎么能怪不腾出地方来造房子给人住。我自己知道不可理喻﹐不过是因为太喜欢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清洁﹐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国的一鳞半爪给保存了下来﹐唯其近﹐没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
这段落的意味在于﹐张第一次明白地道出对香港的“太喜欢”。较之十年前的种种﹐这结论算是出人意料。或许张对这城市的情绪﹐本就是理还乱的千丝万缕。或许因为年岁与阅历﹐除却了锋利的态度﹐开始看出了过往旧地的好处,恐怕对张而言﹐总是真心的。这香港之行的后半段﹐色调仍是物质的。张爱玲探访老街﹐倏忽忆起原是摆绸布摊的繁盛处﹐辗转之下﹐因一块玫瑰红的手织布﹐竟做起了中国纺织史的考据﹐洋洋近万的文字﹐由唐宋明清十三行忆至大陆解放﹐实实在在地偏了“游记”的题。然而﹐这时的张爱玲﹐大约与这浮华放纵的城市与文字﹐已隔了很久﹐终于恣肆起来。
张爱玲眼中最后的香港。隔开四十余年的烟尘﹐终于见了天日。其实早在1963年﹐便有公开发表在《The Reporter》上的英文版﹐有个俏皮的标题“Are you Mrs.Richard Nixon”(你是理查德·尼克松太太吗?)张爱玲此行刚下飞机﹐被一个陌生的男子误认为尼克松太太,后者是美国前总统的夫人。张爱玲终于忍不住﹐带着些许虚荣的口吻﹐与前来接机的中国友人谈起这桩误会。
对方不好意思地说﹕“有这么个人老在飞機场接飞机﹐接美国名人﹐有点神经病。”
这个暧昧的张爱玲。
① 张初来香港是1939年﹐1941年“港战”爆发返回上海﹐共计居港两年零三个月﹔1952年7月二度赴港,1955年8月赴美﹐1961年11月再次来港﹐1962年3月赴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居留香港共约三年半时间。参见罗卡着﹕《张爱玲·香港电影》﹐载黄德伟编著﹕《阅读张爱玲》(香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1998年)﹐页246-249。
责任编辑 张 鸿
责编推荐
这些年来,葛亮给我的印象无外乎三个词:学问、民国、体面。这几乎涵括了所有我对他的认知。葛亮温雅笃定、平和周到,他的一些行为常常会让我对他的年龄产生错觉。我几乎读完了葛亮所有已出版的作品,王德威说他是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颇得我心。
在此处的《暂借》里,葛亮用一种旁观者的客观的目光审视张爱玲与香港的复杂关联,那种复杂体现在心理上、文字上,自然是一种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短小的《书衣》写出了一种情致、热爱,更是一种情怀。
葛 亮:作家,文学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现在高校担任教席。作品出版于两岸三地,著有小说《北鸢》《朱雀》《七声》《谜鸦》《浣熊》《戏年》,散文《小山河》,文化随笔《绘色》,学术论著《此心安处亦吾乡》等。部分作品译为英、法、俄、日、韩等国文字。曾获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被收入“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入选2008、2009、2015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和“2015年度诚品中文选书”。长篇小说《朱雀》获选“《亚洲周刊》全球华文十大小说”。2016年以新作《北鸢》再获此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