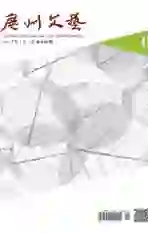艺术理性与“写给无限的少数”
2017-03-21王春林
假若从代际的观念出发考察当下中国文坛,你就不难发现,在那批越来越引人注目的70后作家中,李浩无论如何都应该被视为一种带有鲜明另类色彩的存在。李浩的另类色彩,一方面体现为他对于先锋写作立场的一贯坚持,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他对于小说写作一种自觉的理性思考。或许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写作趋向的总体加强有关,这批小说写作渐趋成熟的70后作家,大多自覺或者不自觉地恪守着一种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尽管这些70后作家一直都在充分地吸收着来自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营养,但就他们具体的写作实践来说,却很少有人能够坚持追求艺术形式层面上的实验探索。对于这一点,李浩有着足称清醒的洞察:“不过,我想我也必须承认,在我们这一代作家身上,某种集体性的欠缺也是相当明显的:和所谓现实、生活贴得过近,和平庸日常过分和解,媚俗,满足于集体讲述与小小虚名,思想深度与创新意识的稀薄,文学理想(真正放置和归属于文学自身的)缺失,对僵化、固化、意识形态化的母语的不察不敏……”①或许正与这种清醒的洞察密切相关,李浩迄今为止的小说写作历程中,一直都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实验探索的不竭热情。在一个文学的市场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的现实文化语境中,一个作家有勇气面对市场说“不”,能够公开宣称自己只为“无限的少数”写作,正是这种不竭探索热情存在的极好证明。何为“无限的少数”?“所谓少数,更要求写作者遵从内心,遵从艺术,勇于探险,而不是曲媚,无论是对大众、权贵、利益,还是对文学史,甚至另一个‘自我,都得抱有些警惕,要求写作者不计利益钝害地去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所有有效的写作都是先锋性的,‘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无限,则是另一个问题,它要求,一个人的写作,既是前人经验的某种综合,又应当有永远不被穷尽的新质,一百年,二百年,当它所依借的所谓‘时代背景生出变化,那些依借这一背景而生发的丰富、深刻、意味都被耗尽之后,它依然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它依然具有新意,它,依然是丰富而深刻的,一百年、二百年后出生的人还能从中读出会心。无限,是前提。写给无限的少数,在已经二十多年的写作中,它一直充当着我的终极理想。”②虽然说李浩的写作实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切近了自己所设定的高远艺术目标,肯定是一个尚待时间充分检验的问题,但对于如此一种写作立场的坚持本身,就证明着李浩小说艺术上一种不竭探索热情的存在。别的且不说,单只是这一点,就理应赢得我们发自内心的充分尊重。
先锋写作立场的坚持之外,李浩在70后作家中显得特别的另外一点,就是他关于小说创作理性思考能力的具备。放眼70后作家群体,如同李浩这样同时兼擅小说写作与小说批评两种文体的写作者,极为少见。一部被命名为《阅读颂,虚构颂》的文学批评文集的存在,便是李浩批评能力的有力证明。收入此书中的文字,除个别篇什外,绝大部分都是李浩关于小说写作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李浩如此一种丰富文学学养的形成,与他对于西方经典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不要说是70后作家群体,即使把视野放宽至整体意义上的中国作家群体,如同李浩这样对于西方文学作品及理论进行过系统阅读的作家也是凤毛麟角。一方面是自身丰富的写作实践,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文学的谱系性广泛阅读,李浩那些关于小说写作的理性思考,很显然正是建基于这样一种前提之上的。惟其如此,李浩在他的文学批评文字中关于作家作品的评价才会显得特别准确到位,切中肯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也只有在作家的这些文学批评文字中,我们才能够更鲜明地触摸到他最根本的小说艺术理念与小说审美理想。在他看来,“一个文本如果经不起细读,经不起反复回味、品啜,缺乏结构和语言上的用心,即使他具备再深刻丰富的社会学、伦理学意义,那也不过是一腔废话”。据此来“反观我们的当下文学,缺乏独立思考,缺乏建立一个独特艺术世界的固执与偏执,缺乏精神冒险,甚至,也缺乏艺术的精心和耐心……”③在诸如此类的理论话语中,李浩关于小说写作的真知灼见随处可见。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批评家身份与小说理性思考能力的具备,对于李浩的小说写作来说,实际上构成的是一种双刃剑的功能。一方面,理性的自觉确实能够使他有效地避免小说写作的盲目性,使他清醒地面对自己意欲建构的小说艺术世界。但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也须得认识到,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过于清醒的艺术理性自觉又极可能构成一种对于小说艺术感觉的伤害。归根到底,小说写作绝不能简单地凭借逻辑推理能力,小说写作的成功与否,所更多依赖的,恐怕还应该是一种带有突出混沌意味的艺术感觉能力。艺术感觉之所以是艺术感觉,正因为其中包含有一种理性所无法说明更无法取代的因素。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在很大意义上道出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真理。因此,在充分意识到李浩理性思考能力助益其小说写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种负面作用的难以避免。
比如说,在李浩的中短篇小说中,就存在着诸如《一次计划中的月球旅行》《A城捕蝇行动》《飞过上空的天使》这样几篇颇具荒诞色彩的“纯”虚构寓言作品。这几篇小说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李浩艺术想象力的异乎寻常。其中《一次计划中的月球旅行》一篇,故事发生在未来的2392年。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篇能够充分彰显李浩小说写作与西方现代文学之间紧密关系的作品。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作家对于小说人物的命名方式上。或许李浩自己在命名时并无特别用心,但诸如约瑟夫·格尔、玛格丽特·乔尔之类带有欧化意味的人物命名,显然强有力地象征并见证着“未来大家top20”颁奖词给李浩作出的定位:“他不讳言师承着欧美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传统,借此他获得了精进的文学姿态和出色的写作技巧。”李浩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情有独钟,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理解李浩小说所无法舍缺的一个必然途径,就是对他与西方现代文学谱系之间关系的考察与辨析。既然故事发生在未来时间,那李浩也就只能够凭借自身出色的想象力来构建小说文本。具而言之,李浩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自己的情节构想。一个方向是约瑟夫·格尔怎么样做月球旅行的准备工作以及在此过程中与邻居之间的碰撞纠葛,另一个方向则是叙述者“我”关于约瑟夫·格尔登月之后可能性遭际的一种猜测性描写。必须注意,这是一篇解构色彩格外鲜明的小说文本。在叙述者的叙事过程中,我们会不时地与这样一种解构性话语“邂逅”:“ 约瑟夫·格尔要到月球上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你期待在他的故事中,出现什么样的惊奇,还是,根本就不对这个故事有所期待?你打算看完它么?”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小说那样一个解构性的结尾方式。当约瑟夫·格尔业已做好全部的登月装备之后,他收到了旅行被取消的通知:“你的登月旅行已经被取消了。我们对此深表遗憾。具体的原因我们无可奉告,不过你可以选择再乘坐我们的下次飞船,我给你的文件上面有下一次飞行的具体日期。”更加吊诡的是,“好在,它只是我的一个想象,我把它存在了我的文档中。它和约瑟夫·格尔的登月计划以及实施没有关系,它只是我个人的想象。想象和现实之间存在关系,但它们的关系不是非常的确定,有时还会恰恰相反。”从表面上看起来,类似于《一次计划中的月球旅行》这样的“纯”虚构作品,依赖的是作家的艺术想象力。但更深入地想一想,你就能够发现,在艺术想象力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的突出。从根本上说,正是依凭着叙事过程中不时出现的解构性话语,依凭着一种事理逻辑的推演,李浩方才可以完成这类“纯”虚构寓言作品的写作。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类似于李浩的这样一种“纯”虚构寓言写作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粗暴地断言这种写作了无价值,显然毫无道理可言。约瑟夫·格尔本来已经做好了登月的准备,没想到,他的登月行动却因为“无可奉告”的莫须有原因而被迫取消。别的且不说,单只是这样的一种情节处理方式,所传达出的便是李浩对于现代人总是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被决定”状态的生存無力感的真切思考。非常明显,李浩之所以要采用非中国化的人物命名方式,在彰显其小说写作与西方现代文学谱系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力图凸显出其小说写作的一种国际性“普世”倾向。更进一步地说,李浩采用此种叙事策略的潜在原因,显然是要凭此而使自己的小说写作得以摆脱所谓地域性的狭隘。但在充分理解李浩如此一种良苦用心的同时,另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这样一种明显抽离了具体的“时代性”“地域性”的寓言化小说写作,果真就能够企及所谓“普世”的人类存在高度么?从个人长期的阅读经验出发,对于这一点,我确实深表怀疑。难道说,出现在李浩自己所心仪的那些作家诸如卡夫卡、卡尔维诺、纳博科夫笔端的人物形象,便都无种族色彩无地域特征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际的情况是,出现在那些小说大师笔端的人物形象,首先是具体的种族的地域的,然后才可能从中抽象出所谓人类存在的公约数来。也正因此,对于李浩诸如此类的被明显悬置的“纯”虚构寓言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我个人的评价态度的确有所保留。艺术想象力与理性思考能力的发达,对于现代小说写作的重要性当然毋庸置疑,但问题的关键处还在于,所有的这些都必须落到实处,都不能处于凌空蹈虚的被悬置状态之中。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此类“纯”虚构作品的构想写作,也正是李浩的理性思考能力充分发挥作用的一种具体结果。假若承认如同《一次计划中的月球旅行》一类小说作品果然意义有限,那么,作家过于发达的理性思考能力的双刃剑功能于此即可见一斑。
正因为我坚持认为李浩“纯”虚构寓言类作品意义有限,所以才会更加喜欢他另外那些明显依托于个人生存经验的写实意味突出的小说作品。比如《一只叫芭比的狗》,故事尽管非常简单,但李浩由那只被叫作芭比的狗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遭遇而对于人性的卑劣所发出的深刻诘问,却是十分发人深省的。芭比是一只毛色棕黄的小母狗,样子很漂亮,在“我们家”备受宠爱。这一点,从它被命名为“芭比”上,即可得到有力的证明。“芭比成了我们家的一员,是我母亲的女儿,我和哥哥的妹妹。”然而,虽然是宠物,但芭比却也终归是一只有生命的活物。到了来年春天,它也要恋爱。芭比一恋爱,就引来了许多只公狗聚集在“我们家”门外。这么多狗的聚集,便对“我们家”日常生活形成了某种干扰,尤其是这个时候“我”的哥哥正在紧张地准备着高考。怎么办呢?在得到了父母的默许之后,哥哥便开始了他不无残忍的诱捕杀狗过程。先后有几只狗命丧哥哥之手。于是,被报复的命运就降临到了芭比的身上。这就有了芭比的失踪与归来。只不过,重新归来的芭比已经大变了模样,不复是曾经的那只毛色棕黄的“样子很漂亮”的小狗了:“它的毛很乱,已经是一条肮脏的灰狗了。散发着臭味的灰狗。它的一条腿断了,它尾巴上的头也没有了,并且,更惨的是,它的两只眼睛已经瞎了。它大约是凭着嗅觉和记忆回来的。”芭比的形象变化,所必然牵引出的,是“我们家”人对它态度的转变:“它不再是原来的芭比了。它不再是我母亲的女儿,我和哥哥的妹妹。它是一只肮脏、丑陋、残废的狗。它是粘在衣服上的鼻涕,是一块发霉的馒头,是一只恶心的苍蝇。”就这样,尽管芭比还是那只芭比,但它在“我们家”的地位却已经是面目全非。关键问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这只被叫作芭比的狗,究竟何错之有?明明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碰撞,其最后的恶果却要由一只宠物狗来承受。李浩肯定想通过这样一只宠物狗前后的不同命运遭遇,充分地揭示表现着人性的卑劣、残忍与丑陋。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那篇旨在关注思考教育问题的《碎玻璃》。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对于我“关注思考教育问题”的判断,一贯轻慢小说作品社会学内涵的李浩肯定难以轻易认同,但我却还是要坚持做出这样的一种艺术社会学判断。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在我看来,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事物,同时也还是一种精神性的事物。舍却了艺术的社会学内涵,所谓的精神性恐怕也就无所着落了。《碎玻璃》所具体展示描写的,是发生在身为学生的徐明与数学教师胡老师之间的一种对峙冲突。在叙述者“我”的视野里,导致徐明和胡老师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其实“不过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关键原因还在于,刚刚转学到我们学校来的徐明在无意之间触犯了胡老师的尊严:“可是那天徐明是个例外,他如果像我们一样,估计胡老师发一顿火也就过去了……可是徐明偏偏没有像我们那样‘低头认罪。”必须注意到,徐明和“我们”之间具体分野的存在。假若说“我们”的表现是一贯驯顺的,那么,徐明的“例外”表现也就自然带有了鲜明的个性叛逆色彩。惟其如此,叙述者才会一再强调徐明对于胡老师的“冒犯”:“尽管我早就忘记了事件的起因,但徐明顶撞了胡老师,还说胡老师错了,这件事我可记得一清二楚。”之所以会是这样,根本原因在于,胡老师的严厉是出了名的。这样一个以严厉著称的老师,根本就容不得学生的“冲撞冒犯”,哪怕这个学生并无错误可言。“我们都知道这不会算完。肯定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胡老师绝不会容忍有人顶撞她的,胡老师是不会放过徐明的。”由于徐明一直都坚持认为自己那次并没有犯任何过错,所以,他与胡老师之间的对峙“斗法”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在学校里,一个弱势的学生和自己的带课老师相对抗的结果,只能是学生的被孤立:“徐明被孤立起来了,在他的身边仿佛有一道墙,有一个看不见的笼子,使他和我们隔绝,我们的奔跑、欢笑甚至打闹都与他无关,他只得一个人待着,他有一个孤独的小世界。”中学阶段,是一个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对于初通人事的徐明来说,被老师和同学人为孤立起来的滋味绝对是难以忍受的。尽管作家并没有直接描写揭示徐明的内在心理,但通过他此后曾经先后把玩具、画册等物事携带到学校来的举动,李浩鲜明有力地写出了他内心中的孤独感。“我们知道徐明是在干什么,他要干什么,可是,我们不能。我们不敢。”就在徐明和胡老师之间的对峙不可开交的时候,胡老师办公室的玻璃突然间被人打碎了。由于徐明的存在,胡老师本能地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徐明。但徐明却坚决不承认是自己打碎了胡老师办公室的玻璃。徐明不承认,胡老师便很生气。然而,就在胡老师实在拿徐明无可奈何的时候,徐明自己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居然把毕加索的裸体画册带到了学校。这下子,胡老师总算抓住了徐明的一个“把柄”。面对着胡老师的咄咄逼人,倔强高傲的徐明终于低下了自己的头颅:“看得出,徐明在‘画册事件中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他摇摇欲坠。眼泪在他的眼睛里打着转儿。那一堂漫长的班会对徐明绝对是一种煎熬,他都出汗了。刚下过小雨的秋天已经凉了。”“画册事件”之后,紧接着在期末考试之前又有“钉子事件”发生。明明是刘佩华把钉子放在了徐明的凳子上,胡老师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徐明狠批了一通。在遭遇了一系列的打击之后,徐明终于跟着他的教师母亲转学到了另外的学校。但小说却并未到此结束。等到期末考试成绩公布的时候,业已转学的徐明再次出现在了“我们”面前。面对着胡老师,徐明一方面竭力强调上一次自己并没有打碎她办公室的玻璃,另一方面却飞快地从书包中取出一块砖头,砸向教室的玻璃:“破碎的玻璃掉了下来,像一场白花花的雨,它们纷纷坠落,闪着银白色的光。”小说情节至此戛然而止。
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碎玻璃”,显然与玻璃的两次被打碎密切相关。第一次打碎,明明与徐明无关,但胡老师她们确是要把这个罪名强加到徐明身上。有了这一次的无端被冤枉,才引出了结尾处徐明故意打碎玻璃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应该注意到,李浩关于那一地玻璃碎片的描写其实有着突出的象征意味。那岂止是一地玻璃碎片呢,那简直就是正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中学生徐明一颗破碎的心。读李浩的《碎玻璃》,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很多年前刘心武的那篇《班主任》。刘心武《班主任》的故事背景是“文革”刚刚结束不久,而李浩《碎玻璃》的故事背景时间却显然要靠后许多。《班主任》中,班主任张俊石扮演着启蒙者的角色,而《碎玻璃》中的胡老师却变成了思想与教育专制的一种化身。都已经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身为教育者的胡老师却依然在以异常粗暴的方式钳制扼杀着学生们的个性自由思想。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在胡老师的背后,不仅有我们的教育体制存在,更有一种深层的社会体制存在。就此而言,李浩这篇小说的意义,也就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是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思考了。在教育问题背后所潜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发展运行机制问题。当年的鲁迅先生曾经大声疾呼要“救救孩子”,现在李浩却在强调首先必须救出身为教育者的老师。如同胡老师这样居然把毕加索也视为淫秽、堕落的教师的存在,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精神世界的健康成长。很显然,只有首先改变胡老师们的精神世界,方才有可能真正地企及“救救孩子”的目标。尽管李浩肯定不同意我把他的小说理解为问题小说,尽管其中也有对于徐明、胡老师以及“我们”各自人性的挖掘表现,但从根本上说,《碎玻璃》的主要价值的确体现为他对于那种旨在钳制扼杀个性自由思想的教育以及社会体制所进行的格外犀利尖锐的揭示与批判。
作为一位具有艺术理性自觉的作家,李浩对于思想在现代写作中的重要性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在《战争与和平》中(我有时真的怀疑,那些反复提及俄罗斯伟大传统、提及托尔斯泰的人是否认真地读过这篇小说,先不要说什么读懂),老托尔斯泰在其中埋入了大段大段的思索,在这部伟大的小说里,他试图探寻人与历史的关系,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他在‘跟大人物的意志与理性创造历史的观点进行论战——小说不再用来(至少是不再专注用来)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它开始审察人的存在,思考人的存在,追问人的存在。可以说,在各学科之间进一步细分、世界越来越丧失它整体性的今天,把‘思引入小说是某种重新整合世界的尝试……在今天,也只有文学还存在那种整合的可能。”④既然认识到了“思”在现代写作中的重要性,那么,尽可能地把“思”纳入到自己的小说写作中,自然也就成为李浩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只要认真地读过李浩的那些中短篇小说作品,即不难发现,其中那些真正堪称优秀的文本,都与“思”,与我们寻常所谓的思想深度存在着不可剥离的内在联系。比如《爷爷的“债务”》,比如《将军的部队》。
尽管叙述者的话语较为含混模糊,但《爷爷的“债务”》的故事发生时间,应该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无疑:“在貌似遥远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或者更早,我爷爷的每日都是如此,他会拾些柴草和牛马的粪回来,所以那日和以往并无不同。”之所以认定是八十年代,还与一句相关的叙事话语有关:“考虑到,三年前自辛集恢复集市以来每五天便有一个集市,这种不同似可忽略不计。”但这种不同,事实上真还不能够忽略不计。这一天的早上,爷爷无意间做了一回“活雷锋”。他在果园路旁的草地里捡到了一个里面装着一包钱(后来被确证是四百二十块七毛二)的灰绿色书包之后,很快就把它交还到了返回来寻找的失主手里。没想到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捡到失物归还失主的道德行为,却最终把爷爷推置到了一种殊为尴尬的处境之中。原来,此“失主”非彼失主。就在爷爷已经不慎把失物交还给前一个“失主”之后,真正的失主方才出现在我们村里。怎么办呢?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家明显地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阵营。一个阵营以“我”的母亲为代表,坚持认为爷爷是在做好事,即使有过错也属于无意之过,不应该对此事承担什么责任。在母亲看来:“我们就是捡到了,让人骗走了,也和这事没关系了,反正我们没有把钱昧起来,反正我们没有故意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们找我们根本就没什么道理……”另一个阵营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爷爷一个人,爷爷的态度与“我”母亲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爷爷使用的和她所使用的不是同一种逻辑,不是同一类‘道德。”面对着找上门来的失主的儿子儿媳,爷爷不仅主动承认自己的失误,而且,“他向人家信誓旦旦,我一定把钱给你们找回来,你们放心。”没想到的是,误领走布包的那个人却没有那么容易找到。尽管爷爷和我的家人费尽心机,四处奔走,那个误领走布包的人却遍觅不见。在此过程中,那个真正的失主老人,居然一病不起,最终离开了人世。老人的死亡,更是对爷爷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不,爷爷不能把它放下,他把这事当成自己的债务,现在,他的压力更大了,毕竟,一个人死在了自己的过错上。”好在经过了一番能够料想到的纠葛冲突之后,事情在正月初四那天出现了转机,误领走布包的那个赵凤亭终于浮出了水面。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爷爷不仅前去讨要布包无果,而且还被赵凤亭用铁锹砍掉了两颗牙齿。四叔因为替爷爷出头复仇而弄断了赵凤亭的一条腿,依法有可能被判处三至五年徒刑。到最后,良心发现的赵凤亭主动到派出所撤诉,四叔被释放回家。在只是少了一些钱的布包被送回之后,爷爷的“债务”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至此,误领走布包的事件方才得以真相大白。却原来,赵凤亭并非骗子,他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母亲弥留之际能够吃上饺子而一时动心误领走了布包。至于被四叔弄断腿,赵凤亭认为那是自己应得的报应,怨不得谁。“事情到此,已经到达它的尾声。爷爷的‘债务最终得到了偿还,巩家村的人不会再来纠缠,而赵凤亭一家也没再和我们有任何联系。”然而,对于爷爷来说,事情却没有真正地终结。证据有二:其一,他曾经悄悄地给赵凤亭的女人送过钱;其二,他一直因为那位失主老人的死亡而耿耿于怀:“我的身上,还欠着人命呢。”“他说得凝重、郑重,仿佛里面依旧有一块放不下的石头。”
小说最核心的人物,显然是爷爷。李浩对于当下时代社会道德问题犀利透辟的体察与思考,也是依托于爷爷这一形象的深度塑造,方才得以最终完成。爷爷本来是要做好事,结果却无端地惹上了难以脱身的“债务”,陷入一场莫须有的人生纠葛之中。面对这样一个莫须有的“债务”问题,大多数人都会采取“我”母亲那样一种尽可能地撇清自己的人生姿态。就此而言,爷爷之主动承揽“债务”的人生选择,自然也就具有了一种突出的理想化色彩。既然自己有过错,那就应该尽量设法挽回。既然自己作出过郑重的承诺,那就一定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兑现这种承诺。爷爷人生选择的核心内涵,显然在此。关于小说写作,我们一贯以为,重要的不是被书写的时代,而是做出书写行为的时代。李浩之所以要在当下这样一种民族道德精神处于严重滑坡状态的时代语境中构想出《爷爷的“债务”》的小说故事,其强烈的批判反思性意义指向是显而易见的。惟其如此,人民文学奖的颁奖词才会对小说作出这样一种评价:“《爷爷的‘债务》关乎信义,关乎旧日乡村美德和它的消逝,也因此成为一面映照现实、比照当下的镜子,表达出我们对那些珍贵而美好的价值所抱有的强烈渴望。任何的美德、信义和价值,都将始终面临来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艰巨考验,因为善与美的生活从来不容易获得,它们需要人类怀抱勇气去锲而不舍追寻。爷爷卑微,‘债务也渺小,但是爷爷的‘债务却知微见著,直指我们需要面对和深思的问题核心。”⑤
《将军的部队》故事情节极其简单,李浩借一位六十一岁老人的回忆性视角,展开了关于“将军的部队”的描写。倘若只是从小说的标题来判断,所谓“将军的部队”,应该有千军万马才对。但实际上,除了作为叙述者存在的“我”以及曾经偶一露面的王参谋和那位宣传干事之外,自始至终活动在小说文本中的核心人物,只有将军一人而已。既然只有将军一人在活动,那又何来“将军的部队”呢?却原来,出现在当年只有二十一岁的干休所勤务员“我”眼中的所謂“将军的部队”,居然是两个装在巨大的木箱里的一块又一块业已成为暗灰色的木牌。在“我”的眼中,“对住在干休所里,已经离休的将军来说,每日把箱子从房间里搬出来,打开,然后把刻着名字的一块块木牌从箱子里拿出来,傍晚时再把这些木牌一块块放进去,就是生活的核心,全部的核心。直到他去世,这项工作从未有过间断”。原来,这些木牌所代表的,乃是将军曾经统领过的那些已经阵亡了的将士。需要注意的是,将军不仅每天要把这些木牌翻出来,而且嘴里还在喃喃自语:“他根本不是自言自语,绝对不是!他是在跟身边的伴儿说话,跟自己想到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人说话,跟过去说话。”确实如此,将军哪里是在翻弄木牌,他分明是在无休无止地在和自己当年曾经的戎马生涯对话,分明是在不断地重返已经过去了的难忘岁月,是对于自己既往生命历程的一种触摸与重温。尤其不能被忽略的是,将军在对过去岁月进行回望时的主体态度。其中不容忽略的,是出现在书本中的将军,与出现在“我”视野中的将军之间差异的明显存在。“那些书上或详尽或简略地描述了将军一生的戎马,在那些书上,列出的是战争的残酷,将军作战的英勇和谋略,以及在艰苦生活中将军所表现的种种美德。”而“我所知道的将军是一个离休的老人,有些古怪,但几乎完全没有什么英勇和谋略”。作为一位被历史记载的将军,英勇和谋略肯定是有过的。但为什么后来没有了呢?小说中的两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一个是王参谋亲眼看到的:“他看见将军紧紧抓住一块木牌,对着它大声说,你就是再活一次,我也还得毙了你!……过了很久,将军突然对王参谋说,你把木牌给我捡回来。……王参谋说他记不太清了,他记得好像他把木牌递到将军手上时,将军的眼红红的。”很显然,这个木牌所代表的那个战士曾经犯下过难以被宽恕的罪过。但将军不仅让人重新捡回木牌,而且还“眼红红的”,所凸显出的,其实是将军的一种悲悯情怀。另一个细节是,当那位宣传干事询问将军:“是不是怀念自己的戎马生涯?是不是想继续战斗,消灭敌人?”“我”的答案却是否定的:“不,好像都不是……怎么说呢?他好像就是把木牌摆出来,想一想过去的事,就这样。”那位宣传干事希望看到的,是一个金戈铁马的将军。而“我”所呈现出的那位貌似只是“想一想过去的事”的将军,实际上透露出的是一种对逝去生命隐隐的无尽哀伤。人都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之所以能够成为叱咤风云的将军,端赖脚下踩着的累累白骨,也即这一块又一块的木牌支撑。惟其如此,他才会面对着这些木牌时貌似“想一想过去的事”。把这一细节与前面“将军的眼红红的”联系在一起,那样一种不无哀伤的悲悯情怀就容易被理解了。就此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李浩的《将军的部队》这一精致短篇,也还隐含着某种潜在的反战倾向。当然,不能不强调的是,在将军这一形象的背后李浩的存在。归根到底,哀伤也罢,悲悯情怀也罢,反战也罢,所有这些深刻的思想意旨,都与作家李浩存在着太过紧密的联系。
说到《将军的部队》,尤其让人惊叹不已的,是李浩对于短篇小说文体特质的精准把握和运用。业内朋友都非常熟悉海明威关于小说创作的“冰山理论”。倘若说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小说写作的“不二法门”的话,那么,短篇小说这一文体就更应该充分地实践海明威的这一理论。而李浩《将军的部队》,显然就是这一方面一个标本性的存在。从表面上看,小说只是写了一个老人对另一个老人的回忆。作为主人公的将军,所翻来覆去不断重复的一个动作,也不过是无休止地倒腾着那两只巨大木箱中藏着的木牌。的确称得上是水波不兴,格外平静。但细细想来,这平静的水面之下,却实在难言平静,其实是波浪翻滚汹涌澎湃。其中,不仅有将军对于既往戎马生涯的追忆回想,而且更有对于战争的反思,对于逝去生命的哀伤和悲悯。好的短篇小说,就应该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应该以不写为写,能够通过一滴水反映太阳的光辉。就此点而言,李浩《将军的部队》就应该被视为一篇经典意味十足的短篇小说。
谈论李浩的中短篇小说写作,无法被忽略的,就是他的那些以“父亲”为主要观照对象的“父亲”系列。李浩实在是一位对于“父亲”情有独钟的作家,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他何以会一再把“父亲”写到自己的小说之中。不过,中短篇小说中所有关于“父亲”的书写,都已经以集大成的形式纳入到了他新近的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之中。因为笔者曾经撰文专门讨论过他的这部长篇小说,所以在这里也就不准备多加烦言了。但面对李浩,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忽略的一点是,他对于小说方法论的迷恋,对于小说形式感的特别追求。读解他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这一点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尽管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篇作品的叙事形式进行细致的分析,但总括而言,李浩小说形式感方面的一大特质却是不应该被忽视的。这就是对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迷恋运用。迄今为止李浩的全部小说中,除了极个别的篇什外,绝大部分采用的都是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说到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在已有将近四十年历史积累的新时期小说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某种意义上,这应该是已经被我们的作家使用到了烂熟程度的一种叙事方式。我之所以要特别地拿它说事,原因在于,同样是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在李浩这里与在其他作家那里有所不同。倘若说其他作家只是在一种叙事方法的意义上使用这一叙事方式,那么,对于李浩来说,这一叙事方式的使用,实际上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本体论意义。更进一步说,李浩只有在小说中写下“我”字,只有在以“我”的面目出现的小说作品中,方才能够有艺术上如鱼得水、得心应手的充分发挥。一旦离开了“我”,李浩便会陷入一种左顾右盼六神无主的莫名焦虑状态之中。他的那些不多的几篇离开了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小说之所以难言成功,原因正在于此。同样的道理,他之所以在篇幅颇大的《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两部长篇小说中坚持使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也与这一点紧密相关。也正因此,我的一点建议就是,李浩在今后的写作历程中,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我”,都不能舍弃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与此同时,必须强调的另外一点是,虽然李浩的小说写作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问题就不复存在。在结束我的这篇批评文字之前,我要再一次重申我曾经当面对李浩讲过的话:“小说的形式建构固然重要,但精神内涵也不能被忽视。”在目前李浩的小说写作仍然过分倚重追求形式感的情形下,强调这一点,肯定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注释:
①②:李浩《写给无限的少数》,见李浩《阅读颂,虚构颂》第198、196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版。
③④:李浩《〈变形记〉和文学问题》,见李浩《阅读颂,虚构颂》第23页、第16—17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版。
⑤:参见李浩《将军的部队》封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版。
责任编辑 梁智强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