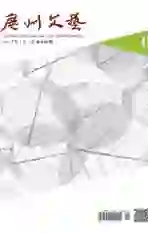书衣
2017-03-21葛亮
葛亮
整理书架,翻出一本书,是北京三联版姜德明先生编的《书衣百影》。这本书是一位前辈朋友的赠与,一直珍藏。书中选了1906至1949年期间的一百张书影,从《孽海花》至《莫里哀戏剧集》。
对于书籍,我是个不打折扣的封面控。这一点体现在对版本的热衷。一本书的成败,作者与出版人只是一端,设计师才是最后那个与读者“狭路相逢”的人。在这方面,鲁迅算是一个先知,他作为不错的装帧家的身份,大概并不广为人知。因为一贯的导师范儿,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的设计师,数得上名字的,有陶元庆、司徒乔、钱君匋、孙福熙几位。其中我特别喜欢钱君匋。钱先生早期的设计,常用美术字体和横竖直线,比如L.Kampf作、巴金译的《薇娜》一书,大开大阖的美术字,独中文书名是红色圆底的反白,十分净简,却视觉张力十足,令人击节。后来接触到捉刀许多学术类书籍的台湾设计师王志弘,其作品素洁大气,很有钱氏的风范,深感相见恨晚。
“五四”时期,作家直接参与书刊的设计,是一大风尚,自然也和当时文人办出版社的传统息息相关。鲁迅、闻一多、叶灵凤、倪贻德、艾青、卞之琳等人都在此领域尝试过。因为叶灵凤的这个才能,当年创造社的出版物颇增添了光华。叶曾为《洪水》半月刊创刊号作封面,刊名“洪水”两字上方是展开双翅的鹰与两条蛇构成的图案,鹰的胸前佩一把长剑,下方是滔滔洪水,左下角是一个撕破了的假面具,画面怪异恣肆。面具是比亚兹莱的招牌意象之一,这个英国人也是叶氏借镜最多的外籍画家,此为一证。因生性唯美,叶也的确对比亚兹莱亦步亦趋,鲁迅曾痛斥他“生吞‘琵亚词侣”,指的也便是这件事。叶当时在书装界的声名很大,或许遮没了其他人的成绩。要说起被“品牌化”的作家设计师,还有个名字不得不提。看了一个作品,可从封面上发现两位新月派诗人的惺惺相惜。1931年,新月书店初版了徐志摩的《猛虎集》,书质感很好,32开道林纸印制,将封面与封底展开,便是一张完整的虎皮。这么现代派的装帧思路,在当时极为少见。虎斑可见书法元素的简约,飞白寥寥,含蓄凝重。放到当下,这样中西合璧的书封,也令人叫绝,它的作者是闻一多。不仅是这本书,徐志摩的另外几本诗作,《巴黎的鳞爪》《玛丽、玛丽》的封面,也都是闻先生操刀,这也是一段佳话了。而对自己作品的出版,闻一多亦是无微不至。当时,《红烛》一书付梓,彼时留美的闻一多,虽然将出版事宜全权委托好友梁实秋与国内书局交涉,但装帧、用纸乃至成本、售价等问题,闻氏仍有细密的考虑,特别是书装,他在1922年11月给梁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封面上我也打算不用图画,这却不全因经济的关系。我画《红烛》的封面,更改得不计其次了,到如今还没有一张满意的。一样颜色的图案又要简单又要好看,这真不是容易的事。我觉得假若封面的纸张结实,字样排得均匀,比一张不中不西的画,印得模模糊糊的,美观多了。其实design之美在其proportion而不在其花样。”纵观时下的书籍装帧,多以夺人眼球为要,比起当年闻先生的简约理念,仿佛不进反退。
1933年,闻一多为他清华大学的学生林庚的诗集《夜》设计了一帧封面,图案摹写美国著名的版画家洛克威尔.肯特(Rockwell Kent)的木刻作品“星光”。画幅右下方却绘上了一只中国神兽“天禄”的石雕。可见其“中西会通、古今融合”的美学理想,不囿于诗作,而是另有薪火。
说起当今的书装设计师,出色的很多。面面俱到不容易,恐有遗珠。所以还是落到实处,从已出版的几本拙撰谈起。
先谈谈操刀《朱雀》初版的蔡南升。当年付梓台湾麦田,出版社问我,有无方法在装帧上传达既历史又现代的感觉,其实是个既易且难的题目。这部长篇小说,关乎南京由民国至千禧七十年的时光,号称“六朝古都”,已然形成了某种人文界域中的Stereotype,多半与沉重、晦暗与救赎相关。我想了想,给了出版社一张汉瓦当上的“朱雀”图,这张图片自然是很优美的,拓印的斑驳代表着历史的断裂,寓意深远。编辑很喜欢,又摇头。说,设计师还是觉得构图太厚重了。我对此也很理解。这本书被收入“当代小说家”书系,有相对固定的版式,稳重沉和。而对设计师来说,却成为“戴着脚镣跳舞”的考验。瓦当的古朴,自然使画面更为凝重,但也占据了诠释的空间。我便说,如果设计师有更好的图案,自然割爱,但定稿发来时,确有喜出望外之感。“朱雀”被保留了下来,在神兽的身边,是纷纷落下的血色的羽毛,细腻可见毫微,整个封面,一时间充满了轻盈的动感,象征着某个当下与远古的连接。我因此记住了设计师的名字。近来看到他的新作品,是资深作家蒋晓云的《桃花井》,半透明的花瓣,是历史光影的重叠,很好。次年,内地出版了《朱雀》的简体版,设计师是聂永真。聂先生是台湾设计界的多面手,听闻与王志弘、萧青阳并称“三驾马车”,但其实是很年轻的一位。早年玩跨界,周杰伦、王力宏、五月天的唱片封套皆出自他手。而打动我的,则是他为宫本辉设计的《锦绣》封面,“直书信纸”格式,朴素而辽远,正是我想要的感觉。永真的设计以简约著称,也以对材质的注重而闻名,所以,简体版的《朱雀》的气象确与台版不同。待样书拿到手上,方明白他对“浅毛棕”的坚持。这种纸本身的手感,的确是对南京最好的注释,持重但不笨重,有一种细致的糙感,是柔润的大气。而“朱雀”的图案,则是昂天腾空的形态,轻灵而凄绝。书名烫黑的字体,又是一番功夫。因为他同时担任了我另一本小说《七声》的设计。《七声》因为纪念之故,用了先祖父挚友王世襄先生的亲题书名。为了呼应王先生的墨宝,永真从二南堂法帖选了“朱雀”二字,与《七声》清新的田园风遥遥呼应,相得益彰。
庄谨铭也是年轻一代设计师中的翘楚。我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书《谜鸦》的装帧,是他的作品。一双翅膀,抽象而幽邃的现代感,为这本书增色许多。待到数年以后,再出《戏年》。我提供给出版社一帧好友赠与的藏地“唐卡”,希望以之表达“此戏经年”之意。封面稿样出来,效果与我的想象如此接近,似心有灵犀。再看设计师,是庄谨铭,虽素未谋面,却有故人重逢之感念。这封面中所表达的民间与写实的意味,与他往日的风格大相径庭,可见一个设计师的可塑性。近见他的获奖作品,列维史陀的《月的另一面》(L'Autre Face de la Lune),一本学术书的封面,做得浪漫而伤感,动人处是他对这位人类学家的心有戚戚。
活跃于内地的设计师,优秀的很多。知名度较大的如出生在香港的陆智昌。朱鹗与张志全,大小书肆,也时见佳作。我很喜欢的一位,是南京的朱赢椿,他的“书衣坊”出品的《不裁》與《蚁呓》,被我放在案头,经常翻一翻。一本书可以令人时有把玩之兴,是很不容易的事。说他的设计并非工作,而是一种态度,此言不差。 南京还有一间“瀚清堂”,近来在业内名声日隆,堂主是赵清。我最近出了简体版《谜鸦》《浣熊》,由他操刀,精致的小开本,手绘的工笔动物,创意也令人惊喜。有时候,看自己的文字成为另一种艺术品的源头,也是件欣慰而幸福的事情。方尺之间,自有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