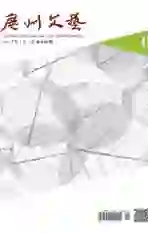阁楼上的母亲(短篇小说)
2017-03-21桑麻
桑麻
母亲身体的变化是从躲上阁楼开始的。
临近中午,她一动不动坐在门楼下,望着楼板出神。那里有一个空燕巢。燕子走了三年,没再回来。夏末秋初,阳光还慷慨地送来暖意。我从厨房打量母亲。她缩着身子,靠在门墙上,显得孤单。我从卧房找出一件暗紫方格外套给她披在身上。她收回目光,扭头看了我一眼,神情怪怪的,没什么表示,甚至连头都没点一下。
我弯腰凑近她的耳朵,大声提醒着,过道风贼,你年纪大了……
她喉咙里咕噜了两下,笑笑,想说话,但没有说出来。
我嘱咐小曼陪陪她,一会儿再过来端饭。
小曼答应着,把书、本子、铅笔盒摞到一起,推到矮桌左上角,凑到母亲身边。
我走回厨房。小曼像是跟母亲说了什么,母亲反应平淡。
小曼哼着“小燕子,穿花衣……”跑向上房。母亲扭头呆望着。
不大一会功夫,她回到门楼下,发现母亲的座位空了。她走出去,一会儿跑了回来。姥姥呢,她问,她去哪儿了?
该是去了厕所。
没有,她说。
她不喜欢我们的。你去板仓家看看。
小曼很快折回来,有点气急败坏,哪有啊,姥姥去哪儿了?
……
我把面条盛进碗里,吩咐她照看厨房,匆忙走出大门。
我在附近转了一圈,找遍母亲可能去的地方,却不见踪影。门前河水宽阔,水浅,流速也不快。东洼地两口深井早废弃不用了。通自来水的当天,村里的三口水井被大人们用磨盘封死了。它们构不成危险。村西有数十丈高的土崖,要二十多分钟才能上去。她走不了那么快,也不会去那里。
我站在门道里,理不出头绪。凳面似乎残留着母亲的体温。她也许根本没有走出院子。我注意到那架木梯。它平时斜靠在墙上,现在放下来了,顶端搭在阁楼上。它被挪动了。母亲会不会上去?
我将信将疑地登上梯子,每登一级,脚下就发出吱吱的鸣响。我双手搭在阁楼边缘,伸颈往里张望。透进东窗的光线很刺眼,一时适应不了。我听到里面有细微响动,蒙眬有一团东西蜷曲在東北角。我有些紧张。我喊了声娘,没有回应,那团东西动了一下。应该是她。慢慢地,她的牙齿、脸庞、睁大的眼睛显现出来。我的心咚咚跳,喉咙发紧,又喊了一声,双腿不由自主哆嗦一下。
我爬进阁楼,掌上沾满灰尘,还粘了些小石粒。丝丝缕缕的蛛网,挂上头发和衣服。我定定神,半蹲着移近母亲,仿佛在接近一个危险的存在。我听到她的呼吸。她缩在墙角,双手护着腹部,有些怕冷的样子,好像我一靠近,就会带来伤害。
我揽住她的肩膀,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她在发抖。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年纪大了,腿脚已不灵便,能爬上去,需要的不是胆量,而是力气。
半个月前,母亲还住在老家——一个围在高楼中的城中村里。区干部们在一个早上汹涌而来。早些时候的拆迁传言被证实了。街面到处是车和人,比庙会热闹得多。村民拒绝他们进到院里。这些“属狗的”坐着马扎守在各家门口。他们吃盒饭,搬来成箱的食用油,提着果篮、牛奶,托各种关系,希望乘夜色登门入户,撬开口子。高音喇叭一直从黎明广播到深夜。红红绿绿的宣传单扔得满街都是。旧城改造指挥部前经常人头攒动,公示牌上“已签搬迁协议”的人慢慢增加,开始三五户,一周过后,平均每天增加一百八十多户。
马松奎是母亲家的邻居,有一天,他突然精神失常了。母亲显然受到了刺激,一直犹豫的她决定把协议签了。
马艳姣是马松奎的小女儿,在区里一所小学教书。一天下午,她领着文教局局长来见她父母。学校停了她的课,让她回来做工作。
马松奎是个不管事的男人,大小事情由老婆做主。他让文教局的干部缠得没办法,就去指挥部签协议,回来,老婆不见了。马松奎没有离开过老婆,他老婆也没有不打招呼离开过他。他一紧张,便痰迷了心窍,一个人低着头,神思恍惚地往村外去,他也不知道该去哪里,走了很远,迷迷瞪瞪进了一个大菜市场,也没有找到他老婆,后来遇见一个本家的侄子,说,你来这里干啥,离我们家十里地啦!他仰着脸没说话。他侄子把他拉了回来。
来到门口,侄子把他扶下车,说,叔,到家了。
马松奎嘴巴一撇,抽泣起来。
本家侄子吓了一跳,赶忙追问,叔,叔,这是咋啦?
这么一问,好像提起了闸门,马松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号起来,艳姣娘哎,艳姣娘哎……嗷嗷嗷……艳姣娘不要我了……嗷嗷嗷……
街坊们听见哭声,纷纷围拢上来,既觉得好笑,又不忘你一言我一语地劝解,艳姣娘跟你过了四十年,咋会不要你;老菜帮子了,谁要;有人打趣,她跑了,你该高兴才对,再找个年轻的住楼房。
哎哎哎——她要要我,怎么说走就走了?马松奎咬住这个事实不放。有人进院看看,确实不见艳姣娘人影,觉得不可思议。玩笑是不能再开了。孩子们看着马松奎的哭相背过身子“嘿嘿”偷笑。
原来,马松奎老婆看他去了指挥部,强作笑脸送走了马艳姣,转回屋里,思前想后,觉得憋屈,又不便发泄,就想出门清静两天,于是坐了长途汽车回了衡水的娘家。
有人在汽车站碰到了她,马松奎不相信,非要挨着街道寻找。马艳姣往衡水通了电话,那边母亲刚进家。马松奎接过电话,止住哭声。他要她连夜返回来。她说自从父母去世,好几年没回过娘家,屁股还没坐热,打算住两天。马松奎又咧着嘴哭起来,又说她不要他了,直到她答应马上回返,才平静下来。
那一夜,很多人没睡好。
我母亲就是。
签了协议第三天,母亲搬离了老家。
头天夜里,等家人睡下,母亲插上屋门,在桌上摆上供品,燃起三炷高香,四肢着地,虔诚地跪下来。她向我父亲还有先祖们告别。她嘴里唠唠叨叨,很久才熄灯。
母亲十九岁那年,被一顶绿呢小轿抬进马家。十年里,生养了我、妹妹和弟弟三个。我们跟爷爷、奶奶、两个叔叔同住在一个院子里。院子不大,四间上房,三间西屋,满打满算七间破屋子,另有三间放杂物的棚厦。夏秋时节,两个叔叔在里面支床休息。后来,大叔参军留在了大西北。二叔当了上门女婿,在二婶娘家安营扎寨。爷爷奶奶离世后,我们慢慢长大,后来进城打工,日子慢慢有了起色。父亲两次在原址上翻盖房屋,一次在1981年,一次在1999年。第一次打倒四间平房,翻盖成五小间;第二次全部打倒,盖起十间楼房、三间平房。搬进新房不久,父亲查出肺癌,已经不能动手术,三个月不到离开了我们。
母亲一夜没有睡好,天不亮就起床收拾。两辆工具车跑了三趟,才把房子腾清。告别的时刻到了。母亲把备好的一只食盘端出来,里面盛着小米和碎馒头渣子,让弟弟放到楼顶上。母亲让我跟她一起去找包队的村干部庆春。在指挥部前,母亲对庆春说,大侄子,我今天把房子腾清了交给你。我有一件事求你。庆春说,婶子你说。母亲说,你们不要马上拆房子,等两天行不行?庆春问为什么。母亲说,门楼下有一窝燕子,小燕子这几天就出窝了。猫啊狗啊的我能带走,小燕子带不走。你们宽限两天。庆春爽快地答应了。
母亲还不放心,说,这窝燕子通人性,有情有义,在我们家住了十几年。你叔叔没了的第二年就来了。年年秋天走,年年春天回。看着它们,我时常想起你叔叔,好像他没走一样。每年春天,我盼着它们来,它们来了我才安心,过日子才有心劲儿。她顿了顿,挨近庆春说,你听着,害燕子是要瞎眼的。庞堡有个孩子捅了燕窝,就遭了报应,高烧不退,后来俩眼都瞎了。
有人喊庆春开会,他拦住母亲的话头,说,你安心离开好了。我跟铲车司机打声招呼,放到最后拆。
回来的路上,母亲跟我唠叨,我们家还住过一窝燕子,来了两年,走了再没回来。燕子不嫌家穷,跟谁家有缘分才肯来做窝。这一窝燕子,说不定是你爹怕我孤单,托了它们来陪我。
我挽着她的胳膊,没有说话。
庆春没有兑现承诺,母亲转身一走,他就忘了。收旧货的还没有把门窗全拆走,两部铲车就开了过来,张牙舞爪一阵撞戳,房倒屋塌,乌烟瘴气,家院就没有了。
我把母亲接来,让她跟小曼住在西厢房。弟弟他们一家去了他岳母家。
母亲每年总要在我家住些日子。她闲不住,忙这忙那,里里外外拾掇得井井有条。这次却打不起精神,没有干活的心绪和热情,不是闷在屋里,就是呆坐在院里,话明显少了,仿佛有满腹心事。
闷闷地过了一周,母亲想回家看看。结局我早就听说了,却没敢告诉她,心想瞞得越久越好。我说,小妹要来看你,等过了这两天,我们一块回去。
还得多长时间?她有些急切。我说不会太长,周日就可以。孩子不上课,她就能来。
那天吃过早饭,母亲梳理齐整,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像走亲戚似的激动。妹妹开着电动三轮车,拉着我们回家。
村庄拆得比我想象的更彻底。除了一家诊所孤零零立在废墟上,再也看不到一座整栋房屋。没有全推倒的,有的揭了屋顶,有的剩下半堵墙。打坏的水缸、丢弃的门板、扯烂的顶衬埋在砖瓦里,对联、年画、书包、作业本、破衣服、烂袜子,凌乱遗弃在空地上。
街道没有了,平地隆起三四米高的建筑垃圾。我们搀着母亲在瓦砾堆中走,跌跌绊绊来到老家旧址前。房屋打倒了。门楼像挨过刀削,一多半没有了,残留着狰狞的砖茬子。街门被拦腰截断,剩下向上敞着的半截门道。照壁上的“喜鹊登梅”还在。要不是这幅永远如新的壁画,还有侄子侄女们用粉笔写下的“再见,老家”“难忘快乐生活”的字样,我们很难认出那就是老屋了。
十几个外地人掂着乙炔气罐,挪来挪去切割钢筋。
我们架着母亲,躲开钢筋断茬,从瓦砾上下来,站在残缺的街门前。踏入门道,看到一只燕子,缩着身子,孤零零立在东墙的一截钢筋上。两只爪子紧握钢筋,像被焊住一样。我们屏息凝视,莫名感动。它看着我们,似乎有所期待。母亲喃喃自语,是它……它回来了……
燕子第一次来我们家,在门道里飞进飞出,两天后才衔泥垒窝,安顿下来。它们要飞到郊外,从枯瘦的环城河边衔泥,半个时辰飞一个来回。母亲看着,不时念叨,多不容易啊。一天下来,垒不了一指宽。湿乎乎的泥巴几天才干透。她注意到干泥巴有好几种颜色,更加动情,它们不是从一个地方衔泥来的,难为它们了。
……
看见燕子,母亲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面色发青。小燕子呢,怎么没有小燕子?
我小声说,长大了,都飞走了。
飞了也该回来,燕妈妈不是回来了吗?庆春这个坏小子骗了我。
立在钢筋上的燕子不动也不飞。它唧唧叫着,像嘟哝,又像试探。母亲嘴里发出“唧唧——唧唧——”的回应。燕子越发叫得急切。母亲面露欣慰。她伸出手,向前移步,想接近它。燕子晃动小脑袋。他们挨近了。母亲呼唤着,想让它飞到手臂上。小燕子开始不安,扭动身子,最后凄厉地长鸣一声飞走了。母亲张着嘴,半天合不上,望着燕子愈飞愈远,直到消失,泪水流了下来。
我说该走了。她退回来,在门口蹲下,翻动砖块,翻着翻着停下来。在砖石下面,我看到一只毛葺葺的雏燕的尸体,下面还有一些暗淡的羽毛。母亲缩回手,不住哆嗦着,沙哑着嗓子,庆春,你个王八羔子,到底骗了我……四条命啊!伤天害理啊,迟早要遭报应。
离开废墟,来到平地上,母亲突然问我,你说村里有多少燕子没了家?我不能回答。她说,我能去你家,燕子能去谁家?
回到我家,母亲默然无语。我扶她坐在床边。她怔着出神。妹妹兑好温水给她擦脸、洗脚。我帮她脱下外套、鞋袜,扶她躺下。
母亲躺了三天,吃饭没了胃口。第四天早上,她强打精神下了床。我给她做了鸡蛋挂面,看她吃下,有了些精神,才赶去织袜厂上班。
一天中午,我下班回来,大门敞着,却不见母亲。她刚康复,难道去洗衣服了?我赶到河边,远远见她坐在上游,背向我,身边没有洗衣盆,也没有衣服。她低头在水边吃力地挖着什么。
走近了,看她坐在地上,上衣挨着地面,湿了水,留下一片暗渍。我不知道她出门多久了,身下坐出一个水坑。她抓着一截筷子粗细的铁棍,翻动河泥,手掌和胳膊上沾满泥污。
我在她身后蹲下,听到她嘴里发出奇怪的声音,后来知道是模仿燕子的呢喃,唧唧、唧唧,欢快喜悦。她一边叫,一边搓弄泥巴,放进嘴里,咂巴咂巴又吐出来。她的举止,像个懵懂无知的孩子,却十分专注,丝毫没有察觉到我来到了身后。我脑子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身上一阵发冷,她的精神是不是……我感到害怕。
我不敢往下想,心跳加快,唤她又怕惊吓了她,慢慢后退,离开一段距离再喊她。我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把手搭上她的肩头。她回过头来,没有说话,眼中流露茫然复杂的神情。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我说,衣服都弄脏了。这是干什么?
你看不出来?她的声音很大,在河道里发出嗡嗡的回音。我给燕子准备泥巴。
我不耐烦了,你准备了,它就会来衔呀?沤出病来怎么办,还嫌我忙得不够啊!
我抓起她的手摁进水里,洗净,帮她清理指甲缝里的泥沙。她的指甲划破我的手背,直到流血我才发觉。我很久没有注意过她的双手了。它们在水里泡得肿胀发白。指甲该剪了,看了让人难受。食指和中指的指甲显得更长,锐利回弯,颜色发灰。
我從后面把她架起来。她双腿已经僵硬,马上伸展不开,无法站立。她嘴里发出哎哟哟的呻吟。停了两分钟,我拉着她慢慢走回去。
我坐在母亲身边,心疼地摩挲她的双手。短短半个来月,她变得憔悴、苍老。手背皮肤松薄,呈透明状,掌骨嶙峋,血管暴突。食指和中指的指甲收缩下弯,甲质增厚,内缩成槽,前端变得锐利。我让小曼把剪刀递上来。听说要剪指甲,母亲面露愠色,急忙收拢十指,攥拳,掖进两腿间。
我让她下楼吃饭,她摇摇头拒绝了。我问怎么了,她不回答。我劝得口干舌燥,她依然无动于衷,无奈,我心情郁闷地下了阁楼。
我煮了鸡蛋挂面,盛进一只大碗,给她端上去。
我把碗捧到她面前。她愣怔一会儿,才接过筷子。指甲妨碍了手指动作。她抄起挂面,因为夹得不紧滑落了几次,好不容易夹住一撮送到嘴边,没等吞进口里,又滑落下来。
我拿起筷子喂她。她吃得不快,半个钟头吃完了,我心里稍稍感到舒解。
晚上,我让小曼爸爸上去背母亲下来,同样遭到母亲的拒绝。她拿定主意要待在上面。我心里着急,想强迫她下来,又怕违拗了她,弄出别的事来。转念一想,总有一天,她会主动要求的。好在阁楼上通风、干爽,住些日子不会有什么妨碍。我只好带上笤帚、抹布什么的,上去仔细打扫一遍,铺上帆布、褥子、衬单,放上枕头,备了一条毛巾被和一条薄被子。入夜,陪她睡在上面。
母亲不愿意下楼,也不愿意见人,听到响动,或者有人进院来,就条件反射般地警觉起来。为了安静,也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插死了过道大门,把预留的进出拖拉机的备用门临时当了正门。小曼爸爸在过道里铺上厚厚的谷草,谷草上放了棕垫,棕垫上加了三条棉被,万一发生不测,不至于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母亲在阁楼上一心一意安顿下来,无论坐卧,她总是在墙角,在最里面,连一次到阁楼口的时候都没有。她害怕到阁楼口来,倒是让我放下心来。
母亲喜欢面条、挂面一类的食物,我差不多天天做给她。她不想活动了,手臂的动作变得笨拙,指关节也变得僵硬。她对我产生了依赖感。我喂她她才肯吃。我顾不上喂她,她就下手抓。我纠正了她几次,但毫无效果,动作变得越来越奇怪。她先把食指伸进碗里,好像在试探温度,然后再伸出中指,两根指头像钩子一样回弯,把面条钩起来,再把拇指凑上去,捏住送进嘴里。她歪着头,不是吸溜,而是用牙咬,还不时摇头,吞下一两根,看我一眼。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母亲渐渐失去了对饮食的兴趣,饭量骤减下来。我以为是憋闷和不活动所致,再次动了让她下楼的念头。她死活不肯。饭量减了,人却能睡。睡到晨昏相接,吃饭时都唤不醒。我觉得她在发烧,请了村医和乡医来看。我帮她解开衣裤。他们给她量了体温,看了舌苔,听了心肺,按了肝腹部,没发现什么特别症状,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决定把她送到医院去。她非常反感,一口回绝,说什么也不去。她说她没有病,只是有些胸闷、心烦、不想吃饭而已。我们从几十里外的铁矿请了一位有名的兼通中西医的大夫。他登上阁楼为母亲诊治,半天也没诊出什么病来,最后,他从中医角度给出结论,认为长期情志不舒,不思饮食,导致精神上出了问题,建议继续观察一段时日。
一个周日,妹妹、弟弟,还有弟媳们相约赶过来。我们先后上了阁楼。弟弟坐在母亲身后,像靠背一样让她倚在怀里。我们围在四周。她似乎更怕光了,不愿意睁眼。我们要求了很长时间,她才不情愿地把眼睁开。借着透进来的光线,我们注意到她的眼角膜有时发红,有时发蓝,显得五彩斑斓,有时又像蒙上一层磨砂玻璃。她的视力真的有了问题。她已经看不清我们了,顺着声音寻找辨认着。妹妹捋起她的衣袖,她的皮肤失去了水分,变得粗糙,毛囊发硬鼓起,呈暗红色,似乎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她脸上的皮肤发红发虚,似乎长出一层细密柔软的东西。我们谁都没有多说话。妹妹扭过头,小声地哭起来。
晚上,我给母亲换洗衣服,发现枕上落下一些头发,像丝网般密密麻麻,错综层叠,不是一绺一绺掉落,而是一根根叠加在一起。
我为她梳理,它们经不得一点触碰,像落叶一样纷纷掉落,我手上不觉握了一把。母亲全然不觉,没有一点痛苦。她的头发更显稀疏。
几天下来,她的头发掉光了,头皮光滑、松弛,娇嫩得像新生婴儿。后来,眉毛也开始脱落。其他部位的毛发相继掉光了。这是怎么回事?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她是被诅咒了,还是冒犯了什么?她这是要离开我们,还是要返老还童?人们说的返老还童,就是这样的征兆吗?这个念头马上又被我否定。我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母亲脸庞干缩,眼窝塌陷,又老又丑,手肘关节、脚踝、腰部、脖颈的皮肤松垂,形成道道褶皱。原本体态偏胖的她,脂肪消失得无影无踪,身体像砂纸一样粗糙,毫无弹性,成了一具松皮包裹的骨架。
她已经相当虚弱,坐起一次气喘一会儿。我不敢往下想,越想越害怕。
我们对母亲的情况守口如瓶,尽量不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乡下,患病,尤其是患上怪病,是一种罪过和耻辱。而母亲的病就有些不正常。我用三层牛皮纸糊严过道的门缝,把通往院子的开口用砖头垒起来,留下仅能容身的通道,装上一扇小门,供给母亲送饭进出。通往大街的两扇铁门打开了马上死死关上。
我上班尽量躲避熟人,有一天跟一位邻居走了个顶头,没法再躲了。她问我母亲恢复得怎样了,应该好起来了吧?我一阵紧张,意识到走漏了风声,表面却装作若无其事,语气平淡地说,她没有病,住在我妹妹家。
邻居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一脸核桃皮,头脑却不迟钝。听了我的话,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我不容她再发问,匆匆离去。她尴尬地“啊啊”两声,迈着一双罗圈腿拐过墙角。
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笃笃声,扭回头,什么也没有。我以为听错了,顺着墙后小路往厂里赶。笃笃声又传过来,这次听得真切。我猛地意识到是从阁楼上传来的,仿佛什么东西敲打窗玻璃,带着恼怒的意味。我停下来倾听,声音消失了。我加快脚步往厂里赶。
母亲的饭量越来越小,不再特别要求吃面条,偶尔吃点挂面显得很费劲,后来只能吃些流食。她对气味很敏感,不喜欢鸡鸭鱼肉,这类汤也如此,却对青菜汤感兴趣,尤其用河水浇灌的青菜,喜欢得什么似的。
后来,我惊异地发现母亲的手臂、小腿、脖颈、脸庞,乃至全身,长出细密的绒毛。那些绒毛嫩黄,一周后变成灰褐色,覆盖了全身。指甲增厚、发乌、坚硬如钢、弯曲如钩。她不让触碰,以免划伤我们。
我们不敢问医生,他们不会告诉你什么,结果只能让母亲的病情是传得沸沸扬扬,自取其辱。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母亲与外界彻底隔绝,尽可能使生活看上去跟平时没有两样。面对某些别有用心的偷觑、鬼鬼祟祟的指戳,我毫不理会,挺胸抬头走在街上。
流言蜚语日甚一日,说母亲变成了妖怪,证据是阁楼上经常传出古怪的叫声。有人说不是变成妖怪,而是变成一只大鸟。至于是什么,众说纷纭,有说是一只苍鹰,有说是一只灰鹊,有说是一只乌鸡。这些猜测被另一种声音所否定,一个成年人,如果变化,只能变成一只鸵鸟。也有比较明智的说法,说人就是人,不过是病了,显得脱相罢了。传言让我们不寒而栗。那天拦下我问话的老妇,时常像幽魂一样从我家院墙外经过,明摆着是要捕捉消息,却装得很随意的样子。我保持沉默,全当什么也没听见、没看见。
母亲的饭量突然间增加了,体温略微升高。我们在焦灼中默默祈祷,希望她身上的怪状消失,能像过去那样坐在门口,走在大街上,到河里洗衣服……
我们期待那个时刻的到来。
一个下午,我坐在机器旁,心神不宁,头天发生在河边的情景,始终萦绕在脑海。
夕阳西沉,天气闷热,河道上的天空出现柔和的橘红。几十只燕子低飞剪水。河面一如既往地平静。后来,一群燕子从南面飞来,它们掠过水面,发出嘈杂的鸣叫。过了一会儿,又有一群燕子跟着飞来,与先期飞来的混成一体,好像原本认识似的,快乐地翻飞起舞。很快,像是参加集会似的,燕群从四面八方相继飞临,阵容十分壮观。人们看到了以前不曾见过的品种,有的体小如蝉,有的身大如鹊,有的一身黑灰,有的五彩相间。它们俨然像是接受了某种指令,交替在河面飞翔,像乌云、草垛和波涛。有的飞临我家,在阁楼上空盘旋、鸣叫。它们落在河边,河边像铺上一张黑毯;落在电线上,电线像缠了一圈黑色保温棉;落在屋顶上,屋顶像落下一层黑雪。
人们纷纷跑出来,看着河面上发生的一切,发出阵阵尖叫。我们关紧大门,躲在院里,感到某种不祥正在逼近。
母亲在阁楼上兴奋不安,嚷嚷着要坐起来。我跪在她身后,扶她坐好。她的面庞沐浴在最后一抹夕阳里,显得喜气洋洋,呼吸变得顺畅。她喃喃自语,我听不清她在咕哝什么,后来意识到她有话要对我讲时,把耳朵贴近她嘴唇,她说,你爹……做了王……,他要来……接我啦……。……你们……做儿女的……要迎一迎……我听了浑身发冷,头皮发麻。
……
正神思恍惚着,门卫走进车间,喊我接电话。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小跑着来到接待室,拿起听筒,妹妹已经泣不成声,她说,姐姐,你快回来,咱娘出事了!
我眼前一黑,差点栽倒在窗前。门卫一把扶住了我。他问怎么了。我不能回答,停了一会儿才说,家里有点事……泪水随即滚了下来。
母亲的遗体已经抬到正屋床上,身上罩着两层绣花锦被,四边严严实实压在身下。妹妹做得好,不想让外人看到母亲临终的情状。我扑在被单上,号啕大哭。
我们没有按风俗办理母亲的后事。当天夜里,我们姐弟三人,弟妹和女婿们,以及至近的亲戚,将母亲遗体入殓,连夜送往村南墓地。
复三那天,烧纸回来,妹妹讲起母亲去世那天中午的噩梦。
她撂下碗筷,一阵睡意袭来,顿觉四肢酥软,顾不上收拾就躺到了床上。刚闭上眼,飘忽来到我家门前,远远听见阁楼上传出扣击声,抬头见一只巨喙猛啄窗户,力量越来越大,节奏越来越快,终于啄碎了玻璃。一只毛乎乎的脑袋伸出窗外。怔忡之际,鸟的脑袋变成母亲的瘦脸。她嘬着角质化的嘴唇,十分狂躁地寻找什么,然后,张开双臂想贴紧墙面,利指抓挠,伴着唧唧尖叫,发出刺耳的声响,留下道道印痕。砖屑灰块纷纷掉落。她的多半个身躯露出来。妹妹站在原地,不敢贸然挪步。母亲放松了,整个身体失去平衡,一头栽下来。妹妹失声惊叫。突然,母亲拍击双臂,宽大的紫花睡衣鼓起,像翅膀一样展开。妹妹感到冷风扑面,一时目瞪口呆。在气流的托举下,母亲的身体抬升起来。她逸出窗户,踢蹬双腿,发出声声怪叫,奋力向上跃起……随着一声巨响,重重摔了下来……妹妹一声惊叫,呼地从梦中坐起,已经大汗淋漓。
妹妹骑车赶了过来。
她没有看见梦中出现的景象。
……
三年后,母亲去世的阴影渐渐消散。弟弟拿到了回迁房钥匙。一家人高高兴兴搬进21层新居,度过一个难忘的春节。
春天来了。鴿子从窗外飞过。清明节,我们去给母亲上坟。大家默然无语,谁都不愿提起令人心碎的往事。
在楼下,我们碰见了马松奎。他跟弟弟住同一栋楼,不在一个单元。马艳姣当年虽然劝父母签了协议,但还是开罪了文教局领导。第二年秋假结束,借调整名义,让她去支边。马艳姣因祸得福,雇了一位本地退休的老师代课,每月只需出800元,拿着剩下的一多半工资,躲在娘家生了二胎。
我们还远远看到了庆春。庆春拆迁有功,受到区政府表彰。当天晚上,一次大酒,他突发了脑溢血,出溜到了桌下。幸亏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落下口歪眼斜、不能说话、见熟人只会咧嘴傻哭的毛病。村里让开发商特意调了一楼的住房给他。天气好时,他老婆推着他在楼下转悠。
吃过午饭,我们在中厅说话,小曼去了阳台。窗外有燕子飞过。她悄悄退回来。我们听到卧室传出异样的响声。弟弟意识到燕子撞了玻璃,进去把窗帘拉上。
整个春夏,他回避着阳台,弟妹和孩子们甚至不愿靠近窗户。
隔三岔五,不断有燕子撞上南窗,石块一样坠到楼下。
责任编辑 梁智强
桑 麻:本名王治中,生于1963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邯郸市作协副主席。已出版散文集《在沉默中守望》《归路茫茫》《心是苍青的岛屿》《回归大地的种子》《以右臂的代价》《邯郸道》六部,多人合集《原生态散文13家》。多篇作品入选中国散文排行榜、华语散文年度排行榜、《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散文卷》,收入50多个选本。曾获第3届冰心散文奖、河北省第12届文艺振兴奖、第15届中国人口文化奖一等奖、第1届浩然文学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