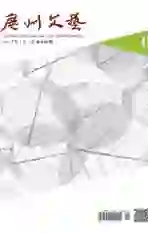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短篇小说)
2017-03-21曹多勇
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为什么他非要跑那么老远去钓鱼?
——雷蒙德·卡佛《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
一
大河湾村四周是水。
村子前面有一条宽宽的淮河,村子后面有一条窄窄的洼地沟。洼地沟与淮河平行,呈东西走向,雨水大的季节水多,雨水小的季节水少,干旱天断水干涸。村前、村东、村西有一溜坝塘,一口连接一口,方方正正,水水亮亮。雨水大,雨水小,坝塘里都有水。涨水天,坝塘与淮河通连,汪洋恣肆,直抵庄台跟,风吹浪打,半夜睡床上,能感受到整个床、整个房屋、整个庄台、整个世界跟着一起晃动。好像整个床、整个房屋、整个庄台、整个世界一起漂摇在水面上。
哗啦啦——是风吹浪打的声音。咯啪啪——是整个世界摇晃的声音。
大河湾村有这么丰富的水资源,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却很少吃着鱼。家人不是不想吃鱼,是没有鱼吃。缺少鱼吃的原因,是别人家有渔网,我们家没渔网。别人家有渔网,经常地下河下塘下沟逮一逮鱼,家里自然而然地就有鱼吃。我们家没有渔网,想吃鱼就得赶集买。赶集买要花钱,父母亲口袋里缺少钱,家里自然而然地一年就吃不上两回鱼。我们姐弟四人,像父母亲喂养的四只小馋猫,闻见别人家的鱼腥味,流着口水回到家,“喵呜喵呜”地向母亲要鱼吃。母亲口袋空,不能赶集,不能买鱼,就数落我父亲。说你望望谁家男人不想办法结一副网,逮一逮鱼,捕一捕虾,回家烧一烧给老婆孩子吃。说你望望四个孩子缺吃的少喝的,一个比一个干巴瘦,个头哪里还能长起来?那是人民公社年代,农民种庄稼没干劲,土地长粮食没劲头,村人一年吃不上半年饱饭。稀汤寡水的日子,吃鱼只是我们家人的一种虚幻盼头。
父亲会结网会逮鱼,就是不愿结网不愿逮鱼。父亲十几岁就和四叔两人一块下河打鱼了。赶上冬天,不用下地干农活,父亲和四叔腾出手,从村子前面下河,吃住在一条小船上,一路逆水打鱼,至正阳关收网回头,前后两个月,一边在淮河里打鱼,一边上岸赶集卖鱼,算是家里的一项重要副业。父亲说那个时候淮河里有鱼,现在淮河里没鱼;那个时候一网打下去,打好了,能打二三十斤鱼,现在呢不说二三十斤鱼了,能打二三两鱼就算不错了。
按理说,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淮河水没有受到污染,坝塘水没有受到污染,洼地沟水没有受到污染,要说这么一大片水域里没有鱼或鱼少,没人会相信。现实情况就这样,没有鱼就是没有鱼,鱼少就是鱼少。鱼少或没有鱼,村里人依旧去逮鱼。洼地沟经常断流,没法养活鱼,他们就去坝塘里逮鱼、或去淮河里逮鱼。淮河水面大,水流急,不能轻易下网。正常下淮河打鱼,要使用一种大网,叫箍网。箍网大,扯开有上百米那么长。箍网的一端沉下河里,另一端留在船上。船上人使劲地撑篙,使劲地摇棹,箍网扯拉开在淮河里形成一个很大的包围圈,围拢住河水里的大鱼小鱼,而后再慢慢地收网,再慢慢地收鱼。早年间父亲和四叔下淮河打鱼,使用的就是这种箍网。现在淮河里鱼少,箍网使不上,村里人家就断绝了箍网。一般人家逮鱼使用的都是拉网。淮河涨水,拉网下不到河里。淮河落水,用细密的拉网在淮河边上拉一网,拉两网,顶多只能拉几条小猫鱼和几只小河虾。太小的猫鱼,太小的河虾,拉网人不去弯腰捡,混杂在泥块中间,扔在原地不动。我们几个孩子走过去,伸手捡起小虾塞嘴里,咸乎乎的很好吃。太小的猫鱼,没有孩子捡拾吃,留那里腐烂发臭招苍蝇。
大部分人家拉网逮鱼,都是在坝塘里。不是涨水天,坝塘自成一体,坝塘与坝塘之间有坝埂子隔断。坝塘里不长虾子,拉网的网眼相对要稀一些大一些。从坝塘这一边下网,沿着岸边使劲地拉呀拉呀拉,拉至坝塘另一边起网。网网不空,有杂草,有村人扔进去的破烂家什、碎砖烂瓦,几只癞蛤蟆少不掉,几条活蹦乱跳的小鱼少不掉,就是缺少像模像样的鱼,连一只螃蟹、一条泥鳅都没有。
父亲不愿结网不愿逮鱼,却喜欢总结事理。他问我母亲,你可知道大河里为什么没有大鱼?大河就是淮河,村人都这么叫。母亲手上忙着家务活,不愿听他说白话。父亲自问自答说,我来跟你说是怎么一回事,上游拦着一个王家坝,下游建着一个蚌埠闸,大河看上去是活水,其实是死水,一河死水怎么能长出大鱼呢?父亲说过大河说坝塘。他问我母亲,你可知道坝塘里为什么连小鱼都没有?母亲停下手上的家务活说,你说大河里拦上坝子没有鱼,坝塘四周都是坝埂子不是更没有鱼?父亲说我母亲,你说的对,也不对,你想一想呀,屁大一口坝塘,今天你去拉上几网,明天他去拉上几网,怎么会有小鱼长出来?
几十年过去,我坐下来仔细地回想一番,觉得父亲说的有道理。套用眼下的话来说,淮河里没有大鱼是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坝塘里没有小鱼是过度捕捞造成的。
二
父亲不愿结网,不愿逮鱼,空闲时间干什么呢?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父亲整天忙得很,好像就没有空闲的时候。除去吃饭回一回家,除去睡觉回一回家,整天身上背着一杆破旧的日本三八大盖步枪,在村子里晃悠来晃悠去、晃悠去晃悠来。那个时候,大队有基干民兵营,建制是一个营三个排。父亲是排长,领着手下十几个人,忙得屁股没有时间粘板凳。庄稼没长熟,父亲要派民兵去各个生产队的庄稼地里巡逻看青。庄稼长成熟,父亲要派民兵去各个生产队的麦场上巡逻看粮。闲冬天,生产队该没有什么要派民兵巡逻看护的吧?相反地,闲冬天更忙。忙什么?召开各种批斗会。今天揪一帮“地主富农”分子斗一斗,明天揪一帮“反坏右”分子斗一斗。这些人统称:地、富、反、坏、右。地,是地主;富,是富農;反,是反革命;坏,是坏分子;右,是右派。哪一场批斗会都少不了民兵出头露面。民兵要去捆绑“地富反坏右”;民兵要去维持批斗会场秩序;民兵要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呼口号;批斗会散后,民兵还要押解“地富反坏右”去游街。全大队十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挨着一个生产队去游街。一场大雪过后,寒风刺骨,路面冰滑,基干民兵一个个无所畏惧,“地富反坏右”一个个瑟瑟发抖,一群看热闹的孩子跟前跟后不停地奔跑着,一个个气喘吁吁,一个个满头大汗。
父亲背着一杆破旧的日本三八大盖步枪,枪管磨得发亮,枪托磨得发毛,枪身上的一根帆布带子断掉后,父亲紧紧地打一个死结疙瘩。我喜欢悄悄地靠近父亲,伸手摸一摸这个死结疙瘩。不要轻看这么一杆破旧的日本三八大盖步枪,在我的眼里,背上这杆破旧步枪的父亲与不背这杆破旧步枪的父亲,不像是同一个父亲。父亲背上这么一杆破枪,他就是民兵排长,带着十几个民兵,就能按照大队干部的指示,去“地富反坏右”家里捆绑上他们,而后拉进批斗会场召开批斗会。就算你是一名普通的生产队社员,要是有了偷鸡摸狗的嫌疑,我父亲背着枪带着民兵,照样去捆绑你,照样召开你的批斗会。一群孩子就更加害怕父亲身上的这杆破枪了,要是一个孩子在庄稼地里手脚不干净,偷一只瓜,扒一埯白芋什么的,父亲撵过去把枪从身上摘下来,平端着瞄准过去,就算枪里没有一发子弹,这个孩子都会吓得跑不动路,甚至两腿发抖尿裤子。一句话,父亲背上这么一杆破枪,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股威慑的力量。威慑村里的“地富反坏右”,威慑爱占小便宜的生产队社员,威慑偷鸡摸狗的村孩子。
有时候,父亲会把枪背回家。回家吃饭,父亲背着枪。回家睡觉,父亲背着枪。这么一杆破枪,在父亲的眼里很金贵。吃饭时,父亲把枪靠在锅台边。睡觉时,父亲把枪靠在床头上。大有人在枪在的意思,大有枪比人重要的样子。父亲这样重视枪,母亲有看法。母亲有看法不直接讲出来,三拐两拐又拐到逮鱼上面。母亲说,你整天背着一杆枪,不如去结网,结网逮鱼老婆孩子跟着打牙祭解馋,你说现在老婆孩子能沾你什么光?父亲批评母亲说,你说这种话是思想觉悟低,拖我工作后腿。我母亲说,好好好,我思想觉悟低,我拖你工作后腿,你思想觉悟高不要回家吃我烧的饭,我不拖你工作后腿,你不要回来家跟我睡一个被窝。我母亲这么一说话,父亲就低头不语了。要是他回家吃饭,就赶紧地吃饭,吃饱饭抹拉抹拉嘴,背上枪就走。要是他回家睡觉,就赶紧地钻进被窝里,生怕迟一步,我母亲赶他走。
三
这一次,父亲有了新的工作任务,真的吃饭不回家,真的睡觉不回家。干什么呢?看管大队里的养猪场。
大队养猪场是新办的。在村子东边的一片空地上,新盖的一大溜养猪场,新买的一大窝猪,不是小猪秧子,一头比一头大,十来头老母猪。听说养这么些老母猪,专门生小猪,改良全大队家家户户的养猪品种。老母猪是长白猪,身子长,体型壮,一看就能生大猪秧子。村里人家过去喂养的都是土猪,要么是花猪,要么是黑猪,一头一头圆鼓楞楞的,怎么看都长不大。长白猪是新品种,要求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开来,每个大队都要建这样一个养猪场。养猪场里有养猪的猪圈,有住人的房屋,有一个大院子,安装一扇大铁门。门两边的院墙及门垛子上,有石灰水刷上的标语口号。院墙的一边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另一边是:“农业学大寨,科学养猪最关键!”门垛子上是:“养猪重地,闲人免进。”院墙上的字横写,门垛子上的字竖写。这样一来,养猪场就算大门敞开不上锁,有专门民兵持枪把守着,一般人都进不去。我父亲领着民兵就是专门做这项工作。吃住在养猪场,日夜把守在养猪场。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破坏科学养猪,就是破坏农业学大寨。
村人说,老母猪比大队干部金贵,大队院子不用民兵把守,养猪场用民兵把守。大队干部没有专人伺候,老母猪有专人伺候。
有专人把守,算是老母猪的警卫员。有专人喂养,算是老母猪的饲养员。此外还从各个生产队抽调十几名女社员专门负责拔猪草。老母猪吃猪草是辅助,吃饲料是主要。听说饲料里含有村人不知道的科学配料,所以叫科学养猪。科学养猪,还要放养猪,还要给猪听广播。放养猪,是去村东的一溜河滩地上,那里地场大,老母猪去那里吃草、拱土、玩耍。十来头老母猪去哪里,饲养员跟着去哪里,几个持枪的民兵跟着去哪里。老母猪赶回猪圈里,饲养员打开一台收音机,选择有样板戏的电台播放开。猪们放养半天累了,听一听样板戏,鼻子里哼一哼就躺下睡着了。放养猪不是我们大队独有,给猪听广播是我们大队独有。全县召开养猪经验交流大会,大队干部脸上很荣光地领回一面大红色锦旗。
我很少去养猪场那里玩。养猪场就是养猪场,长白猪就是长白猪,就算科学养猪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就算我父亲日夜把守在那里,我也没觉得有什么荣光的。老母猪在猪圈里睡觉,我父亲坐在大门边把守,蔫头耷脑的一副模样,像是自己就是一头圈养的猪。老母猪赶在河滩地上放养,我父亲背枪跟在老母猪屁股后面,无精打采的一副模样,像是干着世界上最无聊的一件事。河滩地空旷,除去十来头老母猪,除去放猪的饲养员,四周一览无余,麻雀都不见飞几只,哪里见得到阶级敌人的影子。同样背一杆破旧的日本三八大盖步枪,养猪场的我父亲跟庄稼地的我父亲不像是同一个人。
父亲真的不回家吃饭睡觉,母亲却生意见。母亲手上端着碗,嘴里吃着饭,停一停,愣一愣,跟我说,你大(爸)不知道在那里天天吃什么饭,吃猪饲料吗?猪吃猪饲料叫科学养猪,人吃猪饲料难道叫科学养人?想一想,又说,那就叫科学养着你大(爸)吧。吃过饭临睡觉,母亲铺床,铺一铺,叹出一口气,跟我说,你大(爸)在那里总不会跟老母猪睡在一块吧。想一想,又说,要是真跟老母猪睡一块,赶明睡出一窝小猪秧子,是人还是猪?什么叫睡出一窝小猪秧子,母亲说话我听不懂。
隔一天,母亲烧好饭,自己不吃,也不让我们孩子吃,自己收拾一个布包,布包里塞上两件我父亲的换洗衣服,说要去养猪场找我父亲。母亲说,就算一个大男人家,就算眼下天不热,也不能好多天不洗澡、不换衣服吧。我们家住村子中间,去一趟村东头养猪场得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后,我母亲回到家,我父亲跟着一起回来。一个布包依舊在我母亲手里提着,依旧包裹着我父亲的两件换洗衣服。父亲要吃饭,母亲不让他端碗。父亲要睡觉,母亲不让他钻被窝?母亲烧上一大锅热水,要父亲先洗澡换衣服。我母亲说,你闻闻你身上的一股子猪臊味,怎么进门,怎么吃饭,怎么钻被窝?母亲说这话一点生气的样子都没有,相反一副喜气洋洋,只有过年过节遇见喜事才有过。这一次,父亲没有说母亲思想落后,没有说母亲拖他工作后腿,乐呵呵地依顺我母亲,乐呵呵地洗澡,乐呵呵地吃饭,乐呵呵地钻进我母亲的被窝里。
父亲说,再过半个月,第一头老母猪过窝(生产)下崽,我们就不去值班了。
大河湾从村东至村西,一地秋庄稼眼见要成熟要收割。再怎么说,看护秋庄稼都要比看护养猪场重要。
偏偏问题就出在第一头老母猪过窝下崽上面。这头老母猪明明配上种有四个月了,一副大肚子越长越大,明明大白天外出衔草铺窝,有了要过窝下崽的迹象,不想半夜里“哗啦”尿出一大泡热气腾腾的臊尿,肚子瘪下去,一个猪崽子没有生下來。说好的,公社要在养猪场召开现场会,组织各个大队的干部和饲养员来参观学习。五彩旗子插好,标语口号贴好,锣鼓班子备好。只等老母猪生下猪崽子,只等天亮太阳出,先去公社报喜讯,再敲锣打鼓地迎接参加现场会的代表。老母猪“哗啦”一泡尿,冲刷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剩下来。
绝对是政治事件。
半夜三更,饲养员被控制起来,几个值班民兵被控制起来。我父亲理所当然地被控制在其中。连夜控制,连夜审讯。老母猪肚子里的猪崽子哪里去了?显然是阶级敌人实施破坏活动造成的。谁是搞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显然饲养员和把守民兵嫌疑最大。查过来查过去,一连查了三个白天加上三个黑夜,依旧查不出破坏科学养猪的阶级敌人是哪一个。饲养员和民兵是从全大队范围内精挑细选出来的,都是政治思想过硬的贫下中农。阶级敌人不是饲养员、不是值班民兵会是谁呢?老母猪案件变成一个谜。
第四天,我父亲回到家,不再是民兵排长,不再背一杆破旧的日本三八大盖步枪。我父亲依旧受到怀疑,依旧受到控制,不能乱说乱动。我父亲上工干活,受到生产队社员监管,有乱说乱动的嫌疑,生产队长有责任汇报到大队去。我父亲下工待在家里,受到我母亲监管,有乱说乱动的嫌疑,我母亲有责任向生产队长汇报。我父亲上工不能乱说乱动,在生产队该干什么活干什么活,回家不能乱说乱动,把家里的几把镰刀磨一遍再磨一遍,就把家里的几把锄头擦一擦锈斑再擦一擦锈斑。我父亲抽烟,买不起纸烟,抽烟叶子。一捆烟叶子揉碎放在一只篾匾里,端在眼前,卷一根抽掉再卷一根。我父亲抽烟蹲在门外的墙根上,一边抽烟一边抬头望天。他一副迷茫困惑的眼神,看不透天,更看不透自己的命运。这是他人生的低谷期,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他的一双眼睛只能看到那头不下崽的老母猪,却看不到那个喂养老母猪的荒谬时代。
后来,其他大队养猪场也发生类似情况。一头老母猪眼看着肚子大起来,“哗啦”尿一泡尿,肚子瘪下去。看来跟阶级敌人搞破坏没了关系,看来跟饲养员和值班民兵没了关系,看来跟我父亲没了关系。看来只跟科学养猪有关系,科学解释不了,依旧是一个谜。
父亲不再受到控制,回生产队做一名普通社员,恢复不了基干民兵,更恢复不了民兵排长。父亲曾经受到过怀疑,曾经受到过控制,就像一个生病住院的病人,不是说病好出院了,就跟从前没有生病一个样。
四
这一天,父亲跟生产队长请两天假,说出门去办一件事。办一件什么事?父亲没跟生产队长说,生产队长想问一问,张一张嘴没有问出口。生产队长知道我父亲受到冤枉,生一肚子怨气,他没有必要去招惹。问题是,父亲出门去办一件什么事,也不跟我母亲说一声。母亲不是生产队长,想把话问清楚,就张嘴问出来。父亲说,我现是一个清白的人,不再受到监管,想干什么事没有必要向任何人汇报。母亲生气了,说我父亲,你今天把话说清楚,这些天我在家监管你什么了,我向生产队长汇报你什么了,你在养猪场沾染上一身臊气,不要往我身上赖。
一个人的地位发生改变,一个人的眼光就跟着发生改变。那些天,我父亲出门进门都眯着一双眼睛,不看村里大人的眼神,不看村里孩子的眼神。大人露出来的是一副怀疑和监视的目光。孩子露出来的是一副怀疑和监视的目光。父亲过去背着一杆破旧的日本三八大盖步枪,走到哪里一副腰杆都挺得笔溜直,瞅到哪里一双眼睛都睁得开开的。只有他去怀疑别人,只有他去监视别人,哪里会想到地位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那些天,他成了村人的对立面,家人的对立面,自己的对立面。一度连他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破坏科学养猪的阶级敌人。
我父亲请两天假,出两天门,只干一件事。他去寿县南一个叫隐贤集的地方买回一大捆火麻。买火麻干什么?想结一副网。一副什么网?拉网。
大河湾村只种一种普通麻,不结实,只能做一般用处。火麻结实,结网就得用火麻。火麻火红色,一捆火麻似一捆凝固的火焰。火焰驱散我父亲心里的阴霾。火焰照亮我父亲迷茫的双眼。我父亲一路上扛着火麻回家,弯勾的一副腰身挺直了,塌眯的一双眼睛睁开了。结一副拉网的网片只需要七八斤火麻,父亲一下子很慷慨地扛回三十来斤火麻。父亲知道我母亲依旧生着他的气,他不方便跟我母亲说话,就跟我说。父亲问我,你可知道我一下子扛回这么多斤火麻干什么?我来跟你说一说,结一副拉网的网片需要七八斤火麻,搓一副拉网的纲绳需要七八斤火麻,搓一副拉网的绳子需要十来斤火麻,你拨拉手指头给我算一算,三十多斤火麻算不算多?
表面上我父亲是跟我说话,实际上是跟我母亲说话。表面上我父亲是跟我说结一副完整的拉网需要好多斤火麻,实际上是向我母亲说结一副完整的拉网需要好多斤火麻。
接下来,我父亲便忙着结网了。前前后后,没白没黑,一忙忙了整整两个月。这些天,我父亲除去上工干活,其余时间待在家里哪里都不去,一心一意结他的拉网。我父亲这么一种生活状态,从外表上来看跟过去受到控制时没有什么两样子,其实差别大得很,不是一般的大,是一个天一个地那么大,真的是天壤之别。现在我父亲一门心思在家里结网,渐渐地回归内心生活,渐渐地摒弃外面世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表面是忙碌的,内心是充实的。有理想,有盼头。那就是,早一天结好网,早一天亲近水,早一天打着鱼。这是一种孤独的生活,需要长时间忍受,需要内心真正地安宁下来。
父亲的内心真的安宁下来了吗?
有一天,父亲跟我说,你知道我背的那杆日本三八大盖步枪是一杆坏枪吗?我说,那是一杆破得不能再破的破枪,谁的眼睛都能看出来。父亲说,破是外表,有的枪比这杆枪还破,照样是一杆好枪,照样能把子弹打出去。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父亲说,我来跟你说,这杆枪,破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枪栓拉不开,就算有子弹也压不进去,就算把子弹硬压进去也打不出来。父亲说,其实这杆枪连一根烧火棍都不如。
父亲说这话,是唾弃过去背枪的日子,还是留恋过去背枪的日子?
又一次,我父亲说,我来跟你说一说早年间打鱼的一些事。我父亲说,淮河里有两种鱼稀罕,一种是黄剑鱼,一种是白鳝鱼。黄剑鱼身子黄亮亮的,嘴巴尖溜溜的,确实像是一把出水的利剑。黄剑鱼是一种会飞的鱼。冬天下雾天,雾气大,雾气浓,远处看不清河岸,近处看不清收网,要是网里打着这么一条黄剑鱼,快要露出水面之际,黄剑鱼就会“噌”的一下從网里蹿出来,闪着一道黄亮亮的光芒,在河面上飞起来,借助雾气飞远,像一支飞远的神剑。下网打鱼很难打上来黄剑鱼,天下雾飞走,天不下雾,它会挣脱网逃走。黄剑鱼劲头大,就算一条二斤重的,打出水面来,一个人都很难按得住。
我父亲说,白鳝鱼像一条怪异的蛇,绿脊梁,白肚皮,喜欢吃死人的肉。有人溺水身亡,尸体沉在水里一时半会打捞不上来,就成了白鳝鱼的口粮。有一户打鱼的人家,下水打一网白鳝鱼,连着尸体一块打出水。死人的肚子里装满白鳝鱼,尸体只剩下一副骨架子。这户人家连一副新网都不要了,和鱼、尸体一起丢进河水里。
父亲和四叔下河打鱼,想打黄剑鱼打不着,偶尔打一条两条白鳝鱼,会随手扔进河水里。我父亲说,黄剑鱼金贵,你想吃吃不着;白鳝鱼腌臜,不花钱你都不要吃。
那一年天冷,腊月天冻死河面,父亲和四叔打鱼停下来。翻过年,开过春,父亲和四叔等着开冻天。河面封冻,水下缺氧,大鱼小鱼呼吸不顺畅,开冻时,会浮向水面吸氧,肯定是打鱼的好时机。这一天,天转东南风,一温一暖地吹过来。父亲和四叔闻风而动,早早地破冰渡河,去了淮河那一边。瞅来瞅去,石坝孜渡口至李嘴孜,这么一段是打鱼的好水域。开冻时,冰就是刀,不能在船上打鱼,只能在岸边打鱼,不能逆流打鱼,只能顺流打鱼。父亲和四叔早上过河,船停靠在一处能避开冰流的所在,打鱼的渔网扛上河岸,装鱼的抬筐携上河岸,一直等呀等,一直等等到正晌午,太阳最暖的时辰,冰封的河面都是一动不动,没有开冻的迹象。
四叔问,要是白天不开冻怎么办?
父亲说,等晚上。
四叔问,要是晚上不开冻怎么办?
父亲说,等明天。
四叔问,要是明天不开冻怎么办?
父亲说,等后天。
父亲定下来的决心,不容四叔去动摇。
下午两点钟,一阵“咯咔咔”的响声,从远处沉闷地由弱及强地传过来。紧接着,河岸开始颤动,河面开始颤动,“咯咔咔”“咯咔咔”,冰封的河面闪耀着太阳的光芒,呈现出无数道横七竖八的裂缝。开冻了。真的开冻了。父亲和四叔赶忙扛网拿筐往上游跑。拐过一道湾,他俩看见淮河上游的河面上,在水流的推动下,碎裂的冰块一块叠加一块,像涌起一道凝固的浪头,“咯咔咔”“咯咔咔”,往下游快速地推进。碎裂的冰块叠加起来,推动开来,有一种摧枯拉朽的破坏力量,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好像告诉淮河两岸的所有村人,冰封河面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
等待第一道“凝固的浪头”过去,父亲和四叔就能下网逮鱼了。这一次,使的是拉网。河面开冻逮鱼,只能使拉网。河岸近处,碎冰的缝隙间,大鱼小鱼争先恐后地伸头换气,鲤鱼、鲢鱼、“混子”“咯呀”各种鱼都能分清楚。从李嘴孜下网,再前往石坝孜渡口,父亲和四叔一起拉网,拉上十来丈那么远,网底沉重就拉不动。一网收上来,大鱼小鱼乱扑棱。天气寒冷,大鱼小鱼扑棱几下就扑棱不动了。一网装满一抬筐,差不多有两百多斤重。接着下网,拉十来丈远再收网,依旧一网装满一抬筐。碎冰拥挤着往下游走,父亲和四叔跟着鱼往下游走。抬筐里的鱼就倒在河岸上,就倒在阳光下,淮河那一边的村人看得清清亮亮的。
其他村人晚一步,听见河面开冻的“咯咔咔”声响就晚了。一个碎冰涌动的河面,再坚硬的木船都不敢过,再胆大的村人都不敢过。由于河道弯曲的缘故,由于河流流向的缘故,淮河对岸那一边鱼成群,村子前面这一边不见一条鱼。村人从家里拿出大网小网干瞪眼,就是不敢过河去逮鱼。“咯咔咔”,河面碎冰的声响渐渐地弱下来。“咯咔咔”,村人嘴里咬牙切齿的声响渐渐地响起来。
冰流走远,鱼群走远,父亲和四叔停下打鱼,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起不来身。父亲说,那一天我跟老四真是累得够呛,瞧着河岸边一堆一堆的鱼,心里直发愁,哪里还有力气把这么多的鱼装进船舱里,哪里还有力气把这么沉的木船摆过河对岸。
我问父亲,这是哪一年的事?
父亲想一想说,小鬼子投降那一年。
小鬼子投降是哪一年,那个时候我小不知道。后来我长大查阅地方志得知,日本人侵占淮河那几年,沿岸设立碉堡,禁止村人下河捕鱼。这一年淮河开冻出现这么多鱼,想必跟连续几年禁渔有关吧。
五
简单地说,结好一副网大致分三步。
第一步是捻绳。父亲过去做过这种事,找来一只拨槌子,劈开一根根火麻披,捻出粗细均匀的细麻绳。拨槌子是专门捻线的工具,在一截牛腿骨上钻出一个洞眼,穿上带有倒钩刺的细竹棍就可以了。家里捻线的拨槌子小,生产队捻线的拨槌子大。父亲使用的是大拨槌子,生产队里的。那些天,父亲从生产队下工回家,就像女人似的捻结网的绳子。结网是父亲一个人的事业,母亲想插手插不进,更是不让我们姐弟插手。
第二步是结网。结网,就是结网片。像缝合衣服一样,先结出网片,再缝合成拉网的模样。结网的主要工具叫梭子,竹子刻出来的,六七寸长,一头尖一头平,关键是梭子身上的其他部位要挖空,正中间留下一根针,结网的绳子就是绕在这根针上,梭子穿过来穿过去,结出一个个网眼。结网的另一件工具叫尺子,同样是竹子刻出来的,同样有六七寸长。实际上,梭子穿过来穿过去是把网眼结在尺子上,一口气结出十几二十个网眼,尺子一抽,网眼就能现出来。尺子的宽度决定网眼的大小。结网不能说织网。在我们这里人家的读音里,织、撕不分。结网说成织网,会越织(撕)漏洞越大。渔家听着忌讳。父亲反复交代我们姐弟说,只能说结网,不能说织网。开头说结网别扭不顺嘴,说一说就顺嘴了。
第三步是上猪血。所谓上猪血,就是把结好的网片浸泡在新鲜的猪血里。这样浸泡出来的网片一个方面沥水,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耐磨经用。你想想呀,那么多的猪血渗透进网片里,不是跟家具涂抹上许多遍油漆差不多。不年不节的,猪血难买到。更关键的是,猪血容易凝固。凝固的猪血怎么去浸泡网片。新鲜的猪血哪里有呢?父亲去赶集,集上有食品站,食品站杀猪。食品站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杀猪,父亲带上网片,交给一个杀猪的,交一份猪血钱,还得交一份帮忙钱。村里人家结好网片都是这么上猪血,形成的潜规则,父亲只能照着办。父亲把网片送集上,顺便买回一根拴在网纲部位的竹竿,还有铁匠打出来的网坠。有了这两样配件,可谓一应俱全了。待浸泡猪血的网片晾干晒透,父亲就可着手一样一样去组装拉网了。
集市离村子八里路远。一连两个月,父亲第一次出家门,第一次出村子。这些天,我父亲的心神和眼神都落在结网上,就像一台机器人,每一天吃什么饭,每一天什么时候睡觉,都不往头脑里去。同样地,去下地干活,每一天干什么活,每一天怎样干活,都不往头脑里去。我父亲走在赶集路上,身后是村子,两边是庄稼,他回头看一看村子是陌生的,他转头看一看庄稼是陌生的。好像从来没在村子里生活过,好像从来没下地干过活。这些天,我父亲沿着内心的一条路走得太远了,现在一步一步往回走很困难。结好网片,他要从内心深处一步一步走出来,他要一步一步走向集市,走向食品站,走向铁匠铺,走向竹木行。买竹竿,买网坠,上猪血。
我记得我父亲把一副拉网组装好,就挂在我家的房门前面,一边慢慢地晾晒,一边慢慢地展示。网片是血黑色,网坠是铁黑色,竹竿是青色,网绳是火色。这些色泽的配件组装在一起,就是一副完整的拉网,就是一副随时都能下水逮鱼的拉网。网绳拴在一棵柳树的枝杈上,拉网在风中张开,好像等候着一条条鱼生长出翅膀,从村前村后的水里飞过来。我父亲结好一副拉网,脸上不见丝毫喜悦的颜色,反倒更加地愁眉苦脸。我父亲恢复到受控制时候的状态,闲下来就蹲在墙根下,一根接着一根抽烟叶子。我们家人期待他去拉网逮鱼,他就是闲在家里一动不动。我父亲为什么不去逮鱼?我母亲不去问,让我去问。我父亲说,拉网为什么就要逮鱼呢?这句话回答得连我都一头云雾了。拉网不逮鱼,整天挂树上还能逮鸟吗?这一天,就有一只麻雀愣头愣脑地撞上去,麻雀头插进网眼里,再想出来怎么都出不来。网眼的特点就这样,往上撞,网眼张开,往回退,网眼收拢。麻雀头收拢在网眼里,麻雀的两只翅膀自由着,扑棱一气,哀鸣一气,又扑棱一气,又哀鸣一气。我父亲蹲在墙根下不动弹,两眼紧紧地盯着麻雀,任凭麻雀扑棱,任凭麻雀挣扎。我想把麻雀抓下来玩一玩,但不敢去。我不是怕麻雀,是怕我父亲。我父亲的一副样子像是浑身长满刺,我母亲都不去招惹,我也不敢乱动。麻雀的羽毛一片片脱落,飞舞四散。麻雀不再扑棱,不再哀鸣,渐渐地安静下去,像一条离水死去的鱼。
第二天,我父亲下工回家,从树上把拉网解下来,说是要去逮鱼了。我母亲早早地准备好一只竹篮,悄悄地递给我父亲。我父亲警觉地问,我要竹篮干什么?我母亲说,盛鱼呀!我父亲说,我有网兜。不知什么时候,我父亲结出一个网兜。网兜上拴一根襻绳,往身上一挎,跟我上学背的书包差不多。网兜的网眼比拉网的大,看来父亲逮鱼有想法,只要大鱼,不要小鱼。我要跟着一块去拾鱼。我父亲断然地拒绝,说我小,打鱼的地方到处都是水,打起鱼来顾不上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我八九岁学会凫水,我父亲这样找托词,是不想带我去。我父亲只身一人去逮鱼。我母亲站在家门口,目送我父亲远去的身影,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我不明白我母亲叹个什么气,吸溜吸溜口水问,我们家是红烧鱼煮干(米)饭,还是熬鱼汤贴死面饼?我母亲说,你看你大(爸)那副熊样子能逮得着鱼吗?我不信母亲的预言,在家等父亲打鱼归来。想象中,父亲打了各种各样的鱼。大鱼小鱼,不停地在我眼前穿梭跳跃。好像我眼前的空中到处是水,这些鱼在眼前自由自在地游过来游过去。
我父亲果真空着两手回家,没逮一条大鱼,没逮一条小鱼。我父亲说他是在淮河里打的鱼,不是打鱼的季节,就一条鱼打不着。什么是打鱼的季节呢?俗话说,涨水鱼,落水虾,不涨不落逮“咯呀”。深秋算是落水的季节,只能逮虾,不能逮鱼。父亲结的拉网网眼大,只能拉鱼,不能拉虾。我父亲不灰心,说明天去坝塘里逮鱼。深秋天,水渐凉,鱼沉底。淮河水深,坝塘水浅。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父亲又一连三天空手回家。也就是说,我父亲连着逮了四天鱼,一条大鱼小鱼没逮着。第二天,他说去了村东坝塘。第三天,他说去了村西坝塘。第四天,说他去了北坝子坝塘。北坝子坝塘远,离家有五里路,生产队收工再去时间来不及。父亲专门请上半天假。这一次,父亲去得早,回得早,网是湿的,裤子是湿的,冻得他嘴巴哆嗦着说,鱼网被坝塘里的水草缠住,他要下水去解网。下水解网怎么不脱下裤子呢?有点说不通。
至此,村子四周能打魚的水域,父亲打了一个遍。深秋天,洼地沟干底不见水,自然就不见鱼。村前坝塘离家近,村人千网拉万网拉,都知道拉不着鱼,又都不甘心地还去下网拉一拉。第五天,我父亲会去村前坝塘逮鱼吗?或者说,第五天,我父亲不去村前坝塘逮鱼又会去哪里呢?
六
第五天,我父亲一大早起床,赶在家人起床前,赶在村人起床前。我父亲起床这么早,不像去打鱼,拉网挂在树上晾晒着不去解,而是拐进锅屋里提上一只水桶,走上一条赶集的村路。有比我父亲起床更早的两个村人,一个是早起拾粪的村人,一个是睡错床的大队干部。拾粪的村人追赶一条拉屎的花狗,跑到一片小树林,一抬眼看见我父亲手上提着一只水桶走在前面,觉得很疑惑,就高声地“唉唉”喊两声,问我父亲,一大早你手上提着一只水桶干什么?我父亲说,赶集修水桶。村里人家水桶坏了,要拿棉花塞一塞,等候木匠进村修一修,没有专门赶集去修水桶的,就算去赶集,不一定就能找得到木匠。木匠分三种,打家具的叫直木匠,钉棺材的叫斜木匠,箍水桶、木盆的叫圆木匠。圆木匠少,只有他进村子挨家挨户地找你,你想赶集找找不着。这个大队干部,经常跟老婆说,晚上要在大队部值班,经常一值班就值到别的女人床上,经常要早早地起来更换床。这个大队干部警惕性很高,三步并作两步,撵上我父亲,一把拉住水桶,说我父亲不像赶集修水桶。我父亲问,你说我不是赶集修水桶,那我赶集干什么?大队干部说,养猪场案件大队在继续查,广大革命群众时时刻刻都在监视着你的行踪,我警告你不要胆大妄为轻举妄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好惹的。我父亲站在下风口,大队干部站在上风口。一股一股好闻的雪花膏味道,一抓一挠地扑向我父亲。显然雪花膏的味道来自这个大队干部身上,来自跟大队干部睡觉的女人身上。我父亲吸一吸鼻子问,我今天赶集也要买一瓶雪花膏回来家搽一搽。
过去我父亲是这个大队干部的心腹,现在变成对立面。养猪场案件一旦发生,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再也消散不去。
简单地说,我父亲提水桶赶集是为了买一条鱼,是为了买一条鲜活乱蹦的活鲤鱼。鲤鱼虽然生命力强,要是离开水时间长,照样死。有一只水桶,水桶里有水,鲤鱼浸养在水里,就是一天过去两天过去,照样活。我父亲赶早集,上集下集两个小时。上集只遇见两个村人,下集遇见更多村人。村人一个个都在生产队地里干活。一大早我父亲提水桶上集,两个村人看见生疑惑,张嘴问一问。现在我父亲提水桶下集,村人看见生疑惑,谁都不去问。不是不想问,是不屑问。村子就这么大,村人就这么多,哪一个村人整天干些什么事,村里人人知道。我父亲在家结网两个月,村里人人知道。我父亲连续四天一条鱼没打着,村里人人知道。这个早上,我父亲提着一只水桶去赶集,村里人人知道。村人心想我父亲再怎么怪异,能怪异到天上去,能怪异到地下去?村人心想有无产阶级专政摆在那里,随时可以举起来将你打翻在地,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村人在两边地里干活,我父亲沿着村路走过来,有意晃一晃水桶。鲤鱼在水桶里不安稳,“扑棱扑棱”扑腾出水响和水花。村人“噢”一声全明白,原来我父亲提一只水桶去买鱼,结一副网,逮四天鱼,鱼没逮着,结果只有花钱买鱼吃。村人只是觉得我父亲提一只水桶赶集去买鱼,举动有点太怪异。要是把我父亲这些天的举动联系在一起,就不会觉得我父亲今天早上的举动怪异了。继而村人怀疑我父亲的头脑是不是出了大毛病。一副头脑好好的人,怎么会这样子呢?村人想一想产生一丝怜悯心,村人想一想,还不都是一头老母猪惹的祸。这天早上我母亲在生产队地里干活。我父亲早上的反常举动,我母亲早听村人说了。村人说我父亲的其他闲言碎语,我母亲也一清二楚。村人让我母亲快点回家烧鱼,说看样子是买了一水桶鱼,你们家人吃不掉就喊我们帮着吃。我母亲低头干活不说话,眼泪“啪嗒、啪嗒”一串一串往地上滴。我母亲不担心我父亲提水桶赶集买鱼,担心像村人说的那样他的头脑出了大毛病。
我父亲没有把水桶里的鲤鱼提回家,上庄台下庄台,直接来到家门前的坝塘边。这里有一片芦苇地,我父亲把水桶连着鲤鱼一起隐藏进芦苇里。而后我父亲回家吃早饭,吃罢早饭,候着村子下早工。生产队干活,分早工,上午工,下午工。收早工,吃早饭,再出上午工。村人下早工,我父亲好接着实施他的下一步计划。村人下早工,一群女社员跑在最前面,有一大堆家务活等着她们去做,两条腿想慢慢不了。回家喂孩子,回家喂猪,更主要的是要把昨晚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干净晾晒起来。女人洗衣服的地方就在家门前的坝塘里。有女人回到家,连一个迟钝都没打,就端着一大盆脏衣服下坝塘。我父亲早早地站在坝塘边等着,一同等着的还有扛在肩膀上的一副拉网,还有勾在手指上的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一条鲤鱼窝在水桶里不显得有多大,勾在我父亲的手指上显得个头不算小。鲤鱼浑身金黄色,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一扑棱一扑棱,就有一道一道的金光闪出来。女人停下洗衣服,候我父亲说话。我父亲只有行动,没有言语。只见我父亲使劲地一扬手,鲤鱼滑脱手指,在半空中划一道金色的弧线,结结实实地落在坝塘中心。鲤鱼不怕砸水,愣一愣头脑,摇一摇尾巴,游进坝塘里。而后我父亲不慌不忙地下拉网逮起鱼。
村人看明白,我父亲是自己买鱼,自己放鱼,自己打鱼。
一时三刻,我父亲的举动传遍整个村子,村里大人孩子“哗啦”一声下庄台,围拢住坝塘边,围拢住我父亲。我父亲变成一个另类人,好像我们一家人都跟着变成另类人。村子都这么炸开窝,却没有一个人来我们家说一声。我们家只有我母亲感到奇怪,说我父亲,明明赶集回头,怎么会不见人,不见网,只见锅台边上一只空下来的脏饭碗。
我父亲拉上第一网,收网不见鲤鱼。一条放养在坝塘里的鲤鱼,又不是一条家养的狗,又不是一只家养的鸡,你下网去打,会听你的话。我父亲只打一网,就要收网回家。村人问,鲤鱼不打啦?我父亲说,在坝塘里养着慢慢打。村人说,你不打,我们打。我父亲说,你们想打你们打,你们打着送我家,晌午红烧一块吃。我父亲真的收网回家。村人真的扛网过来打鱼。张三扛一副拉网走过来。李四提一副撒网走过来。王五端一副抄网走过来。不大一会儿,村里各种各样的渔网全部集中在这么一口坝塘里。村人先是拘谨地站在坝塘岸边逮鱼,而后一个跟着一个脱赤脚下到坝塘水边逮鱼,再而后一个跟着一个脱裤子扑进坝塘中心逮鱼。俗话说,鱼头有火。逮鱼的人,在冬天里都不怕冷,况且现在只到了深秋天呢。一口坝塘,岸上,水边,水中心,站满人,布满网,喊声,水声,像是要把坝塘掀翻天。一网接着一网放下去,一网接着一网收上来,就是不见鲤鱼面。水浑了,水浊了,一口坝塘都不像坝塘了,就是不见鲤鱼面。
一条鲜活乱蹦的鲤鱼哪里去了呢?
生产隊长过来催,说赶快去上工,说上工都晚一个小时了,说你们在这里瞎折腾,人家曹振林早下地干活去了。曹振林是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回家里把拉网挂在树枝上晾开,就下地干活去了。
七
结尾一:隔天早上,我母亲烧锅见水缸里没水,找水桶挑水见少了一只水桶。我母亲问我父亲,我家的水桶呢?我父亲想一想说,丢在芦苇地里我忘记拿回家。这两天,我母亲不愿跟我父亲多说话,一个头脑不正常的人,你跟他说些什么呢?挑水下淮河,我母亲肩扛挑水扁担,手提一只水桶,去芦苇地找另一只水桶。水桶在芦苇地里,我母亲走过去,见到半桶水,见到一条活着的鲤鱼。鲤鱼是我父亲赶集买的那一条。明明我父亲伸手扔进坝塘里,怎么会在水桶里?
结尾二:这一年冬天,一场西北风掀掉我家一大片房屋顶。我家房屋顶是麦秸草铺就的,西北风一大,麦秸草一大把一大把往半空飞。我父亲没办法,就想到家里的那副渔网。渔网拿出来,结结实实地网上去,西北风再吹就吹不动麦秸草。
冬去春来,我父亲没有维修房屋顶的打算,一副渔网就网在那里没有动。风吹日晒,渔网渐渐地褪色,渐渐地破旧……
责任编辑 刘志敏
曹多勇:1962年出生于淮河岸边的大河湾村。现为安徽文学院专业作家。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作家》《山花》《钟山》《大家》《天涯》《小说界》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选载。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与人合作)获中宣部第十届(2003—2006)“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好日子》获2003—2004年度安徽文学奖。短篇小说《塌陷区》《这日子应该平静似水》分别荣获第四届、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