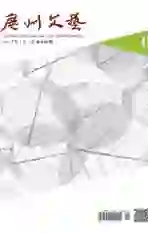谁都别管我(短篇小说)
2017-03-21刘庆邦
潘新年爬到九楼的楼顶,连累带紧张,不免有些气喘。这座办公楼装有电梯,潘新年没敢乘电梯。他的穿着不太好,棉袄皱皱巴巴,有些破旧。他的脸也没洗干净,鼻洼子里和耳朵眼里还有煤灰。而在办公楼里上班的都是公家人,都是干部。干部们都穿得板板正正,头发都梳得油光溜滑。他要是敢进电梯,说不定人家会把他赶出来。爬楼梯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别说九层楼,就是十八层楼,对一个靠干体力活儿吃饭的人来说,也不在话下。爬到楼顶后,稍事停顿,把喘气理顺些,潘新年就走到女儿墙边,手扶女儿墙,探着头往下看。楼下是一个挺大的停车场,停车场里停放着数不清的小汽车。那些小汽车有黑的,有白的,有红的,有蓝的,称得上五颜六色。潘新年听说,现在的干部差不多人人都有小汽车,他们大都是开着私家车上班。干部们拥有小汽车,跟以前拥有自行车一样,已经很普遍,也很普通,不算什么稀罕事。顺着停车场往前看,那是一条横贯矿区东西的马路。马路两侧法国梧桐树的叶子都落光了,缭乱的枝桠暴露无遗。马路上车来车往,人来人往,都是很匆忙的样子。
下井时,潘新年每天都是往低处走,走到地下很深的地方。有生以来,他还从没有上过这么高的地方。他听说中岳嵩山很高,还听说开封的龙庭很高,他都没有去过。人说登高望远,看来站在高处与站在低处所见是不一样的。往远看,他看见了北山的山顶,看见了水泥厂冒烟的烟囱;往近看,他觉得汽车和人比往常要小得多,行驶和行走的速度也慢得多。他平日在马路边走时,见拉煤的大卡车总是不可一世的样子,哇地一下子就开了过去。这会儿站在高处再看,觉得拉煤的卡车并没有那么威风,开得也没有那么快,简直就像是老牛破车。看来距离真是个神奇的东西,一旦把距离拉开,风景会变得大大不同。
春夏秋冬,天上地下,风景总是很多,总是变幻无穷。然而潘新年登上楼顶可不是为了看风景,也无心看什么风景,是为了执行一项计划。他的计划有些悲壮,也有些冒险,对于计划能不能实现,他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他的计划与楼下的地面有关。他低眼往地面看了看,见地面都是用砂石水泥打成的地坪,既平整,又硬邦。倘若他从楼顶跳下去的话,一定会收到可以预见的效果。前不久,潘新年所在矿的一个哥们儿从井口跳了下去。矿井的井筒子当然很深,垂直深度达五六百米。井底的地面也很坚硬,除了石头,还有铁轨。哥们儿的身体和地面接触的一刹那,重力加速度,其惨状可想而知。潘新年对那个哥们儿所选择的赴死地点不是很赞成,摔成什么样是次要的,反正谁死后都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子。问题是,一个人成天下井,难道还没下够吗,非要死在黑咕隆咚的井下干什么呢!
潘新年抬起一只脚,又抬起一只脚,小心翼翼地攀上了女儿墙的墙头。他没有马上站立起来,想蹲在墙头上试一试,看看楼下的人会不会发现他。一个男人从汽车上下来了,打开后备箱,取出两样用硬纸盒包装的礼品样的东西,向大楼门口走去。男人的眼睛平视着,没有仰脸往上看,没有看见他。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年轻女人过来了,女人一边走,一边把手机贴在耳朵上打手机。打手机的女人眼睛里大概只有正和她通话的人,无暇往上看,也不可能发现他。又一个戴着绿袖标的老头儿模样的人走进了停车场。潘新年隐约看见绿袖标上有黑字,但他看不清是什么字。老头儿一手拿着一根长竹片做成的镊子,一手提着安有手把的塑料土簸箕,走走停停,在拣地上的纸片或烟头。看样子,老头儿像是一个在办公楼前打扫卫生的清洁工。老头儿在楼前的广场里转来转去,发现他的可能性会大一些。老头儿只要一伸懒腰,只要一抬头,就会发现蹲在楼顶女儿墙上的他。然而,老头儿很可能是成天低头低惯了,拣垃圾拣惯了,眼里只有地面和垃圾,一眼都不往高处看。潘新年又等了一会儿,又看见好几个人在楼前走过。那些人有进去的,也有出来的;有离得比较远的,也有离得比较近的,但没有一个人往天上瞅。潘新年由此知道了,人作为一种地面动物,在地面吃,在地面住,鼻孔是朝下的,眼皮子也是往下耷拉的。虽然天空比地面宽广得多,也高远得多,可人们很少往天上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猪与狗与牛与羊也差不多,文明不了多少。
为了使目标高大一些,潘新年试着在女儿墙上站立起来。虽说站起来比蹲着高不了多少,他的感觉却大不一样。再往下看,楼的墙壁立陡陡,像悬崖一样。虽说潘新年没有恐高症,往下看他还是有些害怕,有些头晕。高处招风。好在这天风平浪静的,没什么风。要是刮大风的话,说不定能把他从女儿墙上刮下来,那就更可怕了。潘新年不敢站得太靠前,只能把重心后移,站在女墙内侧的边沿。这样万一掉下去的话,他只会掉在楼顶的平台上。平台相当宽阔,恐怕跟楼下的停车场差不多。平台上不能停车,这会儿一个人都没有,他不知道这么大的平台有什么用。
别人不往天上看,潘新年往天上看。没有太阳,天有些阴沉,看样子有一场雪要下。看天也不能老看,他怕看得时间长了,就忘了自己。他只朝天空看了一眼,就赶快把目光收回,将目光落在车流人流川流不息的马路上。腊八已经过了,离小年也不远了,人们的脚步显得匆忙和慌乱起来。年也是一种时间概念,从时间的长短和易逝的意义上讲,年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潘新年不能明白,一说过年,人们为什么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变得如此兴奋。有的人甚至像吃了某种毒药一样,这种毒药可以導致神经错乱,不可自控。一些偷盗、抢劫、杀人等案件,会在年底集中发生。传说年是一种鬼,看来魔鬼的力量的确很强大,很厉害。面对“魔鬼”越来越接近,潘新年不得不承认,他之所以要选择今天这个时间执行自己的重大计划,与过年也是有关系的。
潘新年在女儿墙上站起来后,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果然有人看见他了。一个男人骑着一辆三轮车,车斗子里放着一袋大米,几棵白菜,还有一塑料壶调和油,在马路边由西向东骑。他骑着骑着,停了下来。因为他看见了站在楼顶上的潘新年。骑车的男人大概吃不准站在楼顶上的是不是一个人,他以手遮额,打着眼罩子看了看潘新年。他看清了,站在楼顶上的不是一根旗杆,也不是一根石头柱子,的确是一个有胳膊有腿有头有耳朵的人。然而,他停了一会儿,又骑着车向前走去。他可能是急着回家送年货,没兴趣也没时间关心别的事。一个穿着时髦的女郎,牵着一条大型狗,在人行道上走。四条腿的狗走得快,两条腿的人走得慢,其实等于大型狗在前面牵着女郎走。女郎往后戗着身子,把狗的速度限制一下,才能跟得上狗的步伐。女郎看见潘新年,向潘新年招了一下手。作为回应,潘新年也向女郎招了一下手。女郎也就是招一下手而已,她连半步都没有停留,跟着狗就走了过去。在女郎眼里,也许狗比人要重要得多。又过来一个当妈妈的,领着一个小女孩儿在路边走。当妈妈的身上背着小提琴的琴盒,看样子是带女儿去上小提琴课。是小女孩儿看见了潘新年,她站下来用手指着潘新年对妈妈说:妈妈你看,那上面有一个人。
妈妈也看到了潘新年,说快走,要不就迟到了。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干什么呢,他是要自杀吗?
什么自杀,他可能是在演电影。一个小孩子,不要管那么多!她把小女孩儿拉了一下,硬是把小女孩儿拉走了。
潘新年怎么办?看来他不吭声是不行的,他得喊叫,他得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要让别人听到他的声音。风有自己的声音,雷有自己的声音,公鸡有自己的声音,蚊子也有自己的声音。什么东西不声不响,都很难被别人注意到。于是潘新年运了运气,冲楼下喊了一嗓子。潘新年以前没这样喊过,他的喊带有试验性,好比公鸡打鸣头一声。“公鸡”既然开始打鸣,不妨多打几声,潘新年连着喊了几嗓子。
潘新年的喊叫有了效果,楼下那个惯于低头打扫卫生的老头儿终于仰起了头,看见了潘新年。老头儿大声说:喊什么喊,你是干什么的?你要干什么?
我要跳楼!
你说什么?我耳朵背,听不清,你再说一遍。老头儿把一只手招在耳朵后面,像是通过手掌把耳朵加长。
我要从楼上跳下去。
老头儿这回听清了潘新年的话,他没有感到惊奇,也没有问潘新年为什么要跳楼,就断然拒绝说:你不能在这儿跳,要跳到别处跳去!
废话,我就要在这儿跳!选择在这儿跳楼,可以说是潘新年经过调查研究后的精心选择。周边有杨树,有水塔,有电线杆子,他没有选择到那些东西上面去跳。杨树不够高,水塔他上不去,爬电线杆子呢,他怕碰到电线被电死。出师未捷身先死,那就太不划算了。而这座办公楼是本地最豪华的建筑,也是矿区的制高点。更重要的是,这座楼是煤业集团公司的机关办公大楼,机关的头头脑脑都集中在这里,作为一个挖煤的工人,他不在这里跳楼去哪里跳呢!
老头儿说出的理由是:你要是在这儿跳楼,弄得乱七八糟的,我怎么打扫!
潘新年听出来了,老头儿已对他跳楼的结果有了预想,并预想到摔得破破烂烂的身体会给打扫卫生增加麻烦和负担。这个老东西,真够自私的。他说:我就要在这儿跳。说着,为了表示决心似的,他又大叫了一声。
老头儿对潘新年连连摆手,要潘新年等等,先别急着跳。他跑着到楼里去了。老头儿把楼顶的事情报告给集团公司保卫处,一位副处长从楼里走了出来。副处长问潘新年是哪个单位的?
潘新年见副处长的派头像个领导,说了自己所在的矿。
副处长说:天下矿工是一家嘛,我们都是兄弟嘛,有啥话不能平心静气好好说呢!副处長的态度相当温和,好像和潘新年真的是兄弟一样。副处长接着说:好了,下来吧,到我的办公室去,我给你泡壶热茶,咱们好好聊聊。有什么难处,你只管跟我说,我尽量帮你解决。
潘新年知道,副处长的温和是装出来的,他要是下去,副处长会立即和他翻脸,说不定还会把他控制起来。他才不会上副处长的当呢!他说,如果不答应他的条件,他马上就跳下去。
这样不太好吧。现在是和谐社会,你这样做显然不太和谐,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副处长没问潘新年为什么要跳楼,也没问准备跳楼者所要求的条件是什么,他掏出手机,给矿区派出所的所长打电话,说有一个人在集团公司办公楼的楼顶破坏稳定,要派出所派人帮助处理一下,以免造成不良后果。
听见副处长和潘新年对话,一些干部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马路上的一些行人,也纷纷拐进了楼前的广场。一时间,楼下聚集了几十人。他们都仰脸看着潘新年,目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潘新年身上。即将发生的事刺激着他们神经中比较兴奋的部分,他们的神情无不显得有些兴奋。有的人虽木着脸,装作无所谓,但他眼神儿里跳荡的兴奋是掩饰不住的。日出日落,日子总是很平淡,这里好久没发生让人兴奋的事了。今日有一个人登上了楼顶的女儿墙,或许有一个不错的故事即将上演,值得期待。
在矿区生活的人还知道,集团公司办公大楼的前身,是一处平地起了高台的、大型的露天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挂牌儿批斗过不少人,放映过不少电影,还上演过不少包括革命样板戏在内的戏剧和歌舞。自从舞台被拆除,盖起了办公大楼,人们在这里就看不到什么节目了。当然,办公室也是发生故事的地方,也会有一些小节目。只不过,故事都是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节目也具有一定私密性,人们是看不到的。这下好了,旧的舞台没有了,谁能说楼顶不是更高、更大的舞台呢!“表演者”已经出现在“舞台”上,他双腿并立,目视观众,已做好了预备性动作,节目随时都会开始。谁能说新节目不比以往的节目更强烈、更激动人心呢!
有人颈椎有毛病,不能长时间仰着脸往上看,就回办公室拿出了充气脖套,套在脖子外。拿脖套时,他是跑着进去,跑着出来,像是生怕错过了最精彩的那一幕。有人拿出了俄罗斯军用望远镜,把镜头对准潘新年的脸,在仔细观察一个绝望者的表情变化。还有人大声问潘新年,有什么想不开的?为什么要跳楼?
潘新年的回答是:他在矿上干活儿,快过年了,老板不给我发工资,我没法儿活了。
那人问,老板欠你多少钱?
潘新年的回答让楼下的观众稍稍喧哗了一下,原来潘新年才在矿上下了一个月井,老板欠他的工资总共才两千四百块钱。讨论随即在观众中展开,一个妇女说:为这点儿钱,搭上一条人命,太不值了,人的命也太不值钱了。
一个男人说:人活着不值钱,一死就值钱了。他要是真的跳下来,老板至少得赔给他家四十万块。
一个像是从附近建筑工地跑过来的、手里还拿着泥抹子的年轻人笑了一下说:这倒是一个挣钱的门路,哪天我也跳楼。
天空中飘起了小雪花,雪花薄薄的,片状,轻轻飏飏,落在地上一点儿声息都没有。观众越来越多,楼前已是黑压压一片。迟迟不见潘新年跳下来,性急的人有些等不及了,有人冲潘新年喊:你怎么还不跳,磨磨蹭蹭的干什么,谁有那么多时间在这儿陪你!
有人附和:我看你还是缺乏勇气,还是贪生怕死,要是不怕死,你早就跳了。
有人像是在做潘新年的思想工作,说: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把眼一闭,往前一跨,就下来了,像雪花一样,很轻松的。
还有人提醒潘新年:要跳快点儿跳,等派出所的警察一来,你可能就跳不成了。
潘新年伸出了双手,抬起了一只脚,看样子要跳了。
楼下的人静默下来,都仰起了脸,屏住了呼吸。即将发生的事,使有的人心跳加快,不知不觉间用手捂住了胸口。一个当女儿的抱住了妈妈的一只胳膊,悄悄说:妈,咱们走吧。女儿本来是带妈妈去医院看病,妈妈见这么多人看人跳楼,也拐进来加入观看的队伍。妈妈大概不想错过看人跳楼的机会,说再等会儿,等那个人跳下来咱就走。
然而,潘新年放下了双手,收回了脚,没有马上跳楼。他大概站得有些累了,竟蹲下了身子。
别提人们多失望了。
派出所的所长驾着一辆摩托车过来了,观众为他让开了一条道。观众为所长让道是临时性的,当所长的摩托车在楼下停住,观众复又合拢,把所长围在了中间,并挡住了所长的退路。富有处理突发事件经验的所长,带来了一只电喇叭。只见他不慌不忙地从摩托车上下来,把电喇叭的开关打开,“喂喂”试了试效果,开始与潘新年对话。雪下得比刚才大一些了,雪片子上下翻飞。朝上的喇叭口像是有一些吸力,雪一飘到喇叭口那里,就被吸了进去。见警察来了,潘新年又在女儿墙上站立起来。由于雪片子的密度加大,潘新年的面目看去有一些模糊。所长例行公事似的问了潘新年的姓名、单位、年龄、身份证号码,以及拟跳楼的原因,就把潘新年喊成了潘师傅,说潘师傅,听我口令,向后转,走下来。
潘新年没有听所长的口令,身子没有向后转,他说:你不要管我,我就是要跳楼。
所长说:我告诉你,我的所里可没有氣垫供你跳,你跳下来,只能摔得粉身碎骨。
粉就粉,碎就碎,我不怕,反正我不想活了。
你要跳楼,你老婆知道吗?你要是死了,你老婆有可能会变成别人的老婆,这个后果你想过吗?还有你的孩子,你要是死了,谁关心照顾你的孩子呢?
潘新年的情绪激动起来,说话几乎带着哭腔,说干活儿不给钱,老板不让我活,我有什么办法。你们闪开点儿,我跳呀,我跳呀,我现在就跳。
观众再次兴奋和紧张起来,他们纷纷拿出手机,举过头顶,对着潘新年拍照片,拍视频。他们一边拍,一边以最快的速度把照片和视频发给朋友圈、同学圈、同事圈、亲人圈……圈圈圈。他们的手机像是自媒体,他们的做法像是在进行现场直播。通过直播,潘新年欲跳楼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全国很多地方。受众快速作出回应,有的谴责煤老板为富不仁,没有良心;有的批评社会缺乏公平、正义;有人对潘新年表示同情;还有人愿意为潘新年捐款,祝好人一路平安。这种回应与现场的直播者形成了互动,互动的结果,使直播者颇有成就感,进一步激发了直播的积极性。他们全神贯注,都希望能拍到自由落体的画面。
所长说:潘师傅,不就是两千四百块钱嘛,太小菜一碟了。我来时已经通知了老板,让他马上给你送钱来。天下着雪,你站那么高,受那个罪干什么!我敢给你打保票,要是老板不给你出这个钱,我出,行了吧!我说话算话,这么多人在这儿,大家都可以为你作证。
潘新年没有说话。他仰脸望了望天空,一些雪片子落在了他的脸上。对于是不是听从所长的话,他像是有些犹豫。他的目的是讨钱,既然所长答应了给他钱,他有什么必要继续待在女儿墙上呢!再说在窄窄的女儿墙上站了这么半天,他确实有些累了。
在潘新年犹豫之际,矿上的老板驾着一辆宝马驾到。老板开的是座私营小煤矿,年产量不超过三十万吨。私营小煤矿和国营大型煤炭企业有什么关系呢?关系是有的。有一段时间,说是为了帮助小煤矿搞好安全生产,又说是为了把大型煤炭企业做得更大更强,煤炭产地大刮整合之风,国有煤炭企业纷纷把周边一些小煤矿整合到自己旗下。整合成功后,大矿不但给小矿派去了一些专业技术人员,还给小矿投放了不少钱。其实质有什么改变呢?没什么改变。小煤矿还是私人所有,还是老板负责制,挣的钱还是放进老板的钱柜里。也就是说,国营煤炭企业是为公家挣钱,企业越大,管理人员自己挣到的钱就越少。小煤矿老板是为自己挣钱,煤矿越小,老板挣的钱就越多。钱给人撑腰,也给人自信。煤老板腰一粗,派头就不一样。老板下得车来,说嗬,不错,热闹!他和派出所的所长很相熟的样子,把所长叫成老兄,给老兄道了辛苦。他要过所长手中的电喇叭,说这事儿我来处理。
老板没有对潘新年喊话,他甚至连对潘新年多看一眼都没看,却用电喇叭对观众们说开了话,他说: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下着雪,天怪冷的,大家散了吧!快过年了,大家都有许多事情要做,干吗在这里浪费时间呢!我明确告诉大家,你们是看不到什么的。他上那么高,是逗大家玩儿的。他像个演员一样,希望他的观众越多越好。观众越多,他就越来劲。你们不看他,不给他捧场,他就会泄气,自己就会走下来,不信你们试试。
观众们不太相信老板的话,一个散去的都没有。
潘新年也听见了老板的话,他说:你们不要相信他的话,他就是一个资本家,就是一个吸血鬼。我们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坚决和资本家作斗争。他又对老板说:你不给我发工资,我就是要跳楼,就是要死给你看,让全中国的人都骂你!
老板这才和潘新年对话:你听着,我问过了,你没有跟矿上签劳动合同,我完全可以不承认你是我矿上的工人。我来协助公安机关处理这件事,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潘新年说:不是我不跟矿上签合同,是矿上不跟我签合同。这正是你搞的阴谋诡计,你就是通过这种手段剥削农民工的。矿上规定每个农民工试用期是三个月,你不让人家干够三个月,就借口试用不合格,把人家赶走。你把人家赶走时,一分钱都不给人家,等于让人家给你白白干活。让大家说说,你的心黑不黑?我看你的心比过去地主老财的心都黑!
老板还要与潘新年继续对话,所长制止了他,要他少废话,赶快掏出钱包儿,给楼顶上的人数钱,两千四百块。喂鸡一把米,唤猴一只鸡,把钱数给人家,这事儿就算完了,大家就散了。所长从老板手里要回了他的电喇叭。
老板没有掏钱包儿,说钱算什么,我历来不看重钱的价值。只是那个话呢,我不能给这种人惯下毛病,不能给这种讹诈行为开绿灯。他这种行为跟在马路上玩碰瓷儿是一样的,他这次在这儿玩碰瓷儿得了手,下次换个地方还会玩碰瓷儿。对这种人这种行为的处理办法有两种:一种办法是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把他抓起来;还有一种办法是忽略他,不理他。如果没人看见,没人围观,他会自我泄气,松松拉拉走下来。观众越多,他就越来劲。他目前的状态就是来劲的状态,他来劲就是来给观众看的。所长您信不信,这个人根本不想死,也不敢死,他不会从楼上跳下来的。
所长说:话不要说得这么绝对,万一呢,万一他跳下来,你的损失可就大了。
这时有人冲着楼顶的潘新年喊:老板说你贪生怕死,根本不敢跳楼!
还有人把手機的照相镜头对准了老板,嚓嚓地为老板照相。
老板在自己脸前连连摆手说:我又不是明星,你们拍我干什么!
谁说我不敢跳,我现在就跳!潘新年再次抬起双手,做好了跳楼的预备动作。他的样子像是站在高台上的跳水运动员准备跳水,运动员跳水前都是先抬起手来,伸展双臂。只不过,高台下面是水池,高楼下面可是硬地。
观众的心再次绷紧。
所长的手机在响,他有些着急,对老板说:你掏钱不掏钱,不掏我先替你垫上了,回头再跟你算账!
老兄,您别着急呀!老板这才拉开皮衣的拉链,从皮衣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从里面一五一十地数出了两千四百块。
所长用电喇叭对潘新年喊:好了,下来取钱吧!
计划眼看就要实现,潘新年没有理由继续待在女儿墙上。他蹲下来,往后转身,屁股贴着墙沿,慢慢出溜到楼顶上。
雪越下越大。楼下的人不见了楼顶的人,纷纷开始退场。他们的样子像是有些泄气,还像是有些生气。有人说假招子,有人说瞎耽误工夫,还有人骂骂咧咧,不知在骂谁。
坚持不走的人还是有的,他们是想看看潘新年最终能不能拿到钱。
老板把一沓钱递给潘新年,说你胜利了,把钱数数吧。
在人们的注视下,潘新年把钱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到手的钱不是两千四,只有两千。他看着老板说:还差四百。
老板说:你再上去表演一遍,我把剩下的四百给你。
潘新年没有听从老板的要求,他狠狠瞪了老板一眼,跺脚震了震鞋子上的落雪,走了。
责任编辑 梁智强
刘庆邦:著名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省沈丘县。 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