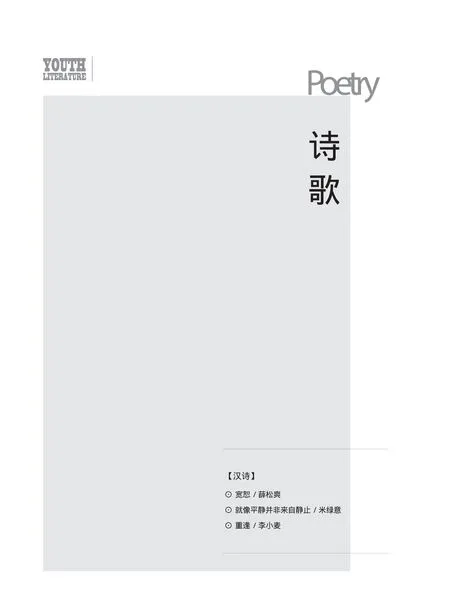异作家系列(二)小的大作家
——美国当代超短篇小说家莉迪亚·戴维斯
2017-03-20⊙文/瓦当
⊙ 文 / 瓦 当
异作家系列(二)小的大作家——美国当代超短篇小说家莉迪亚·戴维斯
⊙ 文 / 瓦 当
瓦 当:一九七五年出生于山东利津,著有长篇小说《漫漫无声》《到世界上去》《在人世的悲伤》《焦虑》《河与流》,中短篇小说集《去小姨家》《多情犯》《北京果脯》等作品多部。现居烟台。

有经验的读者一定不难看出,来自美国的布克国际奖得主莉迪亚·戴维斯更像是一位欧洲小说家。如果美国文学指的是马克·吐温、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或者是戴维斯的前夫畅销小说家保罗·奥斯特的话,确切地说,戴维斯更像一位德语小说家,比如卡夫卡,比如耶利内克、赫塔·米勒,智性的、反故事的、高密度的。她的很多“黑童话”似的短制则酷似安吉拉·卡特,冷峻的戏剧化叙事又使人想到贝克特、哈罗德·品特。此外,她有时像卡尔维诺,有时像科塔萨尔……这是一个转益多师、风格驳杂的作家,像她笔下的人物瓦西里,只需要把性别改换一下就可以是“一个有许多部分的男(女)人,个性多变,心思不定,有时野心勃勃,有时昏昏沉沉,有时热爱沉思,有时缺乏耐心”。但是,她完全不同于美国的雷蒙德·卡佛,对于她能否像出版者所期待的那样像卡佛在中国流行起来,笔者心中没有概念。她比卡佛显然更为小众,也更适合装文艺,她会被广泛谈论,但可能很难被广泛接受。据吴永熹女士在《几乎没有记忆》的译后记中“揭秘”,戴维斯真正的先驱是拉塞尔·爱德森——一位“独特却偏僻的小诗人”。“独特”“偏僻”“小”这三个限定词真是太好了,完全适用于莉迪亚·戴维斯。作家中有大的小作家,有小的大作家,莉迪亚·戴维斯无疑属于后者。
在某种意义上,小说和女人的裙子一样,越短越性感,越短越让人不安。戴维斯充分展示了短篇小说这种危险的魅力。她的小说通常只有一两千字,甚至只有一句话。干净,爽利,如一道道明亮的疤痕。在她面前,“极简主义”大师雷蒙德·卡佛都显得无比繁复。戴维斯的短是格言而非警句,不提供鸡汤似的治愈,只是为了将你割伤。比如:“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已经死了好几年的人。对她来说,刷他的外套、擦拭他的砚台、抚拭他的象牙梳子都还不足够;她需要把房子建在他的坟墓上,一夜又一夜和他一起坐在那潮湿的地窖里面。(《爱》)”不是充满诗意,而是直接是诗,是一个谜语扰动另一个谜语形成的谜语的涟漪——“当我们的女人全部变成雪松时,她们会围在墓园的一角,在大风里哀吟……终于,在那些雪松树心底深处的某个地方,我们的妻子被扰动了,想起了我们。(《雪松树》)”再比如:“蜂鸟在将死的白色花丛中制造爆炸——不止白花在死去,到处都有老女人从书上掉下来……带着她们得了癌症般的脸躺在橡树下。(《烟》)”而“我们镇上的一个男人既是一条狗又是它的主人(《我们镇上的一个男人》)”,那个“妹夫”“如此安静,如此瘦小,就好像根本不存在。是谁的妹夫他们不知道……他不流血,不哭泣,不流汗。他是干燥的。他的尿液离开他的阴茎时甚至都好像先于离开他的身体就进入马桶,就像一发离开手枪的子弹……(《妹夫》)”“在一个有十二个女人的镇上还有第十三个女人。没有人承认她住在哪儿,没有寄给她的信……雨不会落在她身上,太阳从不照在他身上。天不为她破晓,黑夜不为她来临。对于她来说,一个个星期并不逝去,年月也并不向前滚动。(《第十三个女人》)”
看不懂没关系,因为艺术作品价值的高低跟是否看得懂,甚至是否可解都没关系。艺术以追求魅力为宗旨,而不是为了追求意义。或者说魅力是艺术最大的意义,无魅力则无意义。在戴维斯的笔下,小说的可读性虽然被降低,但文本的张力和内在的压强大大增加,魅力的灵光由此闪现,像闪电拓展了天空的领地。
戴维斯在小说中驱逐了故事,她像一个女巫将读者从对故事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转而囚禁于她所发明的语言的咒语。有意思的是,她唯一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就叫《故事的终结》。故事终结,小说开始。因为“一旦故事中的东西变少了,那么处于中心的东西就一定会更多。(《故事的中心》)”在戴维斯的世界里,不但故事的空气稀薄,而且听不到人物的对话,总体沉浸于一种回忆、冥思的状态。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她曾翻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她似乎是以与普鲁斯特背道而驰的方式,以曲折的节制抵达和抚摸时间的长度。
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概念,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戴维斯的写作提供些许启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这里我强调的重点是“对一个行动的模仿”,写出可见的行动,就意味着意义的呈现,戴维斯的写作策略一定程度上如同罗伯·格里耶所做过的。然而,“艺术家妄自谨小慎微,作品却暴露了所有秘密(歌德语)”,像伍德·詹姆斯指出的那样,戴维斯的小说还是不可避免地“带有扭曲的自传色彩”。一个离异的女人,教授,翻译者;一些婚姻生活的遗迹,一只袜子,一个电话,一封信,疼痛与失眠,甚至“她在翻译上下了很多苦功夫,只是为了阻挡那痛苦。(《信》)”,与伍迪·艾伦的《安妮·霍尔》《午夜巴黎》等电影类似,戴维斯以她带有元小说性质的系列短篇构筑起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活图景,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息。除了撷取自身的经历和记忆,铃木镇一、古尔德、W.H.奥登、福柯等人物也都在她笔下做着不同的穿越旅行。
莉迪亚·戴维斯单薄明快的叙述下,隐藏着荒凉而深邃的绝望:“如果你带着一种无法继续生活的绝望,但与此同时你能对自己说你的绝望或许不是很重要,那么要么你会停止绝望,要么你会继续绝望但与此同时你会发现,同样的,你的绝望也可能被移置一旁,只是许多事物中的一件。(《我的感受》)”这让人不能不想到卡夫卡的那句名言:“不要绝望,也不要因为不绝望而绝望。”她笔下面目模糊的猎人,也让人联想起卡夫卡笔下延宕于原罪与天堂之间的猎人格拉胡斯。她和卡夫卡一样,关注的是一种更为本质的精神生活,而非日常生活,这造就了一种戏剧化的间离效果和荒诞怪异的喜剧性。如《瓦西里的生活速写》:“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猎人,而他只是一个胖知识分子。”“在他坐在太阳底下剪圣诞树上用的纸星星时,与此同时,其他男人正努力工作供养一家人,或是在外国代表自己的国家。当他在艰难的寻求事实的过程中发现这种不一致时,他感到安放在他身上的自己很恶心,就好像他是他自己不受欢迎的客人。”而“伯道夫先生抵达高潮时,海伦的血黏在他身上。他迷惑地感觉到,在海伦的血,海伦本人以及十九世纪之间有着某种深刻的关联(《伯道夫先生的德国之旅》)”。
尽管莉迪亚·戴维斯的文本展现了相当独特而自足的经验,但笔者还是禁不住要提出一点苛责。总体上看,她作品的原创性并不够突出,更称不上是一个源泉性的作家(如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也缺乏建构一个伟大的小说世界所需要的足够的时空纵深。她的很多单篇都是一些半成品,一些诗歌草稿,而非完成的诗。但是,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从戴维斯这里,我看到了小说集作为一种新文体的诞生。而这个问题的探讨,首先涉及媒介形式对内容的影响,涉及中西不同的文学生态。中国的主流文坛,是由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构建而成的,而美国和欧洲很少有文学刊物,作家的出道多是以书(作品集)的方式。为文学期刊投稿写作,与创作一本书(作品集)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被选择的相对松散的呈现,后者则意味着更强烈的主体性和更紧密的内在关联性,通常也需要更长时间的孕育。笔者姑且给“小说集”这种新文体下一个定义:小说集是介于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之间的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它是指短篇叙事文本按照一定道理的集合,其内部各短篇之间既相互独立,又以互文的方式相互影响和支持,从而构成一个整体的集群。戴维斯的小说集可以看作是对这个定义的最好阐释,整体的大气有效地弥补了单篇作品的纤弱,而单篇作品的生动丰富了整体的意蕴。不但是“1+1>2”,而且处于整体中每个1都大于个体的1。英文版的《莉迪亚·戴维斯小说集》长达七百多页,从呈现形式上来看,这是一部足够厚重的文本,这既影响了内容,也影响了对其文学价值的判断。莉迪·戴维斯集腋成裘、继而化蛹成蝶的文学之路,表明了一种不经意间的深思熟虑。
按照柏格森的理论,旋律并不是当一段演奏完成后才生成,而是在演奏者按下第一个音符时即已产生。或许未来的小说家在写作之前,首先就应有一个意识,明确自己要写一本小说集,还是写一篇一篇的小说。说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一个写作者最好精通编辑和出版,以便对将来自己作品集的成品样式有一个概念,这会对作家的创作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莉迪亚·戴维斯所推崇的贝克特所说:“不在意一个文本说了什么,只要它是被漂亮地建构起来的。”而这个建构不仅表现在单篇作品内部,也包含着一本书(小说集)作为整体的一个文本的建构。我个人认为,这或许是莉迪亚·戴维斯之于后来的写作者最大的启发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