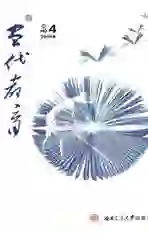两位老师
2017-03-18高怀昌
高怀昌
有两位老师我记忆颇深,至今难忘。
一位是夏老师。
他是一位初中毕业教初中的老师。那时很多老师被打成黑帮,赶下了讲台,师资力量很弱,各门课程都缺老师。夏老师因根正苗红,初中毕业就教了初中。但是根正不等于知识,苗红也当不了水平。夏老师有时会被讲解不了或者讲不伸展的数学题,为难得无法将一堂课讲完。要说这不是误人子弟吗?其实在那个某些人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候,不会也就不会了,我们自个儿认识不到啥是误人子弟,我们那些斗大字不识半升的父母,更不知道误人子弟是个张三李四,所以不会也就不会了,不讲也就不讲了,少会点儿、少讲点儿,谁也不会说啥。可是,夏老师不行。夏老师就会把他不会的题隔过去,而后连夜骑着自行车到几十里以外的村子里,去向他的老师求教,第二天再来讲给我们。
当然,这些都是听说的,夏老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所以每当夏老师隔过一题不讲时,我们就会猜想,他又要往返几十里路,去请教他的老师了,而且第二天,还会看到他那双因无眠而充满血丝的眼睛。后来,他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毕业以后仍然回到家乡,仍然教初中,成了一名非常优秀的中学教师。
自从与夏老师分别后,每当想起他独自奔波于漆黑之中,想起他为了给我们讲好课而熬得血红的眼睛,就会被他那种“求知不怕夜色重,教书不叫一疑存”的精神而深深地感动。
另一位是高老师。
据说他是一位读过私塾的老师,也是一位教书水平很高、人缘很好的老师。这也是他成分高、出身不好、读过私塾,还能一直站在讲台上继续教书的原因。他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那时候,时而要停课闹革命,时而要复课闹革命,在停停复复、复复停停的反复之中,我们虽然读到初中了,成了初中生了,但还是一些野性难驯、肚里头没几滴墨水的混小子,一有撒野的机会,就会忘乎所以,将野性暴露无遗。那时的电影常演的是杨子荣击毙座山雕、郭建光击毙胡传魁之类的内容,我们就叠些纸帽子、纸手枪,模仿杨子荣、郭建光、座山雕、胡传魁啥的,窜到庄稼地里打土坷垃仗,直打得浑身泥土,方才罢战。
记得在一堂体育课后,我们借着跳高跳远在操场上赛跑的余兴,放学后拿着纸手枪冲进了校园外边的小麦地。结果可想而知,一大片麦地不一会儿就被我们糟蹋得一塌糊涂了,直到那个生产队的队长怒冲冲地揪着耳朵,把我们从麦垅中提溜出来,我们才感到了大祸临头,一扫冲杀时的英雄气概,被灰溜溜地揪到了高老师面前。
“高老师,你看那麦子,那可是正在打苞抽穗的呀!看我不把他们家大人叫来,把他们挨个儿揍一顿!”队长用手指头点住我们的头,氣咻咻地说。
高老师弄清原由之后,像《地道战》里的伪保长遇到鬼子一样,连连点头哈腰陪笑脸、陪不是,承认错误作检讨道:“队长,您消消气,千万别告给家长。您想想,他们的家长知道了,手轻手重的,打出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呀!都是我管教不严,管教不严……我这就去给您拾掇拾掇,要是拾掇得不好,我拿工资赔您。您消消气,千万消消气。”说罢,走进麦地,把我们踩倒的麦苗一丛一丛地扶起来,那些踩劈了的,还用草绑在旁边直立的麦棵上。
在那个日落月出的黄昏,我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愧疚和可耻,都感到确实是做错了。于是,大家都哭了。哭着跟高老师一起把我们踩倒的麦子一丛一丛地扶起……